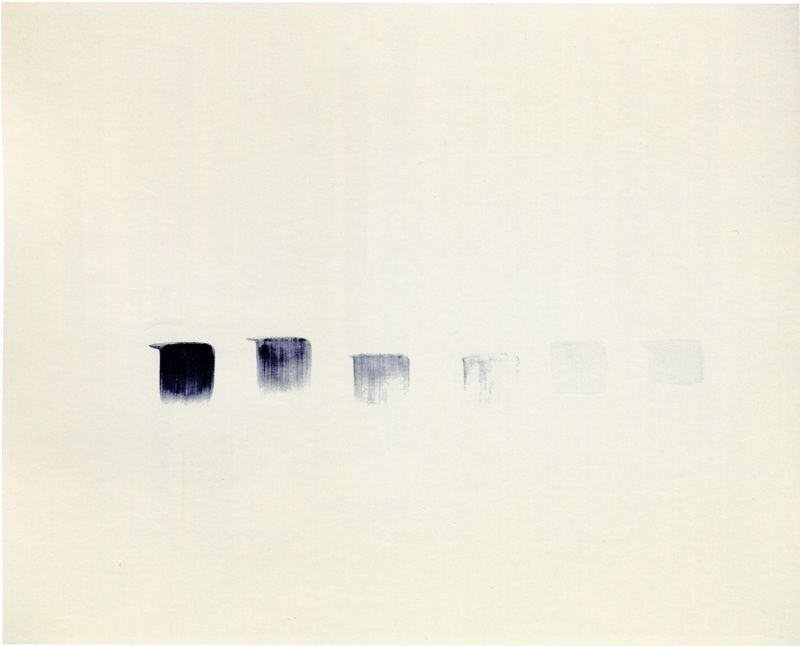「種藝‧眾議:關於評論──評論不是什麼」專題座談紀錄
專題座談:「種藝‧眾議:關於評論──評論不是什麼?」
時間:2016.04.03 14:00
地點:老爺行旅降霖廳
主持:吳思鋒(《劇場.閱讀》編輯、柳春春劇社團長)
與談:
陳泰松(中原大學商設系兼任助理教授)
龔卓軍(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副教授)
郭亮廷(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兼任講師、自由撰稿人及譯者)
記錄:羅倩
周雅菁(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副局長):臺南藝術節是臺南每年重要的活動,我們希望在提供好的節目、環境之外,也能提供更好的評論平臺,有更多交流的機會,在表演藝術和視覺藝術中,評論都是非常重要的,藝術家和評論者都可以一起來學習、成長。今年特別邀請紀慧玲和吳思鋒兩位老師共同來策劃「藝評專區」,邀請八位「駐節評論人」和十五位「新評種」成員,今天謝謝老師、講者們犧牲連假假期,希望大家都能收穫滿滿。
吳思鋒(以下簡稱「吳」):今年臺南藝術節誠如副局長所說,多了評論相關的活動,看戲寫評的隊伍也已經在路上了,臺南藝術節也邀請了幾位駐節藝評人,今年的專題座談有四場,今天第一場討論「評論」。我介紹一下與談的三位老師,第一位是郭亮廷,他的評論文體創造出一種說故事的語境,同時又能掌握戲劇本體與戲劇作品所投射出來的廣泛的社會、文化面向。陳泰松老師是一個很清晰的論述者,總是可以很快的點出展演、觀看的盲點,以多層次且細膩的視角去觀看展演作品。龔卓軍老師的超連結實在太厲害了,擁有不眠不休的強大文字書寫能量,老師的評論很像一種迷宮式的筆記。接下來請老師們分享,再開放聽眾問答。
郭亮廷(以下簡稱「郭」):謝謝思鋒。我大概沒有辦法直接的定義「評論是什麼?」這麼龐大的工作,臺灣的評論發展有它自己特殊的歷史脈絡,我自己常常在想的是「評論變成了什麼?」剛剛談到評論的專業化這件事,評論當然不是謾罵,也不是歌功頌德,評論應該是立基於某種專業。但專業化就能解決問題嗎?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專業化」代表分工、生產線的概念,在藝術的生產鏈上,你負責評論,那你就只要做好評論的工作,是一種分工的概念,我覺得評論的專業化是會產生問題的,因為工作的關係,我常和許多現在被稱為評論人、藝評人、劇評人,如王聖閎、簡子傑等和我同輩的評論人交換意見。基本上看起來臺灣的藝術評論(劇評)是個榮景,在「評論」這件事情上,有非常多新生代年輕劇評人投入。我們這一輩的人把心力投入在藝評書寫上,那是否有會產生某一部份的空缺,比如說相對於中國大陸,我覺得我們被壓抑的東西就是我們一直缺乏「有歷史深度的聲音」,評論的第一手的資料一直沒有辦法連貫成歷史敘事,我們的歷史感、歷史意識沒有被建立起來,這個「歷史區域」是被荒廢掉的一個區域。從80年代小劇場到現在已經過了20年了,關於戲劇的意識、評論的意識到底產生了哪些變化?有哪些命題還可以延續?哪些已經消失?不然我們會一直處於在沒有歷史感的評論觀點裡面。
我想問一個問題,為什麼現在在網路媒體,如台新的ARTALKS和表演藝術評論台不斷有評論出現?我覺得這些大量的評論書寫基本上和國家的補助機制有很大的關係,大部分的藝術創作都是在國家的補助下進行,補助最後需要結案報告,一定需要評論,至少我知道我寫的評論,藝術家一定會看,成為第一個讀者。寫評論這件事如果是歷史的第一手資料的話,這個歷史是補助機制、獎勵機制作為歷史的書寫者,補助機制所獎勵的藝術家將來會成為藝術史的一部分,藝術家或作品達到某種程度上的藝術成就,我其實是透過補助的方式作為歷史的書寫者。除此之外,若沒有其他的書寫方式的話,我們的觀點就會受限於補助機制,我想的是如何開發出有別於補助路線的書寫歷史。
80年代小劇場運動時期的鍾明德、王墨林、紀慧玲、紀蔚然和我們這一輩的評論人是非常不一樣的。前者大部分是學者劇評,現在則是專業劇評,前者不斷持續書寫的只有王墨林一個人不是學者身分,王墨林寫評論不是喜歡劇場或是為了劇場,而是因為劇場在戒嚴環境下,「因為透過劇場來審判戒嚴在我們身體上的殘餘」(王墨林語),他關心劇場是和身體(精神)的解放有關。現在的劇場則變成是一種為了劇場本身而寫的劇場,一種唯美主義者的方式,甚至沒有進入藝術家為何要創作作品這件事來深入討論。
陳泰松(以下簡稱「陳」):謝謝思鋒剛剛的介紹,好像三個人都有各自的形象,一個是講故事、一個是寫筆記,一個是看漏洞的(笑)。我是從視覺藝術評論起家的,三年前我因為台新藝術獎開始投入劇評寫作。這個學習的過程也可以看出「寫論文」和「寫評論」的差異,是一個邊寫邊學習的過程,讓別人知道你如何看事情?關於「評論是什麼?」或是「評論不是什麼?」這個議題,是和視野的提出有關,除了技術或形式主義,從報導式、記者式、學者式的書寫都可以,從來沒有一個專業養成的科系是「評論」科系,身份始終妾身未明。
龔卓軍(以下簡稱「龔」):有,臺南藝術大學有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研究所。
陳:對,但評論還是處在一個附屬「藝術史」的狀態,單純的關於「評論」科系未來應該也是不會有。藝評的專業身分是一流動、跨越的狀態,過去藝評和很多藝術領域都有相關,如和文學、哲學、藝術史與考古學相關。在全球化下的今日,無論是劇評或是視覺藝術評論都會遇到挑戰,因為美學規範或是藝術史都是從西方主導的敘事模式,在今天在台灣我們要如何去建構當下的書寫意識?大家可以思考「歷史意識和藝術評論的關係?」評論從來不是天真無辜的,單純的書寫狀態是比較少的,評論可能和雜誌有關、或是有人邀請你書寫,背後是有一個「話語權利」的操作。
所以今天可以提出什麼樣的視野、見解和觀點呢?其實不太容易回答,不只是提出對於作品的批評而已。我認為需要有一種「個人視野」存在,以此來對抗大他者與集體的制約。評論者的社群在台灣多少是儒家手勢、相敬如賓的狀態,我認為激起一種評論的爭議,才是評論的深化。在臺灣,藝評很多是評論者跟創作者之間的對話,反而評論者和評論者之間的交流關係比較缺乏,缺少了評論者彼此之間的對話。我認為我們應該關注評論者間的交流與對話,關切跟你一樣從事書寫的評論者;他們有何觀點和意見,並引用或參與其他評論者的話語,形成彼此的對話。
龔:我想第一個要談的是從郭亮廷這邊討論的關於「形變」的問題,這似乎是一個基本的問題,如早期的王墨林和陳傳興,究竟是新聞記者還是評論者?對我來說都不是。王墨林是小劇場的導演,陳傳興現在在目宿媒體做「他們在島嶼寫作」文學電影系列,這算不算一種評論?這是我要問各位的第一個問題,究竟什麼是評論?什麼不是評論?陳傳興其實最早是一個創作者,去年三月也在北京中央美術學院辦了個人的攝影展「未有燭而後至」。他並不認為他是攝影家,他自己也是【他們在島嶼寫作】中兩部電影《如霧起時》和《化城再來人》的導演以及整個組織策劃的文化生產者。各位可以想一想,黃海鳴早期到現在也作評論,後來是學校老師也當了臺北市立美術館館長。石瑞仁早期是非常鋒利的評論者,現在是當代藝術館館長。高千惠是在策展和評論之間發展她的特有身份。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比如說李維菁她是小說家還是評論者?或者反過來推得更遠,比如說陳界仁是藝術家還是評論者?高重黎是評論者還是藝術家?
在這個部分會有一個評論不斷「變形」的問題,特別是在臺灣,也就是說,所謂的專業評論,就整個市場、整個學院、報業、雜誌業,這樣一個體制的規格、究竟容不容許純粹的評論存在?以這點來說評論的發展,像剛才提到的專業的劇評要求,會不會是一種幻象?究竟能持續多久?這些年輕的藝評者,像簡子傑本來也策展,現在也進了高師大教書。如何維持純粹的評論者或是研究者的位置?我自己也可以做策展。回溯當代的評論史來看,好像有這樣一個問題存在,比如說剛過世不久的倪再沁老師,也是很重要的評論者,他和陳傳興在臺灣評論史上的重要的爭議事件(關於西方美術、臺灣製造與現代性修辭匱乏的議題),從今天的觀點來看他們,究竟算不算專業的評論者?專業的評論者究竟意味著什麼?這是我想提出的一個點。
我覺得,評論是一個很奇怪的動盪位置,它究竟是新聞還是是學術研究?還是是個中間的混合狀態,文章登到《藝術家》、《今藝術》,就算是評論了嗎?或者進一步說,如果評論為了指向作品,那評論本身是否應該消失?它的存在任務是否就是讓自己消失、不要存在。如果說我們不要過度介入、過度詮釋,評論如海德格曾經評論荷爾德林的詩所說的,戶外的一座鐘,詩就是鐘,評論是一片雪,從天上飄下來,飄到鐘上就融化了,評論是馬上要融化掉的東西,這是海德格的觀點。意思就是說,評論寫得越好,越有超越性,評論應該就更沒有獨立存在的理由,評論是為了鐘而存在,而不是為了自己存在,因此,若要回答評論是新聞還是學術研究,不如說評論處於一個「曖昧」的位置。這是我今天想要討論的。
像是王墨林、李維菁、倪再沁和陳傳興,某種程度都將評論者的身分進行轉化,先不討論外部因素,他們內在究竟做了什麼選擇?就像我之前問黃建宏的問題,究竟內部做了什麼選擇,使得評論的位置不再那麼純粹了,評論者必須要去做另外的事情,去做館長、做策展、做影像生產等等。反過來說,為什麼藝術家在某個階段後如高重黎、陳界仁開始做一些其實滿像評論的事情?高重黎對攝影史和影像史、陳界仁對於影像的本體論問題,都有重要的寫作。陳界仁刊在《ACT藝術觀點》64期的文章,從〈《蔣渭水:臺灣大眾葬葬儀》紀錄片,談異議音像「從對抗策略到再質變運動」〉真的很不錯,值得一讀,這個時候藝術家陳界仁是否變成評論者陳界仁了呢?
我是從Maurice Blanchot〈評論是怎樣一回事?〉【註1】來談,一般會認為評論就是一種個人自性品味的價值判斷,但對Blanchot來說,不管是小劇場、現代文學或是當代藝術,作品本身也在探尋一個新的價值,作品自己也無法很清晰的下判斷,作品內部可能就會有很多內部的雜音,就像你要怎麼評論高俊宏和他的三本書《諸眾:東亞藝術佔領行動》、《陀螺:創作與讓生》與《小說:台籍日本兵張正光與我》呢?他寫的比你還多、評論的比你還深、思考的比你還複雜、比你還矛盾,所以評論在這邊,要如何去面對一整個生命投入到一個場域、做作品,一路發展他對世界、自己和臺灣的疑問,有些疑問也是懸而未決的藝術家?可是他是學者嗎?不完全是,他南藝博士班還沒畢業,但是他也不是新聞記者,當他出書的時候,藝術家的身分好像又改變了。在當代如果我們要問說究竟什麼是評論時,等於是要問說究竟什麼是藝術?如同什麼是劇場的評論,等於是要問究竟什麼是劇場這樣一個問題,就會變得比較複雜。評論對Blanchot來說就是「深思熟慮的精神光芒」。
評論作為一個行動,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探索自身的存在和可能性,可能不要輕易嘗試,你會跟著藝術家(對象)作調整和改變,有很多複雜的過程,比如說高俊宏往山裡跑、去廢墟裡面做作品,你要跟他去嗎?或是你謹守一個原則,我絕對不接觸創作者,我就在我的辦公室和書房裡面寫,這樣其實就和雜誌記者差不多。即使是今天的雜誌記者,他們都覺得需要到現場。所謂創作者的「深思熟慮的精神光芒」並不是你在辦公室或是截稿壓力下硬擠出來的狀況下可以簡單想像的,它牽涉到環境和歷史的複雜問題,就這個層面來說,評論實在是一個漂泊的運動。這是第一個關於評論者位置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歷史意識的清理,最難的是歷史觀與認同問題,最難通過的是日治時期連接到明代、清代這一塊,很多年輕的藝術家和評論者想要通過的這一塊,怎麼相互連結,和臺灣現代藝術發展的關係等等,對台灣來說這之間是切斷的,有著劇烈的轉變。對我這代和年輕如郭亮廷這一代,對我自己來說也是非常複雜的。通過一段不清楚的歷史,通過這一段,也許你會變得面目全非,變成一個你完全不認識的人,你會知道一些原先你完全不知道的細節、事情或生命。像黃亞歷的《日曜日式散步者》,對我來說就非常頭痛,要如何評論一個本身就非常複雜的作品,某種程度評論者的心思要比他更複雜,知道他如何安排影像、聲音、字卡、哪裡找這些材料、訪問等等,複雜程度超過我們想像,當你能夠想像的時候,其實你已經變成另外一個人了,這就是評論很微妙的地方,讓你生命開始漂泊,你想要評論,但其實評論會改變你,藝術家(對象)會改變你,這種改變是冷不防的,是無法關在書房和辦公室想像的東西。
郭:兩位老師的分享頗有啟發,龔老師也是我的老師,我想回應的是,評論是否一定要透過文字?班雅明在《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品》提到,在電影發明之後再也找不到比鏡頭更厲害的群眾評論,這是文字完全沒有辦法超越的。好,我為什麼會這麼緊張,因為陳泰松也是我的老師,像泰松老師剛剛提到的,語言(話語)之於評論的重要性在哪?既然有這麼多比語言更厲害的評論工具,我可以當攝影師,為何要寫文字作苦工呢?我再舉例思想家漢娜鄂蘭「平庸的邪惡」的觀點,她以社會學的觀點來分析社會現象,社會現象和劇場演出一樣也是稍縱即逝的,為何要分析如此稍縱即逝的事情呢?為的是要命名,把一隻狗命名「小白」,牠死掉的機率就會比較小,因為有名字的東西能存活比較久,這是我們還需要文字的地方,文字用來抵抗遺忘。語言(文字)強大的力量甚至會影響我們如何去看待、感受影像。回應我剛剛討論的關於歷史意識的問題,我覺得劇評人身分有點像人類學家,在現場作第一手觀察與紀錄的人,去通過一段歷史,但如果我們沒有一個更大的關懷,如龔老師舉的例子,海德格說評論像飄下來的雪花,他們更重視的是更有歷史感的問題。相對於現在,評論更像是一種雪花,臉書文字或是網路留言比評論更可以即時性的反應,我覺得評論的價值是,如果這個雪花沒有這麼快消失的話,是因為我們對於它的冰冷、它的溫度、它的濕度會有更具體的感受。
龔:冰雹嗎?
郭:對啦(笑),冰雹比較大塊一點。我認為評論是一種初步的命名(如知道那隻狗叫小白)。如果我們把「評論工作者」類比為「人類學家」,回到一剛開始討論的,我們好像一直在作田野調查,但始終說不清楚一個部落(劇場、社區、場館)的故事,對生命史的脈絡無法建立起來,最後田野調查只會是一個個的檔案而已。
陳:文字和藝術現象(無論是劇場或視覺藝術)的關係有時免不了是強勢與弱勢(隱微與顯耀)的力量關係,是一種相互運作的語言。藝術家有時也會以藝術創作的模式進行批評,或藉由文字去參與評論,所以批評是無所不在,能有複多型態。另一個問題是,田野經驗不能證成評論,如同在在辦公室寫作也無法否決評論能有穿透或掌握作品意義的契機,如羅蘭巴特說的:「評論也是一種創作」。你的書寫能愉悅人嗎?能給人以知識的愉悅!評論是在這方面的分享,而不是審判機制。回到當代評論的問題,它的確有複雜面向。另一個問題是「評論有沒有用」?這好像在問評論在當代話語裡不具決定性的力量,是作品本身反而更有力,有其自身評價體系的運作模式。以西方人的角度(經驗)來說,評論在當代的文化世界已經不是那麼具有關鍵力量了。引用Groys Boris的看法,他認為評論在今天所處的位置,其專業性有如處於一種手工藝的生產狀態,算是一個夕陽工業,處境顯得困窘。我雖然不完全這樣想,但這種處境多少反應了當代藝評所面臨的難題。
聽眾A提問:我有滿多問題想問的,第一個是老師們會比較想要討論或評論哪些作品?選擇的理由是什麼?標準是什麼?評論做為某種支撐的力量,沒有機會被評論到的作品或是對於自己不感興趣的作品是否就會被漸漸被遺忘?第二個問題是,老師們如何去看對創作者或戲劇的創作者的回應?因為戲劇的創作者和評論者好像隔著一道牆,不會有交流的機會?有什麼方法可以增進彼此雙方的交流?第三個問題是老師們對於1990出生的後生晚輩,如何從中找到書寫脈絡的建議?
龔:我剛提到的文章(〈評論是怎樣一回事?〉(Qu’en est-il de la critique ?)),網路上有部落格翻譯。關於文章選擇的標準可以分為幾個階段,第一個是打工階段,為雜誌寫,可能持續一兩年。下一個階段可能會開始認識一些人,開始和專案或團隊合作。在此之間可能很多都是業配文或專案任務型的。最後一個階段,也是最難的階段,如何超出業配文,就是屬於自己特殊的歷史脈絡要建立出來,去接案子或是主動提要寫什麼。
書籍的部分可以參考陳傳興的《憂鬱文件》、《木與夜孰長》、《銀鹽熱》,都是重要的評論書寫,他非常關切臺灣藝術的現代性、文化的現代性和政治的現代性、殖民問題等等,也做了很多這方面相關的書寫與觀察。我們都引用國外,不引用自己的評論者或是藝術家,這是一種歷史脈絡不清楚的問題,很多評論的觀點就這樣去寫了,不管前面誰寫過,誰做過。我自己到後來覺得,在臺灣做為一位評論書寫者,應該去弄清楚王墨林、陳傳興等評論者寫過什麼、做過什麼,我可以如何去接續或打開新的問題意識。如對於台南的傳統畫師潘春源、潘麗水,有聽過嗎?沒有聽過的這些名字,可能才是最重要的,他們從清代、日治時期畫到80、90年代,1996年蕭瓊瑞老師開始研究時,潘麗水已經過世了,這些廟畫的畫師,他們算現代美術嗎?是不是我們美術的概念出了什麼問題?這是一個歷史的問題,因為我們的美術概念是從日本輸入的,而日本的美術又是從歐洲這邊建立起來的,這些都會牽涉到研究、書寫。比如說我昨天去看雲門2的《十三聲》,他們的身體動作、服裝色彩、投影、音樂、美術設計,這些歷史背景的脈絡究竟是什麼?這些對評論者來說都是非常困難的功課,至此,評論就會像泰松所講一樣,評論會變成一種創作的狀態,背後完全都是沒有被處理過的大量的知識與論述話語。
陳:我補充回答最後一題,評論涉及藝術生態的掌握,必須從它的當代狀態出發,去了解同時代人在做什麼,或試圖從話語的漏洞談起。我們不可能去掌握藝術家思想的所有面向,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和感覺方式,一定要去了解當代人在幹什麼,不然當下的歷史就會如同前代那樣被遺忘,所以不是掌握藝術史的理解就可以去寫評論。如果你發現有趣的觀點,就去冒險寫寫看,之後還可以繼續修正與發展,然後再繼續寫。評論不是學者式的嚴謹書寫,每一次都有想掌握的問題,評論是可以謙虛地去寫你感興趣的部分。
觀眾A提問(接續提問):我還想再問一個問題,某些劇團會擷取評論文章的某一部分來作宣傳,會變成一種片面式的訊息,老師如何去看待這樣片面擷取文字這件事?
郭:就是說評論會變成是劇團的行銷文案,這沒有辦法去阻擋,評論發表後就是公開的。關於你剛剛提的怎樣選擇哪些要評論?哪些不要評論?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當你看戲看到一定的量,你會發現某些戲都沒有人寫,票賣最貴或是觀眾最多,但是沒有人寫。比如說現在很多的文創劇團,但劇評人寫的就比較少。這是必須要去問的問題,我認為這些也是需要去書寫的,之前我和思鋒有參加一個德國劇評家舉辦的討論會,他對於臺灣的劇評人只挑自己想寫的感到不可思議,他認為以德國專業化的標準來看是不可以的,德國的劇評人在年初就會排定當年所有的行程,這樣才能生產出即時評論,所有的功課在到場看戲之間就要做完。比如說一本小說改編的戲劇多達600多頁,在看戲之前做好功課,才能在兩天內生出評論,覆蓋率(所有的戲都有人去評論)才能達到最大。所以我認為這些偏商業的戲還是需要去評論的,不然創作者會誤會他自己。
吳:表演藝術評論台對臺灣劇場作品的評論,大部分作品的演出場域都是實驗劇場、小型劇場,評大劇院的戲比較少。後者這一種大眾的、市場的、通俗的戲劇書寫,反而容易被忽略,回到我自己,在面對這一類作品,反而不知該如何著手,
另外,「表演藝術評論台」的出現和「ARTALKS」的改版,出現了像郭亮廷所說的評論媒體化的問題,因為網路的量的需求,很容易被收攏在單一作品的評論裡,比較無法有時間關切整體,也許這個問題從以前就有了,能書寫生態面的評論人很少,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另一方面,的確也觀察到有些評論人慢慢建立自己觀察的範圍,大家在閱讀評論時,可以像對待一位創作者一樣,去觀察該評論人從以前到現在整個評論的書寫脈絡。
也想請問龔老師關於編輯工作的經驗,包括編輯《ACT藝術觀點》、策展、書籍出版與文字書寫的經驗。現在有很多評論人,但是卻缺少記者和編輯,表演藝術類的編輯大多都是《PAR表演藝術》出來的,目前表演團體舉辦的活動或是文宣、場刊,較多宣傳、資訊,創作者和評論者之間仍然缺乏更深度的對話。
龔:我回應一下,好像真的需要一些機關刊物,文章需要在媒體上面刊登。我最近在看《日曜日式散步者》,楊熾昌一群人成立的「風車詩社」,由藝術家組織刊物,引進文章、資訊。做刊物需要一群人一起做,它代表一個群體的形成,一個刊物一定是跨領域的,我也認為評論者之間的聚集、討論是必要的。就評論者而言,寫作是孤獨的,重點是周邊環境要如何去構造?一群人編輯刊物會形成一個發言的平臺,形成的力量會遠遠超出你的想像,可透過刊物去提出結構面的質疑、翻譯或是對話,這是我自己在編輯經驗中的體會。一個刊物不應該一個人運作,好像表演藝術類特別嚴重,應該是幾個重要的核心編輯來形成團體,有一個刊物的運作代表一種長期的決心。我先講到這邊。
吳:今天這場座談,從「評論的專業性」、「歷史意識」、「文字作為評論的工具仍舊可以有效?」陳老師講視野和評論之間必須相互引用甚至引起爭議,可能才是評論的開始,到龔老師將評論打回原型,提出歷史的懸而未決狀態等等。這場討論就到這邊,謝謝。
註釋:
1、 〈評論是怎樣一回事?〉(Qu’en est-il de la critique ?)內文請參閱網址:http://blog.roodo.com/pleiade/archives/13085735.html
2016首發於台南藝術節官網(當時連結已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