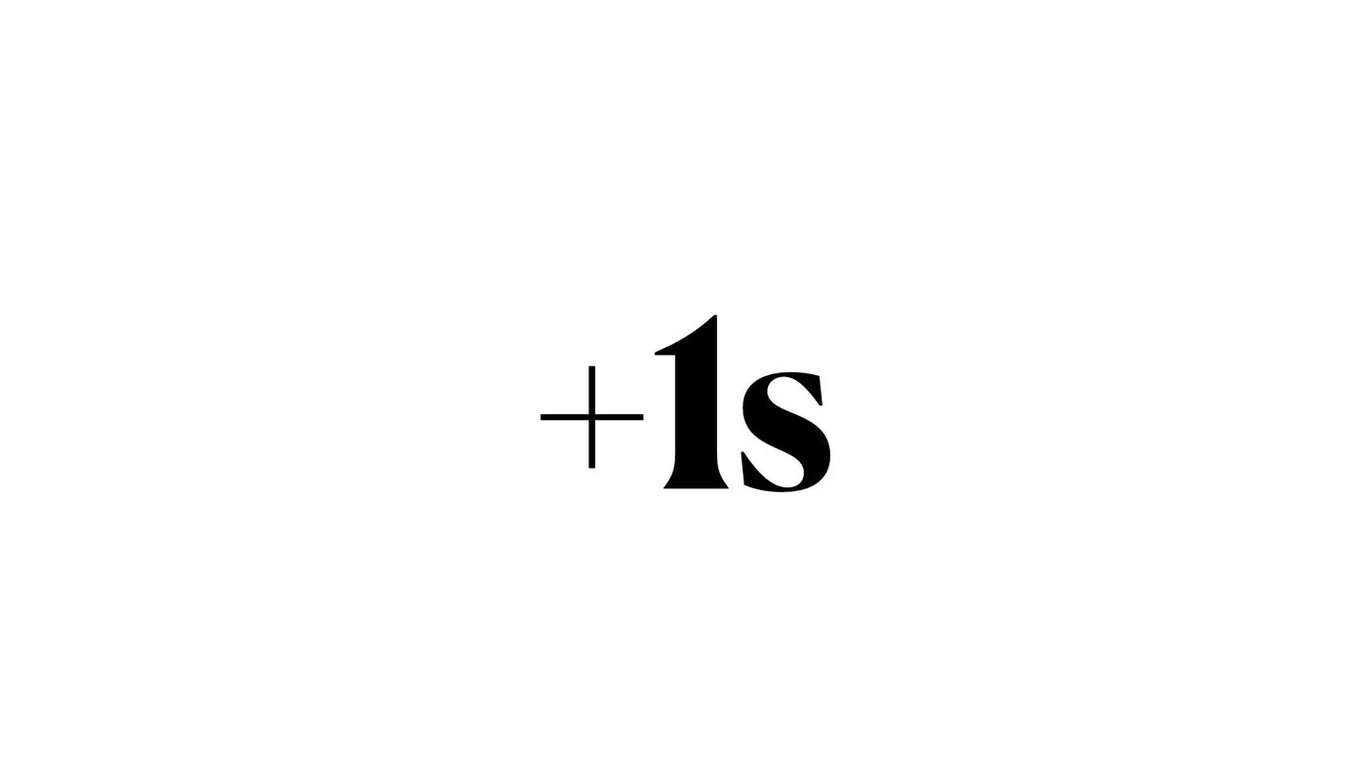剑心的政治光谱

剑戟片的传统延续到了二十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漫画改编的《浪客剑心》系列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继承和延续。
系列优缺点显而易见。缺点,一言蔽之,是叙事不能像动作戏一样凌厉。《最终章人诛篇》把整个系列的缺点放大了,更拖沓,尤其是闪回的场景(系列重复使用镜头的确非常多),之前人气高的角色轮番登场,在偏向粉丝服务fan service和呈递故事的意图间来回游走,坦白说,电影本就没多少故事可讲,剧情瘦骨嶙峋,冲突只有最平直浅显的复仇,没有再多挖掘,所以才如此多填充吧。好在动作戏依然实在的优秀,人物弧光也最终画上圆满的句号。
而《追忆篇》避短扬长。其一,是系列中最扎根于历史,最写实的作品,像千禧年后,舍弃哥特和坎普(camp)的超英电影;其二,让动作戏成为人物性格的对话出口,乃是所有动作片成功的关键。毫无疑问是系列最佳作。
这是技术上的观感。
原作是优秀的漫画作品,如果我们把类似挥刀速度可以扭曲时空的元素一笑置之,仍有诸多讨论的空间。
《浪客剑心》的故事讨巧地放置在新与旧,进步和保守的激烈冲撞中。人物冲突在历史的情景中似乎总是更加值得回味,即使这种放置是娱乐化的。“放置在历史中”,并非仅限于过去的某个时空,比如某个历史朝代,而是说,时代背景塑造了人物的动机,所以现代故事,同样可以放置在历史中。
基于时代的理念更容易产生超过血缘和权力这样原生的冲突。这和人们常喜欢说的“主义和生意”的伪善其实是相反的,因为这两者其实并不互相排斥。用另一句话说,是暴力并不解决道理的问题。观众有多关心打架,其实是关心打架的人背后的动机。原生的冲突,易理解,浅显单薄;理念的冲突,对创作者而言容易变成大杂烩,但对观众有期待。
这一点,现代的商业电影做的并不好。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漫威《美队三:内战》中,一开始两个阵营的冲突是对超级英雄的管理方针有分歧,最后怎么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他杀了我妈”和“他是我兄弟”,电影并没讲清楚。这是用了障眼法糊弄过去了。
而因为现代性的启蒙,新与旧不再是仅仅是朝代的更迭和天命所归(Mandate of Heaven),对与错也超脱了武侠小说中被浪漫化的江湖义气和朴素正义观。
同样的放置,可以在昙花一现的黄飞鸿系列,仅特指第一和第二部,中看到。即使黄飞鸿的银幕形象经久不衰,我甚至仍然认为这两部作品是被低估的,因为黄飞鸿代表的是一种方向。在特定的创作和商业环境下,跳脱于历史之外显然更保险,而这种基于个人的表达而不是工业流水线的创作迅速消耗殆尽,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飞来飞去的那种武侠片,始终还是大多数。
黄飞鸿代表传统和保守,在西洋留学十三姨的启蒙下,日臻进步(progressive),在近现代中国的阵痛中,逐渐拥抱现代性。
剑心的弧光则完全相反。
起初,社会动荡变革中,一无所有却武艺高强的剑心与师傅意见不合,师傅的立场是典型家长式的,不要过问政治,被人利用。于是,剑心怀揣拯救苍生的崇高理想出走,成为维新派的杀手。家长,是五四中的蔡元培,是鲁迅痛骂的杨荫榆,是八零九零后的父母。弟子则像极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描述阿廖沙提的著名“当代青年——
秉性正直,渴求真理、寻觅真理并且信仰真理,而一旦有了信仰,便切盼立刻全心全意地投入,切盼迅速干一番大事业,为此必定愿意牺牲一切,乃至生命。不幸的是,在很多情况下,舍身也许是所有的牺牲中最轻而易举的。
不同的是,剑心身怀绝技,死不了,牺牲的是人的情感,甚至对权力无戒心和抱负(这是许多左翼赧于承认的),以革命理想的名义杀人如麻。
引发剑心转变的也是他身边的女人(们)。
雪代巴如同地狱里的微弱的光,虽然微弱,却还一点光。半推半就促成的“田园牧歌”生活恰好落在剧本写作所说的伪胜利(false victory)上,意味着剑心的英雄之旅,不会在这里轻松地走完。虚假和真实的脆弱天平一旦倾斜,就不能回归原位。短暂拥有了一点后是彻底的剥夺。相比之前只是没有人情世故,剑心要失去更多,失去听觉、视觉,只剩杀人的本能反应,亲手毁灭具有欺骗性的希望,斩断自己和世界刚建立的联结,打入地狱之底,才能踏上了更艰苦的重新成为人的旅程。
好在,感知幸福并不是人类情感的唯一证明,经历背叛和失去的痛楚,如果可以恐惧,可以失望,可以悲哀,可以懊悔,承认自己即使无救赎的希望却仍有渴求(Inf. IV: 42),那么或许快乐也不再遥不可及。
鸟羽伏见之战后,新时代到来,鸟尽弓藏。杀手需要有目标,如同激进的左翼总需要寻找下一个斗争的对象。这和革命需要反革命续命的推论并不遥远。已经战败的齐藤一所说的“仗剑生,为剑死”意为一旦成为理念的手段,似乎只能继续在革命的路线中无休止地斗争下去。
剑心并不认同,在此时收手不再杀人,选择逆刃刀浪迹江湖,利刃向己,重视生命高于理想。武侠小说的结尾,英雄女侠总是取巧地放言,从此游山玩水,回避真正尖锐的存在危机。剑心入世,是救赎,也是(重新?)塑造自我的开始,和神谷活心流的“活人剑“不谋而合,促使剑心主动选择神谷薰成为他的道德指南针(moral compass),往后的主要冲突来自于能都否坚守“不杀”这一信条的试炼。更重要的是,这些选择,都自然地引向广义上超越(override)原生血缘,自己选择缔结的家人,家庭——自我最直接的延伸,也是最容易理解的保守对象。
剑心修炼的飞天御剑流的终极奥义是生死置之度外之后的求生意志,正是剑心的人物弧光。起于立誓维新成功后不杀,剑心承认了他人生命有普世而不是选择性的价值,终于自我。自我就是,超脱外界和任何集体分派的身份,预期,勉强和顺从,认识自己生命的价值,承认自身的行动力(agency),维护自己,保卫来源于自身作为个体的价值,把自己也囊入这个价值普世性。
角色的终点,剑心和神谷薰在深山中牵手,似乎看到安兰德中短篇《颂歌》的影子——
我不是他人实现目的的手段,我不是被使唤的工具… 我不是祭坛上的牺牲。
这就是人斩拔刀斋和绯村剑心的区别。能定义俗套的“自己是谁“这个问题的人,毕竟只有自己。正如博尔赫斯所提的十二世纪波斯诗歌《群鸟大会》那样,寻找者即被寻找者,追寻过程既是答案本身,当你真的找到这个答案的时候,答案是什么就不再重要,或从来都不重要。
这一蜕变是自省的,反应性的,如果同时带有政治属性的,那就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