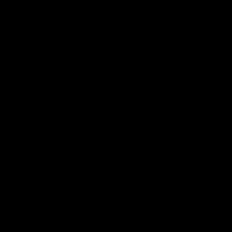討論回顧|災難,非常亦如常——阿潑、潔平、富察與眾人的夜談
九月初,阿潑的新書《日常的中斷》在台灣正式發行。藉著這個契機,她把第一次公開談論新書的活動交給了 Matters ,正式加入了我們在線問答的主角行列。
由於阿潑一開始就挑明了寫這本書是「拿『記者』身份來和既有的災難敘事/框架『對決』」,我們特別決定請有震災現場報導經驗的潔平,來跟她進行交流;而這本書的幕後推手,八旗文化總編輯富察,也全程在線參與討論。
活動進行了一個多小時,潔平突然私下跟 Matters 團隊說:「今天晚上有自家人圍爐夜話的感覺。」
這句話,或許對「災難」這樣沉重的課題來說似嫌溫馨歡愉了些,但的確有其道理。這天晚上,最活躍的這三位與談人,彼此原本平行的人生,正是因為 2008 年 5 月的四川大地震,而迂迴(但極富意義)地產生了交集。
那一年,25 歲的潔平,生平第一次以記者的身份進入震災現場。她坦言:「在此之前沒有見過任何一種死亡。」
我特別特別感謝和慶幸的,是隨身的背包裡裝了錢鋼老師的《唐山大地震》。錢老師在書裏說,他採訪唐山大地震那一年23歲,這場地震教他從災難的角度,重新認識了這個星球。我後來才明白,是他的這句話,給了我一種超出生離死別本身的視野,在潛意識里,時時刻刻提醒我理解血腥畫面之外,災難的深意。
(潔平)
相反地,花了好幾年時間追逐「災難」這個課題,寫出《日常的中斷》這本書的阿潑,其實不曾親眼見證過災難發生後的最初現場。2008 年,因為加入了台灣援助川震的隊伍而進入四川災區,她回憶道:
我覺得慶幸(?)的是,到達災難發生地時,屍體都已被清理乾淨,儘管鼻子還能聞到某種味道,但至少心情上衝擊小了很多。但因為從來沒有在第一時間出現,所以也無從探究到底在那種情況下,要怎麼問問題或者面對他人撕心裂肺的痛。
(阿潑)
或許正由於迥然不同的現場經驗,在這場討論之中,阿潑一開始試圖拋出來的課題,是關於災難現場的「真實」與新聞報導的「再現」是否必然難以共容?
作為一個閱聽眾,我很容易被災難新聞吸引,新聞畫面裡的哭天搶地每每都讓我跟著痛哭流涕,但哭完後,會覺得哪裡不太對勁。新聞訓練跟記者身份也會讓我腦海裡出現觀景窗,明白這些素材或題材是怎麼被框定的,而那些又是如何被內化成災難新聞的 SOP,報導產製流程怎麼跑,最後反映在收視率或點閱率上。雖然我從未在第一時間出現在災難現場,我仍清楚那些鏡框外還有很多東西因為篇幅時間或諸多限制,無法被收納進來……
涉入災難的人如此之多,但在媒體報導框架裡只有「災民」、政府、救災人員(志工),他們的性別族群階級乃至於背景與心理,往往被概化單一,未能見到多元與複雜性。但這可以怪記者嗎?在那種與時間賽跑的壓力下,有誰能像人類學家或社會學家那般從容?沒有辦法,在現場採訪的困難,無人能想像。
(阿潑)
無人能想像的困難,究竟有多難?潔平以川震後第四天在北川縣城的一段親身經驗,為大家做了最充分的說明:
我問他,你家人還平安嗎?他指了指河對岸的一棟樓房,說都在那裡。我順著他的手指看過去,一棟房子在山腳下,沒有倒,有四層樓高。我於是說:啊,幸好樓沒有倒…… 他稍微沉默了幾秒鐘,說:這棟樓本來是5層……我的爸爸媽媽爺爺奶奶,都住在一樓。
(潔平)
「像是這種情況……你根本,就是沒辦法做任何採訪的啊……」潔平絮絮地說著自己的反思。
只要不是太著急,只要在現場,還讓自己是個人,不是個工作機器,保有對痛苦的強烈同理心,許多夾帶著血淚的故事,都會向你走來。太多的痛苦需要傾聽了。只看你如何去公共化地處理這些沉甸甸的聲音了。
(潔平)
無論是不是關於災難的故事,公共性是新聞報導必然的依歸,但災難報導之所以難,也就在於人在「非常」狀態下的情緒張力,其實並不容易表述。對此,小城試圖提出了一個釐清的問題:
當我們在講述災難的時候,我們是否有這樣一個目的,即為了讓沒有經歷過災難的人,更貼近經歷過災難的人的真實感受呢?提高這種「共情」,會對於兩個群體各自產生什麼影響?
(小城)
針對這個問題,阿潑從自己因為記者身份而苦於難以呈現災難下人與群的複雜面貌,則不免有所慨嘆:
是的,所以所有災難書寫都是先從描述災難現場或發生開始,而且會從災民視角出發。我也是這麼做的,初初我幾乎每一場災難都這樣開始,後來覺得乏味了,因為很快就會發現其實都很像,都是在「情感」或「人性」的共同性上激盪。因此,災難的閱聽眾才會同哭同笑同感。所以災難電影災難小說大概也就是那個樣。
可是這太耗感情了。但除了激出感情、產生共鳴,然後熱烈捐款、衝去當志工或嘆口氣外,實際上能改變什麼呢?沒有。
(阿潑)
另一方面,潔平倒是從往後擔任編輯的經驗出發,提出了一套克服這道難題的實務方法:
經歷過這些,我在做編輯時,如果再遇到地震(比如花蓮地震),會調動兩個記者,從最一開始,就朝兩個方向努力。在現場感受故事的記者,不用分神去拼有效信息鏈;負責調查有效信息鏈的記者,即便在現場,也不需要寫生離死別的故事。這樣就有可能在現場過後,盡量留下人性的、和調查的,兩種深度報道。
(潔平)
而針對佳禾詢問:在這麼多的框架侷限之下,處於災難現場,媒體是否根本就做出真正的「好新聞」來?潔平則認為:
有局限的東西,不代表在那一刻沒有意義。局限是一個後設的視角。而在潮流中,所有努力抹去泡沫、試圖沉澱出有效信息、有價值調查、有深度人性故事的努力,都應該被肯定。如果沒有這些,也不會有阿潑這本書,後面的所有研究也都沒有了基礎。在這個意義上說,災難現場,反而恰恰驗證了「新聞是歷史的草稿」這句話。
(潔平)
除了記者在災難現場進行採訪的道德拷問與專業艱難,這場討論另一個聚集眾人目光的焦點是「中國社會」。十年前,還沒有來到台灣成為出版人,正在上海非政府組織圈子工作的富察,其實跟川震也有相當深刻的淵源。
2008年5月12號,我在上海。晚上六點鐘的時候,我和上海幾個朋友一起成立了一個NGO聯合,叫做新駝峰航線。把從上海募集到的物資用空運的方式運到四川。那也是我作为中国公民意识的,第一次觉醒和第一次实践。
(富察)
新駝峰航線是川震後中國的非政府組織所發起眾多自救行動之一。對富察來說,當時的他一度感覺到這可能會是一個「中國在災難中覺醒的時刻」,「公民社會」一詞成為全國性風潮、廣泛佔據媒體版面;然而,後來的現實卻走向了公民社會的消失。對此,他拋出了一個困難的問題:
我們一度天真以為中國真的會有一個公民社會的崛起,然而卻拜一場災難之所賜。如果沒有那場災難,如果沒有不幸死去的10萬人,我們能夠享受這短暫的是五年公民社會好時光嗎?
(富察)
不過,潔平並不完全同意這樣的說法,她提出了自己的觀察:
08年之後一度蓬勃的公民社會景象,不能說是四川地震帶來的,而是89之後很長時間的耕耘,經過了03年-08年相對寬鬆的市場化媒體發展,在四川地震的大災難刺激下,收割了果實,又在之後跟著四川重建、微博興起,紅紅火火地過了又五年左右。…… 像梁曉燕老師等很多89一代,在90年代之後,一直在做基礎性的培育NGO、培育公民社會基本概念的工作,有這些基礎,才能有後來壹基金、免費午餐這樣超大型的民間慈善組織的出現,也才能有在地震發生當時,全國人的同情心、愛心能被有序組織的基礎……
要說「公民社會」在媒體上的顯性話語出現,應該是2003年孫志剛事件,那時候還有公民社會元年一說。但在川震之前,的確沒有那麼全民性,而是知識分子走進公共比較多。川震的確是個開始。(其實不能迴避,2008年還有北京奧運,大量自發的志願者,也是某種程度的公共參與)
(潔平)
川震或許是中國公民意識大團塊聚積的開始,但不幸的是,既使在川震之中,公民社會也沒能超克國家政府設下的框架;而在川震之後,社會力可以發揮的空間更是每下愈況。先後經驗過 2008 年四川地震和 2010 年玉樹地震的災區現場,潔平無奈地說:
四川地震中像豆腐渣一樣倒塌的中小學、幼兒園,和埋在廢墟里的五千多孩子。在最初的時候,這明顯的人禍揪住了整個社會的心,但很快就被滅聲了。災難敘事變成了「多難興邦」「救援英雄」「感恩的心」,受害者被連續打壓了十年,除了逼迫他們生第二個孩子之外,政府至今沒有解除對遇難學生家長的維穩……
如果說四川地震讓我第一次意識到人禍比天災更可怕,那玉樹地震,簡直動搖了我做記者的信念根基:第二次離開玉樹的時候,我知道,這裡的故事,再也不會有所謂的真相了。。。因為在這裡,天災抹平了一個藏族小鎮,在無比正當的理由下,一兩年後,長出的,完全是個漢族小鎮了……
…… 我們多想有台灣那樣,整個社會疼痛之後,帶著痛成長、學習的機會。但在中國,倒不是媒體的責任了,整個社會就像是一台電視機一樣,幾十年來,反復播放著同樣的、割裂的、無法有連續經驗繼承的災難。
(潔平)
對於中國社會在政局變化下逐步走向沉寂、噤聲,阿潑也感受甚深,她提到:
我最後一次去中國是2014年底,去唐山。之後再也沒去了。為什麼?因為我在北京見了一堆自由派記者,每個都是絕望的語言,有的早離開了,有的在我回台灣後離開那行。沒有言論沒有新聞自由的天空,確實相當令人窒息與絕望。
我後來在埔里遇到四川的學者,她跟我說魯甸地震如何封鎖如何阻絕訊息,如何防止其他NGO進去,聲音非常低非常低,像是根本不想承認。
(阿潑)
然而,如果我們對災難現場所折射出來的問題有足夠深刻的反思,很快也會發現問題不會只是「政府施——人民受」的單向權力關係而已。在回答曉雅關於政府主導的救災是否會破壞人民(特別是少數民族)源於信仰傳統的自我調適能力?潔平也提醒了現場的狀況往往比我們想像得要複雜,她說:
其實這個問題,在現場是更複雜一點,沒有局外人想象得那麼分明。世俗的救災,與信仰的救贖,不是同一個層面,也不矛盾的。在災難當時,藏人對救災者的感恩,絕對是非常真誠、淳樸的,我看見過好幾個藏族老媽媽,一邊念經文,一邊拿出毛澤東像(也不知道是藏了多少年的),對著來救援的軍隊喃喃地說:共產黨萬歲。我猜那是她會說的為數不多的漢語。那種感恩是很真實的,因為去高原救災的年輕軍人也確實是很辛苦,受災的藏人都看在眼裡。只是後來,事情一定在慢慢起變化,也一定會令許多藏人還來不及反應,生活已經徹底變化了。
(潔平)
類似的群體信仰、傳統、文化在災難衝擊下所迸發的爭議課題,在 2009 年南台灣莫拉克風災後許多原住民部落面臨是否應該遷村下山的抉擇時,也形成了很棘手的狀況。
據我所知,族人也是對立的,很多人實在想趕快回到安定生活,所以選擇平地或下山。他們感到非常難過,因為好像他們是罪人,就該被批評。
但山上危不危險?告訴你,就是很危險。這種危險怎麼來的?就是一直以來的山林開發。
…… 事情其實沒有山區平地遷村或原地重建這麼簡單,但你知道我看藤枝部落或好茶那樣失去土地連帶根也失去,也是非常難過。但這不是這次風災遷不遷村如何決定的問題。他們是一直在被迫遷移的。
(阿潑)
從莫拉克,聯想到川震,再拉回九二一,又跨到日本的三一一海嘯。阿潑在討論時的思路,如同她在《日常的中斷》這本書裡的寫作風格,雖然表面上是談台灣以外的三場亞洲巨型天災,但其實她不斷地將在外地田野裡的所見所聞,與台灣本地的經驗進行參照。身為這本書的編輯推手,富察便直言:「欣賞阿潑的台灣視角,把這樣亞洲三場巨大災難連結起來,是台灣獨有的思考。」而阿潑則認為:
寫國外的東西對我來說容易得多,距離產生美感(?),而且感覺比較多東西可以學。這大概也是人類學者的天性(富察會不會跳出來說你看你看),人類學家都是研究異文化,就是因為不會有一種理所當然的先驗,而能從根源刨起。大概就是這樣的感覺。
但我終究是個台灣人,所以,我回答與思考的一定是台灣也有的問題。
(阿潑)
於是乎,阿潑最終將《日常的中斷》寫成了一本「突破單一地理空間、幾乎成為制式的時間框限」,帶著跨文化比較企圖的著述。
坦白說,不是很容易定位這究竟是一本怎麼樣的書。它想帶給讀者的視野,不是實用性質的防災觀念或政策檢討,若非要一個簡單的概念來涵括,或許是災難的「普世性」,以及它之於人類社會的意義,正如同潔平在討論一開始為了這本書所下的註腳:
災難如常,一次一次的災難,於人類在地球生活的共同經驗而言,應該是一種往前邁進的累積,和學習理解的日常。
(潔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