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要抓起沙
很多时候,我发现很难厘清眼前的纷杂。
01
关于李文亮医生的调查出了结果。而他的亡故实情,其余人的训诫,整体系统的追责与反思,是否止步于此,我已如忽地失焦般,不知该有何寄望。
其实在中国监委调查组的报告中写明了一些经过——2月6日19时20分,已进行插管,持续胸外按压;而21时30分,仍在进行心肺复苏按压;直到22时40分许,才使用上借来的ECMO。
2015年欧洲复苏委员会(ERC)指南认为虽然正在进行高级生命支持,如果缺乏可逆性病因以及心脏停搏已经超过20分钟者应该停止心肺复苏了。而校友线的消息,则是李医生6号的下午就已情况极危,晚上8点半已出现心脏停跳,抢救到9点半宣告死亡。
心肺复苏的持续按压,超过数十分钟以上,是极易对人身造成肋骨骨折等严重损伤的。有关当局将李医生的所谓抢救一直拖至凌晨2点58分,只是秘不发丧的肮脏操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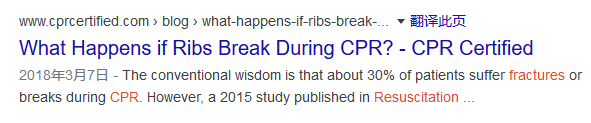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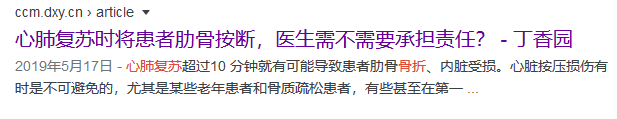
何况,李医生是一介普通人身份,却极难得的具有高尚的精神,勇敢说出“健康的社会不应只有一种声音”,而整个政府体系灭绝人性的行径,不仅生前要训他的人,治他的话,死后还要辱他尸,扰他的魂,最后还妄想掩盖这一切,这足称天理当诛,人神共愤之罪行。
李医生个人,好似得到了平反与抚恤,这像是顺应民意的举动。然而撤回1个人的训诫,处理基层的警员,丝毫不见真正的反思,对于所有明眼人,无需多言。
中共体系似乎一直都是如此的,无论怎样的倾轧和斗争,怎样的伤天害理,就如六四一样,他们绝不会认错,不论整个体系内如何的血债累累,他们也能自欺欺人般的定性一番。
让我由衷不解的是,这种绝不轻易言错的姿态,本质上更多的,是真正的强硬,还是内里极为心虚的软弱?这甚至不是简单的色厉内荏,而是一种表面的和缓、顺应,但实际上又铁幕般坚硬,殊难改变——至于内里是真的强有力的自信,还是充满着胆怯,时刻忧惧着丧失正确,真是无法可知。
这类并不鲜见的操作,似在透露着执政者的混乱、拙劣甚至愚蠢。可同时,又像包藏有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企图——他们或许自认找到了和缓、铁幕、自信、忧惧,甚至低劣和宏远全部,都同汇于一炉的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他们操纵和蔑视一切人性,眼见皆刍狗,不仅仅是对百姓,对自己竟也同是如此的。
而驱动他们如此行事的源头,除了对权势不可救药的耽溺,我找不到其它可能。
何伟(Peter Hessler)在纽约客的文章《和平队与中国断联》(The Peace Corps breaks ties with China)中写道,在1998年,他作为志愿者在中国授课的最后一年,中国推出了两项在日后看来影响深远的举措,一是开始建立互联网的墙,后被英语世界所知为Great Firewall;另一是宣布要打造一批国际一流大学,后在国内被称为985高校。
【注:和平队类似孔子学院,不同的是,以将年轻志愿者送到偏远落后地区高校任教的形式展开。在中国以“美中友好志愿者”之名展开活动,已有27年,共计前往四川、重庆、甘肃、贵州的93所高校。】
他说,这两项同时开始的举措,折射出一种美国社会难以理解的策略——教育开化和严控管制齐头并进,同步推行。(They reflected a strategy that was hard for Americans to grasp: the idea that education and restriction could proceed in tandem.)
他形容这种并行,像是一条高速公路的正反向车道。而生长于中国的我深知,类似的融汇,远不仅于此。这些复杂和“多元”看似总在预示着有很多值得向往的可能性,但往往在现实中,尽是挣扎与撕裂,在张牙舞爪的等待着个体。
在中国的和平队已被彻底叫停。它在美国受到参议员、众议员等诸多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对,在经济效益、政治意义、队员后续就业等社会状况、被渗透的风险等诸方面都遭到苛责。其实本质上,“这都与不断增长的反华情绪有关”,在国会等各方压力下,这项支出比美国国际太平洋大比目鱼委员会还要少的项目,宣告终止。
何伟写到,“在九十年代,中国方面可以随时取消该项目,但地方大学能够以某种方式与高层的保守派沟通,认为和平队的这些老师值得他们冒险,这似乎是一个小奇迹。”
(In the nineties, we had known that the Chinese could cancel the program at any time. It had seemed a small miracle that local colleges were somehow able to communicate to high-level conservatives that Peace Corps teachers were worth the risk.)
而二十年后,“美国的大趋势变成了:人们觉得,每一次外交联系都是一种威胁,每一次的交换都是零和博弈,取而代之的是,人们不再相信自己,不再相信他们曾经最优秀的模式,而是带着偏执和妄想,退缩到封闭世界中。”
(It seemed part of a larger American trend: every foreign contact was a threat, every exchange was zero-sum. Instead of trusting themselves and their best models, people regressed to the paranoia of those with closed systems.)
这位写下中国三部曲的美国人,他来到中国重庆涪陵的时候,才27岁,如今已过去14年了。他的书写得太好了,我脑海中,好像仍能看到他在北京的街头,在长江边的小城,在大漠的长城遗迹旁晃荡。我能深深感触到,此时的他,是多么无奈和惋惜。
不仅美国官方高调的宣布和平队终止,中国的评论文章,也给出了欢庆般的口吻,观察者网引用旧时“别了,司徒雷登”的句式,致意“和平队,走好,不送”,其中特意写到“在华27年,美国外交部门本意是想‘养狼’,但最终收获的却是一窝哈士奇”,并以“和平队走了,贸易协定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结尾。
类似的嘲弄,又何止于此呢。看看国内媒体到处幸灾乐祸,取笑各地的防疫策略——凡是逐步变得有序的国家就会从视线中消失,他们总能精准聚焦到最能引起国人优越感之处,似乎越是混乱和灾祸,越是他们的盛宴。
况且,并非只有我们如此呢。表面上看,因为外交部发言人,在Twitter上无根据性的指责美国军方将新冠病毒带到中国,彻底激化了矛盾。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到了要天天把Chinese Virus挂嘴边的地步了。而英国脱欧党的领袖Nigel Farage则是呼吁西方需要打起精神,联合起来对抗中国。
而若没有国内执政者在疫情扩散全球后愚蠢的宣传策略,和外交部姓赵的蠢物,这一切会否不一样,已经无从得知了。
我深知对立与割裂就隐藏在时代表面下,且已摇摇欲坠,但我不曾料到它如此轻易的,就被激化。
无数的人涌动着,欢呼着,脱钩吧,断裂吧。却不会想到,这曾是多少诚挚的人,梦想的,与力图尝试的,去弥合那么一点点的连接。
02
方方的日记,越写越勇敢。可如果不是周边的环境愈发凶险,又怎会需要这样一位老太太,必须这般勇毅呢。
她说以为只有她那一代人,曾深陷僵化麻木中,需要自己与自己斗争,自己为自己解毒,她没有想到,当下的一代人,竟也会有这样的日子。
何伟说在他任教时,全中国只有7%左右的高中生进入大学,而如今,这个比例高达45%,这无论怎样看来,都应该有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
可我们的今天却是另一种模样——举报和揭发,再加上扒出全家式的批斗,成了大仁大义的代名词;在疫情中短暂的热烈讨论后,似乎一切不同的声音,都在被追猎;只有立场和标签是重要的,一旦不同,不论是外人,还是同胞,都会被投以最大的恶意。
而在国际上,这数年间美国退出一系列联合国组织,又大举修墙,英国则是毅然脱欧,这些都是明显的分化割裂型倾向。持这样政见的首脑人物,如川普、Nigel等,他们会选择轻易的加入到激化对立中,似乎并不让人意外。
欧美社会,是具有鲜明的反种族歧视之基础,可当下的这一场反华势头,竟也已不乏拥趸了。当初投票支持着美国、英国走出那样分化脚步的大众,是否也会随着这些首脑一同加入到更激烈的对立中,拦在他们面前的,只剩那一根虚拟的,也并不牢固的反种族歧视的界线。
这些天我看了很多报道,很多有识者就像何伟一样,怅然于这般的发展,也很疑惑,世界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因“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而进入大众视野的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在赴德国各地学校的演讲中,会讲到人类的文明中,总会出现极端的,反文明的力量和浪潮,而这是奥斯维辛等一系列惨剧的根源。他希望人们能警醒,时刻提防着这种反文明的反扑。
这也是我认为“写诗是野蛮的”会具有的一层含义——诗歌是人类文化艺术的集大成者,是文明的象征,可人类文明中总是如影随形的,有着反文明的存在,那么即便是诗歌也无法脱身在外,它必然也是具有野蛮的。人类应当深刻认识与警醒的是,每一种文化,每一个人的人性中,都不可逃脱的含着野蛮与反文明的因素,这是人类文明中一切野蛮的唯一来源。
在阿多诺对于学生群体,明显冗长的讲稿来说,我不太觉得当年德国的学生们,能从他的演讲中收获多少警醒。
但德国人有他们自己的方式。其中有一种叫“绊脚石”的艺术项目,由艺术家岗特(Gunter Demnig)发起,将正面是黄铜板的立方体石块,置入建筑物前的道路上,几与路面平行。黄铜板面上会详细记载着,一位位遭受灾祸的犹太人生平:姓名、出生年月,以及或工作或学习或生活于某区域某建筑,最后是这位犹太人的去向,他们大多是亡于各个集中营中。

迄今,这种绊脚石已在德国700余城镇铺设,仅柏林就有4700多块。它们亮着微光,存于一栋栋建筑前,走过的人,不会真的被它们绊倒,但在心里,很难忽视这其中的警醒。
而我们国家,悠久的历史,无数的朝代更迭,或者辛亥以来100多年里,新旧左右的挣扎中,我不觉得我们留下了多少关于自身野蛮的警醒。
我们也有一些纪念方式,在警示着民族曾危亡,可那是针对外界威胁的。而从传统儒家的“三省吾身”走来,我们的社会,却一直很少关注自我应有的反思,有的只是“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就像告别了数千年的封建时代,这100多年后,我们自以为迈入了文明的新时代,可当下的我们却深深迷恋着宏大叙事,沉醉在那些光明和正确的讲述中,总是在回避我们必不可能缺少的黑暗与野蛮——以及因它们已重复了无数次,当下仍在继续重蹈的覆辙。
对于现在的英国,我缺乏了解,但从美国社会来说,他们也缺乏对于反文明的警醒。
虽然由于美国社会由各族裔构成,且有黑奴等历史,各移民族裔都会十分注意争取自身权益,人们会对种族歧视有匪浅的提防。但总体社会中,有相当一部分的人,生活里仅以美国为中心,沉湎于“God bless American”的满意自得中;而且由于宗教传统等因素,虽然整体社会中很重视人性的复杂多面性,但不少见的会把一些极野蛮、反文明的特质,归结于邪恶、魔鬼类的原因;还有一方面,是极度商业化发达的娱乐文化产业中,会出现把血腥暴力当作卖点的现象,对野蛮的司空见惯,看似在讲述,在提醒人们,却也容易使人麻木——这些都会实质上干扰真正的警醒。
还有一项更显见的事实,英美等国一直以来,在文化上尽量弱化北美土著印第安人的几近屠灭,在很多社会主流讨论上,比如当下瘟疫的讨论,都会经常回避殖民者登上美洲大陆后,屠杀和瘟疫致使数以百万计印第安人的死亡。
绝大部分土著部落已断绝传承,所以相关事实和数据很难考证,是一方面的原因;而整体英美社会在这方面,缺乏对于反文明和野蛮的反思与警醒动力,可能是更本质之因。
这般看来,全球范围内,尤其以近年来愈发明显的中美对抗为主色,这种缺乏警醒和反思的野蛮浪潮,在当下愈渐透出反文明的意味,是有其根源的。
加之网络时代里,戾气、对立和割裂的情绪更加容易释放、激化,这种大势,是否会进一步演变恶化,少有人愿意看到,可恐怕,更难有人可以预料。
03
几年前,我有感觉到,身处的时代,在一个平衡与失去平衡的微妙阶段,我试过描述它,但很难让自己满意。然而眼下的大势,就这么倏如其然的来到了。
当它到来时,我是震动的,有一种强烈的不适。我惶然,我没有找到这种大势下,应如何自处的方式。
人类学家项飚在十三邀中提到“附近”的消失,他说,在他们读书时,有一种自信,可以在“附近”构造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爱,因为那时,与周边的邻里社群,接触的人都会有一种较紧密,较长远的连接,这是构造良好关系的基础。
而随着社会演变,网络时代推进,这种“附近”被消解了,社会变得更碎片化。人际接触,不再是相对紧密长远的,而变成即刻的,就像顾客和外卖小哥那样。这样,人们逐渐失去构造爱的自信,取而代之的,是对于整体抽象社会系统的信任。而这种信任是被便捷性裹挟的,在不断的方便快捷中,只有迅速的获得,才会有满足感。换言之,需要沉思,积淀的事物,变得不讨喜,人们的反思性也很容易减少。
这是很有见地的观点,但我不会全然认同。网格化碎片化的社群空间,的确容易消解构建爱的基础,甚至加剧分化对立;可在过往历史的长久岁月中,人类就真的彼此良好相处了么?
实际上,即便是紧密的宗族和社区中,亲密的家族间,亲友间,都一直以来的,会发生恶意的释放,敌意的对立,甚至残酷的倾轧斗争,这源于人类骨子里必然带有种种欲念和缺陷,也正如前文中,阿多诺所讲反文明与野蛮的根源。
人性一直都是善恶交织的,我想在项飚和许知远读书的年代,正是人类好不容易真正得到大范围和平中的光辉岁月,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更是如此。在一个积极的文明大势下,人们会更愿意展现善,是有信心构造爱的。
而随着社会的演变,人类盲目的一味促成经济、网络与全球化的推进,很多情绪与人性的碎片却在无人注意下,渐渐的积聚起来,终是形成了又一次反文明与野蛮的大潮。“附近”的消失,恐怕只是其中一方面罢了。
如此形势下,不止是我国当局,西方政治势力,以及何伟等旁观者,我想我们有很多的角度都可以发现,人们对构建爱失去信心,转而投到了铁幕与对立中去。
信心纷纷丢失之时,我的那一份同样无处寄予,因为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
在国内,影响力最广的言论者,早已不是“公知”们,而是胡锡进这类人。区别于疫情下暴露出的许多体制内又蠢又坏的无能之辈,这位掌控党宣重要喉舌之一,长达十数年的胡编,毫无疑问是有能力的,极精明的人。而这种精明最厉害之处,就是往往能对民众,掩盖他刀笔吏的本质。
笔下凡事可大可小,从不会缺乏倾轧与斗争之能的刀笔吏传承下来了,而如今,清议读书人却几乎不再有存在的空间。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带有浓烈的西方意味,这在愈显对立的浪潮下,成为被污名化的必然,甚至连写入所谓“核心价值观”的自由、民主都成了人人喊打的对象。
人们选择性的遗忘,就在我们自身的传统中,一样有着清议读书人,对公共领域发出该有的讨论与监督。
国内媒体曾登过一篇美国学者的采访,又在不久后删去,其中戈德曼(David Paul Goldman)讲到,中国目前的执政体制,比起鲜明的意识形态,其实更偏向务实,更像古代官吏集团体制的延续。
而我们的反应是,删掉这样的报道;就像我们保留了官僚,保留了刀笔吏,却删掉清议读书人一样。也许当局以为,这样便不会像古代官吏体制了。
务实是中华民族一大优点,亦是一种难言之隐。因为务实,只要能有一段和平稳定的岁月,中华百姓总是能欣欣向荣起来,这种韧性让许多人惊奇不已。
但国内那么多读过书的人,他们对少数异见者的追猎,那种不断变得更加熟练的斗争和倾轧,这同样都是务实的选择。因为刀笔吏和官僚,正是如今读书人可以汲汲于仕途的前程指引,何不早点练起他们最擅长的技能呢。
对于这种官僚与刀笔吏大行其道,而整体社会仍在大肆鼓励更多的年轻人也走上同样道路的环境,我没有办法感到妥协或亲近。这意味着,我们将与反思和警醒越行越远。
其实不少时候,我非常厌恶国内宣传中的愚蠢和荒唐,就如近年来一种常见的宣称——中国历来是友好的,从未有过扩张心态。
而事实上,不仅如前文中一再提及,中国历史上从未少过斗争倾轧,战乱屠戮之事,鲁迅先生所说满纸都是吃人绝非虚言;
而且,这种官方的愚蠢矫饰,正是一再暴露——国内体制的宣传,完全放弃了一切反思和警醒的可能,深陷可笑的自欺欺人中;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传统中,一直是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类的追求。平天下,就是在讲中国人中的入世者,历来会秉持着一种想要塑造整个世界的期望。而这种入世者又是以政治人士,尤其上层为最的,为了千秋伟业的梦,有一些人,甚至能够不顾逆时代潮流,反人类文明等一切代价。
也许正因为此,我特别羡慕身处港台与海外的评议者们,他们对这一切包藏极其险恶祸心的虚假与丑恶,都可以直言不讳,去正面粉碎、戳破这些卑劣谎言。而在国内重重封禁下的我们,无法做到,更多的只能带着镣铐舞蹈。而很多时候所谓尽可能的表达,只是一种无法直面核心,无法尽述的自我安慰罢了。
甚至有时我会想,这种压抑,这种被迫而不得不的深藏,它能让我的所思所言更凝实么,能成为一种沉淀么——感觉像是自己,在尝试着为这份惊人的压抑找一点意义,真是卑微的可以了。
我非常感谢这类评议者们,他们有的如柏杨,是极强力的,也有如陶杰先生般是颇富才学的,还有很多具深厚媒体经验的如明镜的何频先生等等。他们极大开阔了我的视野,好像可以短暂的解除我精神上的枷锁,那种痛快言说的嬉笑怒骂,有时带给我很大的慰藉。
但我仍无法全然认同,他们对于我们自身民族的批判。
他们的批判态度是坚决的,让人叹为观止。在批判的内容上,有很多部分确实是言之有物的,能引发许多深思。但无论是酱缸说,还是劣根性,或对政体的批判,都具有将一切现实的问题,全归结于一项过于单薄的根源之倾向。而我看来,这更像是一种过于简单和轻易的宣泄。
就像近期陶杰与何频先生经常谈到的,似乎我们国家的斗争倾轧,反人性和文明等特质,都应与中共的政治体制密不可分。可我不仅在久远历史中看到大量的相同景象,更在眼前的世界里,看到仿佛穿越而来的官僚与刀笔吏,看到欧美社会中,也在涌动着反文明的暗潮。这些让我疑惑于他们笃定的言论。
对于一个生在内地,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也在其中生活的人来说,我能明显感到中共体制内那种极纷杂的共融。它于表面上,呈现出一种类似拿来主义的态度,什么好用,便取用什么,所以像戈德曼会讲,这显出一种务实之感——市场经济,推行教育,注重实体经济全产业链,注重科技,追求人性的美好,一定程度的自由,鼓励创新等等,都会被拿来利用,拿来塑造社会。
但所有的这些,绝不会彻底放开严格的管控。这种自始至终紧绷着的管控,是直指操纵与统治的——这并不是以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为核心的,实际中,马克思们也只是被拿来利用、宣传一番的工具罢了——它整体更像是一个对权欲极其迷恋的古代官僚集团的延续。
我能察觉到这种所谓“务实”中的重大隐患,其实欧美社会中,一样存在极多复杂的元素,可中国的问题,是各类执行与宣传都偏向于极致——这是官僚集团体系过于庞大,而行政素质参差不齐,很多地方行政能力都十分低劣,所导致的。若不强力到极致,就无法真的实施。这导致“治大国如烹小鲜”的平衡程度掌控,极为困难。
我们总是看到,许多互相矛盾,会引起人性挣扎撕裂的宣传实施,同在上演,还都要全面彻底的推行,演到偏执的地步,这不仅仅是针对百姓,其实对于中共官员层面是更甚的。
他们一面宣扬着要服务人民,构建美好,强调信仰忠诚,天天进行所谓的学习,自我革新;另一面又是严格管控,人命和人性只是稳定操纵下的棋子,不值一提,一切政治指标都是奔着经济和稳定而去的,沉浸在利欲熏心中的,大有人在,可不论他们内心如何张狂,浸没在钱权欲里,他们偏偏又必须表现得精神廉洁,才有望长久的稳定,太多的个体,都成为言行极度扭曲的人。
这种挣扎,比比皆是——而这些挣扎,与古代中国中,儒家的各角度学说,仁道和王权,立心与利欲,再加以其他各类纷杂学说的纠缠,是很像的;不同的是,当下的这些撕裂乱象中,加入了来自全球的思潮,以及网络时代的一切。
所以中国的状况注定是极复杂的。而一种简单的批判,难以引起足够深远的反思与警醒。这大约是我在一系列强力的批判者中,难找到足够认同感的原因。
我甚至没有办法像何伟那样,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和现实差异是横亘于前的,我无力轻易的跨越。
我会发现,还是许知远、梁文道这类的读书人,或像许倬云、陈嘉映一类的学者更让我心生亲近。他们会有一类共同点,对于外物的接收和评价,似乎会显得迟缓,他们不太轻易的去下断语,而总是愿意关注与思索着事物的复杂性。
他们心念间有着执着,也能看到广阔的高速流转的外界。他们倾向于选择一种似是慢吞吞,钝钝的方式,却始终在回应着自我与时代的一切。
由内而外,这些都透出着一种执着与平和的相衡,让我极为向往。
但同时,他们的犹疑,始终保持开放的不定态度,也会一直提醒着我,或许我和他们可以算作同道者,但每个人需要面对的犹疑和不定,天性和现实都是不一样的,终是很难成为同路人的。
我必须意识到,自身的面前,是一条孤寂的路。
就在这几日,我偶然间看到韦政通先生及其思想和文字。网络上登载有限,我没能全面的了解,但我触动于这样一段往事——金岳霖之徒殷海光,于韦先生是亦师亦友的。殷先生曾对他说:“你啊,就好像一块孤炭,你一个人可以发光的”,这后来成了韦先生长久的鼓舞。
韦先生去世于2018年,编辑和好友们为他的遗世之作取名《异端的勇气》。他写过“我爱异端”等一系列文章,来讲述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他相信知识分子有着自己的社会见解,学术思想与人生选择,若要选择忠于自己的判断,自然很容易被当作异端。而韦先生用他91岁的一生,堪称离经叛道的人生旅途,证明了他对成为异端,是全然不惧的。
他写到:“人生要有意义,就是要走自己的路”,“活在当下,可能是生命学问中唯一绝对的真理”。
我没能看到全本,如今之势,这样的繁体书,不知何时才能买到了。可即便只言片语,已蕴藏着极大的力量与慰藉。
我大约是没有孤炭的天赋的,或许也没有异端的勇气,但我渴求意义和自由,我决不愿活得扭曲的。即便在这倾世之势,仍想汲汲于一种平衡,异常艰难,我也需要走下去。
想到另一位执着的读书人唐诺,讲到他最触动的一幕,是博尔赫斯在晚年时候来到撒哈拉沙漠,他抓起一把沙,对旁人说,看,我在改变撒哈拉。
也许,我也处在,隐藏着难以想象的狂暴,不可捉摸,更无从相抗的撒哈拉中,可我仍要抓起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