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德侯爵《歐司田,或放蕩之災》:道德是一種勇氣,而非規範
簡介
薩德的《歐司田,或放蕩之災》講述的是一個壞心眼的伯爵想要害死自己強暴的女孩 — — 艾涅斯婷 — — 但最後沒有成功的故事。然而,透過這則故事,我們與其說放蕩之災是指伯爵 — — 歐司田的放蕩與邪惡,不如說,「放蕩之災」,是在指縱慾過度的權力體系所導致的災害。

這個權力體系,在故事中透過不同的角色 — — 他們不斷阻擋艾涅斯婷為自己復仇的想法和舉止 — — 來反映他們的影響。比如說最常出現的,就是他們在一開始都希望艾涅斯婷就這樣嫁給玷污自己貞操的伯爵,來挽回所謂的「聲譽」。
薩德曾說:「我是一個被攝政王毒害的世紀之子。」這句話反映了十八世紀貴族們的生活有多麼的放蕩與淫靡,在當時,這樣的習性、生活方式甚至被認為是貴族應培養的「嗜好」或「特質」。就像馬術一樣。而「道德」,則被拿來利用,馴化一般平民百姓,讓他們順服上層人士,甚至不敢對腐敗的政權發起革命。
這或許也是為何薩德的很多作品,常常出現反「道德」思想的緣故。在這些作品裡,守貞、反對暴力、不願同流合污的婦女或是人士往往下場悲慘,尊循惡道、作惡枉法之人則處處得勢。其中,最能代表的作品便是惡名昭昭的《索多瑪一百二十天》和《貞女的厄運》。
這也使得薩德的小說在那個時代被視為是不道德的小說,是敗壞風俗的禁書。而在現代,研究薩德的人或許會幫薩德做出一種辯護:薩德之所以寫出這樣的小說是出於對那一時代一種不得已的反抗,因為在那一時代,事實就是如此。正如薩德的另一句話:「一部最能反映社會風俗的作品,也或許是最引人入勝的作品。」更有甚者會認為,薩德的書寫正是一種揭露政權虛偽的革命書寫。揭發政權、宗教底下各種不義的舉止。
然而,《歐司田,或放蕩之災》這齣劇本,讓我們不得不去重新反思薩德對道德和「惡」的想法。因為這個劇本有太多和薩德其他重要作品完全不同的地方。首先,這個作品沒有色情和施虐的描寫,和薩德作為一個色情作家的形象有很大的差別,相反地,處處充滿了道德的勸諫,因為幾乎所有的角色都在勸告伯爵不要繼續他的惡行,並歌頌美德的舉止。再來,是這部作品中對女性主角的描寫與定位,以往,薩德作品中的女性不是卑微、屈服權力而被虐待的女奴,就是和邪惡同流合污,一起作奸犯科的女鴇。但文中的艾涅斯婷不但沒有遂了伯爵想要娶她入門的意願(這同時也是劇中其他角色 — — 例如女僕 — — 給他的建議),還計畫跟伯爵來一場堂堂正正的決鬥。最後,是這個劇本的結局:放蕩子失敗被殺,捍衛自己的美德獲得勝利。讓人完全無法想像這會是薩德所寫的作品。
一個最簡單的解釋方式是:這部作品要問的問題和其他部不一樣。如果說薩德的其他本作品是為了諷刺、批判和彰顯權力的邪惡以及他們常常散佈、宣傳的道德教育是多麽虛偽,那麼這個作品要問的問題便是:如果我們已經知道所謂的道德常常是權力灌輸給我們的陰謀(規範),那我們要如何面對發自內心的良知?特別當我們看見身邊正發生著許多罪大惡極的事?
道德掙扎與權力的陰謀:罪與罰的不對等
在這齣劇本裡,所有的角色都在面對道德掙扎。然而,我們要注意到,這種道德掙扎和一般我們在倫理學所看到的電車議題等道德議題不一樣,他們不是在比較哪一種行為才是正確,或比較正確的。相反,他們多數早就知道哪一個抉擇是符合道德的,只是他們在考慮的是,是否自己要為了良知和權力體系做抗爭。
我們可以看到,《歐司田,或放蕩之災》裡所描述、定位的道德地位,和薩德其他部批評道德觀的作品不同,在這裏,道德的認知、想法帶領人們反抗權威,而非讓人對權力的壓迫變得軟弱、順服。這種轉變,或許和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有關,因為這場革命除了讓薩德能從巴士底監獄重獲新生,回到生活。也扳倒了當時腐敗的政府。並讓他在1790–1791間寫出這齣戲劇。
不過,有意思的是,《歐司田,或放蕩之災》的原著小說 — — 《艾涅斯婷》,是薩德在被關在巴士底監獄時寫出來的。兩者在劇情雖然有相似的角色結構跟情節,但整體而言,兩者的差異十分巨大,小說不但細節複雜,牽涉到不同的時空背景,最重要的結局更是完全顛覆我們對改編戲劇和薩德本人的想像。
在《艾涅斯婷》裡,女主角沒有復仇成功,相反地,歐司田的詭計得逞,讓艾涅斯婷的情人赫曼不但被設計成功,判處死刑身亡,自己也被自己的上校父親誤殺。成了一場徹底的人倫悲劇。至於這位伯爵,雖然詭計得逞,但仍然被送上法庭判處流放。雖然悲慘,不過事情發展成這樣,倒還符合我們對薩德在其他作品的印象,但更弔詭的就是這部小說到這裡並沒有結束。在流放了好幾年後,艾涅斯婷的父親竟然選擇原諒、寬恕這位伯爵的罪過,幫他跟國王要到了赦免狀,還他自由之身。至於為什麼,上校這樣說:「一個人蹲監獄,就彌補得了他給社會造成的損害?假如想讓他補償,就應該給他自由,而不要他永遠生活在囹圄之中……你走吧!你自由了……先生,你用不著感激,這樣做只是為了我自己。」
上校甚至說了這樣的話:「『唉,美德呀!』他有時叫道:『也許所有這些事情發生,正是為了歐司田回歸你的聖殿所需!真是這樣的話,我也得到了安慰,因為此人的罪刑只是給我痛苦,而他的善行卻給予所有眾人。』」。
為什麼上校會認為監獄的關押不能彌補伯爵的罪過?理由大概有兩個。其一,是因為薩德關押在巴士底監獄的漫漫長日,讓他徹底見識到國家底下更巨大的黑暗和邪惡。因為在監獄裡,獄卒們對待囚犯的方式,就像薩德的許多作品中所描寫到的虐待。加上那個地方環境極差,充滿了耗子和噁心、早已過期、腐壞的伙食。獄卒甚至會用他們的伙食或是否幫忙寄信件的服務來威脅囚犯,命令他們做出逗弄人的舉止等等。更恐怖的是獄卒可能不告訴他們什麼時候是他們的死刑日期,讓他們每天皆活在龐大的恐懼裡,不知哪一天自己即將面臨死期。所以薩德曾經說:「監獄不但沒有讓我變好,反而讓我變壞了千百倍。」因為一但你進入了裡面,承受完各種巨大的精神壓迫,出來後,除了不時湧現的痛苦回憶,你也可能嚴重喪失你對他人和社會的信賴。
薩德反對監獄第二個理由,是因為監獄乍看雖然是懲罰罪犯罪行的所在與刑責,但實際上,監獄扮演的功用恰恰是藉由把所謂的「罪惡」轉化成一種交易,透過關押的懲罰去抵銷過去的罪行,進而讓罪犯不用好好省視自己的行為,只需要接受懲罰就好。也就是說,對薩德而言,監獄透過不停強加的懲罰,剝奪了人去和自己的惡思辨的權利。甚至讓人不用真的認真看待與背負自己過去所做出的惡行。
這種感覺類似很多人求學時被老師罰寫的經驗吧。只要把罰寫的項目趕快寫完,就沒事了。至於自己當時到底做了什麼事被老師懲罰,恐怕早就不在意了,反正已經被罰寫了。
這樣的想法讓人聯想到另外一個人所寫的另外一本小說。是十九世紀的俄國作家,叫做杜斯妥也夫斯基,他寫的那本小說則叫做《罪與罰》。這本小說的主角叫做拉斯科爾尼科夫,是一個貧困休學的學生,由於繳不出房租,他在憤恨之下殺了一直以來他十分厭惡的經營當鋪的老婦人和她不小心目擊事件的女兒。事發之後,警察抓了一些嫌疑犯,不過並沒有抓到拉斯科爾尼科夫,這讓他覺得奇怪,因為在那樁犯罪裡,他並沒有周全地事先做好任何防護措施,所以他覺得自己應該很快就會被抓到,導致他還沒被警方面談前就緊張萬分。但更荒謬的事情來了,在被警方抓到的嫌疑犯裡,竟然有人自稱、自白那件案子是他犯下的。你可能會以為對主角來說,這難道不是美事一樁嗎?但事實恰恰相反,這個消息不但沒有讓主角開心、鬆了一口氣,甚至讓他面臨更大的恐懼跟不安。除了一方面是他覺得自己不但殺了兩個女人,又害到一個無辜的人去頂替自己的罪罰讓他良心不安,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他一直在害怕、擔心這個消息其實是警方所策劃的陰謀,他們早就鎖定他了,並派人監視他,觀察他是否有良心不安的舉止,例如他有多少個晚上睡不安穩,或是有多少次他食慾不振?並測量他需要經過多久的時間才選擇自首,進而決定他的刑責有多重。這些由自己所想像出來的「監視」日夜不停地折磨我們的主角,讓他不停地在街上失魂地遊蕩,去想自己做這件事情,究竟是否真的是自己的罪惡?還是是社會環境的壓迫讓他不得不如此?這些事情的思索與思辨將決定他是否要去自首。
這個故事的內容,或許過於誇張了。不過他除了讓我們注意到一種犯罪的心理和思維外,也讓我們看見道德真正同時也是最可怕的力量:自我監視的體制。另外一方面,這則故事的內容揭示了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終其一生都在探討的一個問題,或者說,一個矛盾:為何有人犯法了,雖然願意接受懲罰,卻不認為自己有罪?而有人即便沒有犯法,卻產生極大的罪惡感?換言之,為何「罪」與「罰」的關係,在人的內心裡能這麼地不對等?
慾望與道德的關係:權力
如果我們回過頭來看《歐司田,或放蕩之災》這齣戲劇,我們會驚訝地發現,其實 — — 真正的道德之所以產生並得以運作,關鍵便是「罪」與「罰」不對等的關係,因為只有這裡面的角色每個都深深感受到心中的「罪」與外在的「罰」無法取得平衡的矛盾感受時,他們的道德意識才能被喚醒和激發。可以說只有在經歷這種矛盾的時候,人們才會思考道德對他們而言的意義。
「罪」與「罰」的不對等,反映的其實是一個權力不對等的問題。在這齣戲劇中,儘管做惡事不對的,但沒有人會因為同流合污而受到懲罰,相反的,還可能跟著伯爵享受到不少好處;但若是為了心中的道義反抗伯爵的意志,除了可能得承受無法反抗成功的風險,還可能受到朝廷、社會階級等權力單位的壓迫,流落更慘的境地。這也是為什麼艾涅斯停在結局的時候必須策劃一場對等的決鬥。
這一場權力對等的決鬥,其實是一個勇氣的考驗。可是我們要注意,他考驗的不是只是艾涅斯婷的決心,同時對歐司田而言,也是一個機會提供給他去面對他對愛涅斯婷的情感。因為從其中一場獨白戲中,可以發現即使是扮演壓迫者的伯爵,本身其實也是一個被權力壓迫甚至監錮的人。他的詭計多端反映的與其說是一種邪惡的心思,不如說是因為對愛感到膽小和缺乏勇氣,而只好仰賴權勢的手段來強暴與逃避他對艾涅斯婷的情感,並乾脆將自己定義成所謂的惡人,這樣就不用進行可怕的道德掙扎,不用對自己衝動的行為感到後悔。
對薩德而言,人一直存在著一種為惡的本能,這種本能可以說是人的慾望裡含有的一種成分。就是想要獲得權力,或者想要依賴權力的傾向。這樣的傾向即便透過理性、啟蒙、科學仍然難以根除,甚至有時還反過來被這個傾向利用,仗勢欺人,進行更龐大的屠殺與獨裁統治。而這種傾向也正是劇中所有的角色都在抵抗、掙扎的。
或許,在薩德的想法裡,真正的道德只會誕生在反抗權力的勇氣中。他之所以在許多小說或論述裡批評道德,並不是因為他反對道德或是善,而是因為他討厭那些把道德看作規範、看作一種為了順服命運的處世態度的想法。因為對那一個受到宗教影響的時代來說,「道德」常常最後是要人們逆來順受,假裝惡有惡報、善有善報是世界運行的法則,或者讓人們認為所有的不幸都是為了死後上天堂的修煉。卻不教導人應該要學會為自己反抗,去學會在批判中認同自己。
道德是一種勇氣,而非規範。這並不是在說,人不應該用道德來規範自己。而是在說,人不能把道德的規範當作死硬遵守的規則。因為一旦道德成為一種規則,便有可能被權力的慾望、本能拿來利用,阻礙人們對自己的認同,甚至無法對自己的遭遇形成反思。使道德淪為邪惡的酬庸。
筆者以前上完課回大學宿舍房間休息時,常常遇到一個問題。他總是很難明白為何他的室友總是要把他搭電梯的行為(房間在四樓)視為一種懶惰的象徵。只要電梯不是剛好在一樓,室友就會選擇走樓梯,至於他則在一樓慢慢地等電梯(哪怕電梯要從十樓下來)。並接受室友開的玩笑:「你很懶誒~這點路都懶得走!」「明明就你們懶得等!!!」他總是這麼回應。搭完電梯回到房間後,早就在房間的室友又會繼續開玩笑:「搭什麼電梯!你看我用走的都比你快!」,「嘛~搭電梯是省力氣又不是省時間嘛~又不趕時間。」
日子慢慢久了,就開始好奇:為何人們判斷懶惰的標準是透過走多少路、用多少力的勞動,和達到目標的速度來決定的呢?而不是看一個人願意花多少時間來等待,甚至品味一件事呢?這個疑問,直到看了米歇爾.傅柯的一本書才得到一些些解釋。
米歇爾.傅柯在《懲罰的社會》(或者另一本比較有名的書:《規訓與懲罰》)裡寫到,在工業革命以前,人們對懶惰的觀念和現在大有不同。在還是農業生產為主的時代裡,人的作息是配合作物生長的作息,也因此,一個人如果被認為是懶惰的,那麼大概是因為他從事農作的時間並不符合作物生長的作息。這樣的想法後來對開設工廠的資本家造成了困擾,因為如果人們當時對「工作」的想法是如此,那要如何說服他們在以前不是工作的時段裡留在工廠裡工作呢?
傅柯在研究這些歷史資料時發現,恰好就是在工業革命,工廠開始林立的時候,誕生了接近現代體制的教育體制和學校。這些學校不完全是政府辦的,甚至有很多是資本家主動贊助和興辦的。同時,傅柯也注意到,也就是從這個時期開始,學校和人們開始教導、傳播和現代較為相像的道德價值,其中包含懶惰、節儉等等。而定義懶惰的方式,便是測量一個人完成事情的速度與效率。
從這點來看,慾望和道德的關係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複雜,一般來說,我們總是以為道德的產生是為了規範人的慾望,但實際上,有時,道德反過來是被慾望所產生、所運用的。而且我們會發現,在不同時代,一當人們對可慾望的事物有新的見解時,道德的體制也會跟著翻天地覆。
道德中的暴力 與 暴力中的道德
《歐司田,或放蕩之災》的原著小說《艾涅斯婷》在剛出版的時候,曾經遭到批判,認為他寫的這本小說不道德。過沒幾天後,薩德就在報紙上回應這樣的批判,他首先說:「我從沒寫過不道德的小說,今後也不會寫……」,接著他談論到他對小說的想法:「要能夠讓小說、悲劇引人入勝,不必總是設法使美德高奏凱歌……相反,只有當美德受到侮辱、遭到不幸,美德才更加吸引人,更加美麗。……韋勒泰爾克(在報紙上批評薩德作品的人)大概是個不講道德的人,所以才不懂得人們是怎樣崇拜美德的。」
只有願意認識人類罪惡的一面,並承認人的慾望對自我的建立、生存有重要、不可抹滅的作用,才有可能激發一種真正對道德的渴求。這樣的說法相對於一種假的道德,這種假的道德就像一種蠻橫的權力一樣,要求人們只能根據他的內容去形塑的自己的認同、自己的渴望,並否定越「權」的思考。他批判韋勒泰爾克的地方就在於,韋勒泰爾克把道德當作一種理想生活的形象來遵從的想法,而不是把道德視為一種觀點,回來認識自己進而批判社會的方式。
最後一個在這齣戲中可以討論的主題,是暴力。
如果我們認同艾涅斯婷想要以決鬥的方式去表達自己的反抗,或者劇終赫曼對歐司田執行「正義」的私刑,這會碰觸一個疑慮,也就是暴力這個議題。因為直到今天我們都認為,使用暴力是不對的。那麼我們可以說愛涅斯婷的決定 — — 哪怕是具有勇氣的 — — 仍會是道德的嗎?
羅洛.梅寫過一本書叫做《權力與無知》,這本書表面上談的是權力,和人們的無知,實際上他真正要談的,是關於副標題的內容:為什麼人會有暴力。也就是暴力在人身上的根源是什麼?
羅洛.梅的想法是,暴力的某些要素是人不可或缺的,因為暴力的產生和人想要獲得認同的心理有關。也就是,當一個權力體制不認同某些群體、或是某些個人的時候,一當人的忍受力達到一個極限後,暴力就會產生。
「只要人們不受重視,就會有暴力的動亂。每個人都會有受重視的需要,如果社會不能實現此一可能,那麼人們就會透過破壞的方式取得。」
另外一個薩德反對道德作為一種規範的原因,或許也在於此。他並不是討厭道德的理想,而是反對道德裡將暴力視為不道德或非人性的想法。對他而言,暴力並非不道德,相反,暴力是人性中非常重要的一種表現。或者,就算暴力是不道德的,他也是人生而不可或缺、至關重要的人性,但許多道德思想的灌輸,都試圖要人們忽略、漠視甚至否定自己內在的暴力經驗、暴力想法,但他們不知道的是,只有知道自己擁有多可怕、多深層的暴力潛能,你才能知道你 — — 作為一個人類 — — 可以擁有多大的自由和可能性,以及可以擁有多大的權利去決定自己的生活和幫助他人。
辯證:真正的惡/真正的善
甚至,我們可以說,對薩德而言,其實世界上最不道德的事情,就是以道德的名義去要求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情況下都應該保持理性、保持善良的規範。因此薩德才會說上帝其實是真正的惡魔 — — 也就是一個蠻橫的獨裁者。原著小說《艾涅斯婷》的結尾,上校說他的寬恕是為了他自己,而不是為了伯爵,是因為真正被上校寬恕的並不是伯爵的罪惡,而是上校認為人不應該產生暴力、邪念的想法和認知。而所謂的罪惡,相反地,沒有被赦免,而是被還給犯罪的人,這意思在於:只有犯下罪行的人才能對自己做出真正的懲罰,因為只有如此,一個罪人的悔悟才能把自己心中對自己罪惡的不停譴責,轉化成不停行善的懲罰。
真正的道德將行善作為人的懲罰,作為和惡相處的方式,而不是遠離惡的途徑。這種想法在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中也看得到,他們都認為只有人在明白、意識到自己從來就不是完善、完美的物種,且也知道不論行多少善事也永遠到不了那種境界的時後,他們才會知道什麼才是行善的意義,並願意持續下去這種能夠被真正稱為「信仰」和「人的尊嚴」的事物。
所謂的惡是人作為生物的自然本能嗎?也許是,至少在薩德的書寫裡,惡的本質常常和他所稱呼的「自然」有著密切的相關。也因此對他而言,文明和各種啟蒙哲學家所認為潛藏在野性中的罪惡,是一種一直被誤解的力量。這種力量在平常的時候幫助人們生存,甚至幫助人們發展自己的欲求和野心,但一當陷入困境就就只能化身成罪惡的樣貌。
要說這樣的東西是罪惡的,薩德或許無法有意見。但他看不下去的是,人們把這種誤解當成真正的道德知識來理解,甚至藉由曲解,想辦法讓人認為出現哪些行為的人就是惡魔、就是不是人。因為所有被稱為罪惡的事物,源頭都在人們共有的自然本能裡,只是有沒有被喚醒而已。而就像斷頭台、監獄、機槍、導彈、核子彈的發明一樣,「社會實際上只是在用更大的惡去對付惡」,卻以國家、法庭等機構宣稱這是正義。薩德由此認為,這種假裝自己根本不邪惡、不野蠻的道德認知,才是真正最恐怖的邪惡,因為他背後常常就是所謂腐敗的權力和徹底無知、裝單純的偽善。
有一個親戚,一直很難理解為什麼人會有憂鬱症。因為對他而言,人只要放下執念,不要有那麼多欲求,就不會有過多的煩惱。簡單過日子,以「單純的心」,全心信仰上帝,並學習樂觀就能過好日子。這樣的「善」正是薩德厭惡的。因為這樣的善要求人們假裝惡(也就是各種對人生負面的東西)根本不存在,只要「單純」、不要在意自己的渴求,一切就會消散。以為人之所以有各種煩惱,都是因為慾望太多、不夠單純。
「生命是善惡的混合;沒有純粹的善這回事;因為如果沒有惡的潛能,也就沒有善的潛能。這就是人的經驗之所在。人生不是脫離惡,才成就善,而是雖然有惡,依然為善。」
在這兒,羅洛.梅對善惡的想法,或許過於正向。但似乎可以和薩德有些呼應。因為對薩德而言,人對道德的追求,並不是完善自己,而是透過道德的探尋,回來面對、認識和理解自己內在難以被控制、同理、想割捨又無法割捨的部分。進一步說,追求道德,就是去理解所謂的惡,所謂被人們認為負面的事物,而不是假裝遠離他。因為事實上如果道德和一種勇氣、反抗相關,那麼他必然需要一種「惡」的潛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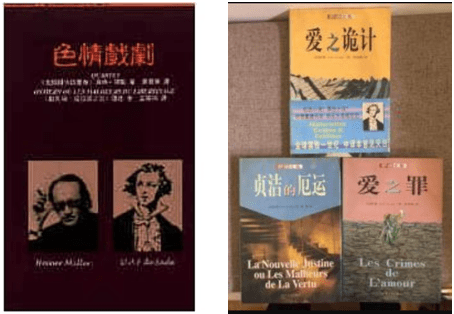
(原文刊載於部落格:文學實驗室)
Medium:https://medium.com/@f0921918962
方格子:https://vocus.cc/1111/ho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