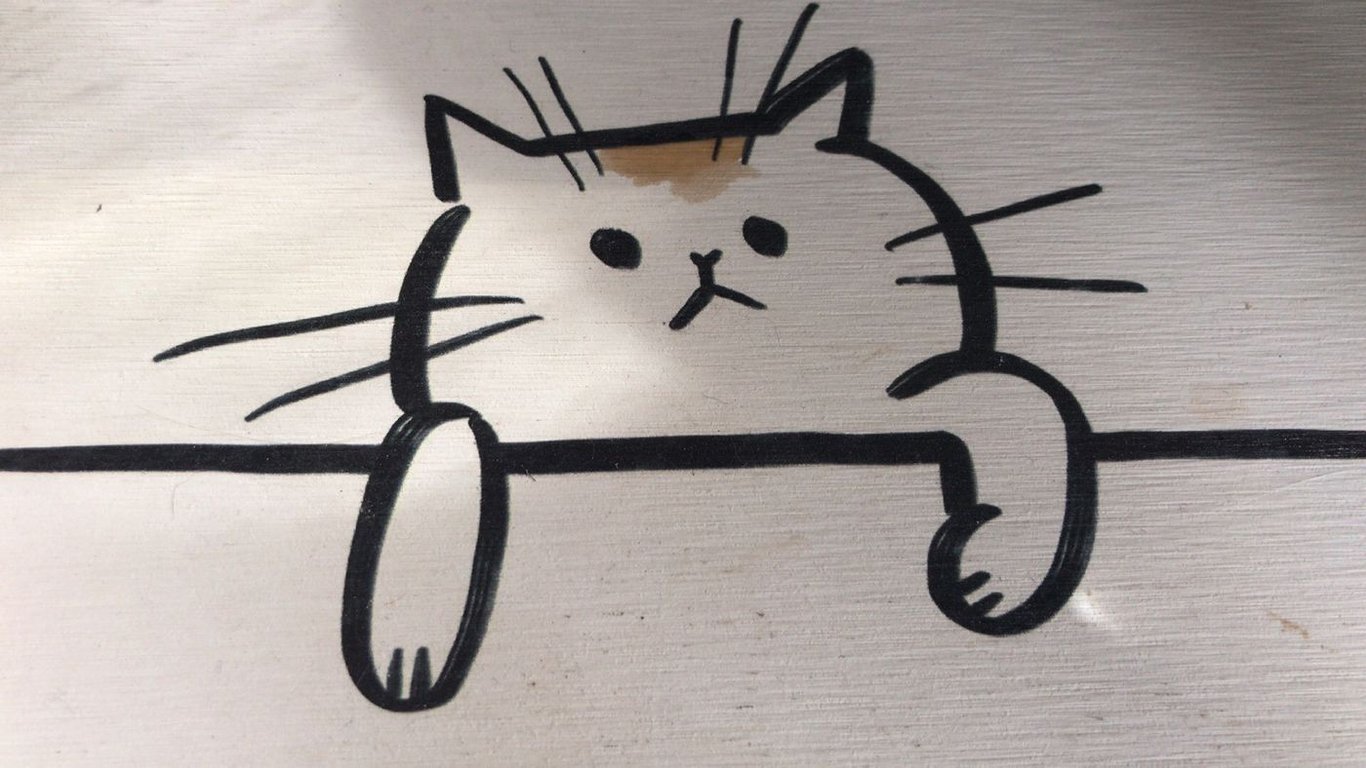群豪与皇帝:《天龙八部》讲了一个失落的常识
暑假重读《天龙八部》(新修版),忽然觉得这是一部直指当下的启蒙之作。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这回重读特别注意了一个隐藏角色。这人姓群名豪,出场时一般叫做“群豪”,有时也叫做“群雄”。
但凡读过金庸的都能认出这个角色——比如群豪道、群豪齐声应道、群豪心想,群豪惊呼、群豪轰然叫好、相顾失色、面面相觑以及一惊而醒,诸如此类。
这角色也常分饰多角,比如有一人忽道,另一人道,有时也附身在有名有姓的代表身上。不过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常常化为同一人物代称,或影视剧里的群演,面目模糊,藏得很深。
《天龙八部》里的群豪尤为重要,发言甚多,声势最壮。可以说有群豪,才有萧峰——群豪膜拜萧峰,冤枉萧峰,围攻萧峰,想要杀人,还想要诛心,直接酿成了聚贤庄惨案和少林寺大战两起重大群体事件,最后引发雁门关辽宋边境战争。
试着梳理萧峰事件,很容易发现其中有着十分令人眼熟的发展模式——
一则传言出现,很快破圈成为热点事件,群豪震惊,先声讨后围剿,扒皮的扒皮,预言的预言,事件扑朔迷离,受害人众多。有人幕后主使,有人推波助澜,有人随波逐流,有不明真相者,更有无辜牺牲者,恶人隐匿,小丑跳梁,当事人深陷泥潭,迷惘连连。待到结局反转,群豪再次震惊,一切竟源自某个人散布的谣言。但此时悲剧已然发生,朝廷也对此事定了调。
如果试着像读鲁迅一样读《天龙八部》,不难发现金庸在小说中在群豪身上传达给我们的启示可谓用心良苦,不亚于鲁迅的杂文。
1
先看丐帮群豪,其特点是简单粗暴,胡搅蛮缠。
全冠清煽动谋反,在杏子林中开公审大会,是因为有个传言已经激起了水花:乔峰(即萧峰)是契丹人。因此即便全冠清人被制住,仍敢大声指责乔峰,说你现在还没对不起兄弟,但很快就要干了。接着更推论出乔峰是杀人凶手——乔峰视马副帮主为眼中钉,总觉若不除去,自己的帮主之位便不安稳。依据便是他尚未完全证实的结论:乔峰是契丹胡狗。
这是车轱辘推论,但符合群豪心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众所周知,讲出身的强势逻辑是群豪上纲上线的理论基础,胜在简单,但经不起细究,一细究便会走向粗暴。
智光大师讲述往事,说听到契丹武士(萧峰生父)抱着妻子痛哭,心中难过,意外发现“辽狗居然也有人性,哀痛之情,似乎并不比咱们汉人来得浅”。
赵钱孙则进一步修正,说辽人也是人。
就有群豪代表叫了起来——
辽狗凶残暴虐,胜过了毒蛇猛兽,和我汉人大不相同。
智光大师说自己不忍心杀契丹婴儿(萧峰)时,马上又有代表反驳——
……我亲眼见到辽狗手持长矛,将我汉人的婴儿活生生的挑在矛头,骑马游街,耀武扬威。他们杀得,咱们为什么杀不得?
乔峰甘愿交出打狗棒时,其支持者与反对者进行了一次试探性的辩论。
——我瞧乔帮主不是契丹人。
——何以见得?
——我瞧他不像。
——怎么不像?
——契丹人穷凶极恶,残暴狠毒。乔帮主却是大仁大义的英雄好汉。适才我们反他,他却甘愿为我们受刀流血,赦了我们背叛的大罪。契丹人那会如此?
——他自幼受少林高僧与汪帮主养育教诲,已改了契丹人的凶残习性。
——既然性子改了,那便不是坏人,再做咱们帮主,有什么不妥?
其实辩论到此已经快跳出简单逻辑,提出新辩题:一个人的好坏和出身有关系吗?但群豪哪会深究?深究了就不是群豪。
群丐随即分两边站队,内讧一触即发。
为什么会这样?后来的情节告诉我们,指控乔峰杀人,是全冠清、白世镜、徐长老为了色欲和名声的栽赃,心中有鬼,自然要胡搅蛮缠。
但真相大白时,群豪却又开始细究了。
吴长老认为丐帮向来光明磊落,不能冤枉好人,立即有人跳出来说,提出新概念。
——咱们见事不明,冤枉了乔峰,那不错。却不能说冤枉了好人,乔峰难道是好人吗?
接着便有人顺势推导,又把话绕了回去。
——对啊!乔峰是契丹胡狗,是万恶不赦的奸贼,冤枉了他有什么不对?
好人还是坏人,不在他做没做坏事,仍在于他是否异类。受害人不完美,便仍值得批斗。很快,大家异口同声,得出合理结论。
——各位兄弟,乔峰是契丹胡人,那不错吧?可没冤枉他吧?
——是丐帮的声名要紧呢?还是乔峰的声名要紧?
——当然是丐帮的声名要紧!
这番话乔锋全听在耳中,岂能不有恍然大悟之感?国事是大事,帮派事务是大事,基本是非和个人情义是小事,绕来绕去,雄辩滔滔,到头来是为了名声——所谓大义不过是与禽兽无异的强者逻辑,简直狗屁至极。
2
再看聚贤庄群豪,其特点是先声夺人,强词夺理。
丐帮审判萧峰时,不敢动手,是因为打他不过。聚贤庄群豪规模远超丐帮,因此一上来就给萧峰定了性:武林中新出的祸胎,人人得而诛之。
这么多英雄是如何一时间聚集的呢?金庸写了个很有意思的细节。说大会召集者自己名头不响,怕叫不来人,便在请帖里署上了薛慕华的名字,还特意备注他就是知名的薛神医。江湖上谁不想结识神医?故蜂拥而至,可见多是势利之徒。
乔峰为给阿朱治伤主动来到聚贤庄。群豪见他驾了辆骡车不由猜想:是毒药炸药?是毒蛇猛兽?还是薛神医父母妻儿给他抓了?
岂料车中走出个小女孩,既不美貌(易容了),也与乔峰非亲非故。
契丹人哪能这么讲义气?群豪无语。
待到双方动起手来,场面一度尴尬。
少林高僧使出大宋国字号功夫太祖长拳,乔峰也以太祖长拳迎战,且打得更漂亮。群豪竟忍不住喝彩了——可怎能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政治不正确。
乔峰眼看要赢,有高僧叫道——
你这契丹胡狗,这手法太也卑鄙!
乔峰回应得理直气壮——
我使的是本朝太祖拳法,你如何敢说太祖“卑鄙”?
高僧干脆直接上手,使出少林绝技天竺佛指。乔峰抓住逻辑漏洞反问——
你以天竺胡人的武功,来攻我大宋太祖的拳法。倘若你打胜了我,岂不是通番卖国,有辱堂堂中华上国?
这一问逻辑严密,铿锵有力,群豪心中一动:天竺契丹都是胡人,咱们怎么厚此薄彼呢?不过,群豪最擅长自圆其说,心想——
嗯!这两种人当然大不相同。天竺人从不残杀我中华同胞,契丹人却暴虐狠毒。如此说来,也并非只要是胡人,就须一概该杀,其中也有善恶之别。
接着忍不住又想——那么契丹人中,是否也有好人呢?
再看辩论中乔锋如何攻击对方的逻辑漏洞——
你们说我是契丹人,乔三槐老公公和老婆婆明明是汉人,那便不是我的父母了。莫说这两位老人家我生平敬爱有加,绝无加害之意,就算是我杀的,又怎能加我“杀父、杀母”的罪名?玄苦大师是我受业恩师,少林派倘若承认玄苦大师是我师父,乔某便算是少林弟子,各位这等围攻一个少林弟子,所为何来?
少林高僧气得不轻,指责乔锋强辞夺理,居然也能自圆其说。
乔峰道——
若能自圆其说,就不是强辞夺理了。你们如不当我是少林弟子,那么这“杀师”二字罪名,便加不到我头上。你们想杀我,光明磊落的出手便了,何必加上许多不能自圆其说、强辞夺理的罪名?
对于群豪的心思,乔峰已心如明镜。不过这并非他的胜利,而是不得不陷入对方逻辑。这正如鲁迅曾说,所谓“辩诬”,你只要去辩,就已经着了对方的道。你若理亏了,就是承认罪过,你若有理了,对方就动粗。
群豪阵仗都摆出来了,却输了场面,于是恼羞成怒,群起攻之,一名代表这样呼吁道——
管他使什么拳法,此人杀父、杀母、杀师父,就该毙了!大夥儿上啊!
为了尚未证实的事情,直斗得血光四溅,脑浆迸裂,酿出惨烈祸事,没仇也真成了仇——祸胎究竟是谁?
3
契丹人中也有好人,这难道不是再简单不过的常识吗?
群豪显然并非智商不够,而是被猪油蒙了心——丐帮长老指责别人和自我批评时最爱用这个比喻。新修版中金庸特意详解了佛教三毒“贪嗔痴”,说得不仅是“有情皆孽”的主角,也是盲目的群豪。
萧峰为阻止战争自尽,在场的群豪已是“中原群豪”,性质很接近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的“低声议论”几乎有了鲁迅笔下看客的影子。
——乔帮主果真是契丹人吗?那么他为什么反来帮助大宋?看来契丹人中也有英雄豪杰。
——他自幼在咱们汉人中间长大,学到了汉人大仁大义。
——两国罢兵,他成了排难解纷的大功臣,却用不着自寻短见啊。
——他虽于大宋有功,在辽国却成了叛国助敌的卖国反贼。他这是畏罪自杀。
——什么畏不畏的?乔帮主这样的大英雄,天下还有什么事要畏惧?
群豪当然不知道,萧峰是大英雄,更有大慈悲。他最怕的是无冤无仇的人相杀相害。他的噩梦是辽宋大战,“无数男女老幼在马蹄下辗转呻吟,羽箭蔽空,宋兵辽兵互相斫杀,纷纷堕于马下,鲜血与河水一般奔流,骸骨遍野……”
当年在少林寺遭群豪围攻时,他要护着段誉。段誉说,你不用护我,他们和我无冤无仇,如何便来杀我?萧峰苦笑,甚感悲凉——
倘若无怨无仇便不加害,世间种种怨仇,却又从何而生?
他曾处理丐帮叛乱,聚贤庄战群雄和平定辽国内乱,深知群豪最易盲从,人越多越是无头苍蝇,越想跟随有权有势的强者。比如他助辽帝平叛,于万军之中拿住对方首领,不是他学会了挟持的阴险手段,而是认清了谁是一呼百应的有权势者,用个人能力改变权力的运作方式。
那些期望一呼百应的人,自然也懂这个道理,甚至更懂。萧峰的战争噩梦恰恰是他们的美梦。这种人往往出自群豪,他们的智力武力位于金字塔顶端,比如一心只想做皇帝的慕容复。
慕容复是绝对的伪君子和投机分子,脑中充斥政客手腕。他大事小事都从功利出发,一切人都是他的手段。三十六洞七十二岛的群雄召开造反大会,商议革了天山童姥的命,抓了个小女娃娃(众人不知她便是童姥),要当场杀了。
—— 众家兄弟,请大家取出兵刃,每人向这女娃娃砍上一刀,刺上一剑。这女娃娃年纪虽小,又是个哑巴,终究是缥缈峰的人物,大夥儿的刀头喝过了她身上的血,从此跟缥缈峰势不两立,就算再要有三心两意,那也不容你再畏缩后退了。
这是群豪彼此心知大家都有贪生怕死临阵退缩的倾向,要立下投名状,人人都有进无退,却并不管这么欺负一个女娃是否讲道义。
这时段誉提出抗议,骂群豪卑鄙。群豪道:我们被天山童姥折磨的比这还惨,一报还一报,有什么卑鄙的?并建议在场的慕容复出手制止。
慕容复拒绝得理直气壮——
段兄,人家身家性命,尽皆系此一举,咱们是外人,不可妄加干预。
但他的真实居心所在,在这场戏之前金庸就写得明明白白了——
这三十六洞、七十二岛之中,实不乏能人高手。我日后谋干大事,只愁人少,不嫌人多,倘若今日我助他们一臂之力,缓急之际,自可邀他们出马。这里数百好手,实是一支精锐之师。
这个外交思路,几乎是慕容复遇见各类群豪都会套用一遍的——包括他明明很讨厌的段誉,十分看不起的丁春秋,但凡有可能“为我所用”,他就可以称兄道弟。反之,为了名和利,最爱自己的表妹可以杀,忠诚的家臣可以杀,甚至给敌人下跪叫爸爸。
慕容复最后疯掉是必然的,因为他的行为到了极点就是把自己也当做家族复兴的工具,而不是一个人。“北乔峰,南慕容”,对待“人”的价值上,的确是南北两极。
4
雁门关外辽宋士兵互相打草谷是《天龙八部》的关键细节。
打草谷就是侵入敌方领地抢劫,凌辱虐杀平民。这在史书中上有明确记载。金庸三次正面写打草谷,先是自认为汉人的萧峰遇见宋兵杀辽人,再是已做了辽国高官的萧峰见到辽兵抓宋人,最后是辽帝亲自邀请他射杀汉人。
三次描写都刻意突出残忍细节,可见其用意之深。打草谷行为包含着所有战争都有的仇恨逻辑:将敌人简化为非人的异物。辽国人眼中宋国人不是人。宋国人眼中辽国人不是人。以此推论,与我国族(观点/立场)不同的都不是人。不是人,就都可以否定、凌辱和消灭。
萧峰禁止辽兵打草谷,阿紫却违令出去抓了游坦之回来折磨——一个汉人女孩仗着辽人的势抓了一个宋人,视之为玩物。这是金庸用人物处境对国族出身的更深一层反思,甚至比萧峰的夹缝处境更值得深思,因为阿紫和游坦之的心智更接近普通人(一个巧合:两人都失明了)。
阿紫成长在阿谀奉承尔虞我诈的环境中,聪明全用在了诡辩和扣帽子的江湖伎俩上。她共情能力完全缺失,一切只为满足自己的爱恨喜好,即便对萧峰也是要完全占有的态度。游坦之则痴傻,没有自我意识,一味听令于仇恨与贪爱,任人驱使,就算拥有强大的武力也不知如何运用。
这两人都行为逻辑单一,非此即彼,这是极端分子的共性。他们不是典型的群豪之辈,或者说都在某方面超出了群豪,但却最易被群豪利用。
什么人最喜欢利用极端分子?全冠清,丁春秋及一切做着权力梦的人。如果说庸常之中包含天然的恶,那么权力必然是释放恶的催化剂。这才是可怕之处。
萧峰回辽国之后,避开了武林群豪的纠缠,却遇上了真正的强者:皇帝。皇帝的强大不再个人武力,在于手握的权力。耶律洪基让他带兵南下,萧峰拒绝,并标明了自己立场和态度——
萧峰是契丹人,自是忠于大辽。大辽若有危难,萧峰赴汤蹈火,粉身碎骨,尽忠报国,万死不辞。
这话的意思非常清晰,为国赴难和开疆辟土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行为,不可混为一谈,这也是金庸笔下所肯定的江湖道义的延展,一己私欲和为国为民是两回事。
但皇帝不这么想——反而和全冠清之流思路接近。耶律洪基道——
赵煦这小子已萌觊觎我大辽国土之意。常言道得好: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咱们如不先发制人,说不定便有亡国灭种的大祸。
然后又劝萧峰,意思是你既然说尽忠报国,那让你出兵怎么不出兵?言外之意是,为什么不听我这个一国之君的话?
萧峰再一次拒绝,耶律洪基手就按在刀柄上,瞬间便起了杀心。慕容复杀忠臣包不同的场景,如出一辙。
萧峰为了两个国家的和平死后,辽军撤退,大宋作何总结?——雁门关指挥使忙不迭地向宋帝报喜——
说道亲率部下将士,血战数日,力敌辽军十馀万,幸陛下洪福齐天,朝中大臣指示机宜,众将士用命,格毙辽国统军元帅南院大王萧峰,杀伤辽军数千,辽主耶律洪基不逞而退。
这就是官方定调。皇帝自然高兴,犒赏三军,论功行赏,自觉英明神武,比太祖太宗都厉害。歌功颂德之声,洋洋盈耳,庆贺大捷之表,源源而来。
果然,皇帝常常都是痴的——不是痴情、痴迷,是白痴,猪油蒙了心,这才是佛学里“痴”的意思。
5
《天龙八部》写于一九六零年代初,和之前那些以真实历史做背景的小说(尤其是射雕三部曲)相比,这本书主角的身份和家国观念是前所未有的——萧峰是契丹人,段誉是大理人,而虚竹则最后成为西夏驸马,这些地方在当时都是大宋的“外国”,几名主角之所以“三观合”,二话不说就结拜(虚竹和萧峰甚至是未曾谋面就隔空结拜了),是因为他们对于是非善恶的基本判断是基于今天我们所说的人道主义。
金庸成长于抗战年代,思想意识中有着那个时代的强烈印记,这在小说人物有强烈的表现,如最典型的是郭靖,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天龙八部》中的英雄当然也为国为民,但身份的复杂立场决定了他们要更“复杂”地处理为国为民的问题,并以“人的价值”来超越国族立场的狭隘——或者说,他们心中在意的是少林方丈所说的“苍生”,而非凌驾于人苍生之上的权力、道德或任何观念。这一点是金庸通过武侠小说对历史和自我观念的大胆反思。《天龙八部》成书已近六十年,此时社会形态早与那时不同,但这则庞大寓言一般的小说在今天却尤为值得重读、细读。它的故事中不断提醒我们:要正视人的复杂,关怀人的价值——这是我们失落已久的常识。
此时此刻的我们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喧嚣中。国际关系保守,文化观念冲突,翻云覆雨的舆论空间、动辄诛心的挖坟举报和杀人无形的围歼封杀,从大处到小处,无一不是对 “人”和“价值”的简化和消灭。
金庸的启蒙如此“应景”,恰如鲁迅从未过时,是令人心情复杂的事情。你所担心的死灰早已复燃,随时可能成燎原之势。雁门关内外,莫不如此啊。
注:原文引用均出自金庸《天龙八部》新修版。
零二零一年九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