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人不在燈火闌珊處(愛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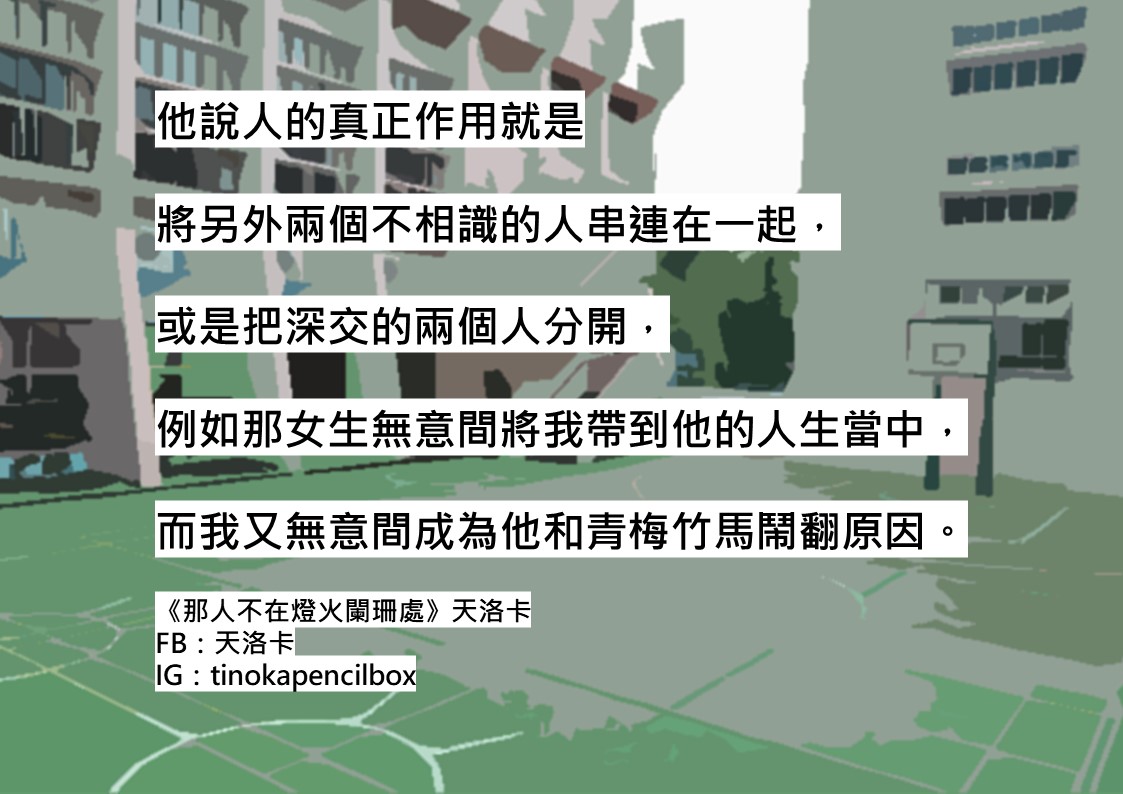
午餐用膳後,男生們大多會將多餘時間花在學校操場,或場上打籃球,或場外觀賽。我亦不例外,在場邊與同學輕聲討論打球技巧。忘形之際,一個籃球高速自後側飛來,狠狠砸中我右耳耳背。場中男生上前向我連聲道歉,我只道不要緊。男生拾球後繼續回場較勁,沒把事情放心上。當然,我也沒所謂,小事一椿。
令我在意的反倒是球場另邊有個陌生男生對我微笑。
匆匆一笑,半秒即逝。他轉頭跟身邊友人繼續說說笑笑。我挺肯定自己想多了——對方不是故意對著我笑,僅是他的站立姿勢及面向角度湊巧朝著我這邊來。
但我還是記住了那抹笑容,記住了他的臉容氣質,記住日光照在他臉營造出來的明暗。
為何記住?我解釋不了。
好幾個月過去,夏天轉換為冬。颯颯寒風成功減少場邊女生數目,男生仍然在此閒聊逛蕩。同行朋友忽爾興起,動身到場裡打球。我笑笑婉拒,說吃飽想睡不想動。
我獨坐長椅一邊,納悶之際,兩個男生前來佔坐長椅另端空位。
其中一個是他。
那笑那臉那明暗,歷歷在目。
心頭一顫,我馬上別過臉去。數秒後,我稍為冷靜,意識到自己的失態,佯裝無異,繼續觀看球賽。不過他似乎察覺我的異樣,有意無意對我展露笑容——一個意味深長的笑容。
我尷尬離座回課室去。走樓梯至三樓時,他竟從後叫住我。
「你遺下銀包。」
「謝謝。」
「不用客氣……」
奇怪。看他忸怩模樣,他似乎還有話要對我說。說甚麼?不是必須相識的陌生人可以如何打開話題?甚或是「為何要展開話題」?
氣氛尷尬,四目交投,卻不知如何是好。
直至提著半滿水桶和微濕地拖的校工在我倆之間經過,彼此才回過神來,甚有默契同時分別從兩個方向離開。我往上,他往下。
誰料在午飯時間完結後,我們還是在五樓走廊再次碰面——原來我們都是中五生。由於班別不同、社交圈子不重疊,所以未曾正式認識。
不要緊。現在互相自我介紹就可以。
「我是文班許家偉。」
「我是理班李浩榮。」
***
其實我早已知道許家偉。
我心儀對象就是喜歡許家偉。
被拒絕的心情久久不散。我開始留意許家偉這個人。
拜託阿強向文班生打探有關許家偉的事。某文班生說許家偉無啥特別,亦無專長或短處,是個存在感不強的乖學生。
我不明所以——為何心儀對象看上他?
不是認為心儀對象定要接受我或是對方必須比我優勝,只是我真的找不到許家偉有何可愛之處。
不服氣。
繼續觀察他。
匆匆數月,秋去冬來,我對許家偉好奇不減。
某天午餐後,我和阿強發現許家偉獨坐操場長椅,於是立即齊齊上前佔據長椅另端,近距離觀察他。他似乎發現我們的奇異目光,動身離開。正感沒趣,阿強發現地上有一個銀包。查看內裡,看見許家偉的學生證。
阿強建議取走內裡金錢和學生證,再將銀包交到校務處。我反對,擔心惹禍上身。阿強問我是否討厭許家偉。我無正面回應,僅是堅持物歸原主。阿強讓步,將銀包遞給我。
我急步追趕許家偉。
不明白自己此刻行為。正如阿強所問,我不是討厭許家偉嗎?人前,我一直表達對許家偉的討厭;人後,我曾多次理性分析過自己有沒有討厭他的實質理由。沒有,尤其在我對心儀對象忘情以後。
奈何留意許家偉經已成為我的習慣。
遠遠看見他的身影,我自然而然打起十二分精神;聽到心儀對象與好友聊天時提及許家偉,我對他的好奇大於對心儀對象的;走經中五級壁報板,會不經意試找許家偉的名字……
「你遺下了銀包。」
「謝謝。」
「不用客氣……」
經已物歸原主。他道謝,我虛應,然後該是沒有然後。但我們還是愣在原地。
該要說甚麼?還需要說甚麼?沒有啊!但我們還是原地愣著。
他是否一早知道我?他是否早已察覺我在留意他?不會吧……
我望入他雙眼。
不。我鐵定他不認識我。他的眼神迷惘疑惑忐忑,似乎在期待甚麼……
一名校工在我和許家偉之間走過。我在視線被阻擋當刻回過神來,低頭轉身離開。
我回到操場側長椅。阿強仍在,問我有否教訓許家偉一頓。我苦笑罵他發神經。阿強收起笑容,認真勸我別壓抑情緒。我說理解許家偉是無辜的,不會繼續討厭他。
上課鈴聲響起,學生魚貫回課室去。人群中,我在五樓走廊與許家偉迎個正著。他驚訝之情洋溢於表。我反倒開懷笑了,笑他遲鈍,後知後覺。
許家偉臉紅,禮貌地點點頭,上前自我介紹。
「我是文班許家偉。」
「我是理班李浩榮。」
***
畢業多年,我跟李浩榮從未聯絡過——當我這麼講,舊生聚會上人人皆表出乎意料:「你們當年那麼要好,竟然未曾聯絡一次?」
我笑笑點頭,不多解釋。
畢業禮當晚,他告訴我,他的心儀對象喜歡我。我問他那女生是誰,我可以當面拒絕她。他說不必,因為他已不愛他。我感到奇怪:如已釋懷,為何重提。
李浩榮笑笑,笑說他已覺悟,明白人的真正作用。
聽到這莫名其妙的答案,我就知道他醉了——他喝下很多酒。
他說人的真正作用就是將另外兩個不相識的人串連在一起,或是把深交的兩個人分開,例如那女生無意間將我帶到他的人生當中,而我又無意間成為他和青梅竹馬鬧翻原因。
我大概聽出話裡的話。有點難過,有點無奈,有點害怕——害怕今晚坦白心聲以後,我和李浩榮再無交集。
但我沒有阻止他。
他壓抑已久,情感需要釋放。這很可能是我以朋友身份給他的最後禮物。
我慫恿他繼續說下去。
他跟阿強相識於幼稚園。他倆都是頑皮孩子,經常氣得老師向父母投訴,父母夜裡就來一頓痛打。他們經常看到對方手腫腳瘀,起初會擔心對方身體,後來發現彼此不怕捱打,只怕玩得不痛快。相顧輕笑,再玩再捱打……玩著捱著,二人同甘共苦十四年,彼此之間有一種難以言喻的默契——只有阿強看出他非但未曾討厭我,反倒羨慕我的不起眼。
我好奇李浩榮何解會羨慕不起眼的人。
「不被注意、不被期望,方能活得自由稱心。」
我問他是否有煩惱,可以向我傾訴,也許我能想出好辦法。
李浩榮報以苦笑,沒有正面回答。
那夜,他喝得爛醉,我送他回家。
伯母應門。是個凶神惡煞的中年婦,語調急促,不帶尾音。她接過李浩榮,留下一句道謝,利落關門。
門關。心頭若有所失——感覺永遠不會再見到李浩榮。
其實沒甚麼大不了。這是人生必經的離合過程。不會令我受到任何傷害,亦不會令我蒙受任何損失。著實沒甚麼大不了。
但我掛念他。
不是偶然想起,不是遇上麻煩、需要向他求助,不是看見眼熟物件進而聯想。沒錯,是真正的掛念——我無法自欺。
想起他,我不期然會笑;想起他,我感覺窩心;想起他,我會自覺孤單可憐。
我漸漸意識到這是甚麼一回事。
糟糕了!怎麼辦?怎麼辦!不知道。
不要說。不要聽。不要見。
希望時間會沖淡一切。
***
依稀記得畢業翌日在自家客廳梳化醒來的畫面。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極端的光與暗、黑與白——廳燈沒有亮起,窗外日光耀眼得刺痛,室內與室外亮度差異極大。眼睛無法於短時間內適應,煞是暈眩,有一股酸餿灼熱自胸腔冒升。想吐。沒法吐。
阿媽沒有理會我,背對我在廚房煲湯。她對著湯煲說:「昨晚是他送你回來。」
我敵不過暈眩與劇烈頭痛,重新軟癱梳化上。沒回話打算,反正阿媽定會繼續說下去。
「我不明白你為何喜歡他。」
「我也不明白。」
「那就不要繼續喜歡。」
「感覺,並非可以自由控制的。」
「我亦無法自由控制我的兒子喜歡誰。」
「我也無法自由選擇誰是我的母親。」
「真抱歉——未得你同意就把你生下來。」
「你該要對我感到抱歉。」
我晦氣,毫不掩飾對她的討厭。
阿媽沒再多話,繼續在廚房忙著。
真要命。人生就是那麼多無謂紛擾。我的人生屬於我,為何旁人總愛插手?
抵著頭痛,我硬撐起身子小便去。
在抽氣扇綿延不斷的摩打聲襯托下,小便聲清脆得噁心。噁感令我清醒不少,昨晚回憶開始隱約浮現。
我似乎講過一些不該出口的話。
真的嗎?我真的把話說出口?
為何這麼驚訝?阿強醉倒後,我特意喝下更多酒,不就是為了把話講出口嗎?
便意盡,醉意消,騰出來的腦空間被後悔和自責分佔了。我呆上半晌才提起褲子洗手去。
為何要走到這一步?
阿強早已看出我對許家偉的感情,擔心我走上「歪路」。我有點兒生氣——誰有資格定義這是否歪路。阿強自知沒能說服我,乾脆將觀察所得告訴我媽。性格暴躁的阿媽一反常態,冷靜淡然勸我切勿繼續投放感情。
「世人表裡不一。口說開明,實質守舊。」
「是嗎?你呢?你口說放棄,心底裡在支持我吧?」
「別倔強。」
「我想要知道你的真正想法!別敷衍!別蒙混!」
「我想你放棄。」
「原因?」
「現實終歸是現實的。你將要面對的困難並非單靠信念、希望和愛情就可以解決。」
「我知道。」
「何解還要繼續下去?」
「感情易放難收。」
阿媽沒法回嘴——「感情」一詞明確否定了邏輯和理智,她還有何話可說,只得被動地待我回心轉意。
傍晚,我約見阿強,在公園暗處與他打一架。我們手腫腳瘀,有如兒時被父母教訓一樣。看著彼此頹喪模樣,我既心痛亦生氣——我們的友誼不該淪落至此!我們該可以當一輩子兄弟手足!
架後,我沒有留下片言隻字,待身體稍稍恢復後首先離開回家去,懶理阿強依然躺在草地上粗喘不已。
阿媽見我身上有傷,許是大概明白那是甚麼一回事,沒有多問,亦不予關心。
我不在意,一心思考如何在畢業禮當晚向許家偉表白……
畢業禮,是終結也是新開始。學生們穿戴整齊,戰戰兢兢上台領受證書。莘莘學子前途未卜,能夠掌握在手的只有當下。今朝有酒今朝醉,齊齊喝酒齊齊醉。
阿強取來一支烈酒,邀我對飲:「追求真愛不是那麼容易。至少要比我更能喝。」
我欣然接受。他很了解我,許是估計到我將會乘著酒意找許家偉表白去。我唯一擺脫阿強的方法就是先把他灌醉。我們都不是省油的燈,自小經常一起偷偷喝酒,十分清楚對方酒量和醉態——一旦倒下,沒有廿四小時可醒不過來。
小醉。半醉。大醉。
阿強半伏枱邊,傻笑問我:「想好如何表白了沒?」
「直接講我愛他。」
「如果他拒絕?」
「沒怎麼樣。就像我之前被女同學拒絕那樣。」
「如果他接受了?那怎麼辦?」
「我當然是高興!」
「我在問,他會怎麼辦?你認為他的內心強大得能夠與你共同面對往後一切?」
阿強問了一個我沒有想及的問題。
***
事隔四十年,我和李浩榮在阿強的喪禮上再次聚頭。
李浩榮說他在畢業禮後與阿強斷絕了聯絡。我為此道歉。他問我為何道歉。我重提他酒後那段說話。他反問我是否真的認為過錯在我。我答不肯定——我無心令他們鬧翻,但我確是他們鬧翻的原因。
李浩榮苦笑,笑容意味深長。
「阿強沒講錯。你真懦弱。」
「活了那麼多年,經歷那麼多事情,我不得不承認自己的懦弱。」
「你仍然單身?」
「是的。」
「要我當媒嗎?」
「不了。難為情。」
李浩榮失笑,笑我不值得被愛。
我陪笑,笑說我懂得珍愛自己就可以。
多寒暄幾句,我和李浩榮相互道別,分道揚鑣不復見。
抬頭望天,天陰雨冷,冷入心脾。
回家吧。
開門。門後空洞空虛空蕩蕩。
「戚戚慘慘悽悽,清清冷冷,覓覓尋尋。」興之所至,我一邊脫鞋,一邊倒背《聲聲慢》首三句。
「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沒有脫襪,懶洋洋得撲到梳化上,順口接上《青玉案.元夕》末句。
枕臂望窗,映入眼簾的是極端的光與暗、黑與白——廳燈沒有亮起,窗外日光耀眼得刺痛,室內與室外亮度差異極大。驀地憶起日光照在他臉營造出來的明暗,憶起他的臉容氣質,憶起那抹笑容。
大概是一見鍾情吧。
奈何我當年愚鈍懵懂,後知後覺。
如果我當年及早清楚知道自己的意向,結果會否不一樣?
我笑自己想多了:結果會是一樣的。
我是懦弱的人,我珍愛自己,所以我不會為他人冒險。我寧願花上一輩子去幻想錯過了的美好愛情,亦不會勇敢踏前一步去追求愛情。
李浩榮說得沒錯,我不值得被愛。
***
事隔四十年,昔日摯友躺在棺材裡,往日心上人站在我面前。
百感交集……
當年我為了許家偉與阿強鬧翻,事後亦沒敢聯絡許家偉。同時失去摯友和心上人,情感上的痛令我失眠了好幾年。那時候,還以為痛楚會一直維持下去,有如浪漫淒美感人的愛情電影情節。
不過電影終究與現實不同:角色的難忘遭遇濃縮在短短一個半小時裡,情感故此顯得激烈而深刻;現實中的情感必須經過時間洗禮和加入許多愛情以外因素,例如家庭、工作、健康、個人財政等等。
痛楚自然而然被淡化掉。我漸漸忘了阿強的忠肝義膽和許家偉的獨特魅力,直至今日再聚……
「認得我嗎?我是許家偉。」
「認得。你是文班的。」
許家偉淺笑,笑容如昔,淡然清雅溫婉。
閒聊之間,發現他仍然單身。究其原因,他只道難為情。
「你不值得被愛。」我蔑笑。
四十年過去,許家偉仍是當初那個許家偉。
阿強沒講錯——他的內心不會強大得能夠與我共同面對一切。
「我懂得珍愛自己就可以。」許家偉笑著說。
許家偉在認真?他真心認為這是珍愛自己的行徑?
我哭笑不得。
無意跟他繼續對話。
多寒暄幾句,我和許家偉相互道別,分道揚鑣不復見。
抬頭望天,天陰雨冷,冷入心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