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女人不能上饭桌一样,有人不想让你上书桌,也多的是理由 | 9位女性的写作空间(上)
三明治最新出版的《最好朝南》是一本由22位中国女性共同写下的、关于她们某一段生命历程的非虚构作品合集,在书中你将看到22位女性亲笔写下的24个真实的生命片段。书中的12个问题和12种境况,远远不能穷尽让女性感到困惑和挣扎的议题,或女性正在经历(事实上不少已持续了很长时间)的状况。但发出声音和尝试描述本身,意味着对“正视”的鼓励。任何讨论和改善,首先基于敢于直面的勇气。
现在,我们邀请了九位《最好朝南》的作者来写写自己的“朝南房间”。
鲨鲨:流浪书桌
《一个问题10:一个母亲说不爱自己的孩子,是被允许的吗?》作者
多年前婚房装修时,我和G先生特意在L形客餐厅里辟出一面墙定制了双人书桌,因囊中羞涩而能省则省的新家里,这是几十个平方里我心中最“浪漫”的角落,因为我俩在这里,并肩作战。
生娃以后,家变得逼仄,那书桌成了尿布台,抚触台,玩具堆放处……但不得不说,它高度合适不累腰,空间宽敞收纳力强,还真是是育儿路上的得力助手。
好在我和G先生的适应力还不错,遇到需要在家临时加班的时候,可以轮流带娃,“错峰”搬砖。G先生往往在书桌上扒拉出一片空地,夹在桌板上的长杆台灯一开,灯光内外,泾渭分明。灯光内 excel、邮箱、微信界面来回切换,灯光范围之外,桌面上影影绰绰的轮廓,从婴儿健身架、日渐演变为积木桶、声控狗、青蛙天平、遥控小车……
而我则转战餐桌,头顶上方的暖光,装修时据说是为了让菜肴看起来更诱人,洒落在加班人的键盘上,仿佛暗示着我在“养家糊口”。我常坐在正对厨房门口的方位,一抬头就能看见厨房台面上温奶器,那盏小小的红灯亮着,像是一种无声的陪伴——“我也在工作呢”。
2022年,我换了一份工作。入职第一周,我感觉飞书真是一款很好的办公软件:所有的联络独立于微信之外,同事们几乎绝无可能看到我朋友圈里有关柚子的内容,我们在彼此眼中就只是一个纯粹的“工作伙伴”,婚否、育否,无人知晓,无人在意。那些需要加班到半夜的事项,那些频繁的出差安排,一视同仁。对于一个害怕偏见的职场妈妈来说,这种冷漠却让人觉得格外温暖。
我的工作日,全靠柚子的外公外婆照顾孩子的衣食住行,因此只要不出差,我坚持让柚子晚上和我睡一起:让老人得以不被打扰的安睡,似乎是我仅能尽到的一点点“孝道”了。柚子听着睡前歌曲和故事睡着以后,我会跪在床边的瑜伽垫上加一会儿班甚至轻声接一下电话会议。有时候也懒得关掉音频,手上钻着数据、写着策略、画着图,耳边是小猫终于钓到了一条大鱼、乌龟终于跑赢了兔子、小货车终于把货物送到了目的地、小火车跨越障碍继续往前开……
后来,居家办公开始了,雪上加霜的是,柚子的早托班也停课了,这就意味着 “居家”与“办公”二者不可得兼,我不得不开始了吉普赛式办公。尝试了很多咖啡店和自习室,最后在附近的Tims安顿下来,电源多,网速快,可以参加线上会议不会打扰其他人,晚上10点才关店,以及,最最重要的,隔壁就有一个挺干净的洗手间。我告诉G先生我很满意的时候,他若有所思道:谁还记得,人家可是一家咖啡店啊。
那时候线下餐饮都只能开放50%的座位,隔座就餐,Tims的小圆桌,一个放我的电脑,另一个放我的手和鼠标,点餐码是一个凸起的贴纸,手的动作略大一点,就会碰到那处凸起,似乎在提醒我不要白嫖。于是我喝遍了冷萃+各种糖奶组合,也尝试了很多种餐食,如果说疫情在我身上留下了什么痕迹,可能就是让我成为了一个碱水贝果爱好者。
再后来,2022年结束了,工作和生活也回归了原来的节奏。年度业绩回顾的时候,我拿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好绩效,那一天,我去Tims 用我的巨额积分换了一杯新品,感觉有点太甜了,不太能适应,然后看到网易云音乐一本正经地对我回顾道 ——
2022.06 长夏不知为何
这段岁月里你变得很执着于这首歌
《小松鼠流浪记》;
你的年度歌手“宝宝巴士”
听TA的作品次数超过92%的用户
你是TA当之无愧的最佳听众
我并不是一个专业码字的人,也不算文学的爱好者,《最好朝南》里收录的我的习作,是三年前我在产假期间给我自己的私人纪念。而我的书桌,也并不是什么精神乐土,更多只是一个职场妈妈在两个角色里竭尽全力的谋生工具罢了。
这三年间,我还是觉得我和其他妈妈在很多心态上不太一样,还是“没那么爱”。可是柚子已经可以口齿清晰地说妈妈爱我,我也爱妈妈的时候,我想,这个问题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柚子自己。时间最终也没有给我答案,但柚子给了,那就以他的答案为准吧。
而职场妈妈的书桌之狭小,反倒是我这三年来最大的感慨。可能是因为已生育的身份,我知道的此类事例比以前多了很多。很难想象,明明就是亲历过人间疼痛极值的人,明明就是曾经见过凌晨随便几点的城市的人,明明就是能和不可理喻生物互相驯化的人,明明就是要给烂摊子随时兜底的人……职场凭什么质疑她们的吃苦耐劳精神、时间管理能力和责任心?
或许就好像女人不能上饭桌一样,有人不想让你上书桌,也多的是理由。



密斯赵:一隅
《一个问题09:在婚姻之中,还有可能回到“单身”状态吗?》作者
自搬出上西区和先生团聚以后,我们在哈德逊河对岸的一居室安顿了下来。
我的书桌是刚搬去Boulder时选了木头定做的,等了两个月才到,当时最不缺的就是时间。在一居室的客厅,我把它安置在bay window旁,右边墙上挂着淘来的中古钟,手边是和先生初识时他宿舍里贴的旧京都地图,眼前则是我在香港合租时胜似亲人的朋友相片、历年收到的明信片、单向历里的文字、每一次旅行的证据……似乎人安顿下来的标志,就是把过往经历的纪念品一一收藏,集成一路走来的印记。
没想到疫情期间,这个颇为浪漫化的书桌成了我的办公桌。我和先生两人背对背,度过了一个个因为有彼此的存在而不觉压抑、孤单的日子。
两年后,为了迎接宝宝的来临,在我预产期一个月前,我们搬去了附近的两居室。先生把一整扇窗留给了我。再一次地,我将这些纪念品集合重组。整理才毕,宝宝就出世了。这之后我的写作时间和空间都被打破,阅读和写字大多完成于累瘫在沙发的片刻、短暂逃离哭声和亲职责任的咖啡馆和各种不堪的间隙,这样竟也在产假三个月间完成了三篇非虚构。
这个月,我们又搬家了。虽然我的角落还欠缺一幅statement piece,但先生看到就笑着说,这真是你的地盘,真的“小女”。我也笑了,这可能真的是家里唯一一处完全不被我新的母亲身份和家庭生活soil的空间。而这个曾专注于写作的空间也愈发成为了它本身的象征。现在,我在饭桌写作、在通勤路上写作、下定决心离开家去咖啡馆写作。伍尔夫没有小孩,她说女人需要自己的房间。身为母亲的女性写作者,房间的门随时会被推开。
拍相片的时候发现,书架第一排竟都是女作家的作品。在美国买中文书不易,我也最怕搬家时的重量,所以家里有的都是最喜欢的可以反复阅读学习的作品。最近读完的,有托朋友从国内带来的张怡微(我最欣赏的国内同龄女作家)的《四合如意》、颜歌客座编辑的《读库·爱尔兰文学合辑》。刚刚翻开的是在旧书店淘的Joan Didion的Blue Nights。这个小小书架上最令我感动的,是两本一模一样的Women at Work(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它们是我的先生和我的好友不约而同送我的同一年的生日礼物。
最近愈发向女作家的能量体靠拢。这与其说是一个性别选择,不如说是文学的选择。长大之后,同为女作者,我自然地摒弃了男性视角和男性表达的男性经典,而踏上了更多元、更真实、更有新意因而更尖锐的女性创作的沃土。因此也对女性书写和其它社会议题的交缠有了更深的讨论和理解。母亲的身份在此常常是矛盾的,我们似乎都在某个节点或仍在不停挣扎、怀疑、重建。
我怀念曾经的书桌,但现下空间里的家庭生活——和Joan Didian同时淘到的Madeline童书、身后先生刚吹起来的恐龙气球、厨房里的学饮杯……它包围我、打扰我、选择我、也滋养我。





杰西:星巴克的吧台长桌,是我的写作台
《一种境况06:对相亲对象的要求,家人只有四个字:男的,活的》作者
一杯冷萃/拿铁,一台电脑,一本计划簿,从2019年我初次开始写文章的时候,星巴克的吧台长桌就成了我的写作台,我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星巴克气氛组"。
很多朋友表示不解,星巴克这么吵的环境,怎么写作?
可对我来说,星巴克写作早已成为习惯,不只是因为这里的桌子高度合适,充电方便,写作间隙可以放心去商场上个厕所;更是因为我在家里更难写作。
北漂多年的我,之前一直跟其他人合租,家里只有那十平米的房间是完全属于我的,但在卧室中,我很难坚持写作,会很不自律地突然玩手机,或者习惯性地躺下。即使后来我在北京一个人住复式,楼下是客厅和开放式厨房,写作环境远离了床,我也总觉得很不舒服,还是要经常往咖啡厅跑。而且即使在客厅或者办公室,只要是有熟人的聊天环境中,我都很难写作,因为我很习惯去搭话,难以集中精力。
反而在星巴克这样看似吵闹的环境中,周围一切的聊天都与我无关,对我来说,他们的聊天仿佛只是背景音,我可以更加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而且到处连锁的星巴克,对于经常搬家的打工人来说,再方便不过了。
当然不自律的我在开始写作之前,会有半小时左右的适应期,我会先给电脑充电,然后习惯性在我的计划簿中把当天或者近期的安排写好,立立flag敲打一下自己,打开手机随便玩一下,这个过程中脑子里其实不断闪过文章的思路,在灵感乍现的瞬间列好提纲,开始写作。
非常有意思的部分是,在我开始写作前的准备期,旁边的声音或多或少也会传入我的耳朵,这成了我的"人类学观察地",我有碰到在这相亲的年轻人,也碰到妈妈们在这里讨论教育,最近逃离北京回老家的我,还在这里碰到一个妈妈指导孩子写英语作业,说的都是山东味英语......这一切都成了我的脱口秀段子素材。
有朋友说房子是租的,生活是自己的,建议我好好布置自己的出租屋,可对之前随时搬家的我来说,生活确实是自己的,但我不会花钱多努力地布置出租屋(当然也是我懒,总觉得没必要为出租屋花钱买大件,毕竟大概率带不走)。
最近回家稳定后的我开始研究买房了,而且房子还没买我就开始在思考装修了,在我的设想中,我会将客厅和阳台打通,保证家里有足够的阳光,放弃传统的餐桌,置办一个类似于星巴克这种高度的吧台长桌和椅子,在长桌的一角做一个属于自己的水吧台,把客厅不同角落都摆上书,争取把星巴克的写作气氛带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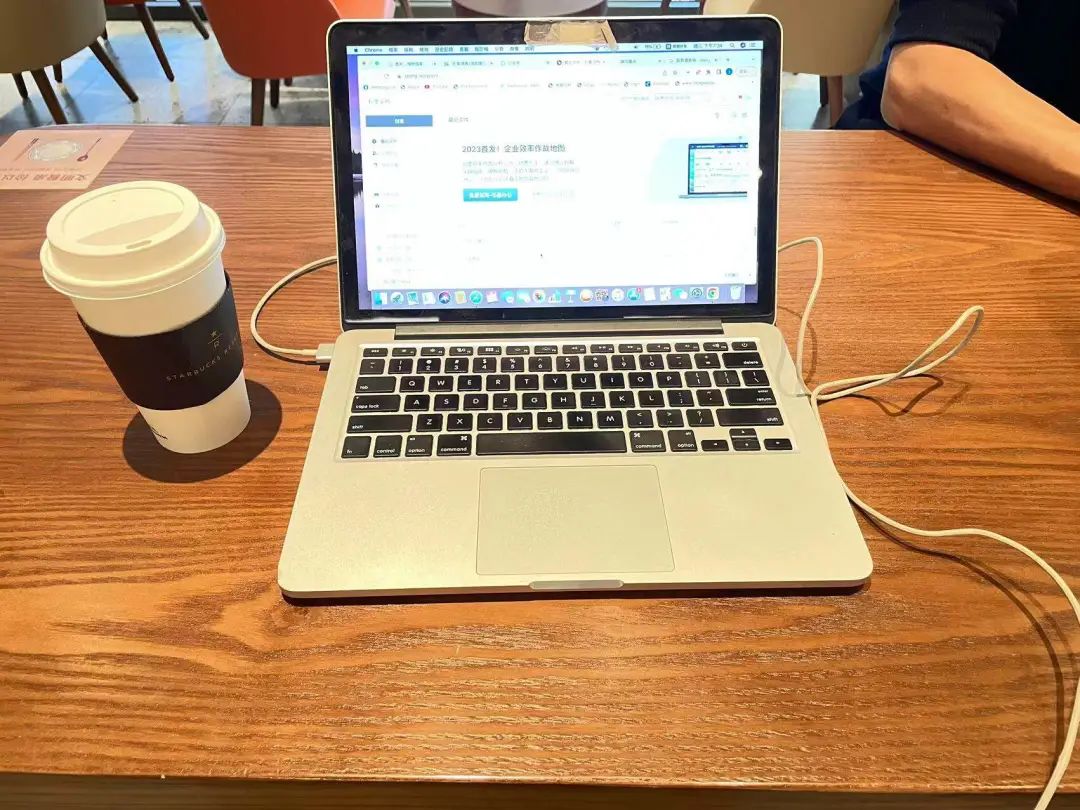


Emma:我渐渐意识到,一间固定的书房已不再重要了
《一个问题11:做试管婴儿是因为想要一个孩子,还是不愿意接受自己是“生殖无能”?》作者
也许从一开始,书房对于我,就不仅仅是一个空间上的概念。
每个喜欢读书和写作的人都希望有一间单属于自己的书房,我想啊:
那一定得有满墙的书柜,上面都是我喜欢的书,有一扇推开就能够被大自然包裹的窗户,外头吹来和煦的风,窗帘拂动,白天有很好的日照,晚上一盏台灯透着柔和的光。
冬日的暖阳,盛夏的午后,初春的细雨,一年四季,空气清新,温度适宜,我坐在书桌前读书,写字,做我想做的事情......
至少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一直想象着这样的画面,书房是有空间感的,甚至有时间感。
只可惜上学时候的我,没有多少时间读闲书,每天晚自习回来困得睁不开眼睛,躺在床上准备熄灯,瞥一眼书架上的书......我默默安慰自己,加油努努力,等考上了大学,想怎么看便怎么看!
与其说那时候我想要一间书房,倒不如说我想要自由。
从小女孩长大,到步入社会工作,到结婚生子,到人到中年,我在这个一线城市已经拥有过三套房子,但无论是第一套70平米刚结婚的小两房,第二套90平米的学区房,还是第三套120平米的郊区复式大四房,都没能挪腾出想象中的那样一个叫作书房的空间。
——
孩子刚出生时,我们住在第一套房。
两个房间得有一个留给帮忙照顾孩子的老人,另一个稍大的做主卧,一家三口睡在一张大床上,婴儿床挨着,剩余的便是衣柜和走道。
没有专门的书架和书桌,看书和码字要么坐在床上靠着床背,要么到客厅的餐桌上,拨开一堆奶瓶水杯碗筷,勉强划出一小片区域。
书仍然很多,但总没有婴幼儿的杂物多。因为没有专门的书柜,我慢慢养成了一种“阅后即焚”的习惯,书买回来立刻看,看完立刻放到有储物功能的床底下,这样既不占地方也不会蒙尘。
写文章一样要速战速决,既然连张像样的书桌都没有,那只要是能放平电脑的地方便是书桌,码字前要思考的都得提前想好,抬手便敲字,不然时间拖得越长,更加腰酸背痛。
后来我慢慢知道,很多有孩子的人家庭办公条件和我差不多,都不宽裕,但毕竟他们的需求只是一张宽敞的办公桌,而我的想要的是抛开妻子和妈妈角色后的自在。
——
孩子上幼儿园后,房子开始有了“学区”的概念,我们搬到了老破小的第二套房,为了得到一间独立的书房,我对依然狭小的空间布局做了一番仔细的打算。
两间朝南的卧室,一间是主卧,一间是孩子的房间。客厅有一处暗角,一般用作餐厅,被我隔开成了一间带室内玻璃的暗房,平时它是书房,一应台灯电脑打印机都配置妥当,老人家过来小住的时候,书桌挪到玻璃房外的客厅,小床打开变大床,它摇身一变又成了客房,这个设计被我这楼上下邻居们夸赞不已,都想要抄了去。
此刻我坐在客厅的角落,常常码字的这张书桌边上,它最近又被搬了出来。
这位置是整个家里最昏暗的角落,它刚好位于客厅和房间南北直线通透的正中间,也是两边光线进屋逐步递减的最末端。人在书桌前,面朝着壁,背对着入户门,左右两边有对流的灌堂风穿过,桌上大白天地开着台灯.....它看起来确实有一种随时会被调剂的不安定感。
幸好家里的每个角落都有书,也许是先有足够多的书,才发现放书的地方不够的缘故吧,书架也到处都是,材质还不相同,木质、铁质、板材......在家里我是走到哪读到哪,读到哪放到哪。
比方说今天天气好,我就会坐在朝南卧室的懒人沙发上面,晒着太阳看书;如果今天是阴天,我就坐在客厅的角落,书桌上开一盏灯,光聚焦在不到一平米的空间,感觉效率特别高;要是哪天身体有些疲劳,我就捧着书半躺在沙发上随意地翻翻;至于说入睡前,那随手抄起床旁边的一本书,看着看着把它搁下。
——
再后来,我们在郊区购置了第三套更大一些的房子,四个房间,上下两层,空旷而清净。
我没有再安排独立的书房,每次过去带上平板笔记本,随手带上几本书,孩子有自己的活动,老人家也有各种外出的安排,我就这样安静闲适地在家里待上一个周末,做做饭,看看书。
我渐渐意识到,一间固定的书房已不再重要了,我曾经想方设法在不断推进的人生阶段给自己腾出的独立空间,而那早已不局限于家中的某个角落,某张书桌,某扇窗户。
无论我结没结婚,生没生孩子,这个家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居住,房子里有多少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在我心里早已有了一片栖息之地,我可以在里面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读书,写作,发呆。自由和自在散落在每一处角落。
它不会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空间。
——
记得看《黑暗森林》的时候,面壁者罗辑从两百年后的冬眠中醒来,他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人类的生活基本转入了一千多米的地下,树状的房屋,无线供电,随处可见的显示屏和全息投影。在那样一个世界里,所有的墙壁都没有了,到处都在发光,人的衣服可以随着心情变换出不同的图案,人要处理事情,搜索数据,点击身边任何一件平整的物件都会成为操作界面,动态图像一直闪动。
我当时想,这样一个科幻的,虚拟的,未来的世界,和我们现实世界最大的不同之处,不正是它超越了空间和时间的范畴吗?可惜那样的世界是自由而孤独。
而我曾经想象的书房,它看得见摸得着,有精准的面积和巧妙的布局,妥帖地安放着我人生中的种种,我不需要那样一个科技感的未来,现在这样就很好。





三明治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3年5月出版
女性在生育之前,知晓身体可能受到的伤害吗?
养育了3个孩子的22年婚姻,要因为惯性而延续吗?
长期遭遇家庭暴力,靠自己能离得成婚吗?
随先生搬到陌生城市,事业停滞,顺势成为“家庭主妇”是应该的吗?
一个母亲说不爱自己的孩子是被允许的吗?
做试管婴儿是因为想要一个孩子,还是不愿意接受自己是“生殖无能”?
作为一名女性,不想来月经,可以吗?
送给妈妈一个跳蛋作礼物,会怎么样?
22位女性作者,24个真实的生命故事。
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说:“女人如果打算写小说,她必须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
在《最好朝南》里,这些女性写作者用文字构建自己的 “朝南房间”。她们大都不以写作为生,把故事写下来的目的,是理解自己。
这些故事是非常私人的个体遭遇,是对个人而言有重大意义的生命片段,是在日常生活中不会轻易对别人提起,甚至连最亲密的家人朋友也不知晓的经历。
通过写作,她们向身处的境况提问:作为女性,“我”经历了什么?为什么“我”会经历这些?这些经历对“我”意味着什么?它们如何构成了“我”的一部分?
她们写自己的生命,也用生命写作。
***延伸阅读***
《最好朝南》书序 by 三明治编辑李依蔓
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刘宇婷谈《最好朝南》背后的故事
三明治创始人李梓新谈女性的Life Writing






支持三明治,让更多故事和个体表达被看见。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