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紀錄:我們需要戲劇構作嗎?!(下)
2018–07–23

主談:許仁豪(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助理教授)
回應:陳佾均(譯者、戲劇顧問)
主持:紀慧玲(表演藝術評論台台長)
紀錄整理:羅倩(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生)
時間:2018年4月25日19:00–22:00
地點:社會創新實驗中心A-2社會創新實驗大型活動講座
陳佾均:
謝謝大家來。雖然過去寫過一些相關文章,但我從來不覺得我是戲劇顧問的代表,很多人像吳政翰、周伶芝也都在做類似的事,而且各自在不一樣的傳統、不一樣的類型裡。但我覺得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只要是做藝術創作的事,就不可能有食譜、不可能是什麼職業就固定就怎麼做事;每個人的做法都不一樣,所以他們才是創作者;不會因為他是哪個國家或哪個系統就一定怎麼樣做事情。也謝謝仁豪將理論與脈絡做了一番梳理。那我現在希望做的就是盡量不神秘化戲劇構作這件事情。像《戲劇顧問:連結理論與創作的實作手冊》序言做的,不是去問戲劇顧問是誰,或戲劇構作要做的事是什麼,而是針對個別實踐者,詢問他們怎麼去切入這個工作,那麼全部收集起來就可能會有一些觀察、有一些體會。以下針對仁豪的分享來做回應。
一、仁豪在後半部好像將戲劇構作視為當代劇場的代表。但是大家不要忘記那是因為那是「當代」戲劇構作,所以當然會受當代美學影響。簡單來說,因為當代美學在價值上的轉換,趨向重視集體創作與外部連結,在這個轉變下,帶著一身技藝並須慢慢琢磨作品的導演、編舞家或演員可能無法勝任自己去做這一切。因為一個外部的知識系統或取徑是當代藝術需要的東西,所以戲劇構作才興起。不是因為戲劇顧問應該做這些事,而是當代藝術的核心價值影響了當代戲劇構作的實踐。就如同過去,因為各藝術間分家的狀況比較清楚時,戲劇顧問基本上就是一個學者,做考究的工作,不用看排,可能就是類似文學顧問這樣。所以這是希望釐清的第一點,戲劇構作的興起是和當代的美學價值以及制度轉變(如現在的策展)相關連的。
二、談論戲劇構作可以從三個不同層面來談,各有不同意義:第一、從美學或哲學的層面(譬如前述美學價值的逐漸傾向集體創作,為何重視外部性、異質性等),第二、是從實踐層面來談(目前劇場人的生態是如何工作),或者第三點就是剛剛仁豪提到的,從育成的層面來看。我先講結論啦,任何火紅的事情都很可怕,因為變成體制的影響力很大,成為系所就會開始教學生,影響觀念,不得不慎。現階段我還是認為應以個別創作者取向來決定是否需要戲劇顧問,而不是直接體制化。建制化很容易,但如何規劃教學才是重點。不可能是範例的複製,我們不知道未來的劇場會如何,而是訓練思考和解決問題的工具。公式化的複製未來的人不會派得上用場。
三、前面仁豪提到一些「物件劇場的戲劇構作」、「舞蹈劇場的戲劇構作」,我想確認一下那些只是案例,並不是說好像某種劇場就會有一種戲劇構作的方式或固定路徑。
四、德國雖然體制內劇場非常強大,但還是有體制外的創作團隊,那他們在創作條件上往往就跟台灣是一樣辛苦的。體制內的戲劇顧問做的事情也有可能僅限於比較傳統的部分,譬如修改文本、準備資料與做節目冊。當然內容要多激進就是看個人。
五、關於戲劇顧問的姿態:過去比較保守的年代,戲劇顧問是以大學者的身分參與,而那也是一個大導演、大學者受崇敬的年代,戲劇顧問當然就是很受尊重的。當代的戲劇顧問就我的理解,仁豪提到很多結構決定的事情還是導演主導,戲劇顧問頂多是參與集體創作,並不是取代導演。我也會站在一個角度思考,如果這些是導演本身就可以做的,為什麼還需要戲劇顧問?我想這份工作的不獨立性也和仁豪提到,這是一個不相信天才的年代有關,相信對話的重要性,而不是那些事就是由那些人獨力完成。我承認這樣的價值取向比較偏向歐陸思考,認為「衝突是張力、辯證是趣味」,並重視批判性和處理異質性的能力,所以更加需要戲劇顧問這個角色。在實務上,戲劇顧問的確可以處理一些導演能做卻沒有力氣做的,例如導演、編舞家會花很多時間在修質地。那戲劇顧問刺激你去接觸外部;這個意思不只是說拿個議題跟你撞,有時也是關於取徑的問題,譬如一個電影導演在看身體,跟一個編舞家看身體就不會是一樣的路徑。戲劇顧問可透過對話,用各自的背景去看同一件事情。比較重要的是如何運用戲劇構作的思維,或許沒有戲劇顧問也有可能有其他人發揮類似的功能;但有這個人在,就能保障這件事一定被會執行。
我2009年從德國回來,一開始做劇場行政。有機會實踐是耿一偉推薦我去當北藝大學生製作的戲劇顧問,當時主要是修文本(德國劇本)解釋背景等等,比較是做文本工作,工作相對單純。慢慢摸索我可以做什麼,導演需要什麼,後來當代性的概念進來後,我很開心現在不是因為有德國劇本或有德國導演才會找我,而是創作者在形式、美學,或議題上想要與人討論,或者在創作者有跨出自己領域的時候。
我還記得2009年回臺灣時北藝大已經有在討論成立戲劇構作系,或是成立有業界需求的舞台監督系,當時連我自己都覺得大家都已經夠窮了哪有錢再請一個戲劇顧問,但其實有這個需要就會有這個錢,如同二十年前也不會想到需要多媒體設計與行銷宣傳,現在就有。

六、關於仁豪提到「後戲劇」的部分:雷曼提出「後戲劇」本來就是總結藝術的發展,也不是說一位學者預測、發明了什麼趨勢,而是他的觀察。的確他的影響力很大,但也是因為那個時代到了,大家的實踐已經到了那個重視斷裂的時刻。非文本邏輯不是反文本什麼的,非文本邏輯的核心在於它不接受一個封閉一致的世界。另外,雷曼在書裡說到,「戲劇劇場(dramatic theatre)不是冗詞,因為劇場不一定是戲劇的」;如「話劇」這個字會出現(德國也有這樣一個指稱以語言為主要表現形式的劇場,“Sprechtheater”),就表示之前的劇場不是只有在講話,所以需要一個區別的指稱。其實以話劇為主導的劇場發展不過也只是兩百多年的事而已。所以雷曼談後戲劇觀念時,不是帶著要介紹什麼新(的東西)、好像他發現了什麼新潮流這樣的態度,而是要指出「戲劇劇場」的人造性;也就是大多數人認為劇場理所當然的樣貌(戲劇主導)僅是一個很有限的歷史情境下的產物。所以從這裡回到對劇場的想像,如果我們問戲劇顧問做的是什麼,也就會依情況而有所不同。當然首先這和每個人的個人特質、表現力和創造性有關;但假設如果真有所謂不同國家的「派別」,那也是出自各別社會對於劇場的社會定位和期待值的不同。我們之前有提到18、19世紀法國或德國的國立劇院的機制,不管其動機或發展為何,只要是建制下規劃的劇院,本身已經有其目的。我們在不知道戲劇構作可以是什麼的時候去參考這些歷史上的案例也是很自然的,不過我覺得戲劇構作可以做什麼,可以不用被劇場體制的想像影響。
七、因此戲劇顧問不用非是科班出身,但必須和表演藝術的實踐是在一起的。仁豪剛剛問我說德國現在有沒有戲劇構作的科系,我不太清楚美國的狀況,但以德國來說,最早就是雷曼在九零末創的;也就是說現在線上的戲劇顧問,當然都不是念這個出身的(他們唸書時還沒有這個系),念哲學、文學、美學、宗教,甚至生物。所以對於藝術的鑑賞度比念什麼重要。所以最後想談一下關於育成的問題,我認識一些德國比較資深的戲劇顧問其實也會有點擔心,怎麼現在很多戲劇顧問真的就是「科班」出身,覺得怎麼會一下子有好幾個這樣的系所。但這沒辦法,體制本來就是會跟風,體制作為比較大的包袱,就是會需要拿一些既有的想法,應變得又比較慢。除非領導該系的人很有遠見,否則科班訓練出來的會和戲劇顧問的工作有所牴觸。這份工作本來就需要從外部帶入異質性,如果在養成上和創作者念同一套戲劇史、擁有同一套美學價值、一樣的社會政治傾向,就沒什麼用了。談到育成,這些都是現在進行式,我們現在的決定,會決定未來的樣子。我看了一下目前德國有的幾個戲劇構作系的規劃,其中法蘭克福那個系讓我看了滿感動。就是雷曼九零末創立的那個,他們在面對當今歐洲右翼興起的情境下,推行的是「比較戲劇構作」,追求更國際化的視野,不願意落入單一國家的思維。它是有這樣的願景,那他們的課程規畫可能可以是一個參考。課程的設計目標首先認為學生要知道現在實際上劇場的樣貌,而這包括知道其傳統和框架。所謂傳統就是要知道現在既存的表現是哪裡來的,譬如劇場史這些基本的必須知道,但同時也是關於其「框架」,就是包括劇場的生態。所以在規劃上偏向解決問題與面對衝突的能力,需要實務與理論兼具。此外,還有一個重點是要打開對社會的想像力(要有辦法想像未來的社會、未來的藝術會是樣子,所以光是臨摹大師是不夠的)。因為自己學很重要,所以系所會強化多媒體的資料庫,讓學生有充分的參考養分。同時要培養學生對「新」事物的敏感度,以及能夠概念化事情(能夠將現象變成概念)的能力。實踐上可能包括講座、排戲、社會踏查、學習多媒體與電影史(不會只侷限於戲劇史,媒體能力已是必備)、觀察並抵抗創作在經濟與政治上所受到的壓制等。同時強調學生在在學還較受保護的階段,就能和其他學生創作者交流、認識,這樣未來就會有已經擁有一個強健的連結網絡等。這些都是他們在規劃系所時在意的。
八、回到亞洲,我也覺得很難有一個亞洲的範例,應該是要由下而上長出自己的東西。我覺得我大部分做的是幫創作者建立一個結構,然後拆掉那個結構,再建立一個新的結構,簡單講是這樣吧,我的工作。戲劇構作在台灣有三個原因有實際的需要:一、現代劇場作為一種外國形式,常常要面臨嫁接問題;二、臺灣有很豐富的表演傳統(傳統戲劇、傳統身體),提出這兩點我指的是,我們的異質性比歐洲大,那戲劇構作就更有開發的空間。第三,是以臺灣的四大國家場館來看,國家級的場館多元了以後勢必要做一些在地的連結或耕耘,那這些都會指向脈絡的整理和挖掘,也就是戲劇構作的本行。我們可以討論臺灣的戲劇構作可以處理什麼、如何找到自己的方式來談。例如針對傳統戲劇怎麼辦?或針對特定城市、觀眾群怎麼辦?就可以是一種戲劇構作的討論,而且事實上已經有在發生。所以我是覺得我們本來就有在做類似的事,只是現在「戲劇構作」這個詞幫我們概念化這些工作、給了它一個名字。
順道一提,《戲劇顧問:連結理論與創作的實作手冊》這本書的作者是學美學、學術出身,也做很多實務工作,她厲害的地方是把很抽象的東西化成理論文字,而且匈牙利出身的她非常熟悉文本劇場。可是即便她這麼強,現在在英國也較往Dance Dramaturgy發展,據我的了解是因為英國劇場的文本傳統實在太重,不太有發展空間,所以英國一直用Literary Manager是因為這樣。
仁豪後來舉的例子,比較是從Dance Dramaturgy的角度,其實在不同領域討論Dramaturgy會完全不一樣。對舞蹈界來說,Dramaturgy是新名詞,就像之前講的,那可能和現在對舞蹈的理解和定位有所改變了,所以有了這樣的發展。但對於整體戲劇史脈絡來說,這就不是新的概念。
最後分享很久以前,有一次和歌仔戲老師聊天。他就提到戲劇構作的工作很像他們說的戲包袱(戲曲知識非常豐富的人)。所以,其實也不一定就要用這麼當代方式去切入戲劇構作的思維,譬如要田調啊什麼的,實踐方法也是可以放回這個藝術形式本身。因為戲包袱一樣是一個對這種藝術形式的傳統、可能擁有哪些工具是熟悉的。

Q&A時間
紀慧玲:
聽完兩位的討論,我有兩點要分享:第一,開系還是要審慎考慮,學生未來可能會面臨找不到工作的問題。第二,臺灣缺乏什麼所以需要Dramaturgy?或只是作為思維與文化傳播而引進Dramaturgy?
王墨林:
臺灣劇場資深的表演者,這些在做身體訓練、身體表現的小劇場演員,我很早跟他們講過,要想想看,你們沒事就去參加Jerzy Grotowski工作坊,這跟你們身體的關係是什麼?還是說跟你們的表演有關係,需要有Jerzy Grotowski身體的樣態,是否能表現出自己的力量?還是最後只是表現出Jerzy Grotowski?這幾年開始流行舞踏,不論是論述或是某種原因下的舞踏表演者,整個身體動能都是基於完全模仿的情況。三十年下來,一直強調身體,身體技術又積累了什麼?沒有人談。我和劉靜敏(後改名為劉若瑀)對話過,優劇場(現為優人神鼓)做的身體訓練與身體表現,最後走向修行,走向了宗教,而不是身體。像雲門舞集與林麗珍(無垢舞蹈劇場),都走向修行,劇場可以有儀式,但不是宗教儀式,舞蹈不是宗教。
同樣的,回應兩位講者與今天的論述,我一直耐著性子聽,想知道現在從國外回來的年輕人,他們怎麼看臺灣的狀態,臺灣可以講英語、德語,而不必講普通話,這是怎麼回事?論述當中完全沒有看到臺灣。你們剛剛提到每個地方環境不一樣,表現的劇場也不一樣,是的。假如你們回來臺灣真的把這二、三十年臺灣劇團、身體、體制、補助等各方面的關係都談進去,而不是一下子只談國外這些非常成熟的例子,我們才能有可以對接的想像,除了傳統戲劇,我們的現代劇場對於外國人來說毫無特色與可看性。現在有一群年輕人不拿補助也在做表演,他們太有可能性了,或是延續80年代小劇場運動至今的黎煥雄與鄭志忠。我自己是有點不太爽,沒有人告訴你們要回頭來看自己的東西,我是覺得臺灣不需要劇場構作,臺灣的劇場200%太商業。應該要回頭看臺灣的脈絡是如何做,調研然後才來論述,而不是一直覺得臺灣劇場跟不上建制化歐美國家的劇院體制,覺得差別人太遠,距離常常阻礙我們往前。鄭志忠在清華大學的演講,談他的身體與走路的方法,他已經能展開自己在地性的說法與論述了。
今天聽完演講,我更確定這個問題,臺灣的劇場走到所謂主體或文化還要很長的一條路要走。這是你們的責任,你們要留給下一代什麼?就回來好好做臺灣的扎實田調。臺灣根本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做什麼東西都要補助,完全國有化,我們真的有很多問題需要重新思考。
許仁豪:
我離開美國之後,在中國大陸工作好長一段時間,也做了相對的田調,再回台灣兩年,比起我對中國大陸的認識,我坦誠我對臺灣在地脈絡並不熟系,的確必須回頭去理解。我想用Dramaturgy替代原本的理論很大的原因是,我認為臺灣正面臨和全球一樣的高等教育危機,在資本主義極度發展下,人文學科不停被學校執政者說,你們的用處是什麼?學生都不來唸?還被威脅說你有沒有想過五年後文學院就消失了,每天都被迫去思考這個學科存在大學的意義是什麼?學校的性質是科學與商業為主的研究性大學,可能和北藝大的情況又不太一樣。我的學生不要說對本土脈絡不感興趣,和我作為90年代求學的學生,會想總有一天要離開臺灣看看先進世界的人在做什麼是非常不一樣的,現在的學生對離開臺灣的欲望都沒有動力。
回應小紀姐的問題,現在的大學生把大學當成職業訓練所,對生存狀態的漠然。我想做Dramaturgy不是要移植與複製,作為學者,我的私心是在臺灣來做產學合作(KPI),連結產業。這是非常務實性的思考,這是現在學生想要的,我很難過的講出這個事實,這和我在90年代當大學生完全不同,是鄙夷談任何與金錢有關的事,認為藝術是很崇高的。
在現今高等教育壓力下,早上在網路上聽關於Dramaturgy的討論,現在美國也開了一堆Dramaturgy科系,但有位教授就說現在劇場沒有人要請這些學生來工作,得到這個學位之後要去哪?但是娛樂性的場所、遊樂園等商業機構可能需要Dramaturgy。不是所有學生都適合走高度社會批判、高度藝術、高度菁英的研究工作,它沒有辦法靠市場運作,可能就需要國家補助機制。回應大墨,的確需要回頭梳理臺灣三、四十年來的脈絡,包括補助機制、戲劇生產、劇場資源分配,包括需不需要Dramaturgy,也需要持續深化討論。也請具有實務經驗的佾均回應大墨。
陳佾均:
我覺得大墨講的我認同啊,大概做幾點回應:第一點是說,我不是阿忠(鄭志忠)這樣的創作者,從我個人的實務經驗,就是很務實的在做,當一個團要做一個戲,針對我們具體的時空,也會處理關於脈絡的細節,但還不到大墨講的那個層次。因為我今天只是與談,我也不是以藝術家的身分來,所以我今天的發言其實是撇開我的實務經驗,譬如我跟誰做了什麼、怎麼做這些的。我剛才回應的出發點是事實上我們的大劇院和學校系所都有在想納入戲劇構作的事。所以我想說的不是大墨那個高度的,我的重點是,不要神秘化這個工作,也不要對這個職位有任何制式的想像。也想補充,我沒有覺得德國比較先進,他們的發展蓬勃這麼多就是因為補助多很多,他們的劇院體制可以養四百個戲劇顧問也不代表做的事情就一定很有生產性,他們那樣也有他們的問題。我自己平常有限的實踐,我覺得我有做一些脈絡的事情,但不是大墨說的那個層次。說真的如果要談大墨提的這個層面,今天題目就不會這樣訂,講者也不會是我和仁豪來談。
許仁豪:
大墨的回應提醒我,回到未來課程結構設計,臺灣藝文生態四十年變遷是要涵蓋在課程中的,未來讓學生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延續發展下去。
陳佾均:
大墨說的那個層次之外我覺得還有很多小的事情可以做。我想仁豪在學院也會面臨實際推動的困難。在我有限的工作經驗裡面,我是覺得,很多人在說要讓劇場更親民、劇場這塊餅可以做大一點……一個不菁英化的劇場當然也是要經營,可是,很多連文化菁英很多人也不看戲啊,看金馬的、看小說的、做當代藝術的都不看戲也很奇怪啊!我認為戲劇構作可以做的是,不是只是簡化讓它變得比較容易進入,而是透過製造和外部的連結,讓更多人會對劇場有興趣,變成比較廣義的文化生產。
許仁豪:
這次我在學院透過學生畢制尋求企業商演合作。和企業合作反而可能將從來不進劇院的觀眾帶進劇場。例如在高雄,一般民眾生活其實和劇場無關,很多民眾從來沒有進過劇場。
私立大學日文系學生:
我覺得大家想的太灰暗了,我來臺灣念大學才開始接觸現代舞,從去年開始看表演,每個月看一到兩場舞蹈,偶爾會看戲,以前我家附近只能看到京劇,很無聊。不用太執著於什麼脈絡,不管去外面學還是怎樣,臺灣人就是會帶臺灣性。我從TED Talks雲門創辦人提到有長輩之前從沒有看過現代舞,非常感謝林懷民帶來美好的東西,我認為是藝術行銷的問題,藝術行銷可以結合Dramaturgy,要讓更多人看到。我比較喜歡看外國團,臺灣團缺了一點新奇。
余岱融:
今天談了非常多層面的主題,從強調社會性脈絡的當代創作、臺灣身體的田野調查、文化生產、藝術推廣、尋找新觀眾,更凸顯Dramaturgy工作的歧異性,很期待像這樣的討論可以繼續辦下去。在臺灣目前已經有一些實踐,如「松菸Lab新主藝─創作徵選計畫」裡的創作陪伴,不同的藝術節、場館的徵件也有協助配對或要求設立戲劇顧問或創作顧問,以及也有些表演藝術團隊已經有駐團的Dramaturg等等,我會想知道更多同行是如何進行工作,包括像傳統戲劇已經有類似Dramaturge的角色「戲包袱」。以這些不同的在地經驗為基礎,我相信我們會更能跳脫概念式或相對空泛的語言討論,打開Dramaturg可能性,與更豐富的實踐想像。
林璄南:
我曾當過當代傳奇的Dramaturg,今天還沒有談到的是Dramaturg也可以有好多位,或是一群人;Dramaturg也能肩負行銷推廣的角色,這部分談的比較少。當你做跨文化改編時,基本上是需要Dramaturg的,以當代傳奇以京戲為班底要做希臘悲劇、莎士比亞為例,導演本身能掌握的難免就有其侷限。另一方面,歌仔戲也改編過《羅密歐與茱麗葉》,過程中未必有Dramaturg,卻參考電影,這樣的跨文化改編的演出也是有的。再以我自己比較有經驗的例子來談,我做莎士比亞研究,今天要做《哈姆雷特》改編戲曲版本,常常創作者會搞不清楚版本,這時候是需要Dramaturg的。比如在芝加哥大學附近幾百人的劇場Court Theater,就會找芝加哥大學的教授David Bevington做Dramaturg。
陳佾均:
當然戲劇構作有無限可能,不過就現行來說,你是從單一製作或從場館的層次去做考量的就不同,譬如場館的戲劇顧問就有涉及行銷或觀眾經營,而這也可以是有娛樂、教育或其他內容的。這些各種不同的面向,其實都是一種脈絡開展,也可以納入大墨之前講的,我們的國家場館也可以有一個劇季來整理台灣表演身體的發展、或譬如六零年代以來的莎劇改編這類,然後我們一起去看看中間發生了什麼。我覺得戲劇構作的存在,指向不那麼作品中心的發展,更去肯定作品的意義不是在完成執行那個作品上。不是只是工藝技術上的討論,我也可納入市場的脈絡、或特定主題像是年輕人的脈絡等。這些雖不是史觀層次的,但也是可探索的脈絡。
許仁豪:
我想回應錢從哪裡來這回事?錢決定這次的Dramaturge要做什麼事。如果你是場館裏頭的常設Dramaturge,機制會告訴你要做什麼,同時你也可以在其中偷渡自己想做的。接案的Dramaturge,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導演只要我的希臘悲劇知識不要別的。另一種是需要花費大量時間的、涉及藝術想法生成到最後產出,Dramaturge的工作在劇組就需要有一定預期的報酬。
陳佾均:
對,涉入比較多就一定比較多,大概就跟一個設計差不多,那是一個時間成本和能量的問題。現在也越來越多集體創作,對設計們也是一樣,不只是戲劇顧問,會希望你從概念發想就在,互動與期待不同,費用就不同。我想補充的是,過去大家對合作的想法比較刻板,可能比較會是以請教專家的態度,專家也比較是用給筆記的方式,如果只有這種可能就比較可惜,尤其是如雙方期待有落差的話。其實戲劇顧問和創作者的互動還有很多的可能性。我的意思不是說專家一定要跟創作者混在一起,有些學者他也是真的有興趣了解劇場人怎麼工作,但有的也不需要。
高美瑜:
以我對公部門的觀察,雖然中山大學不能全部代表公部門,但在整個產業生態還沒有很理解Dramaturgy的情況下,建議公部門或國立院校先不要急著成立科系或做任何建制的動作。目前看到,臺灣戲曲中心或是松菸,都是從出資者或是官方角度,以安排或指定的方式,要求參與某項計畫補助案的劇團必須設置Dramaturge一職,而不是來自於劇團自己的需求。無論是劇團本身或公部門,皆可能因為不理解Dramaturge究竟能做什麼,而直接依中文「戲劇顧問」表面的意思,找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來當「顧問」,而非真的需要他。學戲曲出身的我比較關心戲曲界的問題,也就是傳統戲曲團隊需不需要這個角色?也許像搬演莎劇或其他跨文化的文本時有這種需要,此時劇團自然會去尋求專家的協助。我認為從劇團需求出發,找到自己想要合作的對象以及需要Dramaturge做什麼,蒐集足夠的民間需求再做建制也不遲,否則科系一旦成立,公部門資源一窩瘋跟著投入,反而引導了產業生態,Dramaturge的意義和作用就會歪掉,建議先從案子、課程、學程做起。
2018–07–23首發於表演藝術評論台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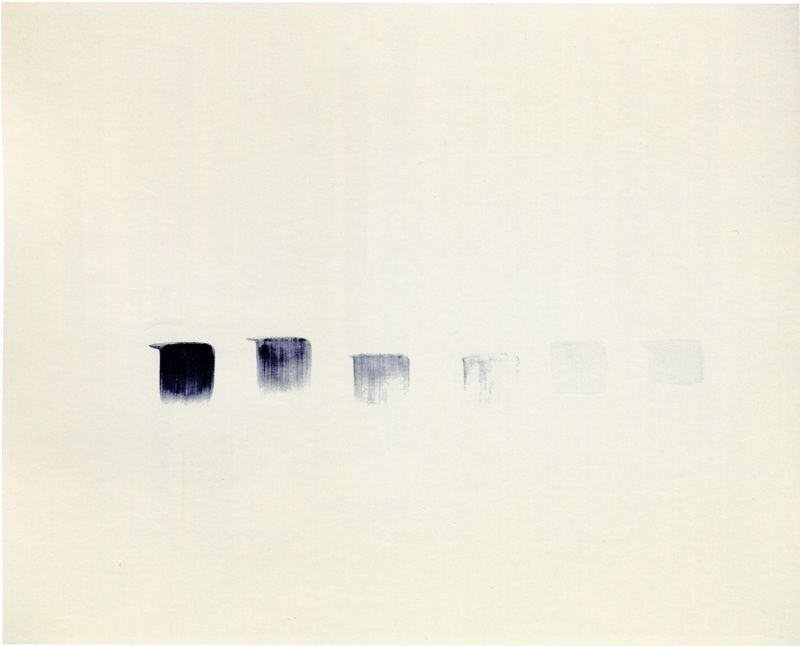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