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兮魔兽》:沉默的地狱,无人的天堂
当我第一次发现在豆瓣上搜不出《悲兮魔兽》的影视词条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部禁片,而是怀疑自己打错了这个略显拗口的名字;就像在我第一次听说这部影片的英文版标题“Behemoth”时,并没有想到这是一部中国导演的作品。
1 叙事结构:神曲写人间
一部借用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Divine Comedy)》的情节结构作为叙事构架的影片,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首映并入围主竞赛单元,简直是其最好的面世时机。在《神曲》中,但丁“自述”了自己追随维吉尔(Virgil)的向导,经历地狱(Inferno)、炼狱(Purgatorio)和天堂(Paradise)的诗人旅程。影片充满了对《神曲》的象征性借用,用来描述内蒙古地区从矿物开采,到钢铁冶炼、城市建设的巨大产业链。导演以赤裸地睡卧在土地之上的肉体自比但丁,以背负着半人高的镜子的工人向导象征诗人维吉尔;影像以纯色画面的突然出现与淡出作为不同主题篇章的转场过渡,黑色与红色象征地狱,灰色象征炼狱,蓝色象征天堂。



1.1 黑色的矿山幽谷,红色的炼钢厂
中文片名“悲兮魔兽”是Behemoth的音译,出自《圣经》旧约,是上帝创造的一只可以吞噬山丘的混沌怪物(chaos-monster)。影片以巨大的矿山爆破声和深沉嘶哑的图瓦呼唛(一种喉音唱法)开场,仿佛远古巨兽的狂叫与嘶吼。黑色的矿山幽谷是巨兽掘蚀的累累伤痕,也是矿工日复一日的人间地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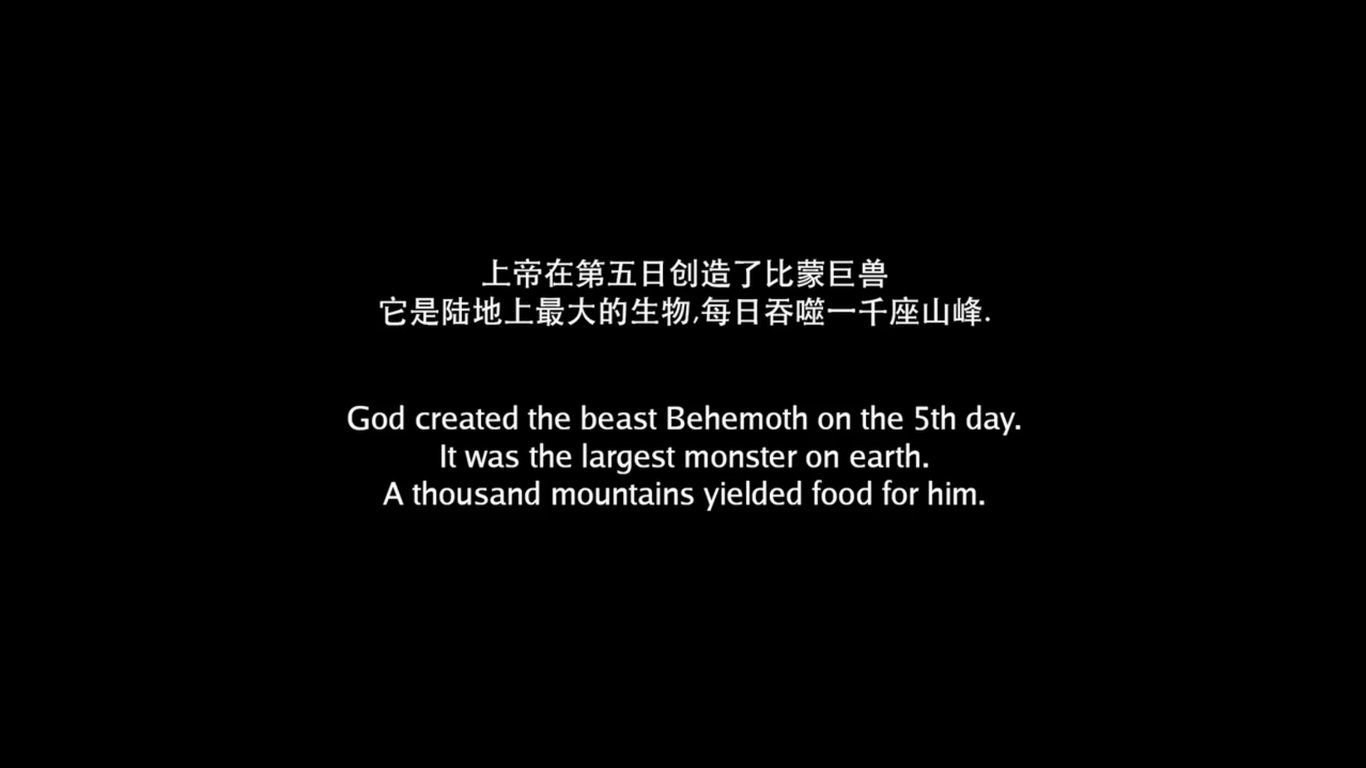
第一部分的影像叙述并不连续,镜头画面的切换之间没有连贯的逻辑关系,更像是刻意为之的破碎拼接和生硬对比,亦如撕裂的地景。旷野上的游牧家庭和矿的劳作、休息景象交织反复;草原、矿山、井坑、员工宿舍、家庭的场景来回穿插。

在导演的记录中,不论是运煤的夫妇还是下矿井、开矿车的工人,下工回到家中后,他们似乎都有一件尤为重要的事情:洗脸,认真地、精细地、费力地洗脸,洗去脸上的矿土和煤尘。在旁白中,导演称之为“粉墨(makeup)”,工人们满脸煤灰的肖像特写也成为作为影片中最有标志性的视觉语言之一。但我仍然觉得,对洗脸这一动作的观察性记录比诗意的描述和直接的凝视都更加意蕴深远。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巧合,我在第二次回看影片时才注意到,在导演镜头追随的一个矿工床铺上方,墙壁上写了一个大大的但并不显眼的“忍”字。当然我其实也不知道工人写下这个字时意指何如,甚至不一定是目前的这位工人留下的。但在“地狱”里,最大的考验不就是对“罪罚”的长久“忍受”吗?


由红色幕布转场过渡的钢铁厂是全片最“激烈”的段落。跳动飞溅的、猩红色的铁水和剧烈沉重的鼓点节奏与沉闷的矿山截然不同。如果矿井是地狱的苦役,那钢铁厂大概就是地狱的酷刑。

1.2 灰色的尘霾,蓝色的城市
与《神曲》3x33章均等结构极为不同的是,影片中灰色所代表的“炼狱”和蓝色所代表的“天堂”占比却很小。我不清楚这种时间比例的严重倾斜是导演有意为之还是素材所限,但从结果呈现来看,却很有巧妙之处。导演用了四分之三的篇幅写矿井与钢铁厂的“地狱”。一方面,当然是为了更多地展现这一产业链对原产地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和人力成本。但另一方面,从矿山到城市似乎也可以被看作是底层劳工的“人生路径”,或者至少是被工业化、城市化所宣扬的一种人生奋斗理想范本;在糖衣之下,却是长久的、日复一日的磨难与劳作占据了大部分的人生。
在《神曲》之中,炼狱,与地狱和天堂最大的不同,在于时间的流逝。时间在地狱和天堂是停滞的,亦是无尽的、轮回的;而炼狱中所受的苦难却有终结之日【1】。烟囱、雾霾、病房、手术室、尘肺病人沉重的呼吸、白色的抗议横幅……以及昭示着一切终结的坟墓,是“炼狱”的地景,也是尘肺病人漫长又短暂的生命倒计时。
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天堂”的取景,选在了鄂尔多斯的一处“鬼城(ghost city)”。兴兴建造的城市是辛苦劳动之人的向往之所,也是煤钢产业链的尽头。色调虽然鲜艳而又明亮,但“天堂”无人,只有无云的天空、空荡的街道和阵列的住宅楼。
2 视听语言:凝视与沉默
影片介于纪录片与艺术电影的中间地带,非虚构的纪录与虚构的“表演”、超现实的布景交织。
从学习的角度而言,影片的镜头语言是易学的。总体上,导演倾向于使用一种摄影式的静态拍摄方法,构成了一种非常标志化、风格化的镜头美学。尤其在拍摄地景时,很多时候先是固定的机位与镜头记录场景中一段时间内缓慢重复的机器移动和工人劳动。接着镜头缓慢地平移或旋转,形成一种长卷式或全景照片式的场景记录和一种空寂、辽阔的影像氛围。
在一次采访中,导演被问到和被拍摄对象的关系,他说摄像机是他打猎的枪(“The camera is my gun for hunting”)【2】。我确实在导演对人物对象的拍摄中感到了一些攻击性,并且因此感到一些“不适”。导演似乎刻意在以一种和拍摄机器相似的方式“凝视”被拍摄的工人们,镜头下的工人是沉默不言、没有情绪的。每当我看到影片中两组对煤矿工人和炼钢工人的脸部肖像特写,我总是试图去设想还原导演在拍摄之前是如何与他们进行沟通的?我当然不得而知。我只能揣测,导演拍摄这组影像的首要目的似乎是为了直观地展现煤灰与汗水在脸上留下的辛劳的痕迹,而并非拥有这些“脸”的人们。导演保留了一些“不自然”的影像片段,工人们在拍摄过程中不经意瞥到镜头或忍不住瞟向镜头的尴尬眼神,是打破这种“凝视”关系的瞬间,作为观众的我总是不禁为镜头的“冒犯感”感到抱歉。当一个人没有情绪表达、没有语言的时候,和受难的机器有什么区别呢?工人们在电影里发出唯二的声音是尘肺病人沉重又微弱的呼吸和咳嗽,与总是突然出现的、音量巨大的器械作业声和制作的音效形成鲜明的对比。将工人们“机器化”的当然不是导演赵亮,我也相信“沉默地劳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工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导演只是带领观众顺应“真实”地凝视着一切,可我总在他们目光瞟来的瞬间想,他们或许也是有话想说的吧?只是我听不到。

在大量静态的、凝视般的镜头之外,也有一些片段呈现移动的视角,且往往带有超现实的意味,例如手持镜头跟随背着镜子的“向导”、在草原上搬家的队列。关于超现实画面的讨论在影片放映之后其实很多,甚至往往是在表达技法方面最受关注的部分,倾向于被解读为一类颇具象征意义的符号,例如背对镜头的裸体、仿佛镜面破裂的画面、绿植盆栽、佛头、镜子等等。它们当然充满了导演想要传递的种种隐喻,但于我而言,这些超现实的画面只是一些填充叙事结构的微小支架,是缠织在非虚构内核上的外壳,使故事的外形更加饱满。
3 魔兽(Behemoth)是谁?
最后,在追随“向导”的晃动镜头中,导演说“我们就是那魔兽,那魔兽的爪牙”。但“我们”又是谁呢?作为“爪牙”的“我们”是每一个底层劳工, 在自己帮忙建造的“地狱”中忍受一掘一铲的辛劳,洗赎吞噬山峦的罪孽;作为混沌怪物的一部分,“我们”在说不清道不明的裹挟之中机械地共同破坏,却孤独地承受后果。

导演在后来的采访中有直接地谈到这部电影对于社会主义工人境遇的关切以及对于他们坚韧毅力的敬佩【3】。当然,电影是有批判的意味在的,批判工业系统对于工人的冷漠与剥削,批判房地产开发的肆虐与资源浪费,批判人类物种的贪婪。但我认为,电影与其说是在批判,不如说是在表达一种悲哀以试图唤起一种泛泛的反思。换句话说,电影中并没有指出明确的被批判主体。就像混沌的怪物,裸露出爪牙,本体却仍在雾霭之中。通过对于生态地景的展现、工人劳动环境的恶劣,配合诗意的旁白,导演直观地呼唤一种震撼和悲悯的观众情绪,但也止步于此了。全人类终将共同地面对环境破坏带来的灾难,但灾祸与磨难并未公平均等地降临在每一个人身上。鬼城无人,但导演和观众都知道,那里并非真正的“天堂”。工业生产底层的劳工在天堂城市里找不到蔽身之所,资本市场的巨手却可以自由地遮掩行踪。
或许,只是或许,导演是在巧妙地反叛以规避审查,但仍然无法逃离“禁片”的命运。
参考文献
【1】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E-Uqjox5UM
【2】http://www.filmcomment.com/blog/interview-zhao-liang-behemoth/
【3】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