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5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卡尔·波普
野兽按:《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卡尔·波普尔关于政治哲学的一本著作。本书批判历史主义的目的论(历史发展有必然性,历史根据普遍规律而发展,人的主观意志不起作用),批判对象包括柏拉图、黑格尔和卡尔·马克思,指他们以历史主义为依托、巩固自己的政治理念。桂冠图书正体中文版译者是东吴大学哲学系教授庄文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简体中文版译者是陆衡等。
2020年4月,商周出版发行了全新修订译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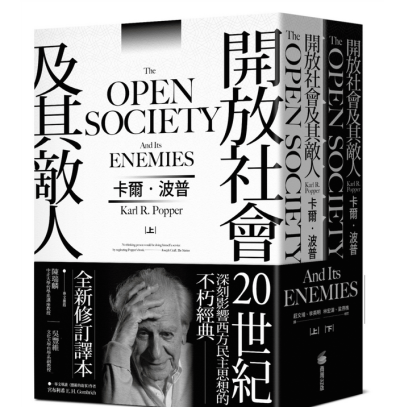
真相已死,民粹當道!
在這貌似自由開放的年代,
我們是否已在渴望封閉社會的回歸?
☆自由主義巨著,深刻影響殷海光等台灣知識份子☆
☆75週年經典回歸,全新修訂譯本☆
——「極權主義對於文明的反叛,和民主文明本身一樣源遠流長 。」
《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是理解近代西方民主思想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作者卡爾・波普(Karl Popper, 1902-1994)被譽為20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1937年,他為逃避納粹迫害,移民紐西蘭,1946年二次大戰結束後遷居英國。波普原本主要的研究領域是科學哲學,但從1938年開始直到冷戰結束,他將關注轉至政治哲學,尤其著眼於如何對治、批判納粹德國、蘇維埃主義等極權思想,《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便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1945年出版後,旋即轟動西方學界,也奠立了波普無論在左派或右派都屹立不搖的劃時代地位。
本書分為上下兩冊,分別為「柏拉圖的符咒」及「預言的高潮:黑格爾、馬克思及其餘波」。在書中,波普批判了三位西方傳統中的思想巨人──柏拉圖、黑格爾與馬克思。波普認為他們的思想構成了當代極權主義的起源,也是20世紀種種暴行的基礎;黑格爾、馬克思的歷史定論主義,更否定了人們改變與做出選擇的可能性。
波普主張:理想的社會,應是一個建立在自由討論與理性批評之上的開放社會,而開放社會的敵人,即是不容異見的獨裁專制,以及伴隨暴力手段的烏托邦理想。後者甚至可能毀滅人類文明,重返極權的部落主義。他也強調:開放社會的敵人,同樣會打著「開放」旗幟,而行專制之實。只有清晰分辨這種虛偽,肯定理性與自由,才能在政治、社會制度以及種種問題上,求得實際合理的根本解決,並創造出更理想的未來。
作者簡介
卡爾・波普Karl Popper
1902年生於奧地利維也納,為猶太人。1937年,因奧地利被納粹德國吞併,被迫流亡至紐西蘭,於坎特伯雷大學任哲學講師。1946年遷居英國,任教於倫敦經濟學院,講解邏輯和科學方法論。1965年受封為爵士,1976年當選皇家科學院院士。1982年獲頒榮譽侍從勳章。1994年逝世於倫敦。
波普被公認為20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哲學、科學哲學家之一,以否證論、開放社會理論聞名於世。代表作有《科學發現之邏輯》(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歷史定論主義的貧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等。影響許多當代知名的思想家、科學家與經濟學家,如費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索羅斯(George Soros)等。
譯者簡介
莊文瑞
臺灣大學哲學博士,曾長年任教東吳大學哲學系,研究領域包含科學哲學、知識論、邏輯、死亡學與政治哲學等。譯有《培根》、《邏輯與哲學》、《西方的智慧》等書。
李英明
臺灣彰化人,政治大學法學博士,曾任政治大學東亞所所長,現任中原大學副校長。譯有《科學社會學》等,著有《論馬克斯恩格斯的科學觀與辯證法》、《哈伯馬斯》、《文化意識型態的危機──蘇聯、東歐、中共的轉變》、《資本論導讀》、《社會衝突論》、《全球化時代下的台灣和兩岸關係》等多本著作。
【上冊】
編輯人語
專文推薦/在二十一世紀讀《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陳瑞麟
專文推薦/以理性持續走向啟蒙與開放的社會 ◎吳豐維
專文導讀/關於《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出版緣起的個人回憶 ◎宮布利希
致謝
第一版序
第二版序
緒論
第一部 柏拉圖的符咒
宇宙起源和命定的神話
1 歷史定論主義和命定的神話
2 赫拉克里圖斯
3 柏拉圖的理型論
柏拉圖的描述社會學
4 變動與靜止
5 自然與約定
柏拉圖的政治方案
6 極權主義的正義
7 領袖的原理
8 哲人王
9 唯美主義、完美主義與烏托邦主義
柏拉圖的抨擊的時代背景
10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附錄
柏拉圖和幾何學(一九五七年)
〈泰阿泰德篇〉的年代問題(一九六一年)
答辯(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五年增補
【下冊】
第二部 預言的高潮:黑格爾、馬克思及其餘波
神諭哲學的興起
11 黑格爾主義的亞里斯多德根基
12 黑格爾與新部落主義
13 馬克思的社會學決定論
14 社會學的自主性
15 自然與約定
16 階級
17 法律和社會系統
馬克思的預言
18 社會主義的來臨
19 社會革命
20 資本主義及其命運
21 對馬克思預言的評估
馬克思的倫理學
22 歷史定論主義的道德理論
餘論
23 知識社會學
24 神諭哲學及反理性
結論
25 歷史有意義嗎?
附錄
一、事實、標準與真理:再評相對主義 (一九六一年)
二、評註史瓦茨雪德論馬克思的著作 (一九六五年)
桂冠版代譯序:論「理性與開放的社會」 ◎莊文瑞
桂冠本修訂版序:卡爾‧波普的細部社會工程學說 ◎莊文瑞
桂冠版謝辭 ◎莊文瑞、李英明
在二十一世紀讀《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陳瑞麟/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講座教授
對科學新聞感興趣的人,也許會看過某些大科學家談做科學的目的,在於「否證」或「推翻」一個理論假設;對金融經濟感興趣的人,也許會關注索羅斯(G. Soros)和「開放社會基金會」的新聞。1「否證」與「開放社會」看似毫不相關,其實都是二十世紀大哲學家卡爾.波普最重要的思想遺產:前者是一個科學哲學理論的核心;2後者是一個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理論的核心。兩者可以說都是波普同一個哲學觀點在自然科學領域和社會政治科學領域的展現。
《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是一本批判極權主義的經典,成書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其時,極權主義右翼的法西斯主義國家德國和義大利,正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令知識分子感到深惡痛絕。相反地,標榜左翼的馬克思主義與共產主義,從《資本論》出版以來,吸引全球大量知識份子追隨,其時更在蘇聯的帶頭之下對抗法西斯主義。這樣看來,馬克思主義似乎屬於反極權主義的陣營?然而,《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批判的標靶之一,卻正是馬克思主義!為什麼?馬克思主義為什麼是開放社會的敵人?
二戰之後,全球陷入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壁壘分明的冷戰年代,波普和其他反對極權主義的思想家如海耶克(Hayek),成為二十世紀自由主義的最佳辯護士,他們的思想一起遠渡重洋,深深影響了台灣的自由主義思想家殷海光,3以及殷海光以降的知識份子,催生了日後的台灣民主化運動。這是《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對台灣的實質貢獻。可惜,在威權統治之下,即使批判馬克思主義,波普這本巨著直到一九八四年才被莊文瑞教授和李英明教授合譯成中文,由桂冠出版社出版,並馬上成為當時人們推崇的自由主義寶典。然而,一九八〇年代末起,由於解嚴之故,台灣慢慢步入波普所言「開放社會」,各種新奇的西方思想大量湧入台灣,曾為禁忌的左翼馬克思主義,搖身變成吸引文青的新思潮,強烈批判馬克思主義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反而逐漸淡出知識分子的視野。
二十一世紀已過二十年了。從一九八〇年代到今天約莫四十年之間,我們經歷了全球局勢的巨大變動。最重要的事件要數中國自一九七九年起的改革開放和資本主義化,經過三十年,中國憑藉其龐大的勞動力而變成「世界工廠」。遺憾的是,中國並沒有像其他東亞國家一樣,在現代化之後進一步走向民主化,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反而以長期累積的工業與國家資本的力量,加上當代的數位科技,把中國打造成一個嶄新的數位極權國家,並自豪於中國已經創造了一個「中國模式」,足以與「西方模式」並駕其驅、甚至取而代之。中國已經蛻變成二十一世紀新極權主義的領頭狼,它所威脅的不僅是台灣,也包括全世界其他自由民主的國家。在二十一世紀的新局勢之下,商周出版把桂冠當年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加以修訂重出,顯得特別應景。
現在,擺在我們眼前的問題是:該如何重新閱讀、使用這本一九四〇年代批判極權主義的經典?讓我們回到之前的問題:為什麼當年對抗法西斯極權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本身也是另一種極權主義?關鍵在於「歷史定論主義」(historicism)這個概念。
波普認為「開放社會」的敵人是政治哲學上的極權主義思想,代表性人物是兩位西方哲學與思想史上影響最弘大又深遠的哲學家:古希臘的柏拉圖和十九世紀的馬克思。兩人的年代相差極遠,思想系統也大相逕庭。可是,在波普看來,共同點在於他們的社會科學理論,都滲滿「歷史定論主義」的錯誤。歷史定論主義是關於人類社會發展過程的理論,主張所有人類社會都會循著一條歷史發展的法則,註定(必然地)走到預定(言)的目標或終點。這條法則,主要是由於經濟力量與政治力量交織而成的,因此透過政治與經濟的研究,找出歷史法則,就可以預測社會的未來或預知歷史的最終目的。從預定目的注定會實現這一點來看,歷史定論主義又可稱為「歷史目的論」(historical teleology)(波普自己沒有使用這個詞)。歷史定論主義預設社會科學研究的集體主義(collectivism)和全體主義(holism),也預設歷史法則必是政治經濟法則,這兩個預設共同為政治的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搭建了溫床。
今天中國政府的思維和論述,是不是充斥著「歷史定論主義」的氣味?中華人民共和國把「鬥爭」和「集體」寫入其憲法中,在官方文件裡充斥「國家」、「秩序」、「神聖」、「必然」、「絕對」、「堅定」、「偉大」、「統一」、「齊一」、「犧牲奉獻」這些「強大有力」的字眼,中國政府動輒「統一是必然的」、「社會主義是唯一歷史正確的道路」等宣稱,在在迴響著「歷史定論主義」與「極權主義」的泛音。
當然,《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不只是批判對手,也積極正面地建立能營造出「開放社會」的理論架構:事實與規範(決定)的二元論、方法學的個人主義、漸次的社會工程學、社會變遷的體制主義(或「制度主義」)等。對於前幾個觀念,讀者可以參看莊文瑞教授的兩篇序文簡介,我在此簡單談一點莊教授沒談到的「體制主義」。
波普駁斥存在一種朝向特定目的歷史法則的論點,但是他並未否認有國際貿易理論、景氣循環理論等等重要的社會學法則,波普認為它們是社會體制的功能。「社會體制的建構基本上是遵守若干規範,而後者是人為了某種目的而設計的,特別是刻意創設的體制。」(第五章)人為的社會體制的維繫或改變產生了社會變遷,這表示人類可以掌握自己的未來,而不是遵循什麼必然且不可變易的歷史法則。基於這樣的觀點,波普也批判馬克思的「經濟歷史定論主義」,其主張一切政治或法律制度,都不再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只是生產力決定的結果。波普反過來論證:好的政治制度(如民主制度)才有可能產生良好的經濟成果──這種觀點,得到二十一世紀經濟學家的實證研究的強烈支持。4從這裡也可以看出《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持續邁入二十一世紀的歷史意義!
對於西方哲學和政治社會哲學有所接觸的讀者,可能會對波普貼在柏拉圖和馬克思哲學上的標籤感到些許困惑:柏拉圖的「理想國」和「哲人王」(philosopher king)不是倍受稱道嗎?馬克思哲學的「勞動異化」的概念不是深具人道關懷嗎?5如果你有類似困惑,這正好可當成你閱讀本書的動機。甚至,你可能在投入閱讀之後,發現波普其實非常稱讚柏拉圖的天才和馬克思的人道情懷啊!那為什麼又強烈地批判他們的理論呢?這正是波普從他的「批判理性主義」思想風格中體現的著作風格:批判不是一昧否定,而是給予對手最合理、最堅實的詮釋,再以更周全、更敏銳的分析和論證來駁倒對手。是不是如此,我只能請讀者親身印證。
最後一個問題:誰應該讀這本書?如果你對科學哲學有興趣,而且已接觸過波普的科哲理論,那麼透過《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可以看到波普如何在政治社會領域中鋪陳思路、滔滔雄辯、力駁群哲;如果你對社會政治領域、相關哲學、民主理論與各種政治上的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極權主義等等)有興趣,當然更不該錯過這本巨著。
注釋:
索羅斯是一位爭議性人物,他靠股市與金融投資累積財富,得以位列全球富豪排行榜之內。他曾師事波普,深受波普「開放社會」思想的影響,因此成立「開放社會基金會」,推動自由、民主、人權、開放社會等理念,曾介入多國政治、經濟事務,引發一些國家的金融問題,而被相關國家政府指責。但他也是一位慈善家,持續捐出大筆款項以扶助弱勢與貧困,這兩種看似矛盾的行為,其實都是在身體力行地實踐波普的「開放社會」理念。 ↩
對波普的科學哲學「否證論」內涵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見「線上華文哲學百科」林正弘(二〇二〇),〈卡爾.波柏〉一文;另見陳瑞麟(二〇一〇),《科學哲學:理論與歷史》第三章。 ↩
參看殷海光在一九六六年發表的《中國文化的展望》第十二章〈民主與自由〉的論述。見二〇一一年台大版「殷海光全集」第二冊。 ↩
例如二〇一二年出版,在二〇一三年被譯成中文的《國家為什麼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衛城)這本書。兩位政治經濟學家艾塞魯默和羅賓森使用大量的具體案例,辯護一種「制度主義」的立論,主張正是不同的制度使得不同的國家變得富裕或貧困。他們最新的著作《自由的窄廊》則是一本回答波普所謂「自由的詭論」的問題,即「自由」如何可能與強大的國家機器共存的實證研究,這兩本書都可以看成「認可」(corroborate)《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的社會與政治理論。 ↩
對很多當代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者而言,馬克思主義最值得稱道之處正在於他的人道情懷,例如他的早期著作《一八四四年經濟學與哲學手稿》。至於《資本論》一書有三巨冊,非專業研究者大概不容易消化。讀者可對照著看萬毓澤教授的詮釋《你不知道的馬克思》(木馬文化)和《資本論──完全使用手冊》(聯經)。 ↩
以理性持續走向啟蒙與開放的社會
文化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吳豐維
出生於奧地利的猶太裔哲學家卡爾.波普,是二十世紀科學哲學最重要的奠基人物,一九三四年即以《研究的邏輯》(Logik der Forschung)一書在德語世界獲得相當的成功(一九五九年的英文版改以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的書名出版),得到維也納學派與海耶克的注意。然而,他在學院生涯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間他遠走到南半球的紐西蘭任教。直到一九四五年出版了《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不僅成為他最廣為世人傳頌的著作,也為他爭取到了倫敦政經學院的教職,將他一舉推向哲學世界的中心。
波普以自視甚高、難以相處聞名,讀者若翻開《開放社會》一書,不僅可以看到他上下縱橫、評點古今哲學大家,也可以讀到他對同期哲學家維根斯坦、海德格、雅斯培等人不客氣的針砭。《開放社會》的文氣壯志凌雲,但此書的寫作過程卻是波普學術生涯中相對低潮的時期。他在坎特伯雷大學(University of Canterbury)教學負擔繁重,而且校方(尤其是系主任)並不支持他的研究。他心中夢想的去處是海耶克任教的倫敦政經學院,但是他的出版份量不足,不利他爭取教職,《開放社會》是四十二歲的他的最後一搏。(註)最後,《開放社會》獲得海耶克的高度讚賞與協助出版,波普也在其力薦下前往倫敦任教。
此外,他在書序裡稱自己的寫作是受到一九三八年三月納粹德國入侵奧地利的刺激,是對極權主義及其思想底蘊的挑戰。然而,《開放社會》的孕育卻是無心插柳的結果,是波普寫作《歷史定論主義的貧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一書的副產品。波普在自傳裡提到,他一九三六年受邀到海耶克的討論課上演講歷史定論主義的貧困,之後著手改寫,結果篇幅越寫越大,只得切割出來另外成書,就成了《開放社會》一書的雛形。因此,《開放社會》其實是《歷史定論主義的貧困》的姐妹作。《開放社會》的洛陽紙貴,有部分因素是與二戰後反法西斯的時代氛圍相契,甚至波普對共產制度的批評也剛好對準了冷戰下西方世界的主旋律,然而,嚴謹的學術根底與宏觀的史識,更是此書成功的關鍵。
《開放社會》是一本大部頭的著作,英文版七百多頁中就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密密麻麻的注釋,展現了波普資料搜集的認真與嚴謹。除此之外,這是一本論戰性格十足的哲學著作,針對性極強,批判的對象就是二次大戰期間肆虐歐洲的極權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波普認為,在這個民主國家面臨存亡危機的時刻,自身的敵人不是門外來的陌生人,而是內在於歐洲文明的思想傳統,尤其是柏拉圖、黑格爾以及馬克思這三位哲學史的偉人。他認為,柏拉圖與黑格爾成為了歐洲法西斯政權的共同思想根源,而馬克思則啟發了俄國史達林錯誤的規劃經濟,他們三人的思想將導致歐洲社會的閉鎖與部落化,因此他在序言直言「偉人可能會犯大錯」,為了使我們的文明持續下去,世人「必須拋棄順從偉人的習慣」。
為何波普將柏拉圖、黑格爾與馬克思三人視為是當代民主社會的敵人?原因就在於他們共同的思想特色:歷史定論主義(historicism)。必須注意的是,波普所謂的歷史定論主義有其限定的意義,是指「相信人類歷史具有如自然一般的法則,只要發現這些法則,我們就可以預言人的命運」的學說。波普身為科學哲學家,同時也對社會科學的哲學與方法論感到興趣,他的問題是:歷史定論主義可以成為自然科學般的方法論嗎?他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認為,在自然現象上,我們發現不因人類意志而左右的自然法則,但是在人文與社會現象裡,我們所形成的規範則是人為而變動的。因此,波普反對人類歷史有任何既定的規律與法則,他認為「未來操之在我們,而我們並不依賴任何歷史的必然性」,若我們相信歷史有必然的發展軌跡,將會把人類社會導向他所謂的封閉社會(closed society)。在波普看來,柏拉圖所建構的「理想國」、黑格爾談的「精神」與「辯證」、馬克思談的人類社會的演化,都具備如此的封閉性。
在三人之中,波普對柏拉圖的批判最為嚴苛,他幾乎將柏拉圖視為是蘇格拉底的「猶大」(Judas),背叛了蘇格拉底的批判性與對民主雅典的信念,而走向嚴格階級制度、思想審查、阻止政治變動的極權主義制度。波普也視黑格爾為康德批判哲學的叛徒,將原本被康德貶為「幻象的邏輯」的辯證概念,轉變成精神發展的內在邏輯,並積極地為普魯士王國的官方意識形態服務,成為德國國家主義的思想根源。不過,波普卻對馬克思相同同情與欣賞,他肯定馬克思對人道與自由的追求,他對馬克思的批評主要是方法論,尤其是馬克思視之為科學的歷史唯物論。波普認為,這三位哲學偉人自以為作出了如同自然法則一般的科學預測(scientific prediction),其實給出的是神諭般的歷史預言(historic prophecy),前者可以促進知識的增長,後者則對人類社會的發展有害。在波普看來,他們三人都懷有某種理想社會的設定,採取的是一種他所謂的「烏托邦社會工程」(utopian social engineering),試圖將原本不完美的人類社會改造成完善的版本,實質上則是將人類社會推向不再變動的封閉社會,當代的法西斯主義與極權主義正是他們思想影響下的產物。
身為科學哲學家的波普認為,人類知識的增長過程是透過無數次的試錯(trial and error),我們無法設定知識與真理的最終樣貌,只能努力否證自身的猜測與假設,因此,知識的探索過程是無窮無盡、沒有終點的。波普將這套科學哲學放在自己的政治哲學,提出了「細部社會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的主張,認為一個開放社會(open society)應當採取局部與有限的社會改良,並經過不斷的嘗試與偵錯,不應當預設最終的理想面貌,而與柏拉圖等人的「烏托邦社會工程」大相徑庭。在波普所設想的開放社會中,人們抱持的是一種「批判態度」或「理性態度」,勇於自我批判、自我挑戰,從不預設自己的觀點是不可錯的真理,他將之稱為「批判的理性主義」(critical rationalism)。這就是波普對於受極權主義肆虐的歐洲文明的解方:以自由、開放、民主、批判的態度重建自身的文明。
從《開放社會》一書不難看出,波普的思想典範是康德這樣的理性主義者,他所嚮往的精神遺產正是啟蒙時代的思想。因此他在書序裡就表達了,自己的聲音就像是十七、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的推動者,自己的志業如同三百年的運動一樣,「努力使自己的心靈免除權威與成見的束縛,努力建立一個拒絕絕對權威的開放社會,使其符合自由、人道與理性批評的標準」。身為啟蒙理性的繼承人,波普認為自己在柏拉圖與黑格爾身上看到了反理性的部落主義(tribalism)的傾向──凸顯規範的神秘與禁忌、訴諸集體主義(collectivism)而貶抑個人的獨特性,甚至將國家視為神聖的有機整體。
儘管如此,有許多學者指出波普對於柏拉圖與黑格爾的詮釋過度武斷與不公。例如,波普在自傳裡便承認,自己在撰寫《開放社會》一書時,正是二次大戰打得熾熱之際,遠在紐西蘭的他在搜集資料上有不少困難,例如,在閱讀柏拉圖的著作時往往找不到最佳的譯本,必須自己辛苦地在古希臘文原典裡摸索。儘管如此,波普不僅是第一流的科學哲學家,他也發揮了驚人的哲學史洞察力,在古希臘哲學、德國觀念論與十九世紀社會科學哲學的發展中找出彼此的親緣性與內在關聯,並進一步提出他對二十世紀極權主義發展的診斷與解方。在閱讀《開放社會》的時候,讀者站在波普的肩膀上,看到的不只是個別與斷裂的哲學理論,而是縱貫兩千多年政治哲學與社會哲學歷史的史識。
《開放社會》出版迄今已經七十五年,人類已經走過二次大戰後的凋敝,走過了冷戰,走入全球化的二十一世紀,然後又面臨排外與民粹浪潮的世界格局。波普這部反思二十世紀極權主義的巨作,時至今日是否仍有意義?答案是肯定的。極權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並非只拘泥於某個特定的政權與國家,它所內蘊的反理性、反個人、崇尚部落主義、迷信禁忌與權威的幽靈,仍舊徘徊在我們的世界。如同康德在兩百多年前對啟蒙運動的總結,啟蒙的精神就是「走出自我導致的蒙昧狀態」,唯有仰賴眾人的理性運用,人類才能走出權威的桎梏與束縛。不過,康德也提醒,切莫以為人類已經到達啟蒙的完成階段,我們仍在啟蒙的道路上。同樣地,波普也相信,開放社會沒有完成式,它總是在與封閉社會與部落主義的搏鬥中體現自身,理性是我們的武器,開放則是人們永恆追隨而沒有終點的理念。
註:關於此書出版的曲折歷程,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波普本人的自傳《無盡探索》(Unended Quest: An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 Routledge, 1992)以及其好友宮布利希(Ernst Gombrich)寫的個人回憶(“Personal Recollections of the Publication of The Open Society”,收錄在Popper’s Open Society After Fifty Years: The Continuing Relevance of Karl Popper, Routledge, 1999)。
編輯人語:《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出版緣由
商周出版編輯 梁燕樵
《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是20世紀大哲學家卡爾‧波普政治哲學的代表作。首次出版於1945年,隨即在西方學界引起轟動。這部作品以充滿激情的筆調,力斥極權主義與當時流行的馬克思主義,擁護自由民主與理性思想。雖然書中對柏拉圖、黑格爾的詮釋與抨擊,引發了諸多爭議,但仍無損其地位,深刻影響了西方的自由主義與民主思想。
波普的思想不只震動西方學界,也飄洋過海影響了1950年代的台灣知識份子。如戒嚴時期的自由主義代表殷海光先生,便深受波普思想的感召,而波普大聲疾呼的民主自由、個人主義、開放社會等思想,也成為當時知識份子對抗專制政權的重要武器與精神支持。直到一九八四年,這本巨著終於由莊文瑞、李英明翻譯出版,一時洛陽紙貴,可惜隨年深月久,逐漸從台灣市面絕跡。
在西方,《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經歷數次修訂增補,影響力始終不衰。2013年,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以一卷本的形式將其重新出版,並加上了新的導讀與宮布利希(E. H. Gombrich)的回憶文字。2015年,美國現代圖書公司(Modern Library)將《開放社會及其敵人》選為20世紀的百大非文學作品(100 best non-fiction)之一。漫長的70年過去了,波普所抨擊的極權政體並未消失,民主、自由與理性卻面臨了前所未有的動搖與威脅。或許正是這樣的原因,促使人們必須重新回望這些理想的原初起點,而這也正是經典必須持續存在的原因。
基於這樣的想法,在2018年,我們與在東吳大學哲學系任教的莊文瑞教授取得聯繫,他欣然同意我們重新出版此書的計畫,並全權授權我們根據新版重新校訂譯文。由於當年的政治氛圍,某些較為敏感的文字,不得不加以隱諱、修飾,本次校訂則一一還其原貌。書中的譯名、哲學用語與注釋格式,也都依據新的研究成果與出版品,加以斟酌更新。此外,我們也保留了桂冠版的兩篇代譯序〈論「理性與開放的社會」〉及〈波普的細部工程學說〉,它們對於想理解波普思想的讀者,仍極具參考價值。
過程中,莊教授提供了我們許多重要而寶貴的建議,在此謹致上最深的謝忱。而中興大學歷史系的周樑楷教授,亦在史學方面給予協助,亦在此一併致謝。此外,也非常感謝宮布利希的孫女萊奧妮(Leonie Gombrich)慷慨授權我們翻譯其祖父的回憶文字,以饗讀者。
最後,我們也將此書獻給已故的桂冠圖書公司負責人賴阿勝先生。沒有他的熱心與無私,不會有《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的第一版問世,更不會有今日的全新版本。在此謹以出版人的身份致上最高的敬意。
摘自第十章〈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我們會把巫術的、部落的或集體主義的社會稱作「封閉的社會」(closed society),而把個人必須面對決定的社會叫作「開放的社會」(open society)。
我們不妨把封閉的社會比擬作有機體。所謂國家的有機體或生物學的理論,就有相當程度的適用性。封閉社會也像獸群或部落一樣,都是類似有機的單位,其成員是由類似生物鍊結的東西聚集在一起的:諸如親族關係、共同生活、分享共同的成果、共患難同甘苦等等。封閉社會是由具體的個人組成的具體團體,他們的關係不是分工、貨物交易之類的抽象社會關係;它是具體的有形關係,例如相互接觸、彼此問候等,雖然這樣的社會也許是奠基於奴隸制度,但是蓄奴的問題和蓄畜沒有太大的不同。因此,有機理論之所以不能應用到開放社會,正是因為開放社會缺少這些層面。
我所謂的這些層面和底下的事實密不可分,在一個開放社會裡,許多人都在社會裡力爭上游,以取代其他成員的地位。這點也許就導致階級鬥爭之類重要的社會現象;但是有機體裡,我們不會看到類似階級鬥爭的東西。有機體的細胞或組織有時會被比擬作國家的成員,為食物而你爭我奪;但是腳絕不會想要變成大腦,身體其他部分也不會想要變成胃部。由於有機體中並沒有任何事物可以對應於開放社會成員為社會地位而競爭的重要特徵,因而所謂的國家有機理論其實是個錯誤的類比。另一方面,封閉社會對於這種社會競爭的傾向也所知不多,包括階級制度在內的種種制度,因而都成了神聖不可侵犯的禁忌;有機體理論應用到它身上,也就不為過了。因此,我們不難發現,大部分企圖以有機體理論應用到我們社會的,原來都是以偽裝的宣傳方式要我們返回部落主義的社會。
由於開放社會缺少有機體的特性,在某種程度上,我應該稱之為「抽象的社會」。它大抵上可以說是喪失了具體或現實團體的特性,或諸如此類現實團體的體系。很少有人理解到這點;我們也許可以誇張地說:我們可以設想一個人們其實沒看過的社會—所有行業都由相互孤立的個人經營,彼此以信件或電報往來,外出也都坐汽車(就連生育都沒有個人元素,而以人工受精來繁衍後代)。這個虛構的社會可以稱為「完全抽象或去人格化(depersonalized)的社會」。現在有趣的是,我們現代的社會在許多方面很像這種完全抽象的社會。雖然我們並不會一直待在汽車裡(成千上萬的人在街上摩肩接踵),結果還是像是關在汽車裡一樣,和同行的人沒有任何個人關係。同樣,某個工會的會員的意思也只是一張會員卡,並且對素不相識的祕書捐繳交會費而已。生活在現代社會裡的人,幾乎沒有有親密的個人接觸;他們孤立而匿名地生活著,結果就是不快樂。因為社會雖然變得抽象,但人的生物性格並沒有多大改變;人有社會性的需要,而開放社會卻不能滿足這些需要。
當然,我們的描述有太過誇張之嫌。以後不會也不可能有個完全或極為抽象的社會。人仍舊會組成現實的團體,也有各種現實的社會接觸,試圖滿足人們的社會情緒需要。不過在現代開放社會裡,大部分現實的社會團體(除了某些幸運的家族外)都是可憐的替代品,因為它們不能提供一種共同生活。而且許多團體在整個社會生活裡也沒什麼功能。
我們的描述還有另一個誇大之處,那就是至今只看到它有百害而無一利。不過,它還是有好處的。它可以建立一種新的人際關係,只要人們不再被偶然的出身決定,而可以自由加入社會各個階層;因此,一種新的個人主義就應運而生。同樣的,隨著生物性和身體的關係漸趨淡薄,精神的關係則可以扮演要角。不論形如何,我們希望以上的例子可以闡明抽象社會和具體或現實社會團體之間的矛盾,也說明我們現代的開放社會的運作大體上是透過抽象關係去進行的,例如交易或合作。(現代的社會理論,例如經濟理論,也正是著眼於這類抽象關係的分析。至今仍然有許多社會學家還不明白這點,就像涂爾幹等人,一直不放棄獨斷的信念,認為社會一定要就現實社會團體的觀點去分析。)
有鑑於此,我們明顯看到,從封閉社會過渡到開放社會,可以說是人類最深層的革命之一。基於上述封閉社會的生物特性,人們對於這種過渡一定感受很深。因此當我們說西方文明源自希臘時,應該理解它的意義是什麼;它的意思是,希臘為我們開始了這個偉大的革命,而這個從封閉社會過渡到開放社會的革命迄今似乎仍然原地踏步。
當然,這種革命並不是刻意造成的。古代希臘的封閉社會、部落主義的瓦解可以上溯到統治的地主階級開始察覺到人口成長的那個時代。這意味著「有機體的」部落主義的末日到了。因為它造成統治階級的封閉社會內部的社會壓力。首先出現的是某種「有機體式的」解決方式,也就是衛城的出現。(在派遣殖民者出去的巫術儀式裡也突顯了這個解決方式的「有機體」特性。)不過這種殖民的儀式只是推遲它的瓦解而已。當它造成文化接觸時,甚至產生了新的危機。其結果是導致對於封閉社會最大的危機,也就是商業,以及以貿易和航海為業的新階級。到了西元前六世紀,這種發展已經導致舊有生活方式的部分瓦解,甚至產生一連串的政治革命和反動。它不僅導致像斯巴達那樣企圖以武力去保護和維持部落主義,也造就了偉大的精神革命,發明了批判性的討論,其結果就是擺脫了巫術性的強迫觀念。在此,我們看到第一個新的不安定徵候也出現了:那就是開始感覺到文明的壓力了。
這種壓力和不安是封閉社會瓦解的結果。甚至在我們這個時代,特別是在社會變動的時候,仍能感覺到它。這種壓力是由於開放和部分抽象的社會生活對我們要求而造成的,它要我們努力合乎理性,至少要摒棄情緒上的社會需求,要照顧自己並且接受種種責任。我認為,我們應該承受這個壓力,作為增進知識、合理性、互助合作以及存活率和人口數所要付出的代價。這是我們身而為人必須付出的代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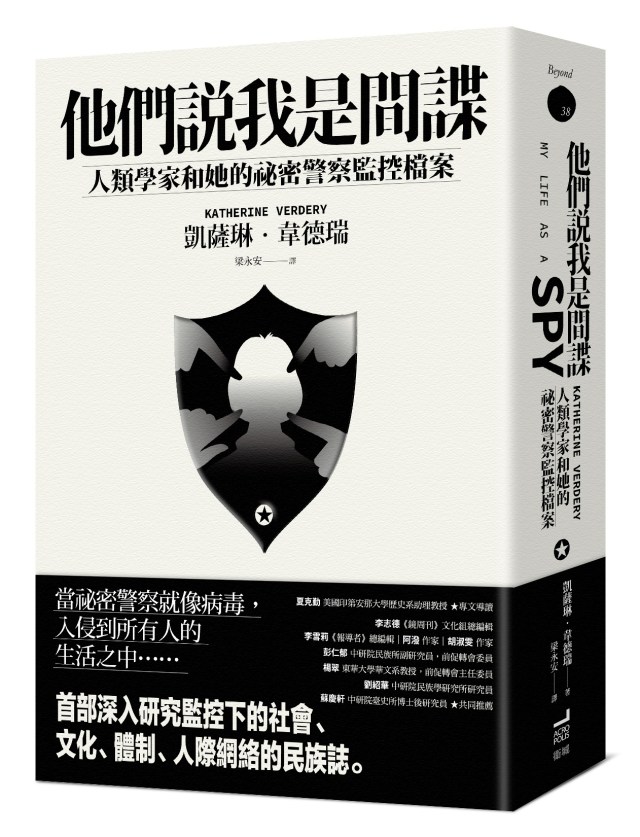
書介:《他們說我是間諜:人類學家與她的祕密警察監控檔案》
◎蘇慶軒/國立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助理教授 1
人們回顧過往,通常可以說明自己為何是現在的模樣。對於人生可以掌握的部份,自己的選擇大概影響了日後人生的發展,而另些無法掌握的部份,則可歸於不可知的命與運。不過,受過威權統治的人們卻可能有不一樣的體驗。例如受到國民黨政府壓迫的政治受難者,經過多年關押而出獄後仍須面對政府的監控,不只求職謀生處處碰壁,還要面對社會歧視與孤立,職涯受挫的憤怒與遺憾,讓柯旗化感嘆為「台灣監獄島」。2另一些未受直接迫害但懷疑自己受到監控的人們,在回顧人生時可能不免多了些憂慮,擔心自己現有的模樣,無法歸因於自己的選擇,也不是命與運使然,而是那隱約感受到的政治力量所操弄的結果,甚至猶疑自己是不是誤將政治操弄的影響,當成人生境遇的偶然或必然。
如何理解威權統治的影響與遺緒,成為新興民主社會無法迴避的問題。蘇聯解體後,已有許多研究在重建與探索威權統治下的生活樣貌,突現權力與制度如何左右被統治者的人生,祕密警察滲透社會以鞏固政權的歷史,更加吸引社會科學研究者的目光。中東歐社會探索自身歷史的經驗,也有些作品透過各種書寫與翻譯而引入台灣,但相較於主流關注政治、法律與歷史面向上的討論,衛城出版的《他們說我是間諜》則藉著人類學田野研究的特殊性,進一步呈現更加微觀的「威權統治下的人生」。
本書的作者、美國人類學家韋德瑞在冷戰時期多次深入羅馬尼亞進行田野研究,一方面成為共產主義社會研究的翹楚,另一方面也成為羅馬尼亞祕密警察監控的對象,嚴密的監控活動由此產出大量的檔案紀錄。雖然這些檔案紀錄是在描述與分析韋德瑞的活動與思想,但卻與韋德瑞認識的自己不同,其中的歧異甚至與本人的認知相互競爭,讓她重新檢視自己在羅馬尼亞的人生。因此,她以「沒有什麼比閱讀自己的祕密警察檔案會更讓你納悶自己究竟是誰」為開場,啟動一次重新認識自己的過程。
祕密警察檔案中的韋德瑞有許多版本,也有著各自的化名,但無論是哪個版本,在羅馬尼亞祕密警察眼中皆是意圖刺探情報與威脅國家安全的「間諜」。
人類學家在田野中發展社會關係與取得信任的技巧,是為了融入當地及蒐集資料,因此韋德瑞投注許多心力,以便贏得在地居民的信任與友誼。從這個角度來看,韋德瑞能夠理解田野調查引來秘密警察的懷疑,在冷戰時期實屬合理。然而,祕密警察檔案的不合理之處,在於描述韋德瑞的觀點。秘密警察拼貼著蒐集來的情報,將韋德瑞描寫成數個與她自己認知不同的人,這些「分身」在研究者的外衣下,隱匿著對羅馬尼亞的敵意,使秘密警察必須不擇手段地蒐證,揭穿她的意圖與威脅。
祕密警察檔案讓韋德瑞更加感到衝擊的,是她無法斷然否認檔案內容中的描述,因為祕密警察並非全然虛構出一個陌生人並強加在她身上,而是將她實際的活動,與祕密警察或線民的臆測雜揉在一起,或者對她的言行進行偏頗的紀錄與解讀,因此這些「分身」確實神似韋德瑞記憶中或者田野筆記記錄的自己。祕密警察的描述,讓韋德瑞產生似我而非我的衝擊,使她在比對檔案內容、田野筆記、記憶,以及重回舊地求證檔案內容的過程中,需要重新理解當時的自己與當地的居民。
檔案也顯示,祕密警察為了蒐證而向韋德瑞佈下細密的網羅,讓她難逃祕密警察的耳目。這個情蒐用的網羅,是用韋德瑞的人際關係編織而成,輔以可供竊聽與偷拍的科技工具作補強。不過,這個網羅不只用於情蒐,也用於滲透與影響韋德瑞的言行思想,包含阻撓她的研究進度、左右她的想法,甚至探弄她的人性弱點,以便誘使她產生有利於羅馬尼亞共產統治的觀點與認知。換言之,監視是為了控制,而監視與控制構成了祕密警察掌握韋德瑞生活的動態過程。
為了建立監控韋德瑞的網羅,祕密警察需要從她身邊招募線民。當年與韋德瑞相遇相識的人,可能在檔案裡也有著不為她所知的「分身」,他們在普通人的外衣下,隱匿著情蒐與側寫韋德瑞生活的任務。這些線民與韋德瑞的交情深淺不一,其中有些人與韋德瑞往來時,曾讓她感到愉快,例如熱情招待她的「雅各布」夫婦,但這些愉快的經驗其實是祕密警察授意經營的,而讓日後閱讀檔案的韋德瑞備感難受。有時祕密警察為了更深入地洞窺韋德瑞的秘密,而利用她年輕時活躍的性生活,一方面壓迫曾與韋德瑞發生親密關係的男性,要他們必須向祕密警察舉報她的動向,另一方面也鼓動其他男性向她求歡,以便刺探更多情報。或者,祕密警察決定介入韋德瑞的研究,試圖將她從依賴與人往來的人類學家,轉變成依賴圖書資料的歷史學者,因此一方面讓她難以推進實地訪查的進度,另一方面在她被迫倚重研讀圖書資料時,派了可以協助詮釋資料且受她信任的「斯特凡」在她身旁,以便達成日後祕密警察坦承的目的:「我們想讓妳愛羅馬尼亞」。
經過比對記憶與田野筆記,韋德瑞從檔案中認出了線民,並探訪其中幾位。由於祕密警察監控用的網羅是用她的人際關係編織而成,因此在探訪線民的過程中,韋德瑞發現身旁曾發生自己從未意識到的人際關係爭奪戰。
韋德瑞作為外來者,需要經營與取得當地居民的信任,才能展開田野研究;與此同時,祕密警察為了在韋德瑞身邊佈線,就需要吸收她所信任的人,才能貼身監控。換言之,越受到韋德瑞親近與信任的人,越可能成為祕密警察威脅利誘的對象,這些人必須在背叛友誼或承受迫害之間作出選擇。韋德瑞當年不知道的是,她所經營的某些人際關係在無意間成為自己的護盾,與祕密警察試圖收緊的監控網羅相抗。不過,這不意味著這些願意守護韋德瑞的友人都能安然無恙,當祕密警察無法侵入與瓦解她的某些人際關係後,有時會強力介入與切斷連結,讓她的友人失業、恐懼或流亡,就像韋德瑞熟識的比爾曼夫妻,最終失去工作與流亡德國。延伸監控的需求,韋德瑞發現祕密警察因她的到來,而得以深入過去不易滲透的鄉村,擴展了國家統治的範圍。
本書更精采的地方在韋德瑞重新梳理人際關係的過程,無論是她探訪過去熟識與信任的朋友兼線民,或是與經手監控業務的祕密警察面談,都曾歷經一番心境上的轉折,而可窺見人性受過威權統治刻劃後的明與暗。然而,韋德瑞終究是外國人,因此即使她的人生與秘密警察有了交集,也不會盡受威權統治左右,最終仍然可以是自己命運的主人。
就在本書於台灣出版的同時,大量監控檔案在台灣開始出土,這些檔案出自威權統治時期情治機關之手,檔案裡的人被情治人員或線民深淺不一地刻畫出另一種人生。與羅馬尼亞祕密警察相似,維護國民黨政權的情治機關也是從被監控者的身旁招募線民,透過人際關係掌握被監控者的動向,並軟硬兼施地影響他們的認知與選擇。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提出的報告指出,情治機關侵害被監控者的隱私,細密地記錄他們的一舉一動。例如受促轉會委託的林國明教授研究團隊,尋訪到的一位受訪者,在翻閱自己監控檔案後說道:「好像我們就是關在籠子裡面的動物這樣在看」。3 與此同時,協助情治機關建立網羅,以便關住被監控者的線民,大部分來自被監視者的「親朋好友」,因此閱覽檔案讓被監控者的人生出現裂痕,當年的學運領袖、現今的立委范雲便感傷「曾經共同打拼的同志情誼與信任,好像在一夜之間被敲碎」。4 更糟的是,相較於羅馬尼亞民主化後在檔案開放與面對歷史的政策上有所進展,台灣才剛開始受到衝擊。因為情治機關的阻撓而無法辨識檔案中的線民,讓有些被監控者在閱覽檔案後更感挫折,只能在當年志同道合的同伴中猜疑誰才是情治機關的線民。5
人們因為本能,需要互信互賴與發展人際關係,但在威權統治的影響下,人們卻不免猜疑,關係的本質究竟是圓滿人際互動的需求,還是得寸進尺的侵犯與操弄。韋德瑞的觀點是個鮮明的對比,映照出成長於民主與威權時代的差異。出身美國而自小崇尚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價值的她,在重新認識自己與叩問研究羅馬尼亞的人生時,警覺「必須拋棄在美國文化脈絡中一種主要以個人自主角度思考的傾向」,因為在威權統治下,個人不是自己人生的主宰。相較之下,受過威權統治的人們,可能懷疑自己人生的境遇是否曾受威權統治刻劃與左右,而有著「我不是我的我」的複雜情感。若人生的選擇無法擺脫被威權統治操弄的痕跡──即使像是從技術官僚一路「被栽培」至黨國層峰權位的繼承,沒有選擇地在威權統治者的視野裡機巧謀算與兢兢業業──當人生走到盡頭時,恐怕不免懷疑「我是不是我的我」。或許,這不僅是個人曾被長期監控而不免叩問人生的問題,恐怕也是受過威權統治的社會面對過去時待解的疑惑。
面對過去必然艱難,然而唯有「歷經自我,才有自由,國家也是這樣」。6
※注釋
前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研究員。感謝衛城出版社的邀稿,也感謝作家阿潑對本文初稿的意見,文責由作者自負。 ↩
柯旗化,2008,《台灣監獄島:柯旗化回憶錄》,高雄:第一出版社。 ↩
林國明,2019,〈威權統治時其校園與社會監控之研究訪談/H17〉,轉引自促轉會,2021,《任務推動及調查結果報告書 第二部 探求歷史真相與責任的開端:壓迫體制及其圖像》,頁2-413。 ↩
范雲,2010〈告密者、我和我的被監控檔案(中)〉(范雲 FAN, Yun 臉書粉絲專頁),轉引自促轉會,2021,《任務推動及調查結果報告書 第二部 探求歷史真相與責任的開端:壓迫體制及其圖像》,頁2-414。 ↩
如有人指出「我們這十個人裡面都是我當初的好朋友,我亂猜害了其他三個人,他們是不是也變成是受害者,我們其實集體都是這一個監控下的受害者」。促轉會,2021,〈當事人意見調查計畫訪談/G2〉,促轉會第1105100190號簽,轉引自促轉會,2021,《任務推動及調查結果報告書 第二部 探求歷史真相與責任的開端:壓迫體制及其圖像》,頁2-419。 ↩
李桐豪,2020,〈【近看李登輝】我不是我的我〉,《鏡周刊》。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200226pol001/,最後瀏覽時間:2022年5月27日。 ↩
我們與監控的距離:從香港、新疆、非洲看中國的「數位威權輸出」
文:普麟(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
2019/09/10
香港政府日前強推《逃犯條例》修訂引起香港民眾的憂慮,更在日前導致了百萬香港人上街頭的「反送中」抗爭運動爆發。但沒想到竟然有與抗爭相關的加密通訊軟體Telegram群組管理員被香港警方盯上與入門搜索,讓該群組名單與聊天記錄被港警掌握。[1]這起事件不禁讓人開始反思,是否當我們高度依賴科技的同時,就難以逃離受到大規模的科技監控的可能,甚至更讓人擔憂的是,在這背後監視著你的「老大哥」,就是試圖對外輸出威權的中國政府…
故事要從華為被美國封殺開始談起…
美國政府從2018年開始以危及國家安全為由盯上華為之後,又於今(2019)年5月由川普總統簽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國企業採用被認為將對美國國家安全造成危害的外國電信公司,而美國商務部也將華為加入制裁名單,許多科技大廠包括Google、ARM也暫停對華為技術支援;[2]美國國務卿Mike Pompeo於日前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更大力批評華為執行長任正非曾稱華為沒有與中國政府進行合作是錯誤的說法。[3]不過,為什麼像是華為,以及許多中國科技大廠會被美國政府盯上、甚至是封殺呢?
澳洲智庫「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下屬國際網路政策中心的研究團隊,就針對當前中國科技公司的發展與全球佈局進行深入的調查與研究,並於2019年4月發布了名為《中國科技巨頭的圖像與行動軌跡》(Mapping China's Tech Giants)的研究報告。這份報告主要包括兩大部分:首先是中國共產黨與國內科技巨頭的政商關係,以及這些科技公司在黨國政治發展所扮演的角色;其次是這些科技巨頭在中國與全球的業務擴張之實例。這個研究最終目的就是要回答中國科技巨頭在全球的擴張,對於世界各國的政治、人權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
正如同Pompeo對於華為與官方連結的指控,中國的政商關係除了靠著政府補貼,官方更以法律明文規定企業內必須設立黨組織,而企業不但要參與黨的活動,更需配合國家的情報工作。[4]像是華為以及許多被稱為中國「國家隊」的科技公司,無論是接受官方補貼或是企業決策受到黨的干預,都會讓這些企業成為中國達成政治目的的工具。所以這篇報告才會指出,由於中國試圖透過網路與科技向全球輸出其治理模式,加上許多中國的科技公司也被中共以黨委會組織所牢牢掌握,因此很明顯這些企業絕非是單純從事商業行為的公司而已。[5]
走向全球的中國「數位威權主義」
ASPI的報告將中國當前的科技發展與黨國機器的結合形容成是「數位威權主義」,並引用了自由之家於去(2018)年發表的網路自由報告。該報告就以《數位威權主義的崛起》(The Rise of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為題,分析各國政府運用科技手段控制民眾、以及全球網路自由倒退的狀況,並特別強調中國政府將監控技術對外輸出,正是造成數位威權主義在世界各地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6]
在自由之家的報告中,數位威權主義的發展主要包括兩大領域:其一是在網際網路,像是網路言論自由、不實謠言的散播、對隱私權等面向的侵犯,其二則是利用科技直接監控社會大眾,例如由監視器、臉部辨識與AI技術所結合的「天網」(Skynet)系統,以及用來評估公民信用程度的「社會信用系統」(social credit system),而後者的發展更是高度依賴北京政府對於網路的掌控。[7]自由之家主席Michael J. Abramowitz更指出,北京領導人最終目的是在國際上用威權主義來取代數位領域現有的自由規範。[8]
那麼,與華為類似的中國網路與科技公司在中國對外輸出「數位威權」的過程中,又是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呢?
ASPI的研究團隊追蹤了包括阿里巴巴、騰訊、華為與海康威視等12間中國主要的科技公司在全球的業務與投資,發現這些公司不但參與了中國政府在新疆維吾爾族地區的人權侵犯行為,例如協助建置通訊、監視器與臉部辨識等監控系統。[9]同時,這些中國科技巨頭還在世界各國與當地的專制政權進行合作,利用由中國所提供的科技與網路技術來強化社會控制,進而導致當地人權與自由的狀況持續惡化,例如在這份報告中所提到的個案像是辛巴威、委內瑞拉與白俄羅斯等國家,以及由華為在各國所協助建置的「智慧城市」計畫。[10]
當東方巨龍來到遠在非洲的辛巴威
無論是自由之家或ASPI的報告,都提到了接受北京政府威權輸出的辛巴威國內人權倒退的狀況。不過,辛巴威的例子在非洲國家並非個案,而且早在數位威權的相關研究出現之前,中國與辛巴威的威權合作就已經相當密切。[11] 史丹佛大學政治系Larry Diamond教授更指出,[12]中國於後冷戰時期以一個主要的援助者、投資者與地緣政治行為者的姿態出現在非洲地區,讓這些非洲的威權政府獲得了北京在政治上的支持(political patron),成為抗衡西方國家勢力的選項。
辛巴威在2002年接連被美國與歐盟制裁之後,緊接著前獨裁強人總統穆加比(Robert Mugabe)開始推動辛巴威的「東望政策」(look east policy),同時中國政府也擴大對辛巴威的經貿合作、投資與軍事援助,甚至還包括外交與政治支持,例如在2008年聯合國安理會一項對辛巴威制裁的表決中投下反對票。13[13]根據研究指出,由於辛巴威長期以來的人權紀錄非常不佳,而過去中國政府給予辛巴威的援助並未包括人權、環保與民主治理等附帶條件,造成的後果反而是提高貪腐的嚴重程度並降低政治課責性,同時也會削弱公民社會所扮演的角色。[14]
近年來,北京對辛巴威獨裁政府的支持也反映在中國科技公司與辛巴威的合作。其中,華為、中興通訊等公司不但與辛巴威的通訊建設進行大量的投資與合作計劃,甚至還參與了辛巴威政府對網路與社群媒體的龐大監控計劃。[15]除了線上監控,辛巴威政府採用了由海康威視(Hikivision)所提供的監視器與監控設備,更於 2018 年與中國的雲從科技(CloudWalk Technology)簽署合作協定,由該公司提供辛巴威政府臉部辨識技術與資料庫。[16]
辛巴威前總統穆加比在 2016 年將中國稱為是社群媒體監控的模範,並希望辛巴威能夠加以效仿,於2017年繼任總統的 Emmerson Mnangagwa 也依舊維持過去的統治模式。辛巴威政府除了與中國保持友好關係之外,仍繼續在北京的協助之下將辛巴威打造成如同中國一樣的監控國家。[17]在今年1月辛巴威抗議通貨膨脹與油價高漲的示威抗議中,政府不但動用軍隊來鎮壓示威群眾,更切斷網路並封鎖Facebook、Twitter與WhatsApp等社群媒體與通訊軟體,利用科技手段來瓦解抗議群眾進行組織的可能。[18]
一樣都是威權輸出,多了「數位」兩個字有差嗎?
既有對於威權擴散的相關研究,在擴散與輸出的模式多半是分為「價值示範」與「實質政策或影響」。[19]其中,所謂實質影響是指,學術研究發現由中國所提供不附帶人權、環保與民主治理等條件的援助或投資,往往會讓許多非民主國家的專制政權更有資源壓制反對勢力,並造成人權與自由的倒退,而這樣的模式又常發生在非洲國家,像是辛巴威就是一例。[20]
除了來自北京的資金,中國的科技公司以及其所提供的各式監控技術,更是直接讓這些威權政府能夠有效進行社會監控,掌握一般民眾的個資、實體行蹤,以及通訊與網路上的各種紀錄,以犯罪預防之名打壓社會異議者,直接在當地複製中國的「歐威爾式監控國家」(Orwellian surveillance state)。
在威權擴散的價值示範面向,中國的數位威權主義背後所代表的價值觀也讓這些威權國家領導人印象深刻,並開始公開讚揚中國的社會治理模式,例如辛巴威的前總統穆加比。例如辛巴威政府在面對示威抗議時採取封鎖社群媒體與網路的做法,就如同中國在面對新疆維吾爾族抗爭時的回應如出一轍。[21]
數位威權主義的輸出就如同其它形式的威權擴散一樣,透過威權大國的價值示範或實質利益讓在地國家在政治發展上朝向威權的方向移動,只是前者在手段上是透過數位與網路科技等手段,讓政府在控制民眾上更為直接且有效。甚至,這些在世界各國所蒐集到的龐大數據與資料,又會再回傳至位於中國的資料庫,協助中國政府與科技巨頭公司訓練AI ,不斷強化中國數位威權的科技發展。[22]
ASPI的報告不但補充了過去相關領域研究的不足,更讓我們得以瞭解這些中國科技巨頭在北京對全球各國發揮影響力的過程所扮演的角色。
美中貿易戰的升級與新疆的監視器
無論是中國或辛巴威政府透過控制網路與社群媒體來避免群眾在社會抗爭中進行組織與串連,或是香港「反送中」抗爭中有Telegram群組被政府所掌握(甚至是Telegram本身受到來自中國的大規模DDoS攻擊)等事件,[23]都反映出當代公民社會的抗爭者在面對威權政府時出現極大的資源與科技不對稱。[24]但是,抵抗中國數位威權在全球的擴張,並非是毫無希望。
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指出:「……把海康威視公司列入美國黑名單。這也標誌著川普第一次因為其在監視和大規模拘禁維吾爾人——一個主要是穆斯林的少數民族——中起的作用而懲罰一家中國公司。」[25]然而,在新疆的監視器鏡頭與美中貿易戰有什麼關係呢?
由於全球的資通訊產業早已形成複雜但完整的跨國分工產業鍊,無論是IC晶片、智慧型手機或是監視器材的生產,過程都是跨國分工及生產,只是目前許多關鍵技術仍掌握在美國手中。因此,中國於 2015 年提出「中國製造 2025 」(Made in China 2025),同時又於近年來大力推動IC晶片的自主製造,以及5G行動通訊與AI等技術的發展,甚至不擇手段地對歐美企業進行竊密,除了想在全球科技爭霸上快速取得優勢外,也是為了擺脫對美國的技術依賴。[26]其最終目標就是要建立符合「中國模式」的網路治理型態以及科技規範:不僅是在技術上超越歐美國家,而是在高科技領域的規範與價值上取代現有的西方標準。
川普在美中貿易戰開打後祭出了關稅手段,甚至與其民主盟友聯手對中國企業如中興、華為等科技公司進行制裁或封殺,背後原因除了因為許多中國企業常涉及侵犯智慧財產權與商業竊密,另外也有國家安全的疑慮與考量,更因兩強科技爭霸被外界形容是「科技戰」(technology war)。[27]其中,就像《紐約時報》在報導中所提到,如果美國考慮限制提供零件與技術給海康威視的做法屬實,可能將影響其監視設備的出貨與業務運作,也讓阻止中國數位威權的擴散出現更多的可能。[28]
回到報告本身,正如同ASPI指出由於這些中國科技公司的規模、擴張速度與不透明性,導致在公開資料蒐集上一定會有所疏漏,所以ASPI也鼓勵社會大眾協助共同新增與補充相關資料,讓這個專案計畫的資料庫更加完整。透過不斷揭露中國科技巨頭的相關資訊,才能協助全球的民主陣營擬定因應中國數位威權的反制政策。
※本文修改自作者在《新社會政策》的發表文章,請參考:普麟,2019,〈當中國透過科技威脅全球民主——淺談中國的數位威權輸出〉,《新社會政策》,第63期。
參考文獻
無國界記者,2019,《中國追求的世界傳媒新秩序》。
Ambrosio, Thomas. 2010. “Constructing a Framework of Authoritarian Diffusion: Concepts, Dynamics, and Future Research,”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11: 375-392.
Bräutigam, Deborah. 2010. 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ave, Danielle, Samantha Hoffman, Alex Joske, Fergus Ryan & Elise Thomas. 2019. Mapping China’s Tech Giants,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Diamond, Larry. 2010. “Introduction,” in Democratization in Africa: Progress and Retreat, ed. Larry & Marc F. Plattne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Erdmann, Gero., André Bank, Bert Hoffmann & Thomas Richter. 2013.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 Authoritarian Regimes: Toward a Conceptual Framework, GIGA Working Paper 229.
Freedom House. 2018. Freedom on the Net: The Rise of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Hall, Stephen G. H. & Thomas Ambrosio. 2017. “Authoritarian Learning: A Conceptual Overview,” East European Politics 33(2): 143‐161.
Hodzi, Obert, Leon Hartwell & Nicola de Jager. 2012. “‘Unconditional aid’-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China’s development assistance to Zimbabwe,”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1): 79-103.
Human Rights Watch. 2019. China’s Algorithms of Repression: Reverse Engineering a Xinjiang Police Mass Surveillance App.
Lv, Aofei & Ting Luo. 2018. “Asymmetrical Power Between Internet Giants and User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2: 3877–3895.
Masunungure, Eldred V. 2011. “Zimbabwe’s Militarized,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65(1): 47-64.
McKune, Sarah & Shazeda Ahmed. 2018. “The Contestation and Shaping of Cyber Norms Through China’s Internet Sovereignty Agend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2: 3835–3855.
Michaelsen, Marcus & Marlies Glasius. 2018. “Illiberal and Authoritarian Practices in the Digital Sphere: Prologu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2: 3795–3813.
Shahbaz, Adrian. 2018. “The Rise of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Freedom on the Net: The Rise of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Freedom House.
Weyland , Kurt. 2017. “Autocratic Diffusion and Cooperation: the impact of interests vs. ideology,” Democratization 24(7): 1235–1252.
註釋
由於香港警方聲稱有工具可以破解該群組管理員的小米手機,最後他不得不交出手機,請參考:Paul Mozur & Alexandra Stevenson, “Chinese Cyberattack Hits Telegram, App Used by Hong Kong Protesters,”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3, 2019.
Cecilia Kang & David E. Sanger, “Huawei Is a Target as Trump Moves to Ban Foreign Telecom Gear,”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5, 2019; Russell Brandom, “What happens to companies that defy the Huawei ban?,” The Verge Jun 2, 2019.
在這段專訪中,Pompeo更特別解釋如果一間企業接受中國政府的補貼,就難以避免受到官方的干預與影響,例如協助北京從事間諜行為,請參考:Jessica Bursztynsky, “Secretary of State Pompeo: Huawei’s CEO ‘isn’t telling the American people the truth’ on China government ties,” CNBC May 23, 2019. Pompeo還向媒體表示自己與各國政要會面時也會不斷解釋華為所帶來的危害,當他與德國外交部長Heiko Maas會面時更表明未來美國將會停止與那些允許華為參加電信建設的國家共享情報資訊,請參考:David Brunnstrom, “Pompeo tells Germany: Use Huawei and lose access to our data,” Reuters May 31, 2019.
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第30條規定包括企業在內的組織,「凡是有正式黨員三人以上的,都應當成立黨的基層組織。」第33條則規定無論國企、私企的黨組織都要協助企業「貫徹黨的方針政策」,中國的《公司法》在第19條也規定:「在公司中,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的規定,設立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開展黨的活動。公司應當為黨組織的活動提供必要條件。」此外,中國於2017年所通過的《國家情報法》,在第7條更規定「任何組織和公民都應當依法支持、協助和配合國家情報工作…」賦予公司與私人企業必須要協助國家從事帶有政治目的的情報工作之法源。
Cave, Hoffman, Joske, Ryan & Thomas 2019: 17-19
Freedom House 2018.
Shahbaz 2018。延伸參考:Bradley A. Thayer & Lianchao Han, “China’s weapon of mass surveillance is a human rights abuse,” The Hill, May 29, 2019;Paul Mozur “Inside China’s Dystopian Dreams: A.I., Shame and Lots of Cameras,”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8, 2018. 另外,Michaelsen與Glasius(2018)則是將數位威權主義分成監控系統、隱私權與不實謠言,以及對言論自由的侵犯等三大面向。
Michael Abramowitz & Michael Chertoff, “The global threat of China’s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 2018.
國際NGO「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所發布的報告則指出中國政府利用手機APP來大規模監控新疆居民,以便警方完整掌握可疑民眾的一舉一動,包括可能的政治反抗活動(Human Rights Watch 2019),請參考:“How Mass Surveillance Works in Xinjiang, China: ‘Reverse Engineering’ Police App Reveals Profiling and Monitoring Strategies,” Human Rights Watch, May 2, 2019;相關報導請參考:Darren Byler, “China’s hi-tech war on its Muslim minority,” The Guardian, April 11, 2019.
Cave, Hoffman, Joske, Ryan & Thomas 2019: 11-13.
例如辛巴威的執政黨「辛巴威非洲民族聯盟-愛國陣線」(ZANU–PF)就會定期派遣高階幹部前往北京接受中國共產黨的訓練,請參考:Andrew Kunambura , “Mnangagwa eager to adopt Chinese communist model,” The Zimbabwe Independent November 30, 2018 ; Kuda Bwititi, “Zimbabwe: Zanu-PF, CPC Forge Stronger Ties,” allAfrica May 8, 2019. 本段請參考:Erdmann, Bank, Hoffmann & Richter 2013。
Diamond 2010.
Masunungure 2011.
Hodzi, Hartwell & Jager 2012.
此外,辛巴威還在2016年通過法律,允許政府扣押民眾的上網裝置(例如手機或筆記型電腦),阻止一般大眾在集會或抗爭時使用社群媒體,甚至還在2019年靠著封鎖社群媒體與強行斷網的手段,直接打壓抗議燃油價格上漲的群眾運動,請參考:Peta Thornycroft, “New Zimbabwe law allows seizure of smartphones and laptops as Mugabe turns on social media,” The Telegraph August 7, 2016; Columbus Mavhunga, “Zimbabwe Activists Push Back on Social Media Restrictions,” VOA February 7, 2019.
Amy Hawkins, “Beijing’s Big Brother Tech Needs African Faces,” Foreign Policy, July 24, 2018.
Ray Mwareya, “Zimbabwe Drifts Towards Online Darkness,” Coda Story, February 26, 2019.
Zimbabwe blocks Facebook, WhatsApp and Twitter amid crackdown,” BBC, January 18, 2019.
Ambrosio 2010; Hall & Ambrosio 2017; Weyland 2017.
Bräutigam(2010)則認為這些非洲國家原本就由威權政府掌權、人權與自由程度不佳,因此中國的援助並非是導致其國內人權狀況倒退的主因。
北京政府在2009年鎮壓新疆維吾爾族抗爭中,就曾關閉當地網路長達10個月的時間,請參考:Edward Wong, “After Long Ban, Western China Is Back Online,”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4, 2010.
數位威權主義在中國的快速發展,讓這些數位科技巨頭與一般民眾形成極大的權力不對稱與落差,也因此除了中國政府的角色,數位科技巨頭以及其所掌握的權力自然也成為亟需關注與研究的對象。參考:Lv & Luo 2018。
Jon Porter, “Telegram blames China for ‘powerful DDoS attack’ during Hong Kong protests,” The Verge, Jun 13, 2019.
Lv & Luo 2018.
Ana Swanson & Edward Wong, “Trump Administration Could Blacklist China’s Hikvision, a Surveillance Firm,”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1, 2019;中文版報導可參考:Ana Swanson、黃安偉,〈美國或將中國影像監控巨頭海康威視列入黑名單〉,《紐約時報》,2019年5月22日。
Arjun Kharpal “China is ramping up its own chip industry amid a brewing tech war. That could hurt US firms,” CNBC June 4, 2019.
“Huawei has been cut off from American technology,” The Econnomist May 25, 2019; David J. Lynch “How the U.S.-China trade war became a conflict over the future of tech,”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22, 2019. 另外,以台灣為例,早在2013年政府就禁止4G業者採用包括華為在內的中國製設備,更於去年由國安會宣布八大關鍵基礎建設相關產業都禁用中國製產品,以行動表達支持美國的立場,請參考:曾雅凰,〈國安會宣布!明年起8大關鍵基礎建設禁用中國製產品〉,民視新聞網,2018年12月15日。
相關新聞可參考:Arjun Kharpal “US takes aim at Chinese surveillance as the trade war becomes a tech war,” CNBC May 26 2019; Cassell Bryan-Low, Colin Packham, David Lague, Steve Stecklow & Jack Stubbs, “Hobbling Huawei: Inside the U.S. war on China’s tech giant,” Reuters May 21, 2019.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