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见杂志丨一个历史性交汇点:10月7日后的以色列左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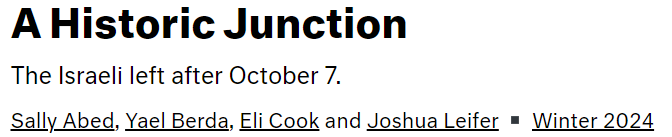
译按
本文原题“A Historic Junction”,见于《异见》(Dissent)2024年冬季号。
《异见》是一份左翼知识分子立场的美国政治和文化杂志,创办于1954年,注册为非营利组织,一年出版三至四期。 另有播客等线上内容,发布于其官方网站。
本文受访者Sally Abed,是巴勒斯坦裔以色列活动人士,草根运动组织 Standing Together全国领导人之一。Yael Berda,是以色列希伯伦大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副教授。Joshua Leifer,是以色列海法大学历史学副教授。
访问者Joshua Leifer,是《异见》杂志编委会成员。
正文中加粗的字为原文所有。小标题为译者添加。译者听桥,对机器形成的初步译文有校阅,不能保证理解准确。
一个历史性交汇点:10月7日后的以色列左翼
Sally Abed Yael Berda Eli Cook Joshua Leifer 两个多月的密集轰炸后,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继续造成可怕的人员伤亡。截至本文撰写时,以色列军队已造成近两万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平民。根据联合国数据,自战争开始以来,约180万人,即加沙人口的80%,已在国内流离失所。
在以色列国内,紧张、恐惧和愤怒的气氛普遍存在。高楼大厦上悬挂着巨大的广告牌和横幅,上面写着: “团结就是胜利。”平民和穿制服的士兵一样,手持M-16步枪走在街上。但对政府战争行为的不满情绪也开始酝酿。哈马斯和其他巴勒斯坦派别继续扣押着至少120名以色列人质,但是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政府往往将带他们回以色列当作次要任务。
在这一背景下,尽管镇压加码,以色列左翼组织者和反占领活动分子仍已开始重返街头。他们的要求是: 停火,并达成释放所有人质的协议。
12月6日,我与三位以色列左翼活动家、思想家就以色列左翼目前面临的挑战进行了讨论。
——Joshua Leifer
“10月7日事件形成了一个历史性交汇点”
Joshua Leifer:对以色列左翼人士来讲,自10月7日以来,事情生了什么变化? 政治版图如何转向?
Yael Berda: 今天,在Kirya(以色列军方总参谋部所在地)将有一个小规模抗议活动,口号是“停止战争”。我一只想这么做,至少有一个月了。一开始是很难鼓起勇气去抗议,后来是很难找到伙伴。我希望是二十人,也许是三十人。这将是一个巨大的胜利,有几个原因。(括号中文字为原文所有。——译注)
一个原因是,10月7日后,政府立即展开了对(左翼活动人士、公民教师)Meir Baruchin的大规模打压。他被关了四天,确实遭到了虐待,并被指控叛国罪,因为他贴出了加沙儿童的照片。这给你的感觉是,左翼人士无法为加沙平民表达悲伤或痛苦。这在过去的两周里发生了变化,你被允许表达痛苦,但还是不能反对战争。
我和一个同为活动人士的非常要好的朋友谈到一次抗议活动。我对他说:“要是我们被捕了怎么办?要是右翼人士攻击我们呢?我们以前也这么干过。我们知道如何应对。”然后他说:“对我来说比较难的是,被所有人当成疯子看待。”这种极其孤独、极其怪异、遭到极度误解、极度不正当的感觉,对我来说是全新的。
我们现在有一个威权政府。客观困难是真实的,但人们的头脑中也在发生着一些事情。他们无法承受社会压力。
Sally Abed: Standing Together每三到五天在全国各地举行一次集会。我们正在动员民众。我们正试着找到一个可以安全抗议的漏洞; 实际上,我们租用了婚礼场地举行会议。有犹太左翼人士来到我面前嚎啕大哭,说:“感谢你让我们觉得我们被看到了。”
我们在以色列一个非常黑暗的地方。有一种感觉是,我们在为这个社会的灵魂而抗争。作为一名以色列的社会主义巴勒斯坦人,假如你在两个月前问我,我未来三年的战略是在以色列建立一个新的左翼,我会告诉你,他们正在解决社会正义问题、经济问题,并且真的试图触及边缘。已经完全变了。我们必须从废墟中重建的新的以色列左翼有一个全新的使命。10月7日事件形成了一个历史性交汇点,在这里,主要问题将是有没有和平。我不认为“和平”会是那个词,但下次选举将涉及这个问题。和平不是问题已有很多年了。
Eli Cook:今年早些时候,我几乎每周都去卡普兰大街(Kaplan,这条特拉维夫的大街已成为反对司法改革计划的示威的同义词),参加那里的大规模抗议活动。那些抗议活动是新自由主义的,相当保守,或以维持现状为导向。但我可以每周都穿着我的反占领T恤衫去,并游行,没有一次因为参加抗议而经历不愉快的事情。我们曾经认为“我们是正当的外围人士,但我们是组织的一部分”。但我完全同意Yael说的,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了。
自从上一次停火在11月底结束以来,情况发生了一些小的变化,你现在可以至少认识到加沙苦难的一点点。但这很难。可我要说的是,释放人质的抗议活动给了左翼以色列人一个说出“结束战争”,或“停火”,或 “我们可以换个方式讨论消灭哈马斯,而不需要消灭半个加沙”的方式,同时依旧说“我们把以色列人带回家”,我也完全认可这一点。至少对我来说,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去,听到那些甚至不是左翼人士的人说: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进行全面人质交易,结束这部分的战斗吧。
许多民意调查显示,以色列人已经转向右翼。但同样的民意调查显示,比比(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已经完蛋了,绝大多数人将投票给本尼·甘茨(Benny Gantz)。我不是说甘茨是有点激进的左翼人士,但我确实认为他那里有某种东西。(本尼·甘茨,是现任以色列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战时内阁三名成员之一。——译注)
与此同时,出现了进一步的倒退。(2005年)当以色列从加沙地带“脱离”时,真正的左翼人士总是说,这不能是单方脱离,必须伴随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进行某种谈判,不然只会造成一种巩固哈马斯而伤害温和派的局面。已发生的事情恰恰是这样。但以色列的主流讲述已成了“你们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我们已离开加沙,而你们仍然这样做”。
“以色列公众几乎没有机会了解正被犯下的暴行”
Leifer:我想问一下要求释放人质的抗议活动。远远地看,那些抗议活动往往是许多人在以色列见证的有关战争如何进行的异议的唯一代表。你们在多大程度上认为,以色列社会的其他成员理解战争目标的零和本质?完全轰炸和摧毁加沙与遣返其余人质是相互排斥的目标吗?那是一条或许有效的可能的异议路线吗?要不就是呼唤战争的声音太大了?
Berda: 我们确实看到人们走出去参加这些抗议活动。那是我们作为左派所拥有的唯一亮点,我们得好好利用。政府没有在不停火的情况下把人质带回来的计划。他们没有一个关心人质或所有以色列人安全的计划。为人质抗议的是那些“求生”的人,而不是“求死”的人。但政府确实有一个计划,那就是财政部长Bezalel Smotrich的“决定性计划”(要求吞并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并驱逐反抗的巴勒斯坦人)。他们还有一个在加沙建立定居点的计划。这是摆在桌面上的唯一计划。
Cook: 也许我过于乐观了,但我不确定,最终的计划是在加沙建立定居点。从战略意义上讲,没有任何计划。做这些决定的人是政治家。一切都太肤浅,太见利忘义了。我认为内塔尼亚胡的目标是抓住叶海亚·辛瓦尔(Yahya Sinwar,加沙地带哈马斯的首脑) ,享受他的萨达姆·侯赛因时刻。为了那一刻,内塔尼亚胡会不惜一切代价。
关于人质: 感觉以色列人已经成功分离了他们大脑的两部分。他们想轰炸加沙所有这些不同的地区,但也想把人质带回家。这种脱节令人不安。我们还听说,哈马斯提出的停火建议从10月中旬开始就摆在桌面上了。但以色列方面的说法是,假如以色列没有在加沙北部采取行动,哈马斯绝不会放弃妇女和儿童。很多人可能相信这是真的。但严肃的记者表示,情况并非如此。
Abed: 官方说法是,由于伤亡,加沙的民间社会最终会说服哈马斯放弃。想想这种思维方式是多么扭曲。在以色列,我们是已经抗议了十个月的公众的一部分,在这个政权下,你确实有很高的言论和结社自由,而我们仍没有成功推翻政府。那么,认为人们可以因为以色列在轰炸哈马斯而推翻他们:在什么样的世界里,这种情况会发生呢?但以色列官员就是这样为杀害平民辩护的。
Berda: 几十年来,以色列一直在经历一个让公众认为巴勒斯坦人是低等人的相当方法论的过程。一方面,由于社交媒体的存在,你无法完全逃避加沙正在发生的事实,另一方面,以色列公众几乎没有机会了解正被犯下的暴行。在目前收视率排名第二的十四频道(Channel 14,大致相当于福克斯新闻)上 ,你可以看到计数器显示有多少“恐怖分子”被杀害,其中包括所有的伤亡,即所有儿童和所有妇女。
作为左翼人士,我们正与这只巨型机器斗争。这甚至不是关于假新闻,而是关于公众如何看待极度脱离巴勒斯坦人的现实,极度脱离我们作为以色列公众的利益的这一整件事。要转变这一模式,需要做很多工作。这让我很沮丧,但我的生存机制是“我们如何改变?”因为我不能接受。我们需要理解,我们如何才能克服在道德上教育以色列公众的冲动,同时,我们如何才能理解他们的情绪状态。但要给人们一套完全不同的信息,一种对生活的不同看法,对我们的现实的不同看法,也是非常困难的。
“以色列采取的策略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这正中哈马斯的下怀”
Leifer: 在国际左翼那里,一种正在发生的争论是这样的: 以色列的左翼是边缘化的。以色列社会已经变得极度军事化,对巴勒斯坦人的痛苦漠不关心,所以从战略上讲,与以色列左翼人士接触是没有意义的。但至少在我看来,假如有什么变化会在以色列内部发生,那里就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去组织和改变公众舆论。但假如国外的左翼完全排斥以色列的左翼,什么事情会发生呢?
Abed: 现在很多人都在说,“成问题的正是进步人士”,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这恰好给了右翼讲述以可乘之机。我在学术界看到了这种观点的影响:比如,认为后殖民主义现在是反犹太主义的。有些以色列学者说,他们已从后殖民理论那里“觉醒”,他们不再打算运用这一理论。这种“觉醒”正在全面发生。
对我来说,关键问题是,我们能改变这个地方吗?有可能吗?要不就是,不可挽回了?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BDS)的一个问题在于,它假定以色列社会无法改变。假定以色列无法改变,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重要对话就不会再发生。情况变得更糟了。(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是一个要求以色列遵守国际法,结束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的国际性运动,发起于2005年。——译注)
不过,人们为什么还要花时间关注国际左翼说了什么呢?我们必须停止战争,拯救人民,拯救这个国家,使其免于威权改革,免于社会服务的全面毁灭。我们还有工作要做。我现在最不想花时间做的事就是坐下来和远在天边的某些白痴吵架。你在这件事上的赌注是什么?是想让人们活着,还是想让人们死去?什么在赋予生命?什么在使更多的死亡合法化?是什么造成了让我们无法回头的极化?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不可能在所有战线上都介入。
Cook: 我不认为以色列特别病态。但是我对以色列人无法看到事情的另一面非常不满。在政治方面,我试图向以色列人提出务实的而不是说教性的观点。我一直试图说明的真正关键要点之一是,以色列采取的策略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这正中哈马斯的下怀。哪怕在最实际的层面上,这也是一项误入歧途的政策。
过去的几年里,我也认为以色列左翼和许多美国左翼是各说各话。我可以在推特上说,比如“占领必须结束”,所有在美国的人也都会说,“是的,占领必须结束”:只是我没有意识到,当他们说占领时,他们意味着一切,而我说的是,以色列离开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我确实觉得这是个挑战。
Yael提出“抨击进步人士”正中右翼下怀,我完全同意这一观点。但我们也看到,以色列公众是多么欣然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激进左翼形象。这些形象确实损害了以色列国内的左翼。右翼人士说:“你看到了吗?他们不是在谈论和平,他们不是在谈论生活在一起。他们在谈论‘从河流到大海’”。我觉得当他们看到巴勒斯坦国旗,而且只看到巴勒斯坦国旗时,他们会想,“哦,这不过是民族主义。这是我的国旗和你的国旗之间的战争。”
显然,这不是所有人。但我确实希望,在这场战争结束后,我们能与美国左翼就我们未来的具体目标进行一次真正深入讨论。有时候,我觉得以色列自身和占领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这种模糊的界限是以色列右翼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解决的问题,他们的观点是,来自希伯伦南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前哨的定居者攻击巴勒斯坦人,烧毁他们的橄榄园,与来自海法的以色列左翼犹太人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双语学校,没有区别。我在海法大学教书,那里并不完美;绿线(Green Line)里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但那与在被占领土上发生的事有很大不同。(绿线,是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与埃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之间根据1949年停战协议划定的分界线,用于区分以色列本土与由以色列国防军或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控制的其他区域。——译注)
Abed: 我们已经在讨论了。我不知道够不够。我至少为美国四十个不同的组织做过五次简报,其中有来自“黑命攸关”、“日出”(Runrise)和“如果不是现在”(If Not Now)这些组织的人。
巴勒斯坦解放运动试图告诉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绝不想怀疑或评判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愤怒是非常真实的。集体创伤是非常真实的。我的绝大部分争吵事实上是与那些海外巴勒斯坦人进行的,他们生活在这些理论化的解放幻想中。
几十年来,巴勒斯坦解放一直遭到严重诋毁,被认为是非法的,并遭到打压。我们必须理解,目前的人气爆发与此有关。不过,你到底想做什么?我想做正义的人,但我们承受不起只做正义的人的代价。我想公开表达我实际上有多愤怒。但我们没有这个特权。
人们问我,难民怎么办?历史正义呢?作为以色列的一名巴勒斯坦人,我对巴勒斯坦人的集体解放负有责任。我相信这理当引导我们达成一个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停火协议。我们必须停止目前的暴力镇压。但密歇根州的一个难民真的打动了我。他说: “假如我们不解决返回家园的权利问题,我将永远不会与以色列人进行任何有关和平的对话。”我没有表现出对他的愤怒,因为我理解他是从哪里来的。但加沙的孩子们眼下在说什么?你觉得这是他们释放的紧急信息吗?
我们的任务是确立政治意愿。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理解并承认以色列社会的关键作用。出于自身利益。出于对权力差异的认识。没有在以色列社会内部确立政治意愿,就不会有解放,不会有和平。那么,你想传递什么信息?你想说服谁?谁是你的观众,你的使命又是什么?
Berda: 我在“人人享有土地”组织(A Land for All,该组织提出了两国联盟模式)工作了很多年。返回家园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你问,你觉得加沙的孩子会想这些事吗?当然,你比我更清楚这一点。的确,对绝大多数以色列人来说,“从河流到大海”的返回权是一幅全面毁灭的图景。但在现实中,含义是多重的。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有民主,并生活在那里。
Abed: 但我们现在没有进行复杂对话的特别待遇。作为社区组织者,我们没有这种待遇。
Berda: 我只是说不要忘记,有人试图让其他人比他们眼下更害怕: 那些人一次次不断动员10月7日的袭击和所有的恐怖事端,以确保没有人能对人类有任何信念。我们不得不注意并质疑这一点。这与道德说教无关,与批评的意愿有关。我们需要批评,也需要同情。
Abed: 我每天都在经历这样的事情。这是有可能的,但非常复杂。进行组织和公共讲述是非常不同的。
Berda: 是的。我试图谈论返回家园的权利,并告诉人们,加沙地带是在1948年建立的,是巴勒斯坦人浩劫的产物。那里的人们把返回权作为他们的讲述的一部分。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否意味着将有一场永远的战争?或者,这一问题有可能解决?我们能想象一种不同的生活吗?我们能想象其他人是怎么想的吗?以色列人会告诉你:“我的心是封闭的,我没有同情心,我听不下去了。”他们是认真的。他们的心真的封闭了。他们真的听不进去。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告诉他们: 首先,你是安全的。国际左翼对告诉以色列人这些不感兴趣。
Abed: 我总是说,巴勒斯坦解放使得犹太人的安全成为必要,反之亦然。我对双方都这么说。你支持以色列?你必须解放巴勒斯坦人。你支持巴勒斯坦?你必须谈谈犹太人的安全。那比人质重要得多。这是观念上的更重大转变,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程式,我疯狂地重复它。这是必须出现的新左翼的基础。当你谈到和平和结束占领时,它与那种深刻的、关乎存在的兴趣和需求有关。
“人们对内塔尼亚胡的仇恨和愤怒即将爆发”
Leifer:我们正在进行的这样的对话是如何转化为实际政治的呢?正如我们所提到的那样,下一次选举将不仅仅是“赞成比比”、“反对比比”的投票。与此同时,公共话语似乎已经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向右转了。但你也会在某些时刻听到新闻播音员和分析人士发表令人惊讶的评论,他们说:“得有一个政治解决方案,现状不能继续下去。”
也许会有一些裂缝的光,但与此同时,正规化的组织相当稀少。工党(Labor)和梅雷兹党(Meretz)在功能上是不存在的; 和平与平等民主阵线(Hadash)正在做重要的工作,它仍然有代表,也许联合名单党(Joint List,一个由四个阿拉伯多数党组成的联盟)可以再次复活。但这些都说明不了什么。当改变一些事情的需求极度强烈时,你如何处理缺乏政治选择的情况?这是向更广泛的以色列公众说明占领管理模式不能继续下去的最后机会吗?
Cook: 很多人都同意,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处理冲突了。在内塔尼亚胡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有很多人批评他,批评他支持哈马斯,支持他们,为的是永远不允许一个自主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达成两国方案。尽管这么说很可怕,但我猜,现在出现某种解决方案的可能性比10月6日时要高。在那之前,以色列人相信:“我们可以永远这样下去。我们会只负责占领。我们并没有真的为占领付出任何代价。”但这需要有足够政治勇气的人站出来推动那种妥协。
假如你在10月7日之前告诉我这样可怕的事情会发生,我就会预料到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以色列人之间会爆发一场内战。虽然有镇压,但内战并没有发生。甚至在主流电视上,人们都认为哈马斯是针对所有人的,他们不只是试图杀害犹太人。有些人已经开始说,或许我们必须废止“犹太民族国家”法(它巩固了以色列作为一个专属犹太国家的定义)。曼苏尔·阿巴斯(Mansour Abbas)眼下在以色列的某些圈子里很受欢迎。这是我们可以建立联盟的信号。一切都不会和以前一样了。政治选择将出现真空,我们必须用希望和建设性主张填补这一真空。我们也确实需要唐纳德·特朗普不赢得2024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曼苏尔·阿巴斯,是现任以色列议会副议长,联合名单党主席,阿拉伯裔。——译注)
Berda: 甚至10月7日之前,在反对司法改革的抗议活动中,我从许多年轻人那里听到的一件事就是,他们不得不进入公务员队伍,成为政府和政策制定的一部分。袖手旁观,憎恨正在发生的事情,对那些事情保持沉默,就像过去二十年里许多人那样,眼下是行不通的。一定程度上,我们正在见证军队的激进化,行政部门的激进化。人们已经认识到他们以前忽视的关于西岸占领的事情。
有些天,早上醒来后我会想:“我怎么才能在美国找到一份工作,让我的孩子们离开这个鬼地方?”第二天,我醒来后会想:“我应该从政吗?有人会听我不得不说的事情吗?”我和这地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还有其他人没有。我们已经看到了左翼人士的流失,我们必须找到留住人们的办法,而留住人们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怀抱希望。
犹太人-阿拉伯人伙伴关系眼下是一个可以有的很好模式,哪怕它是有条件的,是非政治化的,是非社会主义的。我确实认为这将使我们能够模仿我们想要的左翼。这将为我们打开不被边缘化的空间。当我说“我们”时,我指的是社会主义的、进步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左翼,他们谈论和平、占领、社会正义和福利。一个或两个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提出一个重建议程以保证安全和生命安全,是非常重要的。这需要很长时间。我认为我们都觉得很孤独。与此同时,我对梅雷兹党和工党不再存在的事实感到满意。我们不是在修复什么东西。我们在建造新的东西。
Cook:许多以色列人现在明白,哈马斯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因为安全部队被转移到约旦河西岸,去保护定居者。定居点不会给你带来安全,这样的说法从一开始就是以色列左翼立场的核心。所以,对我来说,一个小的裂缝已被推开,我们必须利用这一点。约旦河西岸的狂热分子、激进的定居者、想把中东点燃的人,他们对以色列的每一个人都是巨大的威胁。
Leifer: 假如内塔尼亚胡决定不辞职,那么再度爆发更激烈抗议活动的可能性有多大?
Cook: 我完全可以想象这样一种情形:假如战争结束,那时内塔尼亚胡将很难离开自己的家。人们有太多愤怒情绪,尤其是那些家人遭到杀害或绑架的人。这些人将在主流以色列人中拥有道德权威。
Abed: 人们对内塔尼亚胡的仇恨和愤怒即将爆发。
Berda: 我希望我能像你们俩一样乐观。我认为他们正在酝酿内战,认为他们会拼个你死我活。我希望我的判断是错的,我希望这太有末日色彩。但我不确定他会以民主方式下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