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erything is about sex,但性的一切全靠自学
本文为“不止身体”专栏文章之一,本文首发于beU Offici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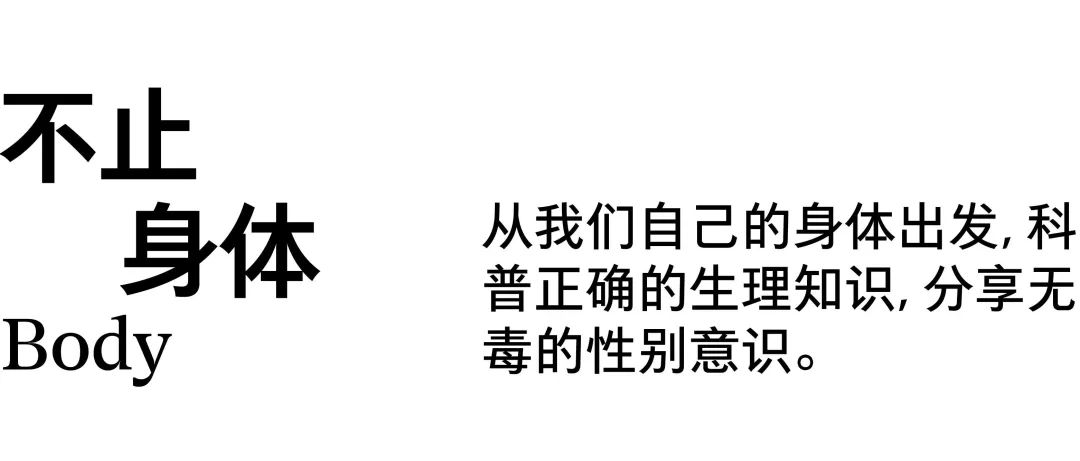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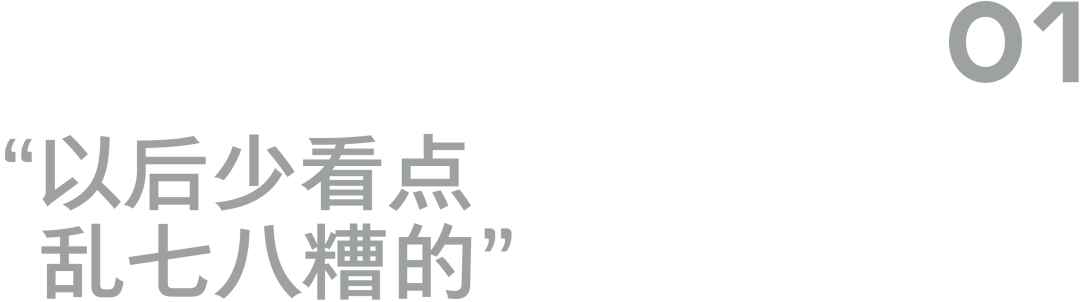
除了月经初潮时妈妈沉默地递来卫生巾,我从未从家长那里得到过像样的性教育。非要算的话,在我成年前,我家发生的唯一可以和性教育勉强挂钩的时刻大概是这样:
某一天,还是中学生的我拉住我爸,说要给他读一段《故事会》,我不记得我读了个什么,也不记得为什么要拉他来听。但我能回想起读到了这么两句话:“…...他印堂发黑,房事不济…...” 我爸全程沉默,我读完后,他连忙说:“好了好了出去吃饭。”
后来某天,我妈我爸和我三人开车去某个地方。突然,他俩其中一个问我:“你那天读的文章,怎么说到什么房事不济啊?”说实话,直到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 “房事不济”这个词好像有什么问题。我不知道到底有什么问题,但任何一个小孩在中学时期的敏感都足以让 ta 立刻反应过来此时此刻必须懂装不懂。于是我说:“啊?不记得了。”(其实记得)懂装不懂的回答奏效了,他俩松了一口气,淡淡地说:“哦,以后少看点乱七八糟的。”
我没接话,但我更清楚地记住了“房事不济〞这个词。终于在一个获准上网的周末,我打开搜索引擎,郑重其事地输入 “房事不济”四个字。然后......然后就学习到了一些新知识,也终于理解了那天对话时空气里微妙的尴尬。
现在回想这件小事,不得不说这真是太典型了:小孩知道什么不该问,家长也一如既往拐弯抹角,这一套性教育太极拳,几乎是大部分中国家庭的写照。

更好笑的是,作为女孩我们接到最具代表性的招式是:“要懂得保护自己,不要吃亏”。这真的很难评。首先,你被默认是异性恋;其次,你被暗示在关系里自己是会“吃亏”的;最后,到底什么是“保护”和“吃亏”,不管你懂不懂,说这句话的人都默认你懂了。
以上就是我从家庭中接受到的全部性教育内容了。至于学校,你也一定能够想象:初中生物课,男女分开,女生讲月经,男生讲......男生讲什么我至今也不知道。我只知道,班上的男生还是会用“黑木耳”开玩笑,女生之间试探胸部大小的游戏也在继续......这些时刻慢慢融进青春期的日常变得无伤大雅,而青春期距离我把一切想通并敢于把阴蒂纹在身上还有很久、很久。
性教育匮乏的青春期里我产生过很多困惑。我习惯了月经的造访,也习惯了遮掩着拿卫生巾,但并不理解这些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出于好奇点开黄色小网站,并在一段时间内反复好奇反复点开,同时也感到深深的不适和不安;我发现触碰自己身体不同部位会有不同的快感,也特别想知道其 ta 同龄人是否也会这样做;我从大人隐晦的对话中推断出我妈有过“小产”,并立刻自动联想起父母房间的门锁拧不开的时刻......

就是因为在包括但不限于以上的所有问题上我从未得到过来自“大人们”的正面回应,所以我才在长大后对性教育产生了很强的兴趣。
促使我感到“我必须”去学习性教育知识的契机有两个,都发生在我读本科期间。
第一个契机是我表姐怀孕和她女儿的出生。2014年,表姐怀孕,她对这种全新的身体变化有些焦虑,我非常希望能为她做点什么,但没怀过孕的我能提供什么帮助呢!巧的是我的一位老师刚好在当时怀着二胎,她常和我们分享做妈妈的感受,她给人一种“她已经完全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的全方位自信。所以我在某次课后主动找到她,询问她能否给我正在孕期的表姐打个电话,或许能给表姐提供一些安抚和信心。
我的老师真的给我表姐打去了电话。我并不知道她们聊了什么,现在回想我才意识到,或许这样对相互是陌生人的她俩是有些尴尬的。其实是我不自觉地代入了姐姐的焦虑,才会不断思考做点什么。这种“做点什么”的焦虑,是我想成为性教育工作者的底层情绪。换句话说,正因为我没有接受过好的性教育,而这种匮乏导致了太多本可以被抚平的焦虑,所以我不希望 ta 人再经历这个过程,尤其是当我可以做点什么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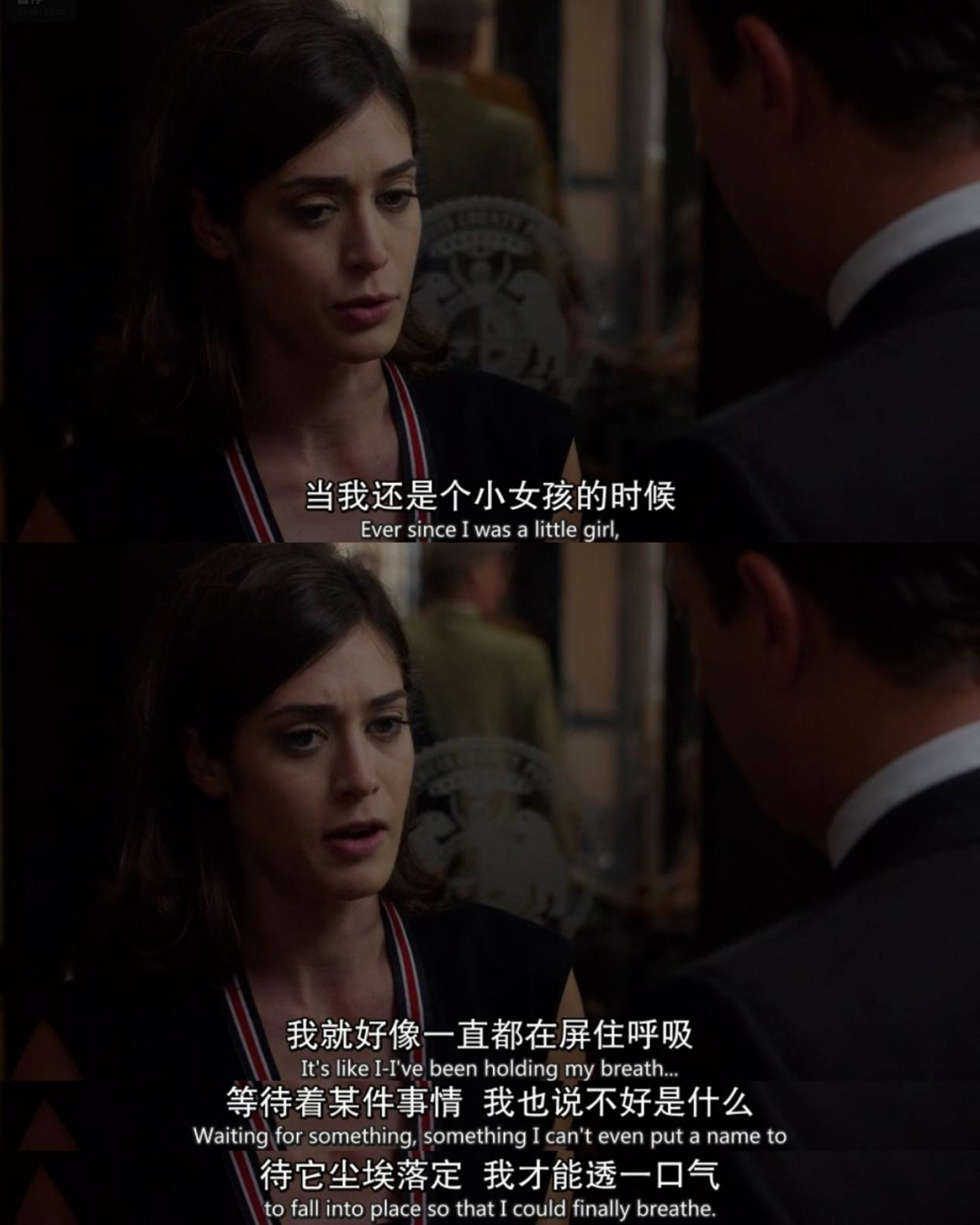
2015年中我的侄女出生,我的焦虑更加紧迫了。在当时我的想象中,她随时可能会被这个可怕世界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伤害。我更加密切地关注儿童保护的新闻和科普,并时不时把我认为有用的内容转发给表姐或者家族群里。
没过多久,另一件促使我学习更多性教育知识的事也发生了。2016年,我在西藏的一个乡村小学支教,某天傍晚我照例去食堂吃饭,走到门口时我看到有一群男生正被罚蹲马步。我问校长发生了什么,校长说:“他们昨天晚上不知道干什么,跑到女生宿舍里。” 这给了我很大的触动,想给西藏的学生上性教育课的念头也就此萌生。不过,那时我不知道怎么和校长提出这个需求,也不知道怎么上一堂性教育课,我也担心课程内容是否会和当地的文化或习俗有所冲突。
但我一直记着这个细节,也继续关注着性教育,零散地学习和拼凑着相关知识。终于在2017年,我报名了一个较为系统的儿童性教育课程。这时我的侄女已经两岁。我从课里学到更多,但疑惑于怎么把这些知识运用起来。
我尝试和表姐分享“性教育是终身教育”的理念,偶尔也和她讨论一些知识点,但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真的有用。直到一天我姑妈(表姐妈妈)在家庭群里说我侄女今天在客厅突然毫无征兆地尿裤子了,她收拾了半天但不懂为什么会这样。
我看到消息后立刻对应到刚学的知识:幼儿会经历学习如何憋屎憋尿的阶段,这个阶段里 ta 们会在大人认为不合适的场合或时间突然排泄,这是人类学习如何控制自己身体的必经阶段。我立刻回复说“这很正常”,解释原理,提醒不要责骂,她只是在练习,慢慢就知道什么时候憋不住。大人需要告诉她下次再憋不住记得说,让她相信大人会帮助她。是的,这也是性教育。性教育中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了解和照顾自己的身体,不为任何自然的身体反应和需求而羞耻,并敢于诉说和求助。

这个细节给了我信心,原来我储备的知识真的有用,只是要等待合适的讲述机会。接下来几年,我主动被动地拥有了更多机会。我持续地学习着,也更多地实践着。我参与公益性教育课给小朋友讲课,为性教育公众号供稿,去性教育短视频平台实习,也被邀请参与更多更广泛的性与性别议题的讨论......我也从2019年开始了性别与发展研究的硕士课程。
时间来到2020年,我因为不想上网课休学一年,也因此有了再次回到西藏的机会。这时我完全知道怎么上好一节儿童性教育课程,我联系了4年前支教学校的校长,向他提出回西藏上性教育课的想法,他非常支持。于是我在20年7月再次回到学校,给三到六年级的学生上了一堂性教育课。


“Everything is about sex”这句话在很多场合都被引用,在性教育领域它也成立。成为性教育工作者的过程中,我发现这并不是单个人、单个家庭、单个机构的责任,普及性教育也不可能一朝一夕完成,而是需要很多资源、机会,甚至运气。
我在过程中抚平了许多私人的焦虑,逐渐不再介意没能在成长中得到好的性教育。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朋友圈转发不同的性教育科普内容,有朋友因此找我讨论,因为 ta 也想在朋友圈做类似尝试但犹豫有些内容是否要屏蔽家人。这种犹豫非常真实,我过去常有,但在当时我的分享也几乎没避讳过任何人,因为只有不了解,甚至不认可的人也看到,才有可能产生一点什么。收获或震动,那是 ta 们自己要去消化的了。

我的家人一定也看到了那些内容。做性教育的几年里我通过很多方式跟家人告知、暗示、表达过我在做什么,我不会是你们想象中的“正常”女的,别期待我会做任何按部就班的事。我相信这让他们有了一些心理准备,至少他们不用再主动发起尴尬的对话,说些“保护自己”的废话。我给自己做了性教育,且不仅仅在这个层面上做了自己的家长,养育和关爱自己。
前年某一天我和我妈一起去取快递,是我收到的生日礼物。她问送了什么,我说安全套,她笑一笑没再说话。这实在很微妙,在性教育上,当我掌握更多理论和知识,成长为对性不拐弯抹角的大人,当“少看点乱七八糟的”的指责只会得到我有理有据的反驳而不再奏效后,家人反而自(被)觉(迫)放弃了更多的追问。尴尬依然存在,但不同的是,现在的主动权在我。
也是前几年某次回家,表姐跟我说侄女对厕所垃圾桶里的卫生巾很好奇,表姐就给她介绍了月经和为什么会流血。形成对比的是,侄女同学家家长对这些问题有点回避,那家小朋友就总还是提问。表姐说:“解释过后,她真的没有再问了。” 她的语气里依然留有一些不可置信。
但不是所有小孩都能有 ta 应得的资源。时隔4年再次回到西藏时,已经有女孩因嫁人而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这让我想起更多细节:我支教的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是女生,但我也听过家长说“别打儿子,女儿随便”;校长跟我一起为考上大学的女生筹学费,但他偶尔也会劝我早点结婚;村里很多女人都很能干,但男人却成日喝酒打牌到处耍......这世界实在有太多缝隙和参差,我无法关照和做到所有。
Everything is about sex,但对许多人来说关于性的一切全靠自学。在这条路上,我做了所有我想、我能、我该做的事,我也会继续做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