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一本书在现代中国的历险
野兽按:乔治·奥威尔的《1984》是我的启蒙读物之一,我当时读的是辽宁教育出版社的董乐山译本,里面描述的男主角所在单位真理部的工作令人马上想起了现实中对应物。“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
一个生活在“2+2=5”的国家里的人,每一个都值得读一读这本书:“这就是越多人看《一九八四》,自由就多一分保障的理由”。
当奥威尔虚构的遥远未来——1984年到来时,东亚国刚刚与昔日盟友大洋国反目成仇,而大洋国则与宿敌欧亚国握手结盟,但在这三个国家的官方声明和记录中,敌人和盟友却从来都没有变过,因为党的政策永无谬误,一贯正确,如果有人质疑这一点,那他一定是在境外敌对势力的诱骗下犯了思想罪,需要进行改造或是消灭。
《1984》甫一出版就被共产国家的老大哥苏联的官方报纸《真理报》和其他共产党控制下的媒体斥为反共作品,连带奥威尔本人更被骂作“蛆虫”、“章鱼”、“鬣狗”和“猪猡”。
1951年7月18日,一位名叫巫宁坤的留美学者踏上返回中国的邮轮,此时,他已经毅然决心放弃写了一半的博士论文,“放弃在一个最富裕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事业,回去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服务”,这位年轻的知识分子深信一旦回国,他“一定会受到对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在临前走,这位自少年时代就开始阅读高尔基的小说和共产党的秘密传单的学者,在他的行李箱里装满了他到处搜罗的左派进步书刊,其中也包括一本乔治·奥威尔的《1984》。
在巫宁坤登船前,他的一位好友,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前来向他道别,当巫问李“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时,李只是笑笑说:“我不愿被人洗脑子。”当时的巫宁坤对这句话茫然不解,直到30年后,当再度离开中国返回美国的巫宁坤提笔写下他的回忆录《一滴泪》时,他才理解李政道这句回答的真正含义,以及行李中那本《1984》仿佛命运般的预兆。
当初发出“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预言的陈梦家,则扮演了巫宁坤回忆录中历史殉道者的身份。1966年8月24日,在北京考古研究所里,陈梦家恐惧地听着旁边东厂胡同里发出的凄厉的惨叫。在那里,拷打从下午持续到深夜,红卫兵们除了用棍棒皮鞭打,还用沸水浇烫被绑在葡萄架子上挨打的两位老年妇女,“像杀猪一样”。为避免遭受同样的命运,10天后,陈梦家在家中上吊自尽。或者按照那个年代的正确用语:“自绝于人民”。
“1980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这本书和赫胥黎的《奇妙新世界》、扎米亚京的《我们》并称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但是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不管怎么说,乌托邦和历史还有一点区别。前者未曾发生,后者我们已经身历。前者和实际相比只是形似,后者则不断重演,万变不离其宗。乔治·奥威尔的噩梦在我们这里成为真,是因为有些人以为生活就该是无智无性无趣。他们推己及人,觉得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看法。既然人同此心,就该把理想付诸实现,构造一个更加彻底的无趣世界。”
这本刊物的其中一个读者王小波在多年后写下了这段初读《1984》时的感受。这篇《1984》的译者就是著名的译者董乐山,1979年,董就在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陈适五的支持下把《1984》翻译成中文,分三期刊登在《国外作品选译》上。直到1985年,花山出版社决定以内部发行的方式出版“反乌托邦三部曲”。只有手持局级证明才能购买这本书。
附录
李夏恩:《1984》一本书在现代中国的历险
刘绍铭在翻译《1984》的过程中曾经看到过董乐山的版本,叹惋于董译的第一个发行版仅有区区420的印数,但他相信一个生活在“2+2=5”的国家里的人,每一个都值得读一读这本书:“这就是越多人看《一九八四》,自由就多一分保障的理由”。
“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奥威尔 《1984》

1942年10月10日,39岁的乔治·奥威尔在这天的日记中提到了一件事:为了庆祝中国革命纪念日,伦敦BBC广播大楼上特意升起了中国国旗——很显然,这是一个信号,用以显示同样遭受到轴心国攻击的英国与中国同仇敌忾的决心。但就像奥威尔惯常的冷峻幽默所发现的那样,这面国旗“不幸的是升颠倒了”。当然这不会是刻意为之,但也足见英国对这位万里之外的海外盟友的漫不经心。但此时的英国自身尚且自顾不暇,故而对远东地区的盟友也仅能以悬挂国旗的方式来表达支持,即使是对自己在远东的殖民地——香港、新加坡、缅甸等地,也只能敛手坐观其在日本军队的凌厉攻势下相次连属沦亡敌手。

四年后,这些关于中国、日本以及远东地区的只言片语,在奥威尔的大脑中拼出了一个未来世界的超级大国“东亚国”的形象。在奥威尔的想象中,这个国家是在二战后通过十年混战建立起来,其领土包括中国、南洋和日本群岛等地,其内部奉行的,是一套被称为“崇死”的意识形态,其核心价值是“消灭自我”。这个国家与被俄国并吞了欧洲之后建立的欧亚国和美国接管了大英帝国之后的大洋国鼎足而立,并称三大超级强国,彼此之间和战不休。当奥威尔虚构的遥远未来——1984年到来时,东亚国刚刚与昔日盟友大洋国反目成仇,而大洋国则与宿敌欧亚国握手结盟,但在这三个国家的官方声明和记录中,敌人和盟友却从来都没有变过,因为党的政策永无谬误,一贯正确,如果有人质疑这一点,那他一定是在境外敌对势力的诱骗下犯了思想罪,需要进行改造或是消灭。
当这个构想最终成为一本名为《1984》的小说并于1949年6月8日刊行于世时,奥威尔从未想过这本小说还可能会有除了西方读者以外的其他读者。尽管他在书中确实提到了那个以中国和日本为原型的“东亚国”,但这不过是书的背景而已。况且他此时肺疾已深入骨髓,无法等到亲眼看见他笔下的1984的现实版本——死神在他写作时就已经把镰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了。
但就在小说出版的两个月后,一个不具名的邮寄包裹跨越千山万水寄送到中国北方最大的城市北平,被交到北京大学一名叫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英文教授手中。
1949:一个来自“1984”的邮包
燕卜荪在二战时与奥威尔同为BBC电视台东方部的同事,两人私交甚好。当燕卜荪战后远赴中国后,缠绵病榻的奥威尔尚且惦念这位“像人们常常做的那样消失在中国”的老友。
甚至那个不具名的邮包也是奥威尔让出版商寄给远在中国的燕卜荪的。在寄出前,奥威尔特意叮嘱不要按照惯例在信中附上“作者赠阅”的纸条。因为那时北平已经处于中共的控制之下,而《1984》甫一出版就被共产国家的老大哥苏联的官方报纸《真理报》和其他共产党控制下的媒体斥为反共作品,连带奥威尔本人更被骂作“蛆虫”、“章鱼”、“鬣狗”和“猪猡”。奥威尔不想老友因与作者的交谊而遭受不必要的麻烦。
但燕卜荪的反应却表明奥威尔的苦心全都付诸东流——他很不喜欢这部小说,刻薄地评论称这部小说“像烙铁一样在想象力上留下永久的伤疤”,将其看做是作者糟糕身体状况孕育出的怪胎。燕卜荪也许也将这本书转给了他的几位北大同事和学生看阅,但似乎同样没有收到任何回应——《1984》这块石头看来尚未在中国的湖面上激起一圈涟漪,就悄无声息地沉入水底了。
不过这显然已经不是奥威尔所能担心的问题了,1950年1月21日午夜,这位忧心忡忡的小说家带着一揽子未来写作计划去世。在他去世的半个月前,英国正式承认中共建立的新政权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在2500公里外的天寒地冻的苏联首都莫斯科,中国大陆新政权的领导人毛泽东正在宾馆里等待共产主义世界的老大哥斯大林的接见,好向他表明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已经投入共产主义的怀抱。至于欧亚大陆的另一端,振臂高呼的口号、随处可见的标语、红旗和布告,以及喇叭里震耳欲聋的宣传,一起汇成一股滔天巨浪,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席卷整个中国大陆,每个人都被卷入其中。
在中共新政权最初的几年里,没人会认为现实中的中国与那本反共小说《1984》有任何联系(实际上也没多少人读过)。小说中以俄国为首的欧亚国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鏖战正酣,而现实中的中苏则宣称已经结成了牢不可破的联盟。即使是细节也对不上:小说里东亚国是经过了十年混战才建立起来的,而中共夺得政权的内战只打了不到四年。
表面上看,现实与小说的唯一相似之处,就是这年晚些时候爆发的朝鲜战争。很多人认为这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点,或许也因此一战,奥威尔小说中世界三大国的预言将会成真。但现实中,这场战争的战火从未超出朝鲜半岛之外,而且很快就被遗忘了。而燕卜荪,作为少数读过《一九八四》的人,对这场战争的回应是和他美丽的太太一起用中国传统的布袋木偶“编排了一出表现世界人民联合抗击美帝国主义的木偶戏,并且主动到处演出去支援抗美援朝运动“。燕卜荪深信共产党领导下的北京是个“民情振奋、前景光明”的地方,在这里度过的时光“愉快而刺激”
从燕卜荪参与这些政治运动的满腔热忱可以看出,他肯定没有认真阅读老友这部遗作,至少没有仔细看“两分钟仇恨节目”这一段。当他在1952年离开中国时,这个国家正开动全部政治机器进行“三反五反”运动,各地成立的人民检举接待室门庭若市,人们排起长龙来检举自己的亲朋好友或是坦白自己思想最深处的罪行,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清除社会的毒素,从而建设一个更美好的国家。燕卜荪也是如此认为的。在他伦敦寓所最醒目的墙上,他小心地挂上了一张毛泽东的画像,就像《1984》里家家户户都要张贴的老大哥画像一样。

“‘1984’来了,这么快!”
燕卜荪走得恰得其时,足以让他的心中仍能保留一份对红色中国的长期好感。这些使燕卜荪爱上红色中国的事物,同样也引诱着海外游子“重新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加入到“如火如荼的建设新中国”的宏大事业之中。1951年7月18日,一位名叫巫宁坤的留美学者踏上返回中国的邮轮,此时,他已经毅然决心放弃写了一半的博士论文,“放弃在一个最富裕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事业,回去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服务”,这位年轻的知识分子深信一旦回国,他“一定会受到对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在临前走,这位自少年时代就开始阅读高尔基的小说和共产党的秘密传单的学者,在他的行李箱里装满了他到处搜罗的左派进步书刊,其中也包括一本乔治·奥威尔的《1984》。
在巫宁坤登船前,他的一位好友,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前来向他道别,当巫问李“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时,李只是笑笑说:“我不愿被人洗脑子。”当时的巫宁坤对这句话茫然不解,直到30年后,当再度离开中国返回美国的巫宁坤提笔写下他的回忆录《一滴泪》时,他才理解李政道这句回答的真正含义,以及行李中那本《1984》仿佛命运般的预兆。
“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
这声后来被巫宁坤当做是预言的声音,出自另一个从美国归来的学者陈梦家之口。陈是诗人,同时也是最著名的殷商甲骨文和青铜器的研究学者。早在1947年,他就从美国回到中国,最终在1949年中共建政时选择留下。初回中国的巫宁坤因为临时没有分配住房,所以先在他以前的同学,现在陈梦家的夫人赵萝蕤家中。在巫宁坤眼里,这个未来将被他视为先知的人“不过四十多岁年纪,但又瘦又黑,经常皱着眉头,走起路来弓着背,仿佛背负着什么无形的重载,看上去有点儿未老先衰了”。而使陈梦家发出这句“预言”的原因,是有一天,广播大喇叭传出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
广播体操在红色中国的历史中占据着一个荣耀的位置,成百上千人被一个巨大喇叭里传出的尖嗓女声召唤到一个巨大的空场中,这个空场就被称为操场,然后跟着军队里哨令般的节拍,在同一时刻转动身体,伸臂抬腿,整齐划一的动作让个人融化在集体的汪洋之中,在同一声号令的命令下,与其他千百人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在党看来,集体体操是最能体现“团结就是力量”这句口号的事物,对成批制造共产主义新人尤为重要。对此,既可以将其当做是党期望改造人民体质的一种善意,让每个人像50年代海报中所展示的男男女女一样,有着发达到夸张的肌肉和黑里透红的健康肤色,以便在未来注定将会发生的共产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世界大战中赴汤蹈火,冲锋陷阵。同样,像陈梦家这样的人却会联想到《1984》中那段著名的对集体体操的描写,电幕里传来“震耳欲聋的哨子声”,“一个年纪尚轻,身材消瘦,但肌肉结实,足登运动鞋、穿着紧身上衣的女子”在放映“老大哥看着你”的电幕上出现,用粗声粗气的声音命令每个人举手弯身:“听我的口令做!一、二、三、四!来吧,同志们,多用点力气!”

陈梦家从广播体操中嗅出“1984”的危险气味,而巫宁坤则寻踪追迹,愈发感到奥威尔的虚构未来世界正在自己身边化为现实。一如《1984》中大洋国意识形态下制造出来的“新话”,成为燕京大学教授的巫宁坤不得不用“阶级斗争”之类的“新概念”、“新名词”来装扮他所教授的英国文学史。在“三反五反”降临时,他不得不和其他上千万人一遍又一遍齐声练习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就像《1984》里对老大哥万众齐呼:“大!大!大!”一样。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全班的二十几个男女学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于谈恋爱,有的忙于搞‘进步’政治运动”。只有少数几个真正热爱文学的学生找上门来,谈论《正午的黑暗》(阿瑟·库斯勒作品,讲述一位忠诚的老布尔什维克党员,前苏共中央委员鲁巴肖夫在斯大林大清洗中被捕审判,最终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处决致死的故事,正是这本书启发了奥威尔创作了《1984》)和《1984》。
但让巫宁坤意想不到的是,在这个现实版的“1984”的世界中,拥有一本《1984》本身就是罪行。当1955年那个炎热的夏天到来时,巫宁坤发现自己已经沦为全民公敌,他当年从美国归来的爱国义举已经成为了证明他是美国特务的罪证之一,昔日的同事召开批判大会公开指责他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手持搜查证的公安警察闯进他的住所,搜查所谓的对美国发送情报的“发报机”,在一场夜间小组的突击审讯中,一位讲师指责他组织了一个名为“ABC”的反革命集团,这个“ABC”社团本来是一个桥牌俱乐部(A Bridge Club),但却被解释为反布尔什维克俱乐部(Bolshevik)的缩写。但他最大的罪行是指导他的学生阅读包括《1984》和《正午的黑暗》这样的反动作品,“为他们反对共产主义和新中国提供了理论基础”。
“你看过《正午的黑暗》和《1984》。情况如果不断恶化,就会抓人、关人、甚至杀人。”当1956年大规模的反右倾运动如火如荼之际,巫宁坤忧心忡忡地告诉一位他昔日姓江的学生,这位学生和他同是巫宁坤学生的堂兄因为在反右运动前参加大鸣大放运动而受到批判:“历史常常是用殉道者的鲜血写的。人类社会今天的处境会更坏,若不是有那些殉道者奉献的牺牲。”在这说完这番话后不久,这名学生就不得已回单位去了。巫宁坤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四个月后,当巫宁坤看到长城时,他实在无法理解“这座巨大可怕的灰砖建筑物如何值得人们赞叹”,奥威尔真该把它放进《1984》里,在山海关的门楼上写下但丁写在地狱门前的名言:“放弃一切希望吧,你们进入这里的人们!”
两年后,巫宁坤在被迫放弃公职、开除教育工会会籍,并张贴了一张感谢党的革命人道主义关怀的大字报之后,被送去劳动教养。在一间铺着草褥子的水泥地监房里,巫面对着墙角发出刺鼻臊味的尿桶开始了自己的劳动改造之路,他被训导用昔日同事和朋友批判自己的方式去批判别的犯人,同时也遭到其他犯人的批判。之后,巫经历了强体力的劳动、无休止的认罪、饥饿、身体浮肿、疾病和红卫兵小将的批斗,当他奉劳改队长的命令挖好一个“六尺长、二尺宽、三尺深”的坑,把病饿瘐死的犯友老刘枯瘦的尸体埋进去时,他曾相信自己很快会“和这个死鬼合用同一个坑”。但奇迹般的是,巫宁坤竟然活了下来,并且可以和他同样饱受折磨的妻子一同离开中国,将这个被他视为《1984》真实版的故事写下来。
但当初发出“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预言的陈梦家,则扮演了巫宁坤回忆录中历史殉道者的身份。1966年8月24日,在北京考古研究所里,陈梦家恐惧地听着旁边东厂胡同里发出的凄厉的惨叫。在那里,拷打从下午持续到深夜,红卫兵们除了用棍棒皮鞭打,还用沸水浇烫被绑在葡萄架子上挨打的两位老年妇女,“像杀猪一样”。为避免遭受同样的命运,10天后,陈梦家在家中上吊自尽。或者按照那个年代的正确用语:“自绝于人民”。
欢迎来到“1985”
1979年5月,即将进入盛夏的时候,一本名为《国外作品选译》粗糙灰色的刊物正在北京大学东方二楼235号宿舍中传阅,按照一位阅读者的说法,人们阅读这本刊物和其它读物就像“杰克·伦敦《热爱生命》里那个刚被营救起来,饿疯了的生还者,不顾一切地寻找和藏匿食物一样”。此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从狂热的街头政治和暴力中被解脱出来的人们,开始贪婪地阅读任何一本与大字报和最高指示内容不同的文字。但这些视为冲破禁忌的文字并非是任何人都有权阅读,就像这本《国外作品选译》,它主要刊载的内容是被官方定义为“篇幅过长或性质不合的材料”,“不适合放在仅供高级领导阅看的《编译参考》中”的海外翻译文章,因此仅“供领导和同志们参考”。只有有内部关系的人才能订阅这本刊物,而且每期高达五角钱的订阅费用,也足以让当时生活费最多不超过五十元的大学生望而却步。
但对渴求编外知识,或者按照他们私下的叫法“好读野路子书”的年轻一代来说,这种内部读物有着异乎寻常的吸引力。而235宿舍的年轻人幸运的是,他们中的一个名叫刘晓阳的人恰好正是那种有内部关系的人,因此,这本期刊被一期期地偷偷带进宿舍,让官方规定没有资格看这些文字的眼睛大饱眼福。
就在这本内部刊物的第4至6期,恰恰就刊登了奥威尔的《1984》。按照附在小说开头的开篇词的解释,这部小说的作者奥威尔,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这本小说的性质,是“以当时苏联社会作为他设想未来社会的版本,把一些与他资产阶级个人自由主义格格不入的现象夸大丑化”,“由于符合当时冷战的需要,一时成了反共经典著作,影响很广,凡是涉猎现代国际政治资料的人,几乎随处会碰到这本书。”
尽管译者在开篇说明词中即对这部小说用尽咒骂之辞,并且小心地引导读者在阅读时不会将其中的有害毒素与中国联系在一起。但对足够敏感,真正读懂开篇词的读者来说,这些严厉的话语恰恰是一颗烟雾弹,用“批判”为辞来作为译者和读者的双重政治保险。
“1980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这本书和赫胥黎的《奇妙新世界》、扎米亚京的《我们》并称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但是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不管怎么说,乌托邦和历史还有一点区别。前者未曾发生,后者我们已经身历。前者和实际相比只是形似,后者则不断重演,万变不离其宗。乔治·奥威尔的噩梦在我们这里成为真,是因为有些人以为生活就该是无智无性无趣。他们推己及人,觉得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看法。既然人同此心,就该把理想付诸实现,构造一个更加彻底的无趣世界。”
这本刊物的其中一个读者王小波在多年后写下了这段初读《1984》时的感受。这篇《1984》的译者就是著名的译者董乐山,1979年,董就在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陈适五的支持下把《1984》翻译成中文,分三期刊登在《国外作品选译》上。直到1985年,花山出版社决定以内部发行的方式出版“反乌托邦三部曲”。只有手持局级证明才能购买这本书。凡是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人都知道,在那个短暂却空前开放的时代,所谓的“内部发行”不过就是一句广告词,这四个字的真实含义是:你们这帮无权无势的草民们,虽然买不起特供搞不了官倒,但起码可以在读书上享受一下儿领导干部的待遇。对这个版本的《1984》的读者来说,他们得到这一切需要付出的代价是1.75元。


但很不幸的是,那年正赶上戈尔巴乔夫上台,所以并没有引起太大的轰动,但却制造了一股潜流,在这批八十年代的秘密读者中,除了前面提到的王小波之外,还有余世存、傅国涌、许纪霖等等这些后来在文人共和国中赫赫有名的人物。
就在大陆推出第一个“内部发行”版的董乐山译《1984》时,台湾东大出版社也推出了另一个译本的《1984》,这个版本的译者叫刘绍铭,刘是海外中国文学研究耆宿夏志清的得意弟子,他第一次读到《1984》是在大三的时候,那时是1958年底,那时国府迁台初期的反共浪潮已经渐入尾声,生活在自由中国的刘绍铭对奥威尔书中的世界并无感同身受之处。直到1960年代末期,文革烈焰已经能够隔海相望,其实已在美国教书的刘绍铭才想起这本涉及“预言、讽刺和政治”的小说:“毛泽东说越乱越好,他的逻辑让我想到《一九八四》大洋邦的口号:战争是和平,自由是奴役,无知是力量。《人民日报》每天报道公社超额完成的数字,使我想到大洋邦迷理部的公布。刘少奇、彭德怀这些开国功臣可以一夜之间成为反革命、走资修正叛徒,使我想起大洋邦一句新语:非人。意指世界上从来没有这个人。红卫兵大义灭亲的故事,使我想起大洋邦探子团——即旧语所谓童子军——的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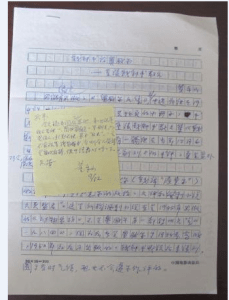
“真的就是这么巧。是奥威尔慧眼通天?还是世界上所有极权政体都有这种特性?”刘绍铭相信“一部作品要真的感动一个作者,有时的确需要客观的形势配合”。刘在翻译《1984》的过程中曾经看到过董乐山的版本,叹惋于董译的第一个发行版仅有区区420的印数,但他相信一个生活在“2+2=5”的国家里的人,每一个都值得读一读这本书:“这就是越多人看《一九八四》,自由就多一分保障的理由”。

“如果说,我们今天读来觉得书中描述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有幸没有变成事实的话,那么这并不是说将来就不会出现。我们最好还是把它看作1994年或更远一些未来可能出现的危险,而有所警惕。”也许董乐山说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刻意避开历史,而是放眼未来,他担心的不是上演,而是重演。
刘绍铭在2009年旧书重提时再次引用了董的这句话,但他相信《1984》里的灾难也许不会如董所担心的那样发生:“即使老大哥再生,也不容易强迫走资毒已深的红男绿女走回头路”。
但刘相信“2+2=5”的威胁仍然存在,只是也许会换一种形式,《1984》的本质是对思想的禁锢,极权的本性是将自由思想作为乱源加以禁止。新的技术手段会更有效率地过滤那些被禁止的词语,传媒技术的发达会更强有力地将意识形态的口号灌输到民众的心里。
2010年,刘绍铭的译本被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引进,此时中国大陆已经有了数十个版本的《1984》,包括多种盗版。再没有人会因为拥有一本《1984》而受到批判,身陷囹圄。董乐山的译本已经成为“钦定译本”,也是所有奥威尔格言警句的制造总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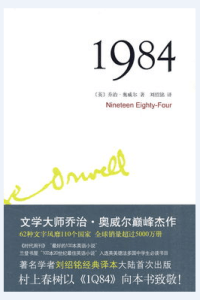
但《1984》的魅力仍未因之有所衰颓,反而历久弥新。《1984》的其它译本也被不断推出,孙仲旭的译本就是其中之一,尽管在此之前孙已经读过董译本,但他仍然选择了翻译一个自己的版本,因为这是属于他个人的经历,对他来说,“这是本非常压抑的书”在翻译过程中,这个四十岁的中年人曾经两次落泪,他从奥威尔中看到了他自己,或者说是体味到了生命可以如此痛苦,虽生犹死。
1984年的30周年时,孙仲旭悄悄地与这个世界告别,在他去世的一个月前,他引用了《霍比特人》里的一句话:“你不能现在放弃”。他的稿费最高只有千字七十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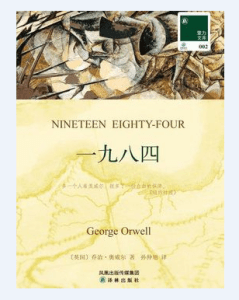
这或许是《1984》在现代中国的又一个悲剧,就像小说的结尾温斯顿满含热泪的说出“我爱老大哥”一样,它就像一个徘徊在小说和现实中的幽灵,不断在一代又一代读者的耳边低语,告诉那些愿意通过这部小说去审视现实的人一个简单却无比艰难的道理:在2+2=5的国度里,说出2+2=4需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
但是它值得。
来源:共识网
Like my work? Don't forget to support and clap, let me know that you are with me on the road of creation. Keep this enthusiasm toge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