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2 不存在的3億人:漂流、貧困、難以翻身,中國農民工的掙扎與悲歌
野兽按:長居中國的日本記者山田泰司,親眼目睹自己的農民工朋友生活日漸艱難,國家愈壯大,人民就愈渺小而愈微不足道的殘酷過程,並寫下最真實的第一手記錄。
2008年的北京奥运和2010年的上海世博,让世界见证了中国的繁盛与强大的国力,但随着城市的扩张与经济的成长,远离家乡、自四面八方聚集而来,追逐「中国梦」的农民工,不仅没有飞黄腾达的机会,反而陷入难以谋生的窘境。山田泰司亲身与这些生活艰苦却乐观的农民工长期往来,发现他们腹背是敌,不但被城市人排挤,也被制度排挤,更深深受制于政策的瞬息辄变。愈做愈穷已经不再是最大的困扰,问题是即便牺牲自己的人生,却似乎再也成就不了什么。
努力的人,不是该获得回馈与奖赏吗?
为何却彷彿总是在受惩罚?
贫穷,注定是一代传一代的吗?
他们像被限制在农村出生的诅咒裡,只能遥望城市人注定更好、更光鲜的未来。原本就悬殊的贫富差距,更在这十几年内剧烈扩大,大得就连原先乐天、欣然乐见国家富强的农民工,都忍不住要嘶吼一句:「政府到底要我们怎么生存下去啊!」
占了先机、具备条件的人冷漠以对,政府则沉默不语,而挣扎、痛苦,甚至绝望无处申诉的农民工们生活的空间,又被一纸又一纸的拆除公文渐渐限缩,甚至面临被切除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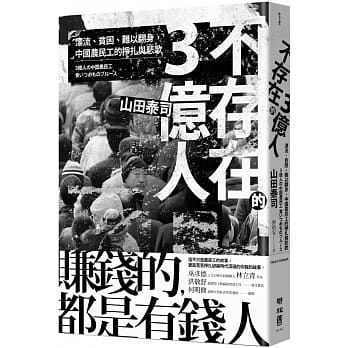
中國版的《絕望者之歌》!
「賺錢的,都是有錢人。」
「那才不關我們的事,上海已經人滿為患了,我們沒有餘力養那些農民工,他們趕緊滾回家鄉去就好了。」
即便苦苦掙扎、萬般忍耐,也注定無望的低端人生。
和爆買、豪奢無緣,始終懷抱希望,卻瀕臨絕望的中國農民工。
「上海正要把他們驅逐出去。」
長居中國的日本記者山田泰司,親眼目睹自己的農民工朋友生活日漸艱難,國家愈壯大,人民就愈渺小而愈微不足道的殘酷過程,並寫下最真實的第一手記錄。
2008年的北京奧運和2010年的上海世博,讓世界見證了中國的繁盛與強大的國力,但隨著城市的擴張與經濟的成長,遠離家鄉、自四面八方聚集而來,追逐「中國夢」的農民工,不僅沒有飛黃騰達的機會,反而陷入難以謀生的窘境。山田泰司親身與這些生活艱苦卻樂觀的農民工長期往來,發現他們腹背是敵,不但被城市人排擠,也被制度排擠,更深深受制於政策的瞬息輒變。愈做愈窮已經不再是最大的困擾,問題是即便犧牲自己的人生,卻似乎再也成就不了什麼。
努力的人,不是該獲得回饋與獎賞嗎?
為何卻彷彿總是在受懲罰?
貧窮,注定是一代傳一代的嗎?
他們像被限制在農村出生的詛咒裡,只能遙望城市人注定更好、更光鮮的未來。原本就懸殊的貧富差距,更在這十幾年內劇烈擴大,大得就連原先樂天、欣然樂見國家富強的農民工,都忍不住要嘶吼一句:「政府到底要我們怎麼生存下去啊!」
占了先機、具備條件的人冷漠以對,政府則沉默不語,而掙扎、痛苦,甚至絕望無處申訴的農民工們生活的空間,又被一紙又一紙的拆除公文漸漸限縮,甚至面臨被切除的命運。
中國經濟富強了,城市欣欣向榮。對此,山田泰司說道:「入住率如此低的地方,摩天大樓卻一棟接一棟的蓋,到底是蓋給誰住的呢?」
各界推薦
巫彥德(人生百味共同創辦人)
林立青(作家)
洪敬舒(台灣勞工陣線研究部主任)──專文推薦
何明修(台大社會系教授)──推薦
作者簡介
山田泰司(Yasuji Yamada)
山西大學、北京大學留學生。1992至2000年任香港日語報紙記者,2001年移居上海,任職於雜誌《美化生活》、 《CHAI》。長期於日本《日經商務電子版》上連載中國觀察專欄。
譯者簡介
劉格安
政治大學畢業,現為專職譯者,譯作類型包含商管、醫學、旅遊、生活、歷史和小說等。聯絡信箱:mercitapo@gmail.com
推薦序1 難以謀生的國度/林立青
推薦序2 都市要的是勞動力,不是人/洪敬舒
推薦序3 你是這社會中的少數,還是多數呢?/巫彥德
主要人物介紹
序章 難謀生者
日益擁擠的大都市
務農的年收入不足生活
四分之三的農民工沒上過初中
第一章 希望(奧運、世博)
一、留守兒童
沒錢就只能退學了
綁架犯,站住!
只有女人、小孩與老人的村莊
「又土又窮的農民小孩,哪有可能上學?」
戶籍分開的親子
連留守兒童都算不上的孩子
和春立的約定
電話打不通的理由
重逢
五人中有兩人中輟
「謝謝你記得我。」
二、女服務生的產地
一群不存在的人
產壞人的安徽省
無可奈何的豁達
三、受雞肉擺佈的人生
大方捨去尾數的餐廳
便宜好吃的店消失了!
北京奧運與上海世博的衝擊
過於懸殊的貧富差距
只有超市跑不了
曾經存在的良心
希望尚存
四、優衣庫(UNIQLO)的新娘服
中國農民眼中的優衣庫
十五歲出社會的新郎
「優衣庫一定有!」
大紅羽絨外套作嫁衣
五、當衝突化解分裂
上海與曾野綾子的勞動移民爭議
「狗與中國人不得入內」的現今
盡是上海人的公寓
被中國人討厭的中國人
「那個日本人根本不懂這裡的規矩。」
排外的上海人改變了
第二章 爆買與PM2.5 83
一、重見藍天,民工離去
廢棄物價格暴跌的理由是空氣汙染?
消失的貧民窟與農民工的住處
有貧富差距,但沒有嫉妒
走投無路到連面子都不要的男人
二、鬼城
「爆買」背後增生的鬼城
亞洲金融風暴與雷曼兄弟事件
公寓大廈林立的鬼城
「沒人會買沒有資產價值的公寓。」
內需不振,推動亞投行與貨幣寬鬆
中國巴黎
缺乏活力的建設潮
經濟繁榮的倦怠感
三、單親媽媽的煩惱
身為單親媽媽卻不能有小孩的矛盾
住在野狗吠叫的廢墟中的母女
無法洗澡、蓬頭垢面的三歲小孩
不管幾歲都領最低薪資
單親媽媽的懲罰
不平等的罰款
違反一胎化的母女
訪日爆買與轉手出售
可憐的莉卡娃娃
第三章 異變
一、遊民老闆
無家可歸的朋友
廢棄物回收業的困窘
出生地是癌症高發地區
失落世代的生存選擇
「我喜歡廢棄物回收的工作。」
美容沙龍投資客
與生俱來的貧富差距
二、家庭女傭目睹的異變
熱愛放鞭炮的中國人
隨處可見的「自首」、「舉報」標語
充斥習近平夫妻海報的農村
銳減的工作
「害怕工作被搶走」而無法返鄉的民工階層
強硬的政策是危機感的表徵
三、光天化日下的站壁女子
中國不存在暗巷
拆除圍牆的真正用意
光天化日下大量出現在市中心的流鶯
共產國家的特種行業
非洲民工與中國流鶯
第四章 夢幻王國與夢的幻滅
一、任務完成
「或許這次真的撐不下去了。」
工作開始減少
世博與迪士尼的美夢
市郊房租飆漲
集體消失的幼稚園生
驅逐地方出身者的上海
二、雖然蓋了高速鐵路
地溝油做的乳瑪琳
沒錢的人吃蠟燭
鄧小平的法國麵包
就業機會增加了嗎?
重獲生存價值的中高齡者
收入過低,年輕人不願回流
三、自用車與馬桶
馬桶外露的房間
農民間的貧富差距
與住家不搭調的汽車
和泡沫時期日本相同的危機
奢侈的車內比瀰漫殘敗感的家更令人嚮往
近在眼前卻遠在天邊的上海迪士尼樂園
四、同類相食的溝鼠
住在地底的百萬鼠族
做生意看門道
同類相食的掙扎與現實的選擇
個人利益最大化
逃跑的菁英
第五章 徬徨
一、聳然佇立的正宗哥吉拉
生氣的哥吉拉與不生氣的人類
面對不公不義也雙手一攤說「沒辦法」的中國人
被都市拋棄的農民
離開窮途末路的上海,前往新天地
無以為繼
重返毫無展望的上海
頌揚中國的失業者
二、流離失所
家不是用來住的
失控的上海不動產泡沫
已達薪資天花板的農村出身者
失去立足之地的農民
著眼於日本的中國農民
三、EXILE與中國農民
EXILE=「民工團」
問題的轉移與歧視
佯裝成正經報導的官能小說
第六章 第一次看海
驅逐農民工
一夜致富
儘管告別了沒有窗戶的房間
「大家的運氣真好啊!」
廢墟,最後的落腳處
尾聲 農民工該何去何從?
西裝與鶴嘴鎬
巨大的貧富差距
雙親餓死的震撼
同樣的世代,不同的背景
除夕夜的日式炒飯
中國夢的極限
夢醒之後
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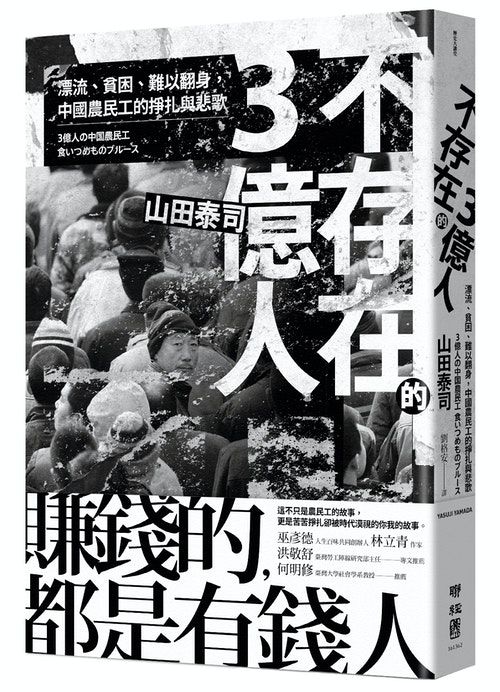
推薦序1(節錄)
難以謀生的國度
林立青(作家)
作者在書中不只一次寫到了農民工在城市以及在不同地區的「認命」,而且對來中國的日本作者非常友善,但是寫到城市居民時,他點出了地區階級,其中最明確的便是上海人對於其他縣市人民的優越感。在書中作者用了不少細節,描述上海人對其他地區居民的明顯歧視及找碴的行為,對於安徽以及河南的群眾有近乎於種族歧視的對話,也對勞力工作者極為不尊重。
其次,他觀察到在二○○七年以後,移除舊建築物的都更明顯排除了原先住在此地的群眾,造成經濟差距的嚴重擴大,此時黑心食品也開始變多,而當人們發現就連自己都難以透過勤奮和努力翻身時,道德便開始低落。就連作者自己自二○一四年開始,也租不起位於上海的房子了,因為房價在一年以內長了整整一倍,原先守著店面,願意去掉結帳零頭小數給予老客戶優惠的商販,也退出經營。
再來,出身日本的作者,觀察到在中國進行量化寬鬆,中國旅客到日本大量購買免治馬桶座的時候,中國的房地產泡沫也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而且不見遏止,連帶的影響是在關於中日兩國的討論之中出現的各種爆買狀況。
最後一點讓我最掛心的,是國家的體制傷害了弱勢族群的未來可能性。作者寫到一名未婚女性在生下孩子以後,發現自己因違反規定必須負擔高額罰金,只能住在被淨空的廢墟之中,而孩子完全得不到良好的照顧,相比之下,如果有認識的官員,則可以讓罰金降到只剩下不到三十分之一。
在讀完本書後,我一直記得作者提到,中國是一個貧富差距極大,而且讓人們難以謀生的國度。
推薦序2(節錄)
都市要的是勞動力,不是人
洪敬舒(臺灣勞工陣線研究部主任)
中國的人口每五人中就有一位農民工,這數據頗為驚人。換算臺灣兩千三百萬人,等於是四百六十萬名工作人口,也就是近全臺一千萬勞動人口的半數。放眼全世界,除了大規模的天災或戰亂,少有地區或國家能出現這麼龐大且規律的人口移動。
移動是全球化的附產品。資金流動帶來或帶走發展機會,讓人必須尾隨勞動市場移動,農民工、臺灣的北漂現象及藍白領的跨國移工都是如此。所以每位農民工動身出發之際,我想大半都與一九九○年林強的〈向前走〉懷著同樣的夢。
阮欲來去臺北打拼,聽人講啥米好空的攏在那,
頭前是現代的臺北車頭,我的理想和希望攏在這
農民工與臺灣的北漂族有著強烈的既視感。從農村到城鎮到都會區,臺灣也經歷了持續追逐更好的就業機會所形成的內部勞動遷徙;五○年代工業化起跑的同時,農地繼承歷經數代分家切割,漸難以成家,臺北及高雄兩大都會地區工商業的就業機會,成為巨大的拉力。至今許多落戶的臺北人,便是當時父親先離家打拼一陣子,等工作及住所安定就接走老小,等成就規模再大些,再拉著手足親友共同打拼,從移動家庭擴大為家族移動。山田說上海餐廳有許多來自安徽的服務生,臺灣許多行業也有同鄉幫。三重、中永和更是移居家庭的落腳城市,為一河之隔的臺北城提供都市建設或維持舒適生活不可或缺的工作。
……在城市拓張階段,體力勞動最是便捷的本錢,農民工投入建築或流水線生產,憑的不是技術而是不拒絕加班的毅力及體力。勞動的汗與淚成為澆灌產業與都市茁壯的養份,但被吸到乾癟的軀殼總是在某個時刻過後成為被割除的對象,因為他們已被當作髒亂落後的象徵,亮麗都城形象的破壞者。
就業的惡化還不足以逼退一心要向上爬的人。對底層社會的人而言,他們早就不過問想做什麼,只怕明天睜眼後卻沒得做。能夠逼退他們的手段只有剝奪居住機會,於是大規模拆遷出現了。如同書中一直流轉在各處廢墟的喬女士說的:
如果光是找到一個住的地方就耗盡心力,也不可能講究什麼工作意義。
推薦序3(節錄)
你是這社會中的少數,還是多數呢?
巫彥德(人生百味共同創辦人)
也許有人會覺得:我知道貧富差距是一個社會問題,我們好像不缺一本書來告訴我貧富差距有多大。 但這本書之所以值得推薦,是因為作者以不帶偏見的眼光,記錄著他與許多經驗貧窮的主人翁互動,而從這些互動中我們可以看到,社會問題只是貧窮的一個面向,生活在貧窮中的人,他們有的不只有貧窮。例如即便身處貧困,書中主角們仍然重視著人與人的關係,對於遠道而來的作者,也務必要請他吃一頓平常連自己都捨不得吃的大餐。這本書提醒我們,在許多主流媒體追捧著成功、富裕、發展等等「進步」的同時,那些經常被人忽視的餐廳服務員、外送員,也努力地活著,努力記得自己從哪裡來,努力在都市的生活中維持人的樣子,而認識與相信彼此同樣身而為人的本質,只是在不同的生命經驗上有差異,這是改變社會排除最重要且最難的一步。
我想系統性社會包容是否發生,在於整個社會是否有足夠的能力聽見與聽懂更多截然不同的聲音,特別是那些來自社會邊緣的,甚至是來至邊緣之外深淵的聲音。這樣的聲音被聽見的初期常讓人不安、不屑,而當人的素養足夠穿透自身不安與不屑的情緒,多聽見一個過去沒被聽見的聲音,那麼會被社會推向邊緣的人就又少了一群。透過作者的筆,開啟了一扇傾聽更多聲音的門,讓我們聽見生活在上海底層生活者的聲音。
「進步」,是一個人過得特別好?還是大家一起過得不錯呢?
近代中國的大國崛起之勢似乎勢不可擋。在我自己家族聚會的餐桌上,上一代每每談及中國,都是羨慕中國的崛起與富強,多多少少有那麼一絲惋惜沒有跟上這個崛起之勢的意思。然而,大家欽羨的是競爭論下的成功,當每個人都追求自己最大的利益時,便會帶來社會最大的發展。贏家全拿,而每個人都想當那個贏家,在這樣的情況下,社會發展得愈快就捨棄愈多的人。
當我們看到北京切除事件,明白了現代大多數的「進步」是屬於少數者的效率,是以多數無權無勢者的不便利換取少數有權有勢者的便利。那麼,那會是值得我們追求的嗎?
你與我,是這社會中的少數? 還是多數呢?
導論(節錄)
這本書要寫的,是一群與爆買或反日無緣的中國人的故事。身為日本人的我,與生在中國內陸農村地區的他們,幾乎是在同一時期,也就是二十一世紀初來到上海,並在我來到這塊土地上工作與生活將近二十年的期間內,因為一些機緣巧合而相識。
在藉由二○○八年北京奧運和二○一○年上海世博等活動推動國家建設的中國,他們是一群靠著身體,將國家描繪的偉大藍圖,體現在上海或中國其他城鎮的功臣。在中國被稱為「民工」或「農民工」的這群人,如果不是他們忍著肌肉撕裂般的痛楚揮下鶴嘴鎬,挺著嘎嘎作響的背部或腰骨不停搬運鋼筋,如今可能就沒有狀似鳥巢、造型充滿個性的奧運體育場,或上海那一幢幢充滿近未來感的摩天大樓;如果不是有她們擔任家庭女傭,接下煮飯洗衣、接送孩童、照護年邁雙親等各種家事,上海的男男女女肯定無法在好不容易建設好的摩天大樓中,全心投入辦公室作業。
另一方面,中國在戰後依然屢屢發生像大躍進(一九五八—一九六一年)、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一九八九年)等動搖國家的亂事,直到二十一世紀即將到來之際,國家才開始安定下來,其中一群成長於特別落後的農村、到大約二十年前都還沒有機會接受充分教育的無學歷農村出身者,儘管表面上在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受到「知識分子要向農民學習」這樣的推崇,實際上卻陷入無法賺取現金收入的「難謀生者」窘境。對那些難以謀生的農民來說,大都市確實起到了提供「賺取現金」門路的作用,而這是農村或地方城市都難以做到的。
其中自十九世紀中葉起約一百年間,曾為英國、法國、美國租界和日本人居住區的上海,正如一九二六到二九年間、共在上海住了將近一年的詩人金子光晴,將租界時代的這塊土地評為:「儘管皆為難謀生者投奔之地,二者卻有些許差異,滿洲是攜家帶眷去種松杉之處,上海則是獨自從人前消失,耗個一、兩年去澆熄熱情之處。」(金子光晴著,《骷髏杯》(暫譯),二○○四年,中公文庫)一樣,這裡向來都在接收那些在其他土地上一敗塗地或難以翻身,以至於走投無路的人。
雖然說是接收,但從來就沒有人熱情招待他們,更沒有上海人舉雙手歡迎他們加入。在居住方面,有些低所得者的住所不僅沒有廁所隔間,甚至連沖水馬桶也沒有,只有一個他們稱為「馬桶」的便盆突兀地放在那裡,環境往往十分惡劣。
即使如此,無論是沒有學歷的農民或失業中的外國人、無論勤奮或懶惰、無論有錢或貧窮,就接收背景成謎、來歷不明的人這一點來說,上海算是整個中國獨一無二的特例。這個來者不拒的寬闊胸懷,孕育出中國第一商業都市上海的活力,形塑出這座過去被形容為「魔都上海」、與中國其他都市有明顯區別的城市的獨特魅力。
作為政治中樞的北京沒有上海這般自由,而且如果在規模不大不小的都市出現不說地方話的外人,立刻會引人注意,被由中國共產黨安插在居民之間,一個名為「居民委員會」的自治組織網給網羅通報,肯定無法自在地生活。倘若不是上海的話,我這個不屬於任何組織的外國人,恐怕沒有機會邂逅來自中國農村的勞動者吧。
我是因為在生活了八年的香港無法繼續謀生才輾轉來到上海,當時雖然已找到落腳的職場,但維持不到半年就失業,至本書出版(二○一七)為止的十七年間,大部分都是以沒有歸屬的自由業者身分維生,但每次都順利得到簽證,可以長居在這座城市。
在這十七年間,居民委員會的相關人員只造訪過我家一次。三年前,在我搬到現居處的隔天晚上,三名中年女性來訪。由於那是我第一次與居民委員會的人接觸,因此稍有防備,但她們問道:「有多少人住在這裡?你有固定工作嗎?」我回答說我自己一個人住,大部分時間都在家寫東西,她們便你一言我一語地嚷嚷了起來:「真虧你有辦法寫文章」、「我就寫不出什麼東西來」,隨後又莫名其妙地瀟灑離開了。
日益擁擠的大都市
過去這二十多年來,儘管經濟方面稱不上充裕,許多農民工還是得以在上海找到安身立命之處,然而他們最近這一、兩年卻面臨不少艱辛與波折。
有的人工作減少,有的人每轉職一次薪水就縮水一次,有的人在失控的房地產泡沫下因付不出房租而流離失所,有的人則一次面臨以上所有衝擊而走投無路。他們在瀕臨極限的狀態下,沒有一天不想著離開上海,其中也有人真的離開了。不過不久之後,所有人又都鬱鬱寡歡地重返此地,因為無論是到其他都市或返回鄉下,他們所處的環境絲毫不見好轉。
農民工的這種行動,究竟有什麼象徵意義呢?
若從結論說起,這代表包含上海在內的中國大都市,都已經沒有餘力接收「難謀生者」了。尤其是沒有學歷也沒有技術的人,無以謀生的現象益趨顯著。無論是在大都市、地方都市或農民工的故鄉,他們甚至連不求「滿足」但求還能「接受」的東西都已經開始無法獲得了。
這些農民工如何才「能接受」這一切呢?關鍵就是,他們能否至少在還無法確信「下一個會輪到我」之前,還能擁有做這個夢的機會。這些農民工住在如同廢墟的破屋中,視而不見高級公寓的都市人,做著都市人不想做的基層勞動或雜活,一直支撐著他們的就唯有這個「明天就會輪到我」的希望而已,但那個希望如今正迅速破滅。
他們這樣的情狀在中國,尤其在都市地區,已被認知為社會問題了嗎?不,事實正好相反。
二○一七年初夏,我向一位在上海數一數二大報社擔任記者、目前獨立出來從事藝術相關工作的上海朋友提到,最近上海愈來愈艱困了呢,沒有工作的人也變多了。他卻說:「啥?艱困是什麼意思?你說誰很艱困啊?」
他一臉不可置信地反問,似乎聽到了什麼真的令他意想不到的消息。
於是我告訴他最近發生在上海農民工身上的狀況,他只說了一句:「喔,或許真是那樣吧。」
然後就沒有其他反應了,彷彿這事是發生在其他國家一樣。
一想到他是前報社記者,我對他的反應就不勝唏噓。但即使如此,他在上海出身的中國人之中,並不是特別遲鈍的人。因為不光是過去幾乎形同免費從國家取得的房地產,在這兩、三年的失控泡沫下,價格如天文數字般飛漲,而且在上海生活,還會時常聽到附近鄰居成為億萬富翁的傳聞,所以看在上海人應該無法想像那些家庭女傭、工地的體力勞動者,或最近興起的宅急便、外送員等每天出現在眼前的農民工,明明跟自己一樣居住在上海這塊土地,卻遭遇生活狀況比幾年前惡化等情形。農民工的身影肯定投射在上海人的視網膜上,但實質上卻形同視而不見,彷彿他們根本不存在。
二○一六年六月十六日,上海迪士尼樂園開幕了。開園第一年的遊客人數就達到一千萬人,遠超過目標的百萬人次,業績似乎蒸蒸日上。
另一方面,在接近「夢幻王國」迪士尼樂園開幕的二○一六年春天,發生了一個鮮有人知的現象,一群過去為了追尋夢想而來到上海的人們,正如雪崩一般大舉遷離上海。遷離的人潮多到有的幼稚園甚至因為大量孩童離開上海,面臨經營不下去的危機。
這群人就是在上海從事基層勞動或體力勞動的農民工。失去工作與住處的他們,在上海著實失去容身之地後,歷經了一番艱辛波折,最後如遭驅逐一般離去。他們是一群即使想走也不知往哪走,一群走投無路、進退兩難的人。一群被迫妻離子散的人。在上海屬於貧富差距社會底層的他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其中存在的真相是,在海納百川的廣博胸襟下逐漸膨脹的上海,如今面臨成長極限,終於開始痛苦哀號,把容納不下的地方出身者驅逐出去。
在這個「夢幻王國」成功引來人潮的城市再也看不見夢想的一群人,上海的無情切割蘊藏著急速失去光輝的危機,畢竟這裡向來以「來者不拒」的態度,塑造出其作為一個都市的魅力,並吸引人潮與錢潮的投入。然後上海的這副模樣,在國家憑藉強大經濟實力,企圖以「一帶一路」將勢力擴大至歐洲或非洲,並大手筆買下希臘港口或非洲資源等強勢行徑背後,也與整個中國努力掙扎,連在非洲都試圖創造出國民就業機會的模樣遙相呼應。
在歡慶夢幻王國開幕的上海、在不願再予人夢想的上海,以及再也看不見夢想的人群中,也可以見到拚命扶養四歲女兒的單親媽媽喬女士的身影。
「或許這次真的撐不下去了。」
「剛才房東來趕我離開公寓了,叫我五天後搬出去,或許這次真的撐不下去了。」
我的智慧型手機在二○一六年剛開春不久的三月初旬,收到喬女士在緊要關頭傳來的這封短訊。
「連她也這樣啊。」回撥電話的同時,我嘴裡喃喃自語著,內心確信「他們周圍正在發生什麼事」。
我所謂的他們,指的是農村出身並從農村地方來到上海工作的人們。長久以來,他們都被統稱為「農民工」,但如今農民工也有了第二代、第三代,其中也有不少第二代以後的人念到大學畢業,進入都市企業工作,成為所謂的白領。只是目前在整體比例上占壓倒性多數的,還是最初農民工從事的工作,也就是在從「改革開放」進入高度成長的一九八○至九○年代的中國,在都會地區從事因「辛苦、骯髒、危險」而面臨人手不足的建築工地體力勞動、倉庫作業、工廠產線工人、服務業外場、富裕階層或中上階層家中女傭的人。
工作開始減少
前文也提到過,上海的家庭女傭工作大約從二○一五年秋天開始減少。喬女士原本的兩家客戶,也是在二○一五年十一月減少為一家。就在她擔心新的一年會面臨什麼狀況時,又遭到房東的驅趕。
我聽聞喬女士被驅趕的消息後,確信「他們之間正在發生什麼事」是有理由的,因為那兩、三個月以來,除了喬女士之外,也有愈來愈多在上海從事基層勞動的地方出身友人說過「我在煩惱房租要提高一倍的事」、「感覺好像快被趕出公寓了」、「我被解雇了」之類的話。
沒有足夠經濟能力為妻子準備婚宴上的婚紗,只好讓她穿優衣庫紅色羽絨外套出席的長順,也是其中一人。來自安徽省農村的他,在高中升學考試落榜後,十五歲就到母親工作的上海,透過親戚的介紹開始在花市工作。他的父親思順和我同為一九六五年出生,今年(二○一七年)五十二歲,母親比父親小兩歲,今年五十歲,兩人都只讀到小學畢業而已。思順曾經對我說:「雖然我上了六年小學,但最後只讀到三年級而已。」在現年四十歲以上的中國農村出身者當中,思順的學歷並不算少見的特例。
言歸正傳,十五歲就到花市工作的少年長順,因為受不了工作太辛苦,做了兩星期就辭職回到父親以務農維生的老家。附帶一提,我就是在長順辭去第一份工作,失意地搭車返鄉時,在長程巴士上認識他的。其後,他三番兩次變換職業與居住地,一會兒在東北遼寧省的瀋陽幫親戚帶孩子,一會兒又到浙江省沿海城市寧波的海鮮餐廳當服務生,然後再度回到上海當髮型設計師,最後在二○一二年,來到上海浦東機場附近的物流倉庫當作業員。雖然薪水視加班程度而定,但平均下來也有四千元(新臺幣一萬七千六百元)。那一年,他認識了在附近電子設備組裝工廠當作業員,而且同樣來自安徽省農村的十七歲少女,兩人認識之後在隔年的二○一三年結婚,並於同年生下女兒。若加上妻子的薪水,家庭總收入是七千元(新臺幣三萬○八百元)。
我還記得那一陣子,長順曾用稍微多了些自信的表情對我說:「我在工作中學會操作電腦,薪水也調升了。這是我第一次覺得工作很有意思。」
他說將來想買自己的車,載女兒去兜風,為此必須先考到駕照,於是在二○一五年花了一萬元(新臺幣四萬四千元)考到汽車駕照。他成為一個孩子的父親,工作上也愈來愈得心應手。從十五歲出社會起算已經第九年了,到二○一五年年中為止的兩年多期間,也就是二十二到二十四歲階段的長順,出社會以來第一次感覺生活充實,並過著可以描繪未來夢想的生活。
世博與迪士尼的美夢
擔任家庭女傭的喬女士雖然從成為單親媽媽開始,就過著相當辛苦的生活,但從擔任商場銷售員的二○○八年開始,到大約二○一○年為止的那幾年,每天都過得相當充實。「薪水方面,底薪非常少,業績抽成所占的比例比較多,但只要努力就會得到相對的薪水。當時即使把一半的薪水交給鄉下的父母,在上海還是可以留下一筆充足的生活費,也能存得到錢。我那時覺得要存錢重新裝潢老家也不算太困難,心想我有來上海真是太好了。雖然懷了孩子以後,必須辭掉工作,但如果繼續待在那裡的話,我想即使經濟不夠充裕,應該也不會有什麼困難。」
出社會八年多來每天為眼前生活忙得不可開交的喬女士,第一次對自己的將來感到樂觀的那一年,就是北京舉辦中國第一場奧運的二○○八年。兩年後的二○一○年則是舉辦上海世博。然後華特迪士尼公司也在這一年,與中方正式簽訂建設上海迪士尼樂園的合約。
長順的父母那一代人,也就是出生於一九六○年代中期到一九七○年代中期的第一代農民工,大約從一九九○年前後開始離開故鄉,前往北京、廣州、上海等大都會。然後大約從二○○五年開始,喬女士、長順等第二代農民工開始往上海聚集。世博和迪士尼樂園所創造出來的需求,將他們吸引到上海,支撐著他們的美夢。
然而到了二○一五年,這些動向卻開始變調。在中國經濟減速的同時,上海市中心的都更也暫緩下來,於是我愈來愈常聽到在建築工地從事體力勞動的農民工朋友抱怨說:「最近工作減少了,害我閒得發慌。」此外,由於都更開始減少,因此以往靠著收集拆除現場廢材料或廢棄物維持生計的農民工,也面臨可回收品項驟減,不得不改行換業的狀況,或是在找不到新工作的情況下,因為無法維生只好離開上海的人也大幅增加了。除此之外,在接近年底的時候,我也開始從家庭女傭口中聽見工作減少的哀號聲。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