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想念戛纳|23位电影人重温难忘瞬间

在电影世界里,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戛纳电影节的非凡魅力、宏伟的艺术和偶尔的荒诞,每年5月的戛纳电影节,明星和导演们都会聚集在这里,接受媒体和同行们的审视、赞美和评判。在疯狂的一周半时间里,年度的电影杰作逐渐掀开了面纱并开始赢得了世界级的声誉。狂热的掌声和喧闹的嘘声此起彼伏。今年,因为冠状病毒的疫情,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但是我们并没有就此放弃。因此我们采访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人,邀请他们谈谈对戛纳的回忆和对电影未来的看法。以下是经过编辑节选的摘录:
亚历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Alejandro González Iñárritu)
他在戛纳上映的电影包括了《巴别塔》(Babel,2006)
我第一次去戛纳电影节,是为了放映《爱情是狗娘》(Amores Perros,2000年)。事实上,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参加电影节。当时我们的预算很紧缺,所以我们决定住在戛纳外二十五分钟车程的小镇上,因为那里的房间要便宜得多。
有一天,我被邀请去参加和其他导演们的合影留念,就在晚上七点王家卫的新片《花样年华》(In the Mood for Love)首映前。我妻子玛丽亚(Maria)和我都认为只要在六点十五分打车出来就能及时到达。想不到那时根本叫不到出租车,尽管我穿着燕尾服,玛丽亚穿着长裙和高跟鞋,但是除了跑步去,我们别无选择。当时室外的温度高达三十五度(华氏九十五度),因为交通问题车都停在了路上。我们跑的时候,我妻子脱掉了鞋子,我先是脱了外套,接着摘了领结,然后又解开了一、二、三个纽扣。
我们到达已经下午七点零一分了。我重新穿上了外套。我的身体几乎浸泡在汗水里。笑一笑!闪了一下!咔嚓!闪了一下!喊着“Cheeeese!”对于一个电影人来说,进入这个有着二千个座位的传奇的节庆宫(Palais Des Festivals),就像是一个天主教徒走进梵蒂冈一样。从我们坐的后排位置,在这部比我们大四十倍的屏幕上,我们观看了《花样年华》。走出电影宫,玛丽亚和我非常安静得走了大概十分钟。到海边的时候,我们突然停了下来。玛丽亚抱着我,靠在我的肩膀上泣不成声;我也抱着她的肩膀哭了起来。《花样年华》深深地触动了我们,让我们无言以对。就在那个瞬间让我回忆起为何我要成为一个电影人,即使有时候感觉很傻也很难。

爱丽丝·洛尔瓦彻(Alice Rohrwacher)
她的《幸福的拉扎罗》(Happy as Lazzaro,2018)和《奇迹》(The Wonders,2014)曾入围了戛纳电影节
戛纳改变了我的生活。它向我展示了那些拓宽了我天马行空思想的电影,也为身为导演的我伸出了热烈的臂弯。就在我写下这段思绪的时候,我听到了窗外传来的邻居卡洛( Carlo)的声音——而他也和戛纳有些瓜葛。
我从来没有和卡车司机卡洛·塔马蒂(Carlo Tarmati)交谈过,因为他是我父亲最大的对头。我们两家的房子就坐落于比邻而居的小山坡上。每当我父亲和卡洛互相斥骂和指责时,他们的喊叫声就会在树林里回荡。
在我为《奇迹》(The Wonders,2014年)选角时,卡洛来试镜了。当时我很尴尬,因为他是一个敌人。但是他天生是个演员的料。随着我们的合作,我们也开始越来越了解了对方。然后我们的电影被入围了戛纳电影节,当时我就慌了。我想带卡洛去,但我也想带我的家人,但是他们万一在电影节期间开始吵架该怎么办?
我还记得(2014年)《奇迹》剧组的红毯仪式上,我的姐姐阿尔巴牵着我的手、参演电影的四个小演员、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女儿、光彩夺目的莫妮卡·贝卢奇(Monica Bellucci),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卡洛。我用紧张的眼神看着我的父亲。放映开始后,卡洛和我父亲在电影中找到了自己,他们一起笑,一起哭。他们一起分享着恐惧。他们很喜欢我们共同完成的这项工作。在放映结束后的宴会上,他们彼此调侃取笑。几天之后他们成了最好的朋友,形影不离。
森林里再也没有传来愤怒的叫喊声了,取而代之的是彼此亲切的问候。在与世隔绝的乡村隔离期,卡洛·塔马蒂是我父母唯一见的外人。他们彼此帮忙一些无法独自打理的农活,他们互相陪伴,每天晚上就寝前都会打电话给对方问候。
而这只是戛纳改变我生活的很多方面的其中之一。

本·萨弗迪 (Ben Safdie)
他和哥哥一起拍摄的电影《好时光》(Good Time,2017)入围了当年的主竞赛单元
那是2008年,我有一部短片在戛纳的“导演双周”(Directors Fortnight)单元展映。我很着急,朋友让我坐在他摩托车后座。我没有头盔,而且是这辆摩托车上的第三个人,这两条在戛纳都是违法的。不过我想反正就这么一小段路,肯定会没事的。当然,我们立刻被警察拦了下来,他们让我去中央警察局缴纳罚款。
在警察局的时候我被告知,警察局长让-马里·贝雷戈(Jean-Marie Beulaygue)想见我。这一切的感觉就像是发生在《爱丽丝餐厅》(Alice’s Restaurant,1969年)。当我走到休息室的时候,让-马里已经在那里了,他问是否可以一起喝杯咖啡。我吓了一跳,问他问什么。“因为你是个电影人啊。”他激动地说。原来他参与了所有“导演双周”单元的讨论会,而且尽可能地看更多的电影。我想,戛纳的警察局长理所当然是个影迷了。在互道再见之后,让-马里让我保证如果有机会再来的话,一定要和他打招呼。我笑着同意了,不过当时几乎是百分百肯定我不会再来了。
出乎我的意料,我的哥哥和我发现第二年又要回到戛纳了。那个时候更为疯狂了,我们几乎没有任何时间做其它事情。我们马不停蹄地从一个会议跑到下一个会议,就在这时,我的法国制片人打电话给我说:“刚才有两个警察过来找你。”我让他冷静下来,然后就走去警察局。让-马里走了出来,脸上绽放着灿烂的笑容,“欢迎回来!”
很快到了2017年,约书亚和我又一次来到了戛纳,这次是主竞赛单元。我不想再次引警察上门,所以就直接去警察局问候下老朋友。出人意料的是,那里没有人知道我说的是谁。我给他们看了照片,告诉他们让-马里的名字,但是,无人知晓。当我走回海滨大道时我开始怀疑自己对这一切的记忆。就在我几乎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我突然听到有人在导演双周办公室那边喊我的名字,正是让-马里!原来他多年前就从部队退休了,现在在电影节工作。他笑着拉着我走进了办公室大楼,“你看!我们认识吧!”原来,他一直和那里的工作人员讲我们熟识的故事,但是没有人相信他。以下这张照片我们一起拍摄于2008年。

约书亚·萨弗迪 (Joshua Safdie)
对我们的父亲(他出生在意大利,在法国长大)来说,戛纳电影节是一处圣地。从小到大,我们就不得不经常面对大惊小怪的父亲,“这部电影在戛纳电影节上映了!这是一部经典!”无需任何争论,戛纳的王者地位已经潜移默化地嵌入在我们的脑海里了。很自然地他保证他一定要会和我们一起到蓝色海湾(Riviera)。
2008年的时候,他参加了每一场晚会,去看了我们的票允许进入的所有的电影放映。第二年,也就是2009年,他没有办法参加,对他来说这是一次巨大的损失。当我们八年后再次来到电影节,这次是主竞赛单元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是不会错过这一次的!他不想在行程和住宿事情上麻烦我们,只是不停地对我们说:“我会去的,不用担心我。”
那时还是伊斯兰国肆虐期间,安保工作特别严密。在我们首映礼的前一天,电影节官员提醒我们注意红地毯的规则和限制。他们告诉我们,警方把红毯的安保工作做得比大多数政治集会都要严密。所以当我们第二天看到红毯上的照片时,你可以想象我们的惊讶。我们就在那里,本,和我,(巴迪·杜瑞斯 Buddy Duress、罗伯特·帕丁森 Robert Pattinson和泰丽尔·韦伯斯特 Taliah Webster)就站在红毯顶端。在我们身后,每个剧院的入口处旁边都站着一个警卫或警察。然后,就在右边,他就站在那里……我们的父亲!不知怎的,他以某种方式悄悄躲过了警察、电影节工作人员和电影节的负责人们。他悄悄地在楼梯的顶端找到了一个可以安静拍摄的地方。

韦斯·安德森 (Wes Anderson)
2012年他带着《月升王国》(Moonrise Kingdom)来戛纳了
你有关于戛纳的轶事趣闻的特别回忆吗?
迄今为止我还只去过一次(《月升王国》Moonrise Kingdom,2012年)。蒂耶里·福茂(Thierry Frémaux,电影节的艺术总监)确实很懂得如何操办电影节。这里有来自全球各地的各种类型的好电影,而且,还有什么比在地中海沿岸观看一部完美修复的251分钟的《美国往事》(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1984年)更美好的事呢?
最近你在做什么?看了哪些电影和书呢?
我有一个四岁的女儿,所以,和大多数处于同样状况的人一样,我现在也是一个兼职的业余老师。我所读的很多书都与古埃及、恐龙、昆虫和亚马逊雨林有关,不过也有帕特里夏·海史密斯(Patricia Highsmith)、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和埃尔莫·伦纳德(Elmore Leonard)的作品,以及一本关于瘟疫的书。我们每天晚上都会看一部电影,最近几个晚上我们比较喜欢的电影有:《寂寞芳心》(Alice Adams,1935)、战胜恶魔(Beat the Devil,1953)、《毫不神圣》(Nothing Sacred,1937)、《为所应为》(Do the Right Thing,1989)、《归途路迢迢》(The Long Voyage Home,1940)、《近松物语》(A Story From Chikamatsu,1954)、《极乐大餐》(La grande bouffe,1973)、《深情的朋友》(The Passionate Friends,1949)、《撒哈拉六号基地》(Station Six-Sahara,1962)、《好莱坞的价值》(What Price Hollywood?,1932)和《杀机》(Winter Kills)。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Clint Eastwood)
他是戛纳的宠儿,曾有五部影片入围主竞赛单元,2009年获得终身成就金棕榈奖
我去过好几次了。几年前,他们举办了《不可饶恕》(Unforgiven,1992)25周年的放映活动,那是我最后一次去那里。很高兴有新的观众去看一部老电影。
我已经好多年没看这部电影了,所以很想亲自去看看。它一直坚持着。有时候,你会觉得我都做了这么长时间了,该会怀疑,我做的这些到底是什么鬼东西。但是当你看到它时,很多东西都会重新涌上心头。
第一次去的时候(《苍白骑士》[Pale Rider,1985])非常有趣,也有些手忙脚乱,因为你需要跑来跑去,还有很多人,所有的事情都需要当即完成。当你后来再去的时候,就会相对轻松,因为你会说,好吧,我不想把自己搞得太紧张,因为最终你都需要去回答很多问题。

贾樟柯
他一直时戛纳电影节的常客,《天注定》(A Touch of Sin,2013)和《江湖儿女》(Ash Is Purest White,2018)等多部影片在戛纳电影节上亮相。
2013年的时候我收到了电影节午餐会的邀请。我英文水平欠佳,对这样的活动感觉有点累。出于礼貌,我打算现身后就尽快离开。
当我到的时候,我看到福茂、李安导演和一个坐轮椅的人围在一起聊天。我和他们打了声招呼,就出来在外面吸烟。李安导演的助手过来叫我。李安看着坐轮椅的人说:“小贾,贝托鲁奇导演(Bernardo Bertolucci)想和你聊几句。”
我睁大了眼睛,下意识地喊出来:“啊,他是老贝啊!”
这不是不恭。因为贝托鲁奇在中国拍摄过《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1987),中国的电影工作者用中国人的方式称呼“老贝”,就是自己人的意思。
贝托鲁奇导演握着我的手,开始说话。李安开始帮助我翻译,“怎样能看到《无用》?你的电影我就这一部还没有看过。”我有点不知所措。作为前辈,贝托鲁奇不吝表达对晚辈的鼓励。自己的创作被他关注着,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鼓舞人心了。
2008年,《二十四城记》戛纳新闻发布会的时候,阿巴斯导演站在门口看着我,我走过去,他给了我一个深深的拥抱。我们两个什么都没有说,他转身离去,留下了他的的体温,温暖着我。2015年,《山河故人》(Mountains May Depart,2015)剧组摄影时,阿涅斯·瓦尔达导演(Agnès Varda)在几十台相机面前突然径直走了过来,一只手拉着我,一只手拉着赵涛。之后我再看那天的照片,她的视线一直看着我俩,目光中有一种外祖母般的溺爱。贝托鲁奇、阿巴斯、阿涅斯·瓦尔达如今都走了,但在戛纳电影节,他们把自己的体温和目光留给了年轻一代,让我们从中吸取力量,活着并坚持拍摄着。
☞ 我们想念戛纳|贾樟柯的戛纳瞬间:目光与体温(贾樟柯的未删减版本)

迈克尔·摩尔 (Michael Moore)
这位纪录片导演在戛纳电影节上展示的作品包括2004年获得金棕榈奖的《华氏911》(Fahrenheit 9/11)。他录制了一段关于获奖时刻感受的视频,以下是来自视频的文字翻译版:
大家好,我是迈克尔·摩尔,今天应邀在此分享我在戛纳电影节上的一段回忆。我有四部电影入围了戛纳电影节,那都是非常美妙的经历。就在2004年,我凭借《华氏911》获得了金棕榈奖,而当晚最棒的事情是,当时担任评委会主席的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在台上把金棕榈递给我。在所有的喧闹声中,他俯身对我说:“我想告诉你一件我从没有告诉过任何人的事情。我从来没有投过票。事实上,我甚至从来没有登记过投票。但是当我这周看了你的电影后,我决定,当我回到洛杉矶后,我要去登记投票。今年我就参与投票。”我被这一刻感动了,我对他说,“说实话,我是真心实意的,你刚才告诉我的这句话,如果被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重复了一百万次,如果有一百万人决定参与并投票,那对我来说,今晚的这句话比任何金棕榈奖、及其它任何奖项都重要。那才是真正的奖,是这部电影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所以,我不知道,这就是我对那个夜晚的印象。它只是一件小事,但我希望它能成为一件更大的事。一年后我遇到了他。他告诉我他真的这么做了。他去登记注册了,也参与投票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就这样发生了,而这让我觉得做拍电影是值得的。感谢你的邀请,我很遗憾,所有的电影人都不能、也无法让他们的电影参与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但我希望很快就能看到你们的电影。也祝你们一切顺利。谢谢你。
克雷伯·曼东沙·费侯 (Kleber Mendonça Filho)
这位巴西电影人以影评人的身份报道戛纳电影节多年,后来他的长片《巴克劳》(Bacurau,2019)和《水瓶座》(Aquarius,2016)入围了主竞赛单元。
我记得:
- 在德彪西(Debussy)或卢米埃尔(Lumiere)放映厅里,有人起身离席时座位上发出的令人生厌的标志性声音,有时候这些人是希望所有人都知道他在电影开场二十分钟后就离开的。
- 2010年《豹》(The Leopard,1963)的特别放映。我的记者证让我有机会坐在(影片主演)阿兰·德隆(Alain Delon)和克劳迪娅·卡汀娜(Claudia Cardinale)前面。那是一次戛纳电影节时空折叠的极端例子。他们就坐在我后面看完了整部电影,而且似乎被影片本身和这场放映所感动。
- 《巴克劳》和《水瓶座》放映后观众的反应和起立鼓掌,当灯光亮起时蒂耶里·福茂带着摄制组走了进来,这是疯狂而又独特的戛纳时刻,和其它地方都截然不同。你希望它结束,同时你也会希望它一直继续下去。

阿贝尔·费拉拉 (Abel Ferrara)
他的《坏中尉》(Bad Lieutenant,1992)、《异形基地》(Body Snatchers,1993)和《绝色惊狂》(The Blackout,1997)曾在电影节上放映过。
《异形基地》的首映式晚上,我整装待发,计算好了从酒店到放映厅的五分钟走路的完美时间,然后准备去系领带。只是没有领结!我吓了一跳。当时我妻子对所有的领结都持怀疑态度,但公关部的人要求我把衬衫扣好就可以了,“你是导演,你不需要领带。”就像所有的瘾君子都能在最后一刻找到解决办法,我也想到了一个好点子。我打电话给酒店服务,告诉(服务员)我想用五十美金换他的卡夹式领带。他先是拒绝了,但在我又给了五十美元的法郎后,我得到了这条领带直到午夜的使用权。我们到达红地毯时整整迟了五分钟,这对于负责人来说,无异于在行礼时掐死了戴高乐!
现在我们回到《绝色惊狂》的时间。那部电影并没有入围主竞赛单元,不过因为有丹尼斯·霍珀(Dennis Hopper)、碧翠斯·黛尔(Béatrice Dalle)和克劳迪亚·席弗(Claudia Schiffer)参与,我们要在非竞赛单元(out-of-competition)做特别放映。我提前很多时间到达现场,没系领结,有点焦急地继续等待演员们的到来。我听到我们的公关人员(拿着两部手机)重复说:“好的,碧翠斯还在她的化妆间,好的,她现在拒绝出来。”然后从另一个电话中传来声音,“克劳迪亚终于穿上她的鞋子了,她刚脱了它们。”四十五分钟之后,碧翠斯和克劳迪亚到了。没有人对她们说过一句话,她们开始踏上了红地毯,世界上所有的灯光都为之闪烁。


詹姆斯·格雷 (James Gray)
他有四部电影入围了主竞赛单元,包括2000年的《家族情仇》(The Yards)。
我和这个电影节的关系非常奇怪。举办电影节的人对我非常友好,整个选片委员会对我也是青睐有加。但是对我的电影的反应却非常怪异,它们得到了在这里放映的机会,却被人憎恶,大多数时间它们得到了大片喝倒彩的嘘声。我说,“我为什么要去那里呢?这也太蠢了!”我就是戛纳电影节的苏珊·卢琪(Susan Lucci),因为我觉得我拥有在主竞赛中参与最多却未获任何奖项的电影纪录。让我说我不去那里了(我向你保证会是这样的),我去那里不是为了去获奖的。当我拍摄我的第一部电影去戛纳时就已经做到这一点了。
但我很快就吸取了教训。我想说的重点不是说你应该为我感到难过,恰恰相反。我想说的是,你觉得有必要继续回去,因为你必须回去。大家对这部电影的反应如何并不重要,你必须要去。爱之深嘘之多,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不合常理,你当然不希望别人去嘘你的电影。但这种热情让你知道,实际上嘘声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这种媒体的爱的一部分。我知道这听起来似乎没道理。

科洛·塞维尼 (Chloë Sevigny)
她参演了很多入围戛纳的影片,并且执导两部也入围了电影节的短片,还曾经担任“影评人周”单元的评委。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因为史蒂夫·布西密(Steve Buscemi)导演的电影《伤心树屋》(Trees Lounge,1996)。我记得当时是和(制片人)克里斯·汉利(Chris Hanley)和罗伯塔·汉利(Roberta Hanley)一起飞过去的,他们也都是演员。然后我的行李丢了,这是戛纳无需言说的故事之一,每个人都丢过行李。然后我记得我必须借用罗伯塔的东西,跟着他们去了他们住的伊甸豪海角酒店(Hôtel du Cap),但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那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下榻的地方,可关键是我也不知道哪些人是有头有脸。我记得我和罗伯塔在动物公墓里拍了一张照片,我们两个人慢悠悠得走着,就像是,“我们到底在哪里?”

让-皮埃尔·达内 (Jean-Pierre Dardenne)和吕克·达内 (Luc Dardenne)
他们入围戛纳的电影包括《罗塞塔》(Rosetta,1999)和《两天一夜》(Two Days, One Night,2014)
这个五月对每个热爱电影的人来说都会失去一些东西。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巨大的损失,因为戛纳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家,收养我们的第二家乡,它拥抱我们的电影并让它们受到更多的关注。我们希望明年回来时还是继续以斯派克·李(Spike Lee,今年的评委会主席)担任评委会主席。在我们等待2021年5月的时间里,我们觉得应该利用这次活动的停顿来反思我们的工作,反思电影,反思电影在社会中的作用。
有人说,电影的未来存在流媒体平台的私人空间里。疫情隔离期间这些平台快速增长的用户就是证明。但这种增长难道不是只能证明,流媒体符合一个现实社交生活已经消失的禁锢社会的需求吗?我们真的要生活在这样一个偏执的世界里吗?我们这些社会人难道不就是渴望在公共空间里与他人相处,尤其是在电影院里,我们可以一起在比自己大的银幕上看电影,然后聚在咖啡馆和餐厅里聊一聊看了什么吗?这难道不应该唤醒我们去要求我们的领袖们,要制定和扩展对健康、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基本权利吗?我们也许正处于新型社会团结的萌芽期。这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愿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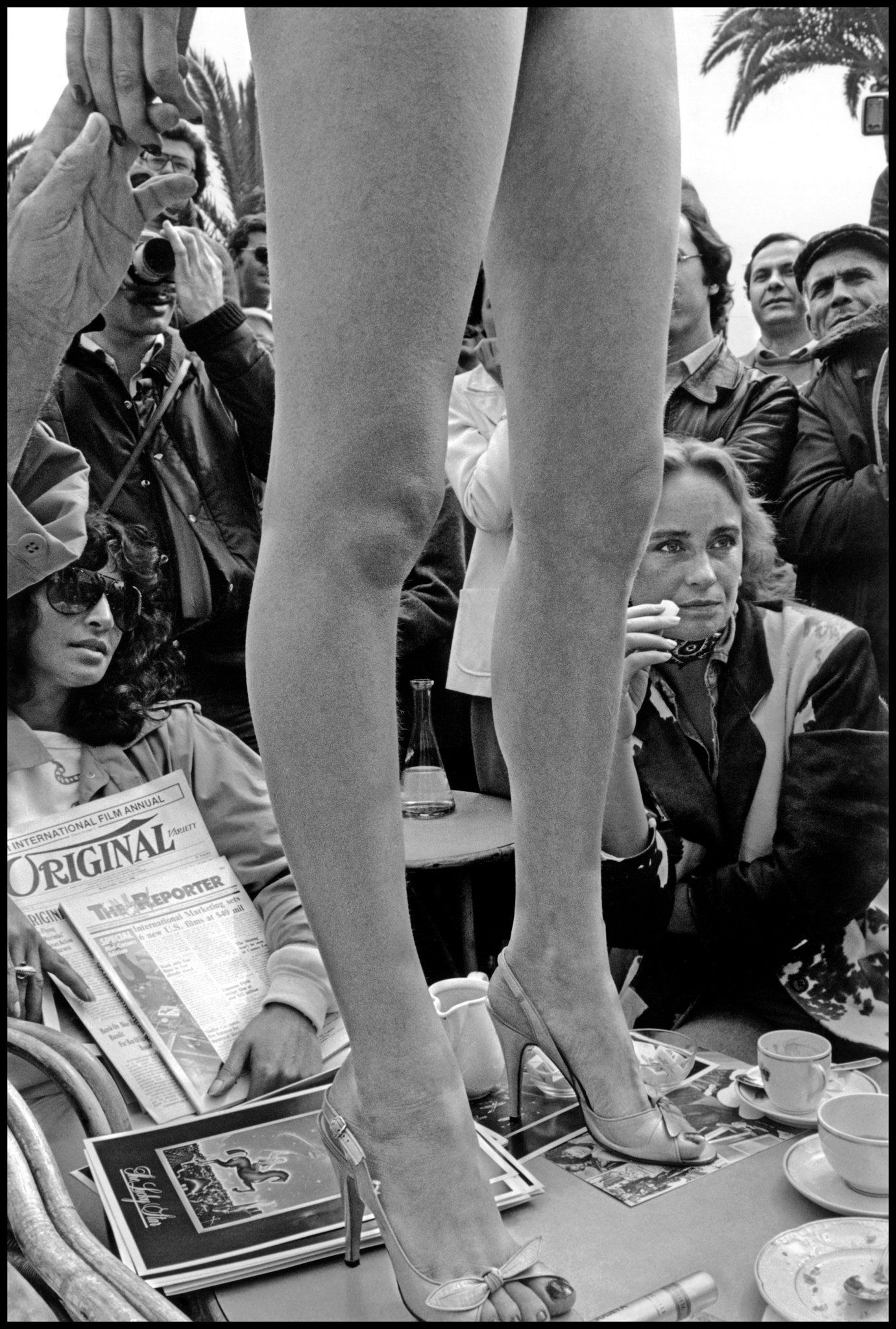
奥利维耶·阿萨亚斯 (Olivier Assayas)
他曾入围戛纳的电影包括《私人采购员》(Personal Shopper,2016)和《锡尔斯玛利亚》(Clouds of Sils Maria,2014)
你有关于戛纳的轶事趣闻的特别回忆吗?
我第一次去戛纳是在1977年,当时和我的好朋友、已故的电影人洛朗特·贝汉(Laurent Perrin)一起。我们当时住在他母亲的别墅里,离戛纳有20多英里。我们通常是早上搭车去电影节,晚上再回来。我记得我在Le Petit Carlton看到了法斯宾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我是他的忠实影迷,但从未敢接近他),他身着一套皮衣,正被粉丝们簇拥着。
最近你在做什么?看了哪些电影和书呢?
我现在正在一家启发我拍摄《夏日时光》(Summer Hours,2008)位于乡村的一座房子里(别幻想了,它真的很好,但电影里的房子是另一回事)。因此,我和我10岁的女儿维琪(Viki, 当她没有和她的母亲、电影人米娅·汉森-洛夫[Mia Hansen-Løve]在一起的时候)被限制在这里。所以我是一个兼职的学校老师,至少在五月中旬学校重新开放前,虽然目前还只是个可能。
最近我正在为A24写一个系列剧的本子,那是根据我1996年的电影《迷离劫》(Irma Vep,1996)改编的。它让我一直很忙,我在创作时也感到激动,甚至有些兴奋,它有些稀奇古怪的低级趣味,还涉及到当今电影的状况。

克里斯托夫·奥诺雷 (Christophe Honoré)
他参与戛纳的电影包括《喜欢,轻吻,快跑》(Sorry Angel,2018)
我的生日是在四月份。一般这个时间,巴黎就会捕风捉影地传播着哪些电影会入围戛纳电影节的风言风语。对我来说,春天总是与避开喧嚣和活跃在电影院里联系在一起。我在生活中失去的,重新在电影院里获得。当青少年时期,我从布列塔尼大区梦见的那些电影似乎是法国南部最美的生活。然后我成为了一个电影人,从而开始经历戛纳选片美妙而有凄惨的冒险之旅。
今年,从我的巴黎阳台上,如果有一两部电影的名字传入到我的耳朵,那微弱的声音听起来犹如墓志铭般的共鸣。我并不想说没有了戛纳电影节,它们就成了死电影,但它们会错过一些东西。它们被剥夺了有仙女和女巫靠在摇篮边的诞生仪式。它们被剥夺了可能的脱胎换骨的机会。所有的电影都不希望有童话般的命运,但观众需要这些传奇故事的延续,我们需要相信电影能拯救我们迷失的生命。没有戛纳的一年是缺失生命力的一年。无需去否认它。它是一个洞,一片真空,一次无法弥补的缺席。


黛布拉·格兰尼克 (Debra Granik)
她的电影《不留痕迹》(Leave No Trace,2018)入围了2018年的“导演双周”单元
在我戛纳电影节第三天的行程表上,写着“声音检查”,对于任何一部电影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程序,毕竟人们都是千里迢迢赶来这里的。音效检查通常都是走过场的形式,重点是确保现场不会有什么问题。而这次的情况恰恰相反——我们能做到多接近完美呢?四位技术人员在电影院里向我致意。他们首先猜测了我们应该把音量停在哪里:杜比6.8。他们播放了一个响亮的场景和一个安静的场景,在这个音量效果下听起来都非常不错,我对他们竖起来大拇指表示赞许。他们回答说,我们现在应该先听6.7,然后再试听下6.9和7.0。这个时候我对他们花如此多时间在这一部电影的音量上感到有些焦虑了,于是我装出掩饰自己不耐烦的样子。相反的是,我看到戛纳技术团队这四位敬业的成员希望能呈现出最好的音效。于是我放松地坐进他们建议的那一排舒适的影院椅子上,向我所在的现实屈服。
是枝裕和 (Hirokazu Kore-eda)
他在戛纳展示的影片中是从《距离》(Distance,2001)开始,也包括了《小偷家族》(Shoplifters,2018)
我永远记得第一次在戛纳走红毯的时候。那是2001年,当时我38岁。我对那一刻的记忆与骄傲、自尊甚至是成就感无关。
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我的敬畏之情。
因为我亲身体验到了电影的博大精深和丰富的历史。然后,一旦我接受了自己的微不足道的存在,以及作为一个导演的不成熟,我开始体验到了快乐。我意识到,虽然我只是一滴水,但我正与电影这条丰沛的河流一起流淌。我意识到我与这个世界有了深刻的联系,以往拍电影时产生的孤独感此时顿然消失。
这是我当年戛纳电影节的经历中最大的收获。

穆罕默德·拉索罗夫 (Mohammad Rasoulof)
他的电影《手稿不会燃烧》(Manuscripts Don’t Burn,2013)和《谎言》(A Man of Integrity,2017)都曾入围戛纳电影节的“一种关注”单元(Un Certain Regard)
在《手稿不会燃烧》上映的前一天,我在戛纳的海边,正急匆匆得赶往电影院,这个时候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停了下来。一个男人走了上来做了自我介绍:制片人卡维·法纳姆(Kaveh Farnam)。我记得他的名字,但是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第二天的放映他就坐在观众席上。电影结束后,他找到了我,拥抱我,并让我答应当我开始制作下一部电影的时候无论如何都要联系他。
两年之后我联系了他,当时我决定要开始制作《谎言》。我们最后决定一起制作这部电影。从那天开始,卡维·法纳姆和我成了最好的朋友和工作伙伴。在2017年的戛纳电影节上,我们凭借《谎言》赢得了“一种关注”大奖。2020年的柏林电影节,我们的《无邪》(There Is No Evil,2020)又赢得了(最高奖项)金熊奖。
此外,我们还共同监制了八部纪录片和三部故事片,都是由伊朗年轻的、有才华的独立导演拍摄的。这些富有成效的合作,是在戛纳电影节上一次偶然相遇的结果。
阿斯弗·卡帕迪尔 (Asif Kapadia)
他有两部电影曾经在戛纳电影节上展映过,其中包括2015年一部关于艾米·怀恩豪斯(Amy Winehouse)的纪录片
如果你运气好的话,你会拥有一个黄金时刻。对我来说,那就是《艾米》(Amy,2015)。戛纳电影节的放映是我们这段奇妙旅程的开始。要有一大群人,还有放映厅里的那种情绪。那是一次很晚的放映,大概在凌晨三点左右才结束,从黑暗中走出来,在街上游荡,然后看到那些评论都是非常正面的。你会想,哦,也许我们在这里收获了一些东西,但你又不太确定。
对我来说,这个阶段比之后到来的颁奖阶段更令人兴奋不已。那会成为一件苦差事。这是关于电影的,这是关于观众们围着街区求票入场的场景。你所面对的是一个真正热爱电影和文化、并把它当做高雅艺术来对待的国家。如果你热爱电影,那为何不能参与体验并与他人分享呢?而且如果你足够幸运的话,你自己的作品将会出现在此地。

阿诺·戴普勒尚 (Arnaud Desplechin)
他有六部电影入围了主竞赛单元,其中包括2008年的《属于我们的圣诞节》(A Christmas Tale,2008)
即使我是戛纳电影节的常客,但让我开口谈论戛纳却还是如此困难。我们知道,电影正在经历观众在观影方式上的大变革。我们也都知道蒂耶里·福茂(Thierry Frémaux)的立场,当威尼斯接受了精彩绝妙的《罗马》(Roma,2018)时,他拒绝了奈飞(Netflix)制作的电影。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正处于电影世界的危机之中,而这次的病毒将迫使我们去梳理所有这些问题。
这次危及迫使我们重新创造新的形态、新的联合和新的模式。我们不能再继续去想:好吧,我们再坚持一年,再多一年。不,这太荒谬了。不让《罗马》入围戛纳太荒谬了,因为它是当年最好的电影。它是属于戛纳的,你知道吗?
罗伯特·艾格斯 (Robert Eggers)
他的第二部长片《灯塔》(The Lighthouse,2019)年入围了当年的“导演双周”单元
整个经历对我来说太疯狂了,因为满场的能量和激情。显然我并不知道戛纳会给我带来什么,罗伯特·帕丁森(Robert Pattinson)和威廉·达福(Willem Dafoe)他们来过很多次了,他们给我讲了很多事情。就在我们放映之前罗伯特告诉我在戛纳电影节被人喝倒彩的感觉。我当时真的挺担心的。在了解到人们不仅接受了这部电影,并且还能理解我和我哥哥的意图,那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然后我知道还有那么多影痴希望能看到这部电影,我想说的是,那真是一次令人难以忘怀的体验。
克莱尔·德尼 (Claire Denis)
她有很多电影参与了电影节,其中包括她的处女作《巧克力》(Chocolat,1988)
在这场疫情发生之前,不管我去不去戛纳,它对我来说都代表着春日里的一阵温暖。即使我不去,我也会知道所有主竞赛单元的电影名单,我会紧跟着媒体报道,阅读所有的文章。每年的五月,我都是在戛纳的陪伴中度过的。
|此文的联合作者A.O. Scott是《纽约时报》联合首席影评人|翻译:佚名@迷影翻译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