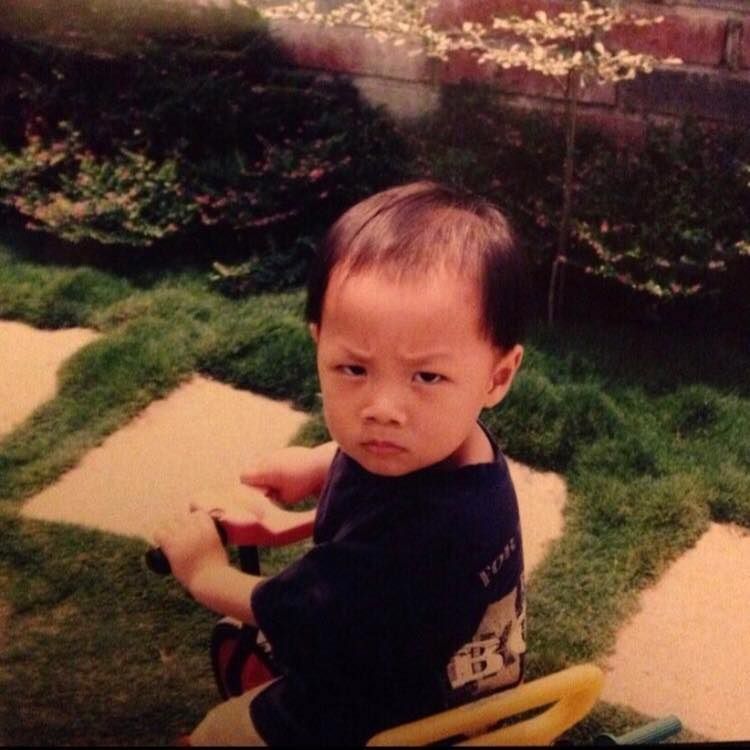未定題EP01
「呼,呼,呼,呼,呼呼,呼,呼…」
「趴噠,趴噠,趴噠,趴噠…」
這是這個人慢跑的第九十個夜晚,除了一片空曠的草原,甚麼都沒有。昨天越過了一片森林,難以想像的潮濕與各種各樣的小動物,還有從葉片上滑落的水滴。存活雖然直覺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不過在奔跑的過程中看到的每一隻青蛙與猴子也都在掠食者的地盤中活著。他不斷地越過粗大的樹根、淺淺的沼澤、不知道底下是否有蛇藏身的落葉堆以及巧妙避開的捕獸陷阱,直直地向前跑,反正有一天會到達出口。誰知道確實出來了,卻來到下一個沒有盡頭的地方,而且完全相反,最多就是看得見反映星光的露水,還有遠方的尚未禿光的樹,如果幾個小時後會有夕陽,就是我們常常在電影裡面非洲場景的那個樣子。誰會想過有一天會經歷在銀河下慢跑的場景? 花錢旅遊順便跑一下沒什麼問題,但是這個人已經跑了九十天。
九十天前,他買的跑鞋與衣物正好到貨,是一整套要出門慢跑的裝備,這可是存了大半年有能力下單的東西啊。最新款的灰色的防風薄外套,穿上去極其舒適的短褲,厚厚的運動襪,抱著近關情怯的心情開箱完之後,感受到原來廣告說的透氣與彷彿不存在都是真的,便穿著他們煮起晚餐,吃飯,整理房間,準備隔天的會議資料,睡著。睡前還想著,鬧鐘響起的時候,就是刷牙洗臉出門慢跑,享受一天開始的時候。
但是他怎麼都睡不好。明明是一個寧靜的夜晚,也明明工作順利,家人平安,諸事大吉,天下太平,就翻來覆去,輾轉難眠。嘗試過看一些廢片,看過A片,或者下床做一些伏地挺身或是核心肌群的訓練,吃了消夜,躺回床上的時候,仍然被大腦強迫醒著。這使的他有一點生氣,老闆幹人不腿軟的,客戶機巴不嘴慢的,作為一個普通的年輕人,他知道這就是還沒出社會時大多數人告誡他的與自己經歷到的真實的就是這個樣子且必須接受的樣子,仍在決心接受的時候沒有那種應該要有的順遂。睡不飽,脾氣會差,脾氣越差,被老闆跟客戶幹的時候就越不爽,越不爽,這種循環就會持續的越長,況且決心運動的心情還有一點,想要感受到小時候大汗淋漓的那種踏實滿足,好幫助自己面對明天,結果你有一顆該死的睡不著的大腦,死都不願意發揮作用的副交感神經。這時候,他感覺到有點生氣,就連生活中最簡單的事情—睡覺—他都沒有辦法好好的掌控,或者不順他的意,又不是想要做個生命的控制狂人,就只是睡個覺而已,這要求到底有甚麼高的。但又能怎麼樣呢,對阿,最幹的就是但又能怎麼樣呢,如果今天真的要背炸彈去炸總統府,你可以就這麼去做,但是我們無法抵抗會來的感冒,會湧現的情緒,還有清醒。
「叩,叩。」
突然他聽見木頭地板的某處發出了一些敲打聲。但是望向四周,沒有任何活物。連隻壁虎都沒有,更不要說是其他小動物,或者樓下的房客,這裡是一間平凡的公寓,樓下除了這個時間熟睡的家庭和可能在和伴侶聊天的死大學生,沒有甚麼特別的人。凌晨四點半,為甚麼會有木頭地板被敲打的聲音?還是我聽錯了?可是那樣子因為受潮有點悶悶的聲音,他認得是自己房間床腳下的那一塊木頭,還是是縫隙之間的老鼠?不過老鼠應該不想要有人發現他們在下面亂竄吧?但他非常害怕老鼠,害怕到不想要有任何一絲可能老鼠從某個縫隙而進到家門,跑到他的房間,或者呼朋引伴鑽進去他的棉被。
於是他翻開棉被,再確認一次這間房子裡除了自己,沒有任何別的活物。確定了,拿出文具盒裡面的三十公分直尺,握著往木頭地板敲了敲。但是聲音有點變化,跟原本那種濕濕悶悶的聲音不一樣,這讓他在聽到另外一種叩叩兩聲的時候愣住了,而後搖了搖頭,也許只是不留意,接著再敲了幾下。這時聲音又變得,變得清脆響亮,好似手中的那把塑膠直尺是塊精練的鋼鐵,敲在赤色檜木所製的大門上一樣。其實…滿好聽的,比起老闆的聲音,但永遠不比現在突然冒出腦海的AV女優的嬌嗔。這次更用力點的敲了敲,結果不小心敲出了個隙縫來,瞬間打了個哆嗦,幹你媽的要花錢換一塊新的給房東了,就是一個囉嗦又自以為是的中年男子,一毛錢都不想花在他身上,但是不得不了,沒有那種回到過去如此便宜的事情。被一雙眼神注視的裂縫,其上與其下仍然是沒有動靜,只是這個人緩緩意識到自己的喘息。手上的三十公分直尺倏忽變得沉重,失去塑膠在窗外路燈照射下反射的光澤,轉為一根沒有顏色,沒有反光,沒有刻度的棒狀物,接著他的形狀變了,變得像一隻刀柄,沒有刀刃,只有握起來是麻繩感的不明物體。這個人看著右手,除了驚嚇,還想起一些歷史題材的影集。不如發了瘋似的把那一塊受潮木頭打個破爛,反正,壞了就壞了,幹你娘死房東。
「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
就算上面有馬英九的臉,也無法驅使他更用力。像是一個勇士,在自己家門外瞥見自己的妻子與一個懦夫私通,然而房門卻被鎖上,邊聽見妻子放浪的叫聲,邊拿著正從戰場上凱旋歸來的那把劍的劍柄,憤恨且瘋狂的意圖破壞改死的木門一般,那樣子的對待這一根這個人的稻草。
「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
「幹!」
這下好了,壞的不只是一塊木頭,而是一大片木頭。他看見木屑揚起,還有折裂的聲音。但是自己住了幾年的公寓的地板下,卻是他從未知道的一片漆黑,這太違反直覺了。他把手上的直尺拋下,遲遲沒有聽見塑膠與地板撞擊的回應,這嚇傻了他,未回過神來,脖子後方突然有一隻手將他壓制在地上,臉頰直碰地板,四肢動彈不得。
「三…小…?」
「…」
將他壓制在地的人沒有說話,膝蓋跪在他的背上,活像個在摔角場上徹底失敗的那一方,差別是輸家有錢領,而這個人到現在還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你可能會問,他為甚麼不掙扎,這沒有人知道,可能也因為這也許就只是一場夢,但是沒有刀子,沒有繩子,沒有任何作案動機,也沒有藥品,沒有槍砲,甚至身上的衣物一件都沒有被拖掉,到底還有甚麼樣的可能,讓某一個人要在這個時間,這個地點,把這個人壓制在地上。觸地的雙膝與右邊的臉頰又麻又痛,被掐住的脖子也造成了呼吸困難,只是這些疼痛是這一夜唯一讓這個人還感受到自己在這的證據。
「是誰…?」
「我啊。」
「幹你娘垃圾,說人話。」
「…我,我…。」
不明人士嘆了長長的一口氣。
在說出根本認不出你是誰之前,他就被一手抓住雙腳腳踝,呈現一個倒吊人的狀態,被一大腳踹進那個深不見底的坑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