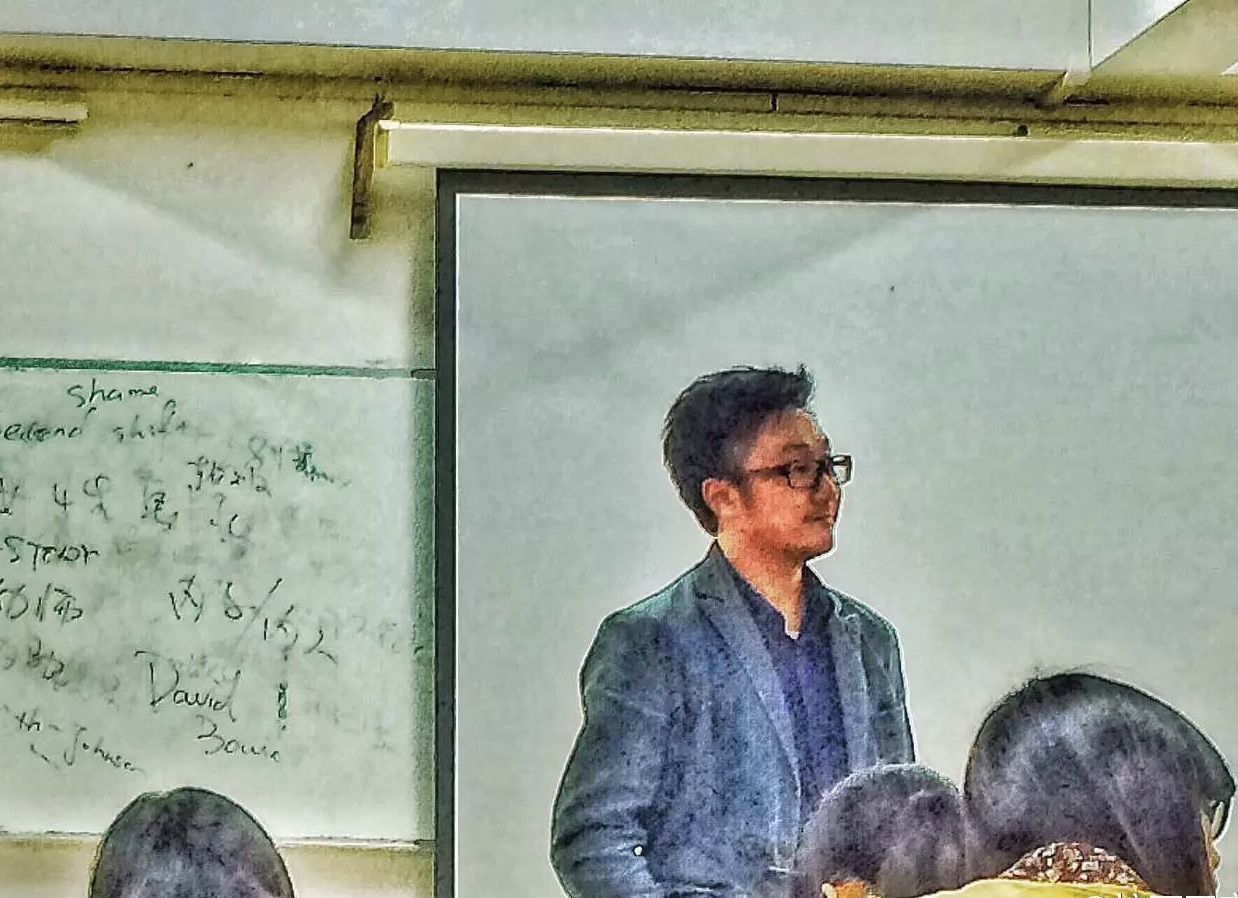哲學家新著:特朗普是法西斯主義者?
本文以《特朗普政府,法西斯?》首发于新京报书评周刊
在當今英美哲學界,傑森·史丹利(Jason Stanley)可算是名氣最高的哲學家之一。在2013年成為耶魯大學哲學系教授之前,史丹利曾先後任教於康奈爾大學、密西根大學以及羅格斯大學。史丹利在哲學中的工作主要集中在語言哲學與知識論。尤其在對知識構成和知識定義方面,史丹利對現在語境主義知識論和能力知識(knowing-how)理論貢獻非常大。他在這方面的學術專著《知識與實踐利益》(Knowledge and Practical Interest)還榮獲2007年美國哲學協會(American Philosophy Association)年度圖書獎。

除了在知識論上的學術貢獻以外,史丹利還是一位活躍的作家,在不同的媒體發表面向大眾讀者的深度評論文章。根據史丹利訪問時的說法,由於他父母都是因為三十年代反猶而逃離游走的猶太難民,同時他父親是一位社會學教授,在這樣的家庭熏陶下,史丹利對自己生活環境中的政治結構頗為敏感。正因如此,史丹利對政治哲學的現實問題頗為關注,也是他現在寫作的重點之一。以一系列評論文章為基礎,史丹利在2015年出版了著作《政治宣傳的運作》(How Propaganda Wor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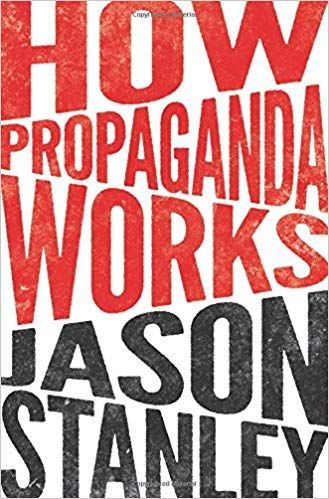
現在,面對當今美國政治中出現的各種怪現象,特別是讓人撲朔迷離的特朗普政府,史丹利新近出版了著作《法西斯的運作》(How Fascism Works),詳細分析了歷史上法西斯運作的特點,並且比較了特朗普政府是如何越來越接近法西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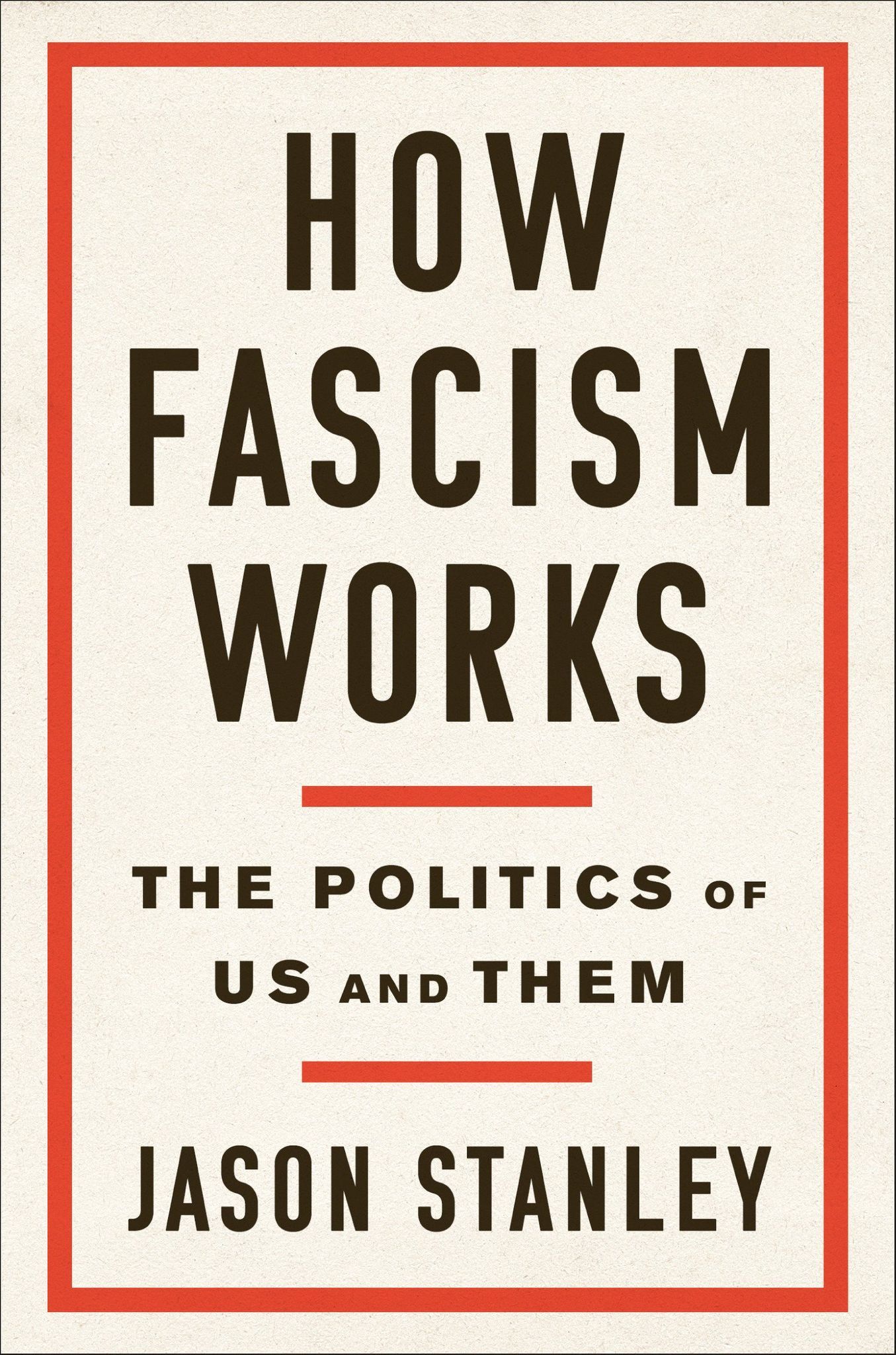
法西斯:歷史與當下的相似
在史丹利看來,特朗普政府與法西斯的運作頗為相似,原因正是特朗普政府似乎有意無意地運用著歷史上法西斯的各種特別手段,去實現它的政治目標。法西斯不僅僅只是納粹德國的反猶主義,法西斯政治的運作有著各種特殊的方式和內容。如果仔細分析,我們會發現歷史和當下之間存在著驚人的相似。
神話般的過去
當特朗普打出「讓美國重回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口號,我們不禁會問,需要「重回」的美國偉大到底指的是什麼時期的美國?在特朗普勝選以後,時任特朗普首席顧問的班農(Steve Bannon)接受採訪時表示,他期待即將到來的時代會像1930年代般令人興奮。那是美國快速蓬勃發展的時期,然而也是非裔美國人遭受吉姆·克勞法剝奪各種權利的時期,也是美國貧富懸殊的時期,更是美國本土納粹思想發展的時期。
在史丹利看來,特朗普團隊設想一個美好偉大的美國過去的方式,正是法西斯核心的運作方式之一。通過建構一個神話般的過去,再建構一個美好過往被摧毀的歷史,法西斯為自己「重建」這個純潔國家的事業提供了辯護。希特勒的納粹說要重建阿利安民族的輝煌,穆索里尼稱「我們的生活就是國家的偉大」。這些神話般的過去都是粉紅色的,因為法西斯知道如何挑選著歷史中可以喚起人們懷舊情感的故事,挑選那些能夠喚起人們熱愛這個「偉大」國家的榮耀的故事。對法西斯而言,關於過去的神話重要的不是歷史的真實,而是這個神話的一致連續:同一套語言、同一個宗教、同一片國土、同一個民族……是否真實對於法西斯政治而言並不重要,正如穆索里尼所言,「我們創造我們神話。這個神話是一種信仰,一種激情。它並非必要是事實本身。」
有了這樣神話般的國家/民族歷史,法西斯領袖們就擁有政治上的正當性:一切的行動就是要讓國家民族回到這一輝煌的過去。希特勒、希姆萊等等都精湛掌握這一技巧,在史丹利看來,也「啓發」到此後的各種類似法西斯的政治活動。所以當特朗普團隊和政府打出「讓美國重回偉大」的口號時,人們很難不想起這樣一種構建神話般過去的策略。當人們反對本來遠在內戰之後樹立的南方州邦聯紀念雕像時,美國極右翼以及特朗普希望通過所謂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來反駁,使用的正是援引並不存在的所謂純粹過往。土耳其刑法中的301條規定「侮辱土耳其、土耳其民族、土耳其政府」違法。史丹利認為,這明顯也是法西斯運作方式的再現。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爾汗·帕穆克(Orhan Pamuk)因提及一戰時土耳其對阿美尼亞人的大屠殺而遭到起訴,引用的正是301條侮辱土耳其。所以當職業美式足球運動員在升國旗時單膝跪地表示抗議時,美國總統特朗普帶頭攻擊這些運動員「不美國」("un-American"),很難怪人們感到恐懼。

敵人在破壞:「我們」與「他們」的政治
既然要回到神話般美好的過去,那說明我們的國家/民族曾經遭到了衰退,遭到了破壞。在納粹看來,偉大的日耳曼的衰落,正是猶太人他們帶來的。史丹利認為,法西斯政治核心的觀念之一,就是要嚴格區分「我們」與「他們」,「我們」是純潔的,英雄的,善良的,「他們」是邪惡的,陰暗的敵人。《法西斯的運作》的副標題正是「‘我們’與‘他們’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Us and Them")。法西斯的政治宣傳裡面充斥著「我們」與「他們」對抗的字眼。允許他族的融入代表了「我們」的消亡,可以說是法西斯意識形態的內核,所以納粹需要保證阿利安民族的所謂純潔。法西斯的政治和各種實際政策可以說便是圍繞這樣的內核展開。
在政治宣傳中,作為敵人的「他們」有著各種要破壞「我們」的陰謀。陰謀論歷史悠久,但是法西斯將陰謀論發揮到極致。通過默許、生產、傳播各種陰謀論,法西斯用「恐懼和憤怒來替代說理的辯論」。《錫安長老會紀要》(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可以算是二十世紀最著名的陰謀論了。據傳,《紀要》是猶太人陰謀統治世界的行動手冊。猶太人根據《紀要》中的指南,「控制各國的主流媒體和全球經濟系統,通過它們來傳播民主、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實際上都是擴展猶太人利益的工具。
偽造一個猶太人統治全球的陰謀論,陰謀論者的目的正是要調動大眾對猶太人的恐懼和憎恨,同時也產生一個責怪的對象:一切不幸都是猶太人的陰謀說造成的。希特勒、戈培爾等等納粹領袖都堅信這一陰謀論,將德國的問題歸結到猶太人身上,聲稱猶太人控制的報紙掩蓋著背後的真相。
陰謀論也是用來攻擊媒體和反對者的重要工具。陰謀論者,特別是擁有權力的陰謀論者,常常用他們傳播的陰謀論本身來批評媒體掩蓋事實:如果主流媒體不報道這些陰謀論,那麼媒體是自帶偏見的並且是這個陰謀的同謀。但是,如果主流媒體真的報道這些陰謀論,結果就是各種天馬行空的胡扯就會污染整個公共討論,使得人們無法理性地探討真相。任何的合理討論都必須預設一些基本的共識,包括基本的討論規則,只有這樣,所謂「觀念的市場」才能正常運作。比如奧巴馬醫改是不是好的政策,這是可以理性辯論的。然而,如果一方相信奧巴馬其實是穆斯林臥底,旨在暗中顛覆美國,另一方不相信,理性辯論奧巴馬醫改便無法進行了。
特朗普正是通過傳播「出生地陰謀」而進入主流政治圈。特朗普不斷攻擊主流媒體拒絕報道奧巴馬出生在肯尼亞而非美國的「事實」。主流媒體如CNN是奧巴馬的手下,所以幫助奧巴馬掩蓋他沒資格擔任美國總統的事實。即使夏威夷州公開了奧巴馬的出生證明,特朗普以及其他出生地陰謀論者仍然堅持,這些出生證明是偽造的。特朗普還宣稱9/11事件發生時上千名穆斯林在樓頂慶祝。競選期間,特朗普仍然不斷傳播各種陰謀論,包括宣稱德州參議員克魯茲(Ted Cruz)的父親參與了刺殺肯尼迪,希拉里的郵件門,奧巴馬監聽他的辦公室。擔任總統期間,特朗普毫無證據的宣稱大選存在數以百萬計的非法投票,所以他才在普選票上輸給希拉里。
通過傳播陰謀論,法西斯可以「引起公眾的不信任和恐慌,證成極端手段。因為猶太人的陰謀,他們是我們國家和民族的敵人,所以將他們監禁是應該的。因為媒體都是自由派的口舌,自由派希望摧毀我們的生活方式,所以我們不應該相信他們的報道,我才是真正的贏家,相信我即可。法西斯政治因此破壞了公眾追求真相的公共空間,強有力的領袖代表「我們」,成為權威信息的來源。同時他們也可以施行極端政策。「墨西哥來的都是強姦犯」,於是我們修建邊境牆,通過「法律與秩序」(law and order)來抓捕非法移民,甚至將移民兒童與其父母分開監禁等等。
史丹利全書分析了法西斯運作的各個方面,對比當今的美國政治,我們似乎可以看到令人不安的相似。歷史上的法西斯政權的各種統治方式,都或多或少地重現在當今的時代。如果史丹利的分析是正確的話,特朗普政府與法西斯的相似度便頗為讓人擔憂了。
單薄的論證:手段就等於法西斯嗎?
儘管史丹利的分析面面俱到,但是要真正證明法西斯正在當今美國重現,他的論證似乎多少有點單薄,並且對「法西斯」這個概念的運用過分鬆散了。
當下美國政治中,極右翼常常攻擊美國的大學已經不在尊重言論自由,已經淪為自由派的領地。在充斥著性別研究、女權主義等學科的大學校園已經被政治正確控制,學校禁止右翼人士的言論。史丹利嘗試論證,美國極右翼的說法與法西斯如出一致,都通過攻擊大學教育來進行反智教育。但是,史丹利的策略是論證現代大學才是真正言論自由之地,但他的論證確實展示出了大學以外的其他場所,比如職場,往往被設置各種合法的言論限制,如要求員工簽署保密協議,合法以在社交媒體發表政治言論為由解僱員工等等。大學沒有這些限制,所以大學擁有真正的言論自由。但是這樣的對比論證說服力有限。大學受到的言論限制少於私人工作場所,這並不能證明大學擁有真正的言論自由,或許大學只是比私人工作場所擁有較好的言論空間。
同時,史丹利的論證也只是避重就輕,沒有正面回應極右翼的挑戰。在當下,大學校園如何處理這些極右翼的言論是十分棘手的難題,僅僅強調大學擁有「真正的」言論自由並不足夠。
史丹利的其他論證還展示了他對「法西斯」運用得非常鬆散。為了展示特朗普政府和美國極右翼就是法西斯,史丹利的做法便是展示特朗普政府和極右翼使用了法西斯曾經使用過的各種策略和方法。儘管能夠喚起我們對當下政治的警惕,這似乎並不能夠證明特朗普就是法西斯,除非我們相信,凡是使用了法西斯曾用過的策略的都是法西斯。當這並不是很好的論證前提。
城市因為雜亂,因而是罪惡之源;農村因為單一所以純潔美好。這是很流行的想法。史丹利在書中將這一想法歸為法西斯意識形態的核心之一。史丹利寫到,「希特勒對大都會城市以及城市文化產品的斥責,是法西斯政治中的標準。」城市之所以受到納粹的批評,主要因為城市在法西斯想象中是被猶太人和移民弄得混雜,而農村仍然保持純潔。特朗普常常採用強硬的反移民措辭,以及不斷錯誤地強調美國城市的犯罪率,也展示了相似的想法。然而,這樣的想法很難說是法西斯所獨有,而且更難認定,持有這些想法的便是法西斯。甚至,反對移民並且愛好鄉間生活的人,很難就說他因此就是法西斯主義者。史丹利的論證在這裡似乎錯誤攻擊了。
另外,史丹利書中核心要展示法西斯政治是一種「我們」與「他們」相對的政治。這一點可能會受到更多的爭議。的確,歷史上的法西斯政權很熱衷使用「我們」與「他們」敵對的語言,當這似乎並不能從學理上證明法西斯政治等同於「我們」與「他們」相對的政治。在一個運作良好的民主社會,「我們」與「他們」的分野常常是政治運作的一部分,比如不同的黨派辯論,爭取選票。民權運動、身份政治、女權運動等等,同樣會運用不同群體的「我們」概念來爭取團結。這些「我們」與「他們」的對抗,似乎並不會導致法西斯式的政治模式,甚至更能讓處於優勢的既得利益者發現其結構性的優勢,加入到運動之中。不少左翼的理論家還希望發展一套「我們」對「他們」的政治理論,例如著名政治哲學家尚塔爾·墨菲(Chantal Mouffe)便嘗試建立這樣的理論。她認為,當代的政治理論錯誤地認為「我們」對「他們」是民主需要克服的。而事實上,「我們」對「他們」是民主政治的核心,只要避免變成敵對的模式。「我們」對「他們」的競爭模式才是真正左翼政治已經追求的政治形態。墨菲的左翼理論恐怕很難被認定為法西斯政治。

所以,史丹利對法西斯政治核心的判斷,似乎是有問題的。法西斯運作的方式,大概有很多種不同的策略和手段。史丹利書中的分析向我們展示了法西斯的大面貌。可是,這並不能夠證明,其中的每一種方式都足以充分定義法西斯本身。法西斯政治是多面的,或者這些面向的如此組合,才會出現法西斯。
認真對待歷史,認真對待當下
縱觀全書,史丹利對當代政治的判斷或許並非完全正確,但他的工作意義重大。正如他所呼籲的,我們不應過分相信「正常」或者「常態」。歷史教訓我們,危機常常發生在人們越來越接受正常化各種不正常的事態,將這些事情看作常態。或許特朗普並非法西斯,但史丹利將歷史與當下進行對照,讓我們產生對不正常的警惕。當流行話語變成「我們是好的,他們是壞的」,「我們的輝煌傳統就是被他們外來移民所破壞」,「他們都是懶惰的動物,不值得享受我們生產出來的社會福利」,「弱肉強食,沒有所謂的正義,我們強大了才有正義」,我們可能就需要注意,認真對待歷史,也認真對待當下。可能全面的法西斯已經消失不可能再出現,但是法西斯的各個方面仍然可能零星地重現。警惕,可能便是我們需要做的,甚至是我們的公民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