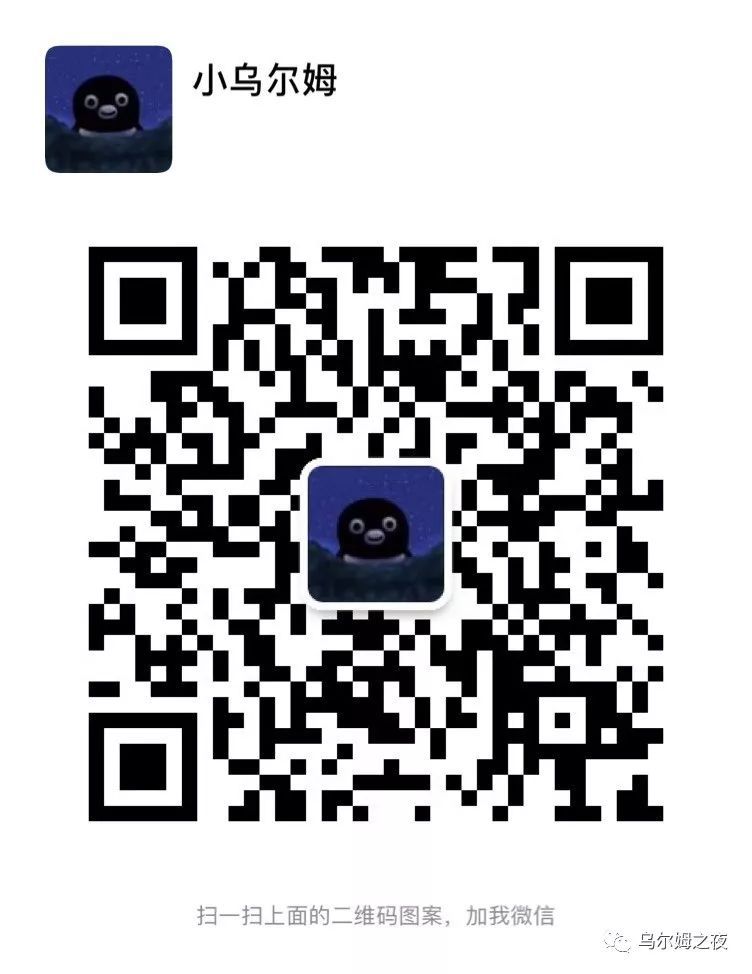韩炳哲 : 我们不应将理性让渡给病毒 | 乌尔姆×疫病时期的哲学
文章译自2020年3月23日的德国世界报,原文标题„Wir dürfen die Vernunft nicht dem Virus überlassen“

我们不应将理性让渡给病毒
译者:数码太阳、yilin、Earthbound
校对:贝码、符号周、🦆
排版:Citron
文章来源:
新冠状病毒是一个制度测试,亚洲明显比欧洲对这次疫情掌控得更好。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感染病例都很少,台湾被记录的感染人数总共只有108例,香港则是193例。与之相反,德国在相当短的时间里(截止3月19日)就有了14481病例!在此期间韩国已经摆脱难关,日本同样如此,而且中国作为发源国,也进一步地将疫情控制住了。
台湾和韩国都没有采取禁止外出或是关闭商店和餐馆的措施,与此同时亚洲人的出欧洲记正在上演。中国人和韩国人想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因为他们感觉回去会更安全。机票翻了几番,此时已经几乎无法再买到飞往中国或韩国的机票。
欧洲则误入歧途,感染人数指数级增长,他们似乎没能控制住疫情。在意大利每天都有上百人死亡,年长病人的人工呼吸器则会被拿走,以救治更年轻的患者。某种空洞的行动主义也值得注意。现在看来,关闭边境明显是主权本身的绝望表达。我们感觉自己回到了主权时代。主权者,就是决断例外状态。谁关闭边境,谁就是主权者。
这不过是主权的空洞展示,它无法带来任何效果。欧洲内部的紧密协作可能比盲目关闭边境奏效得多。欧盟同时还禁止了外国人入境。考虑到现在没人会想来欧洲的事实,这完全是一个无意义的举措。禁止欧洲人出境以保护其他国家,总体上要更有意义。欧洲现在正是流行病的热点地区。
对政府的信任
相对于欧洲,亚洲在这次面对流行病的战斗中证实了何种体制优势?像是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台湾,或者新加坡这些亚洲政府(Staat),从文化上就已决定了是威权性质的(儒家学说)。而且这些国家的人,也比欧洲人更顺从听话,他们更加信任政府。不只在中国,甚至是在韩国和日本,日常生活实际上也组织得更严格。亚洲人这次主要大量依靠电子监控来应对病毒。他们推测,大数据对控制疫情有巨大潜力。
可以说,在亚洲对疫情作战的不只是病毒学家和流行病学家,首当其冲的还有程序员以及大数据专家。但范式转移还没有在欧洲引起重视。辩护者将为数据监控大声疾呼,他们声称大数据拯救人类生命。
在亚洲几乎不存在对数据监控的批判意识,即使在韩国和日本这样的自由国家,人们也几乎不谈论信息保护,没有人反抗当局疯狂的数据收集。中国政府此刻推行了一个欧洲人难以想象的社会信用体系,它允许对公民进行全方面的评价和打分。
每个公民的社会行为都会被持续评分。在中国,人们无时无刻不被监控,每一次点击、购物、联络,社交网络的每一个活动,都被严密控制着。那些闯了红灯,与批判政权者往来,或是在社交网络上发布了批判性言论的人都会被扣分。生活因此会非常危险。
不受限制的信息交换
与之相反,在网络上购买了健康的食物或阅读党政报纸的人则会加分。得到了足够的加分,就可以拿到旅行签证和更优惠的信用。但谁如果分数低到一定程度,就可能会丢掉工作。这样的社会监控在中国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手机和网络运营商与当局之间的信息交换不受限制。那里实际上不存在信息保护,中国人的词典里没有“隐私”这个词。
在中国有2亿台监控摄像头,其中部分采用了高效的人脸识别技术,它们甚至能够识别人脸上的色斑。不可能逃脱监控摄像头的监视,无论是在商店、街道上、火车站还是机场,搭配了人工智能的摄像头可以时刻监视在公共场所里的每一个公民,并对他们进行实时评分。
用于数字监控的整个基础设施,现在则表现为对疫情的高效抑制。
当一个人从北京火车站出来,他将会自动被一个摄像头捕捉并测量体温。若是有人体温超出正常值,将会通过智能手机自动通知给同车厢里所有人。是的,这个系统知道,谁坐在车厢的什么位置。
在社交媒体上甚至有关于用无人机监控隔离区的报道。当有人偷偷离开他的隔离区,会有一架无人机飞来,命令他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无人机或许还能打印出罚单并让它飘到这个人手边,谁晓得呢。一个对于欧洲人来说是反乌托邦的情形(dystopischer Zustand),在中国却显然未遭到任何反对。
不只是在中国,在其它的亚洲政府(Staat),像是韩国、香港、台湾、新加坡和日本,也没有任何反抗数据监控或大数据的意识,他们正陶醉在数字化中。这里还有一个文化上的原因,在亚洲集体主义是占主导位置的,并不存在鲜明的个人主义。当然在亚洲流行开来的利己主义跟个人主义还是有区别的。
大数据对抑制病毒起到的作用,显然比欧洲现在无意义的关闭边境来得高效,但欧洲出于对信息的保护不可能采用同样的方式对抗病毒。中国的手机和网络运营商会把客户的敏感信息透露给安全局和卫生部门。
数字调查小组
政府很清楚地知道,我在哪儿,见了谁,在找什么,想什么,吃了什么,买了什么,要去哪儿。未来大概率人的体温、体重、血糖等也将被政府管控。数字化的生命政治(Biopolitik)以及数字化的精神政治(Psychopolitik)严密地掌控人们。
在武汉组建了数千个数字调查小组,他们仅凭数字技术就可以追踪到潜在感染者。他们仅靠大数据分析就可以找出谁是潜在的感染者,谁必须被观察,谁又必须被隔离。也因为流行病的缘故,未来都将在数字化的掌控中。鉴于这次流行病我们或许甚至应该重新定义主权。主权者就是掌握信息者。当欧洲宣告例外状态或者关闭边境时,他们还停留在过时的主权模式中。
除了中国以外,其它的亚洲国家也使用数字监控技术来对抗这次流行病。台湾政府同时向所有的公民发短信,调查接触人群或是告知感染者曾去过或逗留过的地点。台湾很早就开始搭建信息交换的链条,以便根据旅行记录及时调查潜在感染者。
在韩国谁要是靠近一个住有感染者的建筑物,就会从新冠病毒软件Corona-App收到警告,所有感染者停留的过的地点都被收录进这个App上。很少会有人去注意信息保护或是隐私,在韩国的每一栋建筑物的每一层,每一个商店和办公室里都安装了监视摄像头,实际上不可能在公共空间里活动而不被摄像头捕捉。
结合手机上采集的信息和影像材料,可以收集感染者的完整行踪,所有感染者的活动路线都将公之于众,偷偷摸摸的风流韵事也可能被泄露。韩国卫生局有所谓的“跟踪员”,他们日以继夜地浏览影像材料,以还原感染者的完整活动路线并追踪到接触者。
亚洲和欧洲的显著区别主要在于口罩。在韩国实际上没有人不戴可过滤病毒的特殊口罩就在公共空间里四处活动。这里不是指常见的医用口罩,而是指医生在和病人接触时也会戴的特殊过滤口罩。居民的口罩供给是过去几周在韩国最受瞩目的话题。
工作场所的防护口罩
药房前排起了长队。如何有效地为为全体民众提供口罩,成为评价政治家的标准。(全社会)匆忙准备了新的制造口罩的机器,目前供应情况看起来还不错。现在还有了一个新的App用来通知附近哪些药房仍然可以买到口罩。我认为,向亚洲所有人口供应的口罩为遏制这一流行病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韩国人甚至在工作时都戴着防病毒口罩。政治家们也只会在佩戴口罩的前提下外出,韩国总统也亲自作了表率:即使是在新闻发布会上,他都会佩戴口罩。在韩国,一个人若不戴口罩会理所应当地受到指责。反之在德国,人们听到的是口罩没有太大帮助,这是胡说八道。那么,医生们究竟为什么要戴口罩呢?
人们需要经常更换口罩,因为当它变得潮湿时就会失去过滤功能。但与此同时,韩国人发明了一种带有纳米过滤器的新冠口罩(Corona-Maske),这种口罩甚至可以水洗。它可以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内保护人们免受病毒感染,如果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药,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但是在德国,就连医生也必须飞往俄罗斯才能获得口罩。马克龙则征用了口罩用以分发给医生,但他们只是得到了没有过滤器的普通口罩。他们被告知,这些普通口罩足以抵挡冠状病毒,这完完全全是谎言。欧洲正在走入歧途:如果人们在高峰时间继续挤地铁或公共汽车,关闭商店和餐馆的用意何在?
文化差异
人们如何彼此保持距离?就连在超市也几乎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然而口罩确实可以挽救生命。两个阶级的社会很可能会出现:谁拥有私家车,谁受感染的风险就小。即使那些被感染的人只是戴上普通口罩也将大有裨益,因为病毒因此不会被传播出去。
德国几乎没有人戴口罩,即使一些个别戴口罩的也都是亚洲人。我在德国的同胞们抱怨说,其他人总认为他们戴着口罩很奇怪。这可能要归结于另一个文化差异。在德国盛行一种个人主义,与之相联系的是这样一种理念:普通人会袒露自己的面容,只有犯罪者才会带面罩。由于那些在韩国的照片,我已经完全习惯了人们戴着口罩的容貌,以至于我的柏林同胞们露出的脸对我来说几乎是一种冒犯。我也想佩戴口罩,但我在这里却一个都搞不到。
正如许多其他产品一样,口罩的生产线也已被转移至中国,欧洲因此得不到口罩。亚洲国家正在努力为全体人民提供口罩。由于口罩的供应变得稀缺,中国改建工厂来生产口罩。而在欧洲甚至连医务人员都拿不到口罩。
逻辑上讲,只要人们继续不戴口罩乘坐公交和地铁上去上班,限制出行就不会奏效。人们又怎能在高峰期的公交地铁上彼此保持距离?从该流行病得到的一个教训应该是,将防护口罩、医疗产品和医药等诸如此类产品的生产线重新转回欧洲。
恐慌的原因是什么?
虽然对一切风险都不应掉以轻心,但人们对新冠病毒的恐慌却仍是过度的。连致死率更高的西班牙流感也没有对经济造成如此破坏性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全世界对病毒有如此恐慌的反应?
马克龙甚至谈到了战争和我们必须击败的无形敌人,我们在面对敌人的卷土重来吗?西班牙流感在一战中爆发,那时每个人都处在敌人包围中,但没有人会将这种流行病与战争或敌人联系起来。可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
我们实际上已在没有敌人的情况下生活了很长时间,冷战早已结束。伊斯兰恐怖主义也已退入那遥不可及的过去。就在十年前,我在《倦怠社会》这一篇文章指出,我认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建立在否定敌人基础之上的免疫模式失去了作用。
根据免疫学要求塑造的社会,其特征为边界和围栏,就像在冷战时那样。但边界和围栏亦阻碍了商品和资本的加速流通,全球化拆除了这些免疫界限,以便为资本铺平道路。而如今的随意性文化以及对生活各方面问题的宽容态度,也消除了原先对陌生人或敌人的否定性理念。
无边界的消极社会
在今天,危险并非来自敌人的消极否定,而是来自过度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体现在超负荷的运转,过度的生产与过度的沟通。敌人的消极否定不属于我们这个无边界的消极社会。他人的压迫让位于抑郁——一种源于自愿的自我剥削及自我优化的外部剥削。在一个讲求效益的社会里,人首先得同自己作战。
现在,病毒恰好击溃了这个已经被资本主义全球化极大地削弱了免疫能力的社会。人们会惊恐万分地重新抬高免疫门槛,收紧边境。敌人又回来了。我们与之为敌的不再是我们自己,而是那个外来的不可见的敌人。病毒导致的过度恐慌是一种社会乃至全球对这个新敌人的免疫反应。正因为我们已经在一个没有敌人的积极社会里生活了太久,这一免疫反应才如此剧烈。眼下,人们正把病毒当成一种永恒的恐惧。
导致这场大规模恐慌的原因还有一个,这个原因与数字化有关。数字化正在消解现实。人们通过对抗来体验现实,这种对抗会带来疼痛。数字化整体上是一种“取悦我”的文化,它消解了对抗的否定性。在一个充斥着假新闻和人体合成图像的后真相时代里,对现实的漠不关心应运而生。在这里,真真切切的病毒而非计算机病毒引发了震惊。现实和对抗以敌对的病毒的形式宣告了自己的回归。对病毒剧烈而过度的恐慌反应源于对现实的震惊。
对病毒充满恐慌的忧虑首先反映了我们的续命社会(Gesellschaft des Überlebens),在这个社会中,生命的全部力量都被用于延长生命。对美好生活的关注让位于续命者们的歇斯底里。续命社会抗拒享乐,在这里,最重要的是健康。关于禁烟的歇斯底里最终会变成关于存活的歇斯底里。
我们愿意牺牲一切
我们对病毒的恐慌暴露了我们社会的存在基础。病毒让死亡重新进入我们的视线,而我们曾一度相信,死亡已经被驱逐到了看不见的地方。面对迫在眉睫的死亡危险,我们愿意牺牲一切使生活尚有价值的东西。甚至在冠状病毒大流行之前,我们就已经为存活而奋战了。
眼下爆发的对病毒的战争正是病毒的延续。续命社会正显示出非人性的特征。他人首先是潜在的病毒携带者,会威胁我的生命,因此必须与之保持距离。为存活而战与对美好生活的期许截然对立。否则,在流行病过后,生活就会变成一种存活。然后,我们自己就会变得像病毒一样,成为一种只会繁殖和生存,却不会生活的亡灵。
金融市场对这场流行病的恐慌也是对某种自身固有的恐慌的反映。全球经济的极端动荡让它们十分脆弱。中央银行近年来执行的高风险货币政策使得股票指数逐步上升,但也孕育了某种被压制的蓄势待发的恐慌。
也许病毒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金融市场的恐慌表达的不是对病毒的恐惧,而是对自身的恐惧。即使没有病毒,崩溃也会到来,或许病毒只是另一场更大崩溃的先兆。
病毒不能取代理性
齐泽克声称,病毒给了资本主义致命一击,并召唤了某种朦胧的共产主义。他相信病毒会让中国政权崩溃。他搞错了,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中国将会输出它那套数字化监控的国家体制作为抗击流行病的成功典范,中国将更加自豪地展示它那套体系的优越性。
流行病结束后,资本主义将更加气势汹汹地前进。游客们将继续践踏地球,至死方休。病毒不能取代理性。除此之外,身处西方的我们也可能迎来像中国那样充满数字监控的国家体制。
正如Naomi Klein所述,病毒带来的震惊是个好机会,它允许人们建立一种新的治理体系。在引发震惊的危机到来之前,新自由主义会兴起,就像过去在韩国或希腊所发生的那样。在这次病毒冲击过后,欧洲还有望不像中国那样迎来一个数字化监控的体制。然后,正如乔治·阿甘本所担忧的那样,例外状态将演变成常态。伊斯兰恐怖主义没能做到的,这个病毒做到了。
病毒不会打败资本主义。“病毒革命”不会发生,病毒无力促成一场革命。病毒让我们孤立无援,但这并不会引发任何强烈的团结感。每个人都在以某种方式关心他们自己的幸存。这种彼此之间保持距离的“团结”并不是那种可以带来一个更加和平与公正的理想社会的团结。我们不能把革命托付给病毒。让我们期待,一场人道的革命能在病毒之后到来。作为拥有理性的人,我们必须深思熟虑,并且从根本上彻底限制毁灭性的资本主义和我们无边界的、毁灭性的流动,从而拯救我们自己,拯救气候,和我们这颗美丽的星球。
我们的智性生活正遭受着威胁。
空洞的意识形态话语占据了道德高地,
边缘人的存在本身岌岌可危。
风暴的轨迹难以预测,但气压的异常足以让我们紧张起来。
在世界秩序变化的关键时刻,
掩耳盗铃或是隔靴搔痒,将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我们需要严肃鲜活且诚实的讨论,
在漫游途中搭建营帐,守卫议事自由。
乌尔姆之夜是一场偶然的相遇,它没有任何终极目的,
因为任何神话在当下都会即刻变成一场喜剧。
这是一场理论、反思和跨学科的歌命性联动,
意在打碎一切神话的前提下,无限拓展公共言论空间。
这是一场根植于当下、聚集在案厅、活跃于街巷的解放性实践,
其中没有一个成员,也拥有一切成员。
未来讨论,主题开放,不限学科,由参与者共同讨论决定。
活动目前在巴黎,想要参与讨论或加入团队请联系小乌尔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