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體記憶:十四年與每一天 | 金馬達基金公告 NO.45
昨日是五 · 一二四川汶川大地震的十四週年紀念日。似乎在重大事件的時間線裡,「十四年」並不是一個「值得」大張旗鼓說些什麼的時間點,但對於親歷者、對於曾為這場災難付出過不應付出的慘痛代價的人來說,每一天都是災難發生的那一天。
調查記者在垮塌的樓房裡找到建校的監理報告,救援志工在碎尸瓦礫中看見殘缺的桌椅、文具與身軀,父母、孩子、老師、學生,無數顆牽連在一起的心在一瞬間隨著樓房一起傾塌。而我們不僅要用身體抗住搖搖欲墜的豆腐渣工程,還要以這副身軀不斷地紀錄與寫作——正如它們一直連續不斷地、以名詞與動詞的形式交替出現在公共生活裡那樣——十四年後的今天,大家仍難以斷言是否真的存在「多難興邦」,但可以確定的是,我們的身體已有災難的記憶。在一次次的書寫、哀默與慟哭中,無數個行動的身體匯聚出了重要的集體記憶,接住當時一起坍倒的一部分國家,與生於石縫之間的公民世界。
本期金馬達,將為這十四年裡從未停下過的公共紀念做一份整理,告慰亡人。
整理也為那些因行動而失去自由或遭受不公平對待的行動者們,為正在疫情下失去許多東西的人;為所有人的十四年,為每個人的每一天。
突然,我看见一群人摸进垮塌的教学楼里,我的朋友认识当中的一个人,问,老王,你们又去挖钢筋?那个叫老王的中年汉子说,对,据说下礼拜香港的记者要来,我跟其他几个家长商量了下,准备给他们留点证据……我拿起那钢筋看,细细的灰黑色,手使劲都可以扭曲。
轉載於汶川地震九週年時的紀念文。用來存放化學肥料的「老危樓」只裂開了幾條縫,而向每戶家庭收錢蓋好的「新教學樓」則像積木一樣在瞬間塌得粉碎;隨之坍倒的,還有一部分的國家,與曇花一現的公民社會。一塊村裡的麥田上隆起了大大小小的孩子們的墳墓,但死亡日期卻不全是5月12日,「我问当地的一个村干部,为什么要这么做?村干部说,上面的领导说。如果都写5月12日,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李大眼|写在5.12的爱国帖(经典旧文) —— @李承鹏
站在北川学校废墟前的我很困惑,我依然爱G(國),但渐渐明白碎渣里的钢筋并不是帝国主义悄悄抽走的,那些孩子也并不是死于侵略者的魔爪,而死于自己人的脏手。我更困惑,为什么911死难者都有名字,我们的孩子没有名字……
這篇寫於十年前的文章,仍然「常讀常新」,作者 @李承鹏 在川震前後的「愛國」心情變化,或許是許多人的內心寫照:「我们当然要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可长城也应该保护我们的血肉。爱国主义应该是双向的,单向收费的不是爱国主义,是向君主效忠」。同時,這篇文章也讓我們記住了那位比照國家建築標準、堅持把關校園施工底線的監工,句艳东。
川震十年,“我们的娃娃”还在等一个答案 —— @NGOCN
在谭作人家中,当年由家长填写的问卷只剩下五份了,里面有两道问题,五份答案完全一致:——你对依法维权有没有信心? 有信心 ——如果依法维权困难,你是否准备放弃? 不放弃
這篇文章原發於2018年6月1日,是中國大陸的「六一兒童節」,也是汶川地震後的第十個年頭。文章追蹤訪問了十年後的譚作人,亦記錄了一位在失去妻子後又失去女兒的父親,陆世华的災後十年。「不再高调地为去世的孩子“讨公道”,是陆世华对现实的妥协。清明节时,他写了一段话,开头是这样的:“我们无力为冤死的孩子们讨还公道......只有在祭奠时弱弱的问一声:十年了,孩子们你们还好吗?天堂可有不垮的教室?”」。
十年后,一位年轻的香港记者说,他在咖啡馆里写今年的报道,写完有关谭作人的片段,哭了很久很久。为谭作人的付出,为他至今不悔义无反顾的坚持,也为回应他的呼吁者寥寥无几。十年前,四川的孩子们被豆腐渣工程碾压;现如今,我们的记忆也被垮塌的钢筋水泥板活埋了吗?
「他们曾经那样顽强地保持了逃生的姿态,他们需要成年人呼出他们的声音」。一起聯署校難調查的人除了譚作人,還有謝飴卉。整理譚作人的手稿、在譚作人入獄後於週年祭日之前面世(譚作人:地震死難學生的調查報告),文末則有寫給北川中學兩個遇難者的信,是譚作人「365封信」計劃的第十一封。
聚光灯外的地震亲历 · 没有模糊血肉、没有救灾英雄、没有调查记者、没有家国情怀 —— @hupili
回头看去,那时真的是一个孩子,做不了什么,不知道可以做什么、该做什么。10年过去,趁着记忆还未完全模糊,我想记录下聚光灯外的地震亲历。这里没有模糊血肉、没有救灾英雄、没有调查记者、没有家国情怀。有的是信息的闭塞,基建的落后,匮乏的知识储备与预案,贫瘠的心理干预。震区之外,普通人的生活也充满奇怪的猜疑、恐惧、迷茫,最终形成了「小震不用跑,大震跑不脱」的人生态度,一切照旧。
地震親歷者的另一種真實記錄,「最初的30秒没有感觉,是懵的。」,「那种感觉好像身处暴风的中心,四周都是可怕的宁静。」。在現場,還有各式各樣的「假新聞」侵擾著大家的神經。在終於得到救助回家與家人匯合後,「土制地动仪」成為家中好一段時間的必備品。@hupili 亦開始頻繁寫作記錄,「生怕每过一天,我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东西就会少一些」。
而後雅安地震發生,我又進川,回頭找當年認識的災民,然後用微信聯絡...。災民從不避談他們的冤屈不解與怨恨,他們上訪,看地方官員貪污。很多故事,一時半刻也說不清楚。但作為一個記者,我不時想著去報導災難的姿態跟意義到底該是什麼?今年我寫了篇簡單的故事,談談中國新聞記者在「無法調查」情況下,無意間完成的陪伴。
在災難的新聞報導前,有許多人討論追責、討論倫理,而台灣記者、文字工作者阿潑,則以地震倖存者倪孝蘭與廣東記者的故事,討論了「陪伴」:「倪阿姨說,一直以來她都不敢進來,因為女兒死在這裡。但是去年廣東記者來到四川,鼓勵她要進去,並且陪她一起走。他們兩個還拉鉤,說要堅持下去」。
聚源中学废墟幸存学生的十年:走不出阴影,走不出贫困 —— @王牧
那家装修公司销售组的同事们看到,这位平时沉着冷静的销售员,吓得脸色“发青”。同事们看到张悦的异样脸色,关切地询问起来,她应付着说,只是过度惊吓而已。 在所有的职场经历里,张悦都没有透露过,她是汶川地震掩埋的幸存者。她想做一个埋名的幸存者,她想努力活成一个普通人。
本文為網易人間發表過的文章原文,主要受訪者張悅是江堰市聚源镇長大的女孩,在「教学楼主梁钢筋只有正常直径的三分之二甚至三分之一」裡唸初三的她,是當時地震倖存者之一。從廢墟中走出後的這十年,創傷後應激反應用力地烙刻在張悅的身上,也印刻在這個國家裡。我們仿佛往前走了很多步,又好像沒有走出來。女孩還有一篇自述,「我已經十歲了,重回生命十年了 」。
雪访 I 国家之下 那些不再自由的哀悼与悲伤 —— @江雪
“孩子,你向国旗敬礼,这国家,却沒有为你提供一间安全的教室。”后来,我在记者手记中写下这句話,发表时,却遭刪除了。
江雪老師的這篇文章寫於疫情「元年」,中國因新冠疫情設立國家公祭日(4月4日)的時候。因為一樣的鳴笛哀悼,第二部分寫到了當年的汶川地震手記。「真正的哀悼,是给出真相,让真相记挂在人们心头,让悲剧不要再次发生。这不应该是基本的常识吗?在一切真情流露都要被禁絕的年代,這哀悼是誠實的嗎?」,「我拒絕这样的哀悼」。
中文播客「随机波动StochasticVolatility」最新一期的隔離來信中,有一封來自五·一二地震倖存者的信件。
十多年来,她不断问自己,为什么是我活下来了,仿佛如果不努力记住痛苦,任何欢愉和雀跃就像一种原罪。她长期吞咽咀嚼这种痛苦,也在努力学会与自己和解。一个小小的个体背负着巨大的、排山倒海的苦难,它构成身体记忆、构成某一群体的集体记忆,它可能会沉睡,但希望当它苏醒之日,会汇聚成惊雷,汇聚成呼号。 十多年后,我们又会如何回忆当下经历的这一切啊?我们还会记得吗?它会成为我们的集体记忆吗?还是会像很多事情一样,随风而逝?
十多年後,我們會如何回憶當下因為疫情而起又因其他事情而經歷種種的這一切?我們會記得嗎?這些、那些、全部,可以成為我們的集體記憶嗎?
或許,一切的答案都在這句話裡:
「今天是不能沉默的日子,其实每一天都是」( @AI XIAOMING )。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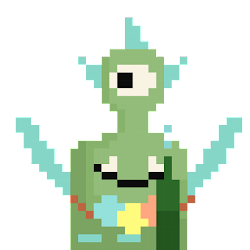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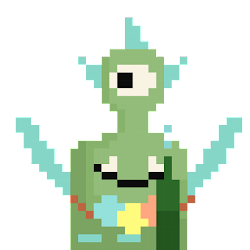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