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文专访朱苏力:司法制度如何面对双重复杂性的挑战?
野兽按:当年为《经济观察报·书评》专访过几位学人,赵鼎新,朱苏力,黄宗智,傅高义,王宁等。遗憾的是当时的媒体环境已经不允许登载崔卫平,贺卫方,徐贲,余英时,秦晖,许章润等几位先生的专访文章了。故而遗憾,没能做成他们的专访。期望以后以自媒的身份去专访他们。搬家中,还好在经济观察报书评公号上找到了原来的推送,专访赵鼎新的那篇已经被删除了。
2014年8月在北大法学院专访了朱苏力教授,和他聊聊他最喜爱的学人理查德·波斯纳法官。采访稿发表在了2014年9月刊的《经济观察报·书评》
2014年7月,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苏力翻译的理查德·波斯纳的《波斯纳法官司法反思录》出版发行。波斯纳法官在该书中指出,由于当代美国司法面临的双重复杂性,美国法官在许多时候正在失去分析和有效应对真实世界问题的能力,变得日益形式主义、管理主义,并试图以各种法律的小机巧来搪塞、对付自己的法律责任。
所谓双重复杂性,一是外在复杂性,二是司法体制自身的复杂性。前者源自社会的科技迅猛发展和全球化,人们的社会活动更复杂,社会环境也更多样,从而引发的争议日益复杂。许多纠纷,法官很难甚或根本就无法理解,更说不上有效应对和处理。后者则是,美国司法系统在过去50年间因种种因素变得更为复杂。
波斯纳的分析表明,司法的某些内在复杂性增长恰恰是为了绕开司法的外在复杂性。除了美国社会和美国法官变得更保守外,重要一点是许多法官对纠纷发生的那些领域缺乏了解,他们没法依据相关事实做出知情的认定和明智的判断。但和普通人一样,法官也爱面子,因此只能高扬司法谦抑,冠冕堂皇地尊崇下级法院、特别是一些专长化的行政部门(例如环保部门、专利局等)的认定和判断,从而避开了若介入可能遭遇的尴尬。
中国当代司法是否也面临同样的困境?面对困境,应如何自处?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专访了《波斯纳法官司法反思录》的译者苏力教授。
问=经济观察报
答=苏力
问:从1994年的第一本《法理学问题》到2014年的《波斯纳法官司法反思录》,二十年来你一直在译介波斯纳的著作给中国大陆的读者,你为什么这么喜爱波斯纳?
答:我觉得他在智力上不断地启发我,我觉得在中国做法律学术太容易政治化,而没有一种对学术真正的、执著的追求。最吸引我的是他对知识的渴望和追求,他对所有的问题都能够从知识的角度去解构,他每一本书都是在开辟一个新的领域,他的著作没有一本是重复的。
波斯纳使我们过往忽视的经验能够进入我们反思的视野,并变成知识的一部分。从而我们今后又可以用这些经验和知识来解释世界或了解世界。如果你没有经验的话,有些人讲的慷慨激昂或大义凛然,你很感慨,但你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你无法验证。你只能说我信这个人,所以我信他说的话。但对波斯纳来说,你可以不相信他,但他讲的这些经验是可以验证的。
问:我们知道波斯纳被誉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美国法律人”之一,他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答:波斯纳大大扩展了法学和法律的知识来源。传统的并且正统的法学理论大致是从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中衍生出来的,比较形而上学,尽管也都受到当时的其它学科的一些影响,但由于法律职业的实践理性特点,也由于法律人的自利、自尊和自傲,法学与其它学科的联系一直不紧密,甚至有意割断这种联系。许多法律学者努力发现法律的本质,试图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自洽的形式化的体系。但是自1960年代经济学进入法学之后,得寸进尺,其它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也都跟随而来。这一点在波斯纳的著作中就特别明显,不仅有经济学,而且有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科学、社会生物学、文学和文学理论、史学、修辞学、博弈论等学科的研究成果;而且在波斯纳的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强有力的思想熔炉中融合起来,这些知识变成了对法律的和有关法律的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和材料。在1986年的一个判决中,波斯纳甚至写进了一个有关发布禁令的数学公式。
波斯纳对法学的一个实质性贡献就是他把美国的以司法为中心的法律的实践上升为一种法学的话语。传统的法理学话语是欧陆的,并且大都是从政治哲学中衍生出来的,关心的是法律的概念(自然法/实证法)以及正义、公平等社会的政制结构问题,对司法的内在视角以及问题关注不够,因此长期把英美的法律观和司法实践基本排除在外。在我看来,只是到了波斯纳这一代人,特别是波斯纳,通过他的知识以及交叉学科研究把法官的经验包括他个人的经验升华为一种比较系统的学术话语。法理学的根本格局已经改变;下一代的学者已经不能仅仅用“法律适用”或”法律解释”或“裁量权”这样一些含混的概念来打发司法过程中的深刻理论问题了。
波斯纳的著作不仅改变了法律的论证,更重要的是它挑战了传统的占主流的法学世界观。所谓传统的法学世界观,就是波斯纳在诸多著作中批判的法律形式主义,即认为法律就是法律,法律自身构成了一个高度形式化的体系,因此只要严格依据这个体系,按照“法律的逻辑”,就可以发现法律的正确结论。正是依据了这一假定,法学获得了所谓的“自主性”。
波斯纳以他的一般的理论分析以及对具体案件和制度的分析挑战了这一世界观。在他的分析中,我们看到,法学并没有这样一个坚实的基础。“法律的终极目的是社会福利,而不是正义”——这是波斯纳常常引用的卡多佐的断言;因此,所有的法律原则、学说、教义和制度,甚至具体案件的判决结果,其正当性都是社会的接受、承认,是其在社会中的实际功能和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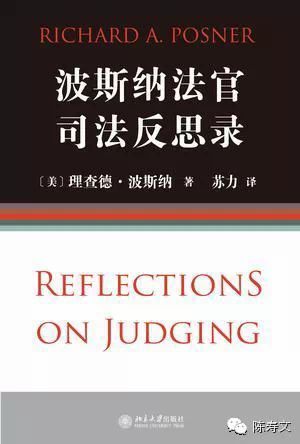
最令人敬佩的是,在波斯纳身上,我们看到他30余年来长盛不衰的学术热情、视野开阔的学术追求以及与之相伴学术敏感和创造力。这一点,对于我以及其他有志于推进中国法学发展的学者来说,恐怕都足以作为一个楷模。
问:你们见过几次面?
答:见过两次。波斯纳没来过中国,我们曾经邀请过他。他非常务实,他说他讲的内容都是美国的,并不一定对中国适用,他知道知识的局限性。我跟他交流,并不是为获得什么真理,而是学习如何思考这个世界,如何谦逊地面对这个世界。
问:在书中,波斯纳法官认为“由于当代美国司法面临的双重复杂性,美国法官在许多时候正在失去分析和有效应对真实世界之问题的能力”。这两种复杂性有什么关联吗?
答:这两种复杂性有关联。但不能说司法的内在复杂性就是对外在复杂性的回应。波斯纳以个人的经历,其他经验材料和统计数据表明,司法的内在复杂性的增加更多源自法官及其他相关人士对个人利益或机构利益的追求,并未做出对外在复杂性的更有效或更称职的司法应对。
在现实世界中,法治所需要的许多信息无法获得,许多事实无法确认,因此法律只能采取某些规则来减少司法对相关信息的需求。其中有不少外观看起来似乎是为了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在我看来,这些“一刀切”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为了减少执法或司法所需要的信息。
我们应当充分赞美规则治理的好处,但也恰恰是在充分意识到好处之际,我们才更应当避免走到另一极端,以为规则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不关注信息、知识和智慧的意义,只注意以法律为准绳,不强调以事实为根据。这种平衡的关注,在今天变得格外重要了。不仅在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技术发展可能为恰当决策提供重要且可靠的相关知识和信息时,要防止简单以规则为名拒绝接受;更重要的也许是,当相关的信息、知识对于正确决策变得至关重要之际,新的知识和信息已经开始重新塑造法律规则甚至重构某些法律领域之际,法律人必须与时俱进,有能力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否则即便渴望开放的心灵,照样可能是封闭的。看看我们的周边,有多少数十年来如一日一直高歌且仅仅高歌解放思想的学界人士!
问:既然现今信息、知识在司法实践中变得如此重要,能否通过强化法学教育来解决这个问题?
答:我不认为通过强化法学教育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在中国,法学一直被视为文科;在文科中,尽管从分类上属于社会科学,但法学教育的实际传统一直更像人文学科,基本还没上社会科学的路数。再加上中国法学教育形成的筛选机制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或是很不利于法学院学生理解这个因科技发展和全球化带来的日益复杂的真实世界。
由于上面说到的法学教育问题,可以想象由此形成的那个所谓的法律人共同体的最大共同处也许就是知识的单一性,而“知识上的偏食只会导致‘弱智’”。一旦“喜欢”文科的法官遇到复杂的问题,周围又是一批同样“喜欢”文科的律师,法学院里也是一批同样“喜欢”文科的教授,可以想象中国法官应对复杂司法问题的能力,令人担忧。
今天中国的法官大多从家门到校门,从校门到法院门,缺乏足够的社会经历,也缺乏丰富的职业经历。若不是从学历看,而是从能满足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之需求的司法能力而言,说句很得罪人的话,这个差距不是缩小了,反而是增大了。
这种例子实在不少。我在此再指出一个重要的例子,一段时间内严重影响甚至促成医疗纠纷的例子。这就是2002年4月1日正式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由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通过这一司法解释,最高法院将过错推定原则作为医疗事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将在医疗事故纠纷案件中本来只是作为特例的举证责任倒置变成了通例。尽管最高人民法院本来目的也许只是便于老百姓打官司和打赢官司,但其实际效果至少部分是激化了社会的医患矛盾。最高法院之所以在精细思考后作出了如此鲁莽的决定,最根本的原因,在我看来,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即王朔的“无知者无畏”。
问:之前采访黄宗智时,他说他很反感法律形式主义,而且美国已经是法律形式主义占了主流地位,中国也开始这样了。波斯纳在这本书中集中批评了法律形式主义。你可以简单解释一下什么是法律形式主义吗?
答:对我来说,法律形式主义就是它想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处理法律的问题,希望在社会科学领域也发现一些永恒不变的规则,然后用这些规则解释一切问题,就此把所有的法律都法条化。但这会产生许多问题,世界是在不断复杂化的。因此你设计的简单规则是不可能应对这些变化的。其次法律面对的是人,人会以各种方式伪装,可以通过说假话欺骗;甚至调动舆论,找关系达到自己的目的。
比如最近发生的佛山政协委员、房企老总何某在水库戏水,看到旁边有妙龄女子,突然抱着她跳进水里,而该女子因不懂游泳而溺水身亡。广州市增城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被告人何某锋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两年。
你说他是过失致人死亡,还是间接故意杀人?这就很难说了。法院裁判说他只是想跟该女子开玩笑,但我们可以发现这其中不光是玩笑的问题。他想的是自己有身份有钱,觉得抱这个女子跳河没什么大不了,最多给点钱当压惊费。因为他的心态,结果才出的事。出事后,受害者家属的心理也会出现变化:如果我把他送进监狱,他赔我的钱就可能很少。现在我女儿已经死了,况且如果我不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他会赔给我380多万,我可以选择拿钱消事。一个案件背后就有一系列的社会因素在其中,如果此时法官不能看到这些社会因素,判案时可能就会出现许多争议。
问:你的意思是,法律形式主义就是把科学研究物质世界的方法套用到研究人类社会?
答:对,法律形式主义相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规则来解决现实问题。
问:这是不是说明我们的法官们已有的知识不足够应付现实情况?
答:是的,这是因为外面的世界发展太快带来的外在复杂性,外在复杂性还包含文化的因素。比如说某男星出轨这件事。在城市里,大家认为他的事不算大,觉得这类事可以接受,以后且行且珍惜就好。但请注意,如果这类事情发生在中国的农村,它依然是个大问题。如果一个男人进城打工,变富裕了,回乡时,老婆已经40多岁,儿子也大了,他回去却要求离婚。周围的人就会说他是陈世美,谴责他。这两种态度就是文化上的差异。
问:说到文化差异,其实一个国家的不同人群之间,也会有文化差异。比如对于死刑的存废,中国的不同群体就有截然相反的两种看法。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答:我觉得死刑不可能被废除,它可能在一个短暂时间很少使用,甚至几十年都不使用。问题在于你不知道今天世界和平的情况是否会永远延续。举个例子,我认为药家鑫不应该被判死刑,结果他还是被处死了。首先他是冲动杀人,另外他有自首行为,但更重要的是,现今的孩子大部分是独生子,你杀了一个人就等于杀了全家。
我写了一篇《从药家鑫案看刑罚的殃及效果和罪责自负》,当时没发表,因为我觉得在那种情况下发表可能反而加快他的死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玫瑾教授当时在中央电视台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对药家鑫的个性和行为作了分析,没有对药家鑫进行道德评判,就引来了网民的集群道德轰炸。
问:事后有些媒体去重新调查,发现了许多事实和之前所得到的信息不同。有人开始认为药家鑫是错杀,认为如果废除了死刑制度,就不会发生错杀的事情了。你怎么看?
答:死刑案件很难让人心平气和,网络也凸显情绪最激烈的表达。无论这是好是坏,法学界都必须正视,力求以建设性的说理方式,避免以意识形态的表态或伪装为技术话语的意识形态方式,讨论死刑案和相关问题。
首先要正视死刑,而不是简单贬斥死刑。这么说是因为,法学界有不少学者,包括许多学法律的学生,都大大低估了死刑的生物基础。出于善良愿望,即使不是把死刑本身视为恶,也常常把死刑存废看成一个纯伦理选择或文化选择,似乎只要法学界集体努力,说服了民众,或是通过强有力的政治领袖的政治决断,就可以废除死刑。
不少法律人因此存在着一种基于自身法律知识和法治理想的骄傲和道德优越,因此也就谈不上尊重民众以激烈语言和情绪表达的他们认定的天理。更糟糕的是,许多法律人也没有能力或不愿努力直接面对深深扎根于人们内心的复仇本能。对死刑,他们好像也给了一些分析,其实和民众一样,只是站在不同立场上表态;一遇上引发社会热议的案件,除了表态,法律人从未给出令人信服或至少会让人予以考量的理由。
就一般的反对死刑而言,法律人给的理由大致有:一是断言废除死刑是历史的潮流;二是枚举多少国家已经废除死刑;三是引证诸如贝卡里亚这样的法学学者的言辞;四是选择性引证某些可疑的研究成果,说死刑没有震慑犯罪的效果;五是死刑可能错杀人,为避免错杀,就应废除死刑,等等。这些理由无论单独还是结合起来都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其实法律人手中没有能够一锤定音的超级炸弹或精确打击的巡航导弹,有的只是信念,尽管包装成了学术。我尊重但不尊敬这些信念。光有信念不管用。面对汹汹“民意”,面对个案事实,你得有能力展开体面且有效果的沟通,即使最终也没达成一致。
法学话语的无力还有另一种表现,在近年来引发社会热议的一些死刑案中,不直接面对普通民众的诉诸,一些法律人把自己的信念隐藏于法律人的技巧,一方面指责民众“实质正义”,另一方面用技术性和程序性法律包装自己的“实质正义”,试图先在个案免除罪犯死刑,然后逐步废除死刑。在刘涌案中,指责侦查中可能存在刑讯逼供;在马加爵案中,指责贫困差别和社会歧视(尽管四位死者同样家境贫寒并且是马的好友);在邱兴华案中,用精神病学的精神病概念置换法律的精神病概念;在崔英杰案中,指责抽象的城管制度。
这类战术有时有效,结果也可能有益。只是,就构建和塑造当代中国社会有关死刑的法律道德共识而言,它们并不成功。有时还进一步撕裂了社会。结果是,法学界和法律人的言说常常得不到民众的足够信任。李玫瑾教授受到的不公道抨击就是一个恶果;许多有理想有追求的法律人也都很郁闷、很委屈。另一方面是不敢得罪民众,有些法律人就拿个案中没接受这些法律人观点的法院出气。法院陷入双重压力,必须应对前后夹击:民众怀疑法院太容易为法律人所操控,法律人则常常指责法院不独立,为民众甚或暴民所胁迫。
而在这些死刑案的社会热议后,有关死刑问题的学理讨论基本上没有任何推进。攻守双方基本各自固守自己的道德直觉和信念。指责和悲叹都改变不了现实,法学界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在这样的现实中推进。什么叫作转型时期,这就是!你不可能指望立法机关或某个领导人下个决心,就废除了死刑。
即使反对死刑的法律人坚信自己恪守的是良知和天理,我认为,首先也必须理解,民众心中恪守的也许同样是天理。法律人一定要能够在这个层面上同普通民众展开对话。法律人也不可能把所有死刑案都成功包装为法条主义问题,教义学分析或法律解释。近年来不少案件都表明,法律技巧的包装只有在相对狭窄的法律界,针对常规案件才有效。一进入缺乏基本共识的领地,涉及的是每个人都能表态的案件,就一定会是各说各话,很难交流。
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2014年9月刊
朱苏力(1955年4月1日-),出生于安徽合肥,中国法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曾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1970年入伍。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85年,赴美公派留学。1992年回国,在北京大学法律系任教。2001年至2010年担任法学院院长。
著作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
《阅读秩序》,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
《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
《波斯纳及其他——译书之后》,法律出版社,2004年
《批评与自恋——读书与写作》,法律出版社,2004年
《道路通向城市——转型中国的法治》,法律出版社,2004年
《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
《法律与文学》,三联书店,2006年
《走不出的风景:大学里的致辞,以及修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