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的框架:脆弱不安的生命
江世威
《戰爭的框架》是巴特勒繼《脆弱不安的生命》之後的姊妹篇,藉由剖析形塑戰爭的話語結構來揭露戰爭的運作機制,並且從戰爭的批判當中反思種族、性別、地緣政治與生命政治的全球議題。
巴特勒在導論中就開宗明義的指出,我們對於戰爭的認識構成了戰爭的事實,而我們的認識又是由戰爭的框架所框定。圖片、影像等媒介在此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因為正是它們決定了我們觀看戰爭的方式。
關於戰爭的討論同時也關係到生命的定義。在戰爭之中我們如何去界定哪些人是值得保護的生命?哪些人不是?一般上我們都會認為兒童的生命是重要的,尤其是當無辜的兒童在戰爭中犧牲的時候必定會引起各種人道的關懷和重視,但是一旦兒童參與了戰爭行動,當他拿起了槍械成為士兵的肉盾和武器,他彷彿就不再無辜,他的生命又變得無足輕重。戰爭揭露了我們對於生命的荒謬認知,並且巴特勒基進的指出,早在他們死於戰爭的砲火以前,我們對於生命的判斷就已經決定了他們的生死。巴特勒擴大了戰爭的範疇,她將所有人都納入了戰爭的場域之中無人能夠倖免。當戰爭不僅僅是指具體發生的戰事,而同時也是由觀看構成的框架時,那麼戰爭就不再是發生在我們日常生活之外的事情,而是與所有人的命運息息相關。
構成框架的條件
戰爭問題的本質是生命政治的問題,它同時涉及到認識論、本體論和倫理學的層面。一方面它關係到哪一些生命被視作生命,哪一些生命又被排除在外,另一方面對於生命的界定又來自於我們如何去認識生命,而我們對於生命的認識最終又關係到哪些生命能夠獲得拯救。
在現有的論述之中,有些人的生命不被視作生命,他們被排除在框架之外無法獲得認可,為此巴特勒認為有必要提出另一套本體論來與現有的論述抗衡。但是在此之前必須先釐清框架形成的條件。
我們對於生命的認知包含了「理解」與「承認」兩個部分。兩者的差異在於,承認有著明確的分類和具體的定義,是已經固定和定型了的;理解則是一種模糊不清,未被確定下來的感覺。所以理解能夠觸及到未被承認框架認可的生命。理解是承認的必要條件,被理解的生命不見得會受到認可,但是受到認可的生命必定是已經被理解的,也就是說生命要被認可就必須先被理解為生命。
框架由理解與承認組成,而構成框架的條件則是「可理解性」。可理解性界定出可理解與不可理解的邊界,它是我們認識事物的條件,我們的認識活動是以可理解性作為給定的前提才得以可能的。可理解性作為認識的前提它必然先於認識存在,並且它本身的輪廓無法被描繪。每個歷史時期都有其可理解和不可理解的對象和區分,因而可理解性具有歷史的普遍性,並且不同時期對於可理解與不可理解的範圍和界定都有所不同,因此認識的框架會不斷的改變。
框架必須經由複製來維繫自身的存在,但是框架的複製不是建立在同一性之上,而是差異。框架的複製本身並不是連續的,它並非在重申框架之中的內容,而是同時包含了在框架之中以及被框架排除的事物。因此框架在複製自身的同時會遭受到它所排除的事物的威脅。框架的再現不是單純的重複,在它本身的再構成過程當中它必須先被打破才能重塑,這是構成框架本身的環節之一。所以框架本身的顛覆和轉變就包含在它自身的複製過程裡。框架的複製有賴於媒介的傳遞,無論是透過新聞、書信、圖片或是網路,框架要想從一處移動到另一處它都必須經由媒介的傳送,而此時正是框架最不穩定的時刻,因為在媒介傳播的過程中,被框架排除的事物就有被揭露,被看見的可能,也只有在這個時候我們才有可能去認識到未被框架認可的生命。
生命的社會性:脆弱特質與脆弱處境
巴特勒對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作出了嚴厲的批判,後者認為人天生就擁有不可剝奪的權利,人的生存本來就應當受到保障。但這種觀點並不能成立,死亡是生命的過程,凡是生命就必然時刻面對著死亡,所以並不存在「天生」免於死亡威脅的事實,認為人具有不可侵犯的權利其實是混淆了實然與應然層面的問題。是否被視為生命與生命應該被如何對待是兩個不同的問題,人是生命但這不意味著他理所當然的就會受到重視。
為此巴特勒給出了一套社會本體論來駁斥人類中心主義的詮釋。這套本體論由「脆弱性質」與「脆弱處境」兩個概念所組成。要使不被認可的生命得到認可必須先理解和接受一個普遍的前提。生命是有限的,生命會消逝,而且生命的持續需要依賴許多的介入和干預來維繫,沒有任何一種生命是可以全然不依賴外在於它的事物而獨立存在的。這便是生命的脆弱特質,是所有生命普遍共有的。只有理解到生命的脆弱性質才有可能進一步去認可生命。
在這裡巴特勒將「脆弱性」定義為「存在之條件」,是讓生命得以作為生命的可能性。同時「脆弱性」也等同於「社會性」,因為人要能生存需要各種社會支持,他需要醫療介入來維持身體的健康,需要工作來維持生計,需要隸屬於群體之中來獲取認同感。所以因為人的脆弱性才催生出各種形式的社會職能。一旦維繫生命的條件無法得到保障,那麼生命也就無法生存,而這便是生命的脆弱處境。
從來就沒有單個個體存在,所有的個體都必然指向他者。區分產生出邊界,劃分出我與他者之間的區別,只有在區分的框架之中,個體才能擁有身份,才能作為主體,才能夠與其它個體區別開來並且發生關聯。在「我」與「他者」之間彼此互為條件,它們構成了彼此的存在,就此而言它們也就是彼此的脆弱性。而上述一切都是由區分的框架所產生,區分構成了生命存在的條件,當我們在理解巴特勒的脆弱性(社會性)概念時,我們可以從最根本的意義上將其理解為區分,生命需要仰賴它物才得以生存,因此生命的存在本身就預設了除他之外的「其它」,生命是在相對於其它事物的區別之中維繫自身的。如此以來也就可以理解框架是如何能夠形塑生命。
問題不在於我們將什麼樣的對象視作生命,是人或是動物都無關緊要,重要的是生命本身所具有的普遍性質,生命易逝並且生命的存續需要依賴各種干預,就這一點上人與非人的物種之間並沒有區別。重點不在生命本身而是構成生命的條件,只有意識到生命的脆弱性,並且讓維繫生命的條件得到保障,生命才能夠作為生命被看見,也才有獲得尊重的可能性。
提出生命的脆弱性前提並不是預設一種先驗的本體論立場。生命的脆弱性是需要被理解和接受才能成立的,生命的易逝必須被理解為哀慟的體驗,這樣維繫生命的條件才會受到關注。框架決定了哪些生命的條件能夠被看見,進而也影響了我們對於生命的情感回應,就此而言我們對於脆弱性的感受和理解也受到了框架的作用。
戰爭不是社會的例外
戰爭不是發生在社會外部的異常狀態,當巴特勒將戰爭理解為框架構成的事件,那麼戰爭就與日常生活的其他領域無異,都是社會整體的一部分。福柯在《必須保衛社會》中異曲同工的指出,對社會生活的治理就是戰爭的延續。
框架區分生命,它呈現特定的生命處境,同時又將另一些生命處境隱匿起來,它讓我們難以看見不同生命之間的依存關係,從而使我們對特定的生命憐憫,對另一些未被表述的生命視若無睹,甚至於對剝奪特定生命的暴行表示認可。戰爭並不是指槍械、砲彈造成的暴力行徑,而是在框架本身,框架的運作就是戰事的編排和部署。
當我們在談論公民權利的時侯,難民、非法移工、無國籍者等等的生命處境就被排除在外,而且後者經常被標籤為犯罪者、經濟掠奪者、威脅社會的不安因子。在這裡公民的脆弱性被放大,彷彿他們時刻處於性命和生計堪憂的危險之中;而難民,非法移工等非公民往往無法像公民那樣享有國家的保障,他們沒有健保,生病時無法得到妥善的醫療照護,並且他們的非法身份使他們經常需要為了躲避搜捕而逃亡,他們之中大部分都無法得到合法的工作只能在條件惡劣的環境之中從事勉強維生的勞動,他們被排除在社會的安全網之外,然而他們的脆弱處境往往不會呈現在公眾眼裡,或者根本不被重視。
框架誇大公民的脆弱處境同時將非法人口的脆弱處境遮蔽,由此產生出兩種對立的情感,使得人們無法意識到彼此之間的共生關係。如果沒有這些非法人口,先進國家根本無法解決勞動力短缺的問題,他們為國家的經濟增長作出了貢獻,但他們從始至終被排除在國家的庇護之外。套一句巴特勒在書中引用的話,他們僅僅是「威脅人類生命的活物」。
脆弱性是極具生產性的概念,因為它能超越身份與國家的界線來理解生命。當我們僅僅從身份和國家歸屬來看待生命,往往會陷入矛盾對立的桎梏之中,而脆弱性的概念讓我們看見個體在具有身份,在相互鬥爭以前作為生命所共有的條件。
如何在反對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下主張倫理責任?
如果拒絕從人類身份去思考道德義務,如果反對從人類群體或個體身上推論出道德歸屬,那麼我們要如何去談論生命的倫理責任?
為此巴特勒提出了一種嶄新的倫理觀,這種倫理觀不是指向特定的個體或群體,而是指向使生命得以存續的存在之可能性條件。當每個人都是他人的存在之條件,那麼倫理責任就不是只針對特定的主體。
倫理責任的目的在於保障維繫生命的條件,巴特勒在此採取了一種黑格爾式的觀點,當每個人都是彼此的脆弱性,那麼我們就有義務和理由不去傷害他人的生命。這種義務無關於種族、國族、性別等等的身份,而是基於生命具有的普遍特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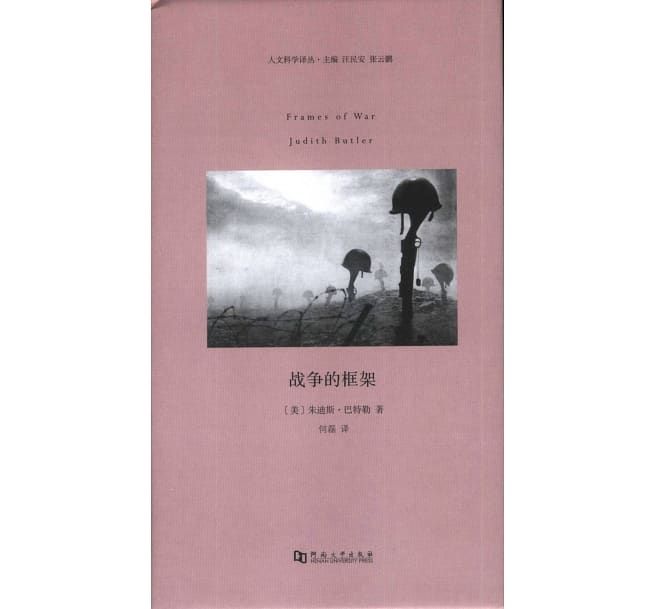
卒子先行wordpress:
https://cornersociologist.wordpress.com/category/%e7%90%86%e8%ab%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