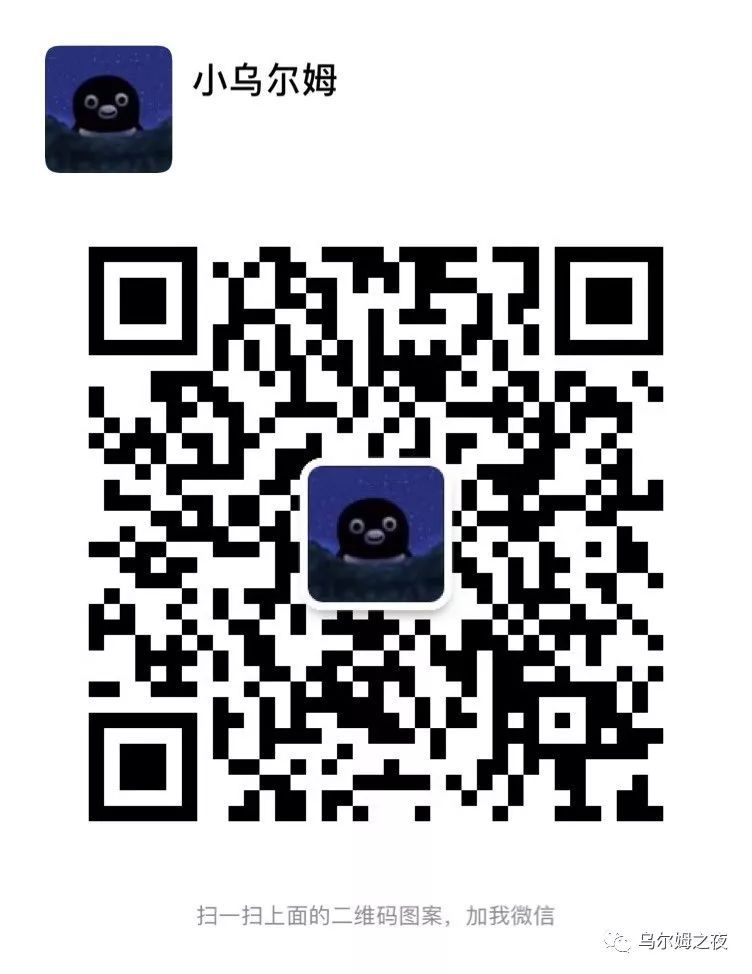阿甘本再论疫情 | 乌尔姆×疫病时期的哲学
本文译自3月24日法国《世界报》对阿甘本的访谈,原文标题为Giorgio Agamben : « L’épidémie montre clairement que l’état d’exception est devenu la condition normale »。

译者:岛夷
校对:🦆
排版:Citron
文章来源:
在《世界报》的访谈中,这位意大利哲学家批评超出常规的安全措施的实施,这一措施意味着应当通过悬置生命来保护它。
国际知名的意大利哲学家乔吉亚·阿甘本曾在他的政治哲学代表作《神圣人》中特别提出作为治理范式的“例外状态”概念。承袭米歇尔·福柯,还有瓦尔特·本雅名和汉娜·阿伦特,他进行了一系列关于“装置(dispositif)”和“命令”概念的谱系学考察,勾画出了“无作(désœuvrement)”和“生命形式(formede la vie)”及“解建制力(pouvoir destituant)”等概念。作为被“不可治理(极左)”派当作理论资源的知识分子,乔吉奥·阿甘本在宣言报(il manifesto)上发表的一篇评论(《冠状病毒与例外状态》,2月26日)引发了批评。原因是根据当时的意大利卫生数据,他强调在减小疫情规模时要捍卫公众自由。在世界报的访谈中,他将会分析为控制疫情而实施的安全措施所引发的“政治与伦理上极为严重的后果”。
问:在宣言报发表的文章里,您写道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是一种“想象的流行病”,只不过是“一种流感”。考虑到病毒的大量受害者以及传播速度,尤其是在意大利,您是否对这番话感到后悔?
我既不是病毒学家也不是医生,在提到的那篇一个月前文章里,我仅仅是原文引用了意大利国家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la recherche)当时的观点。我也不会介入科学家之间关于流行病的讨论。我所感兴趣的是由此所造成的伦理与政治上的极其严重的后果。
问:您写道“把恐怖主义作为实施例外手段的理由看起来已被用尽,一种流行病的发明则为(例外手段)超出一切限制的推广提供了理想借口”。您如何能够确信这是一种“发明”?流行病和恐怖主义一样,就不能将我们引向可能难以接受却又非常现实的安全政策吗?
当我们谈论政治领域中的发明时,不该忘记它不能仅从主体(subjectif)意义上来理解。历史学家知道有从某种角度是上来说可以是客观(objectives)的密谋,好像没有一个可识别的主体来引导也可以自己产生意义。就像米歇尔·福柯在我之前所呈现的,安全治理未必是通过制造例外状态来运作,而是在当它自己产生时去利用它、引导它。肯定不止我一个人觉得对于一个像中国那样的极权政府,流行病是测试隔离可能性和整体区域监控的一种理想方式。在欧洲我们或许可以援引中国作为一个可追随的典范,这展示了政治上不负责任的程度,恐惧向我们袭来。中国政府在它所认为合适的时机就立即宣布了封城,起码应当对此反省。
问:在你看来,为什么例外状态是不正当的,即使在科学家眼中隔离是阻止病毒扩散的主要方法之一?
在塑造我们的语言的巴别塔式混乱状态中,每个领域都追随它们自身的一套理性而未曾考虑其他领域。对于病毒学家,斗争的敌人是病毒;对于医生,目标是康复;对于政府,则是维持控制。很有可能我也是一样,通过提醒我们对此将要付出的代价不应过高。欧洲此前也有过更严重的流行病疫情,但是没有人曾想过对此宣布一个像意大利和法国现在这样在事实上妨碍我们生活的例外状态。就算我们意识到了流行病目前仅仅感染了意大利不足千分之一的人口,我们还是会问当它真的恶化时该怎么办。恐惧是一个糟糕的顾问,我不认为把一个国家当成疫区国,或者把其他人看作潜在传染源是一种好的解决方案。逻辑谬误一如既往:正如面对恐怖主义时我们认可要削减自由来进行防范,同样有人告诉我们应当通过悬置生命来保护生命。
问:我们没有协助一种永久性例外状态的实施吗?
疫情清楚地揭示了例外状态已成为一种常态,政府早已让我们对此习以为常。人们是如此习惯于生活在一种永久危机状态中,以至于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生命已被压缩到了纯粹生物状态,并且不仅失去了政治维度,也失去了一切人的维度。一个生活在永久紧急状态下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自由的社会。而我们就生活在一个为了所谓的“安全理性”而牺牲自由的社会里,并且将被迫永远生活在恐惧和不安状态中。
问:在何种意义上我们生活在一场生命政治危机中?
现代政治从头到尾就是生命政治,后者的关键在于生物性生命本身。新的情况是健康变成了一项应不计代价去履行的法律义务。
问:在您看来,为什么问题不在于疾病的严重性,而在于它所造成的所有伦理与政治的崩溃?
恐惧暴露出那些我们视而不见的事物。首先是我们的社会不再相信除了赤裸生命以外的任何东西。在我看来面对被感染的风险,意大利人很明显已经准备好牺牲一切:他们生活的常规状态、社会关系、工作,甚至是友谊、情感、政治和宗教信仰。赤裸生命不是什么团结人类的东西,它反而使人盲目和分离。就像曼佐尼在他的小说《约婚夫妇》里描写的瘟疫一样,其他的人只是一群必须至少保持一米距离的传染源,要是靠的太近那就必须把他们关起来。即使逝者也不再拥有埋葬权,人们不太清楚它们的遗体到底怎么样,这真的太野蛮了。我们的邻人也消失无踪。看似支配了西方世界的两大宗教:基督教和资本主义,也就是基督的宗教和金钱的宗教,竟然缄默无言,这实在令人震惊。在一个习惯于这种条件下生活的国家里,人际关系会是怎样的?一个仅仅相信幸存以外不再相信一切的社会又会是怎样 ?
问:在您看来,未来的世界将是怎样的?
我所担忧的不仅仅是现在,也是将来。就如同战争给和平留下了一系列有害的科技遗产一样,很有可能在卫生紧急状态结束后,我们会试图将这些政府以往未能成功完成的实验继续下去:譬如关闭大学上网课,譬如一劳永逸地中止一切政治和文化议题的聚会讨论,只用数字讯息交流,譬如到处都可能用机器取代人际间的一切接触,以及传染。
疫病专题文章回顾
我们的智性生活正遭受着威胁。
空洞的意识形态话语占据了道德高地,
边缘人的存在本身岌岌可危。
风暴的轨迹难以预测,但气压的异常足以让我们紧张起来。
在世界秩序变化的关键时刻,
掩耳盗铃或是隔靴搔痒,将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我们需要严肃鲜活且诚实的讨论,
在漫游途中搭建营帐,守卫议事自由。
乌尔姆之夜是一场偶然的相遇,它没有任何终极目的,
因为任何神话在当下都会即刻变成一场喜剧。
这是一场理论、反思和跨学科的歌命性联动,
意在打碎一切神话的前提下,无限拓展公共言论空间。
这是一场根植于当下、聚集在案厅、活跃于街巷的解放性实践,
其中没有一个成员,也拥有一切成员。
未来讨论,主题开放,不限学科,由参与者共同讨论决定。
活动目前在巴黎,想要参与讨论或加入团队请联系小乌尔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