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真的要求道德监管吗?
伊斯兰中宗教警察的可疑根源
穆斯塔法·阿克约/文
王立秋/译
Mustafa Akyol, “The Dubious Roots of Religious Police in Islam”, New Lines Magazine, December 5, 2022, https://newlinesmag.com/reportage/the-dubious-roots-of-religious-police-in-islam/,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做其他用途。
穆斯塔法·阿克约,作家,加图研究所伊斯兰与现代性资深研究员。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全穆斯林世界都在用伊斯兰的“劝善戒恶”概念来限制个人自由、督导风纪,但这种诠释是成问题的。
2022年9月16日,成千上万抗议者高喊着“我要杀了那些杀死我姐妹的人”涌上伊朗街头。他们指的是玛莎·阿米尼,几天前因被指控没有完全遮住自己头发而被德黑兰的“Gasht-e Ershad”(گشت ارشاد,字面义即“巡逻督导”,又被称为“风纪警察”)逮捕的那名22岁库尔德裔伊朗女子。在被拘留期间,她在头部受创后死亡,尸体上还留有瘀伤。这一暴行引发了民众的愤怒,后者迅速转化为全国性的民众骚乱。这场骚乱直到本文写作之时还在持续,虽然安全部队做出了野蛮的回应,但各行各业的人们还在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抗议。
周末,据报道(或误报)伊朗决定废除风纪警察。如果消息属实的话,这将是当局对抗议运动的一次重大让步。许多伊朗分析员自那时起就一直在澄清这些报道可能受到了误导,伊朗的官方媒体已经正式否定了它们。
可为什么伊朗一开始会有“巡逻督导”呢?这制度真像伊朗政权声称的那样,是伊斯兰要求的吗?这些问题对伊朗的未来和更广泛的穆斯林世界的未来来说都很重要,因为伊朗不是唯一一个使用宗教警察的国家:宗教警察也活跃于沙特阿拉伯、阿富汗、尼日利亚、马来西亚和印尼的亚齐省。他们的严格程度可能不一样,但他们的行动都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必须通过国家来贯彻(他们所定义的)伊斯兰的宗教要求。因此,应该强迫女人把自己的身体遮起来,应该惩罚喝酒的人,必须封禁“危险”书籍。在20世纪90年代,在塔利班第一次统治阿富汗期间,该运动甚至极端到销毁了所有乐器(并惩罚乐手)、棋盘甚至风筝。今天,再次掌权的他们号称更温和了,但可以看到,他们和过去几乎没有什么差别。难怪阿富汗的女大学生(如果不穿上罩袍把全身都遮起来,她们就不能去上学)要喊出和伊朗的抗议者同样的口号“女人、生活、自由!”了。
同时,在从阿拉伯世界到巴基斯坦的许多其他穆斯林国家,虽然可能没有专门的宗教警察,但常规的警察——或其“礼仪或公序良俗、风化(آداب, adaab)”单位——还是会监督和惩罚宗教上的行为不端,比如说在抖音上搞“擦边球”,或斋月白天在公共场所喝酒。
对于在西方生活的许多穆斯林,尤其是那些习惯了公民自由的穆斯林来说,所有这些宗教规定经常让人感到困惑。许多人会想,如果不是出于自由选择的话,那么,宗教实践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们可能回想起经常被引用的那句经文“宗教无强迫”(2:256)并因此而得出结论:宗教中的任何强迫都偏离了“真正的伊斯兰”。但质疑伊斯兰中的宗教强迫要求更加深入的讨论,因为长期以来,支持宗教强迫的人一直在用两个权威的参考来为它辩护:古兰中“劝善戒恶”的义务,和所谓的“问责(حسبة, hisbah)”制度。
让我们从古兰开始。古兰中有八段经文(3:104, 3:110, 3:114, 7:157, 9:71, 9: 112, 22:41, 31:17)出现了“劝善戒恶(ٱلْأَمْرْ بِٱلْمَعْرُوفْ وَٱلنَّهْيْ عَنِ ٱلْمُنْكَرْ, al-amr bi-l-maaruf wa-n-nahy ani-l-munkar)”这个表述的变体(或者说提到了这个概念),要么说它是真正的信仰者的特征,要么说它是他们的义务。这些经文中的第一段3:104很可能是最确定的,因为它要求一个具体的人群遵守这个义务:“你们中当有一部分人,导人于至善,并劝善戒恶;这等人,确是成功的。”
正是在这段经文的基础上,沙特阿拉伯的宗教警察,即所谓的“劝从官(مطوع, mutawa)”把自己称作“劝善戒恶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Promotion of Virtue and the Prevention of Vice)”。(自2016年起,他们的权力受到一定限制。但对他们构成限制的,是王室的命令而非宗教改革本身。而且,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限制只是强化威权主义的借口。)类似地,塔利班也有自己的“劝善戒恶部(Ministr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Virtue and the Prevention of Vice)”。伊朗的“巡逻督导”也以伊朗宪法第八条为基础,后者也宣布“劝善戒恶”是“一个普世的、相互的义务”。
但所有这些宗教警察势力,看起来都略过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们怎么知道呢?由谁来定?这些对宗教的诠释真的符合伊斯兰的宗教劝、戒吗?
这些问题是中肯的,特别是因为古兰中使用的术语。古兰中用来指有待“劝导”之“善”的词是“معروف (Maaruf)”,字面义是“已知的”,指习俗性的伦理规范。这个概念在伊斯兰之前就有了,前伊斯兰时期的阿拉伯人用它来指众所周知的伦理价值,如彬彬有礼和与人为善。因此,阿拉伯词典编纂者伊本·曼苏尔(Ibn Manzur, c.1233-c.1312)把maaruf定义为“人们觉得有益的、可爱的东西”。它的对立面,“منكر (munkar,被否定的)”则被他定义为冒犯人类良知的可恶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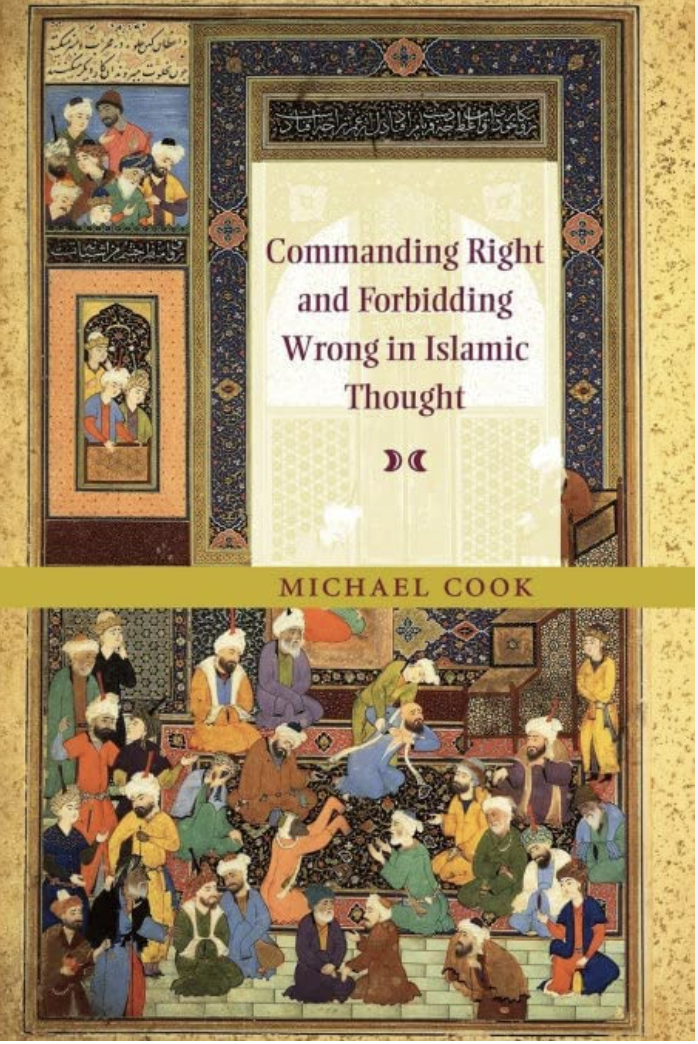
因为善恶难以捉摸,伊斯兰的头几个世纪出现了几种不同的关于这个义务的看法。迈克尔·库克(Michael Cook)在他长达700页的《伊斯兰思想中的劝善戒恶》(Commanding Right and Forbidding Wrong in Islamic Thought)中考察了这些看法,这本书也是关于这个主题最全面的研究。就像库克指出的那样,古兰最早的评注者不一定把这个义务诠释为宗教监督。相反,一些评注者仅把这个义务理解为“劝人信仰真主及其先知”。艾布·阿里亚(Abu al-Aliya, d. 712)就持这样的看法。他是先知同伴的追随者(اَلتَّابِعُونَ, tabiun, 字面义为追随者或继承者,中文又称再传弟子),或者说,是(直接接触过)先知穆罕默德的人之后的第一代人。据报告,阿里亚是这样描述这个义务的:“号召人们从多神论转向伊斯兰并……禁止崇拜偶像和恶魔”。稍后,穆卡迪尔·伊本·苏莱曼(Muqatil ibn Sulayman, d. 767)——他的三卷本巨作是最早的古兰经注之一——也以类似的方式,对这个义务做了有限的定义。对他来说,“劝善”意味着“劝人认主独一”,而“戒恶”则意味着“禁止多神论”。
伊斯兰的头几个世纪还出现了一种对“劝善戒恶”的政治诠释。这种看法认为,这个义务主要涉及发声反对僭主,甚至发动反对僭主的叛乱。事实上,就像库克评论的那样,“在伊斯兰的头几个世纪,叛乱以劝善戒恶为口号的情况相当常见。”理性主义的穆尔太齐赖派也支持这一立场,他们责备传统主义的对手宣扬“(无条件)服从胜利者,即便他是压迫者。”
某些圣训或者说被认为是先知说过的话的确也确立了这种寂静主义的服从观。一则圣训说,“犯统治者者,安拉必犯之”。另一则圣训也裁断说:“听从统治者,执行他的命令;哪怕他鞭打你的后背,夺走你的财富”[1]。据此,哈乃斐派学者伊玛目塔哈维(al-Tahawi, d. 933)在他广为人们所接受的逊尼派信条声明中写道,“我们不允许反叛我们的统治者或那些负责公共事务的人,哪怕他们是压迫者。”这个学说背后有一个合法的理由:事实证明,伊斯兰早期由叛乱引起的内战是灾难性的。但只靠服从——只要统治者坚持伊斯兰的基本信条——来追求和平也建立了一种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而在逊尼派世界,这种文化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因此,一方面,事实证明,在逊尼派伊斯兰中,“劝善戒恶”的义务在政治上非常宽松。而另一方面,这个义务又被积极地用来针对罪人和异端。通常在逊尼派里最强硬的罕百里派就是主要的例子。
在10世纪和11世纪的巴格达,臭名昭著的罕百里派会冲进商店或别人家里砸掉酒瓶、破坏乐器或棋盘,质疑在公共场所走在一起的男女,扰乱什叶派的宗教仪式。
在概念上,这种全方位的强迫,与这样一种看法相伴:“maaruf”(已知的善)被等同于沙里亚的所有命令。伊历三世纪的逊尼派古兰经注家塔巴里(al-Tabari)就反思过这种看法。根据库克的转述,塔巴里认为“劝善”指的是真主及其先知所命令的一切,“戒恶”则是指他们所禁止的一切。换言之,这个义务要求落实所有虔诚的行为,惩罚所有不虔诚的行为,至少是在公众看来不虔诚的行为。(同时,总的来说,家的隐私还是得到了尊重,因为古兰禁止未经允许窥探和进入别人的家。)
为理解这种从“劝善”到“落实善”的引申,我们需要考察故事的开端:古兰。古兰对其信仰者传达了许多命令,并预期他们出于对真主的信仰和对后世得救的希望——而不是因为现世的任何强制措施——而服从这些命令。
比如说,信真主是伊斯兰的第一命令,但古兰只用后世的真主之怒来威胁不信仰的人或者说否信者。类似地,古兰命令穆斯林要礼拜、封斋,不要喝酒或赌博,但古兰并没有明说违反这些命令要受到怎样的惩罚。古兰也命令穆斯林女性着装要端庄,但再一次地,古兰并没有说在现世,不这么做会有什么后果。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古兰的确指出五种具体的罪行要受到惩罚。这五种行为中的四种后来也被写进了伊斯兰教法,它们被称作“حدود (al-hudud)”,或真主的“边界”。这些罪行是谋杀或不义、抢劫、偷窃、通奸和诬告人通奸。这些罪行都要受到体罚,就像在古兰的历史语境中经常发生的那样。
对我们当前的讨论来说,相关的问题是:为什么古兰要惩罚偷窃,却不惩罚比如说,不礼拜呢?古兰本身并没有给出任何答案。但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这两种行为之间的区别:几乎在所有社会中,偷窃都是一个会被惩罚的罪行,因为它侵犯了他人的权利。另一方面,礼拜则是人与真主之间的私人联系,不礼拜并不会对他人造成任何伤害。(事实上,对关于信仰和崇拜的所有问题来说都是这样。就像托马斯·杰斐逊曾经指出的那样,“我的邻居说有20个神或没有神对我来说都不会造成任何伤害。这样的行为既不会掏空我的口袋,也不会折断我的腿。”[2])
但古兰只是伊斯兰教法的开端。在之后的头几个世纪,现世惩罚的范围大大扩大了,而这些惩罚依据的往往是(与传述广泛的圣训相对的)单独报告的,因此也是可以怀疑的圣训。(比如说,因为有报告称先知曾经说过“谁改变自己的宗教,就杀死他”,所以,否信成了死罪。)因为后来的这种对“劝善戒恶”的诠释,几乎所有的宗教命令都变成了可以执行的法律。
比如说,不每天礼拜就是这样变成了一个严重的罪行,就像11世纪著名法学家马沃尔迪(al-Mawardi)在他的《苏丹统治的法度》(الأحكام السلطانية, al-Ahkam al-Sultaniyyah)——这是一个标准的逊尼派伊斯兰政治理论文本——中解释的那样:
如果一个人不[礼拜],声称礼拜不是义务,那么,他就是不信道;治理否信者的裁断也就适用于他——也就是说,除非他悔改,否则就可以因为否信而杀死他。如果他说因为礼拜对他来说太难了所以他没法改,但他同时也承认礼拜是义务的话,那么,教法学家在裁断上有不同意见:艾布·哈尼法认为应该每到礼拜时间就打他一顿,但不用处死他;艾哈迈德·伊本·罕百里和他后来的一群追随者说,他因为不礼拜而变成否信者,因为他否信,所以要杀死他……沙斐仪认为……在杀他之前先要求他忏悔……如果他拒绝忏悔,也拒绝礼拜的话,那么就要因为不礼拜而处死他——一些人认为要立刻处决;其他人则认为,要在他连续三天不礼拜后才能处决。应该用剑冷血地处决他,不过艾布·阿巴斯·伊本·苏莱吉说,应该用木棍打死他。
那么在莱麦丹月不封斋怎么算呢?马沃尔迪写道,不用“处死”不封斋的穆斯林,但还是要“酌情惩罚,给他上一课”。这样的惩罚在伊斯兰法中被称为“تعزير (Tazir,酌定刑)”,意思是由权威裁定而非经典规定的酌情裁断,通常包括鞭刑和短暂拘留。

那么,负责落实这些法律的权威是谁?有卡迪(قاضي, qadis)或法官做主的法庭,但法庭本身并不会去追查违法者。后一个任务——这个任务被马沃尔迪描述为“宗教的根本问题之一”——被称为“问责”,是由“问责的人”或“محتسب (muhtasibs)”来执行的。虽然所有穆斯林都有“劝善戒恶”的义务,但实际落实规定的,是这些国家指定的官员。
那么,什么是问责呢?在伊本·曼苏尔引述的众多意义中,这次意味着执行和管理限制、充分性、监控和评定。古代和当代的穆斯林文献都把它定义为一种先知确立的执法方式。不过,在我们细致考察先知的实践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种截然不同于宗教监管的东西,即市场监察。
在新生的伊斯兰那里,市场是一个根本制度,因为很多第一代穆斯林,包括先知,长期以来都是商人。难怪在迁出(hijra)麦加、在麦地那定居后,穆罕默德会在城中指定一个点宣布:“这是你们的市场,让它宽敞些,别对它征税。”他还经常亲自到市场上巡查,以禁止任何欺诈行为,古兰也在许多经文中严厉斥责那样的行为。
这也是为什么先知会让他的一些同伴去监督市场,防止欺诈发生。有趣的是,据报告,这些监察者之一,是一个名叫萨姆拉·本·努哈伊克·阿萨迪亚(Samra bint Nuhayk al-Asadiyya)的女人——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它说明在伊斯兰早期,女性在公共生活中地位显赫。几十年后,哈里发欧麦尔也派一个名叫希法·本·阿卜杜·阿拉(al-Shifa bint Abd Allah)的女人和三个男人一起监察麦地那的市场。
在伊斯兰的第一个世纪,这些市场监察员被称为“市场工作者”(عَامِل السوق , aamil al-suq),或“市场的监督者”。在穆斯林西班牙,他们也被称作“市场的所有者”(صاحب السوق, sahib al-suq)或“市场主”。科尔多巴学者叶海亚·伊本·欧麦尔(Yahya ibn Umar, d. 901)是这样描述他们的功能的:他们“维持市场的有序运行,特别是在度量衡方面”。重要的是,他没有提到任何宗教监管。
但不久之后,后一个功能也出现了。就像历史学家阿巴斯·哈姆达尼(Abbas Hamdani)观察到的那样,虽然“以先前市场主的身份,市场监察员主要考虑的是物质方面,而非精神方面的东西”,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在9世纪末的时候,我们发现,人们开始把市场监察员的职位看成宗教职位,如今,监察员被称为问责者,即清点人们的善恶行为并绳之以法的人。”
历史学家亚辛·艾希德(Yassine Essid)也注意到问责者的这个双重功能,他写道:
在阅读专门讨论问责的不同论文的时候,我们发现两类责任,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发现面对的是两个形象:一个是砸坏乐器、倒掉酒、殴打放荡的人、扯下其丝质衣服的道德审查者;另一个则是控制度量衡、监察市场上出售的食物质量、确保市场供应良好的行为收敛的市场管理员。
随着时间的推移,宗教监管甚至变成了问责者的主要职责,而市场监督则变得微不足道。在逊尼派传统的顶尖学者之一伊玛目艾布·哈米德·安萨里影响力巨大的《圣学复苏》中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点。安萨里用整整一章来讨论问责,他把问责定义为“为真主的权利阻止恶行以确保被阻止的人不犯罪”。因此,一切被认为有罪的行为,从喝酒到不礼拜都会被针对。安萨里提议“直接”惩罚这样的行为,比如说“砸坏乐器、打翻酒、扯下丝质衣服”。
安萨里还论证了“对宗教创新(指异端)问责”的合法性。事实上,这甚至“比对其他所有恶行的问责还要重要”。
简言之,一开始,在穆圣那里,问责只有有限的市场监察功能,直到很晚的时候,问责才变成全方位的宗教强迫——不仅针对不虔诚,也针对异端。
可宗教强迫不也侵犯了伊斯兰的一种重要价值,一种像安萨里本人那样的虔诚学者也珍视的价值,即崇拜行为背后的真心吗?比如说,要是人们只是因为害怕问责者,而不是出于对真主的敬畏才礼拜,那么,礼拜又有什么价值呢?而如果对异端的压迫是合法的,那这不是会给穆斯林带来无穷无尽的冲突——因为此之“异端”恰是彼之正信——吗?
看起来,在伊斯兰文明的古典时代人们很少提出这样的问题。不过还是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强迫的问题。
其中之一便是奥斯曼哈乃斐-苏菲学者阿卜杜拉·哈尼·纳卜西(Abd al-Ghani al-Babulsi, d. 1731)。伊斯坦布尔的卡迪扎德里运动(Kadizadeli movement)让他深受困扰,这个狂热的宗教团体在17世纪的奥斯曼社会中制造了很多骚乱。这些人受著名的罕百里派学者伊本·泰米叶影响,是信仰上的纯粹派,他们把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怪到伊斯兰内部的“创新”头上,比如说,使用宗教音乐的苏菲道团、像哲学和数学那样的“理性学问”,以及像当时流行的喝咖啡和吸烟那样的被认为是社会恶习的东西。卡迪扎德里派甚至一度影响了苏丹穆拉德四世,后者抄了伊斯坦布尔所有的咖啡馆并处死了吸食烟草的人,更不用说喝酒的人了。(讽刺的是,穆拉德四世本人就是一个酒鬼,他27岁就死于肝硬化。)到17世纪晚期的时候,卡迪扎德里派的好战性有所下降,但没有完全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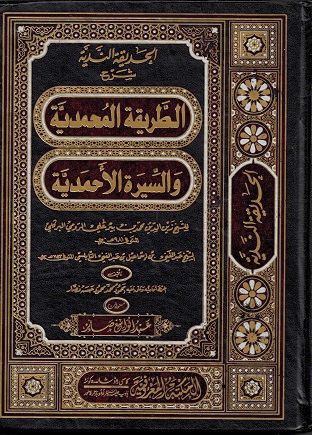
纳卜西在《露水润泽的花园》(al-Hadiqa al-Nadiyya)中耐心地反驳了这些纯粹派。首先,他反对把“劝善戒恶”和在安萨里之后变成标准看法的问责混为一谈。在纳卜西看来,劝善戒恶的义务只是“口头上的”,不需要真去落实。反过来,至于别人听不听,那是他们的选择,因为“宗教无强迫”。根据库克,纳卜西可能是第一个引用古兰2:256来反对伊斯兰中的强迫的人。传统上,人们引用这段经文只是为了说明没有必要强迫犹太人、基督徒或其他人皈依伊斯兰。
纳卜西还在一封信中提到一段经常被搞宗教强迫的人轻视的经文:“你们当保持自身的纯正。当你们遵守正道的时候,别人的迷误,不能损害你们。”(5:105)。纳卜西认为,古兰教导我们,与评判他人相反,穆斯林更应该把时间花在审视自己的灵魂上。
纳卜西还解构了卡迪扎德里派表面上的虔诚。根据库克的转述,他认为,他们那种狂热分子之所以要去劝戒别人,是“因为他们渴望一场自我的旅行,或者说,他们把劝戒别人看作在社会中建立权力和支配地位或吸引重要人物注意的一种方式。”换言之,他们所谓的正义不过是自以为是。

另一位奥斯曼学者,著名的博学者卡蒂普·柴勒比(Katip Çelebi, d. 1657)也考察过卡迪扎德里派的好战性,他看得甚至更加深入,并且不吝惜文字来反对它。在《真理的平衡》(Mîzânü’l-Hak)中,他写道:
我们最高贵的先知对待自己的共同体是友善而慷慨的。后世傲慢的人看不到与先知背道而驰的可耻,出于微不足道的理由,给自己共同体的成员贴上否信者、异端、放荡者的标签。他们使人陷入狂信的悲惨境地,引起不和。普通人哪里知道这些规则和条件;他们以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劝善戒恶,他们争吵而固执己见。他们像石头一样油盐不进。他们参与的这些毫无根据的争论,有时会导致流血事件。穆斯林之间的争斗与不和大多就出于这个原因。
今天,在差不多四个世纪之后,读到柴勒比的这段犀利的批评让人眼前一亮。可喜,也可悲,因为今天“穆斯林之间的争斗与不和”也依然“大多出于这个原因”,也即宗教上的狂热与强迫。从西非到东南亚的各种伊斯兰政权或政党,直到今天都还在互斗、与世俗的势力斗个没完,为的,不过是以自己定义的狭隘方式来“劝善戒恶”。同时,他们又很难让任何人变得更加有信仰或更加虔诚,如果那真是他们的目标的话。相反,就像今天我们在伊朗、在被他们逼着戴头巾的女人轻蔑地烧掉的头巾上看到的那样,他们只会让人失去对伊斯兰的尊重。
如此,我相信,伊斯兰文明的出路在于把“劝善戒恶”和宗教强迫分开。当然,在任何社会中,人们都会强制性地“劝导”一些东西(如做生意时的诚信)、“戒止”一些东西(如偷窃、谋杀或压迫)。从它们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常识这个角度来看,这些东西就是严格意义上的“善”。但人们怎样信仰和崇拜神,只关乎他们自己的良心,所以这些事情也就应该留给他们私人的头脑来自由地决定。
虽然这种论证听起来可能像是巨大的“创新”,但它却牢牢地扎根于对古兰“劝善戒恶”义务的最早诠释,并且事实上和问责的原义是一致的。它也以纳卜西正确解释的那句古兰箴言“宗教无强迫”为依据。以正确的方式来理解,这句箴言的意思是,宗教中确实不应该有强迫。人们应该在自己真诚的信念和自由的选择的基础上,自由地实践、或不实践它。
[1] 这条圣训被认为是弱的圣训,参见https://islamciv.com/2019/09/11/weak-hadith-you-must-listen-to-the-amir-and-carry-out-his-orders-even-if-your-back-is-flogged-and-your-wealth-is-snatched/。——译注
[2] 关于杰斐逊与古兰,参见Denise Spellberg, Thomas Jefferson’s Qur’an: Islam and the Founders, Vintage, 2014.——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