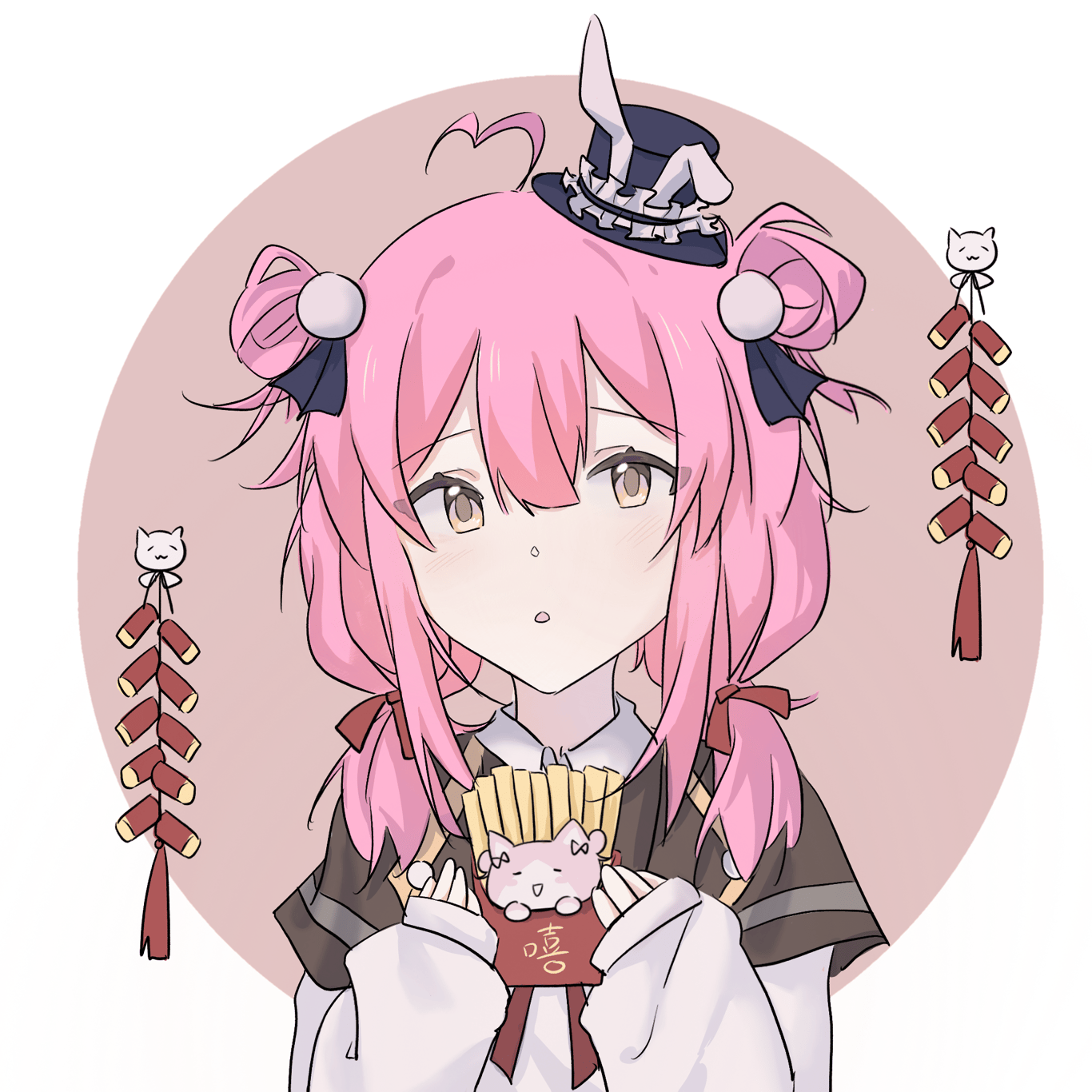主权的僭政
主权尽管在通常印象里是没有界限的绝对权力,但是距离其真正的完全实行似乎相差一段距离。早在博丹对主权作出最初的定义时,就已经指出了主权权力内部的空缺所在:在博丹的论述中,主权权力虽然是“绝对”且“永久”的,但是一旦到了具体实行时,不仅要受制于自然法,还要受制于与臣民的契约。如果我们读过博丹对主权的论述的话,不难发现这里的差距在于主权的所属和实行之间的差距。博丹在第一句就将主权的所属归于国家,而不是具有人格属性的主权者("Sovereignty is the absolute and perpetual power of a Common-wealth......a government with sovereign power, of several households and of that which they have in common" Bodin, Ch.8)
从这个意义上,其实自博丹开始,主权就从来不是君主自有的,而已经是被授予的了。霍布斯部分继承了这个观点,并把主权的来源描述为人民为了避免内战,摆脱自然状态,故相互之间订立契约将权力授予主权者。按照这个逻辑,在人民订立契约后,但又没有正式把权力授予给主权者之前,人民作为一个集体,已经把权力聚集在一块,按卢梭的话说就是形成了共同的意志,并将权力授予了主权者,否则何来这一授予的步骤?但是,人民此时又不可能拥有主权,因为这样被授予权力者就不可能成为主权者,而要么是一个官僚,要么是一个代表;但根据实践来看,主权者拥有的权力确实是主权无疑,因为它事实上掌握了生杀大权,且不用为任何事物负责。而博丹对主权的界定,此时看来更像是古典政治哲学最后一丝苍白无力的反抗。虽然解答了博丹对主权权力的限制问题,但是博丹对主权的定义仍然如幽灵一般回响:主权是不可转让的绝对权力。可在博丹自己和霍布斯的文本中,都能看到主权被授予和转让的痕迹。
但如果灵巧一点说,主权在此处与其说被转让或授予,不如说是主权进行了一次僭越,我们似乎能看到:原属于人民和国家的某种高于主权的权力在此处被主权篡夺并废黜。为避免论述的混乱,我们就仅限于霍布斯的语境来讨论这个问题。人民在订立契约的那一刻作为共同体所拥有的不是主权,换句话说,主权并非由人民一方转移到了主权者一方。因为如果这样,主权者只能成为代表和官员,即不真正拥有主权也没有充分行使他的力量。那么在此时就存在着两种可能,一是如我们先前所猜测的,是主权权力完成了一次对那更高权力的篡夺;二是人民所拥有的更高权力是一种临时性权力,它的作用是使主权权力生效,在此之后便弃置自身。
事实上,这两种可能性并不矛盾。看到第二种可能性是,我们已经有了呼之欲出的想法:这权力正是制宪权。但是,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于现代国家体制,以至于我们默认制宪权就应该是临时的。如果我们回顾最经典的西哀士关于制宪权的论述,我们是无法得出这一结论的;相反,根据西哀士关于国民和宪法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很显然作为制宪主体的国民和制宪权力是持续在场的,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问题:如果制宪主体在宪法制定后已经不存在了,制宪权力也消失了,那又何必再去论证制宪主体和宪法的关系呢?要知道,《第三等级是什么?》是一部言简意赅的小册子,为了起到宣传效果,是绝不会说任何无意义的废话的。
这样一来,我们做出的两种假设就可以串起来了:人民在相互订立契约的那一刻,作为共同体拥有了制宪权力,并通过这份权力设立了主权,但是主权通过某种方式废黜了制宪权力,使得自己成为唯一在场的权力。
不过这样的论述有一点让人质疑,那就是制宪权力究竟有没有能力设立主权。制宪权力的悖论在于,虽然它某种程度上是高于主权的,但它唯一的产出,即宪法,是无法锚定主权归谁所有的这个问题的。主权必须以人格性的方式显现,因为主权要么归一人所有,要么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拥有,而我们业已排除了共同体拥有主权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主权即不是宪法所赋予的,也不是制宪权力设立的,它唯一的来源似乎就是虚无;换句话说,主权权力并不承载一种正当性,在一开始和宪法也并无关联,用本雅明的话来讲就是一种纯粹的暴力。这和承载共同体公意的制宪权不仅不是一种事物,甚至可以说两股相反的力量。主权自创造之初就是虚无,和法秩序毫不相干;而此时制宪权力的产出也仅仅是一种对人民生活的简单规范,甚至只是一种大家共同认可的准则,正如《圣经》所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做。”(士师记17:6)
主权对制宪权力的废黜可以源自军事征服,军事政变或者共同体内部出现的紧急状态,用西哀士的话,“当国民还能做到时,它不应该将自己置于人为形式的束缚之中。这样便会使自己面临永远丧失自由的危险,因为专制制度只要一时得逞,便可以宪法为借口,置人民于某种组织形式之下,于是他们就再也不能摆脱专制枷锁了。”
无论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常设的制宪权力消失了,但是作为其产物的宪法仍然保留着。在此处,主权使法律获得了效力。但就关于人民制宪权的论述而言,法律就是公意,即国民的共同意志,那么何须再借用效力使其生效呢?再退一步讲,制宪主体怎么会受自己的法律约束呢?所以所谓法律效力其实仅仅是主权的效力,如果我们按照经典的启蒙思想家的理路而言,法律本身是不需要所谓效力的,仅仅就它作为公意的性质发挥作用。也许,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中描述的启蒙时代立法者对惩罚手段的设想和现实中实践的差距正是法律和法律效力偏差的体现:在其中,以规训和治理为目的的旧监狱战胜了立法者们想象的为共同体利益设立的惩罚之城。
由此,我们也能看出卡尔•施密特对于人民制宪权现实的误读在哪里,在《宪法学说》第十章,施密特说:“只要存在着制宪权,就总是存在着最低限度的宪法......即人们预设了制宪权主体的这种恒久性。”这也许是基于对西哀士《第三等级是什么?》的一种忠实解读,但是施密特却没有注意到制宪权主体在制宪活动结束后事实上的失能和制宪权力事实上的消散,而将其设置为持续在场的权力,并且或多或少地将其等同为主权,或者将其作为为主权独裁辩护的工具。施密特法学功底深厚,如此解读与其说是误读,不如说是有意为之。但无论如何,这种误读消解了制宪权力和主权不可化约的根本性矛盾,从而事实上助长了主权权力。
因此法律效力也就成为了自相矛盾的语词,法律效力的背后是纯粹的主权暴力,而这是排除了法律的。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阿道夫•艾希曼如呓语般重复“元首的话具有法律效力”,因为法律效力并不依托于法存在,哪怕当时德意志国的实证法已经被废除,但希特勒的言语依然具有法律效力。因为希特勒所代表的正是根本上是纯粹虚无的主权暴力,而这只有在当下实证法被悬置或事实上废除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此时的德国已经舍弃了一切法和法的形式,它仿佛是大可汗的牧群,仿佛大酋长手下的部落,又像是一个蜂巢。纳粹主义带来的劫难之所以是空前的,除了病态的工具理性指导以外,还有就是希特勒通过主权暴力对国民的完全掌控。如阿伦特所说,它“要求良知的声音告诉每个人‘你可以杀人’”。
这也就呼应了本雅明与施密特论战中的核心部分,即主权者究竟能否决断例外状态。显然本雅明的想法更有道理,主权者对例外状态的任何决断都不可避免地导致例外这个概念本身事实上失去意义,因为任何以保卫宪法为名义的独裁都会转入实质上废除法律的主权独裁,那么此时不论是规范还是例外都失去了他们本体论上的意义。主权者唯一能做的,也仅仅就是悬置/废除法律,并赋予法律效力。
面对主权独裁,任何反抗显得苍白无力,除非我们能够重新引入制宪权力。主权独裁最致命的弱点是,它虽然因为纯粹暴力的存在形式握有生杀大权,但也废除了他与正当支配的最后一丝联系。这样一来,这也为革命提供了可能。然而此处的辩证法在于,革命即需要承载正当性和制宪权,又只能以与法律完全无关甚至相冲的纯粹暴力显现。调和这二者的矛盾是一个政治难题,为此,苏维埃作为一种常设制宪机构,作为制宪主体的代表和一般的行政机构并列,也许是对这个难题的一个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