泄露:中国庞大的警察数据库——数百万泄漏的警察档案详细记录了对中国维吾尔族人口的监视(下)
原始文章来源于theintercept.com,由iyouport.org翻译为汉文。本文从iyouport.org原篇转载,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文章分为五部分,分别为:大规模监控;乌鲁木齐公安局的中央储存;从检查点到在线聊天监控;超级警务系统;基于不确信性的拘留系统。由于matters单篇文章的字数限制,本次转载将文章分为上、下两篇。
“超级警务系统”
新疆的无情监视是该地区镇压环境中最容易理解的部分。而更难研究和理解的是(特别是对国外的人权团体来说)它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推动执法。事实证明,新疆的治安强度与监控的超强攻击性相匹配:紧密结合,无孔不入。intercept 获得的数据库揭示了一个深具侵犯性的警察国家的证据,监视人们的想法和热情,进入他们的家庭,干扰他们的日常行动,甚至在完全合法的活动中寻找 “犯罪”。
该地区的当局用一种独特的方法指挥调查和其他警务工作,一位专家在研究了该数据库的部分内容后,把这种方法称为 “超级警务” — — 对任何异常行为进行打击。所使用的战术是全方位的,涉及到民警大队、家访和频繁的检查站。虽然这项工作涉及面很广,但也是根据人们认为的危险性来进行的。各类少数群体 — — 无论是语言、宗教还是种族少数群体 — — 都受到不成比例的巡逻监视。
对使用自己语言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歧视,是新疆治安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许多被拘留者和前被拘留者被称为 “三类人”。这一标签的使用非常随意,指的是所谓的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其严重程度分为三个等级,根据政府对他们的心态和造成伤害的可能性的看法进行排序。被拘留者和前被拘留者的亲属也被警方贴上标签,进行 ”危险性“ 排名和追踪。另一个系统将人分为值得信任、正常或不值得信任。
警方的分类和排名隐含着对少数群体的关注,但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关注是明确的。例如,社区维稳会议记录显示,这些会议特别把重点放在 “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人” 身上,这些人受到的监视比讲汉语的回族穆斯林更强。这些会议还主要关注维吾尔族被拘留者的亲属。
维吾尔族人在信奉伊斯兰教的过程中也受到了警察的监视。文件显示,警方有时会对参加某座清真寺的每个人进行安全检查。
事实上,政府严格控制谁被允许进入清真寺。一份警方文件详细描述了一起事件,三名学生试图去清真寺参加一位朋友的父亲葬礼。正如 Byler 所描述的那样,这三名学生 “只是在入口处徘徊,试图找到走进去的方法,因为他们必须扫描身份证才能进去,但他们担心(前门检查站)会联系警察,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警方对这些学生进行了询问,将他们扣留了几个小时,并将他们列入了学校的观察名单,“尽管他们解释了他们想要做的一切”,Byler 说。
最近的报道显示,当局设定了一个降低清真寺出席率的目标,并且达到了这个目标。许多警方文件都提到清真寺的出席率降低了,有些文件明确地将此描述为 “表明成功”。一份报告显示,在一个清真寺,四个月内的总访问量比前一年同期减少了8万人次:减少了96%以上。这似乎部分是由于一位阿訇的离去和清真寺的暂时关闭,但该报告指出,两年来 “宗教信徒急剧减少”。报告还说,部分原因是游客离开了该市,一些人被送往拘留营,或害怕信奉伊斯兰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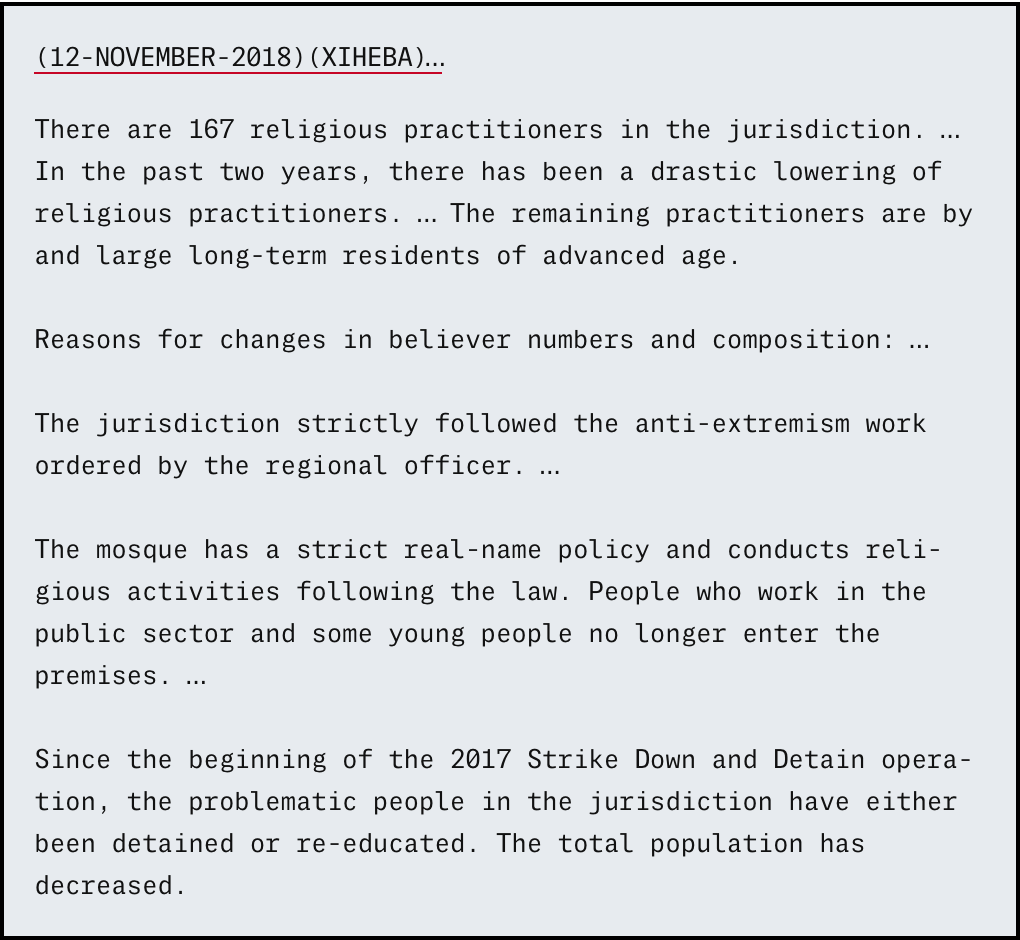
阿尤普说,中国政府认为是极端主义迹象的清真寺活动,可以包括在没有戴维吾尔族花帽的情况下祈祷、在清真寺内涂抹香水,甚至在祈祷时放松。他说,任何在祈祷后不赞美中共的人也会被认为是可疑的。
Byler 说:“有趣的是,他们把公民描述为敌人,这让人明白,他们把这看作是一种反叛乱,其实他们只是想检测谁信奉伊斯兰教与否”。
来自威虎梁一个派出所的笔记描述了一场 “大规模的调查 …… 集中在流动人口聚集的地区”,集中在以维吾尔族为主的新疆南部地区的人。该笔记说,一周内警方已登记605名来自南疆的人,调查其中383人及其同住人员。在同样的排查中,当局检查了367部手机和9台电脑。
新疆当局对伊斯兰教的治安管理特别热衷于追捕 “野阿訇” 或 ”非法传教”。这些术语指的是那些工作不受中国政府认可的伊斯兰传教士;维权组织说,中国当局任意划定这条法律界线,是为了政治需要。这些阿訇可以因为在网上和清真寺中发表的布道而被起诉。
威虎梁派出所的说明列出了60名涉及所谓非法传教的人员,其中50人被拘留。同一份文件称,微信群 “群1教(古兰经ABC)” 中的 “非法传教” 导致一名41岁的回族妇女被抓获,一名62岁的回族男子被行政拘留。
最近的文件,从2017年到2019年,反映出警方越来越难以继续找到违法行为来执行,也越来越难以把人关进拘留所或再教育营。因为在2017年,第一波拘留潮席卷新疆,导致大部分人口被驱逐出乌鲁木齐。新疆党领袖陈全国告诉官员,“把该围捕的人都围捕起来”,延续了习近平在2014年火车站发生大规模刺杀事件和用汽车和爆炸物袭击户外市场后开始组织的强硬做法。
这一时期的警方文件,在第一波镇压之后,反映出对任何形式的可疑行为的追捕意图。
“这个系统的设置方式正在产生超级警务” ,Byler 说,“任何奇怪的或任何一种异常的行为都会被举报,如果你是少数民族,这是他们对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的称呼,那么你就非常容易受到这种东西的影响,你正在被微观层面的警戒,无论是人的警戒还是技术对你和你的生活的密切监视。”
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在法律还没有制定之前,就因为违反法律而遭受迫害。
一份警方文件描述了回族妇女是如何被拘留的,因为有证据表明她们在一个在线群组里学习了《古兰经》 — — 在她们做这件事的时候是合法的,但在她们被拘留之前就变成了非法的。在被拘留之前,她们至少有一年时间没有参加过该群组的活动。
新疆法律的这种不确定性,以及什么时候可能会触犯警察的不确定性,与阿尤普的经历相呼应。他解释说:“人们被逮捕后,就会发现 ‘哦,原来那个(活动)被认为很危险’”。

新疆治安如何变得越来越激进和无处不在的一个例证是,一份警方报告讨论了一家饺子店的一把刀如何没有按照规定拴在安全的柱子上。该报告说,需要在一天内纠正这种违规行为。文件显示,新疆的法律不仅要求用铁链锁住刀具,而且刀具也要有二维码识别其主人的身份。“这只是一种方式,说明一切都控制得很严密,即使是做饭用的菜刀,也要被认为是潜在的武器”,Byler 说。
为了保持 “超级警务” 所带来的最大限度的警戒,新疆当局征集普通公民互相监视 — — 这在中国并不是闻所未闻,但在该地区却被更广泛地实践,尤其是针对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
为了帮助实现这一点,公民之间的相互举报会得到奖励。数据库中的文件包含了这一以前报道过的事实的一些细节。举报者因向警察传递信息而获得奖励,但人们也会因更具体的行动而获得奖励。比如链接自己的微信账号、通过身份验证、发布某些图片都可以获得现金奖励。所有这些都会被追踪并反映在该数据库中。
一份来自警方的公告文件显示,警察和辅警人员面临向当局提交大量情报的压力。这份文件责备乌鲁木齐市新市辖区内的高新区市民提交的情报,“只是为了让举报数量看起来很大而制造的填充物,无法使用,而且占用了大量的人力和时间来处理”。比如,某楼的 “居民举报经常有小孩在电梯里小便”;又如,“有少数市民反映,在网上买螃蟹或月饼时被骗。被骗的金额一般不大”。
随后,该公告又大篇幅地详述了10条 “禁止举报的各类情报”,其中包括与 “反恐政策、少数民族政策” 无关的情报线索,或者与所谓的 “新疆管理纲要” 无关的线索,或者与 “惠民政策” 无关的线索……
基本上,正如 Byler 所说,当局 “就像是直接在说,‘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情报,我们要的是关于穆斯林的情报’” 。
阿尤普在新疆生活时,10个家庭组成的小组每周都要在反馈箱中举报某人一次,这在应用之前就已经存在了。“问题是,如果找不到可以写的东西,就得补写,以免被送到再教育营。这是义务。这就是问题所在,但你不能因为这是义务而责怪举报的人”,他说。

除了单独起草普通公民举报邻居的政策外,新疆当局还通过被称为 “安全单位” 或 “大队” 的更正式的社区团体来组织这些人。根据数据库中的文件,这些单位被划分为10个小组。例如,10户人家或10家企业可能被组织成一个大队,每个小组有一名志愿者像紧急医疗技术员一样响应呼叫,并进行 “反恐” 演习。

安全大队这种东西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传统,即 所谓的保甲制度,10户为 “甲”,10甲为 “保”。这种分形结构形成了一种社会稳控体系,并与治安和民众的军事化有很大的关系。
在现代,类似的制度被冠以 “网格化管理” 的名字。几年前,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这种网格化管理,但新疆的网格单位密度仍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那里的稳控单位用途不同。
Byler 说,新疆稳控单位在以前的政府文件中没有出现过,但如果你在该地区,就会看到各种演习、人们列队行进、企业主佩戴红袖章以示归属,这一点非常明显。
“这是整个人口的军事化”,Byler 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完整的描述它应该做什么。”
超级警务还通过当局的定期访问深入到人们的家中;那些被认为有可能受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或分裂主义影响的人也会经常接受这种家访。这通常意味着维吾尔族人、持不同政见者、经历过再教育营的人,以及与这些人有关的任何人。
社区稳控会议的会议记录详细介绍了这些家访中记录的信息类型。其中包括职业、工作地点、以前的工作、亲属(以及亲属的国民身份证号码)、出行情况、子女所在地、子女就读的学校,以及社区仍在监控的内容。
有些居民被讨论为受到社区的监控或控制;也就是说,社区会派一个邻里守望单位来监控他们。这可能包括住在附近的一名或多名干部成员每天或每周一到两次的家访。
当地警察每天都会探望一些被拘留者的亲属。即使是那些被认为值得信赖的人,也会被家访,“向他们表示温暖,把他们拉进中国的爱国阵营” ,正如 Byler 所说,“搞得就像赢得人心那样” 。
在一份警方文件的描述中,一位儿子被当局关押的老妇人与探望她的警察交好。警方称,这名老妇人对这名警官来说已经像母亲一样。她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一样对待,并公开了她儿子的所有实际活动。文件显示,她是 “通过“ 系统再教育的理想类型。
有些家访是为了检查和寻找宗教物品。文件显示,警方搜索宗教书籍,并拿走祈祷垫,甚至如2018年7月警方文件中提到的那样,一张朝觐的照片,即 穆斯林到沙特麦加朝圣的照片。文件显示,这项工作源于2018年,与政府一项名为 “三清” 的举措有关,该举措旨在鼓励人们从家中清除被认为是极端主义的材料。“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明确提到的关于他们正在检查人们的家庭”,Byler 说。
2018年10月的一份文件描述了这些家庭检查是如何展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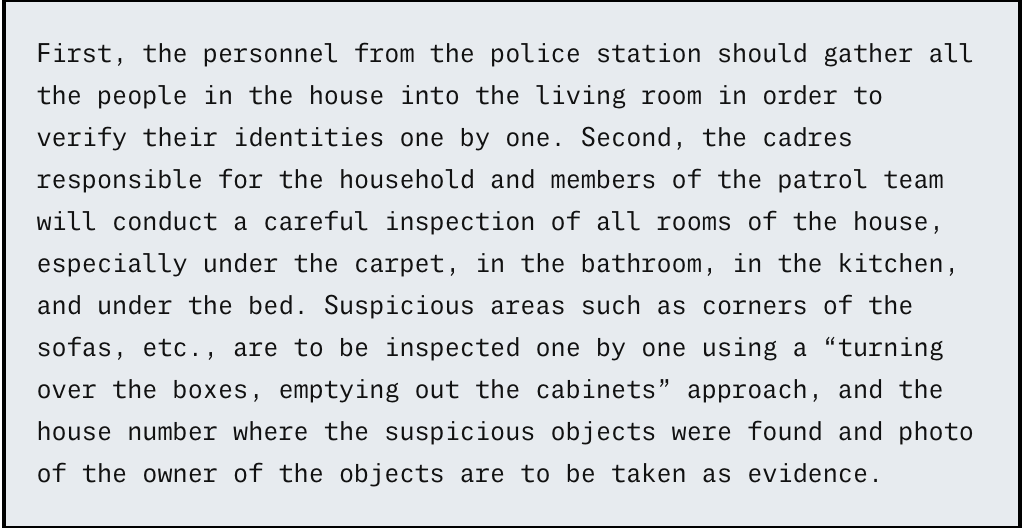
当局还监控被拘留者与其家人之间的电话通话。有一份文件详细记录了这样一个持续4分20秒的电话,描述了谈话内容,以及亲属对政府允许这样做的感激。“这是一个拐点,记录了人们是如何接受再教育的”,Byler 解释说。“如果他们因为亲属不能被释放而哭泣或表现得很生气,那就说明还没有成功接受再教育。”
在许多情况下,亲属被要求记录他们的电话并与警方分享,或者在电话通话后警方立即和他们会谈,以了解他们在电话通话后的情况。
新疆的公民也经常被当局拦在家门口。该数据库包含了两年内乌鲁木齐(人口350万)及周边地区200多万次检查站拦截的记录。其中包括 “情报国家安全重要人员” 等近三十类人员的拦截名单。当一个人在检查站被拦下时,会经过身份检查,通常包括通过面部识别。面部识别有时是通过固定的监控摄像头自动扫描进行的。它也可以通过使用智能手机摄像头进行手动扫描;这些通常用于被认为需要近距离面部扫描的额外的受审人员,例如,因为他们没带身份证。如果一个人的脸部被扫描后在电脑上显示出黄色、橙色或红色的指示信号,表明系统认为其可疑或犯罪,则会对其进行盘问,并可能会被逮捕。

经常在检查站被拦截的人员类别包括罪犯的亲属和被拘留者的亲属。
从这些拦截中保留的数据包括被拦截者的照片、拦截地点的经纬度、数据收集点的名称、车辆和车牌(如适用)、搜查时间、搜查级别、该人是否被释放以及搜查结果。被拦截的人在数据库中被分为立即被逮捕的人、被送回原住地的人、精神病患者、被拘留者的亲属、罪犯的亲属,以及被列为2009年7月乌鲁木齐骚乱参与者的人,在那次骚乱中,维吾尔族和汉族在中国东南部一家玩具厂的暴力事件导致了更广泛的内乱,其中包括对主要是汉族居民的攻击。

基于不确定性的拘留系统
除了监视和维稳之外,该数据库还提供了一个近距离观察关于各种形式的监禁如何被用来控制人口、特别是新疆的少数群体和被认为持不同政见的人。它揭示了一个正在努力调整其言论和政策以适应现实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即使是打着 “培训” 或 “再教育” 的幌子,监禁的时间长短也往往是如此地不确定,以至于当被拘留者被判处有期徒刑时,被监禁者的亲属都会感激不尽。
这些文件说明了新疆复杂的类似监狱的制度,大致可分为四类:临时拘留;“再教育” ;一种被称为 “职业培训” 的较宽松的再教育形式;以及长期监禁。
拘留中心据说条件最艰苦,最拥挤,基本上是审讯和监禁的设施。人们被关在那里,等待调查结束。再教育设施的正式名称是 “教育改造” 营。曾利用政府文件调查过这些营地的 Zenz 说,它们实行的是 “高度强制的洗脑”。那些培训中心据称是为了传授职业技能和其他技能,但却明显像监狱,有铁丝网、高墙、瞭望塔和内部监视摄像系统。
一个公民以一种管道式的方式经历多种类型的监禁是很常见的。乌鲁木齐天山区警方的一份文件描述了一位卷入 “国家安全事件” 的母亲被送进再教育营,然后被送进职业培训学校。
再教育是通过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部门进行的,这是一支侦查跨国犯罪的国内治安部队。这是个 “非常强硬的单位”,经常用来对付异见人士,Zenz 说,“我完全料到那是一个实施酷刑的地方,却无法肯定这点”,他补充说。
当局随后将那位母亲送到职业培训中心,本来 “还是有很多不愉快和胁迫”,Zenz 说,但 “是相对最宽松的了”,并最终导致被释放后继续强迫劳动。“在警察国家,这是最理想的地方,因为你最终能出来”,他说。这类所谓的职业培训中心有别于中国现有的真正的职业培训中心,后者不涉及强迫滞留,而前者,人们会从家中被带走并接受灌输。

2017年在比利时获得庇护的维吾尔族人 Nejmiddin Qarluq 说,拘留的原因并不总是很清楚,因为人们经常被随便逮捕,财产被没收。在 Qarluq 6岁的时候他的父亲被从监狱中释放出来。他自己被判处三年监禁,然后又服了五年半的刑期。他说,他的一个兄弟在1996年被判处无期徒刑,另一个兄弟被判处6年半监禁,现在还在监狱里。他的哥哥、前妻和妹妹在2018年被关进了再教育营。
因为 Qarluq 在14岁的时候就被判刑了,他说,他出狱后的整个生活都在中共警察的监控之下,他根本就没有安全感。而且,他说,在国家的控制下,没有任何自由和隐私,甚至连思想的隐私都没有。
这个数据库中的证据表明,与再教育相比,被拘留率可能远高于外界观察者的看法。这就意味着维吾尔族人和其他人在被关押期间忍受着明显更恶劣的条件。
一份来自威虎梁分局的警方报告提供了整个水磨沟(乌鲁木齐七区之一)被关押和接受再教育的人数信息。当时,2018年2月,该区有803人被再教育,被拘留的人数也差不多,约787人。具体到威虎梁,在押人员的比例更高:在押348人、再教育184人。
Byler 称这是 “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比例,如果我们把这看作是整个地区的常态的话 ”。
“这向我们表明,几乎一半的被拘留者甚至都还没有进入再教育系统,他们只是在接受处理”,Byler 补充道。“这些空间的条件真的很糟糕。如果这些报告告诉我们的是真的,如此多人被关押在这些空间里,真的令人担忧。”
Byler 描述说,拘留营经常 “非常拥挤,根据我们从人们那里听到的消息,由于人满为患,里面的条件非常糟糕 …… 人们有时因为拥挤,不能同时睡觉,因为不能同时躺下来(床其实是一个平台,上面有一块木板,叫 ‘炕’ )。小区里的摄像头不停地监视着,灯光整夜不灭。
相比之下,再教育营的条件要好一些,包括有更大的内院可以活动或教学,更重要的是,有可能被释放的希望 — — 只要 “转化” 教育完成。但数据库中的文件表明,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是一个错误的期待。在100多起案件中,文件里讨论了固定期限的再教育刑罚,如两年或三年的刑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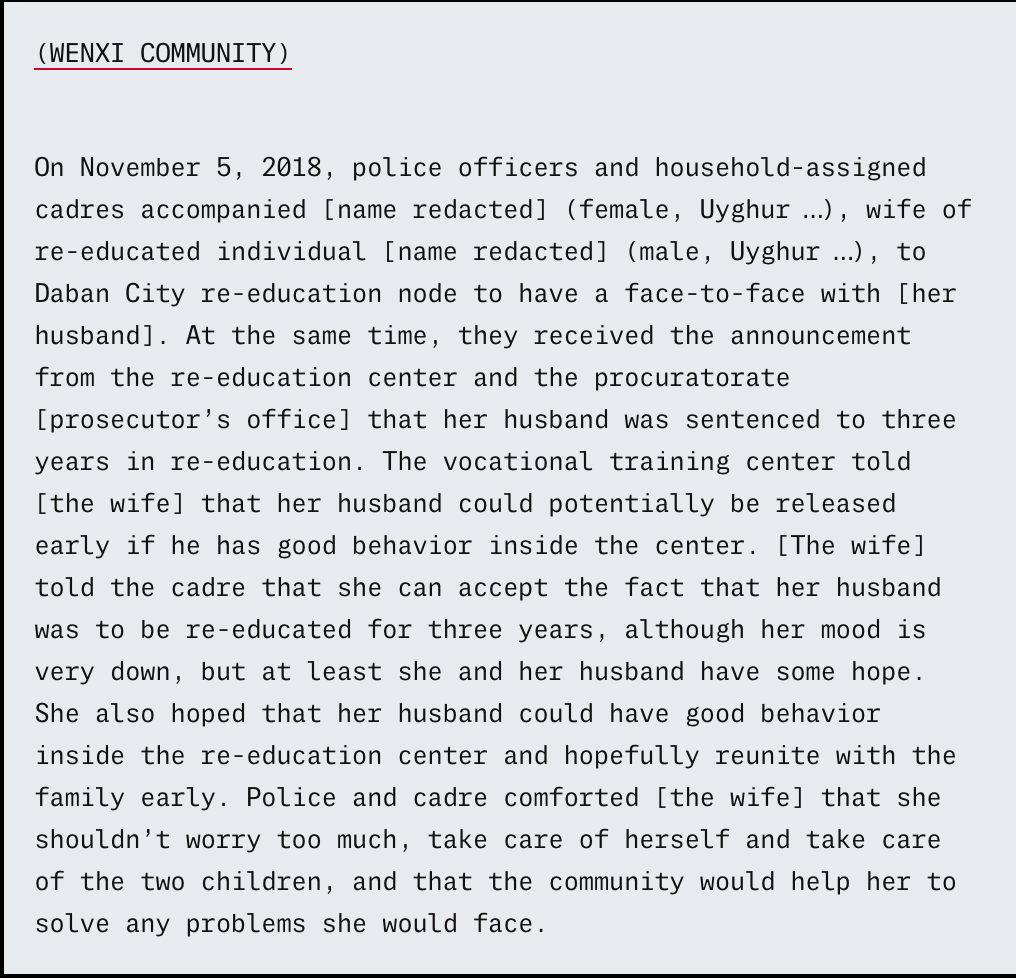
这些判决似乎是以职业再教育的形式分配给那些人的,往往是在他们被长期监禁之后。文件显示,他们是通过一个叫 “两告知、一倡导” 的方案来实现的,“告知” 显然是指关于极端主义的信息 (在再教育中提供的),“倡导” 是指倡导一种提供刑罚的政策。
在这一制度下,亲属和骨干成员通常会在再教育营中与当事人见面,由法官出具 “预判”,期限为2至4年。有时,某些要求也会伴随着判决,比如掌握汉语技能。2018年10月的一篇报道称,“一些三类人员的亲属在了解到 ‘两告知一倡导’ 工作后,非常高兴,因为这样,至少他们知道自己的亲属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出来,他们可以事先安排很多事”。
在该数据库中,作为这一政策的众多例子之一,来自2018年11月的报道显示,一名维吾尔族妇女与其弟弟一起前往达坂城的职教中心接受判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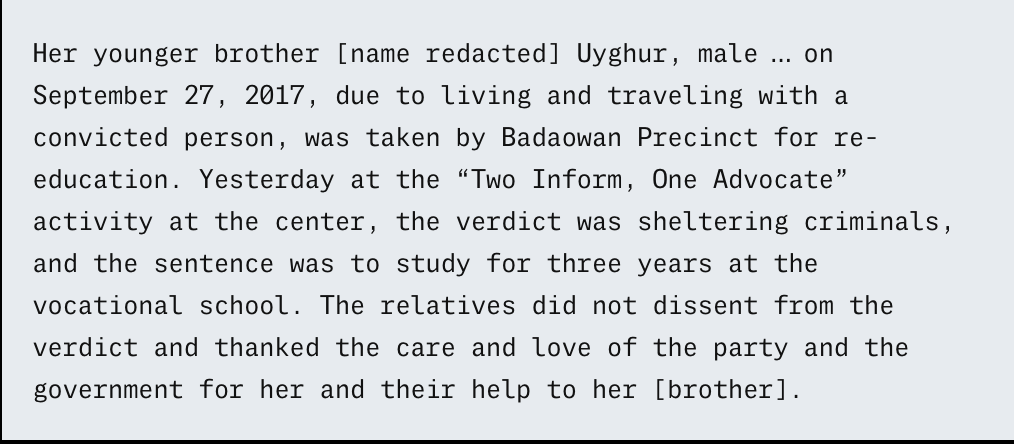
“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因为接受再教育而被判刑”,Byler 说。“他们告诉你,你必须赚取积分才能被释放,所以你应该非常努力地接受再教育,但现在他们说其实这些人已经被判刑了,他们的再教育课程需要三年或更长。所以其实就像坐牢一样。这就是这个制度的暴虐之一,一旦你进了集中营,你就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被释放。”
对于一些迫害最严重的活动,再教育似乎也被封闭起来,成为一种选择。威虎梁派出所记录到,对 “非法传教者” 的归宿,列出了50名在押人员,说只有两人在接受再教育。
Zenz 的大部分工作都集中在被官方描述为 “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 的拘留营。政府将其定位为对那些犯有轻罪的人进行管制的一种比较温和的替代方式,但它们往往是以轻微理由拘留的掩护。尽管强调 “培训” 一词,但这些设施可以像再教育营一样实行强制灌输。
Zenz 此前获得的政府文件曾这样描述再教育:用 Zenz 的叙述,对那些 “认识模糊、态度消极,甚至表现出抵触情绪” 的人,采用 “攻坚式的教育改造”,“确保取得效果”。
一份文件显示,乌鲁木齐七区之一的326名儿童的父母一方或双方都被关押。根据2010年的政府数据,该区人口约为43730人,但维吾尔族人口仅占乌鲁木齐总人口的12%左右。“如果你计算一下该[民族]的成年人口,并注意到有326名学生的父母中有一人或两人被拘留,这似乎是相当可观的”,Zenz 说。
这套文件可在此查阅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