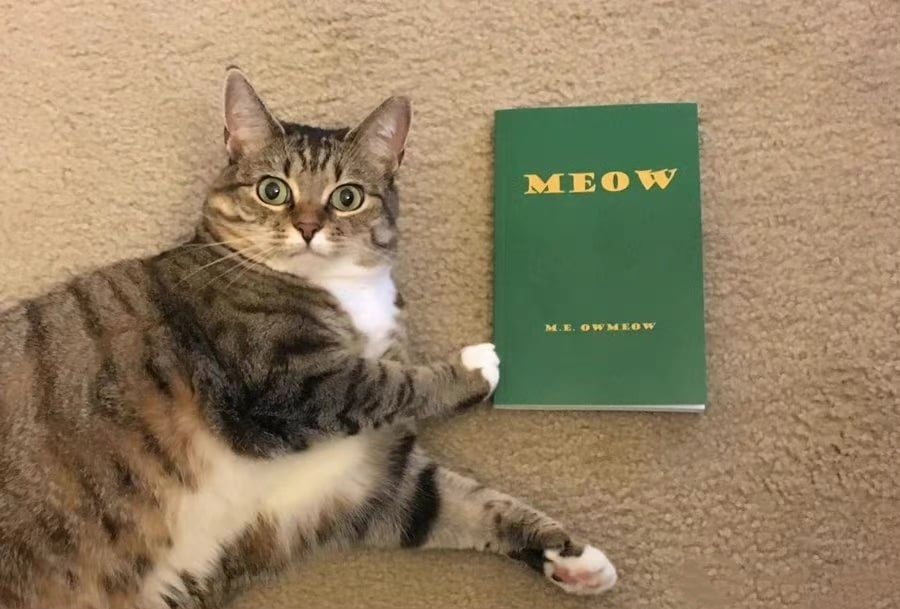【蜉蝣镇回忆录】远航
蜉蝣鎮每年到了春末,就有長達半個月的陰雨天氣。
在這半個月裏,只要在半困時閉上眼睛,不花錢買車票去沿海城市,就能在內陸小鎮體驗海邊生活——需要做的事情只是,摒棄一切腦海中對雨中小鎮的想象,雨聲會在困意的加持下逐漸變形成海浪聲。幸運的時候,家不遠的馬路上還會開過一輛鳴笛的貨運卡車,剎車的時候發出一陣低沈的嗚嗚聲。有了先前海浪聲營造的新場景,貨車在腦海裏就變成了海上遊輪。這是艘年邁的載客遊輪,它在臨行前會嗚嗚地響幾聲,預示它即將遠行,也告訴碼頭送別旅客的人們,該要拿出紙巾準備哭泣了。

你們千萬別覺得這樣的想象只是我們窮酸小鎮人因無錢出遊做出的無奈之舉,是自欺欺人。我要和你們說,小鎮人這麼做,並非出於旅行,而是出於一段過往。我們想象中的遊輪,載著的是許多小鎮人,他們中很多都已經做上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了。
這段過往體量龐大,且現有資料都零零散散,真假參半,所以要篩選出真相並把它說清楚,絕非易事。但我不得不在這回憶錄裏寫出,否則後續故事會因缺乏背景而無法交代明了。如果篇幅過於簡短,人就無法在短暫的閱讀時間裏體會和消化,寫作者自己也會為如此草率的書寫感到驚愕與失望。如果將組成它的巨量事件一一寫出,那我寫的就不是回憶錄,而是歷史書了,就連學者也會迷失在磚頭般交錯堆疊的文字記載裏,以致忘記現實生活其他要務。為了保證這篇交代清楚這段歷史的同時還具有可讀性,我將著眼於描繪它的主要部分,以及現今蜉蝣鎮人如何看待它。
*
早在幾十年前,小鎮發生了場近十年的火災。如果你們還記得,這就是上一篇裏把詩人祠堂燒毀的那場,鎮上每年的陰雨和邊界的河水都無法澆滅它。火災起因至今依舊是一個謎,據說有肇事者,但這說法無依無據,自然也無處追責。小鎮也不是全鎮起火,而是這簇滅了那簇緊接著又起。遭難之處,黑煙像鯨爆一般,裹著刺鼻臭氣四處翻滾、蔓延,尾部則被火焰尖端啃得像是一條條懸吊著的腐敗碎肉。要不是火災發生前後有些人帶著值錢家當出逃,還有些人奇跡般地挺過這十年幸存下來,搶救回一些物件並保存了些許神智,這場災難絕對會讓小鎮變成一座現代龐貝城,自然也沒有現在記錄小鎮的我了。
火災結束後的頭些日子裏,過往小鎮上的植被,被燒死的小鎮人和他們的生活碎片,大到車、家具,小到衣物和日記本,幾乎無一幸免,變作一大片一大片無法辨認原貌的焦黑,厚厚地覆蓋在原先的田地與道路上,綿延近萬平方公裏,像是創世之初毫無生氣的混沌之海。幸存者渾身皮膚連帶著衣物也都被熏得焦黑。他們眼神驚恐而呆滯,拿碎布片捂著口鼻,久久不敢放下,在布團後面悶聲咳嗽。還有人尚存力氣,就背負著被燒傷者淒厲的尖叫聲,在余煙裏四處跌撞著遊走。
頭幾年裏,這個小鎮的一片漆黑,無人清掃,無人修整,人們長期只是依靠外市的援助物資生活,住在廢墟上搭起的鐵皮屋裏,住在還未倒塌的焦黑房子裏。人們開始接受火災防護教育,在其中一次次被迫重溫那近十年種種場景。他們就是久久不肯重建家園,也不讓救援隊伍幫他們重建。外界一提及他們該加緊恢復過往生活,他們就倒進黑黑的地上打滾,讓自己一直保持著一身黑的樣子,以示拒絕。

人們從不應該怪罪當時小鎮人一蹶不振,更不能說小鎮人就是爛泥扶不上墻,因為很少有人經歷過這種量級的災難,自然很難理解這種災難裏人的心境。更何況那時候人普遍沒有意識去關註精神上的創傷(現在也好不到哪兒去),小鎮人自己也沒意識到自己的一具殘破焦黑的身體底下,精神也如此殘破焦黑。人對災難的接收,就像人耳接收聲音一般,都是有範圍的,無論對親歷者還是旁觀者來講,都是如此。
災難開始第一年的時候,小鎮在第一場火災後,頂著失去親友的悲傷,在接下來的大火裏互幫互助,跑去鄰裏,親戚家滅火救傷。到了第二年,人們自發組織成立了救援小組,由於物質緊缺,他們開始聯系外援,同時也哀悼喪生者,並計劃著災難結束以後如何重建。到了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人們對災難結束的期待一次次落空,嗓子也全哭啞了,眼睛都紅腫得像是被人暴揍一頓,卻還要捂著濕毛巾或布頭四處滅火、躲去沒被火舌吞噬、暫能歇腳的地方。這時候,人們夜裏看到一絲星光都以為是哪裏起了火星,條件反射式地抄起手邊的濕布捂住嘴貓起腰。有人看到真的火苗,也不逃了,火爬上全身也不喊疼痛,一心只想把自己燒死,而有人最終忍無可忍,沖出火海離開這個小鎮,到外地闖蕩。其他人卻沒有離開,或出於對小鎮的留戀,或因為實在無心力在鎮外開啟新生活,但也始終有極強烈的求生欲支撐著他們繼續活著。
這還是火災頭五年的小鎮人,我還沒有說後五年是什麼樣呢,那時外人永遠不能理解為什麼小鎮人當時頹喪到了這個程度。我們能聽下一些戰爭,天災,兇殺案,出於憤怒或者傷悲,去說些什麼、寫些什麼。但我們又無法接受另一些,因為它們或是持續時間過長,或是害人手段極盡殘忍,又或是兩因素兼具,完全超過了我們理解範圍,不要說對此有什麼感受或者用文字或鏡頭記錄什麼了,好像多在這樣的災難中體會一會兒,整個人都會搖搖欲墜,無法再在一個相對安穩的環境裏安心坐著。有一小部分人自己沒有親身經歷,卻把自己帶入進了災難裏,哪怕感受到一絲災民絕望,脆弱與無力,都已經被已經發生了的事情壓垮,或是終日郁郁寡歡,或是投身遭災地去為人做些什麼,這一小部分人已然活成了新一批遭難者,而非旁觀者,再也沒有離開蜉蝣鎮。更多人則是因為自己無法,或者更確切地,不敢理解傷痛而倍感自責與愧疚。
人常常不是擅長接受自責與愧疚的動物,我們習慣於將它們深深掩藏,或者剛有苗頭就掐斷。有些人開始組織無限期的悼念儀式,而有些人聽聞災難始末或悼念以後,立刻高調地把「感謝他人艱苦付出,把握當下美好生活」這話宣讀出,當作生活格言,以讓他們自己繼續保持平靜幸福,不受這些災難敘述的幹擾。他們不會在踐行格言上動搖,即便今後這樣的災難仍然可能發生在任何一個人身上,即便一些旁觀者甚至遭難者都表明這格言是一種輕蔑的冒犯。
然而,持有這格言的人似乎就是有意通過這種冒犯和他們保持距離的。他們私底下認為遭災人身上有種不好的能量,會影響他們現有的生活軌跡。這一類人表面上滿懷悲憫地接濟遭難者,實際上只是通過這樣的施舍來和他們更加劃清界限,「你們看,從身份上講,你們是被接濟的,留下一攤爛泥被後世人救贖的,而我們正是接濟者或者後世救贖人,我們不一樣,你要為你造成的麻煩道歉,也要對我感恩戴德」。(這裏有一點需要強調,我並不是說所有施救者都懷揣這樣的私念。)
那代小鎮人在精神上成了一片孤海。他們並沒有真正心安理得地接受幫助,相反一向極度敏感且察言觀色。在一次次被迫想起災難過往的痛苦中,人們早就意識到,有些關懷實際上加劇了他們災難記憶的反芻,也加固了許多外地人眼裏他們低微可憐受害者的形象。終於,小鎮人聲淚俱下地答完謝,就決定送走所有繼續給他們發放救濟物資的人,無論是出於本能的善良還是別有打算的,都心懷感恩地一一送走。人們並不是建立起了雄心壯誌去立馬重建小鎮,只是意識到自己不能再作為受災群眾出現在人們眼前,他們只想像原先一樣,做默默無聞的小鎮人。
小鎮人最後一隊救濟人走後,已經是黑夜,小鎮人紛紛走出住處,手拉著手,排成好多排,開始和地平線上升起的火災亡靈並肩遊走。在黑色的創世初之海上,一排排人與亡靈形成了一股股浪潮,他們不停地尋找岸,準確來說是堆成岸的堅硬礁石,找到了就一排接一排地將他們的腦袋朝著石棱撞去。他們要把自己撞得昏闕,夢想著醒來的時候能夠失憶。在他們看來,失去記憶也許是痛苦過往的最好歸宿,「過去的就讓它過去了,不要再回想了」,這樣他們才能假裝自己和災難發生前一般生活。
現在的我們當然很清楚,這個辦法大抵不能致使人失憶,但他們那時候並不知道。人都因撞擊受了傷,有些人傷勢過重離世,被後續報道成是「自縊」,只有一個人真的幸運地失憶了。之後人們就沒再看到他。據說他背著一個黑漆漆的麻袋,拉著一輛小推車不停地獨自朝北走,翻過了小鎮邊界的山,就再也沒看過他。
那些布滿血跡的石頭被收走了,小鎮變成了一個大療養院,剩下的人只好把渾身黑色和血跡擦掉,好好養病。這些日子裏他們躺在住處百無聊賴,打開全損音質、全損畫質的電視,兩三個電視臺來來回回翻。幾部看不膩的電視劇和文藝節目看了不知道多少遍,再去看看新聞。
直到有一天,新聞報道裏出現了一對中年夫妻,他們站在一家木製工藝品店門口。仔細一看,店裏都是大大小小的船舶模型。旁邊的攤上堆著小鎮人從沒見過的水果,身邊路過的也是人,可面孔和小鎮人和這對夫妻完全不一樣。再遠一點,穿過街市矮房不遠處有一簇稍微高一些的樓,樓能看見幾面就有幾種不同的眼色,亮眼而奇異,樓頂掛著一溜花紋布條在陽光底下的風中擺來擺去。再遠一些還有更多彩色墻壁的房子,層層疊疊沿著山坡往上堆。雖然排布得有些雜亂和擁擠,但整個街市是那種紛雜的有活力的美麗。小鎮人好久沒有見到一個街道能有這樣濃烈的生活氣息了,也從來沒有設想過這個世界有這樣的街市。在電視機那種糟糕的畫質裏,街市的色彩更加炫目,也更讓人震撼。
正在看這個節目的一戶小鎮人突然開始大叫,鄰居從他的破鐵皮安置裏跑出來去看他出了什麼事。他看了看電視機屏幕,過了一會也開始跟著大叫——這不就是之前住在他倆家同一棟樓的那對夫妻嗎!這時,這對夫妻齊聲開口說話:「我們這家工藝品店開了有一段時間了,你們知道蜉蝣鎮嗎?不知道,那蜉蝣鎮大火災你們總聽過吧,我們就來自這個蜉蝣鎮...」轉過頭,他們和一個路過的人用小鎮人從沒聽過的語言交流,過了一會這個路過人就付了錢,抱著一艘小木船模型滿意地離開了。
噢,熟悉的鄉音,他們沒在騙人。那場火災裏他們是最早逃離小鎮的人家之一。原本他們就打算在鎮上熬到災難結束,雖然他們未曾設想會熬多久。促使他們突然做這個決定的是他們的小孩。那天小孩準備逃出時被絆倒,他們的屋頂上落下了帶著火的不知什麼東西,重重地砸向他的背。夫妻及時發現了小孩,把他托起逃到了室外。火撲滅了,小孩不省人事,所幸他們住在小鎮邊界的河邊,那天他們帶著小孩搭上路過的船只連夜逃去了另外一個城市。小孩神奇地活了下來,只是背從此都是向後仰著折成一個角度。
「我們到了一個新地方,也碰到了同樣出逃的同鄉人。」回憶著回憶著,那個折了背的小孩走了出來,夫妻做完那筆生意繼續轉向鏡頭,「那裏人和我們說著差不多的話。這是我們的兒子。那邊人看到我們小孩,他們都會好奇他怎麼了。實在是解釋累了。」
鏡頭切換到他們的小孩,他已經長大了很多,背還是向後折著,坐在搖椅上一言不發。他拿起一艘木船,撥弄起船頂上那一小面帆布旗子。過了一會兒他膩煩了,又動作僵硬地把它放在旁邊用地磚砌出的方形小水池上。
「那裏人嚇小孩的時候總說,『你再不聽話爸爸媽媽就不從地球另一邊回來看你嘍!』地球那一邊是什麼?我們沒上過幾年學,火災之前也沒出過小鎮,怎麼知道地球另一邊是什麼,同鄉人也都不知道。我們邊在那裏打工掙錢,邊打聽那個鎮一些男人女人都去了哪兒。有天小孩回家的時候給了我們一張皺巴巴的紙,說這是他同學從家裏某張桌子上順來的船票。他還說,那個同學的爸爸上一次回家的時候,給他講了一段很陌生的話,那個男人告訴他,這是在地球另一邊學會的新語言。噢,那時候我們才想起到那個海濱城市那麼久,住在離海邊非常遠的地方,竟然都還沒找時間去看海。」
對於內陸小鎮人來說,海邊是一個夢境都難以到達的地方,所以那家人決定去海邊逛逛的那刻一定對大海很期待吧。那家人走到海邊泊船口,就看到眼前一艘高大的客輪擋掉了大半片視線裏的海和天空。有人往船上走,有人背著船走,還有人跟著上船的人走,走到登船口就停下。那幾個人堵在窄窄的梯子上,後面的人從皺眉到不耐煩嘟囔,再到大聲警告前面趕緊讓路。突然船上的船員打了一個手勢,人就慢慢開始退,有的退下梯子,有的退上船身。梯子在一陣鳴笛聲裏嗚嗚地收起。
這家人看著船慢吞吞地吐出之前侵占的海與天,拿著那張舊船票,吃力地念著船票上的字,念出聲......噢,這一頭的名字就是這個城市的名字,船票另一頭的那個地方可能就是這艘船的終點吧。
那次海邊散步的體驗,讓他們繼逃離火災蜉蝣鎮之後又做出了新的大決定,去「地球另一邊」看看!就去這張船票上寫的地方。「人們總是關心我們兒子,知道蜉蝣鎮的事以後總是有人想要采訪我們,要我們講述那段時間的事。如果去了地球另一邊,是不是沒人過問了呢?反正那邊人問起,我們也聽不懂他們說什麼。我倆就是做木匠學徒的時候認識的,說不定在那裏可以靠手藝活掙錢。要是能在那裏住下,我們是不是就有新生活了?」
這家人一定是有一股不執行想法就不罷休的勁頭,剛想到這裏,他們立刻開始計劃出行,四處打聽怎麼辦護照辦簽證,各種流程,直到出行前一天還在忙活焦慮,從行李到各種身份資料確認上無數遍,生怕遺漏什麼。
場景又回到開頭我們小鎮人雨天幻想裏的樣子——這家人離開的那天,同鄉人給他們送行,海浪聲呼啦啦地,像小鎮下雨一樣,鳴笛聲像是開過的運貨卡車,意味著客輪即將出發,道別的時候到了,同鄉人退到岸口,抄起袖口就拿來擦眼淚,根本顧不上嵌進袖口布紋裏的灰塵。那家人在船上的日子裏如何度過,也不可得知,他們節目也不說。只知道後來他們真的後來在船票上那個目的地開了自己的店,只賣自己做的船舶模型,有了新的生活。
這則報道馬上就在小鎮人之間傳開了。鎮上也沒多少人仔細看,於是看了的人就把那家人的遠航故事說給他們聽,順帶著描述了鏡頭裏那個色彩豐富的街市。故事越傳越離譜,到後來甚至有人聽成了那是天上的城市,那家人在那裏生活自足。再加上那座沿海城市的小鎮人也跟著那家人出去了一些,又回來了一些,回來的那波人又和小鎮人講了新的人物故事,一些小鎮人越聽越來勁。噢,這幾年在這裏也是各種重建,我們也沒有幫忙的份,生活馬上要窮困潦倒,不如也出去做點小生意,或者在外面發展自己的手藝吧。
從那時起,小鎮好多人就開始有了開頭那樣的設想。雨天聽著雨聲,這想象的航海場景尤為生動。「大家都要過日子的嘛,這有什麼辦法?有出路總得試試,你說是吧。」他們說。這種念想讓人們紛紛惜別頹喪的日子,一些人留在這裏重建,另一些人打算暫別家人,去那個口口相傳的奇地,在那裏掙到錢又來養活這邊的家人。人們從蜉蝣鎮跑到其他城市,坐上船,告別,又在岸上等人回來,一段時間以後又告別,再等人回來。臨別人們哭一次,下次回來再笑著哭一次,每次哭完又假裝什麼事都沒發生地繼續生活。
不久以後,小鎮人們從浪花變成神話裏的小鳥,匆匆忙忙地叼起岸邊的石子和貝殼去填上這片黑漆漆的原始之海。後來,石頭與貝殼地又馬上有了土,有土就有新的植被和新的樓宇。
小鎮人突然就從停滯哀傷的狀態到掙紮著起身,以人難以理解的速度重建,而這時好多外鄉人甚至還沒從對小鎮人遠遠觀望的憐憫之心中走出來。外鄉人都說,他們可能是真的忘了那個災難的十年,「走出來了」。他們想,或許壓垮人的從來都不是災難,多恐怖的都不是,是人自己,人要是一蹶不振了,那必定是意誌出了問題,小鎮人找回了自己的意誌。他們都講小鎮人是沒有精神創傷的,他們自己也絕不承認。不信你看啊,要是問他們之前的事情,他們都面無表情地搖搖頭不說,扭頭就走。這點我也有所見聞,那個住在下坡路附近的老人不也是我一再央求才和我說那個詩人傳說麼。這在好多小鎮人眼裏,就是「忘記了,放下了」的最佳體現。
小鎮人其實很少提及那火災,本地也鮮有文字形式的記載資料。後來那些在異國闖蕩的人年紀大了,還有些人預感自己所剩時日不多,便依照著小鎮傳統趕緊回來度過余生。他們也不提及大火的事情。唯獨做船舶模型的那家人在外面定了居,大概在小鎮他們無所牽掛,所以再沒有回來。

*
我還是中學生的時候,歷史教材裏也不是沒提過這場火災,只是課本上的內容完全是由外地人寫的,不過當時我們都覺得寫得不賴。他們並不著重寫火災規模和傷亡人數,而是非常生動地描繪了救援隊的規模,小鎮人組織救援的情況,旁邊還有一個淺紅色的小方框裏面寫上一些非常感人的事跡,最後結語曰:救援隊是無私奉獻的,而小鎮人是頑強不屈的,我們可貴而高尚的精神在這場大火裏沒有被燒毀。這樣一看,編課本的人確確實實對具體人有強烈的關懷。與此同時他們也是有極強的共情能力的,在寫救火場景時,他們甚至把人們的心理活動寫得如此詳盡,讓我們一眾學生嘆為觀止——果然我們就是沒心沒肺的一代人啊,竟看不懂幾張模模糊糊的照片裏人臉透露出的心路歷程。
一般來講,小鎮這破地方是登不上歷史課本的,所以上這節課的時候,大家幾乎都很興奮,噢,這本書裏竟然寫了我們蜉蝣鎮,還褒獎了那代小鎮人,原來我們鎮上的祖輩那麼偉大。回家裏我們好多就和長輩分享了這節課的見聞。長輩們聽到以後也沒再補充火災相關的細節,而是馬上和我們說了他們的父母輩遠航的故事。他們說小鎮人天生經商頭腦,勤勞又聰明,去哪都能紮根生長,希望我們長大以後也要延續這優良的精神傳統。
後面的內容我們哪想聽呢,我們這些小孩看不得別人太努力,因為每到這時候,我們總要私底下自慚形穢,但又沒臉直接表露對自己懶惰性子的悔罪。我們真正感興趣的,當然是航海呀。我們的祖輩不僅那麼多次登上巨大的客輪,還去了那麼遠的地方。怪不得我們的前輩總是對我們這麼失望。和他們比起來,我們這些人,成年幾載了還庸庸碌碌,甚至還有不少我這種生病就在家裏休養、不去馬上帶病工作的人。按他們的話說,祖輩人是用自己的青壯年走出蜉蝣鎮,從創世初始為起點開拓了一片宇宙,我們的父母輩努力維護了這片宇宙,而我們這些人,或是過早地在厚望與無法實現厚望的自責中耗盡了出航的燃料(這是對於年輕人來說是相當絕望的悲劇),或是用過剩的燃料點起一簇火,把這片宇宙壓進熱縮片裏,用火冒上來的熱浪烘烤它,把它縮成一片小掛件,掛在書包上,惹人妒忌。
說回那節歷史課,回家聽到了祖輩遠航故事的我們第二天到學校,等到放學就開始交流自己家的航行故事,還有一個同學拿了一張她祖父母登船前拍的合影。那天我和朋友們看看窗外,雨好像停了。其中一位看到那張老照片,興奮地拍起桌子,全然忘記自己的桌面板已經和桌體分離。桌面板「啪」地一聲翻到地上,撿起幾滴水花。
記不清楚我們這些小孩裏誰先註意到了桌板落地的場景,突然和航海故事聯系了起來,把桌板想成了一艘小船,供我們滿足遠航的念想。印象裏後來的事情就是,我們幾個人,有的也拔起了自己的桌板,有的從教室後面抄起靠在墻上的桌板。我們各自抱著桌板子沖出教室,跑到樓下操場。
噢,這裏有一點需要補充說明:我們那所中學的操場非常大,跑道環繞的中間由一層薄薄的土鋪在焦黑遺跡上,因為當時預算不夠,就沒有澆水泥鋪塑膠。中間比四周跑道矮了一些,一到雨天它就會變成一個水池子,起霧的時候你會錯認為這是一片看不見邊際的湖泊,再展開想象,還可以當成是海。那時的我們這幾個抱著桌板的學生就設想,這是一片海。
我們把桌板放到這片「大海」上,桌板完全和水面貼合的那一刻,我們就心想,完啦,闖禍了!我們一會還得扛著這堆濕木板回教室呢!可是這種闖禍的罪惡感絲毫不敵模仿遠航祖輩的興致,我們紛紛把自己手上的桌板都擱在水面上,桌板連成歪歪扭扭的一排,以很小的幅度晃晃悠悠。其中一位朋友用手往前把桌板往前推,可能用力過猛,桌板踉踉蹌蹌地往前跑,竟然滑到了離我們小腿長的地方。
「跨上去!跨上去!」我們對她喊。她毫不猶豫地踩了上去......當然是連著桌板和鞋子陷進了水裏。她毫不在意,直接把腳跨出桌板,伸進水窪裏作滑滑板的動作。我們也紛紛加入了,鞋子全都沈進了水裏,完啦,又闖了一個禍!我們一會還得拖著一雙雙濕鞋子回家呢!
我們那會好像感覺自己也和祖輩一樣實現了遠航的壯舉,雖然我們遠不及記載裏和父母輩講的的他們一般勤勞又意誌強。在那片橢圓形的「海面」上,我們離岸越來越遠,又離對面越來越近,四周車開過的聲音,人群走路說話的聲音和薄薄的霧混在一起,變成了海浪的聲音,學校外一輛車鳴笛,「岸上」的同學看著回頭的我們尖叫,而我們朝他們大喊:「我們都是要遠行的人了,以後會回來看你們的,多保重,莫為我們流淚!」我們唱起小時候長輩教我們唱的臨別歌謠,他們也配合著我們發出哭泣的聲音。
這是現實裏我們實踐小鎮的雨天幻想。
那時我們做這樣的模仿也不純粹是出於戲仿,而是假戲真做,把自己扔回了那段祖輩奮鬥的歷史,那扮演過程中,我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也可以有一種崇高使命,好像只有我們是這些先輩的後裔,就自然會在今後某個時候繼續他們的遠航事業。這場扮演有這樣的效果是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總之我們收獲頗豐,包括因桌板和鞋子又臟又濕而招致的各種責罵。
我們接受的對那段歷程的教育,似乎就這樣讓我們那時幼小的心靈免遭一段悲切歷史的創擊,我們無法想象他們花費了多少心思才想出這樣保護我們的辦法。什麼小孩子能接受那樣無邊無盡的災難書寫呢?不用知道肇事者為何人(甚至是不是人都不重要),也不用知道祖輩為何遠航,以及遠航前日日夜夜做的準備與掙紮,也不用知道我們父母輩告別自己父母以及等祖輩回家時落了多少升眼淚,這些都不重要,連他們自己都一筆帶過。我們就更無需操心了,不是嗎?
其實也是有人操心的。我們後來又扮演了好多次遠航人,繼續拿著桌板跑去操場。這遊戲又好玩又能滿足自己那虛妄的光榮使命,何樂而不為。但突然有一次,那位率先拿桌板劃船的朋友宣布退出這場遊戲。我和她是中學時期極要好的朋友,我被這突然的決定感到震驚。
「你為什麼不玩這個遊戲了,上次下雨的時候你不是還玩得很開心嗎?」我問道。
「我發現了些東西,如果你想聽的話我和你說!」
她是一個對歷史有濃烈興趣,有敏銳洞察力且富有探索欲的人。她和我說,她在一次次遊戲中對出航歷程人的執著精神越來越神往,又想到出航前的那段火災記敘極少,逐漸起了好奇心。她就那場火災開始入手找資料,一遍遍地問長輩,直到發現那段火災竟然持續那麼久,損失如此慘重。為什麼人們都不提呢?人們說,過去的就讓它們過去好了,都不重要了。
沒多久後的小長假,我又和她一起去外地遊玩,逛資料館,偶然間看到展櫃裏一張小小的照片,旁邊字寫著「蜉蝣鎮火災救援隊隨隊記者xxx,攝於xxxx年xx月xx日」,看到那模糊老舊的照片裏那一團黑煙下一攤黑廢墟,記起來,那剛好是先前電視節目裏在異國賣船舶模型那家人逃出蜉蝣鎮的年份。再看看我們的祖輩,他們緘口不言的同時,不是在不久之後莫名暴躁,就是搬起凳子獨自坐到門口呆滯地曬太陽,一坐就是大半天。還有很多變成了我們眼中的怪老人。他們確是有出海經歷,後來也大多回來了,可是這樣的他們和我們書上講的那些富有開拓精神意誌頑強的祖輩,還有課本插畫裏眼神堅毅的祖輩,又是同一批人,我們的腦袋實在是沒有辦法想通。
這樣的疑惑讓她沒心思繼續那場扮演出海的遊戲,我也跟著沒有辦法繼續。我們扮演的時候的劇本,好像不是背井離鄉出海討生活的劇本,而是更古早的,航海家開辟新大陸的劇本,或者出海四處征戰的劇本。
但大家畢竟都是朋友,每次遊戲我們倆雙雙如此決絕地退出實在不夠意思。我們也不想把這種疑惑再傳給他們,反正他們想探索的自然已經和我們一樣去探索了。於是我們倆商議,要不我們就從此就演在「岸上」告別他們的人吧。
我們初中畢業的時候又一次玩了這個遊戲。那年夏天某場暴雨又把操場中央變成一片大海。我們站在跑道那個岸上,他們再次把桌板放到水面上。在他們踏上征程的那一刻,鳴笛聲又響起。然而,我們倆卻絲毫沒感覺到他們在移動,反倒是我們感覺自己在不停地,飄飄悠悠地遠離他們。我們的腦袋暈乎乎的,我們想,這應該是很常見的暈船反應......
一陣暈眩中,我們看見,他們向我們揮手。畢業之際,我們都清楚,這位朋友要去外地上高中,這位和那位不再同學校,還有最右邊那位,遊戲玩完第二天就要離開蜉蝣鎮,去另外一座城市開始提前批錄取生的高中課程了。我倆卻巧合一般地去處一樣,我們在戲裏才是去地球另一邊的人一般,他們面對著我們,和不斷遠離的我們道別,高高地揮起手,帶著哭腔和我們說再見。
我們那個模仿祖輩遠航的遊戲,就這樣保留在了少年記憶裏。
現在想來,有可能蜉蝣鎮才是這個星球的中心,我們這些朋友,從中心出發,分成兩撥,分別駛向相反的方向。在某個時間裏,分別載著我們的兩艘客輪的鳴笛聲響起,我們互相道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