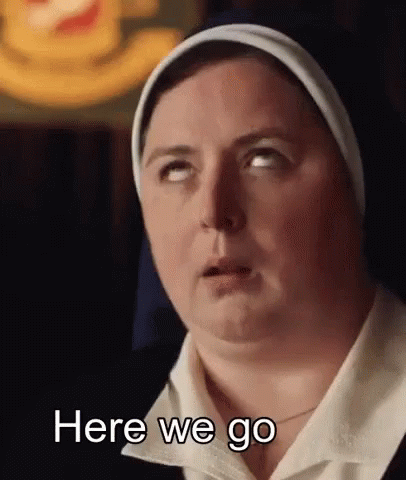春夜
我家楼下的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樱花树,另一棵还是樱花树。
居家多日,那天偶然往窗外一探,惊喜地发现院子里白色的樱花已开了满枝,沉甸甸地往外探。风把花瓣扬起来,零落了一些在空中,便是春日里的一场雪。

往年的这个时候我肯定要找个公园赏樱的。Brunswick centre对面那条小路上也有好几株樱花树,粉的白的,在咖啡馆和书店的门口。去学校有时候会走那条路,无论经过都少次都忍不住拿出手机拍拍拍。
不能出门赏樱,在院子里看看也是很好的,况且家楼下就有樱花,多浪漫。我抄起一件外套就冲下楼。阳光看着暖得很,但一阵风就把这暖意给吹散了。我在风中凌乱,顾不得整理被吹上天的头发,举起手机一通拍。眼角往家的方向一瞥,看到面团的圆脸从窗口探出来,他也举个手机,在偷拍我。
于是这几天,到窗边看看樱花成了每日必备,一天不看就感觉缺了点什么。下楼倒垃圾、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也会在树下多站一会儿。惦记樱花的心情有点像我惦记给十字包涂上黄油,要涂厚厚一层、覆盖满所有角落,没有樱花的一天就是一小块没有黄油的面包皮。

依旧每天写论文,做饭,画画,吐槽,一边维护日常里的琐碎,一边应付着每个微小时刻的天人交战。跟几个朋友聊天,真的感觉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片自己的战场。一早接到X的短信,说是因为在社交网络上提到几个名字,有司找上了家人,要求对X进行教育。类似的事情早已屡见不鲜,波及的范围也越来越近,从某个遥远的未曾听过的名字,到圈子里听说过的某个学者,到身边的人。我忍不住骂了几句,但也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安慰X。不再能清晰地表达观点,也无法准确地诉说情感,到现在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办法好好说。有时我真恨自己。
三三说刚提了离职,她被之前那份工作折腾得心力交瘁。三三一直很能干,很早就坐上管理岗。记得当时她外派去东南亚,几乎从零开始建立一个新的部门,好不容易熬过初创时的种种混乱无头绪,又因各种原因跳槽了。三三喜欢旅游,一个人去过很多地方。她说最怀念在印度做义工的日子,很累但是简单充实。又说刚拼完一副一千片的拼图,接下来打算学学绣花。聊起舆论环境,她让我在伦敦好好待着,“在国内学者会很难受”。我说学者就算了,八成也是毕业就失业,看看能不能把画的小画印个帆布包啥的,卖卖义乌小商品讨生活。然后我们都想起各自大学时代的理想生活,她想当潜水教练,我想开间甜品店。“为什么要鄙视安逸的生活呢?为什么一定要成功呢?能安稳地活着就是最好的啊。”
在剑桥的艾玛说同一栋楼的舍友有了疑似症状,她自己也被搅得心神不宁。还有一个刚去法国旅游回来的舍友说楼里的几个人都迟早会感染上,但这不是坏事,因为感染了之后大家就免疫了。我一边安慰艾玛,一边自己也哭笑不得。转头又和另一个朋友说起这件事,聊到最后我们都觉得可能知识也救不了人类,牛剑清北又何如?“人类不行”,共识达成。
但即便末日明天就到来又怎样呢?我们还是会怀揣一些愤怒、孤独与执念直到最后一刻。昨天为N号门的事情生气很久,转而又看到这事儿引发了男性是否可以为被普遍指责而感到委屈的大讨论。我倒是又谈不上愤怒了,只是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隔膜。成为女权主义者,或许不只意味着要抵抗那些早已堂而皇之的贬损和剥削,还要抵抗渗透到生活最脆弱柔软角落里的孤独感。
研究女性和疼痛有几年了,最深的感触是这种根植于女性本体的痛苦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话题,是一种现实,是每分每秒的经历,甚至痛苦就是本体本身。要一边应对这种现实又要将它当作一个“议题”去研究带给我强烈的撕裂感,因为这要求你将主体经验剥离出来,把它当作一个客体去审视。而这些痛苦其实太复杂,有时也很难归类,可能更恰当的说法是,一种无能为力的恐惧、委屈、狂怒、被忽视与游移不定。
确实我们都说男性在当前的性别结构之下也是“受害者”,但他们承受的苦痛相比女性还是九牛一毛。所谓认识到男性在父权社会之下所受的伤害,更像是女权主义的一个campaign,一种“统战”的方式,但在现实层面其实没有那么多标的物。支持平权光靠“观念”上的理解其实很软弱,仅承认“观念”本身很容易就会滑入对复杂实体的忽视。跨越本体的局限性,需要共情也需要想象力。坐稳性别红利的安全感把很多男性的这种想象力抹平,这很悲哀。但有些人根本不愿去想象,这又是另一回事。成为“男性女权主义者”哪有那么轻巧。一个女性要觉醒与抗争都尚且要经历一番痛苦的自我革命,何况是在整个体系里被资源倾斜被眷顾的那一方。
有时会跟面团聊这些话题。面团无论从哪个层面上说都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男性伴侣,我还记得让我对他好感大增的是刚认识没多久时,一次闲谈他说的一句话:All the societies are patriarchal (现行所有社会都是父权的)。我丝毫不怀疑他会在女同事遭遇职场性骚扰时站出来声援,也绝对相信他不会把母职与生育付出当作理所当然。但当问及他是否是feminist的时候,他依旧会轻描淡写地回答,“I don't need a tag to treat people equally(我不需要标签也会平等待人).” 女权主义者的身份,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标签,但对女性来说,是无数次自我怀疑、斗争、推翻之后脱胎换骨获得重生的身份,它代表的解放与自由意义太深重了。
面团当然没有做错什么,男性身份也不是他的原罪。我只是失落于一份自己无法获得的、全然的安全感,这让我有时难以压抑自己的愤怒。在挑选住所的时候,他会觉得离地铁站十五到二十分钟的距离并不远,我说如果是我的话,一定会选离地铁站步行十分钟以内的地方。十五分钟的路途在夜归的时候也会变得山长水远,走夜路回家时的恐惧感不是你能体会的。
“我可以去接你啊。”
“这跟我说的没关系。你有试过对什么事情感到恐惧吗?你会觉得自己身处的世界有很多恶意跟危险吗?你有觉得自己脆弱不堪的时候吗?”
我可能会一直记得那次争执的结果吧。面团撅着嘴皱着眉,五官皱成一团,倒不像委屈,而是一种试图理解但无法体验的干着急。最后他说,“……我自己一个人晚归的时候是不会害怕,可是你晚一点回家的时候,我会很害怕。”
女性的诉说让人感到尴尬,可能是因为有太多混沌模糊的东西,就连我们自己也无法确定“值不值得说”。一点点的不适,一点点的慌张,都只是一点点。有什么好提吗?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一直以来“值得说的”,都是一套父权的价值体系规定的,而我们所有的叙述,都要以那一套价值为参照。不小心声音大了一点,还有人嫌吵闹。
其实大多数的日常叙事,都不是在控诉什么,只是一种忠于自身的记录,试图在信息洪流中抓住自己,建立一部绝对忠于自己的个人史。有没有读者,读者是谁,都不那么重要了。
想到那部韩剧,《春夜》。丁海寅和韩智敏在夜晚的樱花树下散步,亲密关系、人生、事业之类的事情,跟着两个人的深深浅浅的步子缓缓淌下去。我很喜欢这部剧,也喜欢李静仁这个角色。其实所谓生活里的顿悟和看透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瞬间,而是平淡的一部分。遇见喜欢的人,决定要不要结婚,跟谁结婚之类,都是平常事。李静仁的抗争就是那种平常而柔韧的抗争,有哭泣的怒吼的时候,那也是一种平常。于是我昨天惦记了一整天,晚上的时候,我要下楼看樱花。我也要一个这样子的春夜,有花作伴,让风拂过我心里的角落,不管是抚平还是吹出新的皱褶。
没有灯,但白色的花瓣还是泛起一层柔光。我生活的小小战场,会在看樱花的时候暂停,大自然的恒常终于让我脑海里的喧闹安静下来,一切都只是平常。风很凉,树梢轻轻摇晃。
这是一个真正的春夜。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