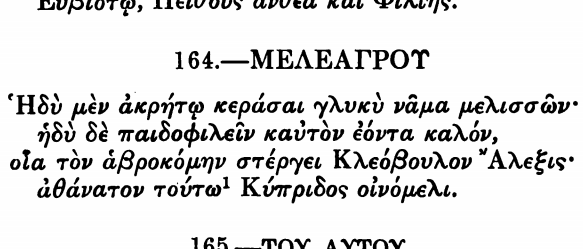(這是一篇小説)硬盤
可能會很長(大約一萬字),很無聊。可能看起來像是一篇政治小説,但我并非想要表達什麽政治諷喻,亦非對時事心懷憤恨蓄意陰陽怪氣。只不過我試圖將一件事挑明,那就是魔怔的人會以一種當下的方式去魔怔,但這并不代表這種魔怔就不是所謂“純净的魔怔”。另外也某種程度上作爲一個寫作練習,平心而論并沒有付出太多的思考和汗水,只是心血來潮想刻畫魔怔的精神狀態。本文所有人物和事件皆為虛構無現實原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正文
最後一節課下課之後二十分鐘,方曉聲來到地鐵站。
儘管一旦從少年時代畢業,就必須意識到自己的生日不過是一年三百多天中再普通不過的一天,卻少有人言及這種殘酷,以至於方曉聲在這種突如其來的不可見攻擊下整整一天都輕飄飄晃悠悠,起床上課吃飯都如同夢游。
因爲許香來約他在這見面,然後一起去吃餛飩。他反復確認和時間和地點,包括地鐵站的樓梯上面還是下面,但現在才想起沒確認出口的編號。按理説,如果許香來和他一個方向,基本可以斷定是向著大學的那一個,但她大部分時間都行蹤詭異,兩人基本沒有在校園碰面過。約定的時間已經過了快五分鐘,方曉聲猶豫著該不該給她去一個電話,滑開手機屏幕後卻又把手機收回了口袋,這種情況他往往只再等十五分鐘,如果對方不現身就將約定作廢。
許香來這個同齡女生作爲女朋友的好處,恐怕還是她所作所爲同樣讓人摸不着頭腦,例如對方圓十里的餛飩店的胡椒粉,辣油,蝦皮和榨菜免費添加情況瞭如指掌。古典學秋季讀書會每次例會解散后,兩人總去這家餛飩店,往碗中加適量辣油和榨菜然後大勺大勺地挖蝦皮加進去。還有一點就是許香來既喜獨來獨往,又熱衷對不熟的人怪話連篇,就像其他人哪怕知道她會聽到也自暴自棄式地議論她時説的,好好的女生整天陰陽怪氣,弱智一樣。
下課之後三十分鐘,許香來橫衝直撞地沿著樓梯扶手小跑下來。她拎著一個深藍色的不透明塑料袋,一路甩來甩去。
“這個給你。”她說,把塑料到提手往方曉聲手裏塞,“生日禮物,你今天生日。”
方曉聲拿起袋子,發現袋口被一截透明膠帶封著,他扯了兩下,透過側面的開口往裏看,“是什麽啊?”
“硬盤。”許香來邊大喘氣邊回答,“不是說外地人那個硬盤,硬盤,電腦的硬盤,你回去再拆,現在不好拿。”
確實,袋子中是一個棱角分明的方形物體,頗有些重量。
“要硬盤幹什麽?”
“保存東西喔。”許香來一副耐心不佳的口吻回答,“你不是說想截圖保存社交軟件動態嗎?這個有256GB,喏,可以一直存到你自殺那一天。”
“那還真是謝謝你了。”方曉聲把塑料袋挂在右腕上,隨即意識到袋子直接勒在肉上有點難受,又移到臂彎處。“吃飯去吧,這次我請。”
“你過生日讓你付錢不合適,而且反正就是餛飩。”許香來從褲子口袋裏掏出十幾個硬幣數了一下,然後全部丟進胸前的口袋。
“方曉聲,我們都到了死在廣場上的年齡,可以説是一條繩上的螞蚱了。”
“隨便你,你要是死了,你爸肯定會鬧到學校要勸退我,別害人。”
兩人若即若離地保持著前後步調,低頭衝著地鐵站的後街走去。
總之,許香來這種人就是不太應該和他一起出現在古典學研究會。可能是爲了和研究對象呼應,六七個人晚上在理工樓空教室讀Epinomis,這是柏拉圖的法律篇的一個小附錄,按理説也沒什麽好讀的。
“方曉聲,同學,欸。“
方曉聲生平最害怕別人在後面叫他,整個人過電似的一震,然後緩慢而僵硬地轉過頭。許香來就一邊猛吸了一口勺子裏紅彤彤的餛飩湯,邊被辣得嘶嘶吸氣邊口齒不清地招呼他,
“方曉聲?是你欸,剛才讀書會我離你一個座位。“
“啊,“她補充了一句,“你怎麽在抖啊?那個,你就是那個動態說Epinomis大半都是bullshit一學期讀它是腦子進水的人,對就是你。”
“我他媽的應該屏蔽你們了啊……”他當時不假思索地自言自語,許香來低頭吃餛飩,她左手按著胸口寬鬆的衣服,防止勺子沒舀住的餛飩掉進碗裏讓辣椒油濺到衣服。
方曉聲自小和別人相識的場面往往類似此類,但由於中文二十多頁的Epinomis而認識還真只有許香來,後者拒絕直接回答爲何參加讀書小組,并且連交往也是後者突然提出。
“反正又不是招人討厭的人……”
“啊?”兩三步遠的許香來以爲他向自己搭話,放慢脚步凑近對方。
“沒事,”方曉聲爲了掩飾不小心將思考内容説出口的尷尬急忙轉換話題,“走快點快到了,你還不餓啊?”
“什麽餓不餓,你要是真的餓那就不吃餛飩吧,吃不飽的。”許香來滿臉莫名其妙。
“沒事,走吧。”
這個時間點的餛飩店人已經不多了,否則確實讓人不好意思大聲説話。走到一張桌子前,許香來停住了。
“今天你生日,你坐裏面吧,不和你搶。”
“謝謝。”他們并排坐下,許香來伸長手臂把桌上快見底的蝦皮罐子和旁邊桌滿滿當當的調了一個個,對大鍋前煮餛飩的老闆娘喊:
“不好意思——,要兩個大碗。”
老闆娘頭也不回説了聲知道了,一旁一個四五年級的小男孩把手上的麵粉在紅領巾上蹭了蹭,繼續幫媽媽拌肉餡。
“許……香來,”方曉聲反復玩著衣服的按扣,問她
“你爲什麽會來讀書會啊?”
“我沒和你説過?”許香來側了側身體,疑惑道。
“沒有啊,而且……”他猶豫了一下,”我覺得你是那種會去LGBT社的人啊,就是他們不是被校方勒令解散了嗎,我覺得你像那種……”
“解散了?那麽倒霉?不是吧?”
“就是他們原來不是中間有那個嘛,那個信息員啊,就他們總得有事做吧,然後還有說前任社長接受境外資金援助……”
“草,這可是你自己説的,我沒有要參加過,你自己是那個看誰都像那個,你自己説話自己負責。
“不是,我説那你爲什麽來古典學讀書會?“
“我不是回答過你嗎?算了可能是我記錯了。你不要和別人說,我小叔是歷史學院副院長……”
“你原來托關係錄取的!?”方曉聲下意識地往裏縮了縮,轉向她。
“哪有人要托關係進歷史學院的,我滑檔生,他不是你們指導老師嗎,感覺可能挺有意思的就加了一個唄。”
“所以你覺得有意思嗎?”
“沒意思。”許香來說,“基本大半内容還是就是蒂邁歐的展開,本來有點意思的細節也都沒再深入了,我覺得雅典來的客人和蒂邁歐開頭的缺席那人是同一個人吧?而且非要用中國文人的微言大義去套沒必要,從字面上看就好了。”
“無非就是在有限的時間内過一種合適的生活,”老闆娘端著一碗餛飩過來,許香來搶先指了指方曉聲那邊,老闆娘把餛飩放在他面前。“謝謝,秩序來自於天體,也就是諸神,之類的……我不那麽感興趣,其實。”
“可能是我不適合參加這種事情吧。”他補充道。
“那你來幹什麽?”
“我……”方曉聲不敢看她,嘆了一口氣,“我想多認識一些人,而且在這個學校不做點事情的話容易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我很庸俗。”
“你想保研?“
“我不想——”
“是啊,保研沒意思,尤其不要在我小叔這種人手下做研究生,我跟你講,他對他老婆就是……”
熱氣一團團地從餛飩碗裏面冒上來,方曉聲的眼鏡上糊滿了霧氣,這股霧氣仿佛也粘稠地,一團團地湧進耳朵中,許香來的聲音模模糊糊地響起:
“你喜歡我嗎?”
他沒有説話,沉重的餛飩碗被放在桌面上,一隻手從他的後頸後面伸過去扯桌子裏側的捲紙筒,老闆娘把許香來的餛飩湯裝得太滿了,他想,這樣不好,拌勻辣油搞不好就會弄髒衣服。
“我不想騙你,”他説,“我不喜歡你。但是大多數時候人們都不是因爲喜歡才在一起的,而且你是很少的讓我不討厭的人。”
“你遲早有一天會討厭我。我不會問你我和你媽掉進水裏你救誰,還不如問你你會不會有一天擧報我,這個倒是比較現實。”
“不到那一天怎麽可能知道。”方曉聲放下眼鏡,往她的碗裏加了一勺榨菜,“食不言寢不語。”
“我哪兒也不去。”他説,“而且256GB也沒那麽耐用,現在圖片分辨率都不低。”
“你以前說想自殺都是認真的?”
“那是不合適的生活方式,柏拉圖已經指出,以一種混亂的方式生活的人,就會轉世變成女人……”
“沒什麽不好的,”許香來又扯了一段捲紙擦桌子上的湯汁,“你不想做女生?”
“這種不是想做就能做的吧?”
“對哦,不是想做就能做。也不是想喜歡就會喜歡,我其實也不喜歡你。”
雖然沒那麽意外,但方曉聲聽到這句話還是難免手一抖。
“你不喜歡我……”
“這個學校除了你以外的人,都應該每三個人中抽三個人出來殺掉。”
“那看來還真是不感謝你不行。”
“去不去散步?”
許香來在鍋臺那裏把錢交給老闆娘,探頭向室内喊道。
“不去——”他對她喊,“我晚上得睡覺的,要去你自己去。”
“好吧,”她扯了一大截捲紙曡起來塞進提包,“好好休息,保護你的眼睛。”
方曉聲回到租住的屋子,燈似乎出了什麽問題,樓道裏一片漆黑。他打開手機的電筒,哆哆嗦嗦地把鑰匙插進門鎖。書桌上橫七竪八扔著筆和草稿紙,他用其中一支筆戳向封口膠帶然後扯開塑料袋,取出那個256GB的愛國者牌硬盤。果然就是一個字面意義上的,平淡無奇的國產硬盤。人恐怕是依靠設想永恆來成爲非動物意義上的人類的,城邦的奴隸和公民,公民和哲人王的區別在於對恆星運動的理解的話,説到底也是對永恆秩序的把握程度。某種程度上來説——他基本上完全沒有信息工程知識,但是硬盤也是依據一定的規律寫入和讀取的,萬一,就算人類滅絕了,只要還有硬盤而且它們夠硬就不要緊。
但是那另當別論,許香來即使對於他而言也不是會讓人喜歡的女生。他厭惡地記起,她總是對一切充滿了不知道從哪冒出來的嘲諷,而且他們真正認識,還是她某次忽然問他是不是高中時候組織過自殺俱樂部,還因爲在同學之間傳播紅歌的纂改版本被家長鬧到學校慘遭處分。因爲許香來覺得他在自己社交媒體上背後説人壞話很好玩,順勢翻完了他賬號中的所有東西,還順藤摸瓜找出了他高中的舊賬號觀賞。他不知道這種女生在想什麽,她們就不會有好好説話的時候。許香來打開他高中時候用的論壇賬號,讀道:
“如果我在阿拉伯國家犯了什麽罪一定要被處死的話,我還是覺得割喉比石刑人道很多。因爲我的頭跟著我已經吃了很多苦,誰不善待它我就要他的狗命……”
“操你媽別讀了!”方曉聲平時甚少使用這類詞語,正因爲如此,才顯得他又怒又窘。
“方曉聲的頭像皮球,一脚踢到百貨大樓,百貨大樓賣皮球,賣的都是方曉聲的頭……”她嬉皮笑臉地添了一句,“不讀就不讀了。”
他不在乎這個説話陰陽怪氣的女朋友是不是導致他也成了學院的邊緣人,反正他原本就不是容易交到朋友的人,但許香來另一個惡劣的癖好就是向他傳播古典學中的“邊緣人”傳統,重複一些“因此城邦的目的就是最高善”,或者講十萬遍瘋人船是什麽樣的。當然,這種行爲不是莫名其妙,因爲高中時代的方曉聲時常直抒胸臆地寫一些自己是自殺愛好者,或者裝瘋賣傻有怎樣的好處一類事情,大概因此被認爲需要教育吧。他不會忘記,尤其是不小心踢到臺燈電源導致必須整個人在黑暗中鑽到書桌底下摸索著把電源重新插好的時候,他必然記起許香來說,他恐怕幾十年後就在精神病院的天井下面呆滯地曬太陽漫游精神世界,那時候她一定會去看望他。
如果保存html文檔的話,一篇文章大約有六七百個KB,仔細算一下這個硬盤確實能存不少東西了。市面上販賣的硬盤有些容量縮水嚴重,他打開筆電連上硬盤檢查容量,當然不是真的有256GB,不過也大差不差。他即使想找誰説説高中的自殺俱樂部,也絕不會找許香來,況且後者根本不愛説話,準確來説是一會說個不停,一會惜字如金,他真的得爲此時常點開她主頁檢查——如果看不到她電話號碼,就説明自己被刪除了聯係人。而且最重要的還是,對於這種人來説,制服她唯一的辦法就是在相同的道路上走得更遠,要麽離開許香來,要麽自己變成加强版的許香來。
“你這種人居然會在學校食堂吃飯?”方曉聲忽然發現一個熟悉的身影。
“沒有,”許香來拿了一份白蘿蔔燒肉,“我在這堵你的,你下一節上課,肯定來不及出學校吃。”
“而且我覺得你應該多吃一點,”她又拿了一份剁椒茄子放在方曉聲的盤子上,“我一會給你刷掉。”
方曉聲其實不吃茄子。因爲茄子軟塌塌的還反光,看起來很惡心,不像植物該有的樣子,但盤子已經被拿下來,再放回去肯定是不行的,爲了避免吃這種毒藥一樣的東西也只能找借口提前溜走。
“你還帶書進食堂?我以爲初中畢業的人就不會做這種事情了。“確實,許香來用胳膊肘夾著一本尺寸不大不小的硬裝書,加上盤子上又放了一碗鷄湯,在人來人往的食堂裏走路有些彆扭。
“這個也是帶給你的,”她把餐盤放在座位上之後扯過方曉聲的登山包,把書放進了給筆記本電腦的隔斷裏,“你必須給我好好看,因爲下次再遇到你時候我要問你感想。”
“什麽書啊?”方曉聲剛要伸手去拿書,被她按住。
“策蘭的詩集,”她説,“你看就是了。”
“我看過啊,”方曉聲有點急,“重死了,你沒看我書包已經有多少書了?”
“那你拿在手上。”許香來用一根筷子去戳大塊的蘿蔔,然後像吃烤串一樣放進嘴裏。
蘿蔔這種東西説實話也挺惡心的,尤其是紅燒蘿蔔。因爲透過半透明的蘿蔔肉,裏面的經絡看起來就像血管一樣,讓人覺得很不舒服。而且紅燒之後就變得髒兮兮的,還有一股詭異的甜味。他想起古典學讀書會的一個蒼白的長髮女生,話少,胸部消瘦,總是穿著一身好看的長裙,一言以蔽之就是刻板印象中的憂鬱文學少女。然而這樣的女孩的社交主頁上卻充斥著醬油排骨的照片和不惜一切代價打贏貿易戰,從這一點上來説,認識許香來總比把只有一個成員的自殺俱樂部經營到大學好。一個喜歡醬油排骨的人是絕對不會自殺的,無論這種人口頭上多麽頻繁地重複一些“討好性人格”,人生的無意義,或者發狂謾駡一切試圖“在社會上站穩脚跟“的行爲。方曉聲惡毒地想,他們從質料層面拒絕理解永恆的東西的可能性,他們會是第一批大腦插管人,他們所欲求的僅僅是像動物一樣無節制的性行爲和無限量的醬油排骨,他們比他們以華麗的辭藻批判的舊世界要遠為低賤,現代性的所有問題都可以歸結爲——
“你不吃東西啊?”
“湯太燙了。”方曉聲趕緊做賊心虛地裝模做樣在湯碗攪了兩下。這個世界已經無可救藥地充滿了陰險的騙子,一個正直的人在其中就像身處野獸群中一樣危險。
“我不喜歡加繆。”方曉聲曾經這麽說,“像加繆這樣的知識分子出於他們一種自私的天真信念,認爲愛或反抗的正當性是自然的且普遍存在於人類中間。誰要是聽信了他們的詭辯,去把含情脈脈的眼光投向群衆,誰就必然付出代價。”
“我不喜歡策蘭。”他微微擡起頭半閉著眼睛說。食堂的白熾燈和熱氣讓人頭痛。
“詩歌社十個人裏面有九個人喜歡策蘭,”許香來仿佛要等他問還有一人怎麽了一般停頓,“第十個人因爲長期不參加活動被除名了。”
“我去上課了,這太難受喘不過氣。”
“上課不要玩電腦。”
方曉聲抓起他的包的拉鏈那一塊站起身來,他的包背帶恐怕不太結實,塑料加强帶都已經斷裂了,但不管怎麽説也得想辦法耗完這個學期再説,因此盡量不要把包背在肩上讓它受力。
對他們這樣的二年級學生來説,如果想要去國外讀研,一年後就應該開始申請,放眼望去連保潔阿姨剛剛拖過的地面都亮得讓人焦慮。人之所以會痛苦,歸根結底還是因爲對未來抱有期望,還有就是不甘心。他能感覺到那本方方正正的書在包裏面壓著草稿紙,有幾個瞬間他簡直想立刻拉開包鏈把書抓出來用力丟掉。但是不能這樣,會沒法交代。他記得很清楚這本書定價88元,他不能爲了這種事情一個禮拜午飯沒有葷菜吃。
硬盤也在書包裏,他能感覺到自己快走的時候硬盤碰著筆記本電腦的外殼,不過應該撞不壞,那個硬盤有一個海綿套——他坐到最後一排,旁邊一個男生斜了他一眼,戒備地背向他稍微側了側。除了和女朋友和自己有關的東西,他也備份別的任何他覺得會被刪掉的東西,挑出其中有趣的讀給許香來聼。這節是中國近代史的必修,就這麽一會工夫教室後半部分已經沒什麽空位了,他慶幸許香來沒有纏著自己不放,否則他就只能在前排瞪著眼睛苦熬。他把筆記本掀開成90度左右,朝自己拉近,鬼知道那個一臉不友好的男生是不是信息員,雖然這種必修課比較鬆但還是有挂科的風險,因此大家多多少少還是會學一點,唯獨那家伙上課手機就沒放下來過,老師也對此人熟視無睹。和許香來不同,他并不是熱心玩社交軟件的人,不算上許香來只有epinomis讀書會的兩個前輩,不熟悉的同學和高中時候的同桌的聯係方式。其實也沒什麽好看的,大家都是比較沉默的人。他百無聊賴地滑著筆記本電腦的觸控區,突然跳出來了學長的新動態。
“(轉載)李大發教授舉報港獨博士生造謠公開信”
學長一向是個冷冰冰的人,轉載帶上一句輕飄飄的“敝專業也有這種廢青”和一個摳鼻孔的表情。方曉聲突然意識到那是什麽了,他戳開那個鏈接,果然。幾天前,那個可憐的博士生在社交網站上說,他(也可能是她?)永遠不會忘記那天,學校的小禮堂座無虛席,國内古典學領域大名鼎鼎的李大發教授給莘莘學子演講,李教授說,批判納粹何嘗不是一種政治正確,納粹做的就一定是錯的嗎?他(或者她)一擡頭,就看到大電風扇從天花板上倒吊下來,晃晃悠悠地轉著。於是他對這番發言大爲吃驚,寫到了個人社交主頁上。方曉聲當時也大爲吃驚,但他記不得自己有沒有輕輕按一個轉發了,可能沒有吧,他怕事。李教授這封公開信毫不留情地指出該博士生是一個港獨分子,被境外勢力蠱惑,惡毒地詆毀他,但他大人大量決定給後者一個重新做人的機會。
方曉聲覺得手脚發涼,他顫抖地打開搜索欄,輸入那個博士生的昵稱,賬號已注銷。查找“我永遠不會忘記……”彈出來一條條動態已刪除。他翻了一遍圖庫,沒有,自己也沒有留存截圖。李教授原本是神學研究者,近年傾心於中國和西方古典的比較研究,以保守主義和反民主政治的姿態聞名。“想當國師想瘋了。”他記得自己和許香來談起他的時候後者抛出這麽一句話。但現實中李教授就是成了國内最重要的幾位古典學者之一,弟子遍佈大江南北。
上課鈴響了。他當時愣住,仿佛偷東西被抓了一個現行一般。快速關掉剛才打開的窗口,仿佛動作慢了就會沾上什麽可怕的病毒,他覺得那個男生在瞥著自己,用一種懷疑或者輕蔑的眼神。沒用了,沒人知道怎麽回事,他習慣性地用手機打開社交軟件,滑到學長的動態下面。不行,可能必須要説什麽,不是這樣的,不是這樣的。輸入文字的光標閃來閃去,太快了,不行,根本沒法構思要説什麽。“我看見了。”?“畜生,你看見了什麽!”他還是顫抖著摸到左上角的退出編輯按鈕,長出了一口氣。來日方長,以後搞不好還得在國内混學術體制。近代史老師走進教室,掃了一眼大半空蕩蕩的前排,和往常一樣調出她的課件。
信息員這些人真的很可惡,爲了黨支部表彰和一點點工資就出賣老師同學。LGBT社還在的時候監視LGBT社的信息員居然還失誤把監視記錄發進了群聊,誰知道是不是失誤呢,也許是故意挑釁吧,反正LGBT社已經被取締了,那家夥不知道現在又在哪高就。但是什麽都不幹的普通學生也可惡,他暗想,如果大家能把日本電視劇中的高中集團霸凌那些技倆給信息員安排一下,久而久之肯定沒人敢做這種缺德的事情了。他還是摸出手機,點開和許香來的對話框,把李教授(他在博客中提到自己和別的他贊同的學者的名字時會把名字標紅加粗)這封公開信鏈接傳過去。
他上課一向不睡覺。再無聊的課,睡覺也是在褻瀆老師的勞動。而且同樣是必修課,近代史總比習近平思想有意思。去年一個近代史老師説錯話被停止教學資格了,聼學長說是個五十多歲中年男,會色迷迷地盯著穿短褲的女生看,上課愛講段子還挺有趣的。這個老師是一個不好惹的中年女人,眼睛瞪得像銅鈴,啪啪地拿一個像收音機舊天綫的東西點投影屏叫他們集中注意力看。他突然發現課本裏面掉出來一張寫著英語單詞的便條紙,他把大寫F的那一竪寫得彎的有點誇張,於是心血來潮把弧度伸長畫成螺旋狀,再加上葉子——好像什麽外星植物一樣。他低下頭專心致志地在便條紙上面畫起了外星灌木叢。
方曉聲的眯著眼睛關掉手機的振動鬧鈴,今天沒有早課,他又和許香來昨夜聊天太晚忘了取消掉給前一天的鬧鈴。他昏昏沉沉夢見家中給他安排相親,對象居然是許香來,他們一起裸著上半身睡了一夜,早晨她背對著他穿上胸罩。仔細想來他確實沒見過許香來的胸部長什麽樣,不過也沒什麽好看的。他打了一個哈欠,就算是許香來,可能夏天也會趁四下無人把手從衣領伸進去拽一拽不太舒服的胸衣,雖然也可能她根本就不穿。但夢中的許香來并不白皙卻瘦削的脊背讓他有點想入非非,普通的生活的精髓恐怕就是早晨看女朋友把胸部放進海綿罩杯。
他拎著豆漿走進階梯教室。沒想到許香來今天來得不正常地早,正常情況應該是上課後十幾分鐘,她貓著腰從後門進來,一路小跑到他身邊坐下。方曉聲問過她爲什麽每次都遲到,還不多不少都是那麽十幾分鐘,後者理直氣壯地回答因爲她要繞路去一家有酸酸乳賣的早餐店。許香來緊緊盯著他,幾乎豆漿剛被放在桌子上,許香來就猛地抓住了他的手腕。
“出去,我有事情要和你説。”她以少有的低聲說。
“怎麽了?不要閙啊,馬上上課了。”
“不行,真的很重要!“她的聲音陡然重起來,“求你了。”
方曉聲從沒見過她這副樣子。雖然説嚇了一跳的話肯定也不至於,但確實是意外。他們走出教室,許香來嫺熟地打開社交軟件,給他看留言。
“律師金千平,希望恢復古代女犯罰入青樓的法律,這個女恨國黨長得還不錯,別浪費了…這什麽啊?”他念了出來,忽然看到了什麽熟悉的文字,“下面是你的用戶名?你怎麽得罪他了?”
“你再看看這個。”許香來點開另一則動態,把手機遞過去,心虛一般地轉向其他方向。
“這個許香來是我初中同學,當時班裏有什麽事情第一個跳出來冷嘲熱諷的就是她,沒有人喜歡她,記得當時她和我們一組出國慶黑板報,放了學人就不知道跑哪去了,真的是呵呵。”方曉聲又讀了一條,“許香來,”他幾乎想抓她肩膀,“大姐,有沒有搞錯,你怎麽回事啊?”
仿佛不敢看他一樣,許香來說:
“你搜我們學校加上辱華就能看到了……有個人不知道從哪挖出來我兩三年前發的動態。”
方曉聲不是沒聼説過這種事,但還真沒想過有一天落到自己身邊人頭上,他露出了一種哭笑不得的奇怪表情,問許香來:
“你打算怎麽辦?”
“閙大了我會被開除,小叔估計都要被處分,我真的不知道。”
上課鈴響了,方曉聲從來沒覺得這陣鈴聲這麽及時過。
“哎你回去上課吧,”許香來用力把他往教室裏推,“哎,我一個人靜靜,你先去上課。”
“真的不要緊嗎?”方曉聲一隻脚踏進教室,又回過頭對她遠遠喊了一句。
“你就讓我一個人待一下吧!”她抓起手提包跑向樓梯間。
有這種事情也不是讓人意外就是了,遲早的事。方曉聲一邊安慰自己,一邊點開搜索欄輸入校名和辱華兩字想看看怎麽回事。映入眼簾的是某愛國系意見領袖義憤填膺發佈的截圖,“辱華”,“侮辱英烈”,“反人類”這樣的帽子讓人看得觸目驚心。他一恍惚,不禁想起了那隻可憐的蛤蟆哭訴自己怕龍王爺追究起還是蝌蚪時候的事情的笑話——太陽穴一陣跳痛。雖然也不是不能理解就是了,畢竟是許香來這種口無遮攔什麽都能拿來搞笑的人。“有沒有搞錯啊侮辱英烈罪是寫在刑法裏面的耶——”他喃喃自語。
人生之所以會出問題,其根源都是想好好活著。這是他初中時得出的一個真理。其實不只是因爲想考好高中,初中生才會痛苦,哪怕對於他們這種稍微不太適應社會的人,也是因爲總是管不住嘴想要意淫自己生活在一個言論自由的地方,才會倒霉。“幾乎沒有人看了黃片就去大街上露生殖器,那我們爲什麽還喜歡看了一些小説電影就心潮澎湃覺得自己活在了可以隨便説話的年代?”他假設自己又不小心把這句話説出了口,然後前排女生聽到生殖器三個字後一臉震驚地回頭看他。那個場面一定很好玩。可能要緊的是找到許香來原話究竟説了什麽吧。他看著截圖中許香來熟悉的頭像。
“你説得好,支那人。”他讀出這條動態。俗套地說,簡直要開始倒吸冷氣了——現在是什麽時期,還敢提這兩個字。還有一條關於邱少雲的,許香來好像在轉發裏回覆誰,她説
“我悟了,原來你國共產黨人入了黨就退了人籍。”
其實應該還有其他的,但這兩條就足夠了,與其説就足夠了,還不如説這種話題一碰就死。剛才恐怕應該把她拖住的。方曉聲不止地揉著太陽穴,忽然冒出這樣一個念頭:
“許香來要是因爲這種事被開除不會自殺吧?”
但是仔細看來,許香來會如何好像和自己也沒有什麽關係。“本來就不是一個世界的人。”他又記起了那本策蘭的詩集,仿佛那不是一本詩集而是一塊燒得通紅的磚頭。策蘭也是死於自殺,但許香來這種什麽都不懂的女人和猶太詩人怎麽可能相提并論。就是自殺的資格問題吧,不是人人都有資格死,這個學校的絕大多數人就沒有資格,他們即使是自殺,實質上也只不過是不滿意——他們就其爲人的本質而言沒有超出塵世的東西。非要説什麽的話,他越想越生氣,幾乎要從教室中奪門而出,當然不能那麽做。
手機振動了起來。他像見到救星一樣抓起手機快速從後門溜出教室。
“喂,喂,”他連喊了兩聲,“喂?”
“許香來,你在聽嗎?”
“在,在。”她的聲音從另一邊傳來。
似乎是爲了發泄什麽一樣,他向對面吼道:
“你他媽是不是活膩了?想死自己去賓館開房燒炭啊,你發的都是他媽的什麽東西,不被搞就有鬼了!”
對面沉默了一會。
“我兩三年前隨便發的怎麽會知道……”
“那你刪掉啊!你看別人被盯上你不知道刪掉嗎!還支那,“他放低聲音,”支那是能隨便講出口的嗎?”
“我知道,”她無力地回答,“你看我那個回覆別人的啊,他們發了一個漫畫,說中國軍隊打到越南把越南猴子都打死了,越南女生只能到廣西賣身。我就是覺得他們這麽説話不對才回了一句支那人反諷……”
“那你怎麽辦?”
“不知道,”她停頓了一下,“好多人過來舉報我的賬號,已經被封了。現在動態都被刪除,再截圖也截不了了。”
“你幹的什麽事啊——”方曉聲好像被釘子扎到了一樣,“我,我……”
“對了,方曉聲,”她忽然想起了什麽,“硬盤,你的硬盤。”
“什麽?”他條件反射地問。
“我給你的硬盤啊!你有沒有往裏面備份存檔?”她的語速快了許多。
“啊……”方曉聲感到一陣難以名狀的失望,但是他確實存了,只是想不到這時候會派上用場。“有,確實有……”
“把它拿出來説不定能救我,要不是有你就麻煩了。”這回許香來的聲音真的輕鬆了不少。
她的小叔可能又能幫上什麽忙吧。方曉聲想起了過去看的小説《1984》,溫斯頓說茱莉亞是個下半身的叛逆:她什麽也不關心,她天真地以爲靠一點點聰明才智就可以一次次化險爲夷一直平安地活著。溫斯頓躺在舊貨商人的床上借日光端詳包著珊瑚的玻璃鎮紙,茱莉亞用光潔的脊背對著他。這種情景想想就讓人感到惡心,絕不能那樣。或許就是那一瞬間,他明白了如何戰勝許香來,他要從她暗示的日常生活那裏奪回自己的死。
“別怕,”他説,“我們下午下了課去公園划船吧,我把詩集帶著念給你聼。”
公園離這個城市的火車站不遠,有一個挺大的湖,種了不少荷花,不過現在都是一片枯草。方曉聲高中時曾經一個人去划船,結果帶的錢不夠付押金,把學生證抵押給了船老大。“清晨的黑牛奶我們喝啊喝,”他自言自語,“連網咖包夜的高中生恐怕都知道這首詩。”他總覺得策蘭的詩大多在寫同一件事,一個孤寂的人和亡靈的末日旅行見聞。這不行。他和許香來最根本的區別就是後者無時不刻帶著一種“來玩玩,玩膩了就回去”的態度。
她恐怕只是害怕不能從這個光怪陸離的夢中醒來,然後去早餐店買香腸和酸酸乳喝吧。
方曉聲來得很早,把雙臂壓在親水平臺的欄杆上,小指吊著硬盤收納袋口的抽繩把硬盤晃來晃去。他忽然下了決心似的,把繩子用力一甩。
他鬆開了手。
硬盤划過一道不圓滑的弧綫,笨拙地扎進湖面。靠著欄杆玩手游的一個胖胖的十一二歲的男孩像是被水花聲嚇到,擡起頭狐疑地四周望了望,抓起脖子上的紅領巾抹了一把鼻涕,換了下雙腿交叉的順序接著在游戲中廝殺。四五點鐘的太陽自暴自棄地在湖水上輕輕蓋了一層,誰也沒法把它徹底戳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