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舅、社会苦痛与当代中国的精神腹地
B站up主“衣戈猜想”在7月25日投稿的视频《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成了爆款。它用了两天获得了两千多万播放量,被官方媒体转发,也在社交媒体引起了更多讨论和争议。

一种关键的批评指出,二舅在人生中吃的苦被创作者审美化、景观化了,而二舅本人也在视频中被消声。这一方面意味着,《二舅》的个人叙事忽视了社会结构层面的问题,而正是这些问题造成了二舅受苦受难的人生。另一方面,二舅本人的主体性在这个试图概括其积极的个人积极形象和坚韧人生的视频中被剥夺(或许此前传出的“二舅走红全家大哭一场”的新闻算是一个具有复杂意味的回应)。
那么,我们可以追问,二舅和他的互联网观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熟悉中国农村的人会说,这样受苦一辈子又仍然坚忍乐观的人并不罕见,甚至相当常见。熟悉“内容生产”的人会说,视频制作者显然具备娴熟的讲故事技巧。熟悉互联网平台的人则会说,内容推流机制和热点的跨平台传播效应功不可没。
然而,在此之外,对二舅的想象似乎包含了一种独特的感觉结构,这不仅帮助该视频在B站甚至简中互联网大火(从经验观察来看,其出圈范围可能超过了2020年的《后浪》),也说明二舅和我们的当下现实密切相关。
经济史学家用“腹地”指称那些在所谓发展与进步中受损的区域,在这种语境中,中心地带的发展是以腹地的不发展和被剥夺状态为条件的。如果农村是(毛时期社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腹地,那二舅无非是那些过于年轻或者即将不再年轻的城市观众的精神腹地。正是通过剥削这样的腹地,中心才得到完满,中心—边缘结构才得到稳固。在此,二舅占据着这一不平等链条上的边缘位置,观看视频的城市(青年)观众则处于相对中心的位置。
当然,被隐没的还有不可言说的、给二舅发了一手烂牌的发牌者。没错,二舅人生的这把所谓“烂牌”,除了相对偶然的致残事故等,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具备任何神秘的命定论色彩,相反,它们每一个都能够延展为一项社会公共议题,甚至创作者也有意无意地点明了社会时代变迁的某些背景与二舅吃的“苦”之间的关联,但这种“受苦”随后被化约为二舅的人生中亟待克服的个人苦难(从而让观众期待看到他克服苦难的某种“平民的个人英雄主义”并获得满足),而这种苦难的社会性质、其所产生的现实政治经济过程和机制都被一笔带过或隐而不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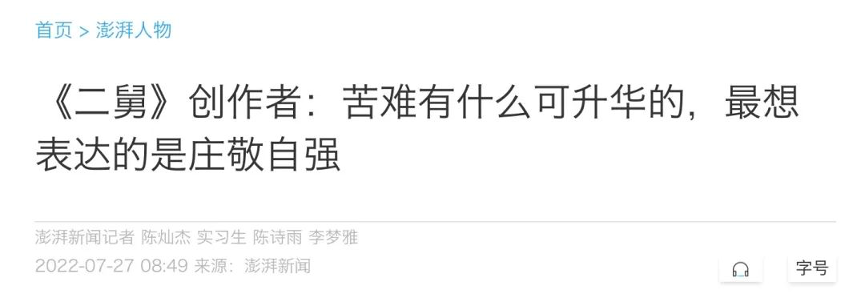
我们或许可以相信创作者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所说,他并无赞美苦难之意,只是想要赞扬普通人的积极精神。如果二舅的故事大致为真,我们也可以对他的遭际感到同情和尊敬。然而,通过上文提到的一系列“个人化”、“去历史化”、“去语境化”的叙述方式,二舅的生命经验在视频中被审美化,变作一种受苦者个人的奇观展示,而这些社会苦难的根源则没有被发掘,二舅本人也没有获得言说的机会。
换而言之,这个故事包含的细节原本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如城乡、残障、劳工、迁移/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等,但在城市自媒体创作者的镜头前,二舅只是作为一个隐忍乐观的模范、标杆而出现。
二舅的这个故事从二舅自己的生命历史中被抽取出来,它残酷的情节、带有解构色彩的语言和温情的结尾却打动了简中互联网的大众,特别是并不乐于歌颂苦难的青年人。通过“我”与二舅之间的比较来实现对自我命运的体认(“我理应度过一个比二舅更为饱满的人生”),或许只是“二舅”的第一个层面。
它的另一个层面则是一个引诱观者认同的“缝合怪”,包裹着艰难的社会现实、颇具“前现代”草根色彩的生命活力以及点缀其中的毛时代符号与神话。当青年观众在两年前看到B站官方发布的“五四”宣传视频《后浪》中那些与自己生活殊异的“后浪”生活,ta们感到愤怒;而今看到二舅的忍辱负重,围绕二舅所编织起的这个美丽故事(一些官媒已经将之包装成一个“奋斗者”故事)却将ta们对底层人民的朴素移情投入一碗中国式新自由主义的鸡汤。
面对缺乏保护机制的原子化社会,“命苦”(牌烂)只能怨自己,也只能靠自己。
或者,也许观众并不都信仰一套“个人应该自我担责”的叙事,而只是清楚或模糊地确知二舅(或其它类似境遇的某人)只能如此。即使与二舅的生活语境天差地别,但对那种宿命般的“给定的宏大历史”和“个人施为无法能动地改变现实”的体验可能确实契合当代中国人的感觉结构——因为你做不了什么,所以面对社会系统的运动,你只能将之当作一个给定的事实去承担,去接受。

回到创作者间接cue观众的那句“我理应度过一个比二舅更为饱满的人生”,手机前的(青年)观众会如何回应和填充这句话?如果“度过人生”并非私人领域内的创造,如果二舅的人生不只是一个安慰人心的童话,那么在二舅和“比二舅更为饱满”的“我”的人生,以及更多叠加各种社会“debuff”或特权的人生之间,我们还应该关心好牌和烂牌是怎么发出来的,洗牌和发牌的又是谁,我们又理应拥有一个怎样的游戏规则。
不仅要拒绝把受苦受难的生命经验美学化、奇观化,还要追究它所隐瞒的社会关联和世界图景,否则那些原本应该“外耗”的东西永远无法走出被迫内耗的境地。
而正因在一个几乎被给定的社会现实面前,“外耗”近于不可能,群众才需要一个二舅,一个(新)时代的精神腹地,毕竟如片中所说,人生总是被期待着通往某种“胜利”。
往期文章:
“被逼无奈”的俄罗斯与“活该”的乌克兰:地缘政治的知识霸权(2022-02-26)
头戴锁铐的娜拉:徐州八孩女子与农村父权叙事(2022-02-22)
东方主义,多重“边缘”与审美解放:回顾陈漫事件及其争议 (2021-12-22)
欢迎订阅 Matters与微信公众号「蜉蝣型幽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