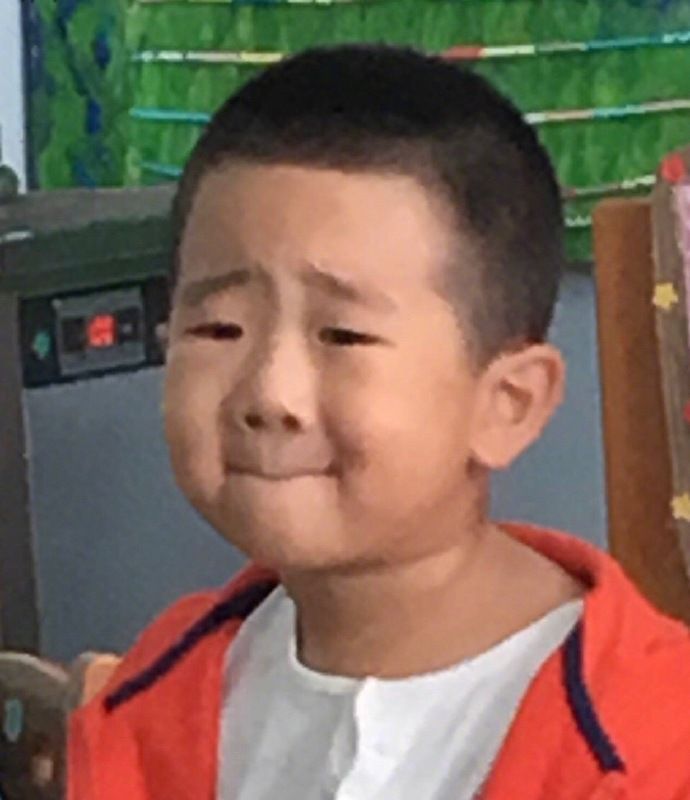走過2019|數位化的淺思
本來這篇打算叫做《碎片(三)》的,因為不知道起什麼名字的小文都歸於《碎片》名下。但看到《我們在Matters寫字》的提議,剛好在年末的這個節骨眼上,索性以「數位xx」為主題,給自己今年的閱讀和思考做一個粗略的小結。
起因是,昨天參加台灣事實查核中心發起人胡教授的講座。除了「事實」「真相」和「新聞」「民主」這些字眼外,期間亦多次提到「數位原住民」這個概念。又趕巧最近正在還債寫關於「知識付費」(pay for knowledge)和修改關於「反轉新聞」(reverse news)的文章,因此有了這個念頭。
關於數位化(数字化,digitization/digitalization),Wikipedia給出的解釋是:
數位化是指將信息轉換成數字(便於電腦處理,通常是二進位)格式的過程。
在如今科技突飛猛進的媒介時代裡,數位化絕對不是什麼新鮮事了。2019年於我,無論是經歷的課程(如數位語藝、數位調查、視覺傳遞),還是閱讀的書目(如《復旦新聞與傳播學譯庫·新媒體系列》),大多可以劃入這個領域之下。由此,聚焦在數位化的語境下,組織出了三個個人感興趣的議題,也藉此分享一些淺見。
首先,是「數位落差」(digital gap/divide,数字鸿沟):
指社會上不同性別、種族、經濟、居住環境、階級背景的人,接近使用數位產品(如電腦或是網路)的機會與能力上的差異。
曾經我在熬夜拍片或加班剪片時,常常會發那種三更半夜的朋友圈,然後被我的外婆和奶奶數落。每每說起這件事時,總有朋友驚訝於她們在使用微信,是的,她們二老都會在朋友圈點讚、關注微信運動的步數排行以及在家族群內轉發某些信息。而同樣的,我在公車上也偶爾會看到一些外來務工人員拿著碩大的「山寨機」和類似於小靈通的「磚頭機」。絕對沒有比較的意思。
其實想說的是,由於「數位落差」而帶來的新型「階級差異」。從David Berlo的傳播模型(Sender-Message-Channel-Receiver Model of Communication)來看,對於傳播者而言,媒介形態的變化,「守門人」(gatekeeper)的角色已經發生根本變化;接受者也已轉變為新形態的產消者(prosumer)。訊息本身所攜帶的真相意義早已灰飛煙滅,導致媒介的放大功能和偏誤效果加劇,由此對社會分化和群體認同產生的影響日益深刻。廣義上來說,知情權、詮釋權、傳播權和隱私權等等問題的發酵。個人認為,資訊不對等(information asymmetry)已經成為當今訊息世界的首要矛盾。
走過2019,媒介對於政治、經濟、文化的介入和滲透更加直白。資訊不對等所牽連出的問題和產生出的後果,無異於埋下了炸彈。如此前的香港事件等等,舉不勝數,而未來還有台灣的大選。訊息戰(information warfare)早已打響。
其次,「數位原住民」(digital native,数字原住民)。對應於像父輩的數位移民(digital immigrant),「原住民」的概念即是指:
從小就生長在有各式數位產品環境的世代。
呼應到上一部分所描述的數位落差現狀。相較於老一輩,如今的數位世代更加「分裂」,無論是在信念態度還是思想行為上都是如此。時間的片斷、渠道的隨意和訊息的碎裂,「原住民」們的思維邏輯、思考方式、处事手腕和人生價值在社會化(socialization)的進程中必定被當前的媒介生態所影響。資訊越來越即時、密集和雜亂,不實訊息(disinformation)和假新聞(fake news)的充斥,注意力經濟(the economy of attention)的興起,流量藝人的催生··· ···一切的一切都在衝擊著「原住民」的認知。前文「gap」中的某些部分,某種意義上來說或許也源自於此。
雖然有種一棒子打死的感覺,但我總覺得所謂的知識付費,實則是在收割焦慮。我絕對讚成認知盈餘(cognitive surplus)下的合理分享。但如今的知識付費總是給我一種轉賣「二手知識」的感覺。用非系統化的知識碎片來填滿認知裂痕和時間空擋,某種意義上的確可以得到自我滿足和社會認同。但對於知識系統性的了解、掌握甚至是運用,我是持著一個悲觀的態度。或許這也是為什麼老師們總強調「回歸原文」的原因吧,所謂的「文獻回顧」即是如此的作用。
走過2019,下半年的兼課經驗讓我更加正式的看待這個問題。大部分的課堂討論,要麼無法發展成為對話(可能是我的問題哈哈哈),要麼也只是散發出輕佻浮躁的味道。若把互聯網的普及算作是「數位環境」,那我也只是經歷過「軟盤」(floppy disk,磁片/磁碟)的時代。但當我面對同齡人和學生們時,依舊讓我慘痛的認識到當今媒介的「荼毒」。
對於越來越多的「原住民」而言,私以為,喚醒思考、搭建邏輯和形塑價值觀絕對重要。在「數位落差」的傳播中真相的缺席,和「數位原住民」結構中思考的泯滅,誠如@IrisChen文章中所提到的獨立思考,批判的思維何等必要。
最後,則是關於「數位勞動」(digital labour,数字劳动):
網路用戶組成了一類被資本剝削的無償勞工(Terranova,2000)
在當前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進程中,資訊已然成為一種商品。而沉迷於網上衝浪的我們,則成為了孜孜不倦的「數位勞工」(digital worker)。我們提供我們的注意力和點擊,構成了如今的拇指經濟。一方面,我們指責「無良媒體」散播的訊息,但另一方面來看,正是我們供養了「無良媒體」,比如反轉新聞。那麼,我們所生產的「價值」是什麼?好比我們在Matters平台中,所收穫的到底是我們賦予「讚賞」的心理價值,還是Likecoin所帶來的實際價值(如果是的話)。
同時,若從Bourdieu提出的經濟資本(economic capital)、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和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來看,無論是微○、臉○、知○還是抖○快○,鎖上屏幕後,我們所苦心經營的社交媒介給我們帶來了什麼?收入、知識、人脈亦或是聲望?以及,這一切又是如何與整個社會發生連結,並作用於媒介生態中的?
但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我們化身為代碼,成為商品(commercialization),並且樂此不疲。Fuchs提出了「玩工」(playbour)的概念以更替「勞工」。但玩歸玩、鬧歸鬧,回歸根本,我們還是在「無私的」付出,無非成為更「厲害」一些的「知識勞工貴族」(the knowledge labour aristocracy)罷了。
走過2019,在「數位落差」趨勢下的「數位原住民」們在辛勤「勞動」之餘,套用Dewey的話,「How we think」?
零零散散寫了這些,雖然套在一個主題之下,但其實也不過是自己的一些思考。不過,就像博一時老師說的「要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位置」,或許吧。
有個學生之前問我,關於讀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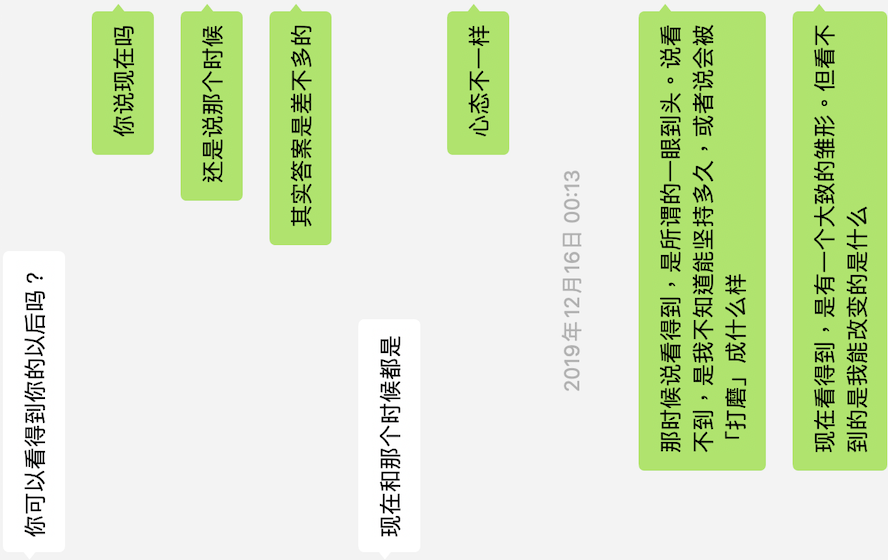
走過2019,我在尋找。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