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回顧 · 姐妹:團結與互相攻擊

講者簡介
劉滿新,墨爾本大學哲學專業博士候選人,同時也是女權主義者、自由撰稿人。此前曾發表過關於女權主義者身份認同的討論文章,諸如「『我不是女權主義者』:另類的女權宣言?」以及「韓國婦女運動史:婦女團體的出現與發展」等。
講座回顧
大家好,謝謝大家來參加今天的這個分享。
今天主要講的是關於之前我們跟朋友討論到的一個話題:在女權運動裏面,我們經常看到很多,雖然大家很團結,但是同時又有很多內部的一些互相攻擊的問題。我們思考了這個問題,然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題目是姐妹:團結與互相攻擊。
1 Sisterhood: 浪漫圖景與攻擊的現實
當我們看到女權運動或者是女權主義的時候,我們會想象這樣的一個場景:不管是運動的內部,還是運動所能帶來的一些結果,我們會看到女性都是團結一致的,相互扶持的這樣的一個景象。想象在一個運動裏面,女權主義者常常會團結在同一個目標,比如女性平等或者是女性解放的這樣一個目標下面,去共同努力、互相扶持、幫助共度難關等等。我們常常會用姐妹情誼(sisterhood)來描述這樣的一個圖景——姐妹之間的聯合。
我們會看到很多大家很熟悉的一些浪漫的、革命情誼的圖像。比如PPT 右邊的這些照片:


在運動的內部我們會看到,很久以前在追求女性投票權的時候,婦女參政運動者一起努力,為信念投身到運動裏面,並且在困難面前互相提供救援跟支持。幾年前(2015)的電影Seffragette中也描述了這樣的一個情景。此外比如在延安時期到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也有這樣的圖景:圖中是當年延安參加革命的一起反對女性壓迫的女革命者。
同樣,在運動外,我們也會看到這樣一些姐妹團結或者是姐妹情誼的場景。比如在圖裏可以看到,韓國的「姐姐來了」運動:很多已經畢業的女學生回到梨花女大,去支持正在反對性騷擾的姐妹或者是受到傷害的女生。人們甚至會看到很多文學影視作品裏面,姐妹之間不管如何艱難都會互相伸出雙手的情景。當然,女性團結或姐妹情誼不僅僅只是出現在一些革命或者是運動裏面,也會出現在我們日常生活,不是很戲劇性的場合中,比如我們熟悉的課堂。一想到課堂,我不知道其他的學科怎麽樣,比如在我們哲學學科裏,看到男生常常會占據了大部分課堂討論的時間,女生的團結則可以互相支持,減少一些影響,不再需要認為自己不如男生:現在男生總是在那裏講,他是不是比我們厲害得多?在一個女生團結的氛圍下,或是擔憂女生的這樣環境裏,女生不用怕自己說錯話,不怕被男生打斷,甚至還可以去挑戰那些自以為是的男老師等等。

在這樣一個圖景裏面,姐妹情誼的力量在於哪裏呢?在於姐妹之間的團結可以創造一個安全的、包容的空間,可以為女性提供一些可以凝結的、互相 bonding 的條件。歷史上或者是現在男生之間的交往是鼓勵的,我們鼓勵男生去玩,去建立友誼;而女性之間的交往往會被壓製,我們或是把女性之間的關系描述成為鬥爭:比如去搶男人,或是變成女生團在一起,圍繞著男人來進行自我發展。而真正的姐妹情誼能夠讓女性能夠擺脫這些束縛,可以互相扶持。
這是我們常常有的關於姐妹情誼的很浪漫的一個圖景,或者說是我們的一個理想。但第二波女權主義運動中的一些女權主義者也會描述道,比如圖中的Mary Daly,她認為姐妹情誼是女性之間互相選擇去表達自己,去展示自己的一種方式。

Janice Raymond則寫了一本很出名的書,叫做《激情的友誼》,提到最好的女權主義政治或運動,是從一個互相分享的友誼發展出來的。

最後,大家更熟悉的 Andrea Dworkin,她認為,女性團結是在這些 conscious-raising meeting 裏,女性互相發現了對方:歷史上女性被壓迫的情景與其他群體被壓迫不同,是因為女性總是被打散,然後被一一攻占;因為女性總是要回到家裏面,要麽回到父母家裏面,要麽嫁到丈夫家裏面。所以姐妹情誼就會形成一種非常有價值的空間讓女性去發展自己。但是在這樣的理想下面,我們看到的一些現實會非常地不一樣。

比如在運動內部的不同派別之間,因為具體主張的不同,女權主義者們通常會互相攻擊,有時候甚至會謾罵對方是假的女權來攻擊對方,而且這些攻擊並不是提出理論上或策略上的不同意見,而是直接攻擊對方的動機跟意圖。這些年我們在網絡上看到很多,比如行動派攻擊學院派,搶奪行動派的成果或者是搶奪話語權;比如激進派攻擊所謂的自由派,認為她們出賣女人給男人。我們甚至還可以看到一些女權者開始去攻擊那些受到家庭暴力的女性:是她們自己的錯,因為她們選擇了跟男人在一起。諸如此類。我相信大家在網絡上也會看到這樣的攻擊和對話。
我們在運動外部也會看到很多的攻擊,比如J.K. Rowling,曾經受無數人愛戴,現在可能是網絡上被女權主義者攻擊最多的名人之一。前Sussex大學的教授哲學教授 Kathleen Stock, 因為一些觀點在學校裏受到嚴重騷擾,需要警察保護回家,最後被迫辭去教職。同時我們也會看到其他攻擊,比如有人會熱衷於攻擊所謂的「小三」或者所謂的「綠茶」。
姐妹之間互相描述成是潛在的競爭對手:要麽是競爭男人,就像「小三」;要麽是競爭本來就很少的資源。同時姐妹之間也是各種性別規範的執行者或監督者,她們互相指責對方不夠女人,有時還會對對方的妝容指指點點,甚至會攻擊妝容下面的動機:比如攻擊者會說她化妝化成這樣,是為了怎麽樣,她做這些事情好「綠茶」等等。所以我們會發現在姐妹情誼下面,我們既有一個理想的、團結的目標,同時也會發現一些讓人很痛心的互相攻擊,在這樣浪漫的革命圖景下充斥著女權主義者之間激烈的攻擊謾罵。
到底為什麽我們會這樣子呢?我們不是說好了要一起去反對壓迫女性的各種的製度和男人嗎?我今天希望分享的是關於這個問題的一個答案:為什麽我們會相互攻擊。
2 Trashing: 清理與謾罵
既然我們說sisterhood是有力量的,為什麽還會出現像 Ti Grace Atkinson所說的,姐妹情誼非常有力量,它可以去殺他人,它殺的大多都是姐妹們。這是Ti Grace Atkinson對運動的反思。我們今天的分享首先希望去探討到底什麽是女權主義運動中的相互攻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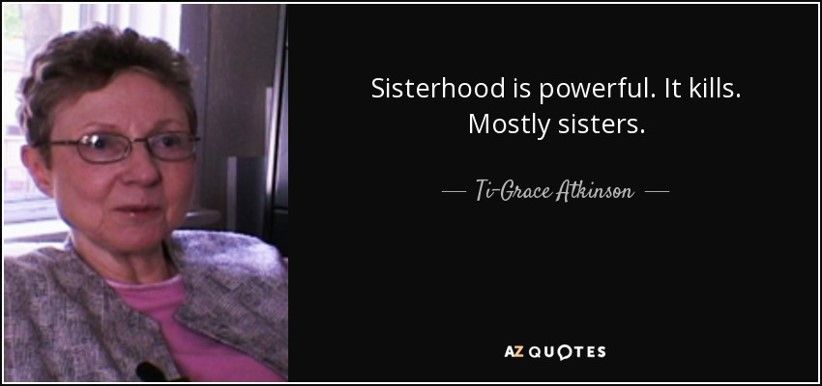
首先,女權主義裏的攻擊並不是一個新的現象,從我們有女權運動以來,我們就有女權運動裏面的人的相互攻擊,而這種相互攻擊在 1976 年被 Jo Freeman 的一篇文章描述出來,叫做 Trashing: The Dark Side of Sisterhood (《清理與謾罵:姐妹情誼的暗面》)。根據她的描述,女權主義運動中的相互攻擊似乎有一種特殊形態,即trashing。所謂 trashing根據中文版的翻譯是清理,但我認為不僅是清理,還有互相謾罵,所以我把它稱為清理與謾罵。

Tashing(清理與謾罵)不同於在運動或學習中出現的意見不同,即disagreement,也不同於互相之間的沖突,更不同於所謂的對立,因為在運動裏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行為。甚至有時候我們會認為這些意見相左,沖突跟對立是有好處的,它們能夠讓我們的團隊和運動保持健康跟活力,只要這些互動能在誠實和有度的條件下進行。
但trashing是一種很獨特的攻擊,它並非針對對方的意見或策略,而是一種針對人格的攻擊,它的目的是讓對方的人格破產。比如:她根本不是個好人,或她根本不是一個真正的女權主義者等等。在Freeman的描述裏,這種攻擊方式通常是很蠱惑人的,而且是非常不真誠,非常過度的,它的目標是詆毀一個人,破壞一個人的人格跟名聲,讓大家覺得這樣一個人從根本上是一個壞人。
這種 trashing 到底會用怎樣的方式呢? Freemen 有這樣的幾個描述:trashing的第一種方式是假裝告訴你,背後其他所有人都覺得你做了很嚴重的一些壞事。比如在運動中突然有人跟你說,誰跟誰都認為你非常綠茶,認為你非常自私,同時她也會告訴你的朋友跟其他運動裏面的夥伴,說你說過一些關於她們很嚴重的話,聽起來就像互相在八卦一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看Freeman的那篇文章,裏面描述了她自己經歷的trashing的一些經驗。
此外還有一種方式,不管你說什麽做什麽,她們都會用否定的眼光來看待你。比如當你為運動寫一篇文章時,她們會攻擊你寫文章是為了奪取影響力,吸引眼球,為了奪取所謂的話語權等等。有時候trashing是會用極高的要求來對待你,比如,她認為你寫關於女權的文章必須具有非常高的規格,必須非常正確,否則你的文章都不值一讀。或者當你去做一個運動的,或是希望去幫助別人的時候,你的任何小錯誤他們都會認為是絕對的錯誤。比如我們希望發聲幫助鐵鏈女時,她們會認為你作為身在海外的留學生,身處這麽好的環境,說這些是風涼話等等。而當你想說我受到攻擊時,他們會跟你說,是你想多了,這時大家會發現這是我們很熟悉的所謂的gas lighting。這就是其中一種策略,它要否定你自己的想法,讓你自己覺得自己的想法是錯誤的。他們最後甚至會忽略你的存在,不管是運動中的會議,或是在平時的討論裏,你在網絡上關於某事件發表意見,他們都會認為你不存在,完全不理會你等等。這些都是Freeman自己經歷過的攻擊的方式。
這樣一種清理與謾罵 (trashing) 到底會產生什麽樣的結果呢?最起碼它侵犯了人的人格獨立,它貶低人的價值,汙蔑人的動機。所以對於運動而言,這樣一種針對突出個人的攻擊,讓女權運動變成一群人不停地在進行所謂的膝跳反應的批評。什麽是膝跳反應的批評?比如每次看到女權的行動或者是一些女權者寫的作品文章,我們第一個反應就變成了:讓我看看裏面有什麽問題,而不是去看這些行動與文章到底為女權運動作出了什麽貢獻。其中任何成就或錯誤,尤其是錯誤,都會引起對那些個人的動機的評判,比如說:她出賣了運動,她寫文章只為了自己獲利,或是說那個人是為了奪取進步運動和女權主義者的道德正當性,讓運動變成他們私相共享的資源等等。
一旦動機被攻擊,大家如果受過攻擊,就知道你是沒辦法反駁的。因為對方並不是針對你的文章或者行動,它針對動機:只要你的動機不純,你做什麽都是錯的。同時一旦被攻擊也沒法挽回,因為被攻擊的內容就是動機,既然我的動機不純,那我怎麽反駁呢?我沒辦法證明我的動機很好,每當我去試圖去證明我的動機很好,都會被動機所限製。
同時對動機的攻擊造成了另外一個現象:任何的辯護者都會不小心中槍。因為被攻擊者受到的是動機跟人格的攻擊,於是辯護者就變成了為不可辯護的人辯護,同時辯護者的動機也會受到質疑。比如對辯護者說,你因為跟被攻擊者的私人關系才會甘心為他辯護,這樣的攻擊沒辦法反駁。
所以這樣一種清理跟謾罵 (trashing) 不僅傷害攻擊者個人,而且會形成一種控製手段。我們看到的一些結果是,比如通過施加組內壓力來讓人服從,任何不聽話或任何反對的意見都會被質疑成動機不純,所以你只能夠服從正在攻擊的那一群人的要求跟意見。同時他們會通過組內結構來排斥一些有個性的個體,因為有個性的人意味著他們的策略或想法跟主流或有影響力的人不一樣。這一排斥會使得許多有能力有熱情的夥伴敬而遠之,然後使有建設性的批評被淹沒在惡意攻擊之中。
如果這些描述跟判斷是正確的話,我們會發現trashing的後果是非常嚴重的。當然不僅是對個人會產生影響,同時也會使整個運動或者是女權主義的發展會受到傷害。那既然如此,為什麽我們仍然會互相trash,互相清理和謾罵呢?以下就是一些相關的解釋。
3 Trashing的系統性解釋
在給出解釋之前,關於今天的分享,我有幾點要說明。首先今天的分享只關註那些系統性的解釋。什麽是系統性的解釋呢?也即我們希望找到的是關於為什麽女權運動或者是更廣義運動裏,會出現這樣一些互相攻擊的情況。我們不討論個別的攻擊,因為這些個別的攻擊很可能是出於個人之間的惡意,這些惡意是比較隨機的,我們沒辦法以此解釋運動內部或外部普遍出現的trashing,盡管帶有惡意的人肯定存在,但我們的目標是解釋普遍的現象,而非關註個人惡意的解釋。這是其中一點。
第二點要註意的是,雖然我會列出很多的可能的原因,但沒有一個單一的因素可以解釋這個比較復雜的現象。我們很難說其中一個原因是最重要的或主要的原因,所以我們在這裏預設清理現象是由多重因素引起的。另外要註意的就是,運動外的攻擊更復雜,出於個人惡意的可能性更高,所以會更隨機。所以我們在這裏只關註運動內出現的清理跟謾罵,或者是攻擊。講完這幾點我們就開始分析為什麽會相互清理。
我主要參考的是Holly Lawford-Smith剛發表的這篇文章 Trashing and Tribalism in the Gender Wars。這個圖就是Holly,她是我的導師,有必要要澄清一下。Holly 這篇文章裏面列出了非常多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她認為是部落主義 (tribalism)。所謂的部落主義指的是在一個運動裏面,比如在女權運動裏不同的派別跟團體之間出現的對抗而導致的結果:被攻擊者所受到的攻擊其實更多是一種公共信號,是給別人看的公共信號,用來維持派別之間的界限,並且向組內的成員展示忠誠。所以trashing通常會出現所謂圍攻的情況,經常會出現有攻擊的發起者跟追隨者,同時也向運動外面的人發出警告。
我們在運動中既然有不同的派別,就意味著有不同的關於整個運動的目標的沖突或競爭。而既然是一個運動,這個運動也就需要更多的人或是更大的影響力,所以某種意義上派別之間會出現這樣一種忠誠於自己的派別,希望獲得更多的資源和更多的註意力的現象。這自然也要求其他的派別獲得的註意力減少。因此有可能是這種部落主義引起了我們互相攻擊,把對方的派別打下來的需要,這樣我們才能夠推進自己的派別所追求的運動目標。這是Holly認為的第一個能夠解釋為什麽我們會經常出現 trashing現象的因素。
關於第二個因素,Holly認為是我們運動裏面所謂的反等級 (anti-hierarchy) 的目標。我們女權運動反對性別等級這一點大家都熟悉,這同時也會自然地應用在自身組織上。我們會認為女權運動是一個非常平等的運動,我們沒有所謂的階級和等級,我們是以反對一切等級為目標的,所以反等級的原則會是女權運動裏面很重要的組織的原則。
但是這個反等級的原則會讓我們錯誤地將突出或者是有成就的人的出現看作是等級出現的標誌。當有人成就突出,或者是因為發言很受歡迎的時候,這個人會很容易地被貼上機會主義者的標簽,也即當個人成就突出時,其他人會感覺到打壓他的需要,以維持所謂的反等級的組織原則。於是Holly認為在運動裏面,我們很容易因為非常強調反等級的原則,而產生了將擁有領導能力或擁有名聲的人看作是他想當領導或是他想紅的這樣的誤解,因此產生了要攻擊對方或攻擊對方的動機的現象的出現。這是Holly提到的第二個因素。
Holly解釋的第三個因素叫做內化的厭女 (internalized misogyny)。因為許多女性長期在性別主義的影響下會內化不少厭女的態度,即便是女權主義者也不例外,甚至特別是女權主義者:因為很多女權主義者很可能是曾經經歷過性別主義的影響或者是壓迫,最終意識到這一點後成為女權主義者,但這並不能消除我們曾經有過的厭女的態度跟信念。所以Holly認為有一些女權主義者相互之間的攻擊可能出於這一內化的厭女。
不過我認為這一解釋似乎是跟個人惡意一樣,非常隨機,很難去解釋誰到底內化了哪一些的厭女的態度和信念。但是trashing並沒有那麽隨機,我們會看到一些特定的人,或是在特定的場景中這些人會受到攻擊,而這些被攻擊的人會有某種可預測的共性,比如前面講到的,成就突出,或者他們的發言更受歡迎和關註。因此我認為內化的厭女解釋不能夠解釋為什麽會出現系統性的攻擊。
文章提出來的另一個因素是錯誤的、錯位的憤怒 (misdirected rage)。女權運動往往會更容易吸引曾經受過明顯壓迫的女性,不管是參與到運動的內部以至很核心的位置的女性,還是偶爾幫助一下運動、討論一下女權議題的女性。大多數人對於壓迫者是保持憤怒的,而且這些憤怒非常合理。然而比起壓迫者,受壓迫者因為有時會更靠近人們或者本身更缺乏力量,似乎會更容易成為人們發泄這些憤怒的對象。而清理往往是因為一些小事情而急速升級而成的。
我們似乎都有這樣一個經驗:我們看到女權主義者互相攻擊的時候,會發現背後的原因其實是非常小的事件,但會突然升級導致人們攻擊對方是一個壓迫別人,或者是出賣姐妹的人。這背後通常會存在一些額外的原因,而錯位的憤怒似乎能夠解釋這種額外的原因。為什麽我們的這些攻擊會升級得這麽快?有可能是出於女性運動裏面的女性的憤怒情緒。
另外一個相似的因素是我們過往的創傷 (unresolved trauma),而類似的女權運動更容易吸引曾經受過創傷的女性。總的來說,女權運動更容易吸引一些曾經受過創傷,且因此更具有攻擊性的成員。另外一點就是,女權運動的對抗性會使得本來就有攻擊性的成員更容易進入到運動,而且會表現更出色。我們看到女權運動或者是女權文章中,人們常常處於批判的態度去看待很多社會中的現象、或是法律等等。所以這就會使得女權運動或者是女權主義自身成為一種對抗性的、批判性的活動,那具有批判性或攻擊性的成員就能夠更好地發揮自己的能力,更容易在運動裏面突出,或者是成為有影響力或處於領導位置的角色。
另外一個因素與地位和權力有關 (status hierarchy and power grabs)。這是一個什麽樣的因素呢?這個因素可以如此闡釋:此前女性都是一些沒有社會權利和社會力量的人,那麽這樣的人在運動裏面能夠通過正義來偽裝自己,從而獲得更多的權利地位,而剛剛講到女性長期的受壓迫和被剝奪權利的地位,會讓女權群體更容易落入到權力鬥爭的心態中。同時在其他女性身上獲得權利和地位,比起從男性身上獲取權利和地位,是更加容易的一個方向。
歷史上的經驗就已經告訴我們女權運動一直在一種資源匱乏的條件下運作,而其他女權者很容易會被看作是資源的爭奪者。我們看到現在主流媒體裏面任何對這類議題的討論,在國內的討論裏面,很多都是男性在參與,比如男性討論國家議題、法律議題。一旦女權者加入,女權者能夠分享到的資源或者是獲得的註意力其實很少。而在女權者的團體裏面,又有不同派別或不同個人在競爭本來就少的這一塊蛋糕時,我們更容易把對方看成是這個小蛋糕的資源爭奪者,因此我們攻擊其他女權者就會使我們自身得到的資源變得更加安全。因為這樣子既沒有刺激到真正的權力掌控者,同時也允許自己自稱是好的,或者是真正的女權者,而對方是壞的或者是假的女權者。那這時候資源自然就必須歸到我身上,難道我們會把資源放到那些壞的、或是假的女權者身上嗎?這也是為我們互相攻擊,甚至是攻擊對方動機的其中一個可能的解釋。
另外一個解釋是嫉妒跟反感 (resentment and envy)。因為女權運動總是在有限的資源下面去做的,因此獲得大眾或者是團體認可的機會本來就很不平等,很容易就會出現只有某一些人出現在聚光燈下的情況。於是其他並沒有出現在在聚光燈下,但同時做了很多貢獻的人,就會產生一些合理的嫉妒跟反感。Holly前段時間才剛剛討論過這樣一個問題:在運動裏面通常會出現這樣一種情況,大家都有同一個目標,甚至大家都是同一個派別裏面的人,但是因為Holly比較隨機地或者是幸運地,被社會或大眾給予了更多的聚光燈或者說關註力,而其他的運動者,雖然大家都是盟友,會覺得我也貢獻了那麽多,為什麽你那麽有幸運可以獲得那麽多聚光燈,能夠推動你想要的目標,而不是我的目標,於是就會產生一些嫉妒跟反感。當這些嫉妒跟反感聚集到堆積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就會出現攻擊的可能性。這也是其中一個,似乎可以去解釋為什麽女權主義者之間會互相攻擊。
最後要講的一個因素,是一直以來大家會在腦海裏面出現的一個現象,就是正義的狂熱 (overzealous moralism)。為什麽會出現這樣所謂的正義的狂熱?最簡單的原因是女權運動或者女權主義是一種正義的事業,而參與到這樣一個正義的事業裏面,往往會讓人產生這種狂熱。因為我在這個正義的運動裏面,我代表的是正義的一方。而同時因為我非常在乎這一運動,或者是我非常相信這個運動或派別裏的一些信條,我就會覺得我不僅僅是代表了正義,我還代表的是一種純粹的正義。於是,這樣一種心理意味著其他人就算也在這樣一個正義事業裏面,他們跟我意見相左的時候,他們代表的並不是純粹的正義。而怎麽解釋他們不純粹呢?當然是因為他們的動機不純粹。於是這樣一種狂熱讓成員們忽略了所謂正義或正義的理論其實很多樣,而對自己的派別是最好的女權主義的確信,使得整個女權運動或不同的女權派別被帶到誰最正確的競爭裏面。
這也解釋了為什麽這種互相清理謾罵或是攻擊會是這樣一種對個人人格和個人動機的攻擊:是因為出現了比拼誰是更純粹的女權主義的行為,同時這也會使得中立的力量退縮,就像剛剛提到連辯護者也會中槍的現象一樣。這時候我們的trashing就變成了 virtue signaling / grandstanding這樣一種秀正義感的一部分。我是最正義的,其他人都不比我正義,所以你們必須相信我;其他人不純粹,所以你們必須相信我的目標是更好的。這種情況會使得不同女權者之間的不同策略變得非常難以理解。因此,我們就不再有派別之間的合作,而更多的是派別之間的攻擊。
以上是總結的一些關於運動裏面會出現互相清理跟攻擊謾罵的可能的解釋因素。再強調一下,並沒有一個所謂的因素能夠解決整一個復雜的現象。另外一點就是,這些解釋很多都是通過個人觀察所總結出來的可能的解釋,要進一步確定哪一些因素起到哪一些作用,可能需要更多關於這一現象做的實證研究或者是去討論才能夠得出。所以以上只是一些可能臆想出來的原因。
4 回到姐妹情誼的理想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就像以前寫政治作業一樣,我們要如何避免這樣一種相互攻擊?如何把姐妹情誼中的團結從這個攻擊的現實搬回到我們追求的理想中的姐妹情誼裏面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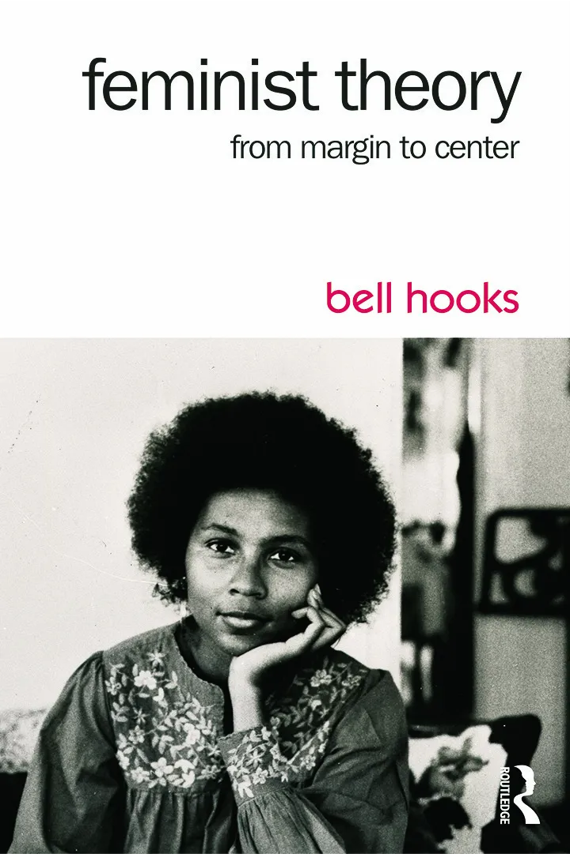
bell hooks,之前去世的很出名的女權主義者,她提到了一些關於女權主義裏如何團結的一些建議。比如她提到女性如何避免互相攻擊,女性不需要去消除所謂的差異來團結,這是我們需要去記得的。我們不需要通過所謂共同壓迫,來平等地為終結壓迫而鬥爭。我們有如此豐富的經驗、文化和觀念,這些財富可以互相分享,我們就是姐妹。因為共同的利益跟信念在向往多元中聯合,在總結性別壓迫的鬥爭中聯合,在政治團結中聯合。
hooks是什麽意思呢?我理解的意思就是,要實現性別平等,其實是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和策略的,這些毫無疑問會是持有不同意見的成員之間長期討論的問題。但是討論也恰好是女權主義者分享經驗與資源的最直接的方法,而不是互相在對方的碗裏搶資源。所以我們要團結的話,應該在和別人交流並且表達反對意見的時候,停止姐妹之間的互相猜忌防禦和競爭的行為。
同時我們要記住,每一位個體參與者都是獨特的,不然就不存在團結。所以每一位參與者都需要通過來自其他參與者的幫助來完成運動的目標。這是bell hooks提到的第一個如何避免互相攻擊的方法。
第二點我覺得是更有趣的問題是,其實我們會很少談論反思責任。反思責任有這樣幾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關於那些自然地成為了領導者的成員,或者是具有影響力的成員,她們可能首先需要去反思自身對運動的責任,無論是有組織的還是無組織的運動。在這個位置上的女性,不管有無意義,她們雖然經常會強調自己只是表達自己的看法,但是這個位置已經決定了她所說的話不再是僅僅為自己說話,不再是僅僅表達個人的觀點或是個人的看法,她們對運動是具有責任的。因為她們已經擁有了足夠多的影響力,在某種意義上已經把握了整個運動的方向,所以她們本身應該具有關於自己對運動責任的反思。當她們去發起,或者是參與到攻擊其他人的時候,她們需要去想她們的目標,或者是她們會對運動帶來怎樣的影響。
同時,我們每一個參與者也要去反思、明白運動的整體責任是什麽。尤其在女權主義運動裏面,個體參與者必須存在的平等的責任,或者責任的平等。這種責任的平等意味著個體參與者根據自己的能力堅持投身到運動裏面,那麽個體的參與者就應該被承認已經盡到責任。我們不應該以過高的要求對待每一個個體的參與者,同時也意味著每一個參與者需要被平等地對待,他們的貢獻都必須有獨特的價值。當然,那一些更早參與的,或者是付出更多個人代價的,我們會認為她們更值得我們去敬佩。我們應該給予她們更多的關註,但不代表其他的參與者,她們的責任或貢獻、價值就可以被忽略,或者是可以被貶低。
這是第二點,我認為我們需要做到的。
最後一點我認為需要做的,是我們如何做到真誠地去反對。我們去討論和實踐正義目標,不是為了分辨誰才是道德上更純粹的,誰是正義路上的偽裝者。不同意見的雙方互相提出的也可能是真誠的反對,我們應該去反思這樣的一些真誠的反對意見。同樣的,如果我們不同意對方的言說跟行動,我們應該真誠地提出我們的反對意見,盡量充分地提出理由。我們需要去避免過分質疑對方的動機,別讓自己對對方動機的質疑影響到我們提出的理由。
最後我想分享Louisa Alcott的一句名言 「help one another is the part of the religion of sisterhood」。以上是關於這個topic的我的一些分享,謝謝大家。

Q & A
Q1:化妝是女性內化,非女性自發的男權背景影響下的產物嗎?
A:我們可以認為是一種這樣的文化。但如果要考慮是否是男權影響下的產物的話,可能需要去看歷史。的確歷史上所謂的化妝,或者是更廣一點的所謂的 beauty norms 這些關於對女性的美貌規範,是男權影響下的產物。我們看到現在那麽大的美妝行業,其中裏面非常多產品的目標們都是美白、皮膚的幼嫩等所謂的護膚目標。然後還有化妝以外的其他美貌的產業,包括比如現在越來越流行的各種整形等等。我們看到這些產業背後很多都是會有所謂的男性中心的影響:比如男性普遍更喜歡這樣的一個身材的女性,從而影響到女性關於審美的態度。至於有沒有女性自發的想要去追求美,做這樣一些行為,當然也會有。但我覺得這並不是問題所在。
問題在於,當女性去自發想要追求美貌標準的時候,我們更應該問的是,這個標準到底是怎麽樣的?假設全世界女性都內化得非常自發地想要取悅自己,去不斷地減肥,我會認為更大的問題在於減肥這樣的一個事情上面,比如這個目標到底是不是合理的,像現在的各種的關於瘦的這個目標,是不是對於女性來說是過分的要求,會忽略了正常女性其實有非常不一樣的身材的標準和要求。那我們可以更多地討論這樣一類問題,而不是關註女性她們去化妝到底是不是媚男,到底是不是自發,到底是不是內化的某一些東西;去談論我們如何能夠改變那一些非常苛刻的、對於女性身材的、女性內化也好、外在的壓迫也好,所帶來的各種的壓力跟規範。這是我對化妝問題的看法。
Q2:女權運動中的社群暴力現象是獨有的嗎?
A:這是個非常很好的問題,這也是本身討論這個問題需要去追問的一個問題。到底 trashing ,或者是互相攻擊是不是女權運動裏面出現的獨有的現象呢?很多人會認為這並不是一個獨有的現象,而是整體的左翼運動或是進步運動會出現的現象。第一就是左翼運動化。進步運動常常會是代表正義的一方,所以會更容易產生所謂正義的狂熱。出現互相攻擊的情況,是因為運動中肯定會有不同的派別,認為自己的目標更純粹,或者是更正義。我們看那一些左翼運動裏面,比如前些年的美國的大選,明明是左翼運動,明明都是在共和黨裏面,但還是會出現很多互相攻擊的情況:比如站在桑德斯的一方對站在希拉裏這一方的攻擊,覺得他們並不夠正義或並不夠左翼。從而使得在大選的時候,當桑德斯輸給了希拉裏,希拉裏成為了民主黨的候選人的時候,很多人因為覺得他們不夠純粹,不是真正代表進步運動,轉而去支持了川普。所以在某種意義上也會導致這樣一種攻擊跟所謂的背叛的行為出現。所以我認為社群暴力並不是獨有的是女權運動裏面的現象,但是我們會在女權運動裏面看到很多的表現很多這樣一種情況的出現,這是我的一個看法。
Q3:trashing是否是網絡時代的產物呢?
A:我覺得並不是。比如像Freeman描述的:在 70 年代她受到的 trashing 就肯定不是網絡時代的產物了,因為那時還沒有網絡。現實的運動裏面也會有線下的攻擊,特別是當你不在那個現場的時候,受到的攻擊自然就多了。但社交媒體自然我會認為是加強這種情況的一種原因。因為我們一看,你發一條微博或者發一條朋友圈,同種看法的人就會一呼百應的出來了。那自然會增加這一種攻擊的可見度,同時也會增加發起攻擊的人或參與攻擊的人的數量。因為大家互相點贊,或者是大家互相轉發之後,對他們產生了一種鼓勵的作用。並且,他們獲得了這樣的一個鼓勵信號,那可能會激發了更多的這樣攻擊。因為我知道如果我這樣攻擊誰的話,我會獲得更多的資支持或者更多的贊賞。畢竟社交媒體整個運作就是基於這樣一種鼓勵和點贊的原則去建立起來的。所以我認為社交媒體化網絡時代不是攻擊的唯一原因,但是當然也是加強了攻擊普遍化的因素之一。
References
- Atkinson, Ti-Grace. Amazon Odyssey (New York: Links Books, 1974).
- Chesler, Phyllis. A Politically Incorrect Feminis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18)
- Filipovic, Jill. “The tragic irony of feminists trashing each other,” The Guardian, 2nd May 2013
- hooks, bell. 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re (London: Pluto Press, 2000).
- Lawford-Smith, Holly. “Trashing and Tribalism in the Gender Wars” in The Moral Psychology of Hate, eds Noell Birondo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2022)
- Lewis, Helen. Difficult Women (London: Jonathan Cape, 2020)
- Lowrey, Kathleen. “Trans Ideology and the New Ptolemaism in the Academy,”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ur 50 (2021), pp. 757760.
- 刘满新《我是清醒的厌女者吗?》
- 刘满新《我是仅仅在秀正义感的女权男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