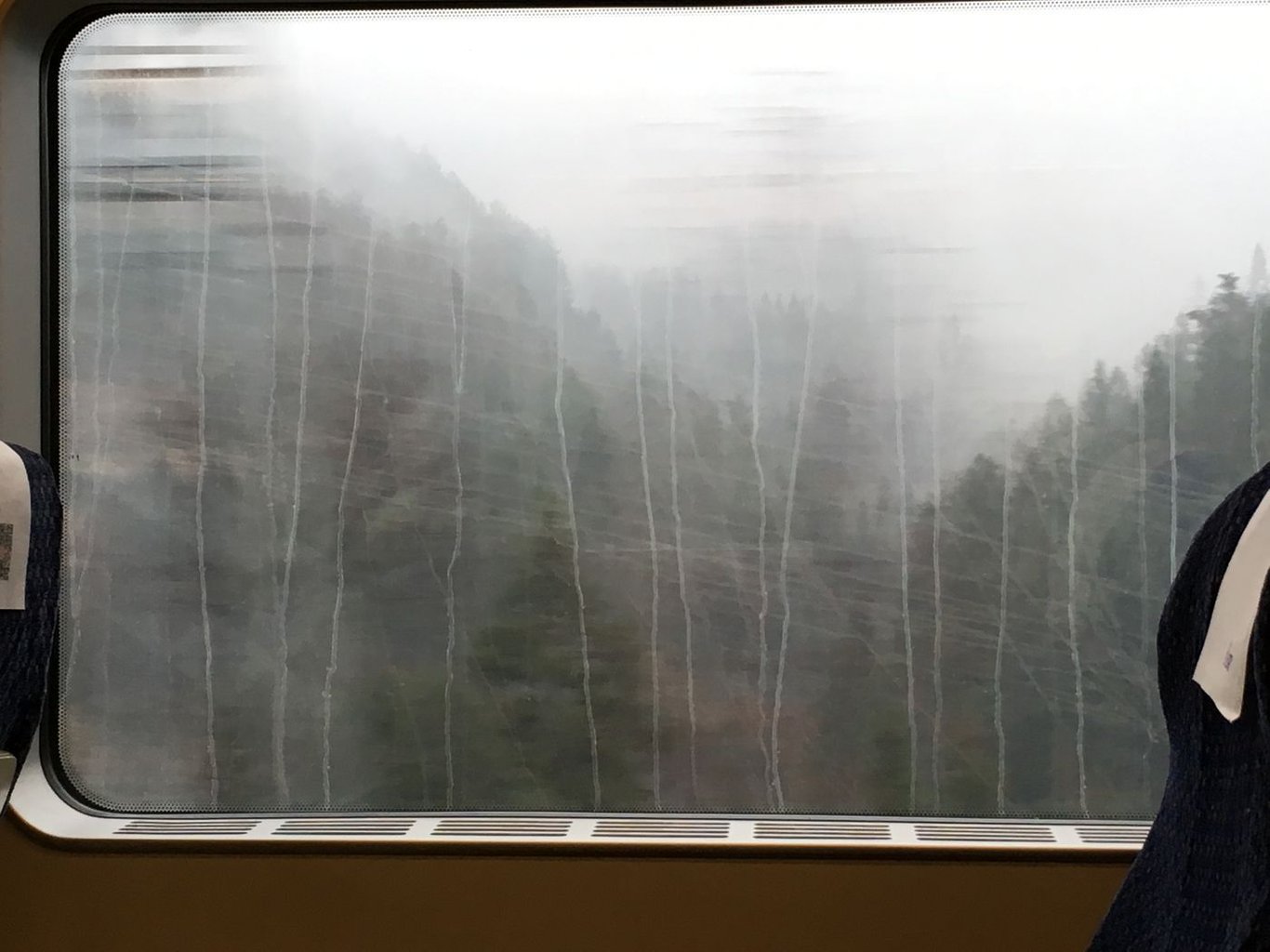瘟疫日记2020.03.01-02 "当洪水从天上浇下时,你站得高一点,你能避开吗?"
为什么我会有“亡乡感”?因为瘟疫打开了隐藏在社会里的恶臭和腐烂,那个轰轰在运作的“熟人社会”机器在崩坏和食血。我一直知道它兼具体面的外表和猥琐的内在,令我伤心的是那个机器在垮掉之前要先卷走许多无辜的个体,卷走无数回忆、对归属的想象。我本来相信人与生俱来的韧性、危机面前本能的合作精神,可现在我更相信人的卑微。在这一切之前,体制的一粒灰,落下来是个人头上的一片云,要是你有所准备带了伞,还能躲过一场雨。有个别人躲不过,但绝大多数人可以。瘟疫是一个滤镜,新的画面里,他人即是地狱,我们都失去了平时的色觉,无从分辨。那粒灰是一座山直接落在人的头上,许多人还没来得及呼救就死了。经历痛苦的死人说不出话,经历痛苦的活人失声痛哭,而故事由打胜仗的人书写。是的,我看到有武汉人说,我们刚刚要把胜仗打完了,说什么丧气话。
我反感武汉的“熟人社会”那一套,我也深知武汉人离不开“熟人”,这是我最恨的一点。在熟人社会里,如果一件事情做得漂亮、顺利,不是因为体制按照正常运转的结果、不是谁做都会得到这个结果,而多半是因为你认识某个人、某个关系、靠某种门道、借某种契机,总之是绕过了正常程序把你作为一个特例去解决了。又或者,如果你了解某些信息,不是因为你作为一个公民享有这个法律权利,而是因为你有某个亲戚、挚友、熟人在某个显赫的位置工作、认识某个在显赫位置工作的人、偶然地有某种特殊渠道而获得小道消息。如果你坐在某个位置,即使没有任何资历和知识你也有发言权;你有再多资历和知识而不坐在那个位置,零发言权。熟人社会就是由无数个“以小团体为中心的资源共享网络“组成的,公私不分、里合外应。这些网络的硬核通常是钱、官、权、某种稀有的社会资源。会打胜仗的人,一定是离“硬核”近的人。反过来如果你拥有硬核中的某一项,那你就摆脱不了一个巨大的人际网络要罩着你、牵制你,你必须要做其中的一员,服从其中不成文的规则。“武汉嫂子”用过的两个成语:沆瀣一气,一丘之貉,就是这个意思。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武汉人,说老实话我每每看到”大单位“里人与人见面后开启那种互相拉关系的汉味精英谈话模式,都觉得扑面而来的熟悉、虚假、尴尬、厌恶。(任何其他味道的精英谈话模式也都让我觉得虚假、尴尬、厌恶。)许多事情因为我后来离开了,了解得不深,但不妨碍我深深体会到个体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的某种可悲处境。当然了,许多当事人乐在其中、生龙活虎、大展身手、毫不可悲;也有人时而如鱼得水、时而反思叫苦;此外,还有人选择不做”打胜仗的人“,那他们也选择了更加自我独立、更加不稳定的生活。独立的灵魂我也在“原生社交网络”之外遇到过一些,这次封城之后我也在网上看到了几位,我很喜欢她们在武汉的存在。——写了这么多得罪自己家乡人的话,这是我第一次想要把一些模模糊糊零零碎碎的感觉写下来。不一定准确,以后想到什么再纠正。
3月1日,《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正式生效。有消息说,零点刚过就有一批公众号被屏蔽。我还看到一篇“南湖读书”微信公号发表后被删掉的文章写国家网信办所颁布的这个规定,并不具有法律法规的效益。因为网信办属于国务院办事机构,其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属于规章,不得设定行政处罚。“在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度,却公然实行马克思当年反对的法令,怎不让人汗颜。”
同日《人民日报》微博发布:武汉市硚口武体方舱医院“休舱”,送出34位康复的患者出院,同时讲剩余的76名患者转诊,不再接受患者。官媒的消息永远都是那么铿锵有力,毫不拖泥带水。同日有人问:为何汉口和武昌有方舱关门,而汉阳似乎仍然床位不够,仍有确诊病患没有被转移留在小区里。还有人在微博发布自家附近还在建设未完工的方舱医院照片:“噢买尬,心情好复杂。”
云南临沧市爆出强制全市中小学生、家长和教职工服用“大锅药”的新闻。注意,是所有人哦。大锅药是什么?就是给你一个清单,去中药店买原料,无特定剂量和比例要求,自己熬制,所有人都要喝。家长被学校要求在家长群里上传喝药照片、视频,还有买药的小票,以此作为春季入学报名的条件。网上被广泛流传,曝光后的第二天这件事被制止。
微博上“二水柚子茶”写下了自己母亲因为非冠状病人的医疗资源被抽断,在癌痛的折磨、彻夜不眠、几乎不再进食的情况下,自杀未遂,后来在医院痛苦的去世的过程:
“现在武汉又公布了增加重症和慢性病购药的药房,每个中心城区两家药店。以往是全武汉市只有两家,还都在汉口。现在官员们醒悟过来了?承认这类人群了?在隔离了各行政区后,这些病人怎么购药?而没有医院门诊开放的情况下,没有办法检查化验,光吃药?真的是天真。唉,聊胜于无吧。本来这些举措公布出来就不是给病人看的。
那天,我看着我妈的心电监护慢慢停止,疯狂的大哭,医护人员过来指责我影响到他们的治疗环境。太平间很快来拖人,医护人员要我赶紧收拾东西跟遗体一起走,一刻不能停留。即使我们进院时,已经都做过筛查,不是病毒肺炎。我兵荒马乱,不停收拾,连给我妈擦身换衣服的时间都没有。在太平间,工作人员告诉我,其实疫情肺炎死的人只有三成,剩下带来的被剥夺了救治权利而亡的人多是我们这样的重症病人,尤其是白血病和透析病人最多。
下午二点,武昌区殡仪馆车来了。你们看到过遗体用裹尸袋装了后,像码白菜一样摞在那些车里吗?因为疫情,因为非常时期,殡仪馆的车是出来后挨个医院收尸,不可能再像正常时期那样,一车一人,有棺材装着。拖回去后两个小时内火化掉,不允许家属跟,疫情结束后电话通知我去领骨灰。我甚至都怀疑,在如此背景操作下,领回来的骨灰会是正确的吗?这样的经历,我终身刻骨铭心。
我一直以为治病两年的痛苦是极限了,却遇到的天灾人祸,被剥夺治病的权利。最后还没有办法办任何后事。太多我妈这样的病人被牺牲都不计入数字,也不会公布。外面一片歌功颂德,一片形势大好。
仿佛集体失忆,一个城市难道其他病都不会生了吗?我姨夫尿血,没办法去医院检查;同一个医院的病友,没办法接着化疗,只能等着疯长癌细胞;网络上孕妇求助的仍然有;胆囊手术的,眼科手术的,急性阑尾炎手术的,胃溃疡吐血的,脑梗发作已经半身麻痹的……中国梦,还要继续做下去啊。”
关于“史上最严网络言控”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端传媒有一篇深度分析。引用几段在此:
“福柯認為,「治理」的邏輯與「統治」的邏輯不同,這二者之間有一個微觀與宏觀的辯證差別。對於傳統社會的「統治」者而言,統治是宏觀的,統治者高高在上,並不介入到被統治的社會的微觀運轉之中;同時,被統治的對象則是個體的,他們並不被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進行分析和監測,而是僅僅在個體犯罪時被施以懲罰。現代國家的「治理術」則不同,治理者需要精密地調控社會的微觀運行,以期得到最高的工作效率和最大化的穩定。而這又要求治理者將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實時監控、進行不斷的規訓,去干預人的意識、塑造人的主體。
這些規訓假借健康、快樂、幸福之名, 「讓每個人更好地生活,然後為國家所用」。而與此同時,個體的人則不復存在,成為龐大人口的一部分,成為社會趨勢的一部分,成為一個統計學概念。這個思路自然地引出了《規定》標題中的「生態」一詞。在今天的中國,輿情被作為一個生態系統處理,它既無所不包,又需要細緻入微地考察每一個微生物的作用。哪個明星發了張照片擋住了一隻眼睛,哪個偶像在餐廳抽煙,哪個微博用戶抱怨食堂不好吃,哪個微信公眾號發了慶豐包子起源考,這些內容都有可能成為一場「輿情爆發」的導火索,都需要時刻監控和審查。畢竟,一隻蝴蝶在這個生態系統裏振動翅膀,是可能引發一場地震的。
於是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今年一月初,中國官方對病毒不慌不忙,卻對「造謠」如臨大敵;又為什麼現在一個人在社交網絡上發布一則求助信息,就可能被告知自己發布的內容含有激進意識形態或敏感信息。畢竟,對國家而言,個體人的健康僅僅是一個個體的問題,輿論環境的「健康」卻是關係到社會生態的「大事」。《規定》的生效或許正標誌着這種治理的常態化,一切生活都是政治生活,一切思想都是意識形態。
諷刺的是,官方宣揚的「正能量」卻被排除在「政治」的話語範疇之外,而一切跟政治有關的討論,都是天然危險的——日常生活的政治化,是通過去政治化的宣傳話語來實現的。一切「負能量」被政治化的另一面,是國家的權力被中立化,被包裝成平靜美好生活的守護者和大前提。宣傳部門收編了「哪有什麼歲月靜好,只不過是有人替你負重前行」這樣的流行語,在政權的維穩與人民的生活之間建構出一種似是而非的聯繫,進而將之發展成專制統治的合法性依據。這種宣傳既是專制話語權力的產物,卻也在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紀初「告別革命」的思潮中找到了連續性,並最終讓這二者獲得了對立統一的大和諧。
正如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楊國斌教授的研究顯示,官方認可的「正能量」、經過「文明淨網」後的內容,往往得以披上「中立」、 「客觀」的外衣得到傳播和辯護,而他們對「悲情」、「憤怒」等抗爭性的「非理性」情感的驅逐也因此顯得無可厚非。這種理性權威的話語試圖達成這樣的結論,即官方的立場不是政治,不是意識形態,而是理所當然,是應當維護的常態,是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輿論「生態」只有在這種「常態」下才是健康的。而這種「常態」下的人們,往往只是想要追求與政治無涉的「歲月靜好」,便落入了權力的圈套,成為「生態治理」的積極參與者。“
最近我被朋友问到:花那么多时间看新闻的意义在哪里?我也问我自己:有什么事情是非要我知道,不知道就不行的吗?——没有。可是,我觉得那些欲辨已忘言的事、荒唐糊涂透顶的事、让人伤心欲绝的事,如果只是静静地发生、静静地被执行、静静地被删掉,这些事情没有被见证,岂不是这个时代里的人更大的悲哀?如果洪水要从高处落下来,那请也落下来我要听个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