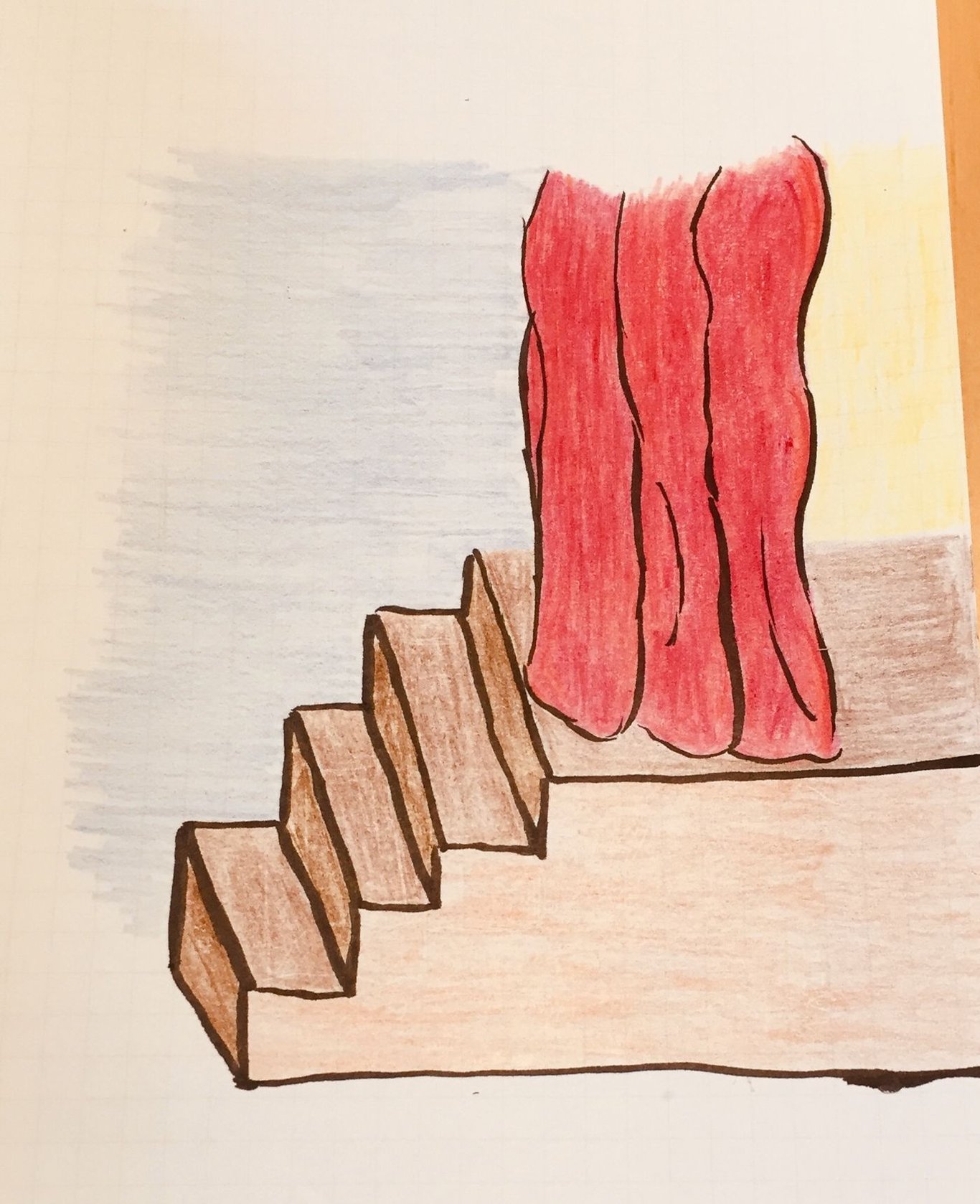版權所有
「解約?」
「嗯。」煦誠避開我的視線,心不在焉地翻弄著義大利麵。「不要那樣看我好不好,其他人也那樣覺得。」
「可是——」
「——我當然也知道這樣很對不起版權。」他叉起一片燻鮭魚,「可是不能再這樣下去。」
版權是她的藝名。她姓秦,英文名字叫Charlotte,縮寫是CC,所以就半開玩笑地叫版權。
「什麼意思?她最近哪裡不好?」
我皺起眉頭。版權對我來說已經是完美的歌手了,她的技巧、咬字、音準都無可挑剔。
煦誠終於抬頭看我,「不是最近。」
我更困惑了。版權是兩年前來的,當時她的聲音驚豔我們所有人。訓練時她總是一點就通,不需要煦誠費盡唇舌。當她的第一張專輯《版權所有》——詞曲煦誠讓我全權負責——發行時,我們都親眼見證什麼叫做一夜成名。連我這個以爲只有歌手才會紅的詞曲創作者,也沾她的光得到了一點知名度。我記得我和她坐在電腦桌前看著Spotify for Artists的數字不斷增加,興奮地擁抱彼此。上個月她推出了第二張專輯,那甚至比《版權所有》還熱門。最近一部電影的主題曲也是指定由她來唱,我看不出她能有什麼嚴重到要解約的問題。
「我知道她的聲音很棒,」煦誠說,「可是⋯⋯她就不能多放一點感情嗎?」
我放下刀叉。「哪有人這樣就要解約的。」
「不是,」他急急說道,「她完全不放感情的話,那就不是音樂,只是旋律而已。你懂我的意思嗎?」
「她有嗎?」我回想版權唱過的每一首歌。的確,她每次錄音都不會哭,不管是多感傷的歌都一樣。我一直以為這是好事。「我聽不出來。」
「可能是我被她的聲音吸引陷進去了吧,剛開始聽到的時候真的覺得非常完美。」他若有所思地說。「可是我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一直聽那種音樂會中毒的。」煦誠望著我,眼神幾近懇求。
「煦誠。」我嘆了口氣。
「你知道我的意思。」他說。我伸手拿帳單,卻被他搶先一步。「先不要讓版權知道好嗎?我想讓她好好唱。」
版權的聲音,我想著。雨刷搖晃著像不太準的節拍器。
版權的聲音似乎一直都是最有代表性也最穩定的。有一次她得流感,高燒三十九度,我開車載她去醫院,一路上她仍然用明亮的聲音和我說話,指著路邊卡車的「尿素」字樣問我什麼意思。
版權奇怪地敬業。給她任何指令她都二話不說照辦,對我的作品更是從來沒有任何意見。明明她是那種連午餐吃什麼都可以爭論半小時的人。
我從來沒想過會有今天。臨走前我在店門口試著說服煦誠,在下個月表演之前訓練版權多放點感情。「她很有天份。我們沒有必要直接讓她走。」我說。他看著我很久很久,最後終於點頭。
第二天版權進錄音室錄電影的主題曲。那是部愛情片,悲劇收場,非常悲傷的一首歌。
錄到一半,煦誠清清喉嚨,試探性地發問:「版權,你有失戀過嗎?」
版權眨著眼,「沒有。」
「也沒談過戀愛?」她還是說沒有。
煦誠沒再多說什麼,只是點點頭讓她錄下去。
結束後我叫住版權,說有些話要告訴她。
「我說了你不要生氣喔。」
「當然不會。」她說,疑惑地看著我。
「不是說你唱得不好…只是煦誠希望,你唱歌的時候能夠多放一點感情,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練習一下。」
版權欣然答應。我們花了一整天聽我和她最喜歡的歌手的作品,比較他們的語氣和用感情的方式,再把下個月要唱的歌都練習了一遍。版權非常認真地聆聽,沒有表現出一點疲倦。
下下禮拜彩排,我們還有很多時間。我以為這樣就可以讓煦誠滿意。
版權輕輕唱出最後一個音。完美。當然很完美——她已經連續練習了兩個禮拜,連在回家路上她也跟著車子的音響唱。我微笑著,轉頭去看煦誠。很好,他完全不滿意。
「版權。」他說。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錯覺,他的聲音有點顫抖。
「嗯?」
「這些歌你應該很熟悉吧?」煦誠說。版權微微點頭。「他有沒有跟你說過歌詞大概是什麼意思?」他用大拇指朝我的方向比了一下。
「有。」版權謹慎地說。
「那我希望⋯⋯你可以稍微揣摩一下歌詞要表達的情緒,好嗎?我們再來一次。」
顯然版權不清楚煦誠的意思,因為她又照同樣的方式唱了一次。煦誠似乎快抓狂了。
「你真的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嗎?」他大步走上臺,全身因激動而顫抖。「完全不知道?」
「煦誠,冷靜一點。」我說。版權不發一語。
「不是,她怎麼可能不懂?要怎麼完全不懂?」他叫道,「天啊,我真的不知道⋯⋯到底為什麼⋯⋯」
彩排草草結束。我像平常一樣載版權回家,她一路上都保持沉默,說出口的話只有「謝謝」和「再見」。下班的她比誰都倔強。
我又回去找煦誠。他似乎冷靜了一些,右手輕輕壓著太陽穴。「對不起,我真的沒辦法。」他抬起頭對我說。
煦誠以前也會作詞作曲。他曾經也寫了很多歌,給不同的歌手唱,獲得不少好評。我認為他比我還有才華。但是在快三年前,像什麼東西斷掉了一樣,他突然寫不出曲來了。煦誠一直都是先有曲才填詞的,連帶他也沒辦法寫詞。一開始他還掙扎過一陣子,每天坐在鋼琴前好幾個小時,像一種絕望的儀式。後來他還是澈底放棄了,成了今天的角色。今天也許是三年來他最靠近過去的一天。
「她唱得不一樣。」他安靜地說。
「對,我們練習過。」
「她是聽別人的嗎?我很抱歉,但是那聽起來不真實。她不是真的那樣感覺,對不對?」
我告訴煦誠我們這幾天我們練習的過程,包括我們聽了哪些歌手的作品,還有版權怎麼模仿他們。
他搖搖頭。「感覺不對,就是不對。我實在沒辦法看著她把技巧擺在感情前面,如果她還成功的話,那我⋯⋯」
「別說了。」我輕聲說。
煦誠低下頭。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都沒有開口說話,最後我打破沉默:「你希望她那天怎麼唱?」
「我不知道。」他望著我,眼中盈滿困惑。「讓她自己決定吧,我真的不知道。」
彩排、彩排、彩排佔滿了我接下來的兩個禮拜。版權決定照練習後的方式唱,而煦誠再也沒有對她發表過意見。每次結束後我都先載版權回家,再回頭拉煦誠去吃飯。他最近有點回到過去的徵兆,我不能讓他有任何踏進琴房的機會。和已經恢復正常聊天頻率的版權相比,煦誠話少很多,也不再提解約的事。我知道現在他不可能讓版權留下,應該說我從第一次彩排就知道了,不過表演結束後我會以觀眾的反應為理由再求他一次。
我以為我對版權隱藏的很好,但是在正式演出那天,上臺前幾分鐘,她突然穿過整個後臺來找我。
「這是不是最後一次?」她直視我的眼睛。
「什麼?」
「快點,這關係到我十分鐘後要怎麼表現。」
「版權,不管這是第幾場,你都——」
「快點。」
我深吸一口氣。「對。非常有可能。」
她立刻轉身走上臺,沒留給我任何解釋的時間。
對那些不知道後臺發生什麼事的觀眾來說,這的確是一場無懈可擊的演出。他們對每一首歌都報以熱烈的掌聲。
但是在應該謝幕的時候,版權說:「最後我想唱一點我自己的東西。」她轉向後面,「可不可以借我吉他?」
她慢慢溫柔地撥著弦,哼出幾個音。起初很小聲,我幾乎不能辨認歌詞。
「不管我的選擇有多麽貧瘠
我都不能跪下乞求肥沃的土地」
這是第一句我能清楚聽見的詞。旋律零散而破碎——版權一直都不太會作曲——但是她的聲音有什麼不一樣。有什麼完全不一樣。
「我隔著一道牆 他很依賴
為了失望而等待」
她的聲音壓抑近乎哽咽。這不是我或煦誠或任何人給她的,這是她自己的東西。
我回過神來時觀眾已經在鼓掌了。版權深深鞠躬,說著:「二〇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All rights reserved。」隨即轉身下臺。
我望著她的背影,用手指抹去臉頰上的淚水。
「是不是煦誠提的?」版權鑽進車子裡時問。
這次我沒有假裝聽不懂,我們都很清楚她指的是什麼。「我不知道,我希望不是。」
「但是只要他幫我說話,我就一定可以留下來,對嗎?」
「對。」我不情願地說。
我沉默地開了五公里左右,然後我說:「你怎麼會知道?」
她聳肩。「你說上臺前嗎?隨便猜的而已,誰知道你真的會承認。我只是⋯⋯覺得煦誠最近很奇怪,尤其是對我。」
我原本打算再問她一個問題,但一看到她的表情,就又閉上了嘴巴。
我在她家門口停下時,她轉過頭說:「謝謝你送我回家。」比平時還長的句子。
「其實那天結束後他們就決定要讓她留下了。」煦誠把葡萄酒注入高腳杯,比平常多倒一公分。「然後我會走,這樣她就可以回來。」
我搖搖頭。「不可能。她已經下班了,她比誰都要倔強。」
那天過後版權就再也沒出現,似乎也沒有人試著找她回來。
「煦誠,我問你,到底是不是你提議的?」
他一副棄械投降的樣子看著我。「不是。一開始是他們說她不夠有特色,她會被取代。她不會一直年輕。」
那為什麼你不站出來支持她?我想著。但是看到他落寞的神情,我實在不忍心再繼續施壓。
煦誠彷彿看穿了我。「我知道我可以說服他們,但是⋯⋯我很抱歉。」
「你很驚訝嗎?那時候。」
他閉上眼睛往後靠。「當然。」
一切像是回到版權來之前一樣。我繼續寫歌,等著有人來唱。煦誠像抗拒不了似的又回到寂靜無聲的琴房。
我常常在想一個問題,那天沒有問她的問題。到底她歌詞裡的「他很依賴」的他是指我還是煦誠?
直到現在我還是沒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