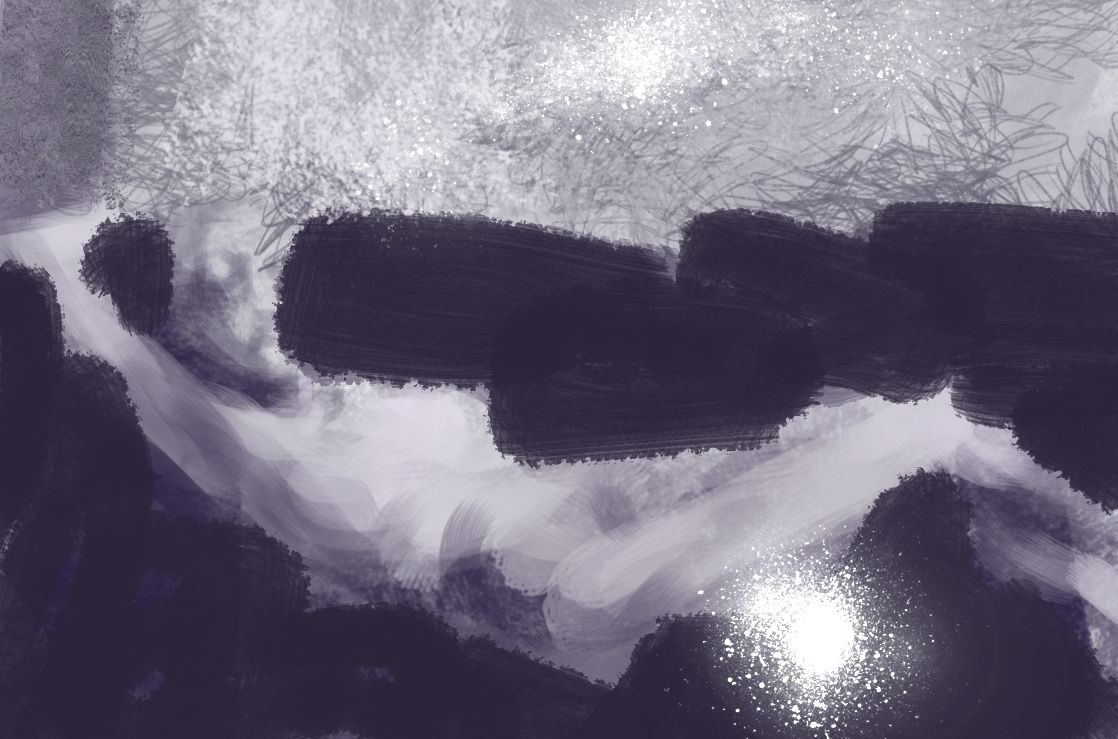参与式艺术:澳大利亚(两篇)
这既是一位艺术家的作品,也是我微信朋友圈的二三事(首发微信公众号Mundans )。
第一篇:《澳大利亚第三天》
《澳大利亚》是艺术家刘伟伟的项目。我本来不想再过多关注这个了,因为朋友圈里了有围绕着它引起的狂欢,但周琰说引用我发在朋友圈的话,一经讨论,她就鼓励我写下来。对于赞美和鼓励,我总是特别受用。
刘伟伟的弟弟刘超,拍出视频让观众投票,决定他是否移民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这个项目的第二部分,也是相当引人注目的一部分。一开始移民选项的票居高,很快,刘超留在中国的选项,就被刷票了。当晚,刷票团的一员,就跑来跟我说了是他做的这件事,以及他们成立了“决定刘超命运办公室”,简称“决命办”,以及他们的其他计划……(我对他所告诉我的内容不会对外公开,除非他已经自己公开了)。昨天,“决命办”贴出一张公告,刘伟伟也对此回应,算是这项目带来的第一起波澜。我基于此,在朋友圈打下这段话:
刷票挺没意思的。
虽然这是件可以严肃、也可以轻松对待的作品。但就我个人来看,艺术家选择刷票、成立“决命办”的行为,是依附于刘伟伟的项目上的,这和之前李翔伟依附上海双年展做的那个项目,在这点上是一样的(艺术家离了艺术圈、艺术体制,就不是艺术家了嘛?)。如果作为一个艺术项目来说,这个大动干戈的行为就变成刘伟伟这个项目的附加品,这是第一个没意思。
而就像刘在下文提到的一些拉票方式,刷票比拉票,是没意思的。更何况也谈不上是反对刘伟伟,或者刘伟伟的艺术项目。依然在两兄弟设置的游戏逻辑里。这是第二个没意思。
总之,绕来绕去都是些小圈子,比较让人失望吧。
最后,我不确定这刷票的动机,是否因为有决定他人命运的机会而产生,对决定他人命运,支配他人的热情,我持反对态度。在这类事情的态度上,我很消极,也是在伴随我父亲走向死亡的时候,意识到的,人既不能背负他人的命运,也不能希望自己的命运由他人负责。生活的重量,命运的路,总是独一份的。
可能作为社群动物的人类,无可避免地要处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震荡之中;处在复杂的社会结构权力结构之下;身于历史堆叠的谬误所指向的、不可回头的时间之箭上。人的境遇是如此复杂,而大部分,平时可见到的艺术,也谈不上是面对了复杂情境之后的回应,甚至也说不清自己要说的事。
在这段丧气的随笔里,关于命运那句话,比较暧昧地表明里我对整件事情的态度。当然,也仅仅是事情本身而已,即:
1.刘超让别人替他做决定;
2. 刷票行为。
除去事情本身,这个事件带来的风波,围绕此产生的讨论和艺术项目本身的架构,要比我的态度更热闹、有意思得多。
在伦理上来说,这个项目本身,并没有问题,刘超是积极主动让度自己的决定权,如果说有什么被迫,那也是诞生这两难选择的社会语境。而这个项目,就诞生在这样的语境之中,也反过来揭示这一语境:是什么,使一个已婚的工人想要移民?
我在项目一开始,就想起阿伦特的论自由,她说道,除了内部自由还有外部自由。外部自由即“我能做什么”,那个“能”,与自由紧密挂钩*。这个项目,看上去是刘超把自己的选择权交出来了,但反过来,反应了他在移民这件事上的不自由。因为生活习惯也好,政策也好,能力也好,他移民的艰难,就显示了他是不自由的。这样来看的话,投票结果是留在中国,不过是继续他的不自由罢了。如果结果是移民,那为了获得这一能力,他要付出的代价,足以让他一次次地深刻感受自己的不自由了。
阿伦特说到在古希腊,只有进入政治空间,“与平等的人比肩,方可自由”*。那么借用王楚禹形容电信工人是“权利难民”的一句话,刘超也是奋力挣扎的难民,可能可以叫做“政治空间难民”、“自由难民”、“平等难民”吧。
而随着刷票的风波,这个艺术项目本身的结构,也进一步显露了出来:
首先是关于契约:一个压上命运的,与公众的合同。这是刘伟伟对契约精神的执着,以及展现。其次,这是一个神圣投票,说它神圣,是因为它绑定了一个人的命运。而这个人就会被投注许多期望,仅仅是目光也足矣。
其中,这种社会契约与神圣投票的仪式感,以及所带出来的政治空间,在国内是几乎不存在,或者存在也是不可见的。二兄弟以自己的命运,设计一个有爆点的适宜传播的形式,来撞击社会现场,将政治空间带入人们投票的手指上,让政治空间得以延展。命运如果看作是一个人一生的肉体轨迹,那他们是选择肉搏的方式在撞击现实政治。
这契约的严肃,带来了在国内环境下,称得上是珍贵的机会:
因为没有机会投票,所以有这种好好投票、严肃的投票机会,它很珍贵,但它的严肃性与珍贵,是因为绑了别人的命运,投票决定别人的命运,这又很残酷。
“决命办”,考虑到他们都是艺术家,或许我可以猜测,他们要用刷票的手法,将这种残酷表现出来,以撼动原本的契约。与此同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投票,到底是过程,还是结果?
我的好友湘湘,也看了这件事,以及绘画艺术坏蛋店的、刘伟伟回应“决命办”的文章下面的评论。她跟我说,“最可贵的是,投票事件,是发生在刘伟伟和他亲人的关系上。就像扔硬币、看正反,让别人决定去留。但我们往往只看到去留,而没有了解事件的中心和语境,他们想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事情可以往什么方向推动。大家都只认定结果,不对的,这是一个过程,它产生了新的信息、新的对话、新的思考方向。”
在刘伟伟的设计中,投票终将有一个结果。但他和刘超作为一个亲历者、就像他后续所设计的一样,这是第一季,还会有第二季…第五六七八季,终结进程的权力在他手上。而围绕着这个项目产生的讨论和风波,人们的观看、参与,最后共同组成了这个作品。
在中国,participatory art 被翻译成社会介入式艺术,这是很可笑的翻译,难道艺术家并不存在于社会中吗?分明只是参与型艺术,粗略地来说,是艺术家与参与者共同完成作品,就像这个项目一样,无论选择投什么票,投票与否,它就是存在。至少这项目折射出来的问题,于我,就像藏于深水的炸弹一样。
*《过去与未来之间》汉娜·阿伦特[著] 王寅丽 张立立[译],译林出版社,p.144
*《论革命》汉娜·阿伦特[著] 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p.20
---------------------------------------------------------------------------------------------------
《参与式艺术:澳大利亚第二篇》
这篇文章成文时,刘伟伟对刷票最直接的回应是对刷票的“不服从”,还未变成“欢迎介入和改造”(《刷票、工人与事件艺术》)。刘伟伟的这篇回应显然比之前的清晰、有条理得多,也将本文所依赖的原情境拓宽了,好些问题都不是问题了。文章内容基于周琰和我的聊天以及与其他人的一些讨论成文,周琰的视角远比我成熟、细致,提到了许多关键点,我看了好几次我们的聊天记录,她给了不知问题边界的我许多启发。可惜周琰拒绝了共同作者的署名,她对这篇文章起了很大的作用,我特别感谢她。
正文
这一篇继续写朋友圈的二三事,关于刘伟伟的《澳大利亚》项目。这个项目开始一小时后“决定刘超命运办公室”就成立了,这几天,我重看这风波,小做梳理。首先,“决命办”的成立是在刘超决定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公众干预的基础上的;而刷票的行为,则基于微信投票本身的漏洞。其中,在决命字02号文件中的第三条,决命办装上了“人民”的外衣。
这在我看来是在反讽“人民”这一集体概念,其行为的冲动、难以预测,以及进一步戳破一个问题:在没有完善机制的情况下,指望社会参与者自觉遵守规则,真的具备公信力吗?是真正的民主吗?
看回刘伟伟对决命字01号文件的第一篇回应里,刘在第5条中表示“作品的诉求里没有提到‘人民来选择’。首先我不知道人民是谁,我也不相信人民这个词语。我说的是‘公众投票’。”
这里可以看到,“决命办”与刘伟伟对群体行为的不同认识。确实,在一些集体行为理论中,社会被认为是无判断力的,非自觉的[1]。在我看来,刘对“人民”一词的不相信,与“决命办”以此为名义,都可看作是对“人民”一词的反对。如果说“决命办”以此为名,表演做群氓破坏规则是对现实的模仿,刘则试图将这一词语打散,回到拥有个体权利自觉的“公众”一词上。
“决命办”的行为,还体现了对刘伟伟的质疑:为了做作品,刘伟伟将自己弟弟刘超的命运祭出来给公众投票决定。而这一点,在“一个人的社会”[2]首次现场讨论,就有人对刘伟伟提出这一质疑,刘超的主体性在哪里?刘伟伟在当时表示,他只负责写自己视角的文字,因此刘超的主动性在他的作品叙述里不明显。
这点周琰也与我说过:
“刘超这样的工人,在社会上是隐形人,而他的语言表达,肯定不如刘伟伟或者我们这些人,甚至他的语言表达会很被动。”
而书写是有限生命的人留下痕迹的一种手段,书写出来的文字所发出的声音,在历史时间中,远比稍纵即逝的口头言说,在“留存”、“诠释、建构当下/未来历史”等各项人类事务(包括政治)上有更大的权力。
在“一个人的社会“中,设立了几条规则:艺术家必须与另一个人“结对子”,且艺术家要在另一个人身上完成田野调查,以此为微观角度,揭示个人如何承载宏观权力拉锯的社会现场。
为此,我问了策展人满宇,这规则是否意味着艺术家将合作者视为研究对象?而非作为一个人。
满宇回答说:
“合作者作为一个主体,并不是客体,把人当客体,是一种对人的暴力。在这个项目中,是希望合作者以及艺术家,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呈现各自的主体性,使合作者和艺术家都能看得见自己、也被别人看见。”
这让我想起,阿伦特说过的,人无法回答“我是什么”(人是什么),但可以回答“我是谁”,而回答“我是谁”则是因为人是复数的,不是单独的,同时每个人的独特性,也由此彰显。在上次黄奕为新造空间的驻地做的关于人类学学科反思的分享里,人类学将“研究对象”重新定位为“合作者”,也同时在重新审视“主体性”在每个人身上的不同呈现。
可以说,在参与式艺术里许多问题都要注意:艺术家的权力边界在哪?参与者的权利又是什么呢?参与者的主体性在哪里?他是否被看见?
回到开头,以及这个风波本身,我将决命办风波的质疑总结为三点:
- 艺术家是否利用了弟弟刘超做艺术项目。而项目内容是让人们投票决定刘超的命运,刘超是否有被双重客体化?
- 投票规则依赖的程序漏洞十分明显,仅靠捆绑刘超命运使投票变得神圣,并不能阻止有人不遵守规则。
- 刘伟伟的回应并没有对这一易破坏的机制有任何弥补,仅仅表示“不服从暗箱操作的结果”,而投票算不算数,又是谁说了算?
以及,根据刘伟伟在第一篇回应里认为,水军行为分为商业操作和政治行为,其中“我对一种政治意识操作产生的刷票行为或者水军行为挺感兴趣,因为这个意识形态的产生,跟今天的权力结构关系密不可分。”
那么,决命办的刷票,是否是“政治意识操作产生的”,或者背负着“某些意识形态”呢?
刘伟伟《澳大利亚》项目的在微信公众号的投票界面
前面几条,是试着将这一风波中,尤其是由决命办的行为所显露出来的视角说清楚。然而,这几点都假装决命办与刘伟伟都在同一个圈层,没有指出,艺术圈与社会、公众的联系实际上并不紧密,就像互联网舆论场与现实政治的联系,并不是看上去的那么紧密。
或许可以调侃地说这个项目正是因为首发在绘画艺术坏蛋店,又以艺术之名,才引来坏蛋店的坏蛋们的回应。而这种玩笑的回应方式是当代艺术系统中常用的手法。这里,就看得出决命办与刘伟伟的分裂所在:
决命办处在艺术圈,而刘伟伟的这件作品,卡在艺术圈和“公众圈”之间。
周琰会在与我说“艺术圈与公众圈的联系薄弱”时,区分了艺术行业从业者与公众的身份。我和赵邦(艺术家)聊天的时候,他也说:“艺术对外部政治空间的隐喻批判仅仅是自慰,现在艺术系统不太存在批判性了,唯一的批判性就是对艺术和艺术家本身的批判。”作为艺术家,他也认为艺术系统与“外部”政治空间并没有太多交叠。
可以说,艺术与公众随着艺术问题与社会问题的区分而分裂区隔开了。有句话说:“政治的归政治,艺术的归艺术”,原意是指政治(权力)不应干涉艺术的表达,可目前来看,却变成了表述艺术创作应回避政治的一句话(这里的政治是狭义的,指日常政治观点立场、政治事务、权力斗争,而非一个更广阔意义上的政治[3])。
同时危险的是,在决命办与刘伟伟的互相回应(实际上就是朋友圈的隔空对话)中,《澳大利亚》这个项目极易被拖回艺术系统内部,变成艺术范围内的批判,那么这件作品预设的参与对象“公众”们也就仅变成阅读量的数字,作品也成了“取消对象的关于对象的艺术”(周琰),这正是现在许多作品的问题。
于此,再整理出三个问题:
1)艺术为什么不能是镶嵌于整个社会空间(包含政治空间)中的,而是分隔的?
2)艺术的批判仅在艺术内部有效吗?艺术仅仅是批判,仅仅是提出问题、呈现问题吗?
3)在朋友圈的隔空喊话(包括在坏蛋店发布)真的有助于将这个作品放置在公众之中吗?互喊的朋友圈怎样才能被突破,到更大网络空间中去?
关于问题1、2,似乎可以从两个大方面来看,一是根据中国原本的传统,艺术原就是给文人士大夫阶层赏玩的,即便描绘个山野村夫,目光也是自上而下的想象。在今天自上而下依然是受过艺术教育的从业者难以改变的视角。另一个是源于西方的当代艺术系统,从进入中国到如今的流变,与中国现状接轨还需要磨合,分隔与难以批判不同语境的事物是自然的。
但这样看问题,尽管有了历史渊源这条线,还是太粗糙,并且实际上是在回避艺术已被种种话术包裹、层层体制抬离了地面的现实。关于体制,我并不了解,这里只对话术大致展开。
话术,不仅是指艺术系统内那些听不懂的名词将艺术作品包装起来,使文本与艺术作品本身割裂的话语,与此同构的,艺术作品也会通过一些艺术手法、语言表达,但是与艺术家经验到的却是割裂的。可以说,从作一个艺术生开始,他的艺术语言,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被有权力语言系统定型,从考学系统到当代艺术系统。
有一天早上,我在中大听了一场关于古希腊古罗马早期基督教时期的“肉体”(flesh)观念建构的讲座。期间忍不住想,一个哲学系的学生,学着这些精妙的知识,遭遇着的国内的现实,会不会哑口无言?我会有这种疑虑,也是意识到,我在遇到现实的具体的剧烈或被麻木到几乎无视的问题的时候,是反应不过来的,是失语的,是无措的,曾经建构出我的世界的那套话语,形成了一层幻觉,与现实是错位的,它们是两个平行世界。
这样来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赵邦会认为艺术仅能批判艺术内部的问题,而难以触及更广阔的现实世界。
问题3,最近朋友圈刷屏的李翔伟断了杨永信家的电(此文已被404)一事,是一个艺术作品成功突破朋友圈,借由自媒体进入了更广阔的网络空间中的案例。当然,我们知道杨永信的事情,在微博上刷了上千万的阅读量,也仍正常营业。就如弦子在《关于女权主义标签,一个讨论》中提到的,网络舆论场与现实政治(权利)[4]的距离。在文中,弦子提到,关于米兔浪潮推动受害者站出来,但互联网上的发声,并没有给受害人实际的帮助,包括法律、经济、媒体等方面的支持,导致受害人再次受到了二次伤害。
“女权不是请客吃饭,真正要推动女性权益,是需要很多人有策略的去做一些事,要如何立法、要如何对企业高校用人单位施加压力、性骚扰受害者如何帮助、家庭暴力如何解决、性别歧视如何解决,这些都需要行动,需要志愿者、需要线下参与。
不是说发出声音没有意义,而是当一个人太过迷恋发出来的声音,就会忘记,还有很多别的事需要做。”
与艺术本身的表达属性带来的、对发声、影响力的迷恋不同(这里的迷恋、影响力是中性词),在中国,互联网将言说从行动中割裂了出来,但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区别,只以为舆论带来的关注和说理是能够解决现实政治[5]问题的。而实际上,只有具备权威的言说,比如法律条文,才能真正成为社会公共空间内人们处理事务的准则。
在这里,我认为可以借用一个理论模型,解释同情者与行动者的割裂。阿伦特在《jí/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描述了一个由无限可复制的双层级结构构成的洋葱状同心圆模型,以描述jí/权主义/运动中的人如何避免“革命”信念与真实世界的不兼容发生的震荡。
阿伦特分析道,希特勒将争取到的群众分为同情者和正式成员,而同情者的组织包裹着正式成员,将他们与外部的正常世界隔开(但同时又是通往外部世界的桥梁),同情者组织不仅圈起正式成员,而且向他们构筑外部世界的模样。[6]而这个结构是可以无限复制的,可以在中间插入同构的新的层级,如“突击队”与“敢死队”。
在今天,我们也可以套用这个模型分析互联网中,我们触角所及的信息是如何将我们包裹起来,以隔开现实世界,算进朋友圈、微博,又有多少层级将我们层层包裹。以及同理,可用在艺术体制及话术上,每个具体的地方,如何通过白盒子或者学院派将艺术家个人包裹。无论是哪种情况的包裹,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在今天确实很容易在这些包裹之中,既察觉不了它们,又避免了来自真实世界的震荡。
趣头条通过阅读时长奖励红包的机制,占有了三四线城市中老年人的流量市场,这一机制与在趣头条每天阅读的数万条短新闻,哪个才是真实世界?
回过头来看,刘伟伟的《澳大利亚》,与决命办的刷票,何者在触及现实政治,而何者在比喻现实政治的现象?
当我们从这里回头看的时候,会发现艺术圈这个“圈”可以不存在,事情就是事情本身,而对现象的比喻仅在艺术手法上显效。
这时,我们可以进一步谈上文提到的问题2的内容,艺术做的,仅仅是提出问题、呈现问题吗?
1968年,在阿根廷“前卫艺术全国大会”中,艺术家费拉里说:“艺术既不是美,也不是新颖;艺术将会是效能和骚动,在艺术家的环境里,一个登峰造极的艺术作品,它的冲击会是类似于为国家自由而斗争的恐怖主义行动。”而这个“恐怖主义”的方法不会压抑艺术(如情境主义的模式),而会维持政治和美学的纲领密不可分的关系……[7]
而最近一年,最具“效能和骚动”的参与式艺术项目,非坚果兄弟的《带盐计划》莫属。《带盐计划》基于郑宏彬策划的“九个发布会”项目提出,在今年六月,坚果兄弟将两万瓶农夫山泉换作陕西小壕兔村民的日常饮用水,带到北京、西安展出,并请观众试喝。此举引来了许多媒体对小壕兔本地环境污染的关注、调查,以及后续的舆论、事件发酵。
在这个项目里,如果只看坚果兄弟的行为,那么艺术表达似乎是不完整的、散落进事件之中的,但他提供了新的路径,将小壕兔乡民日常感知的一部分带到北京、西安,可以说是,用“美学的方法对社会进行了解、批判以及改变”(李一凡)。而如果从整个事件及其参与者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次合作的艺术表达,从开头换水的故事到后来对水污染的调查、村民的发声等等,则组成了一个更为完整的事件艺术。
这两方面,也是艺术家与参与者,在事件艺术中的位置。
当然,就如我们前文提杨永信一样,在中国,光是网络舆论场层面的“效能和骚动”是不够的,那只是一些震荡、影响,真正的效能依然要触及线下。
“屏幕和信息在不断地塑造杨永信的形象,但他背后的体制和医学系统是什么呢?背后的东西,才更应该去搜索。”(朱湘,艺术家)
这篇小长文就要结束,我在这里友情打个广告。“九个发布会”中,武老白基于半年的调研,项目《恋人》正在众筹公里数,他将会把3句话刷上大卡车,走一遭几个城市对同性恋进行电击扭转治疗的医院。
这是武老白的二维码,以每公里20元为单位参与募捐,请于付款键下方备注名字与职业。
“恐惧只有一两种,而讲故事的方法有无数种。”——郑宏彬
注释:
[1]这里的自觉指的是个人意识到自己的主体性,以及相应的权利,但一些理论认为集体行为是无判断力的,而只有在运动中才会自觉。——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P.18
[2]“一个人的社会”是由满宇策划的艺术项目,共10位艺术家参与,于2016年年底启动,2018年10月13日在广州新造当代艺术中心进行第一次现场讨论,艺术家呈现了他们田野调查得到的素材。刘伟伟的《澳大利亚》项目也参加了此项目。
[3]这里“更广阔意义上的政治”既指在发生在公共空间中的人类事务,也指朗西埃提出的“感官世界的重新分配”。
[4]现实政治(权利):加上(权利),是为了对应米兔受害人所处的具体政治情境是权利的诉求。
[5]现实政治:朗西埃在《政治的边缘》一书中定义政治有两大方面,一是政府运作;二是平等的运作。中国作为大政府类型的国家,前者的运作更为强大。
[6]《jí/权主义/的起源》第二版,汉娜·阿伦特著 林骧华 译,三联书店,P.469
[7]《人造地狱——参与式艺术与观看者政治学》克莱尔·毕莎普 著 林宏涛 译,典藏,P.214
参考书目:
《政治的边缘》雅克·朗西埃著 姜宇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jí/权主义/的起源》第二版,汉娜·阿伦特 著 林骧华 译,三联书店 2016
《运动中的力量——社会//yùn动与斗争//政治》西德尼·塔罗 著 吴庆宏 译,译林出版社,2005
《人造地狱——参与式艺术与观看者政治学》克莱尔·毕莎普 著 林宏涛 译,典藏艺术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2015
《人的境况》汉娜·阿伦特 著 王寅丽 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