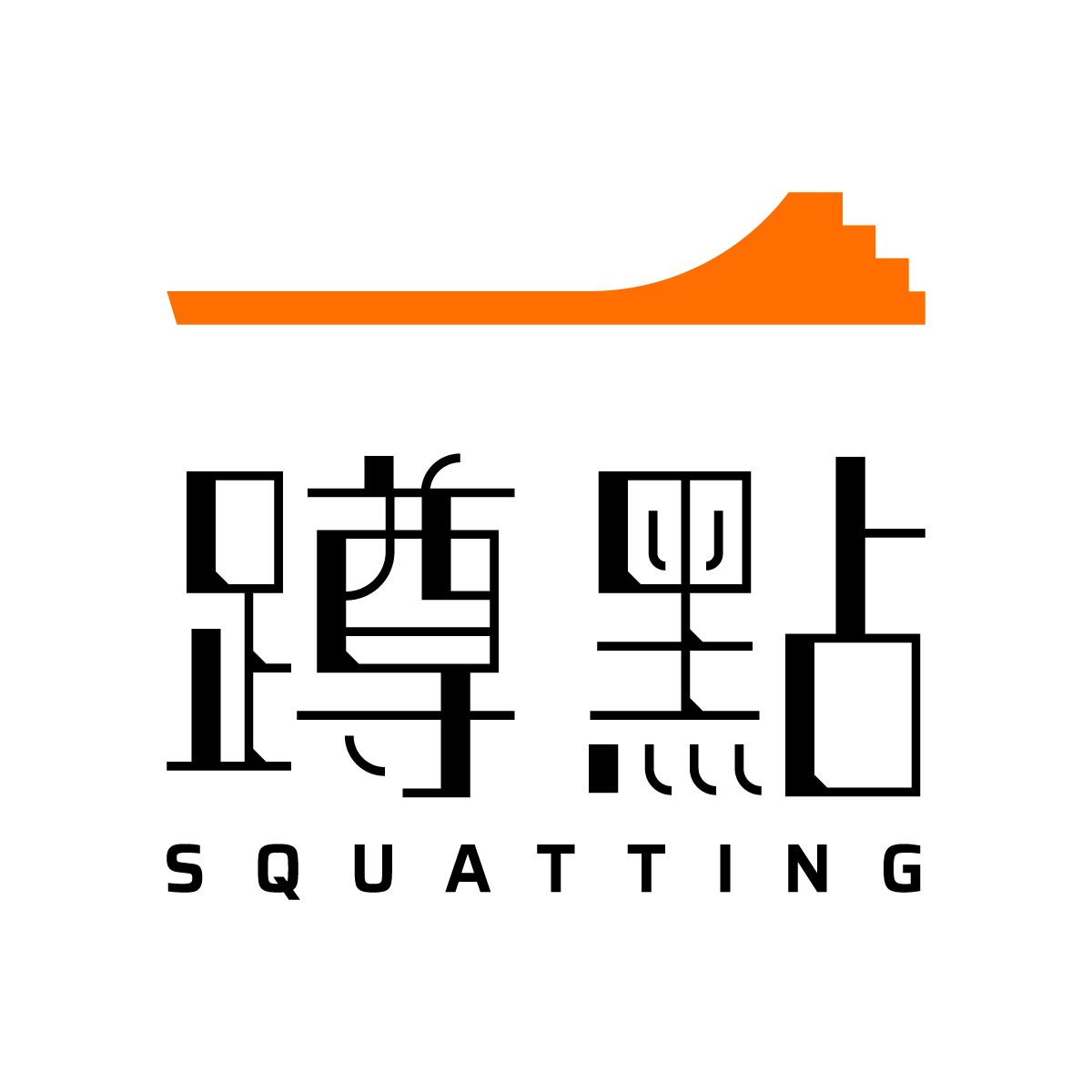【反送中一週年專題】基層工人去咗邊:與工會幹事談基層動員

編按: 蹲點對反送中運動的整體判斷在轉載夕岸的文章<時代遊戲>及其增補、馬蘭的<反思:香港反抗運動週年誌>和與左翼人士討論左翼內部分歧的文章都有體現。但在宏觀分析之外,我們也警惕自身作為左翼論述者容易陷於意識形態批判,而忘記觀察自身與前線的距離。由此,【反送中一週年】專題的最後一篇文章回到運動中基層的動員組織問題。 作為這座城市的大多數,基層在運動中並未受到應有的關注,他們在公眾視線中的隱身令人擔憂。但整場運動與他們的關係頗大:一方面,我們看到基層也在參與著運動——庭審的案件中不乏基層的身影;另一方面,基層承擔著運動的破壞性影響,例如清潔工人要清理被「裝修」後的地面碎玻璃、處理示威產生的道路垃圾,再如失業影響生計等等。 他們對整場運動作何感想?他們怎麼理解「民主運動」?組織者又如何將運動訴求和基層的實際的艱難生活拉上關係? 這一篇文章整理自職工盟清潔工工會幹事Denny To與蹲點關於反送中運動的討論。 Denny To,曾經在社民連做工作,現於職工盟擔任組織幹事。在這篇討論中他分享了運動中他動員清潔工友的組織經驗,以及一路以來對不同組織方式的思考。Denny To在運動初期給會員們(主要是年紀較大的清潔工友)發過無數運動的新聞,也害怕被他們稱為「黃絲」。經過謹慎的問卷調研以後,他了解到基層可能不如大家想像的那麼「藍」,但對工友政治化的組織工作也的確相當困難,而且運動中的大多數手足不一定會記得基層參與的重要性。
口述(討論分享):Denny To
整理:林小鄰 網站:squatting2047.com Facebook:蹲點 Squatting

基層工人:不認同示威者的某些行為,但也不覺得政府是對的
這個運動從出現到現在,基層工人是跟不上。運動在去年六月爆發的時候,我並不是第一時間想自己的工作,想的更多的是自己和香港社會的關係怎樣。我當時和很多年輕人去推動現場的參與,看是否有可能改變整件事情。當時有很多情緒上的波動。
到中期我想,街頭似乎已經不是我擅長的地方,雖然我是社運出身但很快已經被人拋離了,那我就去想運動中我是什麼角色呢?難免就會想到組織工作上面去。
(當時大家覺得)基層可能和運動沒什麼關係,到中後期的時候堵路有點嚴重的時候,清潔工是受到很大影響的,所以我擔心的就是雖然7月之後可能全香港都是黃,但清潔工人呢?
所以八月初的時候我就在工會裡面花了點時間做了一份問卷,給會員填寫。我們工會其實沒有很多人,大概200人左右。最後問了30個人,結果就是還好的,至少我們的工會成員都是偏黃的,都是會對警察不滿,對政府不滿,甚至有三成人在某程度上參與運動的,所以我就放心了:原來基層都不是完全和運動拉不上關係。
在運動早期的時候我瘋狂地將新聞發給會員的,但是他們沒怎麼回覆我,不回覆其實有很多原因,一來基層工人他不怎麼會打字,我發什麼他們都不回覆,但是我知道有部分人會看的。我那個時候風風火火沒有時間和他們聊天,我很擔心發完之後他們會和我翻臉:你們這些暴徒黃絲(笑)。我真是很害怕,所以才做了那個問卷調查,做完之後就有點放心啦。
我們工會做的主要是55歲以上的清潔工人,年輕一點都不會選擇做(清潔)。中後期陸續和工友聊天,他們大部分都不是很了解發生什麼事情的,但是有些模糊印象。哪怕他覺得示威者有些過分的做法,大部分都不覺得政府是正確的,當然我理解他們大部分人可能都是淺黃或者所謂和理非的光譜,有些真的會和子女一起去遊行。八月的時候我成功找到幾個會員一起遊行。
組織者的困惑:工會留人困難重重
其實另一個做問卷調查的背景是我思考上的一些轉變。
我做了(工會)兩三年之後,發現過往的組織方式推進得不是很好。我想其他的同事都有一些相似的處境,林小薇在「二百萬三罷聯合陣線」出來以後寫過一篇文章,她說工會雖然不停做case(地盤工會過去一年追了有兩千萬的欠薪),成績好像很亮眼,但是留不住那些工友。
地盤和清潔很相似,都是基層工種,清潔更誇張、更基層一些。我們都有很多case接,但很多時候工友來求助都是當我們是condom而已:來找你是他有一些問題想解決,他解決完就不會留下了。
有部分傳統恩義心強一點的,覺得你幫我我就留下。但那不完全是工會的關係,我自己想象中的工會關係是怎樣的呢?就不僅是想自己,或者自己和幹事的關係,而是想你和其他同事、工友的關係。坦白說,我們很少機會做到這一步,溝通時間很有限,政治意識的轉變要很多時間,做了一百個case可能轉化到的人都不知道有沒有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五都已經很高了。最後一些成為會員的人是本身的政治意識都可以的一些人,本身他已經有留意新聞,甚至他本身是已經在關心整個行業的人,這就不是靠我們轉化回來的。我們慢慢透過組織工作,慢慢滴水穿石,慢慢轉化那些人的成功案例是少之又少的。人的精力有限,一個組織幹事可以接觸到的工友有多少呢,你日做夜做的話,一個對三百個都很多了。
那時候我想的是盡我所有力氣,最多拉到三四百個工友,已經是很出色的了。現在是兩百個,但是相對於全港八萬的清潔工人都是一條毛而已,那麼不論抓住那三四百個工友做到多出色都好,對整個行業可以有些什麼轉變呢?推進到些什麼呢?我當時有些懷疑。
哪怕經歷過海麗罷工之後都算是有一些政策上的轉變,但很遺憾的是,海麗罷工之後其實工人不是很留得下,一方面可能是他轉了工,第二方面就是當爭取的東西爭取到了之後他罷工影響消退得很快。也可能是我們工作不夠沒辦法轉化他關心整個行業。
這個背景再加上六月之後的運動,我開始在想自己的策略:與其我只找到三四百個,為什麼我不優先去找一下進步一點、政治化多一些的工人呢。所以從去年年尾開始都嘗試去找政治化程度高一些的工友,加上問卷逐個去判斷,哪些會員的政治化程度高一點的,我會和他溝通多一點,對於政治化程度低的工友就真的抱歉了。
之後我嘗試做多一些宣傳。以前我會覺得開Facebook Page沒有用,因為清潔工人都不開Facebook的,他連WhatsApp都不會打字,又開Facebook做什麼呢?
去年開始做了一些轉變,而且好像都有一點成果。就是開了一個「清潔龍阿珍」的page啦,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當工會或者網絡上知名度高了的時候,是會有一些清潔工人來主動找你的。當然那些不是最基層的清潔工人,是年輕的多一些,但是我覺得不太差,是一個嘗試。最基層的那些是很難轉化的,中間、偏年輕的機會就大一些。
這個是我當時自己在試的一個東西:去接觸、去組織政治化多一些的工人。
(怎樣接觸了解工友的政治化程度呢?)
一個方法是膽粗粗地問工友,尤其是有很多和運動相關的新聞的時候。一般我開頭講話就是,你的子女有沒有參與遊行示威啊,他們就會說:我很擔心他們。我會接著問,那你會不會和他一起參與呀?有些正面的就拉他出來一起遊行,這樣開展。
另外,我都留意到整個運動裡面有很多清潔工被抓了,其中一個清潔工是被定「阻差辦公」(罪名),我透過一些方法和他聯絡並且拉他入會。這樣又是一個方向,但串連是很困難,我嘗試和他發展其他工人,看看其他工人有沒有可能加入,都不是很成功。
身分政治:大陸人是不是「同路人」?
身分政治的問題是我自己都緊張的一個問題。全香港的清潔工都只有三種人,一種就是本地出生的老人家,60多歲;一種就是大陸新移民,以女性為主的;第三種就是南亞裔,不講廣東話,可能是泰國人,可能是尼泊爾人。
新移民可能佔了大概六成。新移民是一個很廣的概念,可能他來到香港十幾年,但是口音都還是沒正的,還有鄉音,主要是50歲以上。所以當有一些聲音說到大陸人是不是手足的時候,我就有點緊張,整條筋豎起來。
相比雨傘運動,我覺得這場運動初期在身分政治、排外方面是溫和一些,初期比較百花齊放。到後期運動開始沈寂的時候,一些右翼的声音冒出来成為主導力量。我想其實不是右翼很成功,只不過香港是這樣的意識形態,再加上左翼人不爭氣,才會變成這樣的,這不是一個比預料中更加差的結果。
我擔心會不會「身分」變成了一個成為手足的門檻。就好像身分可以靠積分得到一樣,大陸人需要多一些分數才能成為「手足」?
我關心基層工人對民主運動的參與。當我們說這個社會要改變,要「革命」的時候應該要全民參與,但基層工人的參與和位置在哪裡呢?很多時候看新聞,基層不是沒有出現在運動現場,看法庭新聞,大家知道很多(手足)都是基層,但是很容易忘記他們。這個情況在可見的將來都不大可能改變得到。
第二(跟身分政治相關)令我生氣的就是光榮冰室那件事。光榮的取態和反應我都不是覺得特別誇張,但令我生氣的地方在於,有一些觀點我以為是一些極端的本土派才會去宣揚,但很遺憾那次論爭裡面很多中間派的知識分子都有說:「你大陸人就是殖民主義的殖民者,你多少都有點「原罪」,對某些嚴苛的批評或者是排拒,你都要理解或者是寬容。」
和Denny To的這篇討論在此作結,但其實整場討論會還有很多細節未有記錄。其他前線組織者都對只做case、未能轉化基層工友、未能將左翼分析滲透給工友的問題頗有共鳴和回應,但因討論較零散而未有記錄在此。
蹲點的【反送中一週年】系列以前線基層組織工作作結,是想回應左翼對於整場運動最關心的問題:運動除了抽象的「政治民主」面向,該怎麼加入更落地的「經濟民主」;運動如何避免右翼排外的傾向,連結廣大的基層?
有關於此的實踐,要繼續期待所有人(不論是論述者、還是前線組織者)的齊心努力。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