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美国读博的拉拉公益人,比从前更自由了吗?|野聲电台

1989年生的典典是一位拉拉公益人,曾担任《酷拉时报》的编辑,2016年起在美国亚特兰大就读性别研究专业的博士。在本期电台中,我们和她一起讨论了出柜、政治正确、种族歧视、粉红经济、微博女权、彩虹宝宝等话题,并分享歌曲《离人》,以及去年诞生的新全球女权主义宣言《99%的女权主义:一个宣言》。

彩虹伴我心
秋凉:米兰刚开始封城的时候,我在Vlog里说希望可以保持迁徙自由,现在看来这可能是最昂贵和最难以实现的自由。疫情迫使很多公司转向线上办公,也让人们的线上联结变得更加紧密,我最近就参加了几个性别话题的线上讨论会,认识了一些新朋友,也联系上了一些老朋友。今天我们的嘉宾就是我神交已久的一位老朋友典典,她活跃于中国性别公益事业,曾经在华人拉拉联盟(一个跨区域的华语女同机构)工作过,在范坡坡导演的同志纪录片《彩虹伴我心》(2012)以及国内首部拉拉轻喜剧《美宝飞雄》(2014)中有过出镜,在2012年到2016年主编过一个关注性别议题的刊物叫做《酷拉时报》(目前留存着豆瓣小站),之后前往美国读博。让我们欢迎典典!

典典:非常开心能来「野聲」电台,我是典典。因为疫情期间,我也培养了一个新爱好,就是边做家务边听播客,所以我也有听过「野聲」,所以这次很高兴来。我现在在美国的亚特兰大生活,在读性别研究这个专业的博士,已经(读到了)第五年,要把论文写出来的阶段。
秋凉:欢迎典典做客「野聲」!今年四月典典通过网络(ZOOM)完成了博士的开题报告,可以介绍一下你的论文主题吗?
典典:我在来读博士之前,在香港的华人拉拉联盟工作过几年,接触了各地拉拉和女权议题的活动家,把她们跨区域地联合起来做很多事,还有互相影响,我觉得这种共同成长的过程非常有意思,一方面在华语讲中文的地区,另一方面又跨越了国界和地域的限制,包括有在北美的来自不同地区讲中文的华人,也有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所以我的博士论文就是想从这种跨地域的运动的结盟的角度,来讲一讲我当时工作过的机构。
秋凉:之前我和米兰的小伙伴阿君做过一期关于纪录片《剩女》的播客,讲到自己对性别议题的关注始于2012年上海地铁的“我可以骚,你不能扰”,是一个反对性骚扰的行为艺术,当时引发了从微博到央视的全国大讨论。在范坡坡导演的《新前门大街》(2009)、《彩虹伴我心》(2012)、《来自阴道》(2013)等纪录片中,我们可以看到那几年国内各地关于性别议题的社会运动是蛮活跃的,比如我国在2015年通过、2016年开始实施的《反家庭暴力法》,就和中国女权主义者们的努力密不可分。

那2016年我来意大利留学之后,认识到这边有个“一个也不能少”(Non Una Di Meno,简称NUDM)的运动,也是有跨地域、结盟的、交叉性的特点,比如疫情期间,居家隔离使得世界各地家暴案件激增,意大利的妇女庇护所人满为患,有个27岁的意大利女孩洛伦娜·夸兰塔(Lorena Quaranta)马上取得医生执照,但很不幸在3月30日因为其男友安东尼奥(Antonio)的家暴去世了,NUDM为此积极组织线上抗议,催动意大利新冠疫情专项基金在4月拨款300万欧元用于打击家庭暴力。

那说到疫情,典典所在的美国是目前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据统计,到9月1号,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突破600万例,我们看新闻的话会觉得美国这段时间特别乱,但和典典交流好像没那么夸张。你和国内家人交流的时候会不会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呢?
典典:对,这些主要是信息来源的事情,倒不光是疫情还有其他方面的消息,因为我妈妈现在人在国内,不太懂得翻墙的技术,所以她的信息源基本上受限于国内的媒体和社交媒体,有的时候会发现大家对一件事情的理解很不一样。但我妈妈的心态还比较开放,比如她会顺手转她看到的文章,我就告诉她不是这样的,她也不会极力反对我,也会有“抗议中的暴力是不好的”等一些朴素的观点,她基本上对探讨还算是比较开放,也不会觉得她看到的就是对的,所以还好,还可以沟通。
秋凉:对于一个同志来说,“出柜”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每个人都渴望家人的接受和祝福,所以很多人在看了范坡坡的纪录片《彩虹伴我心》后,特别羡慕典典的妈妈能够接受女儿的出柜。
典典:对,我确实还是很幸运的,我自己没有经历过拉拉身份认同的挣扎,我妈妈就是一个做女性文学研究的学者,她本人的想法可能比较随大流,但她的态度还是比较开放,比如她希望我从小更有女孩子的样子,但也没有强迫我改变,我把头发剪得很短地回来,她也还勉强接受,听说我喜欢女生,她说“啊你现在可能还在探索时期吧”。其实我后来有听说过她还是有一些挣扎的,我来美国后在亚特兰大刚好有个我妈妈的老朋友,就是沈睿老师,她跟我说其实在我高中阶段,我妈给她打过越洋的长途电话,其实有很多的担忧,但当时她对我顶多就是说“你也应该多跟男生交往,不要画地为牢,觉得自己一定怎么样”,其实她的想法还挺酷儿的。我后来听说她当时曾经那么担心,还挺心疼的,一下想到以前她跟我说一些“多跟男生接触”这样的话,我都挺反感的,觉得她不理解我,现在想来其实她已经很努力地去理解我和支持我了。

秋凉:我们说当这个社会的“同志”还在被污名时,子女的“出柜”就会让父母“入柜”,特别是老一辈的同志,可能就真的选择沉默或者忍耐一辈子,而不是告诉自己的家人。那作为在互联网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我们有机会了解更多的知识,找到自己的同类,寻求社群的帮助,但即使如此,能够坦然接受子女出柜的父母还是凤毛麟角。
典典:对,我觉得真正很爱孩子的父母,其实很多时候不怎么是从自己的面子,还是从孩子的利益方面去考量的。像我妈妈她有的时候跟我说她的担忧,也主要是怕社会压力,让生活变得很辛苦,那样就不是特别好,她担心的主要是这些。
Adon:我也(和秋凉)一起观赏了《彩虹伴我心》的纪录片,发觉大陆的男同志好像比较隐性,台湾的男同志我感觉还蛮显性的,就比较“花枝招展”,一看就看得出同志气质。但我也有个学长,他在我们面前是非常显性的同志,但事实上他的家人是完全不知道的,还是有很多这种例子,虽然在台湾同志婚姻已经合法化了,但世代的差距不是这么容易弥补的,我觉得真的要耐心去沟通,我身边的例子是即便到我这个年纪也不太敢跟父母讲的,可能我的下几代会越来越好。
秋凉:不过说到亲子关系,不光是同志子女,即使是异性恋的子女,也可能和家人会有冲突,比如我有异性恋的朋友,因为还没有遇到喜欢的人,就保持单身,但她的父母就没有办法接受,觉得女儿会变成“剩女”,父亲甚至都不肯和女儿说话,亲密和谐的亲子关系可能在哪儿都挺少见的。
典典:其实亲子关系和同性恋这两个事儿没有必然联系吧,我大学的时候有上海的女生和东北的男生谈恋爱,上海那位女生家里对东北人有某种偏见,非得跑来把他们拆散了,我当时觉得“哎呀异性恋也很辛苦”。
在美国做拉拉
秋凉:典典你从华语区到英语地区生活,会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呢?在美国做拉拉更自由一些吗?
典典:这可能是因为美国也很大,中国也很大,所以各个地区的状况不能一概而论吧。刚才说我特别幸运,至少我妈妈本人受过高等教育,是一个学者,也是努力用比较开放的态度养育我,所以我其实一直没有遭受很大的压力,香港的时候也是,我周围的人比较开放。到美国来我来的是美国的南部,保守州佐治亚州,虽然在亚特兰大这个首府还比较开放,市中心的斑马线是漆成彩虹的,教堂有着虹旗也是欢迎基督徒的。但是也有很多人,比如我的邻居,看到我短发就猜测我是拉拉(这也是一种刻板印象),就有一天神神秘秘地跟我说,“我们这边也还挺开放的”,给我塞了个杂志,我一看那里面有篇LGBT的报道,我想这邻居应该是要对我表现友好,但这种刻意表现的友好反而不太自然,我去纽约的时候就觉得他们那边的开放更自然一点。

美国也有地域差异,我的本科生学生也有跟我说,他们是在一些保守州上的高中,说高中的性教育还是守贞教育,就是女性不能有婚前性行为之类的,所以美国的地域差异很大,包括不同的文化背景,如果你是保守的宗教家庭,上教会背景的学校的话,受到的性别文化方面的教育可能就很不一样。性少数身份这一点在世界各地都有大的制度环境,比如美国的同性恋可以结婚,我和我的伴侣说如果结婚对我们某个人的签证有帮助的,可能也会去结婚。我觉得身边的小环境和制度的大环境(对个人)都有影响,美国的制度上也是经过了若干年的斗争,现在对性少数群体有一定的制度保障,但是在文化上还是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压力。
对于我来说,来美国性少数身份方面的解放感,可能有些朋友是有比较强烈的感受,但我在国内就做拉拉运动,在这方面就比较开放,所以其实我来美国以后这方面解放的感受不是很强烈,反而是语言上的挑战是个挺大的难关。第一年的时候特别艰难,现在日常基本没什么问题,但你应该也发现我其实是个挺爱说话的人,平时话也很多,也很喜欢跟别人表达自己,但到这边因为语言的障碍,想说的就没法及时表达出来,其实是挺苦恼的,直到现在都没解决这个问题,还是会有些语言的压力,一想到用英文来听说读写,心里就会比较紧张,跟用中文说话完全不同。
秋凉:我当时来意大利的时候想得比较简单,觉得说英语的人太多了,我自己本身对小语种挺感兴趣的,已经学了韩语,就想再学门意大利语。但后来发现自己低估了意大利语的难度,碰到着急上火的时候三言两语讲不清楚,就特别地受打击,而且这边意大利人一般也不爱讲英语,当我只能讲一门不熟悉的语言的时候,真的有种手无寸铁的感觉,好像丢了自己最唾手可得、最擅长的武器。后来我也有反思下,觉得我讲母语的时候伶牙俐齿其实也是一种特权,作为一个外国人的有口难言可以是暂时性的,但作为弱势群体的失语是一种常态。
典典:你刚说的这个武器比喻特别好,确实用自己的弱势语言,表达的声音不那么如愿的流畅的时候,真的有种失去了所有武器和防御的无助的感觉,我觉得你想得也非常好,可以推到其他在弱势处境的人,比如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或者中国一些方言地区的人,沟通时候那种词不达意的窘迫,其实也是一种弱势的表现。
秋凉:还有我在意大利有时会感觉白人不是很有耐心听你说话的,更多时候是他们只是需要一个亚裔面孔来表现活动的“多元”,而对于我本人的想法不见得有兴趣。此外我个人觉得像这边的一些跨文化交流活动,还是以贴春联、做饺子、穿汉服或者旗袍等为主要内容,其实也是加强了他们对华人的这种刻板印象。今年新冠疫情刚爆发的时候,我们这边的华人更早戴上了口罩,也因此受到意大利人的侧目甚至敌意。你在美国有遇到种族歧视的情况吗?
典典:没错,其实我最近还碰到一个种族主义的情况,就是我前两周去UPS退一个Amazon的快递,有个东西买了不合适要拿去退,我用的return这个词,结果对方居然说why don't you return to China, “要不要回你的国家去”,我当时都懵了,第一反应是怀疑自己的英文,我想是不是自己听错了,为什么突然说这么一句话,但因为都戴着口罩也看不清对方的表情,当时我觉得很尴尬,不知道做什么反应就走了,但在路上我越想越不爽,就决定在email写了个投诉。我常常开玩笑说有的时候去到一个新的地方,你会发现自己一个新的身份。
比如去香港生活的那五年,也是陆港矛盾加剧的那几年,我才开始比较理解地域的身份,可能这是一个我以前没太想过的问题,虽然我从小也在好几个不同的城市生活过,像刚去北京的时候感受到的排外的情绪,过了两年随着我口音不那么明显好像就好了。但是到香港我又一次感受到了语言文化地域所造成的彼此的隔阂,到美国来又一次,而且感觉更加地不好。在香港的时候作为大陆人,有些大陆人可能觉得自己受歧视,但我当时反而比较能够同理香港人,因为我知道在大的经济上,香港会感觉到更大的危机感和压迫感,就算在文化上拿一些优越感来对抗,其实在大的结构上其实是香港人处于更加危险的状态。

但是到美国来,我确实能感觉到作为亚裔的弱势,包括其他的少数族裔。我在的亚特兰大刚好是马丁·路德·金的故乡,也是黑人民权运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地点,来这里后我才了解到黑人的历史和美国族裔冲突的历史,自己也切身感受到。我上的学校在教授和管理阶层都是以白人为主的私立学校,我就感受到虽然“政治正确”是有所谓的多元和尊重少数族裔,但就像你刚刚说的,其实白人可能没有耐心听你说话,也不关心你说的事情,你会感觉到自己被漠视和有口难言的困难。深入的沟通很需要时间精力,很多时候大家对所谓的“政治正确”的批评也是因为它容易流于表面形式,当然如果连表面形式都没有就更糟糕,所以就是这些切身的体会和到一个新的地区学到的东西,确实会拓展我们对差异和歧视的认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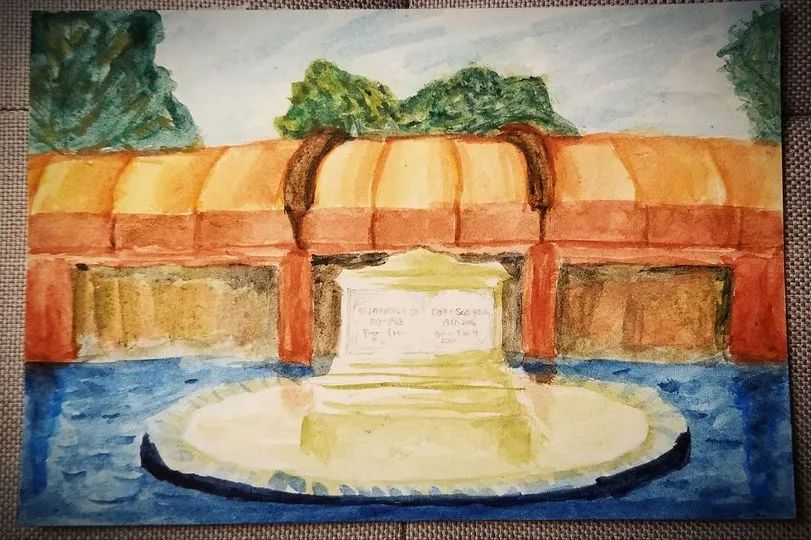
秋凉:我前两年去布拉格旅游,住在一家青年旅舍里,老板娘是个韩国女生,她的先生是当地人,一开始我没有看到脸,听到他们用韩语交谈,男生讲得特别流利,我以为他是个韩国人,后来回头一看发现是个金发碧眼的男生,就特别惊讶,因为我认识到的跨国伴侣,要么两个人都讲第三国语言(比如中意伴侣之间讲英语),或者女方讲男方的语言,很少有男方讲女方的语言而且讲得那么好,以至于特别感动,后来我也反思了自己的这种感动:为什么一个白人男性讲亚洲语言,我就这么受宠若惊呢?
典典:对,就像你说的,因为实际上主流上(语言)是有阶级的,就像欧洲语言比亚洲语言(高级),延续了几百年的殖民结构。美国这边也是,我去年参加北美女性研究的全国大会,有很多性别领域的研究者参会,其中好几位是华裔,和美国人结婚了,她们聚在一起抱怨说下一次要讨论跨国婚姻里的不平等,因为她们都发现自己会变成那个不停用英文沟通的人,跟男方和男方父母沟通,带男方回中国的时候也要负责帮男方跟自己的父母沟通,好像女性承担了所有的翻译和学习外语的责任,男性就算说“为了你,我也学一下中文吧”,但其实没有人能学到真的能交流的程度。
秋凉:我常常碰到的白男所谓“会讲中文”,就是“你好”“再见”“你好漂亮”程度,可能真的是白男特权让他们的跨文化社交比较容易,对我来说可能想要尽兴和精准地表达还是需要母语。
典典:我在美国的第一年因为语言等种种困难就觉得特别艰难,快要在英文的环境里窒息,所以我第二年和几个当时认识的中国来的博士生朋友组织了一个中文的文化沙龙,叫“培思社”,规模挺小的,因为这边中国留学生不是太多,特别对社科文化感兴趣的不是特别多,这边主要是佐治亚理工,可能理工科的学生多一点,他们都很忙。我们现在也有十几二十个人,隔周聚一下,用中文聊一聊大家感兴趣的话题,或者轮流主讲一下自己比较了解的领域之类的。
秋凉:那你现在主要的朋友是中国人为主吗?有没有讲英文的朋友呢?
典典:对,其实我自己还常常反思自己不够open,比较熟悉的人还是在一起讲中文的人,虽然我在学校里面也有参加一个研究会的工会(Union),也在那里认识了一些朋友,但用英文很难彻底地表达自己,进行深入沟通的时候也比较困难,心理上也有点障碍,怕对方听不懂,能够深入交谈的还是讲中文的人。我有时候也挺羡慕有些朋友很快和当地人打成一片,我这两年有在尝试走出自己的舒适区一些,因为课终于上完了,只要专心写论文,所以今年我开题答辩结束后,有报名当地的一个服务少数族裔的政治组织,帮少数族裔的移民投票什么的,是我们系的一个同学的伴侣介绍的,我打算去那里做做志愿者什么的,希望稍微能拓展一些。但是也有一些比较好的朋友,但他们反而不是白人,也是在美国比较边缘的,比如我有个很好的黑人朋友,精神上有些疾患,但人非常好,他的幻觉和不幸的成长经历有关,就像电影Moonlight一样,我和他的交往虽然只有短短几次的见面和聊天,但感觉彼此的交流得很深入,能产生很深的联结。这个也不完全是族裔的原因,有的同学可能你常常上课能见到聊几句,但没有办法产生真正的联结,但跟他就有这种感觉。
Adon:我自己在国外交流的经验来说也是有类似的感觉,学生比工作的时候更明显,同样是外地来的人更有共情感。我在米兰理工读硕士的时候在皮尔琴察(Piacenza)这个小城市,他们当地人有个名词叫Piacentino,就是皮尔琴察人,他们也会向我们介绍自己的城市,开车带我们出去玩,但是你可以感觉到他们在地的圈子是很强的。又比如在米兰的圈子,意大利的南部人上来学习,反而更容易和我们这些外国人接触,因为他们也是外地人刚过来新的环境,但他们好歹还是意大利人,我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意大利的时候,反而是通过意大利的南部人。像很多意大利人虽然来米兰学习,但他们并没有准备好文化交流,因为他们还在自己的国家,尤其是像皮尔琴察的小圈子。我自己后来反思了一下,如果有些外国人在我家乡当地,我也不见得有心理准备去文化交流,一开始比较容易交到和你一样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比如我和很多中南美洲的人成了朋友,他们也有个圈子,也会邀我去参加他们的聚会,所以我觉得在国外,往往跟你一样来到外地的陌生环境的人,反而会产生一种共情感。
后来我工作的时候,有个事务所比较喜欢用外国人,是因为外国人便宜好用耐操,更愿意加班,意大利人和外国人一半一半,有时外国人甚至多过意大利人,我们交流都是用英语。我当时带美国和波兰来的实习生,我们的交流就蛮紧密的,跟其他的意大利人反而会有点脱节的感觉。我还有遇到过有出国经验的意大利人,他回意大利的时候可能更愿意去文化交流,因为他自己也有作为外国人离乡背井的经验,那我之后回台湾的话可能也会更愿意去和在台湾的外国人交流,也很乐意帮他们。
秋凉:生活在一个陌生城市或者陌生国度,多少会有种被疏离的感觉,能够认识一个交心的朋友或者形成自己的小圈子还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带来的歌是《离人》,最早是由歌神张学友演唱,后来台湾歌手林志炫翻唱了这首歌,两位的演绎各有千秋,歌名很像我们这些漂泊在外的人淡淡的疏离感,会有一些悲伤孤独,但又有着千丝万缕的思念和羁绊。
Adon:我自己听到的《离人》是偶然在一个歌唱节目上面听到林志炫的版本,这首歌的旋律我还蛮喜欢的,唱起来的感觉还蛮爽的,我会尽量不去换气,把一整段连续地唱完,顺畅的感觉我还蛮喜欢的。
秋凉: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Adon带来的《离人》。

《酷拉时报》的意义
秋凉:典典曾经担任《酷拉时报》的主编,可以说这个平台是我最早阅读到的一个性别议题学术方向的优质平台,现在仅存豆瓣小站,这几年你会时常想起它,或者想做些事情来延续它呢?

典典:对,《酷拉时报》对我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生阶段,包括我现在读性别研究专业,也是因为做《酷拉时报》期间接触到一些性别方面的理论,会有一些对性别运动的反思。其实我本科期间是学国学的,听起来和性别研究简直相反。(笑)我其实不是《酷拉时报》的发起人,当时类似于一个志愿者,有些性别运动领域的前辈说,中国的女权和性少数(的讨论)从90年代出现到那时候也有十几年了,有可能有一个独特视角的反思论述,可以用性别视角去看待各种问题的这么一个平台,就有这个机会去做。这个视角不是单一的从性少数或者女性权利,而是交叉的,比如“拉拉”这个身份是女性和女性性少数的交叉身份,“酷儿”理论又是反思单纯地划分身份的政治,看是否有跨身份结盟的可能等等,当时先是有这些讨论,后来就说可以试试办一个刊物。参与那些讨论的前辈其实都有自己的工作比较忙碌,我那时刚好硕士最后一年,论文写得差不多了,比较有空,就说那我来做一些具体的执行的事情,也是一边学习一边接手,就这样不知不觉做了三年,这大概是酷拉时报的一个缘起吧。虽然现在微博不更新了,微信(公众号)也被封了,但豆瓣上还有一个“酷拉时报”的小站,记录了过去那三年的文章和对时事的讨论,我现在有的时候还会回去看一看,觉得挺感慨的,每一篇自己经手的文章都还记得挺清楚,对我来说它也构成了我的价值观,构成了我后来看问题角度的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已经是我的一部分了吧。

秋凉:作为一个读者,我觉得《酷拉时报》的文章质量非常高,也非常真诚,会带给我许多新的思考角度,反观现在的“微博女权”,好像更多时候是骂战,比如骂已婚女性是“婚驴”之类的,但真正有质量的探讨非常少见。
典典:《酷拉时报》是基于我所工作的机构华人拉拉联盟和各地拉拉小组的实践,比如有女工拉拉、少数族裔、边远地区的拉拉,也会特意去访谈她们,收集不同的视角,也会有一些跟时事相关的部分,有努力地做比较接地气的内容。我觉得真正有生命力的内容,就像你说的其实在于真诚,学术含量还在其次,我觉得好文章也是在于真诚,就像刚才我们聊到的,怎么样跟跨区域的人沟通,交到朋友,可能也是在于是不是在某个地方找到了真诚的共鸣,而不只是说说场面话。
秋凉:我也有幸见证和记录了一些前辈,比如“月恋花”的于是和“上海女爱”的陈想起,我会觉得采访她们更像是个学习和吸取能量的过程。
典典:是的,这些其实都是最早华人拉拉联盟里的成员,我们最早办的拉拉营,就是让各地小组有个机会聚在一起几天互相交流,最开始承办的小组也包括月恋花和女爱。我还记得我离开大陆前最后一次拉拉营,就是在成都办的,现在想起来都非常的怀念,那时候都是面对面很真诚的交流,大家都希望尽自己所能地给身边人提供一些空间,改变身边的人,改变社会一点点,这种愿望都特别感人。
关于“粉红经济”
秋凉:这些年有个流行词叫“粉红经济”,比如今年淡蓝网就去美国上市了,他们最有名的产品就是移动App“Blued”,你怎么看这种立足于同志人群的商业品牌呢?

典典:我自己觉得有很多方面去看吧,如果乐观地去看的话,不管是同志的app还是别的名目,这种商业上的成功说明这种群体可见度还是在提高。像我表弟表妹那一代的人就会互相开玩笑说“基友”之类的,在我小时候这个话题可能还属于没有人知道同性恋是什么,这个词还比较禁忌和暧昧,那现在这件事比较普及了,大部分人都知道,即使不是很支持,这也是可以讨论的话题,包括女权的话题也是,可能你觉得(微博女权)说的内容不是一个很好的沟通的氛围,或者很极端,反婚反育之类,感觉很“一刀切”,比较把攻击点放在个人上。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比较乐观地认为,2011、2012年我们做一个性别相关的活动,还要主动找媒体,试图在微博上制造热点话题,但现在其实这些话题就挺热了,还有很多大V靠性别话题制造流量来养活自己,这已经是种文化生态上的转变了,性别议题变得更加可见了,如果这么看的话也可以认为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进步吧。包括我妈妈的那个年代,性别方面的东西仅限于学术著作,现在在大众文化中更可见了。当然往不好的(方面)看,大众文化本来就是鱼龙混杂,很容易被资本收编,变成纯粹经济方面的东西,也很容易被主流收编,比如说防治艾滋病可以,但要说性少数人群的人权就比较敏感,肯定存在很多问题,更多是跟整个社会制度有关。
像“粉红经济”在发达国家也有问题,以前大家都要争取结婚的权益,现在社会制度是得到了改变,同志可以结婚了,好像就不用进行更多改变了,不用反思了。其实还存在着性别刻板印象,女性的工作权利和免受暴力的权利等问题,还有更穷困更边缘的同志、跨性别者,选择不进入婚姻制度的人,他们的权益也挺边缘的,不像一些很有钱的白人男同志,他们结了婚好像就过上了中产主流的生活,好像这些权益运动跟他们没关系了,也有很多这样的反思。包括亚特兰大的游行,每年有大银行在那里发彩虹旗之类的,也会有人反思说这些银行的贷款政策其实对穷人和少数族裔,对性少数种穷困的人是很不友好的,但他们借这种姿态来显得自己很进步,叫做“pink wash(洗粉)”,用粉红经济来洗自己,把自己包装成很进步的企业,但其实在经济政治的一些结构上,还是存在对少数群体的歧视和压迫。
关于“彩虹宝宝”
秋凉:这两年还有个讨论比较多的话题“彩虹宝宝”,我们可以说是多元成家的一个部分,大陆的女同群体中还挺常见A卵B怀的情况,你会考虑自己有个彩虹宝宝吗?

典典:其实一直以来都存在,性少数群体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拥有自己的宝宝,这个历史其实很长了,我们酷拉时报做过“多元成家”的概念,不一定是传统,可能几个好室友在一起共同养孩子。对我来说,我的心路历程很有意思,因为我和我妈的感情挺好的,觉得要孩子是件挺幸福的事情,我直到20出头都挺想要孩子的。但后来有段时间我单身了,看到一个得普利策奖的报道,说一些孩子被父母忘在车里的报道,觉得好可怕,我很可能是粗心大意的父母,万一不小心把孩子弄死了怎么办。(笑)当时也接触了一些反生育主义和环保方面的读物,觉得世界上人类生太多了,与其凭空制造一个不如有条件的领养,也是一样的,所以有段时间变成坚决反生育的人。不过我觉得自己反生育和反对逼婚的制度是一方面,但每个人有个人选择,只要不是把价值观强加给别人,就没有什么非反不可的,个人选择和制度应该分开去看待。
我身边反婚反育和很想要孩子的朋友都有,我妈妈是一直很希望我有孩子,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过了三十岁(笑),真的去年又有了想要成家(的念头),不一定是传统异性恋模式,但有点想要一个安稳的生活状态。以前我觉得四海漂泊没有固定家的感觉很好,但从去年开始觉得如果有家人孩子,会是一个很美好的感觉,又开始考虑要孩子,可能这两年先了解下这方面的知识。像你说A卵B怀这个问题,最近国内现在也有个别官司,说A卵B怀以后做亲子鉴定可能会把孩子判给卵母,孕母承担了生育的辛苦,但有可能分手之后因为没有婚姻的保障,什么也得不到,会有种种的辛苦。
秋凉:这个案子是首例同性伴侣争夺子女的抚养权,在讨论谁才是孩子真正的妈妈,一个是提供了自己的卵子(卵母),说孩子的基因是她的,一个是提供了自己的子宫(孕母),承担了怀孕和分娩。前两天厦门市湖里区法院宣判了结果,依据出生证明和入院证明,认定是孕母完成了怀胎和分娩,且考虑到孩子还没有满周岁,还需要母乳喂养,法庭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出于孩子健康成长的考虑,把孩子判给了孕母。
典典:但我觉得这个真的要分情况考虑,这一方面是个法律保障的事情,就算是男的始乱终弃,在出现现代婚姻法之前,即使你百分百确定孩子是那个人的,但一没有亲子鉴定,二没有婚姻保障,还不是说抛弃就抛弃了。包括在美国这边,黑人社群里单亲妈妈的比例非常高,也是因为黑人男性很容易遭受警察暴力,被抓,或被卷入犯罪集团,进了监狱出来后找不到工作,一直在这种恶性循环里面,(黑人)女性一个人带着很多孩子在外面生活,这种没有父亲的现象也很多。
在拉拉群体里我觉得不见得A卵B怀会复制这种情况,至少我身边有很多例子,以及我自己的感受,如果两个人感情真的很好,关系也没有很不对等,那么探讨怎么生孩子是很多方面考虑的,比如说谁的身体比较好,谁更愿意生孩子,因为取卵对身体也是有一定伤害的,双方都是有一定付出的,或者两个人希望和孩子都有某种关系,因为A卵B怀的话孕育的那个人和胎儿也会有互动,卵子也是来自另一个母亲,那也有人觉得“这样生下的孩子是两个人的纽带”之类的,每个人考虑的方面都很多,所以我觉得在具体的事例上很难简单地套一个框架。而且真要说复制异性恋模式的话,我听说把卵子改造成精子是完全可行的,早年日本的科学家曾经在小白鼠身上成功做了这个实验,但我不知道这种实验是不是对人类对男权制度冲击太大,无法应用在人类身上,不然可能真的是两个女性之间是完全可以生育的,就像克隆羊多利也是三只母羊的结晶,就根本不需要男人。(笑)
Adon:身为一个男性,刚开始听到这个科技还是蛮惊恐的,会怀疑男性存在的意义,第一时间也会想到卵子变成精子的可能性,好像比精子变成卵子的可能性要高,而且还有个子宫的问题,所以一开始听到的时候,会让我想到日本在二战后有个小说叫《家畜人鸦俘》,这个小说就有点反映出日本战败后的思维,是不是因为有了这个科技,未来是不是就像小说里面叙述的那么极端,完全是一个女性主导的社会,作者沼正三就是基于女性从生育解放之后对未来的一个想象,当然这也是基于日本二战战败之后,一个很独特的伤痕的文学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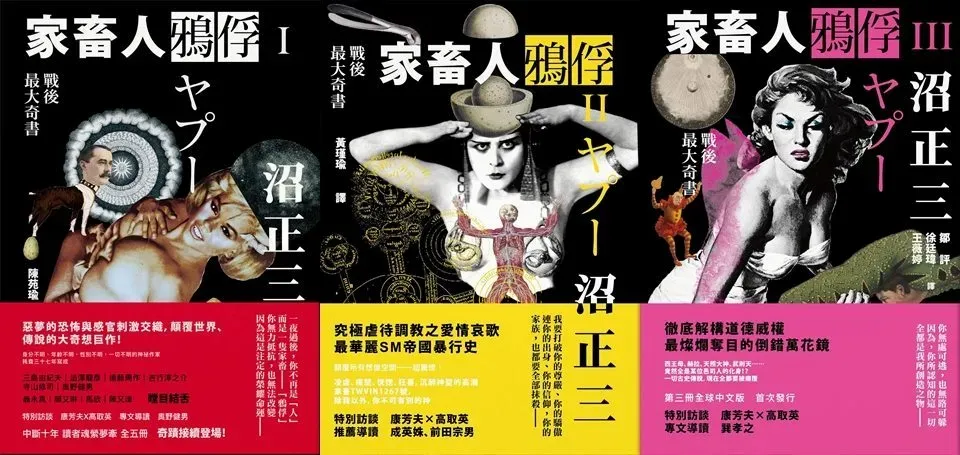
秋凉:我搜到的新闻是说在2006年有位日本的科学家山中申弥获得了2012年度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他找到了一种很简单的办法把体细胞转变成“诱导型多功能干细胞”(iPS),根据2015年英国的报道,借助这个技术,理论上女同伴侣可以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后代,但都会是女孩,因为不涉及男性的Y染色体,所以就可能出现类似西游记女儿国的情形,就是国家里所有人都是女性,生下的也都是女性,完全排除了男性。像Adon刚才提到的作品可能是男性对于未来生殖焦虑的一种想象,那我们也希望科技的进步带来的更多是个体作为选择的自由,而不是去限制个体的自由,也不是巧取豪夺剥削他人的自由。这种科技带来的最直接的改变,可能是我们家庭观念的变化,未来我们会朝着一个全新的地方进化。那我们回到当下,一对女同伴侣还是需要借助精子银行或者捐精者才能生育下一代。我想问下典典,你们未来要孩子的话,在选择精子上会有什么偏好吗?据我所知,去国外精子银行的很多女性是倾向于选择亚洲人或者白人的精子。
典典:对,我和伴侣在这上面也有过争执,她的第一反应还是要找白人或者亚裔,但她也会常常反思自己隐形的歧视,因为她是做心理学发展实验的,做实验的时候会招一些儿童的受试者,她也确实觉得白人的小孩更可爱,对他们好像更有耐心。我们都会反思自己的审美是怎么形成的,比如我们从小看的片子里面白人是什么形象,黑人是什么形象,商业广告里都是什么样的形象,其实都在塑造我们的审美,特别涉及自己生孩子的时候,会有很现实的考量,害怕以后孩子受到歧视,生活更艰难。这其实跟我妈妈对我的感情很像,她不是觉得同性恋不好或者我有什么问题,但她觉得这个社会把同性恋当作低人一等的,给他们的生活制造了很多障碍,她不希望我面临这些障碍。
所以我常常说社会运动所针对的东西,其实要考虑更大的制度和文化是怎么影响个人的,而不是“你这个人就有罪”“你这个人就是种族主义者“,每个人也可以以自己作为一个运动的手段,比如坚持不婚不育,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激进的姿态,但确实没有必要去指责一个人,比如指责她选择一个白人精子来生育孩子,因为指责个人意义不大,个人的选择是受限于自己所在的社会文化所做出来的,如果每个人都能有反思的话,也许会让社会变得更好,但不能强求每个人都自甘放弃自己的利益,去做特别困难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就是反思吧,另一方面就是意识到自己的特权,并且不要把这种优越感加给别人。
我其实自己也很犹豫,因为之前和我的伴侣有些争论,她想要亚裔或者更白的小孩,我就吐槽了她一下,她问:“那你希望我们的孩子从小歧视吗?在美国这种环境里,我真的不希望我的孩子是个黑人。“我就觉得我很能理解她的想法,我们也不可能在孩子这一代改变美国的社会环境,如果我们以后飞到加拿大或者北欧等好像对少数族裔更宽容的社区,那其实就更是一种特权。如果留在中国,我们甚至都很难有机会作为一对同性恋组成家庭,生育孩子等等,每个步骤能做到的事情其实都包含很多特权,也包含很多偏见和周围社会条件一起造成的结果。所以我想可能自己选择的时候,还是会选择对自己好,对孩子好,或者自以为好的东西,但同时也要有个清醒的意识去反思,到底是什么让自己作出了这样的选择,而不是盲目地相信自己的选择只是个人的,或者就是对的,千万不要想要把这些选择来强加给别人或者用来评判别人,我觉得能做到这一点就不错了。

秋凉:我以前觉得世界永远是在进步的,历史永远是在发展的,但现在发现有的时候历史会兜圈,比如前些年酷拉时报所提出的观点放到现在还在继续被讨论,像现在微博上的一些话语可能还不如十年前、二十年前的认知,你怎么看呢?
典典:我以前学过一段时间的近代史,看民国时期报刊上的很多观念就非常先进了,那时候的人就说“婚姻制度必将灭亡”,就在想象应该结成怎么样的情谊,想象育儿是一个公共事业,女性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这样的想象那时候就有,但现实的发展是非常缓慢和复杂的。
秋凉:你在美国这些年还会和以前的小伙伴保持联系吗?
典典:前几年我确实心有余而力不足,光是课业就应付不过来,就稍微少了一点,但从今年开始,其实前两周我还有跟一些新老小伙伴有个线上的联系,大家聊一聊天,觉得挺开心的,也有怀念的感觉。我们这些人经历了这些年的起起伏伏,都已经没有那么乐观了(笑),但还是很感动,知道大家还在关心这方面的事儿,不管表面上的生活方式发生了什么变化,但还没有毫无反思地彻底回归主流,还是带着性别的视角在观察社会,试图影响身边的人,想到这一点就还是觉得挺好的。

秋凉:还有两个月美国总统选举就要迎来结果了,今年民主党的候选人拜登提名了贺锦丽为副总统,她有着少数族裔的身份,如果拜登击败特朗普的话,她会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的首位女性副总统。我还记得四年前希拉里的败选对很多女权小伙伴是个很大的打击,觉得打破“玻璃天花板”选个女总统怎么这么难,也有学者对此做了研究和总结。
今天我推荐给大家的书叫《属于99%人群的女权主义:一份宣言》(Feminism for the 99%: A Manifesto),三位作者分别是辛西亚·阿鲁扎(Cinzia Arruzza),是一位意大利裔女性,来自南部的西西里,还有提提·巴塔查里亚 (Tithi Bhattacharya),是关注巴勒斯坦司法议题的社会活动家,还有一位作者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是阿鲁扎的同事,她们提出的“99%的女权主义”起源于目前这种斗争和全球动员的低落,反对资本主义和种族主义,寻求全球运动的社会与政治联合,为99%的人争取一个更好的世界。那说得通俗一点,她们认为希拉里代表的1%的自由主义的精英女权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而我们的未来在于创造一个可以探索和整理各种诉求的空间,为大多数人也就是“99%”的女权主义”。让我们一起保持愤怒,保持清醒。

非常感谢典典做客我们电台,这种交谈带来的力量一直鼓舞着我。感谢收听「野聲」电台,让我们下期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