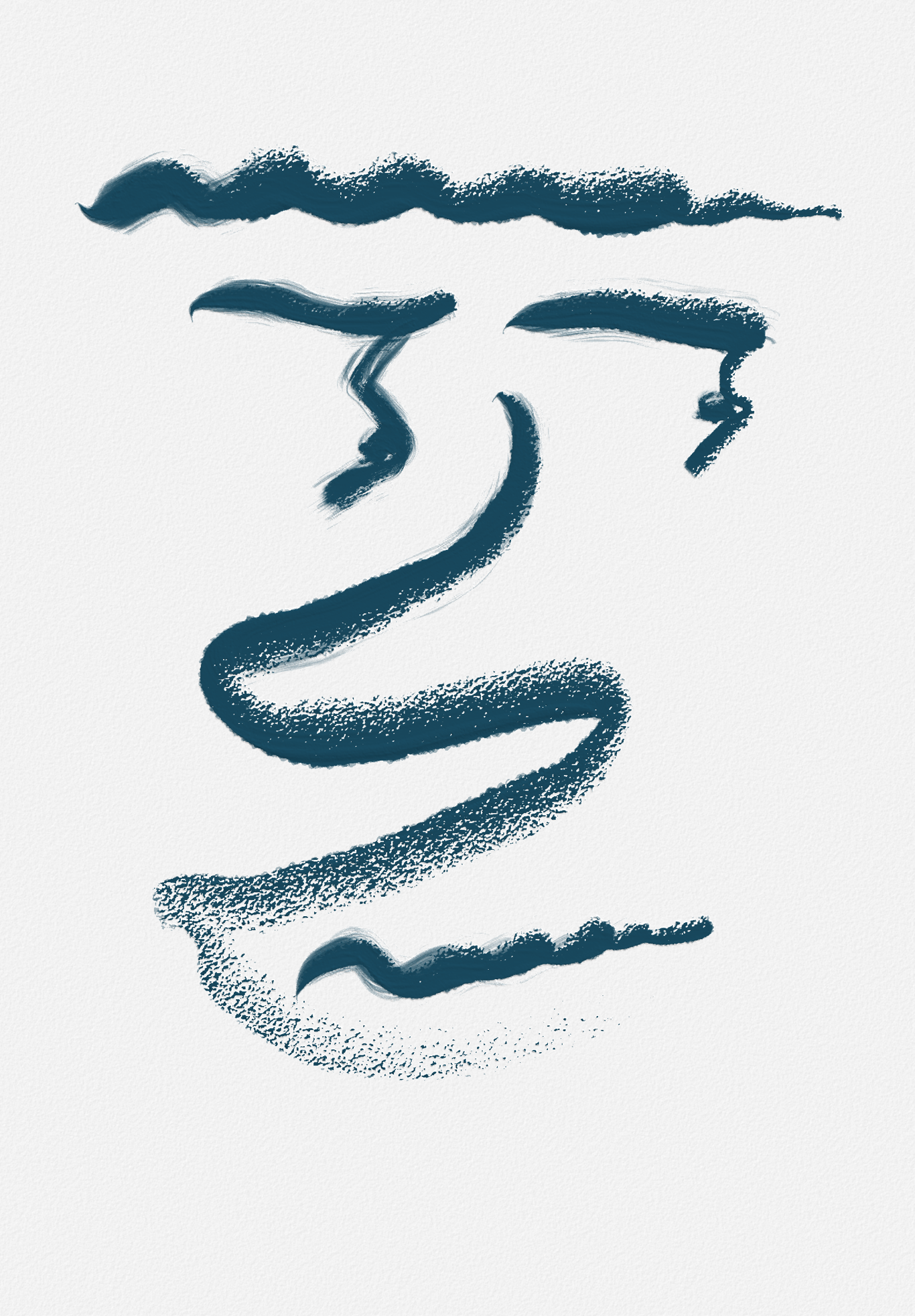实验搭档
入学的第二年,在第一节实验课上如同过去的每个学期一样,学生们要两两配对,以搭档的形式共同完成接下来的七到八组实验。原先的搭档因转学而留我一个人,因此我不得不再寻一个落单的。说来也巧,那个学期刚好有一个之前因病休学,经疗养之后又继续学业的同学,于是我们俩就顺利成章地 “搭了伙”。
我跟这位老兄虽然之前从未打过照面,但是他的事迹我早有耳闻。简单来讲就是传说中的学霸。文质彬彬,温文尔雅,课上教授博士生提出的问题,他好像永远知道答案的样子。考完试,口口声声说自己不知道答得怎么样,但是拿最高分的总是他。听着别人对他得描述,心想大千世界的学霸都强得千篇一律,倒是我们这些学渣弱得千奇百怪。我心里默默感激那个转校的同学,要不是她,我岂能跟他组成一对,这门课不仅及格势在必得,搞不好还可以登顶我成绩单上的最高分。我唯一担心的则是,自己能力有限,所以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拖了人家的后腿。
于是我每节实验课之前都比过去预习得还要认真,不是为了最后的成绩,而是希望在合作时别让他看出来我什么都不会。其中有一节实验课要面对我们化学系一个口碑极差的教授。这个老头脾气阴晴不定,看似平静的外表下藏着一颗嵌满定时炸弹的心。传说他有点瞧不起外国学生,总是恶言相对,但是了解下来,得知他是瞧不起所有人。经常看到他的博士生哭着离开他的办公室,也听别的讲师说他还跟其他教授吵过架。只有他的秘书整天笑呵呵的,会去安慰那些伤心的孩子。真不知她有什么本事,只听闻她几年前好像突然在某一天昄依了基督。
实验当天,我们两个“互相谦让”地让对方先进到实验室以便坐在离教授比较近的位子。按流程,开始操作前我们需要先就实验内容解释一些列知识点,然后简单复述实验过程和预期结果。虽说我也准备了,不过为了有一个流利的开场白,我总会把这个机会留给他。这回的他表现得一如既往得好,但是多少可以看出他注视着教授的眼神有点躲闪,而在教授对于某个没有描述到位的词皱了一下眉头时,他连连解释,略显慌张,我也鼓起勇气在一旁稍作补充,以表现这是我们两个作为拍档,经过认真预习一同讨论得出的结果。随着他老人家眉头展开,微微颔首,我开心地发现原来他也怕这个教授,原来学霸在老头那里并没有什么特权。顿时,我对这位老教授的一视同仁肃然起敬, 而我们“并肩作战”的两小时,好像让我们比以往更熟悉了一点。实验如搭档的开场白一样,一如既往地顺利。我们拷贝好数据,松了一口气。走出实验室,我已经脑补出了一份没有语法错误,图线优美的报告,悠然地跟他道了别。
接下来一次实验他得了重感冒,说话一反平时的轻声细语,而是低沉沙哑,突然变得好不性感。我开他玩笑,引来了他更加性感的笑声。期间,我们商定,分开打分数的实验我们报告分开写,而一同打分数的报告则由他一人完成。虽说,这分明是嫌我拿不到高分,但是我怎么可以蹭着别人的高分还卖乖,当然就一拍即合地同意了。看着实验一个个地推进和报告一份份地上交完事,我那几个月真的是轻松自在。最后一次实验是在春节过后了,我刚巧回国带了些零食,也分了他一点当作迟到的圣诞礼物,也算是谢谢我们这一个学期来的合作。他说:“真不好意思,我可什么也没为你准备。”我连连摇头,心里的如意算盘是,我可盼着你给我们拿一个高分呢。
这一整套实验完成之后我们还有大约两个月时间完成剩下的报告,上交后便可以在学生主页上查分数。快到截至日期了,我的那部分早已经写完,而他的那部分却迟迟没有给我答复。发了他几次消息他也不回。过去一学期他倒是经常不回我消息,我只能理解成优秀学生的专注力了,哪像我整天捧着一个手机。眼看着最后期限慢慢逼近,我甚至破罐破摔地想:反正我只求及格,但是这个分数在学霸的成绩单上应该不会好看才对。
就在我忙着做无机化学大实验的间隙,对他已经无心催促时,我终于收到了他去世的消息。是他父亲给我留的言。我反复查了那条信息里的单词,希望是我语言不过关,看不懂母语者的笑话。应该是在整理孩子遗物时发现还有一个学习费劲儿的同学在一个劲催自己儿子实验报告,才给我发的这个消息吧。那天,他的父亲跟我约好在学校图书馆门口见面,好像要还掉孩子生前借的书和更衣室的钥匙。跟校职人员说起死因,其实就是由于之前的病,突然恶化导致的。他的父亲一遍又一遍地解释叙述,跟我们这些对他而言从来都是无关紧要的人反复念叨着,仿佛每说一遍,伤痛就可以被稀释一分。我拿着那份带着老式磁盘的报告,在一旁听着,无能为力,临走时提了一句:有什么我可能帮忙的,尽管给我发消息。说完之后就觉得蠢得要死,我能帮什么,我从来都无能为力。
回寝室路上,我思考着,我想我最多理解他的家人,但是切肤之痛只有经历着的人才能体会。突然觉得有一句话说得过于乐观了:“父母是我们和死神之间的一堵墙”,只可惜在死亡面前,没有论资排辈,也没有先来后到。我不是他儿时的朋友也不是他爱的人。他的离开,我很遗憾。然而我跟他的交集只有我那时的九千多天的生命和他总共的七千六百多天生命里的几丝而已。我应该会很快忘记他和有关他的一切,就像忘记那个电化学实验里的参数一样忘记他的长相和声音,只是偶尔会想起我的本科毕业证上那一溜成绩中那个唯一的满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