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闇与幽光—对弗洛伊德《释梦》的理论解读(5)
常闇与幽光—对弗洛伊德《释梦》的理论解读(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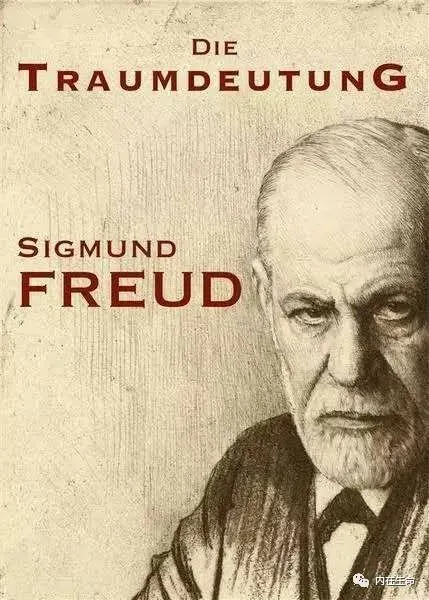
冲突与焦虑
一路走来,如果我没有太偏离弗洛伊德的原意(这当然十分困难),那么通过以上几章论述,也慢慢破开了梦的层层迷雾。我做的不过就是追随弗洛伊德的脚步,反驳关于梦的遗忘和可靠性的诘难、和怀疑做斗争、申明稽查作用或阻抗对此负主要责任;对于自由联想,指出它并不天马行空,而是被暗中限定;精神分析释梦也不是虚构幻想的主观臆造,而是对基本的联想法则的合理利用;为了说明梦的视觉特征和时态转换,弗洛伊德设计出精神装置的地质学模型,以空间和运动的类比提出回归(退行)的概念,论证了它在日常生活的普遍性和病理状态的特殊性;为进一步论证梦的愿望满足理论,弗洛伊德充分考量了日常清醒生活各种心智活动在梦中的地位,援引地质学模型,推论精神装置的早期阶段和发展历程,定义了愿望和愿望满足的直接和迂回方式,以此确立了潜意识愿望在梦的构建中的核心地位,进而推及其他精神活动。他也指出,诸如梦和症状这样的精神现象是复合结构,前意识的愿望也必不可少。在夜间最突出的就是睡眠愿望,如果它能和其他愿望相互配合,做梦就成了合理选择。
我们本来可以在前意识睡眠愿望的基础上继续考察梦的进程。不过还是听从弗洛伊德的建议,把已有的认识串联一下:
1、日间清醒心智生活会留下一些残留内容,它们想继续在夜间活动,心灵也不能完全撤回对它们的能量投注;或者白天的某个活动无意间激发了潜意识的某个愿望,或者说,激活了两者之间先验的象征关系[1],这两种兴奋种刺激因素也在梦中会混合起来
[1]参见《梦的解析》第六章,或《精神分析引论》第二部分
2、参考精神装置地质学模型图示:到了夜间,由于稽查作用的减弱,潜意识愿望的兴奋刺激蠢蠢欲动。但它的属性决定了它不能以原本的形式进入前意识(就像液体水不能脱离器皿),必须在日间经验残余中寻找合适的代理人,对其产生移情转移自身的能量。潜意识愿望通过凝缩和移置作用,形成一些具有强大能量的前意识表象群一一连串场景或幻想。这一过程要么在白天就已暗度陈仓(上述白天活动无意间激发了潜意识愿望时),要么在睡眠中才急不可耐的进行。过去某个愿望因移情到近期印象被唤醒,或近期某个遭到排斥的愿望(它是指向某个对象的意识愿望之反面,例如深爱背后的怀恨、信任背后的怀疑,它也是过去潜意识移情作用的衍生物,曾一度被意识,但失去关注后,能量慢慢耗尽,就像照明火熄灭后,黑暗又重新合拢)得到潜意识的强化而再生。在睡眠状态下,稽查机构有所怠惰,潜意识愿望因此和它的代理人频繁接触和交易,促成一系列负荷它能量的隐藏梦念,这意味着骗过了稽查。弗洛伊德评论说,愿望这种形式的变化就像形成幻想内容:强迫观念、妄想观念一样,这是形成梦的第一个前进或上升步骤。到目前为止,兴奋以观念存在,还没有变化成视觉图像。
补充一点,也是弗洛伊德反复给予读者的告诫:不可用过于机械或实体的观点来看待精神装置。理解地质学模型的要点之一,是绝不能把意识——前意识——潜意识系统看做水火不容的三个空间,并粗暴的认为它们之间有一条醒目的边境线隔开,这样一来就完全不能解释各种心智活动了。除非我们假设系统之间存在渐变的交会区域,两种形态的心智产物可以并存,类似双方商定的“非交战区”或“冰水混合物”。参见以下示意图。我在图5下半部分标记了前意识和潜意识的交会区域,潜意识内容可以上升到此,但稽查机构代表前意识在此设立岗哨,禁止潜意识更进一步。它也会放逐一些被批判的思想,这些思想随即被潜意识收留了。由于前意识系统的居间位置,它靠上的区域近似意识,或者说很容易变成意识;而靠下的区域更近于潜意识,也更不受关注。“梦的伪装”发生在潜意识和前意识的交会区,“润饰作用”则在前意识和意识的间隙发生。
3、完成第一步后,潜意识愿望已在前意识内安插了自己的代理人,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除了这些梦念,前意识里还有无数观念蠢蠢欲动。只有这个代理人更上一步,进入意识,或者说被意识知觉后,才可能形成梦。可睡眠状态通常拒绝这种事态发生,由于睡眠降低了感官灵敏性,瘫痪了自主运动系统,观念也没有了施展的空间。或许在某些情况下,无法付诸行动的强大观念可以引发不自主神经系统的兴奋,(就像我们因为羞涩、紧张、喜悦发生的那些躯体变化一样)让自己被意识,形成纯粹观念的梦。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观念就只能另辟蹊径。
4、清醒时,刺激从感觉端到运动端的运动,由于睡眠被阻断,使兴奋刺激原路返回成为可能。由于兴奋在前意识只能以观念存在,那些负荷着强大能量的隐藏梦念, 因此走上了回归作用的道路,也就是说,潜意识愿望移情而生的前意识梦念,重新后退回向潜意识。在不断退行中,不断吸引相关回忆,特别是那些最早期的视觉印象——兴奋在潜意识的形式是物的存在,在符号系统是原始符号,最初形式是知觉。愿望起始于婴儿的欲望冲动,呼唤原初的满足知觉。至此,梦完成了第二个回归步骤,即兴奋刺激从观念还原为最早的知觉。
5、一旦梦的过程成为知觉,稽查作用和前意识睡眠状态对观念的限制就对它无效了,现在它可以用感性材料直接吸引注意力,迫使意识关注它。 精神分析推翻了心理等于意识的公式,将意识从至高无上的宝座上拉下来,那么,该如何重新定义意识的性质和功能呢?弗洛伊德虽将潜意识视为真正发挥作用的空间,但绝不认为意识是个不重要的现象,因为缺乏意识的知觉感官作用,外在和内在的一切就变得不可知了。意识作为心灵的感官,将各种外在和内在的刺激性质尽收在五感中,既有物的存在,也有语言对物的描述。但在本文第三章我也说过,意识或知觉和记忆相互排斥,它只能反映刺激性质,无法保存刺激通过的痕迹。在地质学空间模型上,由于它靠的最外,所以既能接受整个精神装置外围——身体表面和外部的刺激,也能接受精神装置内部—本能或欲力的刺激。[2] 相对于外部知觉性质的千变万化(例如美食的色香味俱全),内部知觉就乏善可陈,仅有快乐和不快的性质之分。如果再具体点说,那就算痛苦吧。这是因为本能或欲力刺激——由需求引起,累积超出一定范围(因人而异)就会引发紧张的状态,这种紧张被感知为不快甚至痛苦,正如人在饥饿、口渴、便意、尿意、性欲得不到满足时那样;一旦这种紧张消除,不快就立即转变为快乐。也许作家们可以妙笔生花描述这些感觉,但所有描述只能局限在快乐和痛苦两点之间。换句话说,这仅是个量的问题。对某个人来说,体验外部知觉——缤纷的色彩、不同的香气,某种形式混合的味道可以引发快乐的感觉,但绝不能说,快乐有色彩和味道。 [2]这里就涉及到本能或欲力的概念了 ,参见《欲力及其命运》或《精神分析词汇》对欲力一词的解读
既然意识过程具有精神性质,那么前意识和潜意识过程呢?弗洛伊德倾向给予完全否定的回答,因为这些都属于精神装置内部的过程。不管它们怎么运作,只要不能为意识提供快乐和痛苦的知觉,它们就几乎是无关紧要的。那么满足的快乐和不满的痛苦刺激——对精神装置的发展起到了何种作用?弗洛伊德从人类趋乐避苦的天性中推测,精神能量的分配受到快乐和痛苦知觉的调节,其中更重要也更精细的,是如何更有效的避免痛苦刺激,建立一套预警机制。这就要求从前意识的记忆库中搜索经验,找出和痛苦有关的所有印象,快速反应。这里暂不提潜意识的原因是:潜意识即不可知。
这套有关痛苦的预警机制,必须要吸引意识的注意,也就是说它要提供痛苦的可能性。弗洛伊德认为,最有可能的是,借助是前意识的回忆和语言符号系统的关系,唯有语言文字才能将事发快乐和痛苦知觉和观念联系起来。语言符号系统具有某种弗洛伊德尚不清楚的力量,一旦和记忆中的观念或事件建立联想关系,如:吃奶—快乐、饥饿—痛苦,就为这些回忆注入了精神性质。逐渐发展的前意识系统靠着和语言、运动系统越来越密切的关系,甚至在意识到原因前就避开痛苦了。于是在意识感知的范围,精神能量和行为被导向远离痛苦的方向。由于意识可以参与内部决策过程,现在它就不仅仅是知觉的感官了,而是可以执行一部分思维活动的感觉器官了。意识现在成为精神装置的外在感官,一部分感知前意识思维活动,一部分指向知觉。
日常经验提醒我们,睡眠中意识也休眠了。很容易设想,意识对前意识的那个感觉面变得非常迟钝。这符合生理和心理的双重要求,思维必须停下,配合前意识的睡眠愿望。但睡眠对意识的知觉面向影响不大,后者被预设有一定的灵敏性,由一定量刺激唤醒(因人而异);可想而知,变成知觉的梦,就可以用新获得的性质来越过先前的限制,刺激意识的注意了——注意是意识的一种功能,只有被注意才能成为意识。前意识中所有的观念都在寻求注意,但只有那些强有力的,闹出够大动静的观念才能引来注意力,或者它也变为知觉。
梦包含的痛苦或快乐的回忆会引起意识的知觉面向的警戒,从而调动靠近意识的一部分前意识能量投注留意刺激的来源。从这个角度来说,梦的确有唤醒的功能,它让前意识中一部分休眠的力量活跃起来。这部分力量遵从着前意识睡眠愿望,要尽可能的让梦服务于睡眠,比如,尽可能增加关联性和合理化刺激,将梦打扮成一出(表面上合理的)戏,例如莫里那个断头台的梦,他由身体刺激编造出一个法国大革命中慷慨就义的英雄故事。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第六章专门一节探讨了这种“润饰作用”,补充说一下,参照图4,润饰作用发生在前意识和意识的交会区域,这种力量会一视同仁的对待包括梦在内的知觉内容,在梦内容的限定范围内,它必须服从前意识中预期观念的调节,不能漫无目的,也不能太直白表达痛苦。一旦自由的梦被束缚朝向某个方向,弗洛伊德评论说,现在它又是前进的了。
总结一下,潜意识愿望经过移情作用形成复合观念上升到前意识,这是梦的第一个前进过程。移情观念降至潜意识吸引回忆图像,直至还原为知觉,这是梦的第二个回归过程。最后,成为图像的梦刺激意识的知觉面,经过前意识的润饰作用后被注意,这是最后前进的一步。我不惜长篇累牍的描述梦的过程,不免又让人好奇,这三个过程的时间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梦仅仅发生在睡眠快要觉醒的过度时段,觉醒时长因人而异,那些打盹时做的梦更能证实这一观点:剧作家卡希尔米.波佐在短短2分钟的瞌睡间梦见自己看完了五幕剧。在梦故事达到最高潮时,我们醒了,并对最后的景象惊叹不已,完全可以解释为:梦是开始的觉醒,它的完结代表完全的觉醒。
要反驳这一观点并不困难,因为更多时候,梦并没有中止睡眠,我们察觉自己在做梦,似乎处于半梦半醒状态,然后又睡着了。何况根据我们对梦之前的了解,那第一个移情的步骤,可能早在白天就开始暗中相通了。至于其余的步骤,可能发生在夜间任何时候,人们常常觉得自己整夜都在做梦,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
尽管弗洛伊德按照时间顺序仔细的梳理了做梦的几个步骤,但他也强调,那样做只是为了描述的方便,梦的过程并不一定按照那些顺序,实际上更可能“…同时试探不同的路径,[3]兴奋也摇摆不定[4],直至寻找到最合适的聚合方向,最后形成一个稳定的组合…”[5]这种对匹配的追求可能导致梦的工作往往需要不止一天一夜,才能取得它想要的结果。有了如此耐心和充分的准备,梦在结构上的巧夺天工也就毫不稀奇了。弗洛伊德评论说,甚至梦作为知觉的可理解性,在它引起意识的注意前就已经考虑妥当了。就像制定合格的军事计划要周全考虑各种可能性一样。这个准备和测试过程可能煞费时日,但只要成功引起意识注意,它的速度就一下子加快了:因为知觉过程就是瞬时的,变成知觉的梦,也开始享受同等待遇。这就像烟火表演需要精心布置,但燃放的绚丽火花很快就没了。
[3] 这个过程就好像岩浆在某个地壳薄弱地区横冲直撞,最后终于找到某个薄弱点形成火山喷发一样。
[4]此时的兴奋是一种自由能量
[5] 方厚升译《梦的解析》 p534 ,这里自由能量变成了被束缚的结合能量。
那些在夜间就能发生的梦,也许已经汇聚了足够的强度,足以迫使注意力向自己倾斜并唤醒前意识,而不用管睡眠问题。另一些发生在觉醒时的梦,弗洛伊德认为它们还不够醒目,只能等待机会,直至快要觉醒,逐渐灵敏的注意力主动发现它们。弗洛伊德认为大部分的梦都欠缺强度,因为它们都等待快要醒来的时机。如果我们被人从沉睡中弄醒,最初感知的往往是梦的内容,若是我们自然觉醒,那最先觉察的 也 是梦工作创造的知觉内容,然后才是自身或对外部世界的知觉。
比起梦和睡眠整夜的相安无事,那些在睡眠中途就惊醒主体的梦,无疑对梦守护睡眠的功能提出挑战。本着目的论的观点,我们不禁要问,梦作为潜意识愿望的满足,为何会干扰前意识睡眠愿望的满足?或者说,梦干扰睡眠的目的何在?弗洛伊德认为要点在那个精神装置的能量分配上。虽然他坦诚对此了解不多,但肯定一种说法:“…与在白天对潜意识的严格控制相比,允许梦自行其是或仅给它少许关注,乃是一种能量的节约…”[6].也就是说,给予潜意识这一表达途径是适宜的。梦可以和睡眠并行不悖,潜意识的愿望可以和前意识的睡眠愿望和平相处,也可以和其他前意识感兴趣的方向保持一致。弗洛伊德辩解说,尽管梦的确会多次打断睡眠,但醒来以后,甚至在分析过梦后,人通常还能继续睡着。如果把梦比作一只扰人的蚊子,那么梦者将蚊子赶走,将影响睡眠的刺激排除后,他又能睡着了。因此弗洛伊德假设,通过做梦可以清除不利睡眠的因素。
[6] 方厚升译《梦的解析》 p535
我们已经知道,永远活跃的潜意识愿望,借助睡眠的有利因素,通过梦来表达自己,它具有生成梦的能力,可以刺激知觉唤醒前意识。那么完全可以合理的质疑,由于潜意识能量投注的永久性(潜意识愿望的永远活跃性),梦就会源源不断的生成,一晚上做的系列梦不就是例子吗?这些梦当然会刺激到睡眠。我们凭什么认为在经历片刻觉醒,对梦有所觉察后,就赶走了不利睡眠的刺激呢?潜意识的力量难道不会卷土重来,就像被赶走的蚊子又回来吗?
我有时候会做梦(虽然内容一点记不得),似乎处于半睡半醒态,然后越来越清醒,意识到尿急。等我方便回来,立刻就又睡倒了,但这后半程睡眠就没有感觉做梦。偶尔,我也会纯粹因为梦的内容惊醒,但继续入睡后,就不记得此后有梦了。如果以睡眠的暂时中止为分界线,我可以很肯定的说,自己记得的梦都发生在前半程。似乎可以比喻为在赶走那只蚊子时,顺手点上了蚊香。我也就此问题询问了很多人,的确有被打断后,又继续前半段剧情的的;也有说虽然还继续做梦,但梦境往往更模糊不清;所有人下半程睡眠都比较安稳。
经验只能说明现象,要解释这个问题,除了更进一步认识精神装置的运作,别无他法。的确,潜意识愿望永久活跃,如果某些前意识兴奋可以利用它们,就为梦的生成打开了绿灯。潜意识的显著特征是:无逻辑性、无时间性、恒久性。某物成为潜意识就像被收进某个时间静止的异度空间,看似从记忆中消失了,但绝对不是遗忘,也不可能被遗忘,反而被永久铭记。在对心理异常的精神分析中,已经无数次印证这一点。神经症的发作可能仅仅是某个偶然因素,就像鼠人案例里,残酷的上尉讲的老鼠的酷刑刺激了恩斯特.兰泽尔, 并通过一个微不足道的欠款事件完全激发了他的强迫思维。[7]这两个偶然事件只是为尘封的潜意识愿望提供了移情通道,一旦潜意识过程累积了足够的刺激并借移情直达意识,症状就生成了。导致鼠人病态的缘由,乃是他五岁左右父亲的一顿暴揍,病人完全忘记了此事,但对父亲的愤怒、憎恨、怀疑却永久沉淀下来,并时不时被现实激发。更多的事件让弗洛伊德有感而发:…三十年前体验过的一次伤害,期间一旦有机会靠近潜意识的情感源泉后,就能和新鲜的刺激一样产生作用…”。[8] 如果现实的偶然因素触动了回忆,当年的一幕就会以移情的方式复活,由于在伤害发生时,所激发的刺激或情感并没有被适当卸除,这些刺激或情感就会淤积在事件上。一旦移情发生,刺激或情感就会爆发出来,进而控制言行。这正是精神分析可以干预的地方,通过为病人找到一种适当的卸除途径:即语言表达替代具体行动的方式,让潜意识的过程成为意识[9],从而忘却无法忘却的回忆。于是弗洛伊德做出了经典论断:“…人的回忆会模糊,往日印象带给我们的情感体验也会减弱,我们总倾向于这是理所当然的,是时间对心理记忆痕迹的原发效应,但实际上,这是我们的心灵辛勤工作带来的继发变化。这项工作是前意识执行的,心理治疗只能将潜意识置于前意识的控制之下,除此之外别无他法….“[10]
[7]参见李韵译《弗洛伊德心理治疗案例三种》
[8]方厚升译《梦的解析》p535
[9] 关于语言是一种替代运动或卸载途径的论述,参见《科学心理学大纲》或《喑哑与倾听》
[10] 方厚升译《梦的解析》p536
弗洛伊德在实践中发现,寻求突破的潜意识兴奋过程,通常有两种结局:
1、这个兴奋过程被排挤,也得不到表达机会,也就是说,它一直维持潜意识状态。但寻得机会后,它会在压抑的某个薄弱处强行突破,将自身负荷的兴奋一次性释放。进而产生行动,结果可能是某种躁狂或妄想发作。
2.这个兴奋过程上升到前意识系统后,就受制于前意识的规则,它不是直接释放,而是被前意识所束缚。
第一种情况,兴奋或能量是自由、不受控制的、也没有具体方向的;第二种情况。兴奋受到了一定规则的约束,具有方向性。它们即代表了弗洛伊德在科学心理学大纲的假设:自由能量——结合能量[11]
[11]参见《科学心理学大纲》或《喑哑与倾听》
梦的过程上演的是第二种情况:梦成为知觉后,前意识的能量投注(在注意力的指导下)指向潜意识的兴奋刺激,将后者约束起来,使其失去干扰睡眠的能力。如果梦者果真醒来片刻,那前意识就进一步戒备起来,即使兴奋的潜意识还能继续生成梦,但主体也不会再醒来,似乎真的将惊扰睡眠的蚊子赶跑了。弗洛伊德因此评论说:”…允许潜意识愿望自由发挥,为它敞开通往回归的途径,从而建构一个梦,然后只要花费少量的前意识工作来约束和处理梦就行了——而不必在整个睡眠期间都严格管束潜意识,这样更便利、更节约。尽管梦最初是一个漫无目的的过程,然而经过各种精神力量的相互作用,它获得了某些功能….“潜意识愿望只求最快满足,根本不考虑其他因素,它就像泛滥的洪水哪里低洼往哪里流,但受制于前意识后,它就要在一定程度服从目的:“…梦将原先自由的潜意识兴奋重新置于前意识的控制之中,由此释放潜意识兴奋,起到潜意识的安全阀作用….”[12]梦就像水利工程,只需少量维护,就能防止潜意识的洪水肆虐,保护前意识的睡眠。因此,和其他精神活动一样,梦也是一种妥协结构,居间协调潜意识和前意识系统的冲突,同时满足双方的愿望。
[12] 方厚升译《梦的解析》 p536 或车文博译 p361
弗洛伊德承认,之前他一再有意的回避这种可能性:如果两个系统的的愿望不能协调会怎么样?在充分了解了精神装置的结构和功能后,现在可以正面回答了:这意味着做梦功能的失败。梦要满足一个潜意识愿望,但如果这个企图实现的愿望对前意识产生了太过强烈的刺激,以至引起后者激烈的排斥反应时,梦当然无法再继续了,它会被立即打断并代之以完全清醒的状态。看起来,安稳的睡眠被梦破坏了。但这并不是梦的错,它尽忠职守想要守护睡眠的决心也不曾改变,如此只能解释为由于情况的变化,原本实用的某种手段变得无用甚至成为负担和干扰因素,正如古生物学中常见的例子:恐龙、猛犸象、剑齿虎,它们曾经极为高效的生存手段,在新环境下就格外低效甚至妨害。回到梦的话题,如果它不幸因为情况变化干扰了睡眠,但就干扰来说,弗洛伊德争辩道:它岂不具有一个新目的,即提醒机体注意到变化,进而调动资源予以应付,就像在痛觉中发生的一样?
我们之前一直回避焦虑梦的解释,并非不敢面对,而是时机不到。在大胆说出“焦虑梦也是愿望满足”时,我们已经充分考虑了潜意识系统和前意识系统的互动:将愿望置于前者,由后者负责对愿望审查、排斥和压抑。焦虑可以认为是两者的冲突、不相容的反应,[13]…即使对于精神完全健康的人而言,前意识对潜意识的控制也不是完全彻底的;压抑程度可以标志我们精神健康的程度,神经症症状表明了两个系统之间的相互冲突,症状是让这种冲突暂时告一段落的妥协结果….。[14]对神经症症状的精神分析可以看出,潜意识兴奋通过移情,在某个方向大举入侵并压制了前意识,但也只是局部优势而已;前意识虽然还掌控着大局,却无法将入侵的潜意识兴奋完全压抑下去。
[13] 方厚参见《精神分析引论》中,仙女让夫妻俩许三个愿望的故事
[14]方厚升译《梦的解析》p538车文博译 p362
如果这种互不退让的状态持续下去,就会消耗大量的精神能量甚至瘫痪主体。只有形成折中的症状,潜意识兴奋找到一个释放出口,前意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潜意识加以约束,冲突才能暂停。上一章已举过朵拉和另一个女癔症病人呕吐的例子,这里我要以小汉斯为例说明简要说明:小汉斯害怕看到马,因此不敢上街,也不敢外出。他看起来好像被迫(成功)要避开那些可怕的大家伙。所有劝诱小汉斯上街的尝试都失败了,因为他没走出去多远就爆发焦虑。分析显示,小汉斯之前在街上有一次焦虑发作和一些关于马的幻想,此后就不敢上街了。我们可以推测,回避行为旨在防止焦虑爆发,对具体事物—马的恐惧充当了抵御未知焦虑的前哨。[15]潜意识的兴奋释放会造成前意识的极大不快,后者必须极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它使用了和做梦时相同的预警机制,如果判断潜意识兴奋将被释放,或是有这种可能性,就立即引发痛苦让主体采取行动避开更大的痛苦,就像身体炎症反应一样。
[15]参见《5岁男孩恐惧症的分析》
这里补充说下,症状形成虽然意味着某种平衡,但这种平衡也会随着环境变化被打破。有时候情况变得有利,潜意识愿望找到了更有效的替代满足途径,或者当前出现的更紧急情况迫使它和前意识合作时,症状就消失了。那些常年瘫痪住院的女癔症病人,她们一听到家里发生了不幸,便立刻跳下病床,完全忘了生病。而另一些生龙活虎的女人,丈夫一回到家,她们立刻变得病怏怏了。[16]不过,症状也是相当顽固的存在,主体在长,它们也会随着时间累积,不断向更深更广的区域扩大地盘。年纪越大的患者越难治疗就是因为,症状已经渗透进生活的各个层面,甚至和病人融为一体了。这就像当今的墨西哥,政府还在明处控制着国家,但对肆无忌惮的贩毒势力在暗中统治的法外王国却无能无力。
[16] 参见《朵拉—癔症案例的分析片段》
既然我们已经多次提到了快乐、痛苦、焦虑、恐惧等情感,弗洛伊德提醒我们,如果不对情感在精神生活中的作用加以考察,讨论无法进行下去。可以假设,如果任由潜意识内容自行发展不加限制的话,它产生的情感必然是快乐的;可如果考虑了现实因素,这种快乐对主体来说就是不合时宜且危险的。儿童害怕自己对父母的敌意攻击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更害怕遭到以牙还牙的报复——幻想的被遗弃、阉割和死亡。因为痛苦释放源于某些潜意识内容的移情产物,因此这些内容(观念)也遭到前意识的驱逐和压抑。那么,情感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观察显示它们是天生的,“…古老的,甚至先于个人,攸关生命之重要事件的重现…”[17]就好像是某种运动功能或分泌功能,是内在(神经)刺激传导的外在强烈体现。情感由潜意识的内容的释放而产生,本不受主体控制,正如在婴幼儿那样。但发展起来的前意识可以利用对观念的控制,阻止观念和情感接触,不让情感被注意到(让它停留在前意识,不引起意识)。正如弗洛伊德在癔症病人身上发现的,情感与引发情感的事件分离了,后者单独被压抑。由于潜意识的兴奋被前意识妨碍或掐断,释放的情感迫于压抑作用就可能转化为焦虑一样的痛苦。
[17] 参见《症状、抑制与焦虑》
弗洛伊德因此评论说:“….如果听任梦的过程自由发挥,这种危险就会发生,它得以实现的条件,一是先前已经发生过压抑,二是被压抑的冲动必须发展到足够的强烈….”压抑是潜意识和前意识角力的过程,潜意识愿望不断积聚力量,在前意识寻找合适的代理人,而前意识也尽忠职守将它发现的内鬼驱逐出境。实际上,这已经属于神经症的问题了,只是由于潜意识在睡眠中的放肆活动必将引起焦虑,才不得不加以说明。不过他也指出,有关焦虑梦的理论可以作为神经症心理学的一个补充,在焦虑的话题上,它们相互交会。
这里我要举几个例子,有我自己的,也有弗洛伊德本人和他的病人的。
多年前的某天夜里,我因为梦见糟糕的事情被惊醒,发现自己难过的哭了。这似乎是个纯粹观念的梦,内容是父母不要我了。咋看上去,这完全和愿望满足不相干。但我后来反问自己,究竟我干了什么,父母才不要我?于是想起一连串放任自己、违背父母的行为,我只能说,当时最让我羞耻与罪疚的,与性、快感有关。进一步的分析显示了俄狄浦斯的愿望。一旦梦的过程触及这些禁忌,压抑立即被完全启动,预期的快乐变成了难以忍受的痛苦。
下面这个是弗洛伊德在7、8岁左右的梦,过了30多年才加以解析:一个生动的梦:我看到心爱的母亲,她的睡容非常安详,两个(或三个)长着鸟嘴的人将她抬进屋内并放在床上。我从哭泣中醒来,并惊醒了父母。有些人(包括我)最先留意的是“长着鸟嘴的人”,在黑死病大流行期间,这身打扮的人是专门的收尸者,如果真这么先入为主认为梦和死亡有关,那可真被蒙蔽了。弗洛伊德自己说,“…梦中那些穿着奇特、身材异常高大、且长着鸟嘴的形象,来源于菲利普逊《圣经》中的插图,我想它们必定是古代埃及墓雕中长着鹰头的神祇。此外,分析还使我想起看门人的那个没有教养的儿子,小时候我们经常一起在屋前的草坪上玩耍,他的名字我总觉得像是菲利普。我隐约记得,平生第一次正是从他那里听到有关性交(vogeln)的粗话,而有教养的人总是用拉丁文的“交媾”(coitus)[18]说法,梦中选用鸟头也清楚指向了那个粗俗的词。当时,我一定是从这位老于世故的玩伴的面部表情中猜出了这个词包含的性意味。梦中我母亲的表情的来源于祖父在去世前几天的神态,我看到他这样在昏迷中鼾声连连。因此,必然要将梦中的润饰作用解释为母亲将要去世;梦中基调亦与此相吻合:我在焦虑中醒来,情绪无法平复,直到把父母惊醒。我记得自己又看到母亲的面孔时,一下子就安静下来,好像我需要确认原来她没有死。[19]现在我们了解到,小弗洛伊德不是因为梦见母亲有生命危险才焦虑,而是对自己的性欲望感到焦虑,这些内容是通过视觉内容表达的。他哭喊着惊醒了隔壁父母,也满足了一个愿望:干扰了父母(可能的)性关系.
[18]德文vogel(鸟)和vogeln是同源词,后者是性交的粗俗用法。
[19]方厚升译《梦的解析》p540—541
弗洛伊德有位27岁男性病人,患重病已经一年多了,他报告说,在他12岁左右时反复(伴有强烈的焦虑情绪)梦见,一个男人手拿斧头追赶他,他拼命地想跑,但却像是瘫痪了似的不能动弹。这是一个极为普通的焦虑梦,很难看出和性有什么关系。在分析中,梦者首先想起他叔父告诉他的一件事(时间在做梦之后),叔叔说他有一天晚上在街上遭到一个形迹可疑的人的袭击;梦者就根据这一联想做出推断说,他可能在做梦的那段时间听说过类似的事情。至于斧头,他记起当时有一次用斧头砍柴时伤了自己的手。随后他立即回想起他与弟弟的关系,他经常虐待这位弟弟并打他,尤其记得有一次自己用靴子踢弟弟的头并踢出了血,当时他母亲说道,“我担心总有一天他会死在他手里。”就在他的思绪仍然沉浸在有关暴力行为的话题时,突然想起9岁时一次经历。有天父母很晚才回家,他假装睡着了,父母也就上床就寝。随即他便听到喘息及其他一些显得很怪异的声音,他甚至能猜测父母在床上的姿势。后来的联想表明,他已把父母之间的关系类比为自己和弟弟之间的关系。他将父母之间的事纳入到“暴力行为”和“打架斗殴”的概念下,还为此找到一个证据:那就是母亲床上经常出现的血迹。[20]
[20]方厚升译《梦的解析》p541—542
类似的回忆常常在分析中上演,在时间上往往也更久远,以至于弗洛伊德日后提出了“原初场景”和“原初幻想”的概念。[21]不过此时他的评论是“….成人之间的性交会让偶然目睹的小孩感到非常惊讶,进而引起某种焦虑,这是是一种日常生活中常有的经验…”他解释说,儿童虽然直觉到性兴奋,却不理解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不知道父母在干什么。另一方面,父母卷入在内(而把自己排斥在外)引起了儿童的敌意和对敌意的害怕,于是性兴奋在就转化为焦虑了。弗洛伊德也指出,在更早期,指向异性父母的性兴奋(广义和狭义的,参见《性学三论》)尚未遭到压抑,可以自由表达。
[21]李韵译《弗洛伊德心理治疗案例三种》之《来自婴幼儿期神经症之一的病史》(狼人的故事)
弗洛伊德和后来的克莱因,对经常发生在幼童身上、常伴有幻觉的夜惊,都做出了与性有关的解释。[22]他们一致认为,这只能是由于儿童对性冲动的误解和排斥造成的。克莱因指出,分离(包括想象的分离、被抛弃)、母亲的怀孕或弟妹的出生,都可能造成焦虑爆发,如露丝案例。[23]
[22]参见《儿童精神分析》
[23]同上
我自己的评论就此结束,但弗洛伊德记录的滑稽例子让我既感到荒谬,也觉得无奈:大众至今仍在忽视儿童性欲,恐怕某些医生也依旧狭隘,如果无视心理——性欲的因素,就会曲解很多临床现象:
一个身体虚弱的13岁男孩开始变得焦虑而多梦。睡眠很不安稳,并因伴有幻觉的几乎每周都有一次因强烈的焦虑发作而从梦中惊醒,并且伴随着幻觉。对这些梦,他总保持着非常清晰的回忆。他说,梦中,魔鬼冲他大喊:“现在我们抓住你了,现在我们抓住你了。”随后闻到一股沥青和硫磺的气味,火把他的皮肉被烧焦了。他惊恐地从梦中觉醒,最初完全发不出声来。当他能够出声时,家人就会清楚地听到他说,“不,不,不是我,我什么都没做!”或“求求你,我再也不敢了!”有时又说:“阿尔伯特(男孩名)从没做过这事!”后来,他拒绝脱衣服,“因为火只有在他不穿衣服时才烧着他。”因为情况威胁到了他的健康,于是他被送到乡下。在那里过了18个月后,他才从那些恶魔梦中摆脱出来。到了15岁时,他有一次坦白,“我不敢承认;但我一直有针刺的感觉,我的那个部位总是过度兴奋,令使我神经非常紧张,有时候甚至想从宿舍的窗户跳出去。”
(1)他在小时候手淫过,又对此加以否认,并害怕因此受到重惩(例如他的自白:我再也不敢了,以及否认:阿尔伯特从没做过这件事);
(2)随着青春期的开始,由于生殖器部位出现兴奋,手淫的诱惑又复活了;
(3)从他内心迸发出压抑的努力,将力比多压抑了下去并将之转化为焦虑,并且,这种焦虑后来又让他想到了之前所害怕的惩罚威胁。
原作者的推测让我忍俊不禁:
(1)青春期对身体脆弱的男孩的影响,是使之更加脆弱,并导致相当程度的脑贫血。
(2)脑贫血引起性格变化、让他产生魔鬼幻觉以及非常强烈的夜间(甚至日间)焦虑状态。
(3)这个男孩的魔鬼幻觉与自我谴责可以追溯到宗教教育对儿时的他所产生的影响。
(4)在相当长的乡下生活中,由于身体得到锻炼,他在青春期过后恢复了体力,所有的症状均消失。
(5)这个男孩的大脑发育状况可能受到了先天因素的影响,或许可以归结为遗传因素以及他父亲过去的梅毒感染。”
作者最后振振有词的说:“我们将这一病例归类为虚弱引起的无热性谵妄,症状的原因在于大脑局部贫血。”[24]
[24]方厚升译《梦的解析》p542—5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