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一切堅固的都煙消雲散了
「一切堅固的都煙消雲散了」那個日子以後雖不是末日,但至此之後,之於某些人,之於我,這種感覺是確確實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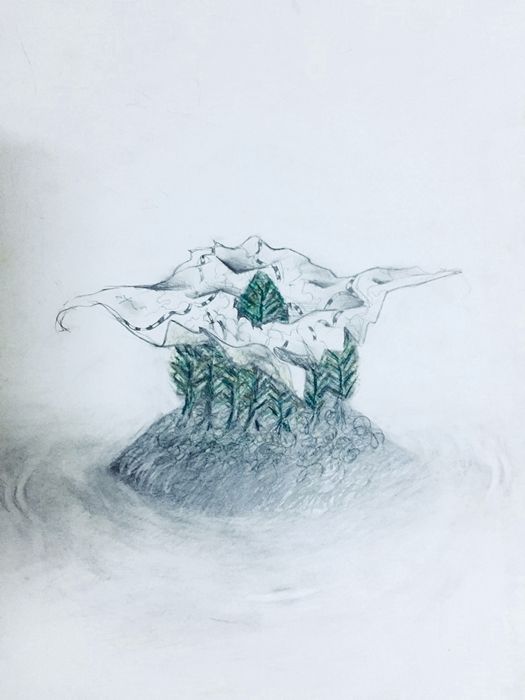
1999年9月21日凌晨,超級大震來襲的時候,我才剛剛回到家,和往常一樣地停好機車,上了三樓住處,打開大門,循線摸進自己房間,一邊推門一邊側過肩頭脫下背包,突然間,整個門框晃動起來……。
書架上的書本霹哩趴趴落下、鬆開的背包墜及腳邊,說時遲、那時快,我緊急張開雙手往外一撐,頂住了正往我身上傾倒的書架以及持續掉落的書本。此刻,地板又幾乎要從腳底滑開,身體像是置身在太空艙一樣,上上下下浮晃了幾下,好不容易才平靜些,不一會,又開始搖晃了起來。
「怎麼回事,怎麼回事?」此時室友的嚷叫聲從隔壁傳出,他慌慌張張從房間裡跑了出來
我也沒好到哪去,忐忑不安地回應著:「……地震」。
驚魂甫定後,我趕緊撥了電話回彰化老家,確知家人無恙之後,接下來兩天停電、有事沒事又搖晃一下的狀況,也就沒特別在意了;不過就是當成碰上幾個颱風日罷了。直到房裡所有可以吃的東西都吃光了,外出去覓食,見到超市幾乎被搜刮一空的架子,才嗅出一點異狀,而在小吃店好不容易發現個正常播出的電視,看著死傷慘重的新聞畫面,才知道外面已經天翻地覆。
回到家裡,我找出電話簿來,打電話確認一些朋友狀況。
草屯的狀況不妙,前女友任教的草屯商職整個給斷層帶抬起,她的電話卻一直不通。幾天之後,接起電話的卻是她母親,這才得知,前女友在外頭的住處屋頂整個垮了下來,那一晚她是從瓦礫堆裡爬出來的;還好,人總算沒什麼大礙。
這下子,我那慢了好幾拍的神經整個被牽動了起來。當下心裡迅速盤算了一回,決定先回彰化家,再往草屯南投一帶看看。
趕到草屯的那天,不巧她也回了嘉義去,就自己往草商去看看,親眼目睹斷層帶硬是將學校整個撕開,幾無一處完好,不同於電視畫面,看見那些曾經走過在心裡留下印記的景色,突然破碎成那樣,才發覺原來房子也是有臉孔的。當下,整顆心也跟著整個扭曲成一團。
待南投一帶災區管制稍微放鬆,我便背著相機跨上機車,從彰化進入台中大里、草屯、中興新村等地方進行記錄。那幾天我就這樣揹著攝影機四處來來去去。今天到這兒,明天又到那兒去,這樣像無頭蒼蠅一樣地,根本對災情談不上什麼幫助。
省府所在的中興新村幾乎成了一座廢城,加上抵達這裡的時候天色已晚,居首的辦公大樓整個被震垮,整個天地只剩入口大道的一株大樹有團亮光,三太子的神像被供奉在紅布桌上,民眾們大排長龍等著焚香、收驚。此時,一輛機車從外頭趕來,後座載著一名腿上纏著繃帶的中年男子,男人費了很大的勁從機車下來,一瘸一瘸地拄著柺杖奔赴神明前,開始焚香頂禮,大聲要神明寬恕他的罪過,保佑平安;後方挖土機咔咔作響,在黑夜中轉動手臂,清理著廢墟。居民們成群地聚集在草地上搭帳露宿,四周盡是門毀窗垮、燈火散走的景色,印象中方正乾淨的一座方城,此刻竟宛如鬼域一般。
劫後餘生慌張來回的螞蟻
我騎車跑到了中興新村,再進去,不久路也只剩下半截,除了幾顆示警的燈號,路燈不亮。前方一片黑暗,狀況不明,我也實在不知要到哪去,要在何處落腳,機車便轉了個彎,折返回家。
如此這般地折騰了幾天,發現騎機車往返實在不是好方法;不只體力消耗,甚至器材、交通都受限,對大局也幫助無多,索性就先回台北了。
在還未完全暢通、太陽一下山就死寂一片的道路上,相信來往顛簸的人車都不會忘記地震後首先復興的行業:檳榔西施。警示燈纏繞綿延之路上,大膽美艷的女郎與俗豔的霓虹燈比以往更為魔幻,在灰白與黑暗擠壓裂縫中,炫耀著生命力的頑強,絲毫無畏強震的猛烈。
強震沿及之處,大里、東勢、草屯、霧峰、中興新村、名間、中寮、魚池、集集、日月潭……,幾乎無一倖免。除了大街小巷散滿五顏六色避難的戶外帳篷之外,好像所有的怪手、工程車全部飛到台灣中部來了,震天軋響地滾著履帶,從這個鄉裡鑽進又從那個村裡竄出地一路挖著、掘個不停,彷彿要把這些殘破的鄉鎮縫起來似的。待天幕一暗,整個世界即刻又陷入缺水、斷電的死寂當中。實際災情遠遠超過了我的想像,隨著跋涉的範圍越來越廣,幫不上忙的無力感也越來越嚴重。
走了一大圈下來,發覺這樣蜻蜓點水、走馬看花,實在是一點幫助也沒,很多地方才剛見識到災情,還來不及深入、就又得繼續往前走。彷彿那大地碎塊一路撞擊過來,腦海裡一邊在崩塌……困惑、迷失、焦急,這或是所謂的倖存者的恐慌吧?
再回台北後,仍是整天盯著電視,注意報紙、廣播、網路上的消息,如何才能更有所為的焦慮反覆驅使著我,心想,加入個救災團隊作義工,若是片子沒做成,至少對當地還有直接幫助。才動了念頭,就發現東勢帳棚學園的消息,況且這條線與自己還多少有些淵源。一來,發起單位之一的「立報」是隸屬於母校世新;二來,團隊的負責人張正剛好是認識的朋友,於是就直接打了電話聯絡,看能否在每週末跟下去幫忙,順便作些記錄,張正一聽爽快地答應了。之後,每到週末就打包機器、簡便行囊,掛在他們的車一起南下,週日晚又跟著要回來上班的他們一北上。
就這樣,地震後一個月左右,我終於找到一個據點,可以專注投入。而這一陣子的整個動態才逐漸有了重心,趨於穩定;而那些模糊的災情與臉孔,也才開始變得清晰、具體起來。這時候,十萬火急的救人行動已經告一段落,拆屋、清理的工作已經馬不停蹄的進行著,空氣中飛滿了怪手挖掘而碎裂的大量塵粒,風一起,漫天塵沙飛舞,直撲眼鼻,有時打在臉上刺痛難當。一整天下來,頭髮、耳朵、鼻孔抹過都是一層沙。
雖然已經入冬,白天日頭仍大,一整天下來,汗水混著泥沙,在水電仍然不通,只能靠著臨時衛浴車來解決洗澡問題的日子,不能說沒有一點折騰,然而經歷過號稱40顆原子彈威力的921大震摧殘,能享用到這臨時提供應急的一點溫情,些微的磨難已經遠遠是一種幸福了。
也是在這裡,在前三十年從未履及的這個鄰近東勢小鎮,我開始重拾一種信心。那是在學校社團、工作經驗的勾心鬥角、算計耗損中一度所剩無幾的:團體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