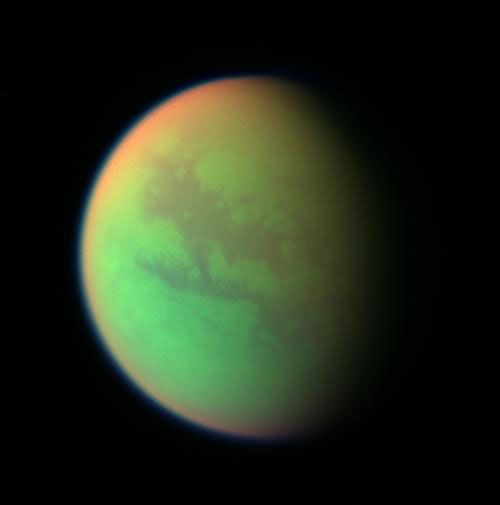流亡
今時今日我會覺得兒時盼望獲得的「任意門」是一種極其荒謬的發明。暫且不論實現的可能性,於旅行而言,累人的移動過程必不可少。這一過程同時造就了「距離」——是跨越西伯利亞的那段能夠被量化的距離,也是人類社會形塑出來的種種具體又抽象的提示人們有關距離的事物,例如邊境檢查。當我離開琿春,從那個破鐵棚邊檢站裡跨過俄羅斯邊境後,我需要把手錶調快2小時。這在地理上毫無道理可言,畢竟我離一個時間慢2小時的地區才十幾公里,但這無時無刻不在提示我:我在別處。此外,往窗口裡遞一本可機讀護照,讓正前方的攝影機記錄下自己的容貌,並聆聽官員往護照空白頁蓋章的聲音——這也是一個進入別處的嚴肅儀式。
抵達伊斯坦堡北郊的新機場,散漫的土耳其邊境官員不願多看訪客一眼,潦草地蓋著墨水快要完全乾掉的印章,上面標示的入境日期難以辨認。通過邊境檢查的走廊後便是機場到達區,走兩步就能看見外匯兌換店,上方的LED螢幕清晰地投放著幾個大紅字「WE ACCEPT RUB(我們接受盧布)」,提醒我腳下的這片土地是目前俄羅斯聯邦公民為數不多的能夠外游的目的地之一。我走向其中一個兌換店,準備把手裡的60歐羅兌換成土耳其里拉,並從排我前面的女孩所交易的貨幣中判斷出她來自烏茲別克斯坦。隨後我來到的士服務台,工作人員向我報價:「前往蘇丹艾哈邁德,最多不超過300里拉(15歐羅)。」上車後,車開到一半,的士司機向我要價70歐羅。由於擔心遭遇任何程度不友善的行為,我沒有太多心思還價。下車後便和住處的負責人穆斯塔法抱怨了這回事,穆斯塔法問我是否有記下車牌號,可以舉報。我說沒有。隨後在伊斯坦堡的數日,我沒有再乘坐過的士。
穆斯塔法身材高挑,留一頭飄逸的長髮。他領我來到住處的公共空間,類似於一個大的客廳,有電視、遊戲機、咖啡機和辦公桌等設施,客廳旁邊是廚房和洗衣房。他還給裡面的住客介紹了我。除了兩三個土耳其人,還有人來自墨西哥、英國、美國和俄羅斯。那位俄羅斯人是一位金髮男性,獨佔著一張辦公桌,上面放著他的電腦支架和耳機,似乎已經在那裡住了很久。
抵達的第二日早晨,我步行前往蘇丹艾哈邁德清真寺和附近的聖索菲亞大教堂。後者的訪客人數極多,隊伍在廣場上繞了數圈,我便將參觀的計劃推遲,繞到旁邊的居爾哈尼公園。公園裡沒幾個人,滿地落葉,只有國父凱末爾雕像附近的地面被掃得乾乾淨淨。我徑直穿過公園,來到海邊。黑色的礁石里藏著一些貓,有一隻躺在一位老婦身旁,她就坐在礁石上,隨後她的丈夫來到,坐在她旁邊。貓依然躺著,沒什麼動靜。我沿著海邊的小路一直往南走,直至一處斑馬線,有四個人朝我走來。
他們是一家四口。我以為他們要兜售什麼紀念品,便說「不用了謝謝」。隨後聽到那位父親說:「我們是敘利亞人。」母親把手放在胸口,直視我雙眼,說:「請幫幫我們。」兩個兒子分別舉著一塊用透明膠帶包裹的紙板,上面寫著「HELP US (幫幫我們)」,嘴裡也喊著相同的內容。我從包里掏出10塊錢里拉,說「很抱歉,我沒有帶很多錢。」他們連身道謝,分別用英語、土耳其語和阿拉伯語說了很多遍,並做著感激的手勢。當天晚上,我從一家餐廳出來,「請幫幫我們」的聲音再次傳入耳朵。那是一位與我母親差不多大的女性,她和她的女兒一同坐在超市旁邊的台階上。「請幫幫我們,我們從敘利亞來。我家在阿勒頗。」這位母親和早晨遇到的母親的措辭與動作基本一致。她隨後從口袋里掏出她的護照,向我展示皺巴巴的護照身份頁——能看出來上面寫的確實是「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我拿出10里拉,並說了同樣的話,加了一句「保重」,她也用不同的語言表達了類似的謝意。
不知是不是巧合,離開土耳其後,我在貝爾格勒的聖馬可教堂門口同樣捐出了一些小錢。下午一點,我從尼什乘巴士抵達貝爾格勒,在公寓下榻後便前往教堂,為一位染疫罹難的好友點蠟燭。我從塔馬登公園的北面繞進教堂,看見一對夫婦站在教堂門口,手裡拿著一些已經折疊得不像樣的白紙。那位父親抱著一個昏睡的男孩。走在我前面的是一位年輕男性,他固然是能聽懂夫婦所講的語言。年輕人得知那一家三口的遭遇後,面色憐憫,在胸前划了十字,親吻了教堂的門框,便走進了教堂內部。塞爾維亞是東正教國家,他划的無疑是東正教十字,與天主教十字有些許不同,前者的順序是上下右左,後者是上下左右。我走到門邊,無法理解夫婦的語言,也看不懂他們在我眼前展示的皺紙片,我只能大概理解成面前這位被父親抱著的昏睡的男孩遭遇了重病,而夫婦站在教堂門口是為了獲取一些治療費用。看著困惑的我,那位父親拉下男孩的一邊褲子,讓我看見他腹股溝處靠右的那個巨大腫瘤,嘴裡繼續嘟囔著我完全無法捕捉的詞彙。我從錢包里拿出20塞爾維亞第納爾——一個相比10土耳其里拉還要小很多倍的數目,說道:「抱歉,我沒有帶很多錢,保重。」父親依然在嘟囔個不停,也許是在抱怨我所給予的20第納爾太微薄,甚至是一種侮辱,也許是在表示最低限度的感謝,母親朝教堂外望去,期待能找到下一個幫助他們一家子的人。隨後,我走進教堂,花100第納爾買了五根蠟燭,走到門外,建築旁有許多由金屬包裹的蠟燭台。我學著其他禱告者一般親吻蠟燭,划東正教十字,並借他人留下的燭火,點燃了其中一根,插在了蠟燭台的水里,借助水底的碎石固定住。余下四根便借用這一根的燭火,但最後一根並沒有插穩,倒在了水里,燭火順勢熄滅。
在伊斯坦堡的一周,除了穆斯塔法外,我與住處公共空間的其他人沒有過多交流。某日晚飯後,我坐在沙發上處理照片時,那位金色頭髮的俄羅斯年輕男性問我是否需要咖啡,我欣然接受,並開始了交談:
「我待在這兒已經三個多月啦。」他說。
「這兒的生活跟俄羅斯相比如何呢?」我問。
「比我家還要便宜一點,但當然是更好玩了。」
「你是做什麼職業呢?」我喝了一口咖啡。
「程序員,你看我那些個裝備就明白了。」
「酷。那你為什麼選擇了伊斯坦堡呢?」
「哎,我的朋友,你知道的,我沒得選呀,所有人都沒得選。」他的那句「我的朋友」讓我立即想到之前在各地有過交流的斯拉夫人,是那種近乎一致的口音和用詞習慣。但這位年輕人的英語比他們要流利太多,讓我毫無障礙地明白他所指的正是黑海對岸的戰事。
「我很抱歉。那,你還打算待在這裡多久呢?」我的這個問題好像過於尖銳,他皺了皺眉,又微笑地看著我,回答道:「直到那個地方耗盡所有的正義,不過事實上人們已經正在耗盡正義了(Until all justice runs out over there, but in fact, people are already running out of justice)。」他把紙杯里的咖啡一飲而盡,回到桌子前,戴上耳機,投入工作。
在貝爾格勒,我為離世的朋友點了兩次蠟燭,第二次是在聖薩瓦大教堂。這次沒有遇到孩子患重病的夫婦,蠟燭也沒有因為景點的名氣較大而比聖馬可教堂里販售的要貴。我從教堂出來,穿過卡拉喬爾傑公園,來到四年前到訪貝爾格勒時寄明信片的那個郵局,打算再寄一些明信片。排在我前面的男人與窗口的工作人員進行著吃力的對話。我竪起耳朵聽了好幾分鐘,大概明白了對話雙方的情況。
塞爾維亞和土耳其一樣,依然是戰事在2022年初全面爆發後俄羅斯公民得以外游的目的地之一。男子是俄羅斯人,需要匯款到俄羅斯,但不懂塞爾維亞語,只好使用破碎的英語,以及俄語。窗口的女人,毫無疑問,母語是塞爾維亞語,也只會破碎的英語——至於俄語,生於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時代的她,借助塞爾維亞語和俄語同屬斯拉夫語族的詞源學(可大可小的)相似性,應該也能勉強交流。他們的對話似乎是沒有特別大的難度,但我確實難以將其稱之為「對話」。那更像是一個塞爾維亞語和俄語詞彙重合度的測試:工作人員向俄羅斯人介紹表格的某個地方該怎麼填,用比較完整的英語,俄羅斯人表示不懂,隨後用一些簡單的塞爾維亞語詞彙,俄羅斯人用俄語里的類似的詞彙重復和確認了一遍,工作人員表示同意/反對。要是碰到一些實在無法互通的內容,這位工作人員會問旁邊的另一位工作人員「某個某個詞的俄語怎樣說」,儘管她同事的半桶水俄語提供的幫助十分有限。雙方就如此交流了十分鐘,俄羅斯人總算弄懂了匯款流程,分別用英語、塞爾維亞語和俄語講了「謝謝」。那天早晨在伊斯坦堡的海邊,給了一家四口10里拉後,我繼續沿著海岸向前走,遇到了兩位俄羅斯年輕女性。她們讓我用手機為她們拍照,結束後也向我講了很多次俄語的「謝謝」(Спасибо)。
和住處里的金髮俄羅斯人交談後,我能想到的是納博科夫在接受BBC採訪時講到的話:「……俄國的一切始終伴隨著我……我永不返鄉,我永不投降。(… all the Russia I need is with me – always with me… I will never return; I will never surrender.)」
過年回家,我與很久沒見面的幺叔公見面——我媽的一個叔叔,排名第七,是家裡最小的,我外公則排名第二。我有兩個外公,第一個外公是我媽的父親,但在她五歲的時候去世;第二個外公是外婆再嫁的,生下了我媽的弟弟妹妹(舅舅和阿姨),但在我五歲的時候去世。幺叔公喝酒喝到興頭上,講起來我媽的父親:「我在你身上看見你外公的影子啊!你外公,就是我二哥,當年可是很聰明的!他讀的是縣里第一名的中學,還會拉那個琴,叫啥來著……哦,二胡!他要是能活到今天看見自己孫子這麼聰明肯定笑掉大牙!」隨後他便借著酒勁開始了對他二哥的一段隔空對話。我從沒有聽母親講過外公的事情,不過她自己也不會知道很多,只和我說過外公去世很早,原因是一些不治之症。所以那是我第一次從別人的嘴裡獲得關於我外公除了死亡之外的其他信息。
這學期有一門檔案學的課程,其中一個作業名字叫「赤柱拘留營的生與死」。教授要求學生基於現有的歷史檔案,而不能是任何二手文獻,重現一個發生在香港日佔時期的某一個/一些被拘留在赤柱的人的故事。
我重新開始思考「流亡」一詞的構造。「流」表示一個動作,亦即非自願的移動。但為何「流」的後面是「亡」,與「死亡」的「亡」又有何聯繫。我寫下旅途中遇到的「流」者:敘利亞人、俄羅斯人、被命運拋棄的人。也從他人那裡獲得了僅存的關於我至親和好友的「亡」者的信息。他們的背後存在著某種力,要麼是人為的暴力,要麼是自然的不可抗力。這種力是對可能性和自由的絞殺,在時間和荒謬的庇護下綿延不絕。這種力消滅了故鄉捆束他們的力,令他們不再有機會回歸。我僅能寫下與他們擦肩而過的瞬間、拍下的照片、給出的10塊錢、看到的腹股溝腫瘤、被描述出來的正在耗盡的正義、有勉強聯繫的塞爾維亞語和俄語……這些內容沒有重量——我無法像1943年的西蒙·韋伊(Simone Weil)一般絕食而死,她用全身的重量和庸常無盡的惡搏鬥。但我永不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