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记者林子人:格子里跳舞,山坡上推石|围炉·FDU


林子人是界面文化的记者,常被人问“文章写得很像论文了,为什么不去读博啊?”她答,读博为开辟新的知识领域,文化记者则为沟通学界与公众,二者处于知识生产与传播链条的不同环节,并无优劣之分。约访子人的那一天,她恰好发了微博,感慨被种种不可抗力捆绑的写作与她飘摇的理想主义火花。本次对话也在这种感慨的氛围中进行,只不过——格子里跳舞也得坚守阵地,推石上山已然是巨大意义。

林子人
“界面文化”记者,播客“鼓腹而游”主播,
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系硕士。
椰子
“界面文化”读者,“鼓腹而游”听众,
复旦大学大一学生。
1.画像
一个文化记者的日常
椰子 | 提起记者,我们想起的往往是抢着递话筒的娱乐记者和宛如神探的调查记者,而作为一个社科方向的文化记者,你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
林子人 | 从我自己的工作经历来说,文化记者的工作形式和其他记者没有本质区别,区别主要在日常工作层面。
工作形式上,我们也需要去采访,如果是群访的话也需要抢着递话筒;我们也需要去调查,如果是做大的深度稿件,需要去查阅非常多的资料,泡图书馆。
在日常工作层面,文化记者更像学者。我们和学界的接触很多,采访对象大部分是学者。我们希望能作为学院和大众的桥梁,把一些学界重要的最新研究用易懂的方式介绍给公众。所以我的日常生活跟在校大学生很像,需要花大量时间阅读,这可能也是和其他方向的记者不太一样的地方。
椰子 | 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最近一篇稿件的选题、构思和创作的过程吗?
林子人 | 我这个月写的最重要的一篇稿子是界面文化“重返90年代”系列报道,我这篇是“重返90年代之洋快餐”。肯德基、麦当劳这些国外的餐饮连锁品牌差不多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进入中国,可以说,它们在90年代的中国掀起了一股很大的风潮。和我们现在一窝蜂去网红餐厅打卡一样,当年肯德基、麦当劳也是那个时代的“网红餐厅”。所以如果我们回顾90年代的消费领域,洋快餐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我花了很长时间来构思和创作。这种大的稿子需要做很多采访,读很多当时的文献,我从着手做到写出来,大概花了四五个月(这个情况比较特殊,一般来说不会花那么长时间去操作稿件)。这个系列其实是我们日常工作之余抽出时间来做的。我们平时还是得紧跟时事热点(毕竟,作为新媒体,需要保证每天更新),所以实际上很难抽出一大块的空余时间来做同一个比较静态的选题。我是每个月挤出一点时间来做这个题的,这个月终于把它写完了,特别开心。
椰子 | 界面文化的读者画像如何?编辑部会鼓励记者“破圈层”吗?
林子人 | 从公众号后台数据来看,我们的读者数约26万,男女比例4:6,大多数是在一线城市,年龄层我推测是20~30岁,所以读者画像是偏一线城市的年轻女性。我觉得这与界面文化比较关注性别议题有关,从平时我们稿件的点击量也可以看出,点击量最好的稿件,一大半都是性别议题。
至于破圈层的问题,我们当然想要让稿件触及更多人,但是现在发现我们读者的增长比最早几年慢很多,现在读者数量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
怎么说呢,对于破圈,一方面我肯定会希望我们能像《新京报·书评周刊》等媒体一样,有更丰富的、更大的读者背景。但是另一方面又觉得,在同温层里面呆着也不错,毕竟现在破圈已经变成了一件有些风险的事。
去年我们发年终盘点系列文章,其中一篇是性别新闻盘点。那篇的反响一方面很好,点击量非常高,也是我们的读者每年最期待的稿件之一;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后台有非常多骂人的评论,突然有很多以前可能根本不看界面文化的男性读者跳出来说,我要举报你们。这种时候就觉得不破圈也可以。
我记得随机波动的朋友们也说,她们并不追求破圈,能在一个圈子里影响志同道合的人其实就足够了。我现在也是这样的想法,希望能潜移默化地影响更多人,但是也不强求破圈。

2.思考
言论空间、教化与传播
椰子 | 目前言论环境日趋逼仄,记者往往也只能在逼仄的空间书写。你会怎样面对这样的空间?
林子人 | 只能接受现实,keep calm and carry on。因为你确实在做你觉得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你确实也在戴着镣铐跳舞。在一个格子里面跳得更好看,这可能是现在所有人都在尝试做的事情。如果你不做,就相当于放弃了这个舆论阵地。能放弃吗?不能。
椰子 | 逼仄空间不只体现在选题的范围,也体现在写作的深度(黄月曾表述为“地雷上种花花”)。为避免地雷炸开,许多记者都会采用春秋笔法、挪用等方式,用他国的、历史的、虚构的事例和书籍来指代这片土地的当下。你曾面对过这样的情况吗?你对这样的写作方式有何感想?又会如何处理这种地雷困局呢?
林子人 | 不能直接写的就想办法绕过去,用其他的方式写——我们所有记者都会面临这种情况。疫情的时候,我写过一篇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稿子,其实也是在回应当时网络上一种“我们可以放弃那些对社会没有用的人”的心态。
我写的时候,其实在导语里明确地点出了这种心态,但是最后上线的版本就是把疫情的背景全部去掉,变成一个单纯的历史稿件。这就是强加的现实,你得去接受。但是我当然觉得这不合理,甚至对个体从业者和对整个行业来说都是一种伤害。
对于个体从业者,我觉得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我自己都已经因为自我阉割到了一定程度,没有办法很直白地表达很多事情了。我感觉这两年我可能在慢慢地丧失这种能力,或是勇气,我不知道这是到底是一种能力还是一种勇气。而对于整个行业,肯定是达不到最初想要达到的效果。更让人绝望的是,整体环境如此,以致很多读者也并不觉得他们需要读到最真实或最有批判力的观点。

椰子 | 除了言论空间的局限,反复面对旧的问题也会使人疲惫。我注意到界面文化每年都会做几类议题的年终盘点,有些问题因为一再出现所以一再被提及,比如反家暴。当反复书写、言说相似的话语时,你会有什么感受?又会如何处理这些感受?
林子人 | 最明显的例子确实是性别相关的话题,每年反复地出现。我前两天还在跟之琪(随机波动的主播)聊天,她也有这个感觉。很多时候话题根本没变,只不过是事件的由头变了,比如前年是蒋劲夫家暴,可能去年就变成拉姆被家暴,事件的当事人变了,但是事件的本质就是那样,于是你就需要反复不停的说同一件事,同一个话题。
我一方面当然会觉得,就像推石头一样,周而复始,车轱辘话来回说;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世界就是这样子的,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你要接受这个现实。
我去年三八节的时候采访了冯媛老师,她算是国内最早的女权活动家,从90年代到现在都活跃在一线。我当时也向她表达过类似的沮丧,觉得我们做了那么多事情,社会也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她的回答让我非常感动。她说,把时间段拉长,其实变化已经非常多了。比如,90年代的时候,根本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家庭暴力;现在至少对家暴有一个共识,至少我们已经推出了反家暴法,让反家暴在法律层面上有法可依,并且在舆论层面,我们也已经形成了这种力量,知道家暴是不对的,只不过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公权力介入的程度和方式。
所以你把时间段拉长,变化还是出现了。而且,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至少我有感受到这几年性别议题的声量在变大,越来越多的女性和男性意识到这是个很重要的话题,是需要认真去讨论或是争辩的话题。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作是不是也在其中发挥了一点小小的作用?如果有的话,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意义了。
所以,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就算不断地重复议题,我觉得也没关系。一步一步走就好了。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Take the baby steps and one step at a time,对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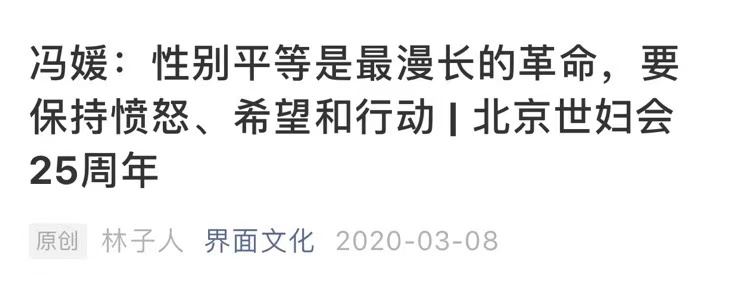
椰子 | 你曾说,“文化媒体的抱负应当是鼓励更多人过智性的生活”。你觉得文化记者是用“教育者”的身份来引导公众吗?你在写作时是如何看待自己与读者的关系的?
林子人 | 我觉得现在的知识分子应该没几个会有勇气说,自己在教育别人,因为公众会觉得“你凭什么教育我”。所以我不觉得自己是教育者的角色,这样太自负了。因为我了解的东西也并不多,我也在不断学习。
我现在会觉得,我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是同学或朋友,然后我希望和ta分享我新学到的一些东西、新发现的好玩的事情。如果这个事情让ta觉得有意思,能够启发一点ta的思考,或者ta愿意给我留言,跟我讨论这个事情,我就会非常开心。看到留言可以说我最有成就感的时刻了,因为我知道有人认真看了这篇文章,并且去思考,并且愿意跟我分享ta的观点。
椰子 | 我觉得我下面这个问题的问法可能并不妥当,我本来想问的是,你如何平衡“教化作用”和“传播效果”。
林子人 | 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你其实想问,我们文化频道的稿件,是更重视学术和观点,还是要想办法让这些比较硬核的话题更加平易近人。
界面文化成立之初,我们就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编辑部会非常信任记者,会让每个记者比较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每个记者擅长的领域和关注的话题都有所不同,比如说潘文婕老师的兴趣是古典音乐,所以你看到的音乐报道基本是她写的。但是除此以外,我们还是需要去追随热点。所以我们每个月可能有一部分的时间去做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另外一部分时间,就要去做一些就更跟社会热点相关的话题,这两部分稿件可以达到一个平衡。

椰子 | 你曾说,从读大学到现在,自己对世界所有的好奇心的出发点就是一个:作为一名当代中国人意味着什么。你现在对这个问题有答案吗?想法有过转变吗?文化记者的工作经验对于这个问题有何启发?
林子人 | 坦率地说,我还没有答案。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时代变化非常快,无论是国家内部环境还是外部环境,都变化非常快。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在我刚硕士毕业的时候,我是万万想不到,五六年以后,中美关系就会差到这个程度,并且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观感会发生如此截然、如此重大的变化。所以,作为一名当代中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话题是在动态发展的。
想法转变过吗?没有。我依然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觉得它不仅事关作为个体的中国人,因为如何在这个时代安身立命一直是根本性的一个问题;也事关整个国家要如何在世界舞台上呈现和言说自己,无论是现在谈得非常多的“文化输出”,还是“大国崛起”,你要怎样去向外界呈现真实的中国。如果想要从国际竞争中胜出,你能不能提出一套替代性的方案,让别人觉得你是有吸引力的,愿意追随你?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现在还没有想清楚,我觉得现在中国更多的是一个 economic power,是时候得去想其他层面了。所以无论是个体还是国家层面,这个问题都还蛮重要的。
文化记者的工作经验让我能近距离地了解现在主流社会的欲望和焦虑,我觉得这对理解这个问题挺有启发的。
3.寻找“少数派”的“同温层”
椰子 | 在此前的采访中,你曾说,改变立场不同的人是很难的,文化记者的目标是告诉那些和你们思想相似的人,你不是唯一的,你不孤独。我当时看到这句话觉得特别感动(我也算是被你宽慰的“你不孤独”的人之一),但回到现实生活,我又会有一种撕裂的感觉。 比如,我总是会在线上呼吁反家暴,无数次说反家暴机制是如何缺失,无数次说应当如何援助受害者,但当身边真的有亲戚被家暴时,我提出的解决方案往往会被长辈说“小孩子别管这事”——我还是很唯一很孤独。你会有这种撕裂的感觉吗?又会如何处理呢?
林子人 | 怎么说呢?我觉得支撑着我的其实是我的同事、朋友和伴侣。我会觉得撕裂的感觉并不重要。因为我知道坚持一些理念,就是会孤独的。不要说是在家庭的小社会,就算在大社会你也是少数。如果不能接受这一点的话,为什么还要做这件事?所以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
椰子 | 我是理智上能够接受“我是少数”,但是情感上还是难免觉得“为什么会这样”。不过你一开始说支撑是你的同事、朋友和伴侣,可能对于“少数人”来说,重要的还是保存体力,多在同温层抱团取暖。
林子人 | 是的。其实这些年我也通过工作认识了更多想法相似的人,无论是其他文化记者,或者是其他在媒体圈做类似事情的人,又或是我的读者,这些人给了我很多力量和鼓舞。同温层抱团取暖的意义大概就在于此。
椰子 | 你父母会看你的文化报道吗?他们会怎么说?
林子人 | 他们当然会看,他们还会听我的播客。我觉得我爸妈会看我的报道,完全因为这是我写的。他们会觉得,这是我女儿的成绩,或者是一个小小的成就,我需要去鼓励她。所以我爸和我妈都会非常积极地转发。但是他们没有跟我讨论过我的稿子,我其实也不知道我写的这些话题对他们有产生什么认知上的影响。现在越来越明白上一辈对世界的认知肯定和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不同,所以实际上我也并不太会主动和他们讨论我自己的工作。
4.另一种身份:
播客主播
椰子 | 你不仅是文化记者,也是“鼓腹而游”的主播,我很好奇你对这两个角色的应对方式,比如你做报道和做播客在准备工作、表达方式等方面的不同之处。
林子人 | 其实和鼓腹而游的另外两位主播相比,我接触播客的时间最短,所以我还处于慢慢习惯的过程中。目前鼓腹而游还没有外邀嘉宾,基本上就只是我们三个主播之间的聊天。最早也是程衍樑(我和筱狸的前同事)提出来,以前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经常凑在办公室里闲聊,程衍樑说其实我们聊天的氛围很好,可以一起做一个类似锵锵三人行的闲谈节目。所以鼓腹而游的定位,就更加像三个文化记者之间的闲谈,同时是有质量的闲谈,能够让更多人产生共鸣的闲谈,能够对社会现实问题进行讨论和反思的闲谈。
我们的准备工作其实跟做记者没有太大区别。也是先定一个选题,然后我们三个开一个石墨文档,把大概要讨论的话题的方向和内容放进去。见面的时候,可能会循着提纲往下谈,也可能就发散出去了。
至于我个人的准备工作,我会读一些与话题相关的东西,用来充实我的谈话内容。很多话题实际上是从我和筱狸老师写过的稿件里延伸出来的,比如说这个题目我写过了,但我想再延伸一下,我希望能在朋友们的聊天中再看看有没有其他思考的角度,所以播客对我来说也是平时工作的一种补充。在这个点上,我觉得做播客还挺有意思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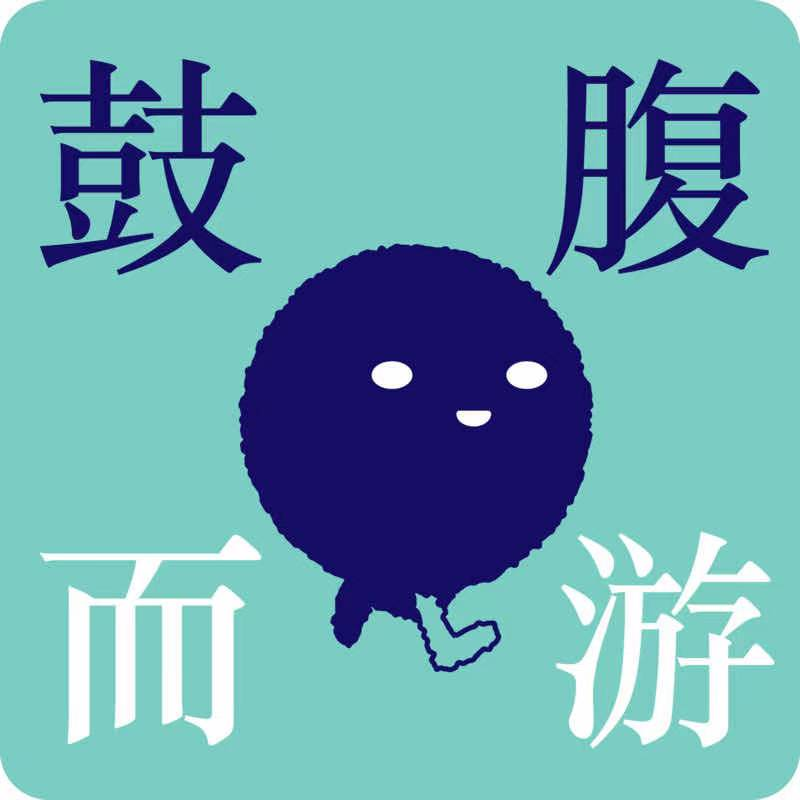
椰子 | 你在之前的采访里说,在写稿之前你会把所有可能用到的书搬出来,把曾经划线标注过的段落在笔记本上再誊写一遍,并思考如何运用。你准备录播客的时候也会这样军备竞赛吗?
林子人 | 尽管我很不想让另外两位主播知道,但是我会这样准备的。在公共演讲方面我是个很害羞的人,我一直觉得我的口头表达能力并不如我的写作能力。所以刚才我也说我在慢慢习惯做播客,我现在可能还没有习惯到每次去录播客能够达到100%放松的状态。所以录之前我会比较认真地做准备,我不知道另外两位主播是怎么样的。虽然这个节目的定位是闲谈,但是我自己在前期准备的时候,肯定不是把它当成纯粹的聊天。
5.给未来的文化记者
椰子 | 在鼓腹而游中,你曾提到自己的“功利性阅读”——平常大多只读工作需要的社科类书籍,读小说便会有愧疚感。这让我想起中学(和大学)的“必读书目”,我现在读和专业无关的书籍时也会有愧疚感,觉得输入效率太低。你目前有找到面对你的“功利性阅读”和愧疚感的疏导渠道吗?
林子人 | 我今年开始有意识地多阅读小说,在暂时不用工作的时候,我前段时间读的基本都是长篇。我觉得多读一读那种乍看之下跟你工作不相关的书,一方面会很愉悦,因为读小说本来就是很愉悦的事情,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它会以很意想不到的方式滋养你,比如对文字的感觉,比如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上的敏感度。读太多社科书的弊端在于,你总是想就事论事,总是想很理性地去分析事情,但是会跳过很多美丽但无用的生活瞬间,而这部分文学可以滋养你的,比如说能不能欣赏一次很美丽的日落,能不能欣赏一朵落花。
我给现在的大学生最大的建议就是,想尽办法多读书,因为你会发现工作以后,你再也没有这么多时间可以自由阅读了(除非你是做文化记者,然而文化记者也没法保证有很多自由阅读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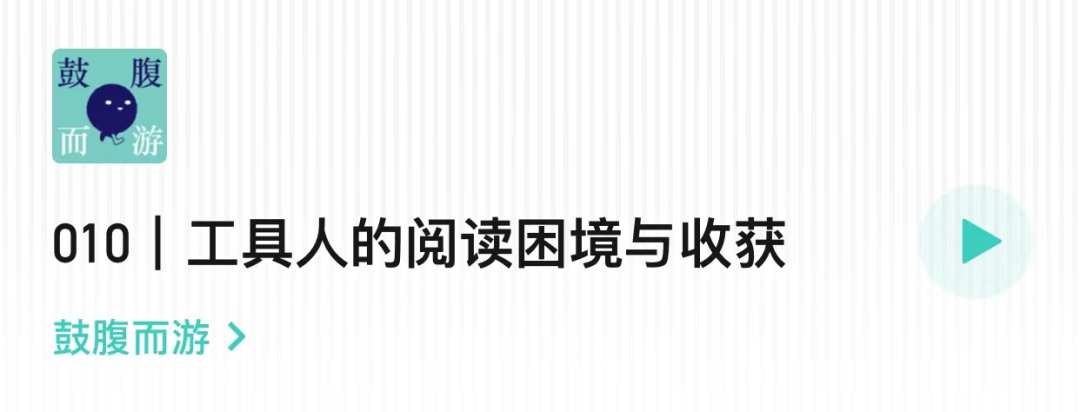
椰子 | 有什么想对未来有志从事文化记者的同学说的吗?
林子人 | 保证一定的阅读量肯定是基本。我们招实习生也很看重阅读,你平时读什么书,关注什么话题之类的。
然后肯定是要锻炼你的写作能力。很多来我们这里实习的同学,履历很漂亮,很好的大学,与文化报道相关的专业,但是他们会出现很难成长为成熟文化记者的情况。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ta们的思维方式难以转换。具体来说,有些同学实习之初,还是在用学术论文的思维模式来报选题和写作。
虽然我刚才说文化记者的工作方式挺像学者,但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还是希望能让我们的文章更 accessible,能够更平易近人,能够被大众接受。所以我们肯定要考虑选题社会意义,以及它能不能吸引读者。但是这一点是学者很少需要考虑的,学者考虑的首要问题就是研究课题新不新,能否开辟更多的学术领域,它的读者可能就是研究相关领域的几个人而已。但是这个思路在文化报道里肯定是行不通的。有一部分同学就是思维比较难转换,然后就发现不大适合做文化报道。
当然同样重要的是好奇心。你对世界有没有好奇心,你对某一社会现象有没有执着,想不想搞明白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觉得这种驱动力还蛮重要的。
椰子 | 那像你们这种比较成熟的文化记者,是如何锻炼出找到公共性话题的能力的?
林子人 | 不断报题,不断地写,一点一点积累。然后我们可能都需要经常在网上看看,看看那些话题有没有做文化分析的可能性。
椰子 | 最后,可以推荐几篇你自己的报道吗?
林子人 | 《不再沉默的女性 | 2020年性别新闻盘点》和《从teamLab上海新馆开幕谈起:我们该如何理解“网红展”?》。

统稿 | 椰子
审稿|Christina
图 | 来自网络
微信编辑 | 李卓颖
matters编辑 | 蔡佳月
围炉 (ID:weilu_flame)

文中图片未经同意,请勿用作其他用途
欢迎您在文章下方评论,与围炉团队和其他读者交流讨论
欲了解围炉、阅读更多文章,请关注本公众号并在公众号页面点击相应菜单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