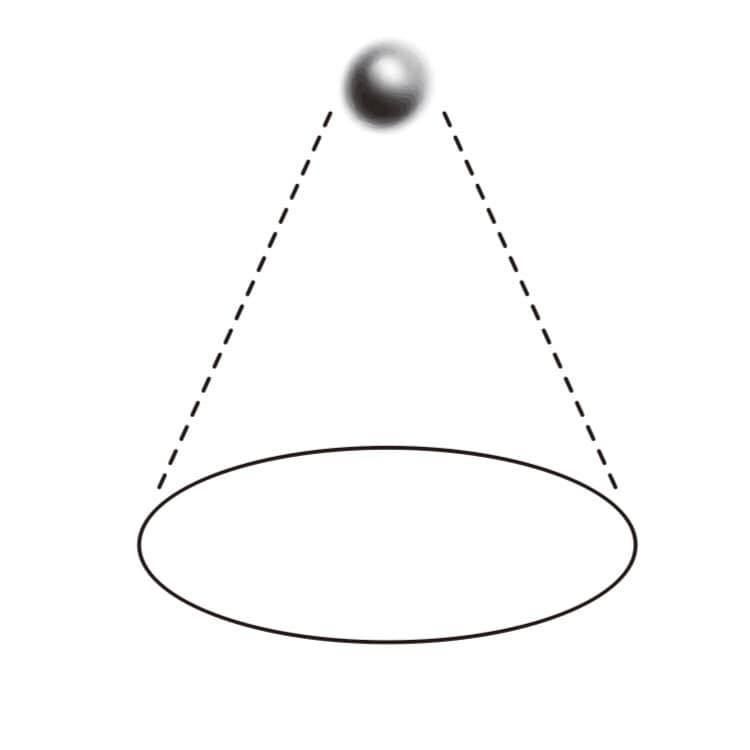【講座側記】吳晟 X 張潔平:向世界去,回鄉土來:以文學耕種年輕的台灣
原文發佈於2022年9月4日,首發於端傳媒《吳晟 X 張潔平:向世界去,回鄉土來:以文學耕種年輕的台灣》。

【編者按】文學紀錄片「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推出最新一集,記錄台灣重要詩人吳晟的《他還年輕》。8月6日,吳晟與飛地書店創辦人張潔平進行了一次對談,講座題為「向世界去,回鄉土來:以文學耕種這年輕的台灣」。以下是對話記錄。 【講座整理】端傳媒實習記者 鄭又禎
張潔平(下稱「張」):今天非常榮幸,有機會在這邊聽吳晟老師做一次親密分享。我本身是一個文學愛好者,也非常開心吳晟老師給我簽書時寫「年輕的文學朋友潔平」,但作為一名文學愛好者,我的成長經歷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在香港,台灣的鄉土文學都是沒有辦法被看到的,我幾乎是到台灣之後才開始讀吳晟老師的作品。
在台灣以外看到的台灣文學,基本上都是現代文學,例如白先勇等,鄉土文學我剛開始認識,但印象很深。去年還是前年我第一次去吳晟老師的書房,他拉著我跟我說他跟中國作家艾青的交往,我當時就覺得這兩個世界怎麼就這樣交會了,讓我意識到其實「鄉土」這件事是穿越國界的。鄉土本身作為一種文學的態度或立場,並不是真的被綁定在國界之內,那次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所以這次我之前就跟吳晟老師聊到說希望能聽他講多一點當年他跟艾青的交往,以及那個時空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吳晟老師在零星文章也提過他在1980年愛荷華作家工作坊的經歷,我當時印象最深的是在那之後你就有38年再也沒有離開過台灣,而且據說是拒絕出國,任何邀請都不去,一直到2018、19年,應該是為了拍攝這部紀錄片才重新再一次踏出國門,也就是1980年是他最後一次在未來的四十年之前離開台灣。到底是什麼樣的衝擊,當時發生了什麼?
1979年對台灣來說至少發生了兩件大事:一個是中華民國跟美國斷交,還有一個是美麗島事件爆發。而1980年工作坊華人世界的入選名單,台灣是吳晟,他應該是斷交之後第一位訪美的作家;中國是艾青跟王蒙,也是很有意思的組合,因為王蒙當時是比較官方的代表,艾青曾經是中國很重要的詩人,但1949年之後被國家流放差不多20年,從新疆到小西伯利亞,非常類似於今天的寧古塔,受了很多年政治折磨;香港的作家是李怡,他現在也在台北。我當時看到那名單就覺得哇,1980年這些人坐在一起到底是什麼狀況。
吳晟老師在自己的文章也簡略寫到過那幾個月對他人生觀、文學觀和世界觀的衝擊。他說,在那裡對中國真相的認識與對台灣真相的認識讓他非常震撼,因此當我們有機會今天來這裡分享時,就一直抓著吳晟老師說能不能講講這一段,那好像是為什麼鄉土這個立場這麼清晰的一個重要時間點。今天時隔四十多年回看這個1980年的作家工作坊,對您的影響是什麼?我非常不好意思給吳晟老師定了一個題,吳晟老師很勉強地答應了。所以我們今天也許是從1980年的愛荷華開始。
1980:生命與思想的衝擊與轉折
吳晟(下稱「吳」):當初潔平到我們家一開始就聊得很愉快,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妹妹是香港媳婦,我1980年從美國回來時,唯一去過的地方就是香港,在那裡住了一個禮拜,所以對香港算是有一定的情感。我們那天談到可不可以來談談1980年對我生命與思想的衝擊和轉折,1980年到底是什麼狀況,我要先從這裏開始談起。
那時台灣剛剛跟美國斷交,台灣(中華民國)從1971年退出聯合國,其實台灣的外交部等於斷交部,世界各國一直跟台灣斷交。但我們這邊一直都講「中美斷交」,這個語詞控制了台灣很多年,甚至到現在有時不留意還是會講出「中美斷交」,其實是中美「建交」,然後台美斷交,應該是這樣才對。可是當時他們發明了「中美斷交」這個詞,結果整個台灣社會跟媒體一直沿用這個詞,由此可見我們台灣人、台灣社會是一直被很多不好、不對的語詞所控制;依照一種比較所謂左派的語詞,叫做「宰制」。
在這樣的背景下,國際作家工作坊由美國國務院委託愛荷華大學主辦,由詩人保羅.安格爾先生(Paul Engle)跟台灣的重要作家聶華苓女士主持,每年都會有一期,工作坊讓世界各國的作家聚在一起,我們大部分都住在一個叫做「五月花」的公寓,那個五月花不是台灣的五月花,台灣的五月花是不同的意思,美國的五月花是跟他們的建國史有關。

1978年年底美國跟台灣(中華民國)斷交之後,其實這個工作坊就沒有台灣的名額了,因為台灣跟美國已經斷交了,又被認為「不是國家」,這個名額就給了中國,中國在1978年之前也沒有名額,一直都是台灣的代表去參加。《他們在島嶼寫作》這個紀錄片系列拍攝過的作家幾乎大部分都去過,余光中、鄭愁予、白先勇、楊牧、王文興⋯⋯幾乎都去過。1979年那時他們還是有邀請,可是被邀請的人不能去,那個人是王拓,他那時已經不能出去了。
1980年工作坊就來邀請我,可是他們很緊張,因為也怕我不能出去,所以就透過非正式管道偷偷寄來。收到信大概是在三月,我一看發現寄件人是「鄭文韜」,就是鄭愁予。我想說他怎麼會寄信給我,我跟他沒有來往啊,一看才知道是愛荷華那邊寄來的。而為什麼要透過他寄給我,因為「鄭文韜」的信件大致上不會被檢查,可是如果你用「愛荷華國際作家工作坊」(就可能被審查),那時候因為台灣政府覺得他們跟中國比較友善。這個很少人知道,我也沒有講過。今天我說的這些其實是我要寫的,但目前還沒寫出來,各位可能是第一個聽到的。
收到信當時我就趕快跟我的老師瘂弦講,瘂弦老師就一直提醒不可以講,絕對不可以講,要人到愛荷華以後才可以講,而且在辦的過程都不可以透露,很可能會因此生變,這個是有前例的。我那時在學校(做老師)帶升學班,需要很專注,要等到學生考完試才有時間去辦出國手續,七月學生一考完(我 )就馬上去辦,沒想到每一關都非常麻煩,但我算很幸運,每一關都有貴人相助,最後一關就是教育部文教處。
我在那邊辦了很久,受盡冷眼,因為「沒有這個條文」。只有大學教授文化交流考察,沒有中學老師什麼文化交流考察,而且辦這個的人說「什麼?生物老師?這個人家是要『國際作家』欸?什麼東西,不行不行。」這種很多我都是自己笑一笑,在他們的認知裡面,整個教育部的條文裡沒有中學老師文化交流的,而且生物老師怎麼會寫作?還有一個問題是每一關都有安全資料。那時的教育部體育司司長剛好是我中學時的體育老師,我遇到他有跟他提到我正在辦出國,他說有困難就去跟他講,我就想說應該是不用,這個是正規的事情,而且還有邀請函。結果沒想到我真的沒辦法了,就去找老師幫我跟他們講。講了以後那個主辦問我:「你跟體育司司長是什麼關係?他從來不關說的喔,他為什麼會替你出面?」我說我是他的學生,而且他知道我沒什麼問題。
可是還是不行。我們老師去查以後才知道,原來我的安全資料「有顧慮」。台灣以前所有機關都有「人二」,就是人事室第二處,第二處是管思想控制的。他們都會做資料,他去查我的資料結果是「思想偏激」,安全有顧慮,所以不准。
辦了很久還是不行,就快來不及了,九月初就開始了。結果冥冥之中真的有貴人相助,我一生真的都很好命,怎麼說呢?我本來想說算了沒出國也無所謂,我這種「鄉土作家」也不一定要出去。其中還有一些談話,我在這邊透露一下應該沒關係,事隔四十年,現在講也沒關係啦。那個主辦人說是我不應該,「你一個生物老師怎麼去參加這個什麼國際作家,你算嗎?」我就跟他說這個工作坊台灣很有名的作家都去過,例如白先勇,他就說「啊?你怎麼能跟人家比?」這個是我當時印象很深的一句話。我當然不能跟他比,他也不能跟我比,我們不能相比的,可是那時候他那種口氣,我實在是很受刺激,但這個無所謂啦,因為當時時代就是這樣,其實到現在很多時候也還是這樣。
我就不要了。也不是我不要了,是沒辦法。結果很巧,我要離開教育部、走下樓梯的時候迎面走來一個朋友,他要上樓梯,我要下樓梯。他一看,說:「欸,吳晟!」我說:「欸,懷民!」林懷民。林懷民他很早就去過愛荷華,不過後來,應該是說因為他去了愛荷華,他才轉而跳舞,他的契機也是在這裡,他如果沒有去愛荷華,應該也不一定會跳舞。他問我說「辦好了嗎?」他也知道我要去,有幾個人雖然不能講是誰,但台灣很小,私底下都會傳,他跟瘂弦老師也很好,所以他知道我要去。我就跟他說「無啊,伊著毋予我過啊。」(沒有啊,他就不給我過啊。)「哪會使毋予你過?行,我𤆬你來。」(怎麼可以不讓你過?走,我帶你上去。)他就帶著我進去找處長。
他跟處長說:「你自己看著辦,這國際新聞啊,你不讓吳晟出國,愛荷華國際作家工作坊他們會發布新聞,『台灣作家因為思想控制不能出國』,你們台灣政府⋯⋯這樣下去你們自己負責。」處長嚇死了,他說有這麼嚴重嗎?「有沒有嚴重,你試試看嘛。」他們也沒想到像我這麼土裡土氣的人也會被邀請,你想想看四十年前我是鄉下老師,一天到晚還在種田的那種樣子,在他們眼中哪裏有像作家?哪裡有像在他們心目中「詩人」的印象?他們說我不能跟白先勇比,不能跟誰誰誰比,那當然不能比啊。這個我絕對不是酸,不要誤會,開開玩笑,因為我很坦蕩的,而且都是好朋友。你想想看,鄭愁予老師還跟我這麼有緣,你知道他每次來台灣去我家最想要找的人是誰嗎?不是我,是吳音寧。
這邊延伸出去講一點。我有一首詩叫〈過客〉,大意是在質問人們到了哪裡才是歸人,才不再是過客?結果我的一個好朋友,教戲劇的汪其楣教授他非常喜歡這首詩,在1987年時把這首詩改編成戲劇來表演。演員在朗誦這首詩時,我就聽到後面說「愁予愁予,台上在念你的詩欸」,我轉頭一看,鄭愁予就坐在我後面,姚一葦教授就坐在鄭愁予旁邊。愁予就有點不好意思地說:「這不是我的詩,這首是吳晟的啦。」
結束以後鄭愁予老師就約我們出去喝酒,當時吳音寧有陪我去,吳音寧那個時候初三(國中三年級),因為功課不錯,我判斷他彰化女中一定考得上,所以沒關係,就陪我來台北。我們就一去喝酒就喝那種生啤酒,很大一杯,吳音寧跟鄭愁予就乾杯,鄭愁予對這件事情印象非常好,所以後來來我們家都會問吳音寧在不在。這算是一個插曲啦,可以知道我們交情都非常好。
愛荷華的三個衝擊
吳:總之,後來就出國了。我稍微慢了幾天到,但還算是剛開始不久,所以去到當地隔天,聶華苓老師就辦了一個簡單的茶會歡迎我。那個時候艾青跟王蒙他們都已經到了,我就到聶華苓老師家,那個場景其實是很自然,艾青那時已經七十多歲,比我現在少一點,他站在樓梯口,我從樓梯上去,看著這個前輩詩人,而且是中國五四以後非常重要的詩人,他地位非常高。有些年輕朋友不知道有沒有聽過「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就是毛澤東1942年發表的延安文藝講話,那次據說就是艾青起草的,所以他跟毛澤東的關係是很密切的。他在樓梯上遠遠地就把手伸出來,我很激動,看到一個前輩、一個這麼重要的詩人手伸出來,我一上去就擁抱他、向他鞠躬。
可是沒想到,就有人在那邊拍照。我也沒注意,然後隔了幾天,當時美國的一個報紙,當然是華文報紙,用半版的篇幅刊登我和艾青擁抱的那張照片,標題叫做「台灣年輕詩人吳晟嚮往祖國」,我嚇死了。我還要回去欸。後來才知道原來是一個叫「新華社」的報紙發的,這個我印象非常深刻,很怕,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怕了,「毋驚我死呢謼。」(不怕我死欸。)
但他有沒有報導錯誤?沒有錯,坦白說。我真的嚮往祖國。在台灣有擁護或依附國民黨的國民黨派,而反國民黨的叫做「黨外」。1980年之前,或應該說美麗島事件之前的黨外其實有分成兩種:一種是比較左傾、帶有社會主義思想的,另外一個是美麗島系統這種的,所謂本土的黨外運動,黨外民主運動當然聲勢就比較龐大,但就比較沒有這種社會主義思想。

那我是屬於哪一種?基本上,我那時跟台灣的黨外運動是在一起的,但我的思想根源是社會主義思想的這種「左統」,坦白說也是真的嚮往社會主義祖國。因為共產黨革命後我們看到很多傳單,那些傳單我都會偷偷搜集起來,學生時代我們都會偷偷念「紅皮書」毛語錄,我們那時有幾個朋友非常熱衷於這件事,但那個時候很危險,被抓到不得了,一定關。
我有朋友真的被抓,他後來教我如果被抓,就「坐禪」就好。因為對方一定會有兩種人來跟你談,第一種是拍桌子罵你的那種,第二種是會跟你好聲好氣說「哎呀不用這樣子嘛,何必呢?我們不會對你怎樣啦,你就坦白說嘛。」這兩種來你都不要理他,也不要說我不知道,什麼都不要講,坐禪就好。我那個朋友就這樣磨了三天,對方沒辦法,就放人了,當然也是比較好運啦。那個朋友非常地信仰左派,台北這邊也有一群左派信仰很強烈的,像最近佩洛西(Nancy Pelosi)來台灣,有幾位去現場衝撞的也是我以前的老朋友。
但我這樣的「信仰」在愛荷華,受到了三個非常大的衝擊。第一個,我開始閱讀很多我們在台灣看不到的東西,當中也包括李怡的《七十年代》雜誌,那本雜誌也報導很多例如美麗島、天安門,還有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所以我又接著看更多文化大革命的報導。你們可能想像不到,而且很多人會覺得我太誇張,但我要很實在地說我這個家國情感很強烈的人,在那邊幾乎每晚都在哭。如果看了文化大革命的報導,你不哭,那真的是難以想像,那個之慘無人道簡直是把人性的惡推到最高極致。像我們台灣這些「小奸小惡」、「小打小鬧」,跟文化大革命相比真的是差太多了,文化大革命那種鬥爭的殘酷是難以想像的。今天在這邊我沒有辦法講太多故事,但每一個故事我讀到都哭得不停,比如說魏京生自傳,那本讀了你如果不哭,我真的佩服你。那段時間我讀了很多文化大革命的故事,很真實,也殘酷到不行。
第二是艾青先生他很坦率地跟我講文化大革命時他的經歷。他很實在地跟我講,我問他當年被整肅是什麼情況,他說他被下放到新疆去掃公共廁所,一個在我心目中認定是中國第一的大詩人,被下放去掃公共廁所。他還提到上面的人有時會來檢查,檢查到廁所有蒼蠅就打,他回了句「你們家沒有蒼蠅嗎?」就被打得更兇了。他說這些其實他都還好,自己很強壯,被打沒問題的;此外他背後有將軍在罩他,艾青也等於是毛澤東的文膽,這樣的一個大詩人都被整肅到這種程度。
台灣很多人在講1989年天安門事件,但其實和文化大革命期間、1976年的四五天安門事件相比,那已經算是沒有那麼嚴重的了。四五天安門事件當時國際新聞媒體都還沒辦法進去,消息整個是被封鎖的,而依照艾青跟我敘述的,我聽了真的是恐懼到極點,我就不轉述了。我其實有問他知不知道那時是誰陷害他,他說他知道,他也有跟我說是誰,當時就是一個陷害來陷害去的情況。
第三個就是我的助理。因為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1978年中國開放,開始慢慢會有留學生和一有些交流,我的助理就是紅衛兵第一批到美國留學讀研究所的。他每次來找我都從遠處就大喊「共匪來了!」他知道我們這邊都稱他們為共匪。我們就還滿好的,他自己就是紅衛兵,他講了很多那種我沒有辦法轉述的故事,因為講了真的會哭,那是人間煉獄一般的悲慘。
那四個月我就是處在這樣的情況。很多人說到愛荷華好像很浪漫、很悠閒,我後來還寫了情詩,但其實那時候的心情很痛苦。這個痛苦第一方面是我嚮往的社會主義祖國為什麼是這樣?不是很進步嗎?我寫了一首長詩,想說早知道這樣,你就讓國民黨慢慢爛嘛,再爛也不會那麼恐怖,我那個時候心情很痛苦,那個叫做「信仰的崩潰」。
另一方面,我有幾次跟王蒙、艾青他們兩個一起去大學演講,當時中國為什麼是派他們兩個,一個是愛荷華這邊邀請的,另一個是政府派的官方代表,王蒙就是政府這邊派的,講話官腔官調,我很不喜歡。一起出去演講,排序都是艾青先講,我第二,因為我是代表台灣嘛,然後王蒙第三。每次艾青講都是實實在在地敘述,我當然也是,而且我到美國絕對不講台灣的壞話,我要罵我回來跟政府罵,我不要在美國罵我們政府,那算什麼?我有一個這樣的堅持,為什麼要在外面講我們自己人的壞話?
有一次王蒙就約我去喝咖啡,我就講說我理想中的中國、理想中的社會主義祖國,怎麼會被你們搞成這樣?我可能比較激動一點。結果你知道王蒙反應怎樣嗎?他就說喔那,那你們台灣呢?你們台灣怎樣?還不是美麗島事件?我就嚇一跳,對啊,我們台灣有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這樣的政府我是很痛苦的。
所以我的信仰崩潰、幻滅,然後台灣那時也是很讓人不滿意,可是不管怎麼樣都沒有中國那麼可怕。那是在我意識上很大的一個翻轉,回來以後大概一兩年都不講話,都不寫文章,你看我的年表可以看得很清楚,我這一兩年幾乎都不寫,除了在美國寫的那一組〈愛荷華家書〉,其實是情詩啦,但因為中年人臉皮比較薄,所以用家書。除了這些之外我就不再寫了,因為我在調適,過了很久才慢慢調整回來,「唉,就是這樣,不要管你了,中國你們自己努力啦,我們台灣問題也很多啦,我就全心全意愛你,愛台灣」我能管得到的,我能盡力的,大概就是台灣社會我們還可以來盡一點力,中國那麼龐大、那麼多人才,你何必摻一腳呢?你家己台灣攏顧袂好勢啊!莫講台灣,你溪州攏顧袂好勢啊,閣講甲中國?(你自己台灣都顧不好了,不要講台灣,你溪州都顧不好了,還講中國?)我要集中精神、全心全意顧自己的故鄉,大概是這樣的心情轉折。
拒絕台北:扎根在鄉土
張:吳晟老師您說這四個月是很大的思想衝擊,最後決定反正不管怎樣就是要來建設自己身處的家鄉、社會,您後來有提出「種植年輕的台灣」。我想問問您當時想到的「建設台灣社會」這件事,很自然地扎根在鄉土,沒有再去(都市),一定很多人邀請您去台北,因為我看到您書裡也寫到說您拒絕了好多次去台北的工作,雜誌編輯等等,是什麼原因讓您覺得一定要紮根在鄉土,而不去考慮其他的可能性?
吳:不曉得欸,這個是我自己個人的思想的一些轉折,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有興趣,因為每個人的生命歷程都不一樣,每個人對自己生命的抉擇也都有各自的一個背景,我簡單地說。我跟我女朋友在學生時代就開始規劃出國,我大哥當時已經在美國完成學業,你可以說是台灣六零年代很早的一批「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我大哥大概是我們溪州鄉第一位留學生吧,我們家算是比較重視教育的。第二,我女朋友的哥哥姐姐在美國也都已經很有成就,他哥哥是真正的「台大的」,我哥哥是成大建築系,也不亞於台大啦,那個時候的成績也是台大的成績,總而言之我哥哥在美國已經很穩定,我女朋友的哥哥姊姊也都在那裡,他哥哥的工作也是很不錯的。你們知道台獨聯盟嗎?不管你認同與否,那個沒關係啦,總之就是我女朋友他哥哥就是台獨聯盟的美國本部主席,有這個背景。我哥哥這方面當然沒有那麼強烈,他是在華盛頓特區做政府單位工作的,等於是美國的公務人員。
他們都發展得不錯,我們也理所當然規劃畢業後要出國,可是我的家庭狀況實在沒有辦法,父親車禍過世後家庭負擔很重,弟弟妹妹都還在唸書,哥哥已經出國、姐姐出嫁,媽媽在種田,我實在沒有辦法那時候就出國。我女朋友當然很不甘願,她寫了一篇文章在講,我就寫了幾篇很哀怨的文章,意思就是跟她說你要出去你就出去啦,不過我還是會守在這裡等你。都是年輕時候的夢幻,都隨便亂講的啦(全場笑),坦白說也不一定真的那麼專情啦,她如果一走我大概就找別人了,也不一定啦,但也非常可能。
我女朋友很不甘願,她功課非常好、很會唸書,一直夢想要出去,我表明說我不要出去,那她就先去教書。她是我學妹,可是比我早畢業,因為我們學校對我非常好,捨不得我太早離開,所以我們老師就多留我一年,等我畢業時就剛好就有兩個工作:一個是在台北,瘂弦老師早就跟我講好說要去當《幼獅文藝》的編輯,他看中我可靠,然後我對文字很敏感,他看過我在校對就說哇你這個校對的功夫太厲害了,所以他就邀我了。
可是冥冥之中人的命運也很難預期,我要去報到的時候就很巧,在溪州搭公車要北上,排隊就剛好看到前面是我高中的國文老師。那個老師是一個很爛很爛的學校的國文老師,那個學校是那種很快就倒閉的私立學校,現在已經不在了,我讀過那樣的學校一個學期,可是我如果沒有去唸那種爛到不必考就可以去唸的學校,就不會來教書了。其實我國小一直都是全鄉第一名,可是初中就差了,命運就是這樣。我第一次讀高一那時,就寫了一本詩集去請這個國文老師教我,他就想說這個學校的學生都是不用考就可以進來的,怎麼會出你這個寫詩的?所以他當然印象很深。
我們一起上車,他問我說從哪邊畢業,我跟他說屏東農專剛畢業,其實還沒有拿到畢業證書啦,因為二月沒有證書,他就說喔屏東農專好啊,好學校,要不要回來教書?就這麼爽快。以前都聽說要送紅包,結果上車沒幾分鐘就要我回去教書,我說可以嗎?他說當然可以,我是校長,我要聘誰就聘誰,你屏東農專畢業很好啊,而且還會寫詩,你來教國文。
我就找我女朋友商量,跟她說現在有兩個工作,讓你來選擇——其實我已經想好了,但還是讓她來選——結果這個女朋友很好、「很笨」,她就說都可以啊,你決定。當時可以說是被愛情沖昏頭吧,我就說如果我回去教書會很辛苦喔,還要種田喔,她就說「農村生活很好啊,很浪漫啊,我們傍晚可以帶著小孩、踏著夕陽去散步,我們可以種菜、養雞養鴨」。我心裡想說「你想得美」,其實很辛苦,那時候我們家兩三公頃都是種水稻,水稻是很辛苦的,要一直工作,我媽媽常講說這是「趕時趕陣」(「時陣」為台灣閩南語「時候」之意),什麼工作都不能延誤的。
後來就決定回來教書,就趕快把我女朋友介紹到另一個國中,她後來來這所鄉下學校報到,在想要不要去租房子,我就說我帶你去租一間很好的房子,我就把她帶到我們家,就順理成章住下來了,也沒有什麼很浪漫的故事。農村生活就這樣開始了。

什麼是「國際觀」?
講到這裡,我們來回看一些重要的抉擇,第一個是不出國,第二個是不去台北。到了1980年我去了美國參加國際作家工作坊,當時工作坊的負責人聶華苓老師對我非常好,好到什麼程度呢?第一,他替我安排了一份在愛荷華大學研究所的工作,就是獎助金啦,還說可以留下來循著文學前輩的腳步在愛荷華拿碩士。我想了想還是覺得算了,教國中跟教大學差不多啦,而且教國中比較穩定,而且我就算拿了碩士博士,像余光中老師拿了碩士回來當教授,跟我回來還是繼續當溪州國中的老師、繼續種田,其實也差不多啦,所以我就婉拒了。
這是第三個轉折點。當時台灣一方面喊反攻大陸,但一方面台灣社會一直恐共,台灣有能力有條件的人幾乎都在想辦法辦移民,或是想辦法拿個什麼卡。我太太家裡就一直叫我太太趁還有名額趕快辦,她也真的去辦了移民申請,結果排沒幾年就通過了,通過以後一直通知叫我們趕快去辦手續,我太太就一直問我要不要,我就跟她說你要去就去啊,問小孩也是都不要,我太太看我們都不要,她後來就去辦放棄,也算是斷了這個想法。
這大概是8、90年代那時的想法。我在70年代台美斷交那時寫了一首詩〈草坪〉,那首其實寫得不是很好,但現在看來自己還是覺得很重要。那時候移民潮是達到最高峰,台灣的移民潮時不時會有高峰,到1995年閏八月又是一個高峰,我那時候寫了那首〈草坪〉,它的意思其實很簡單,就是咱家己的故鄉愛家己顧乎好(我們自己的故鄉要自己顧好)。我那時還沒有出國,但知道歐美環境好,可是台灣那時剛開始建設,到處亂七八糟的,可是我就寫了這首詩表明「咱免去佮人欣羨」(我們不用去羨慕別人),我們也可以把自己的家鄉建設成我們所愛的那樣的環境,所以這首〈草坪〉就很鮮明地代表了我當時的那種思想。
這個思想延續到現在也有大概半世紀的時間,我這樣的思想的根源是我們講很多理論,國際觀、世界什麼什麼,有篇文章我很不以為然,某文化名流在1988年發表了一篇〈何必曰台灣〉,我看了真的很不能接受。我寫了一首詩叫做〈角度〉,就在講你以為你走遍世界,到了德國你就有國際觀了嗎?國際觀不是你在外國飛來飛去,國際觀是在心裡面的。
我是比較屬地主義,我們住在哪裡,就把這個地方顧好、處理好,不要講那麼大。以前一直講中國中國,你在那邊就不被歡迎啊,人民代表大會你也不能參加,你能去那裡發言嗎?人家發生什麼事件,你能去參與、表達意見嗎?都沒辦法嘛,那何必講那麼多?真正要做的就是把自己能盡力的這個地方維護好。
文學的交往
觀眾提問:老師您好,想問您為什麼會開始寫詩?
吳:這個很好回答。因為我開始讀詩,而且讀了很多詩,讀了很多詩以後發現欸啊恁遮的詩攏無寫到我的心情(你們這裡的詩都沒有寫到我的心情),我有很多心情啊,為什麼我會寫出很多農村詩?我當年讀的詩不可能讀到這種勞動的、農村的詩,那我就自己來寫啊,我要表達我自己的生活經驗和情感,這些別的詩人是不會寫的。當然讀別人的詩會有很多的共鳴,但是你的情感或生命經驗別人是沒辦法寫的。我的勞動生活經驗坦白說台灣大部分詩人是不可能寫出來的,因為不但沒有農村生活經驗,而且還沒有勞動經驗,但像我這樣有長期農村生活經驗,而且是真正的勞動經驗,這樣我當然就只好自己寫啦。
張:您剛剛講到1980年在美國的經歷,包括好多次的誘惑也好,或是其他可能性也好,但是不管是陰差陽錯,在公車上自己的老師還是各種各樣的事情,到最後你每一次都決定是留在溪洲。但您講到從美國回來以後在思想上的掙扎和衝突,讓你有一兩年的時間都沒有辦法寫東西。我很好奇您回來之後,會怎麼跟曾經影響您的那些比如說對社會主義祖國有信仰的老朋友,例如陳映真先生等等,你會怎麼跟他們交流你的轉變?包括您對溪州土地非常真摯的情感,和對台灣社會不管外國的月亮有多圓,我們要把家鄉的月亮也變圓這樣,這些東西您還能夠跟當年的老朋友很順暢地去交流嗎?他們會有什麼反應?
吳:關於為何我從美國回來以後四十年都不出國,這我好像還沒有回答,其實跟我定根土地、定根自己家鄉有關。我已經確定我不要揚名世界,也不必揚名中國,我只要台灣的子弟能夠閱讀我的詩作,能從我的詩作獲得一些共鳴,這樣我就夠了。那種所謂國際、到中國,當然有也沒關係,譬如說我的詩集被翻譯成很多國家的語言,現在已經有法文版、英文版、韓文版、越南文版,那個我當然都很感謝,但那不是我的重點。我的重點當然是希望台灣的子弟願意,或者從我的詩作裡面能夠獲得一些感動或者是共鳴,這樣我就夠了。
我不可能成為大師,這個我很清楚,不是謙虛,絕不謙虛,我絕對不可能成為大師的,我只能成為一個很真誠的好詩人,這個是我很清楚的。因為我很清楚我有很多限制,我不必去妄想流傳千古、揚名世界,到中國那邊怎樣怎樣,很多人後來很喜歡跟中國交流,到中國開什麼會,我就不要浪費那個時間。我就是把台灣顧乎好(顧好),安呢就已經真勥啊啦(這樣就已經很厲害了啦),我若是把溪州顧乎好就就已經真勥啊啦,這樣就很好了。
人不用一定要顧到多廣闊,我媽媽常講「人無才調夯天」(人沒有能夠舉天的才幹),每個人能力有限,我們要理解這件事,不必妄想要成為什麼樣子,到中國那邊開個什麼會⋯⋯中國那邊有沒有邀請我?那當然不可能不邀請我的啦,尤其艾青對我是真的好,我看到他一本在香港出版的《艾青選集》,裡面他只有跟他太太合照的照片,除了唯一一張,那一張跟別人合照的就是我跟他跟聶華苓老師的合照,那表示說他對我真的很重視;他也很直接講說台灣的詩人吳晟就是跟他最合得來的,因為我們兩個真的都是農村詩人。他也是一直邀請我去參加一些活動,我都一概不要,因為我不想登陸;至於外國的演講什麼的,我也不想要,台灣都講不完了,還講到外國去?沒有必要。
至於跟朋友的交往,我也不曖昧,大家都很清楚我是台灣立場很堅定的,這個我也不假仙(假裝)、不閃躲,我們那邊的人也都知道我就是綠的,這個我從來都不諱言,也都不用假。但是我的文學朋友就不一樣了,大家都很互相尊重,我講一個有趣的,但是這個表示說我們能夠互相理解啦。
拿我跟瘂弦老師來說,瘂弦老師是非常國民黨的,2000年他說不能讓陳水扁當選,他說陳如果當選「會把我們趕下海」,我說「老師,不會那麼嚴重啦!」老師就說不行不行,我就一直跟他說就政黨輪替而已啦。之後過了幾年老師就跟我說欸吳晟,好像你對欸,好像也沒怎樣;到2004年就又來了,他就說這次真的不行,我就又跟他說老師不會啦,沒問題的。我們兩個就很好,但是彼此互相了解。
而我最尊敬瘂弦老師的是在《幼獅文藝》期間,他都要配合慶典慶祝蔣公什麼什麼或青年節出特刊,會找一些詩人、作家去寫「光輝十月」、「燦爛十月」那類文章。他當然也會邀我,我就很明白告訴老師說我不會寫,你不要邀我,他馬上就明白了,就說那你不要寫,從此絕不邀我寫這類文章。我所有的詩稿他還是不斷刊登,但是絕對沒有寫那些我不知、不信的東西。他不會因為我不配合他而對我有排斥,甚至很理解我這種黨外立場,我沒有什麼好隱瞞的,我都坦蕩蕩,你不認同也沒關係,我就是這樣。瘂弦老師他很清楚,他也能夠包容,這是我覺得非常了不起的。

第二個是陳映真這種大左派。我在80年以前就是這個脈絡、這個系統,如果稍微知道多一點的話,會知道這個脈絡叫做「夏潮系統」。可是我轉變了以後,曾多次跟陳映真這位我最敬愛的兄長去討論,我跟他說我真的很痛苦,中國社會主義真的很可怕,我實在沒辦法再認同,我們也討論到三更半夜一直討論。我很坦誠跟他討論以後還是沒有辦法,但陳映真還是一樣理解我,因為我是很真誠的,然後他也很真誠,我很敬愛他。
我最感佩的是那時吳音寧要出版她的第一本書《蒙面叢林》,就是她去墨西哥探訪墨西哥革命軍那本,那個真的是冒著生命危險去的,她在那裡好幾次差點丟掉性命,採訪回來寫了這一本。我後來才知道,他(陳映真)的一篇訪問裡面寫說「這是我人生最後一篇文章」,在寫吳音寧的這本書寫序之前他已經生病了,而且滿嚴重,但因為他答應吳音寧要寫這篇,所以他抱病寫了這篇。而且那不是應付的文章,是非常深刻的萬字文。你了解到這樣的作家、這樣的人有多麼真誠,多麼重情,願意抱病使勁人生最後的力氣為一個小女生寫她的第一本書的序,你就可以了解我們的情份,不是因為我的思想轉變我就對他有所改變,這是不可能的。
他不是投機者,也不是政客,他就是一個真誠的社會主義信仰者,他還是對中國抱持著期望,而我還是對台灣抱持著希望,我們各自努力,但那個情誼是絕對不會因為有些思想的變化而改變的。所以我跟很多所謂左派的老朋友還是保持著情誼,我們在一起的時候還是會有些思想的討論,但是不會真的怎麼樣。像我這次去拜訪瘂弦老師其實也會稍稍談到,但是他都會用一種很委婉的方式跟我說,也有很多地方會認同我。如果是真誠的思想,文學的情誼不會因為思想稍有什麼改變就被抹殺掉的。
張:非常感謝吳晟老師。聯合文學最近出的《文學一甲子》1跟2兩冊,其實也滿完整講述了包括剛才講跟陳映真先生的交往,我想念一下其中幾句話。
他寫到「陳映真一生堅持他的信仰,為他的信仰付出了七、八年的青壯歲月在牢獄中,沒有妥協餘地,至今也從未從台灣任何政權得到任何好處,這樣的人格,即使反對他的政治立場,也會有一定程度的尊敬吧。」其實吳晟老師在書中對很多很多的詩友都是這樣看待,我覺得文學情誼是一個獨立於政治立場之外的一條線索,其實都是秉持著這樣的立場。然後剛才他講到回訪瘂弦,應該是2019年因為紀錄片的原因,這也是《他還年輕》個人最感動的一個片段,前面都很好,農田啊種植啊——很抱歉我缺少詩意的描述——就是農村很美好。
吳:很像我女朋友那個時候那樣。
張:對,就是被你騙了,你不要告訴他農村的真相。但是紀錄片到2019年拍到吳晟老師回訪瘂弦,兩人在書桌前的交流包含最後開車離開,真的非常感人,我在電影院直接看哭了。我覺得兩位即便是在紀錄片短短幾分鐘的畫面,或者是看吳晟老師跟瘂弦老師的通信,都能看到兩人的真誠,非常赤誠、像孩子一樣、非常純真的交流狀態。
今天也非常感謝吳晟老師給我們做了這麼真誠的分享,包含可能也是滿難得聽到的角度,包含思想上重要的轉折點,整個的文學創作的歷程,個人思想史的歷程,其實背後是台灣從1960年代一直到現在的這個轉變。我自己一兩週前剛從溪州回來,一方面是想跟吳晟老師談今天對談的內容,然後另一方面是對溪州黑泥季的活動非常感興趣,因為他們的海報就是很「農村的美好」,非常漂亮的海報。
去了以後其實在那邊只待了一整天,溪州黑泥季是紀念溪州護水運動十週年,黑泥是當地很重要的地景,或應該說地質,那是一個集合了對一場以農民為主體的社會運動的紀念,音樂會、小農市集,在地的孩子、老師跟父母在黑泥塘裡玩耍,還有華德福教育等等,一個非常豐富的鄉村生態的展現。這個地點就在吳晟老師耕種了20年的土地上,這一整件事能夠發生是因為吳晟老師真的是身體力行在那裡,他的「種植年輕的台灣」不只是寫詩或教育,還是literally(字面意義上)種了很多很多年的樹,那裡有一片很大的樹林應該也是吳晟老師的母親留下來的土地上種的樹林。
我作為一個台灣的陌生人、外人,去到那邊一整天你就深刻地感覺到什麼是耕種,那裡所有的一切都是來自吳晟老師跟他們溪州吳家的耕種,不管是小農的網絡,因為護水運動而保留下來的資源,那片樹林、音樂會、所有的一切。你會看得到一個人一生或一個家族一生的執念所結下的果實是留在那裡的,我自己是非常的被觸動到,所以今天也非常感謝吳晟老師去做這樣一場很真誠的分享。
何必曰台灣?
吳:其實這首詩〈角度〉有點自我辯解的成分在,因為我不想出去,我看了當年我們所處的時代,其實70年代本土意識開始興起,慢慢就開始有所謂「國際觀」的論述,「你們一直都講台灣,可是你要放眼世界啊,多看看世界啊,不要一直只是看你們台灣」,但台灣那時最欠缺的就是本土意識,我們對台灣歷史、地理,甚至文化非常非常陌生,我在20年前已經非常清楚台灣人對台灣還有很多地方不認識,或者甚至是錯誤的認識。
我隨便講一個,你們也許很難相信。我2000年從國中退休,2001年去靜宜大學兼課教台灣文學。第一堂課我想說要教台灣文學,那同學一定要對台灣歷史有起碼的認識,我就問了一個很簡單的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台灣有沒有遭受敵人的飛機轟炸?」結果幾乎有回答的都回答日本。他們說「日本飛機來轟炸台灣」沒錯啊,因為「我國對日八年抗戰」,我們的課本就是這樣教的。「我國對日八年抗戰」這句話像符咒般,控制著現在60歲左右的台灣人,馬上就會覺得當然是日本來轟炸的,因為他是我們的「敵國」嘛,台灣人就被教育成這樣。
幾年前我跟我太太退休後第一次坐小火車去阿里山,火車上就看到一位大概40歲左右的帥哥為一群女生導覽,就聽到他說:「阿里山以前檜木非常多,都被日本人砍光了」,那些女生就覺得日本人很可惡,要去把檜木「搶回來」。我忍不住就上前問他「你這樣導覽對嗎?歷史是這樣講的嗎?」他覺得自己沒錯,還叫我去看官網,說自己是昨天才去官網把資料印出來的。我說是喔,我們的官網是這樣介紹的啊?
兩年前我在國中自己班的群組看到一個「花漾阿里山」的影片,你們可以上網看,裡面的敘述也是這樣寫的,日本人來了開始規劃、砍樹,我們政府來了開始補種。這支影片是在中央廣播電台放的,剛好董事長是我朋友,我就給他看,問他怎麼會放這個影片,他查了以後發現這是林務局嘉義市林管處拍的,他們一時不察,疏忽了所以才重播了那則影片。
這種影片還在政府單位一直播放,傳播錯誤訊息,為何會說是錯誤的?台灣的山林確實是日本時代開始規劃、開始砍樹,可是真正砍得最嚴重是在1950到1970這20年,因為反攻大陸需要經濟發展,所以就砍樹來賣,結果這段歷史被淹沒掉,我們把責任全部推給日本。這就是我們的教育,到現在還是這樣。你想想看,我們「何必曰台灣」?一定要說台灣啊,因為你真的不認識台灣,而且你認識的還是錯誤的台灣,所以還是要「曰台灣」的。
我再講一個,這也是兩年前的事。我去一個民進黨執政縣市的市公所,那裏包含館長有六個圖書館管理員,我就問他們剛才問的「是誰來轟炸我們台灣」,三個說日本,兩個說不知道,只有一個說美國,這一個是裡面最年輕的一位,大概是318學運世代的。長輩們都說「怎麼可能?美國不是我們的好朋友嗎?」你看看,這個就是台灣。
好啦,我們就念詩吧。念詩比較好玩,比較有氣質啦。
〈角度〉
遙遠的星光特別燦爛嗎
如果照不見腳下的土地
那是為誰而炫耀
遨遊的眼界特別開闊嗎
如果無視於身邊的山川
是否隱含倨傲
我也常無比傾慕
聆聽世界風潮的滔滔論述
只是有些質疑
沒有立足點
候鳥般飄忽來去的蹤跡
每一處都是異鄉
都是邊陲
其實我更常怯怯質疑自己
長年守住村莊的田土
是否如人議論的褊狹
在反覆對照思量中
或許不妨這樣說
每片田園四時變換的風姿
每株作物開展出去的角度
也可以詮釋豐富的國際意涵
如果我有什麼褊狹
反而是對於立足的土地
愛得還不夠深沉

註:本文轉載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歡迎關注端 Plus 會員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