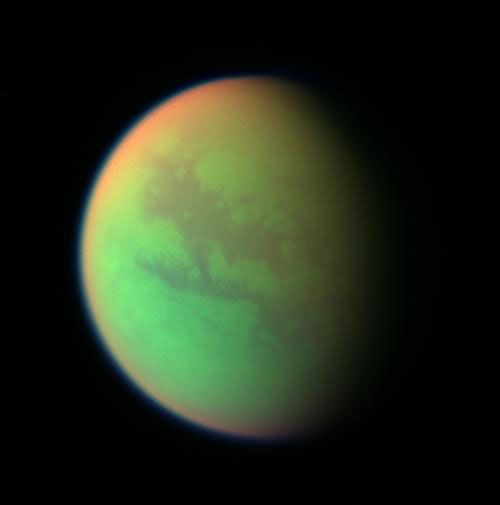回歸
「拜拜!」離開機艙之際,空服員對我招手。
「拜拜!新年快樂!」我補了一句。
「新年快樂!」她回過神來,似乎意識到了當天是2022年的最後一天。
「新年快樂!」站在旁邊的男性空服員也補充了一句。我率先踏出機艙門,一路疾走了十幾分鐘來到邊境檢查,官員把旅行證件遞給我,我跨過那條用黃色油漆標示的但又無形的線,又徑直朝行李運輸帶走去。那也許意味著這19天的獨自旅行的結束。
旅行在歷史中的角色,無論是私人的還是能載入著作的歷史,類似於一些星體。我從地球上觀察這些星體瞬間的光芒,但星體本身大概早已消亡。提取行李的我正處在星體本身消亡的那一刻,但爆炸產生的光芒才剛剛開始它的旅程。上次旅行(我認為旅行必須滿足「獨自」和「跨越國境線」兩個條件)是從中國東北陸路前往俄羅斯遠東。在這三四年間,世界的本體乃至是作為概念的「世界」都發生了深刻變化。一些人依然試圖用暴力和意識形態壟斷其他個體看待世界的視角,這些個體要麼自願要麼被迫接受了這種帶有些許歷史實證主義意味的世界觀。
我個人對「旅行」的定義基本沒有改變:旅行依然開始於念頭產生的一刻;旅行依然不存在「結束」。回歸不是結束,它甚至只是開始的一部分。然而旅行不能沒有回歸(於我而言暫時如此),沒有回歸的旅行叫做流亡。不過旅行可以被稱為短暫的自願流亡。回歸是一種力,把人拽回原來的生活或世界中,並強迫旅行者理解世界的差異:寫字樓里的生活與德里貧民窟的生活都沒有脫離生存的基礎,但旅行者固然會更注意到差異而非基礎:「我這樣的才叫生活;他們連喝的水都不乾淨,能活下來已算萬幸」。而流亡者眼中的世界是均質的——回歸的力消失,他們得以不受限制地進行移動。當然,這不意味著旅行比流亡要好,畢竟流亡者寫出的佳作不計其數;更不意味著流亡比旅行要自由。
「今天為各位服務的機組人員來自18個國家,會說17種語言。」阿聯酋航空的機長廣播如是說。他嘗試打消乘客對基於語言障礙而要求服務的惶恐,展現公司對多種文化的包容。從杜拜前往伊斯坦堡的航班,機長廣播也講了類似的內容:「機組人員來自16個國家,會說15種語言……機長名叫艾哈邁德,來自埃及。」
在出發前正好一個月,伊斯坦堡的獨立大街發生恐怖襲擊,6人遇難,81人受傷,為此我獲得了許多朋友的告誡。我惶恐了兩三天,但沒有對旅行計劃做出任何更改,儘管來到伊斯坦堡後的我,依然沒有(勇氣)走進獨立大街。我僅站在塔克西姆廣場,即獨立大街的盡頭,望向大街裡的人海——那兒迅速恢復了往日的生動,只有零星防暴警察持槍巡邏,提醒人們潛在的危險;價格比非遊客區略貴的旋轉烤肉商販不受干擾地進行交易;而我十幾分鐘前剛在附近的塔迪姆(Tadim)餐廳飽餐一頓,那碗價廉物美的辣椒牛肉湯令我終生難忘。
降落後,在步行進入尼什(Niš,塞爾維亞第三大城市)機場航廈處便是護照查驗。由於只有兩條隊伍,坐在房間里沒事幹的多餘的官員便走出來隨機檢查護照。塞爾維亞邊防會仔細翻閱外國護照,檢查裡面是否有科索沃的出入境蓋章。由於塞爾維亞將科索沃視為其領土的一部分,任何不經由塞爾維亞領土入境科索沃的行為(如從阿爾巴尼亞/北馬其頓經陸路或由其他地區乘飛機抵達科索沃)將被視為非法入境,官員會在這本護照的科索沃出入境章處蓋上「撤銷」。
從房間里走出一位官員,禮貌地向我索取護照,檢查內部的簽證與蓋章。而一翻到護照中間的美國簽證,她的神態發生了變化,開始詳細的問詢:
「您來塞爾維亞是什麼目的?」
「旅遊。」
「您會待在尼什嗎?」
「是的,待到後天。」
「您什麼時候離開塞爾維亞?」
「26日。」
「也是從這個機場走嗎?」
「不是,我之後會去貝爾格勒,從那裡的機場飛回伊斯坦堡。」
「好的,謝謝。」她遞回我的護照。在我把護照交給前方窗口內的另一位官員核查身份時,同樣的檢查科索沃蓋章的流程又重復了一遍,不過窗口裡面的官員沒有注意到美國簽證的存在。
在尼什的第二晚,朋友囑咐我千萬小心,巴爾幹可能會再度爆發戰爭。我一時感到十分費解,在網上搜索後才發現塞爾維亞和科索沃的衝突再次(因為一些常人無法理解的小事)加劇,即便我從窗外望到的人們依然在以合理的步速走路。歐洲小城晴朗祥和的氣氛似乎抵抗著那些荒謬的傳言。我是否有在尼什陷入惶恐?也許有,也許沒有。但是幾天前我站在伊斯坦堡獨立大街的盡頭,對恐襲的惶恐已經消散,或者已經無畏。因為我就站在那兒,在共和國紀念碑下,與所有人,那些早已摘掉口罩的多樣化的個體一道,用參差多態的真實重構著仍在經歷陣痛的世界。
我坐在貝爾格勒的塔馬登公園(Tašmajdan,旁邊就是聖馬可教堂)的某張長椅上,一口酸奶,一口從附近糕點店買來的芝士布雷克酥餅(Burek)。我面前踉踉蹌蹌走來一個小男孩,拿著玩具槍,向我喊「砰」。我也用拇指和食指向他比了手槍,喊「砰」。他的母親立刻跑來道歉,並把孩子抱走。我長期以來認為塑料槍是最糟糕的玩具,因為它正在阻止孩子理解現實世界倫理問題的複雜性。暴力不能解決問題,問題也並非只有好壞或正邪兩面。
在中文大學的頭兩天,我旁聽了兩節課,分別是人類學系和哲學系的課,主題都關於「倫理」。人類學教授說:「對於倫理,人類學家不去評判,不會嘗試建立一種普遍的標準。」她警告課上帶有哲學背景的學生,她隨後可能會對康德作出十分不公允的評價。哲學系的教員則說:「我們試圖建立一種普遍的倫理規範。」但他們在講課的過程中都提到了電車難題,並強調:「電車難題不過是一個對現實高度抽象化的模型,我倒希望我的生活像電車難題一樣簡單。」
我記憶的氣力都集中於這19天,以至於2022年的其他月份自己做了什麼都被不幸地被拋之腦後。也許是站在一種反對線性敘事的角度,這次旅行我選擇了「回歸」作為遊記的序幕。之前閱讀過一本人類學的書籍,作者質疑人類所謂的「發展」是否是倒退的:人最高級的階段在山洞里啃樹皮;而最原始的階段是生活於科技無處不在的社會中。這19天內,我似乎平安地與恐怖襲擊、可能爆發的戰爭以及病毒感染擦肩而過,但我仍在絞盡腦汁理解著那些猝不及防的荒謬所帶來的狐疑、死亡和淚水。世界也許正是如此,沒有那麼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