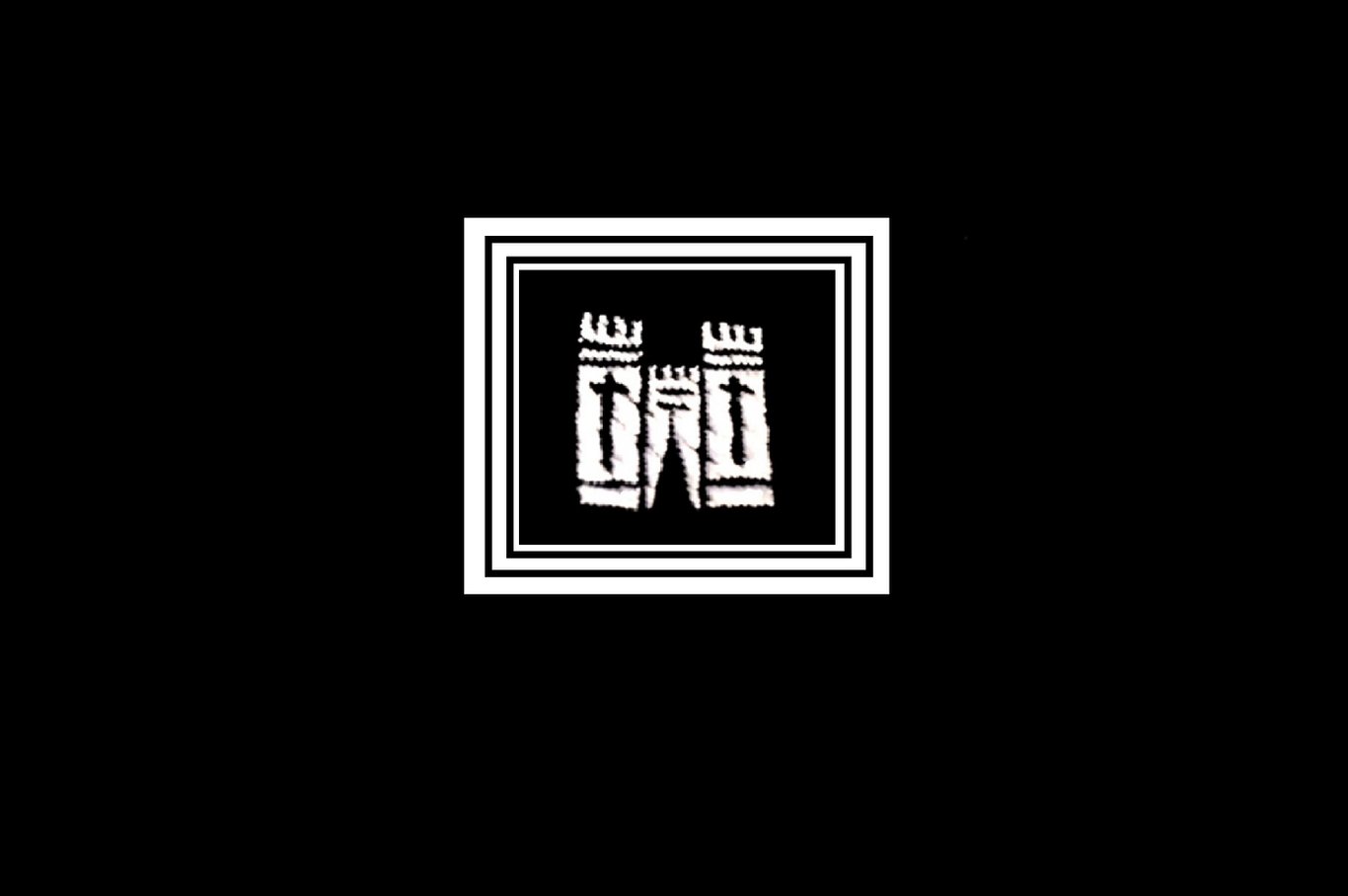中国的性别平等与对立
中国关于性别平等、女权主义、两性平权...甭管你管这个叫什么...的讨论已经陷入了一片泥沼。这篇文章提出的观点着眼于现状的一个侧面,也即一个主要的不利影响因素:广泛存在的性别的本质主义论断。
有这样一种针对性别生物性本质的广泛预设和幻想:男性是好斗的、理性的、独立的,与之相对的是温顺的、感性的、社交的女性。这种预设认为这些以及其他种种性别气质和性格是与生俱来的。
性别偏见大抵是这样构建起来的。女性就应该呆在家里而男性在世界上闯荡,男性擅长数理而女性要去读人文类的科目,柔弱的女孩需要男孩的保护,没有主见的女孩儿需要男人拿主意……
说这是一种性别的“生物本质主义”,意味着它把林林总总的性别特质当成是一种生物性本质——一种不被人的行为与思想改造或左右的自然形成的本质。
总有人非常方便地用性别的生物性一了百了的将这些偏见的缘由搪塞过去。可是,性别的客观差异真的没有生物性基础吗?
现状是:人们对性别本质的认识存在根本上的分歧和疑惑。这个分歧使得,当“性别平等”已经成为了一种几乎公认正确的话语的时候,性别在实际上的平等还是如此遥远。
争执中一端的人认为性别的差异仅存在于生理上,一切生理以外的差异都是社会文化的后天塑造。而另一端的看法则是,性别的生物性本质不仅决定了生理特点,更必然切全盘地影响了有关性别的文化规范、男女有所不同的气质和所适合的社会角色(自然本质的性别观)。
因此,即使两方的基本看法都是:不平等的性别处境是由带着偏见的社会文化建构起来的,他们会采取完全相反的主张。前一种女权要求取消既有的不对称性别规范。无论是文化上的还是法律道德上的性别规范,都不可能通过规定或者暗示“只有女人适合干这个而男人适合干那个”来限制哪个性别的自由权力。后一种女权则要求给予固有的女性特质、文化和角色以和男性文化相同的地位和价值,而不是取消这些特质、文化和角色。
从波伏娃开始,所有深刻的女权思想家都陷入了这一个麻烦的对立之中,在澄清自己的观点中耗费了大多数经历。更别提着眼于社会活动的‘女权小将’们了。其中有一些怀着天真幼稚的自然本质观,将女权解释成了几乎完全相反的东西。
着眼于中国的现状,我发现女权主义的话语很多时候都被这种本质主义的思维侵占了。
譬如说有些“女权主义者”主张婚姻中女方要彩礼要尽可能多一些贵一些,房产一定要男方出钱写女方的名字?为什么呢,因为女性在婚姻中天生处于不利地位,受到经济和身体的剥削,所以她们理应得到补偿。由于男方家族传宗接代的愿望,女人得把自己生儿育女的身体卖一个好价钱。而只有男人舍得为你花这个钱,才证明他看到了你的奉献和付出,并且本着平等的精神施以补偿。
曾经有一个广为流传的知乎帖子,讲一个新手妈妈如何以各种手段来让男人和男方的父母付出更多家务和带孩子的劳动,以及容忍她的小脾气和抱怨。理由则是因为她生了孩子的付出与辛苦需要得到平衡的回报。
这种女权的主张在家庭生活以外的方面还有很多,就不一一赘述了。我们已经可以发现,他们把自身的“生育机器”的地位当成是一种不容置疑的自然本质,顺带着在他们眼中婚姻也有了一种女性总是受欺负受剥削的本质。所以他们不去想着如何寻求经济独立和平等、寻求改变婚姻和家庭生活剥削女性的内核,而是去要求“平等”的补偿,要求将自己卖一个好价格。
私以为有人将这种女权主义总结成是“女利主义”,是毫不夸张的实话实说。有些女权主义者不顾问题的实质,认为这是对女权主义总体的抹黑和污名,于是采取了“不割席”的态度。
有些女权者认为一切对这些的抨击,凡是出自男性之口,都是来自于男性的性别既得利益者的劣根性。这些人认为男性由于性别必然会参与对女性的压迫,所以必然是处于战壕另一边的敌人。当然也不奇怪有些男性认为这种荒谬的想法恰恰反应了女性天生不善于理性思维、短视而斤斤计较的生理本性。
本质主义的性别价值观,就这样将两性平权引向了性别对立和敌视的深坑。
陷入这种歧途,不能认为原因在于中国女人和女权的水平低下。这实则是社会政治等因素导致的后果,而根本不是一个“本质性”的原因。
中国的性别运动,经历了一条和西方“第一波女权运动浪潮”相异的等位阶段。女性的权益,很早就有了社会主义官方形态,一些法条与官方女性组织的支持。这是一个利好的开始,也是一些中国的女权人所说的中国女权的“高起点”,但是带来了这样的遗患:
我们没有一种自下而上的女性团结和自我启蒙以及女性思想家建立广泛深刻的影响的基础。显然,中国的官方组织并没有这样的意愿。并且当最近底层真正拥有革新意愿、关注现实的女权组织有一些新近的发展时,竟遭到了一轮轮的封禁。
另一方面,我们缺少系统的反思传统文化的大众启蒙——五四运动当然算一个借鉴西方的深刻反思,但是1919年根本没有任何一个性别平权的思想能够给我们借鉴。这使得在对“国学”的一片追捧中,人们一遍遍被灌输着阳刚对阴柔、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价值。
似这种特别的观念只是冰山一角,我们的传统文化整个都建立在整体论的本质主义基座之上。这使得中国人在谈论性别问题时,永远有一个基于生物性和整体论的锚定坐标。在以后的文章中,我将展开来谈这一点。
所以现在中国的基本情况是:1)最基本的性别平等权益保障长期缺位——例如在家庭和婚姻生活之中的基本权益,最近反家暴的话题一次次被关注,而其推动的规制保障才刚刚起步;
2)现实的情形得不到官方或组织的关注和讨论——相比起现实的严重性,只存在着零星的讨论;
3)人们的性别文化意识普遍没有得到启蒙,缺少相匹配的理论和态度去建设真正进步的女权活动——于是人们诉诸于浅白易得的性别的生物本质论;
4)超越这一层面的,深刻而有潜在的巨大号召力的女权意见被封禁;
5)或者即使没有被封禁,它也在与严重的污名化的对抗中焦头烂额,而难以推动现实或人们意识的进步——即使这样,我还很少有听到过从内部检讨和”割席“的声音。
这样追根溯源,如果不能讨论那个解决不掉的房间里的大象,我们至少要更加关注被宣传淡化的真实的性别现实。这是我之前文章里所说的关注真实的生活的一部分。
同样重要的,便是厘清生物本质主义的性别观念如何造成了舆论场上分歧和污名化。当然它不是唯一的因素,但可以是一个启蒙尝试的合理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