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叹号时代
当今,即便是再想细心描绘“怀念”这种拨动人心的情绪时,我们也只能寻找到“泪目”“哭了”这种词汇了,而从前,我们说的是“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今年元月时,月与灯依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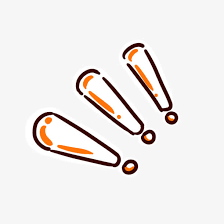
2020的冬日太过漫长,以至于素来遭受冷遇的诗句重新被赋予了温度,友邦日本寄来的援助物资上附带的诗句,成为了大众热议的话题,更是这个寒冬里珍贵的一份温暖。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友邦连连奉上的古诗词一度引爆中国网络,网友们更是戏称“日本给中国开了一个诗词大会”。
与此同时,网络上也开始出现一些反思性的文章,集中讨论中华诗歌文化失落的现状与原因。其实,在诗歌背后,更为深刻的是一种对诗性的呼唤,期待一种隐而不昭却可谓重要的人性品质回潮。
感叹号时代
意图理清诗性在当今时代的脉络,就不得不从文字状态说起,因为历来文字便是诗性的最主要体现。
1948年,美国数学家香农提出了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的信息论,其后的时光里,信息论、控制论成为了引导人类科技进步乃至人类生存逻辑的关键理论基础。
文字的状态同样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嬗变,与信息论的逻辑一致,在当今时代,作为人类交流的语言文字,越来越注重本身的信息效用,而非表达效用。简单来讲,人们在交流的过程中,阅读等接收文字信息的行为,越来越指向获得信息、消除不确定性的意图,而非文字创作者本身的表达。也可以理解为,人们把文字的实际效用提高到了首要地位,而抒情、表意等其他效用,则理所当然地被逐渐淡忘。举一个十分直观的例子,同样是表现革命热情的歌曲,《大刀进行曲》中的歌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就要比《保卫黄河》中的歌词“黄河在咆哮”,传达了更为明确清晰的意思,不可否认前者的实际效用往往更为直接且直观,但其中流失的恰就是所谓“诗性”的内容。为了更为明晰地解释上述内容,在此举一个反例,前苏联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长诗《穿男装的云》中有一句极具诗意但缺乏明确信息传递的句子:“天空红得像马赛曲,晚霞在垂死中飘摇。”
与志在于最大限度消除人类社会不确定性并传达更多信息的信息论相一致,信息时代来到了当代人的生活中。在信息时代中,人们理所当然以更准确、更快速作为生活的直接追求,乃至最高追求。于是,我们迎来了一个网上阅读新时代,文字的状态进一步产生变化。如果说信息论所带来的是“百科全书”式的科学书籍兴起风潮,那么信息时代就主动解构了“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构筑理论,以碎片化、实用化、快速化来主导生活实践。举例来讲,在我们好奇某种从未了解过的生物时,当下时代的绝大多数定会求助互联网,几秒之后即可解开心中疑问,文字在经历信息论的“表意祛魅”后,迎来了自己的“阅读祛魅”。换言之,文字不再是某种带有仪式化阅读的载体,而是取之即来的消除任何疑问的工具。
当消除不确定性与“更高更快更强”的信息时代人类信条相遇之后,两者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合力的最大作用就是塑造了当今网络当之无愧的热词:“定了”“重磅”“权威消息”“速看”“深度”“刚刚”“最新”……不胜枚举的此类字眼,非常明确地体现了消除不确定性与更快、更准确的特性,无疑,这在某种程度上让信息沟通更有效率,但另一方面,文字状态暗中变化,正带来一场情绪僭越意义的反噬。
因为更快更准确更博人眼球的需要,信息时代的网络热词又相当有限,加之网络生态下极为明显的竞争态势,网络上的文章为了得到更多的关注,又无法突破信息论与更快更准确的束缚时,便只有一个选择:诉诸情绪。但由于长久以来文字已经陷于贫瘠的状态,想要通过文字本身的表意来唤起情绪既不简单也不一定有市场,情绪的出口就只剩下一个讽刺的感叹号。
于是,我们见到了当今的网络奇观:在千篇一律的“定了”“最新”等网络热词“审丑疲劳”后,是更为令人不适的一排排连续感叹号,当然,这既不壮观,也不优雅。但无可否认,我们却一道走入了这无奈的感叹号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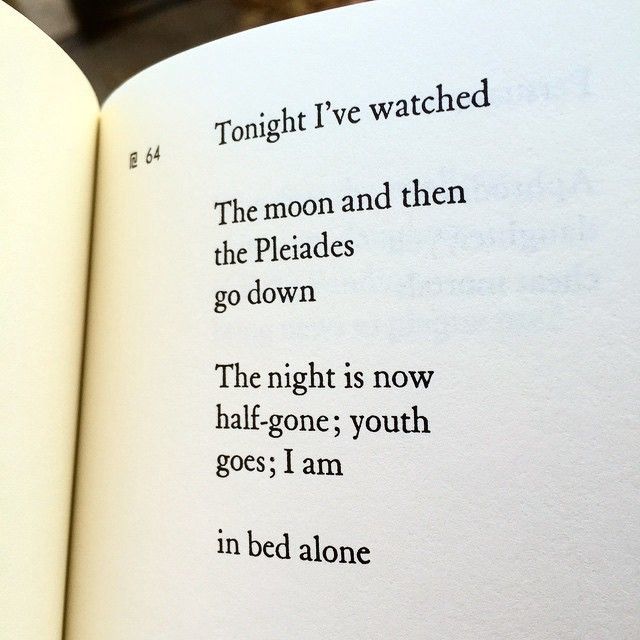
诗性
“我口袋里经常装着尺子、天平和乘法表,随时准备称一称、量一量人性的任何部分,而且可以告诉你那准确的分量和数量。这只是一个数字问题,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
狄更斯在小说《艰难时世》中写出了上面这段令人哭笑不得的文字,可惜的是,狄更斯关于人性无法测量的警醒,似乎并未被太多人记在心里。进而可言,人们似乎乐于选择进入一种缺乏诗性,精于计算的“美好时代”。
当疫情新闻连连轰炸的时候,其中最瞩目占比也最大当属疫情期间的各种数字了。无数人关注着不断变化的统计数字,各大媒体针对每天的最新数据,或撰文鼓劲,或宣传“战果”。在整个社会舆论图景中,统计数字当之无愧成为了关注的中心点。在另一面,关于个体的苦难、付出、遭遇,偶尔出现一篇关于个体的详实报道还有可能遭遇种种不测,即便引起过细小波澜,也很快被实时更新的数字盖过。
在美国大学某堂经济学课程上,有过如下对话,当教师讲赞送道,“在一个有一百万居民的城镇中,只有二十五个人饿死在街上。”一位学生打断道,“不管其余的人有一百万,或者有一亿,反正那些挨饿的人都一样艰难。”日本著名导演北野武在谈论到日本地震的遇难人数时,曾说道,“灾难并不是死了两万人或八万人这样一件事,而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两万次。”而这,就是诗性。
与更快更准确不同,诗性从来不诉诸速度与效率,甚至不诉诸他人的理解。诗性是一种关乎每个人自己的畅想,而这看似自私的逻辑,却出乎意料地生出了人世间最美的花朵:移情。当一个人展开只关乎自己的畅想时,就有了把自己代入别人生活的能力,亦是把自己当作别人的能力。当看到他人的灾难时,通过畅想,人们试图去理解这灾难可能带来的感受,更进一步,假借移情,人们用感受来要求自己与他人,帮助这个世界尽可能地减小灾难发生的概率与带来的损失。
质言之,诗性的自私与浪漫带来了一种把人当作人来看的严肃态度。信息论的蜇伤在于,只关注那些能够进入实用主义计算的东西,对世界有关“质”的丰富性视而不见,对人类是怎样生活以及如何赋予人类以生活的意义视而不见。在这样的视角下,人的多样性和独特性被抛弃了,人的质性差别被抛弃了,人仅仅被当做一个统计数字来看待,或者被当做一种粗糙的简陋物体来对待。美国著名诗人沃尔特·惠特曼曾这样描述诗性:像阳光倾注到每一个无助者的周围,它照亮了每一个曲面,每一个阴暗处;没有什么是隐蔽的,没有什么看不见。
我们还需要诗性吗
反身观察当下,在诗性愈发难寻的今天,我们还需要诗性吗?
信息时代的人们,似乎已经寻到了一种不需要诗性畅想,也不需要自身移情的生存法则。极具代表性的是今年二月的一则新闻,一对在山东汕头打工的夫妻因为种种原因无力抚养所生的婴儿,无奈之下把孩子放到了医院门口,并留下手书:“如果生存下来,一个月内一定前往福利院领回,到时多少钱一并补予福利院。”如此新闻出现后,有些出人意料的是,网络上出现了相当一部分声音认为:明知自己穷,为什么还非要生?
上述事件并非个例,有关网友似乎把贫穷视为“原罪”的讨论也由来已久,在缺失诗性的精神状态之下,人们理所当然地诉诸辩论、打击、寻找借口等手段排解自身的情绪。也正是因此,如今的网络充斥着一个非常典型的生态:调侃文化。任何事件在网络环境中,似乎都可以变成调侃的对象,在此无意去讨论调侃是否应有界限,只是必须指出,在一部分调侃中,消解了本应关注的实质性问题,让很多本可能通过努力解决的问题成为了“消逝的苦难”。这种调侃文化风行,究其原因是在诗性移情缺位时,人类情绪的自我保护机制。当心灵的某一柔软之地被无意触及时,倘若不想推翻自己思维的其他种种预设,最好的方法即是轻描淡写地调侃。所以,贫穷的问题永远在于贫穷者自己,至于可言与不可言的其他种种,只要自己没有亲自遇到,都可当作并不存在的了。
如此,诗性也就消亡了。在这感叹号时代,我们不妨稍作祭奠:
速看!!!定了!!!诗性快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