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家丨齐泽克论左翼必须拥抱法律和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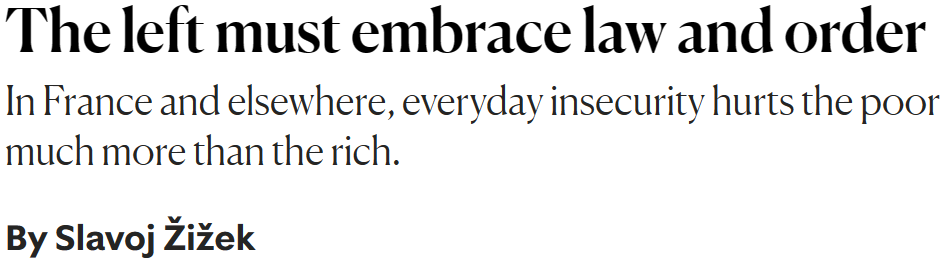
左翼必须拥抱法律和秩序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在这个愈发燥热的夏天,两件事抓到了公众的眼球: 俄罗斯的流产兵变和法国的暴力抗议。尽管媒体已详细报道了这两件事,但其中一个共同特点却被无视了。
6月27日,警察在巴黎的楠泰尔(Nanterre)郊区射杀了一位名叫纳赫勒(Nahel)的17岁男孩,之后,劫掠行为和纵火攻击在法国全境蔓延。在全国城市里,暴徒设置路障,点燃火堆,向警方投放烟花,警方则使用催泪瓦斯、高压水枪和眩晕弹还以颜色。
当警方开始充当独立代理人,威胁说,除非马克龙总统解决危机,不然他们就要造反时,事情变得甚至更不妙了。警方发布的声明无异于昭示,国家权力大厦的外表出现了一道裂缝:警方内部的强硬派响应骚乱时,威胁要对自己的国家采取行动。
可以预见,左派的叙事是:警方有种族偏见;法国的平等(égalité )是虚构的;年轻移民之所以造反,是因为他们没有未来;这场危机的解决之道不是派出更多警察镇压,而是从根本上改造法国社会。愤怒情绪已积聚多年,纳赫勒之死是最新一次引爆,将那些情绪公开化了。暴力抗议是对问题的响应,而非问题本身。
这一叙事揭示了一些真相。2005年,两名少年在被警察追捕时触电身亡,随后,抗议活动爆发:那一刻,厘定了法国青年移民生活的一整套偏见和排斥大白于天下。但,彻底改造社会,以解决身份、经济排斥和殖民造成的不公这样一些历史性难题,正是一个制造难题的方案。在看不到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时,它假定结果是进步性的。
例如,地方的巴士对运送来自巴黎边缘地带、低收入郊区的工人极其要紧,但抗议者以之作为攻击目标,这表明了两件事: 骚乱毁掉了维持普通人生计的基础设施;那些破坏活动的受害者是穷人,而非富人。
假如用解放的愿景加以维系,公众的抗议和暴动就可能发挥积极作用:例如,2013至2014年的乌克兰广场起义,以及在伊朗,因库尔德女性拒绝穿戴那种蒙住全身、只留眼睛的长袍而引发的持续抗议。有时,甚至威胁要采取暴力行动,也是政治解决的必要手段。南非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上台以及小马丁·路德·金领导的美国民权抗议,自由派评论人士推崇的这两大历史性胜利之所以能成为现实,是因为有非国大的激进一翼和更激进的美国黑人采取暴力行动的可能作为奥援。因为存在这些威胁,结束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和废除美国种族隔离的谈判取得了成功。
但那并非今天法国的情况,对这个世界的受苦受难者来讲,暴力反抗不大可能终结于任何形式的进步性和解方案。假如法律和秩序得不到迅速恢复,最终结果可能是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导人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当选新总统。反移民的民族主义者正在瑞典、挪威和意大利掌权,为什么不在法国呢?马克龙给自己准备的人设,是一个没有坚定政治立场的技术官僚。可一度被视为优势的某种立场,现在看来却是致命的弱点。
在俄罗斯,人们很难忽视叶夫根尼·普里戈任(Yevgeny Prigozhin)进军莫斯科一事的滑稽本质。在克里姆林宫向他提出条件后的36小时内,事情就结束了。普里戈任避免了被送上法庭,但被迫从乌克兰撤出他的雇佣军,并前往白俄罗斯。我们没有充分获知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的进军行动,是要占领莫斯科的全面进攻,还是如普里戈任自己暗示的那样,只是一个空洞的威胁,一个不应实现的姿态?整个事件也可能是商业谈判的残酷形式:企图阻止一部法律的通过,该法律规定,像瓦格纳集团这样的非正规部队必须接受正规武装部队指挥。
无论那是一场未遂政变,还是一场通过兵变进行的商业谈判,事情都佐证了这样一个现实: 俄罗斯正变成一个失败国家,不得不将失控的军事帮派当成一场肮脏交易中的伙伴。
法国和俄罗斯的事件是欧洲迈向动荡、危机和失序趋势的一部分。今天,失败国家不只在从索马里到巴基斯坦再到南非的全球南方。假如我们衡量一个失败国家是基于国家权力的崩溃,以及意识形态内战气氛的升温、僵持不下的群众集会和公共空间的愈发不安,那么俄罗斯、法国、英国甚至美国理当收获差不多的理解。
2022年6月19日,德克萨斯州共和党人批准的一些法案宣称乔·拜登总统“并非合法当选”,并指责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John Cornyn)参与了两党关于枪支管制的谈判。他们还在一个宣称同性恋是“一种不正常的生活方式选择”并呼吁德克萨斯州的学童“了解未出生孩子的秉性” 的平台上投了票。
第一项法案即宣布拜登的当选无效,是美国迈向“冷”内战的明确步骤: 政治秩序的非法化。在法国,谈论即将到来的内战在极右翼那里是合乎礼数的必要之举(de rigueur)。6月30日,能言善辩的极右翼政界人士埃里克·泽穆尔(Éric Zemmour)在法国电台发表意见时,将骚乱描述为“一场内战和种族战争的开端”。
在这样的一般情形下,左翼必须扛下法律和秩序的口号,视如己出。新进历史的最令人沮丧的事实之一是,2021年1月6日,狂暴的革命群众侵入权力宝座的唯一案例发生了,当日,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者冲击了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会大厦。他们认为前一年的总统选举是非法的,是由企业精英组织实施的盗窃。左翼自由派的回应混杂了迷恋和恐惧。我的一些朋友哭着说: “我们应该做这样的事情!”。见证“普通人”侵入国家主权之巅,制造一场暂时中止公共生活规则的嘉年华时,他们当中,有人羡慕,也有人谴责。
通过发动大众攻击权力宝座,民粹主义右翼由此窃取了左翼对现行体制的抵制吗?我们现在唯一的选择,要么是腐败精英控制的议会选举,要么是极右翼控制的起义?难怪民粹主义右翼思想家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宣称自己是“21世纪的列宁主义者”: “我是列宁主义者。列宁……想摧毁这个国家,这也是我的目标。我想把一切都搞垮,摧毁今天的所有建制力量。”尽管民粹主义右翼对1月6日发生的事欣喜若狂,但自由派的左翼却表现得像是优雅的旧式保守派,要求国民警卫队镇压叛乱。
在这一古怪局面的源头,我们发现了无政府状态和野蛮威权主义的独一无二的混合。我们正进入一个叛乱和暴民统治,和前所未见的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时代。这就是哲学家凯瑟琳·马拉布(Catherine Malabou)所称的“野蛮的垂直性和难以驾驭的水平性的结合,这种结合既愚蠢、丑恶又前所未有”。而且,历经多年的紧缩政策,国家的“社会职能”遭到侵蚀,它现在只能“通过使用暴力”表现自身。
所以,不能只将国家贬低为支配工具,这一点至关重要。在发生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灾难时和社会动荡时期,进步力量必须竭力夺取并利用国家权力,不只要在紧急情况下平息人们的恐惧,还要打击那些恐惧,那些人为制造出来,控制不同人群的种族主义的、仇外的、性别歧视的、反进步取向的恐惧。
左翼不应畏惧承担更多确保普通民众安全的任务: 有清楚迹象显示,年轻帮派的行为举止愈发败坏,他们威胁到从车站到购物中心的公共空间。提到这样的败坏往往被不屑地视作反动,因为人们坚持认为,我们必须审视失业和制度性种族主义等现象的“更深层次的社会根源”。
但假如左翼无视公共安全,他们就是在向敌人让出一个催生不满的重要领域,在一个无政府的时代,这样的不满会将民众推向右翼。日常生活的不安全感对穷人的伤害,远远大于那些平静地生活在封闭社区中的富人。
(作者是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本文原题“The left must embrace law and order”,见于英国《新政治家》周刊,2023年7月5日一期,7月4日上线。正文中的超链接为原文所有,黑体字在原文中是斜体。译者听桥,不保证正文理解准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