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建筑师朱文瀚:在农村田野调查三年,他的挣扎与信念 | 围炉 · CityU

//由于技术问题,该文章于2021/4/16重新发布

我选择采访文瀚是因为他作为一个90后建筑师,经历非常特殊且有趣。他在豆瓣分享过在广西几百个村落的民居调研和新疆农村的三年学术研究,并提及这三年内心所受的巨大震动。这让我觉得他与我们大部分年轻人所做的选择非常不同。
他读研期间走遍了吐鲁番托克逊县43个行政村,一百三十多个自然村,三百多条坎儿井。这些坎儿井的名字,他打开谷歌地图就能从北到南一个一个细数。为改善新疆农村地区的人居环境,他与人合作设计了简易厕所。艰难压缩成本的同时又保证了厕所卫生,改善了当地农民的生活水平。
我非常好奇一个人如何沉下心来在新疆做了三年的田野调查,在这过程中又看到了什么,思考了什么。
本篇采访展现了一个深入农村的年轻人的想法与信念,以及他对这个时代的怀疑与相信。
注:坎儿井往往出现在干旱区的绿洲-沙漠交错地带,是一种通过暗渠将戈壁地下水引至绿洲的水利设施。

李燊楠 = L
朱文瀚 = Z
对自我的探索
L | 你的同学们大多都会对城市方面的建筑感兴趣,而你却对民居很感兴趣,你觉得你跟他们之间的不同是什么?
Z | 其实这也是困扰我自己的一个问题,我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突然会对民居这么感兴趣。但如果非要找出一些什么道理而来的话,可能要回到中国建筑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即我们的建筑应该往哪去。中国的当代建筑师和建筑学者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如何在这个时代建造出既根植于中国文化又符合现代需求的建筑。
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很多同学选择了去关注城市建筑。但其实更多的中国建筑师同我一样都会到民居或者农村中去寻找答案,这并不是一个非主流的选择,而是一个蛮主流的选择。
如果只是想做设计,建筑最大的试验场在城市。但若是想要寻找某种“根基性”,农村是绕不过去的。
L | 许多年轻人获取资讯的渠道大多通过网络而不是深入实践,而你选择深入一线,做一些民居普查,并且花费了很多代价,你的动力源自于哪里?
Z | 我本科的时候,有着很强的理想主义倾向。我的母校不是什么名校,有着很严重的实用主义氛围,我在其中时常会感受到窒息。大多数学生一入学就会考虑去考公务员,考事业编,毕业后要进国企等等。
但我比较幸运,我的同学们或许不会选择跟我同样的道路, 但他们会很尊重我的选择,也会愿意和我交流。我也遇到了非常好的老师,他们给了我许多指导,也没有浇灭我的理想热情,直到现在我也与本科的一些老师进行有学术上的合作。
当时我对自己有非常高的期望,内心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许多建筑学生一开始踏入建筑生涯时都会有这种冲动,就是一种使命感,觉得自己能够成为中国建筑界的未来(笑),能够为建筑界做出一些实事。我确实是被这样的使命感驱使,去选择一个感兴趣的方向投入巨大的精力,并期望做出一些超然的理想主义成果。
L | 你在新疆调研了那么多地方,收集了那么多的基础资料,但好像学术成果只有三篇。你怎么处理这样的心理落差呢?
Z | 其实并没有什么心理落差。在新疆我获得了很大的自由。我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并且有充裕的经费支持。这得益于我的两位导师,他俩一位是我们学院的院长,另一位是熟悉当地文化和现状的维吾尔族老师,他们在当地有很好的资源和充足的经费支持我去做我想做的研究。他们都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参加高考的人,在各自的领域都有很高的造诣,对民居、农村的问题认识都非常深刻,并且有意愿去做一些实事。
因此我就有了非常好的条件和机会去做一些“费力不讨好”的事,比如做一些实地调研、考察,收集基础资料。这些资料对做后续的研究价值很大,即使它本身发不了太多论文。但这些实地走访的经历对一个年轻人整个建筑观的塑造是非常宝贵的。
辛辛苦苦跑了一年,掌握了很多一手资料,回头一看,没有出什么能够发表的成果。心里当然会很失落,但绝不会觉得没有收获。一线的观察、积累和思考是非常有用的,而成果并不急于一时。此外,新疆地处于整个学界的边缘地带,它的学术资源、平台、以及在学界所受的关注都很有限。建筑学本身这个学科发论文也比较难,而单单是对民居、村落基础资料的收集整理是不好发论文的。这几个因素叠加起来,我对自己一开始就没什么期望,不会觉得自己非要去发论文,能做出一点东西就不错了。
做一些基础资料的收集其实是功德无量的事。现在我离开了新疆,但我的学弟们还在我的基础上继续在做,将来总会有成果出来,这就是价值所在。
在新疆的经历
L | 你们设计厕所当时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能详细说说吗?
Z | 设计农村卫生厕所这个想法是我的一个学妹提出来的,她叫古丽,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建筑师,有过十几年的从业经历。其实她也是受到了一个长辈的委托,这个长辈叫克孜尔凯乐迪·阿布迪腊合曼,是和田当地的一个下沉干部。他在当地发现农村的厕所问题非常严重,卫生条件非常差,对当地居民的生活影响很大。
厕所这个问题近几年来已经不新鲜了,我国中西部的农村地区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要建卫生厕所代价很高,在很多地方厕所都是一个奢侈品,尤其在公共服务设施不那么完备的地区。一般的卫生厕所都要有给排水系统,还要考虑排污,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搞这些设施很困难。
克孜尔先生产生了一个设计想法,想看看能不能设计出低成本的厕所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他本身不是学建筑的,因此想到了自己的侄女古丽。
古丽又联系到了我,因为她知道我一直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可以提供一些建议。古丽在中间穿针引线,她自己参与设计。我则是从农村人居环境的角度给出一些设计上的建议,也参与了一些绘图工作。克孜尔先生在当地联系厂家、动员居民,并且参与了实际建造。
古丽是一个经验很丰富的建筑师,她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成本把控中起到了很很大的作用。最后在各方努力下,项目落地实施了。这是一种简易的装配式厕所,每个厕所都是一个小单元。但有独立的废物处理系统。
厕所虽然是一个很小的设计,但是它还是蛮难的,因为要解决的问题很棘手很尖锐,同时需要把成本控制得很低。
L | 所以最后落地的时候,厕所都是村民自己搭建的,是吗?
Z | 对,当时为了节约成本,我们把它设计成可以自己搭建的。因为人工成本是我们建设成本中很大的一块,把它去掉之后可以省很多钱。即便如此,预算依然捉襟见肘。主要是当地经济条件的限制,因为建厕所始终是要钱的。当地的经济条件非常落后,村民自己掏钱建这个厕所是不可能的。
很多内地的学者或者观光客常常对欠发达地区的居民表示不理解。他们会想,你为什么不去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而且这看起来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能显著提高生活水平。
其实答案很简单,一个人的生活是由很多部分组成的,人会有取舍。比如说一些父母省吃俭用,有经济实力却不去进行消费,他希望自己能够把这些钱省下来用在孩子教育等等。类似的,有了这几千块钱,当地的农民可能会想去买一些羊来发展生产,或者放到孩子教育上面。
所以当时我们面临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是要把成本控制在政府补贴内。政府有个定向补贴,是专门用来造厕所的。我们不能让预算超出这个数额,超出哪怕几百块钱,对于当地的每户居民来说都是很大的一个负担。我们要想办法把单个厕所的成本压缩到当地定价补贴的2000多块钱以内。这个费用需要覆盖零构件和材料的购置,加工费、运输费等等,刚刚好够。


L | 你有说到因为地下水位下降,有些村落会涉及到整体搬迁的问题。居民对搬迁是什么样的心态,有些什么样的想法?
Z | 我们在当地的交流的过程中,看到当地人对搬迁的一种复杂的心态。
有一些村落在搬迁的时候,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不得不搬,因为这个村水没了,不适宜人再居住了(注:吐鲁番有1237条坎儿井,但目前有水的只有200条左右,主要原因是盆地地下水位在整体下降)。


在我们介入之前,或者说在政府介入之前,吐鲁番的村落就经历过自然搬迁。吐鲁番的村落是很松散的绿洲村落,迁徙是当地人的一种本性。这跟我们这种中原地区定居的观念不同。在这种沙漠绿洲地区的聚落,甚至说往北天山以北的游牧聚落,会经常性的搬迁。吐鲁番及居民在文化层面上,对搬迁并没有很大的抵触,不像我们的汉文化里讲安土重迁。
吐鲁番的村落都是绿洲村落。沿着绿洲有一圈坎儿井,是放射状伸到沙漠里面去的,源泉在戈壁的雪山上。你可以把吐鲁番理解成一圈雪山,围绕着一大片戈壁,在戈壁中央的平坦地带是一片绿洲,坎儿井从绿洲往雪山底下发散出去,坎儿井是绿洲面对戈壁的屏障。吐鲁番的早期的村落是围绕着绿洲的,是建造在绿洲边缘的。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他们会修一些新的公路,那么这些公路点旁边会形成一些比较重要的公共服务设施点和商业点等等。当地的居民就会自发的向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迁徙,这在当地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
在绿洲收缩的情况下,当地居民并未对搬迁表现出抵触。
但还会有另外一种搬迁的情况,就是政府为了提供公共服务设施,想要让当地居民更加集中地居住。比如说从地图上看,吐鲁番越靠近火焰山的地方绿洲面积越大,而越往南靠近沙漠的地方,绿洲会呈现出一种非常离散的状态,这样的情况下政府想要提供公共服务是非常不便利的。如果想要建一个幼儿园,让这几个村的孩童都有学上,政府也会希望农民往绿洲内部搬迁,几个村搬到一起。
这个时候村落内部的居民也会有态度上的分化,年轻人希望往内地迁徙,既能够解决他孩子的教育问题,又能够让他们脱离土地,去从事一些非农业生产的工作。
但是面对村落要被废弃的时候,确实有一部分居民表现出了对过去居住地的怀念。因为这一类居住地并不缺水,甚至还会有一些优质葡萄田。因此,一些希望继续从事农业的村民对故土会有留恋。如果迁移到政府的安置点,就要重新开垦土地。而老人可能更倾向于继续从事农业,继续种葡萄,因而他们更愿意留在绿洲边缘。同时这些老年人很难再去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和新的人际关系了。
作为建筑师其实很难去帮他们决定什么,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人呈现的态度也是错综复杂的。所以在一线做研究的时候,你会发现当地人的选择和想法,都有各自不同的视角,都有各自不同的道理,那么在中间去做一个平衡,而不是去武断地判断就显得尤为重要。
L | 如果老人不愿意搬迁的话,他们会被放弃掉吗?
Z | 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但确实是这样的。在搬迁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被遗忘在绿洲边缘的村,这些村落往往是老年人自愿留下来,或者是老年人回迁。因而这些村落老龄人口比例很高,它会形成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的分化,而且这种分化不单单是在绿洲这个层面上,宏观来看是一个更大的虹吸效应,就是县城和城市对整个绿洲年轻人的一个虹吸效应。
其实以更宏观的视角看。在整个中国,东部对西部,城市对农村是与这个关系是同构的,是完全一样的效应。





新建房如何映射出人的生活
L | 关于新建房,你有什么样的评价和想法?
Z | 不管我在广西还是在新疆,都会见到很多农村新建房。这些新建房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农民回到农村自己建的,还有政府统一去帮助建设的。
很多人都批评这些新建房很丑。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新建房确实很丑。


我认为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当地居民在心理上认为它是一种暂时的居所。这其实是一种很普遍的心态,是城市化带来的。人们认为农村必然会衰败。去问大多数人,问他们觉得自己的孩子会继续生活在农村吗?我猜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回答都是:不会生活在农村。如果后代不会生活在农村,那么就没有必要再建造一个我死后依然长存的建筑。也就是说,整个农村变成了一个暂时性建筑的建造地了。不但农民会这样想,政府或者建筑师在推进农村房屋建设的时候,也不自觉会有这样的想法,认为农村的生活是暂时的,城市化是最终的归宿。
建筑师和政府这种想法可能会克制一些,但农民自身这种想法非常明显。他们会认为自己的生活在农村的生活是一种暂时的状态,自己或者后代的最终归宿是城市,这是城市化带来的农村社会心理的一个巨大转变。
那么一旦农村的生活变成了暂时的,就必然带来建设水平上的下降。对于建筑,如果你不设想它十年后二十年后跟你在一起的样子,它就变成了一个临时居所。这种想法带来的建筑风貌退化是非常显著的。
其实这种现象有反例的。
我印象最深的是今年六月份去桐庐那边考察,当时那个场景给了我很大的震撼。一些村子房子全是新盖的,不是传统民居。但它也不是崭新的,房龄二十年左右吧。你能感受到这些房子的质量是非常好的,村落的整体环境是非常好的。



这些房子当然也不能说是非常好看,经常有人在网上笑话它们土,半中不洋。但它们看起来有非常丰富的生活痕迹。也能感受到这些居民是打算在这些房子里生活到老的,甚至会觉得这些房子会传给自己的孩子。
你能感受到他们的房子有对生活思考的痕迹。比如,在这里搭一个小台子,那里挂一个鸟笼。三四户围在一起自发地建了一个小水池,水池中间有一个小堤,这么一小块地方就做了非常细致的设计。你会从这些设计中想象到这几家人是怎么共用它,而这种半自发的建造是隐含了公共讨论在里面的。
而这些房子是有生命力的,不是暂时的居所。
农村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生活在农村的人失去了在农村长久生活的信念。
这种现象在东部其实还不那么明显,但是越往西部,越往偏远地区,越往贫困地区,越往自然条件差的地区,这种现象就越来越明显了,可以明显感受到这种信念在慢慢地破碎。在这样的地方,人们不去追求生活质量,他们会认为我的房子再过十年就置换掉了,或者他觉得老了之后要跟着孩子去城里居住。因此在这样的地方,农村的建筑就必然会衰败,而且它的新建建筑质量会非常差。
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不是批评他们为何建造出这么丑的房子。而是要思考,是什么让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变成了“暂时的”。又是什么,让他们不得不去过这样“暂时的生活”。
我甚至悲观地认为建筑变丑几乎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因为现代社会的流动性非常大,不仅仅在农村,在城市也是这样。在这样的高流动性社会下,人们总觉得此刻的生活是暂时的。一旦产生了这种想法,生活就没有下限了。
L |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里讲到一个城市规划师受到的学术训练与城市居民本身不能适应他规划出来的区域的矛盾。书里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城市规划师把纽约的贫民窟重新规划出来,区域里有多少绿地,房子是什么朝向等等。但当人们搬进去这片规划区的时候,纷纷怨声载道,住在新房子里并没有让生活变得更好,因为许多人说找不到一个能喝咖啡的地方,找不到一个能跟朋友聊天的地方,甚至找不到一个能借一元硬币的地方。其实就是这个区域缺少了一个系统的公共空间,人们缺少了能与他人互动的空间,这个设计也缺乏了对人性的考虑与洞察。那么作为一个城市规划师或者建筑师应该怎么面对这样的矛盾,受到的刻板的学术训练与流动的人之间的矛盾?
Z | 这个矛盾其实是一个时代的主题。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我们上学的时候这是必读的书,它是第一批反思现代主义的著作。这本书的创作背景是整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全世界对理性主义的反思。但这些反思直到现在还主要停留在学界,而我们的社会依然是按照那套理性主义的思路在继续往前推进。
当我们接受建筑师和规划师训练的时候,其实学到的还是理性主义那一套。因为你面临很多现实问题,必须要依靠理性工具去解决。比如说规划一个城市,怎么安排交通,怎么划分区域,怎么让这个城市有效地运转起来。这套工具理性的东西是有效的,能解决问题的,我们回避不了它。而且往往越陷越深。但在接受训练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整个系统是以功利为导向的。现代主义建筑有一句非常著名的宣言叫做“Form follow function”(形式服从功能),这句话在那个时代是一句呐喊。
它其实来源于一个非常好的初衷,在二十世纪初,有一批先驱希望能通过理性去为人类设计更好的生活。他们当时提出了很多伟大的口号,刚才提到的“Form follow function”就是一个。但是这个尝试在二十世纪中叶就失败了。因为它是理想化的,而现实是很粗糙的。
人们渐渐意识到这套逻辑并不能给大部分人带来真正好的生活。近百年给我们整个人类社会带来最大的创伤可能就是一、二次世界大战。一战二战里那些残酷的战斗、屠杀、核武器等等,这些东西给我们带来沉重的伤痛,而造成这些的恰恰是所谓理性。
未来变成什么样?我给不出答案。但就我个人而言,我只能说我相信未来会变好。我的很多朋友对未来都有一种悲观态度,这种悲观情绪也在整个社会中蔓延,这其实是一种动摇,对这个架构在冰山上社会信念的动摇。
而我的选择就是去相信,我相信它会变好,所以这种信念来自于哪里呢?其实是来自于对自己的反思,对自己的认识,在不断认识自己的过程中,去发现自己的内心向好的那面。或者说在认识自己的过程中去试炼,看能不能去勇敢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阴暗面,然后在这场内心的战争中战胜自己。如果能认识自己,相信自己的话,那么就有理由去相信别人,从而相信未来。
这似乎有些跑题了,但从建筑或者城市这个层面上来讲,是一样的。此刻,我们走到了一个死胡同。我们发现那套工具理性的东西无法带来好的设计。这给建筑界带来了一场危机,很多人就不再相信自己能做出来好的设计了。或者说他们不再相信自己的设计了。的确,我们这些设计师现在很少有机会面对人去做设计了,我们面对的经常是一个混沌的、复杂的系统,是庞大的房地产市场,是代表公众的官僚机构,是一群群被抽象成代码的客群。中间与具体的人隔着很远。做出来的东西,如你所说,让人啼笑皆非。
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建筑师,相信就很重要。要相信会有一种好的设计,相信人,相信生活本身的力量,相信自己。抑制设计师旺盛的自我意识,从而去谦卑地面对生活,面对建筑,面对城市。认真对待自己的作品,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发现人。
我相信建筑在未来会有一次复兴,会有一场奥德赛。我期待它到来,并时刻准备参与其中。但你问我为什么相信,我说不出来什么道理,就是一种信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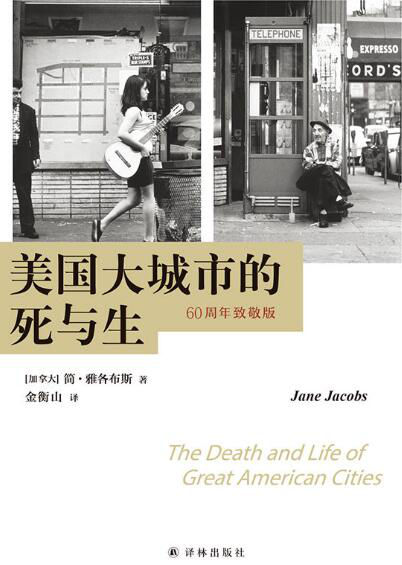
面对农村的无力与责任
L | 你说能对农村做的非常有限,你自己也非常无力,为什么会这样说?
Z | 当然会有无力感。在这个时代,意义被消解,责任被逃避。我们这一代人面对世界,都会觉得自己渺小。所有人都在告诉你,你是这个世界上平凡的那一个。
一个人能做什么呢?回答往往是做不了什么,因此也甩脱了责任。
作为一个建筑师,对农村能做的事情确实是很有限的。农村面临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很多学者认为农村的问题不在于建筑,建筑只是表象。这当然没错,甚至是一句毫无意义的废话。有的人说问题出在经济上面。但经济也远远未达本质。
经济不平衡是怎么造成的?如果你相信有一个叫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上不可能造成这么大的城乡差距。那么这么大的城乡差距怎么来的?那肯定是看得见的手把它扭曲了(笑)。当想要再往下深挖的时候,它可能演变成了一个更深的社会学问题,甚至是哲学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你作为一个普通人,当然会感到无力。但这是我们生活的时代,作为一个建筑师,对于这种宏大的问题,从专业角度看我感到无力。但作为一个人,不能逃避自己的责任。
L | 很多学者没有深入过农村,但你是深入过农村有过具体实践的,你从实践层面有什么看法?
Z | 在对农村问题的实践中,我认识到最重要的事情是:做能做的事,且要直面真实。
面对农村问题,缓解症状和发掘病根其实是同样重要的,而且有时候缓解症状是更加重要的。
关注农村的很多学者会想很本质的问题,探讨农村的症结在哪里?刚才其实我们聊了农村的症结。我们说它在现代性,这是个哲学问题(笑)。一旦从实际的问题探讨到哲学,突然就感觉会很虚无,对吧?那么其实在这个时候你去关注症状就非常的重要。在研究农村问题的时候,很多人会先从经济问题入手往下挖。挖到最后,发现不敢往下挖了,就把嘴闭上了。
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对农村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无需讳言。国内确实也有很多学者在探讨这个话题,像温铁军教授用了非常温情的描述,他说农村化解了建国以来多次危机(笑)。这句话换个角度来想,农村怎么化解这些危机的?它在付出代价,对吧?在发展的过程中被遗忘、被牺牲。城乡二元制,双轨制,工农业剪刀差,统购统销这些政策,有无数的资料可以去认识这个问题。农村的病根在哪,我们是知道的。
关键是症状,农村现在的症状是什么?普遍的衰败,全方位的收缩。几百万的自然村落,以每年十万的速度往下减少,并且有很多学者认为这个过程是没问题的。这么激烈的过程怎么会没有问题?甚至有一些观点认为应该更激进地推进城市化。这种观点我个人是不赞成的。
当你治病的时候,用猛药是很危险的。虽然有可能是对症,但它会导致另外一些症状的加深,比如农村的养老问题和儿童教育问题。这就面临到工具理性带来的平庸之恶,在追求效率的时候,老人和儿童要不要放弃?因为过去的城市化过程中这个问题就很严重,我们的城市化是有选择的,它是不平衡的。现在如果更加激进地往前推,被放弃的人会更多。
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我们有没有到那个地步,也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到那种非要去牺牲一群人的地步?我觉得还不至于。而且这种牺牲会不会带来更大的问题?一定会的。
现在对农村的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救济,远远没有到达理想的水平。我作为一个在城市里长大的人,坐在这里谈论这件事,甚至有一种负罪感。从我的调研经历来看,真的是没有达到很理想的水平。而农村的养老问题,其实被忽视得更严重,因为放弃他们似乎毫无代价,他们不会上网发帖,他们也没有能力报复社会。这些老人没有被纳入养老保险,只有一些基础的合作养老或者发一些低保。
对于农村问题,一旦你把它想象成经济数字,功利地理性地去计算,问题似乎很好解决,但在真实的世界里这些过程是非常具体且残酷的。每一个农村的劳动力进入城市,背后就是一个家庭的撕裂。如果留守老人的生活得不到救济的话,对整个社会的心理影响是很大的。背井离乡的人内心遭受折磨,被抛弃的人绝望情绪会蔓延。如果我们挑战人性,我们只会看到人性中更幽暗的一面。
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不平衡,不是自然形成的,绝不是一种自然状态。它是被造成的,所以农村理所应当被救济。我认为承认这一点是非常必要。整个社会不能去回避这个问题,东部不能去回避在吸西部的血的事实,城市不能去回避对农村的责任。让一个人去承认对别人有亏欠是非常难的,而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里,让一群人承认对另外一群人有亏欠更难。这就是农村问题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死结:事实上的伤害已经造成,但救济却是不直接的,不充分的。最重要的是,它是不真诚的。
不去面对真,整个社会就会付出代价。
我在深入农村的实践中得出来的认识,就是我们必须要直面农村。要更近地去看它,要直面问题,不能去回避它。个人也好,社会组织也好,政府也好,要对这些农村衰败带来的问题,尽可能地直接救济。并且避免一种施舍的态度。
L | 你认为农村的出路在哪里?或者说城市会向哪里去?
Z | 目前来看逆城市化是不太可能的,实际上逆城市化就是个伪命题。最多算是郊区化,那跟回到农村没关系。更激进地推进城市化,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就像我刚才说的,它回避了更复杂的问题。
我们反过来想,人是否能在城市里获得更好的生活?卢梭提出的人的自然状态,我们这里借用一下这个概念。假设人真的有一种所谓“自然状态”,现在的城市生活能否盛放人的自然状态?能不能让人真的幸福?
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城市生活图景是资本主义加消费主义,这样的一个生活图景显然不可能让人回归“自然状态”,它将人异化,把人作为工具。我们被资本的996压榨,然后又去消费中寻找慰藉。不单单是这两者把人禁锢了,城市的生活其实把人对空间的想象完全禁锢了。城市空间和人是一种互相绑架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农村人其实比城市人更自由。为什么?因为农村人至少还有权利去塑造自己的生活空间,这正是城市人所失去的:塑造自己的生活空间的自由。
不管在b站、抖音上,还是一条的视频里,装修、爆改出租房等等话题都非常火热。其实这体现出人们想要塑造自己生活空间的愿望,希望自己与身边的空间发生联系,但城市生活某种程度上终结了这种可能性。大部分人的生活空间被资本和权力塑造,自己没有能力插手其中。
作为一个建筑师,我有更切身的感受。从事建筑设计工作的时候,面对的不会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我们面对开发商的资本,面对的是官僚机构。这两者切断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人被切割到开发商的房子里,进入到被整个权力机构塑造的公共空间里。每一个设计里都在说“人”,但偏偏就看不到人。
这套系统远远还没有到末路,它还在不断地往前推,在扩张。过去,在权力和资本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城市里的人是有机会的。人们还有自由去塑造身边的空间。像一些自发的城市广场、集市,自建房构成的社区。但现在,我们能体会到自己与所在的生活空间的真实联系越来越遥远。
很多人就会问,答案在哪?出路在哪?如果城市不好的话,那我们该怎么办?似乎又回到了之前的话题,这是一个死循环,但答案真的不知道。
但这种未知正是最激动人心的地方,正是建筑师在这个时代的责任所在。
对未来呈现出一个开放的姿态,然后去探索去寻找。去相信,相信人类最终能找到一种生存方式,一种居住方式,能给我们带来真正好的生活。它就像绝对真理或者巴别塔,我们或许永远无法触及,但是此刻还不是停下的时候。
我不太会遥远地去畅想未来城市的出路在哪里,农村的出路在哪里。越想那些越会陷入到一种无力之中,或者陷入到一种虚无主义的批判。
思考目前能做些什么,其实是更重要的。我们可以解决去更真实的问题。去改善城市,去改善农村。在城市里,即便是做商业设计,也想办法让自己的设计更“真实”。去想办法突破资本和权力的桎梏。去找到他们薄弱的地方,去对抗,去实践。在农村里,可以去尽可能保存一些好的空间,尽可能地保留一些真的的生活,尽可能地改善一个、两个人、一个村的生存环境。
或许就在不远的将来,或许就在明天,就会有一次复兴和觉醒。人们会意识到自己的生活都在慢慢地被锁死,从而开始一起去寻找出路。就像一场奥德赛一样,去找回家的路。也可能是诸神的黄昏,在每个人内心展开战争,去战胜自己内心阴影。
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会被卷入到这场反思和斗争中,可能它现在就已经开始了。
所以,就我个人而言的话。出路在哪里,不知道。但是往前走,开始行动,这一点对我来说是更重要的事情。进入到农村,进入到实践,接触到更直接的真实,以一种更有力的姿态去反思去认识去思考,可能给我带来的这种帮助会更大一些。
我现在已经不太去想城市的出路在哪里,农村的出路在哪里,这些问题了。作为一个建筑师或者作为一个人,我的责任在哪里,出路就在哪里。
如何盛放人的尊严
L | 在新疆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故事,对作为人的尊严有什么新的思考?
Z | 在新疆,我一直关注的是坎儿井和自然村落。这两者是绑在一起的。
我导师的朋友,一位退休教授,是专门从事坎儿井研究的。这三年里他也会指导我。他曾反复的跟我提及吐鲁番有一个坎儿井,或许是最后一个坎儿井。那个井应该是在04年或者06年挖的。在托克逊县的旁边的戈壁滩里,那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地方。托克逊县我经常去,也是一大片绿洲,形状在地图上像是一个晴天小人。
这个坎儿井是一个老人挖的,他退休前是生产大队的拖拉机司机。他对坎儿井非常执着,一定要挖一条属于自己的坎儿井。其实坎儿井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就很少有人挖了,因为地下水位下降得很厉害,寻找水源也很难。这老汉退休后拿了一笔退休金,在他几个儿子的帮助下,通过自己的土办法就开始干了。打坎儿井很靠运气,你要先猜测大概哪个位置有地下水,再往那个方向去打竖井。至于打多少口竖井才能找到水源,这是不确定的。有可能打了一两口就有水源,也有可能打了二三十口竖井还是没有。他当时运气很好,在远离大绿洲的戈壁滩上,打了四口竖井就找到了地下水,然后通过暗渠把水引到水面上来。这个坎儿井据说浇灌了50亩地,这片地就变成了一个很小的小绿洲。这是吐鲁番最新的一个坎儿井,也可能是最后一个被开挖的坎儿井。
自从老师告诉我它在谷歌地图上的位置,我就经常在地图上去看它。这口坎儿井在地图上面很渺小,一大片戈壁中一点点小绿洲,孤零零的。它离最近的一个镇大概有二十多公里,离最近的一个村可能是十几公里。我的老师带着他的儿子去过那里调研,给老人拍过照片,也拍过他居住的地方,照片里这个地方完全符合我对世外桃源的想象。
坎儿井是由暗渠和明渠组成的,它会有一小段明渠,明渠把水引到一个小小的涝坝,就是水塘。小水塘周边再往后就是它灌溉的土地,当地人定期把水塘的堤坝掘开来浇灌。那位老人小房子就建在涝坝的旁边,涝坝周边种满了很高的芦苇。还种了一些树,建了篱笆,然后用戈壁上碎石子围了牲畜的圈,还养了鹅,营造出来一个非常小的适合自己居住的环境。2006年我老师去的时候,老人已经70多岁了.如果老人现在还健在的话,现在应该有80多岁将近90了。
我一直想去那个地方去看一看,但那个地方离城镇实在是太远了,几次去调研都错过,直到毕业都没有成行。我内心非常遗憾。因为那个地方建立起我内心对美好生活的认知。你觉得老人的生活是好的吗?在现代生活的定义上是好的吗?它有价值吗?
这种生活对我来说是一种隐喻。就像整个新疆、或是吐鲁番的历史一样。吐鲁番盆地干旱缺水,每年降水14毫米,蒸发量3000多毫米,吐鲁番人想要生存就必须要挖坎儿井。几个老人带着孩子去挖一条井,他们的孩子就建立起村庄。慢慢地,有了两三条井。这几条井周围就能慢慢长出一个小小的绿洲,每一个小村都是一个小绿洲,这些村相互连接在一起就能围成一个大绿洲。人们一直在那里生活。
也许他们最初面对的,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一片荒芜。人们常常说世界没有意义,也许真的没有意义,就是一片荒芜。但那个老人在生命的尾声去沙漠里给自己挖了一口井,这个意象在我心中留下了一颗种子。这促使去努力生活,去思考。它提醒我,不要执着地去问荒漠的出路在哪里。出路可能就是没有出路,一片荒芜。但我们可以在荒漠中去挖一口井,去认真生活。去看到别的挖井人,去跟他们走到一起,去把你的绿洲和他的连接在一起。这就是我从新疆回来之后生活的信条。城市生活何尝不是另一片沙漠?我们作为现代人在生活中感受到的无力,痛苦,剥离与异化。那我们怎么在这样的生活里去寻找自己的根基,寻找自己的锚点?
我们通过行动去挖一口属于自己的井,去相信别人,去相信这个世界上总有人也在挖井。去相信、去等待那些井会一个一个连成一片。去相信人们能把小绿洲变成大绿洲,最后迎来一场复兴。
(亦感谢王卉祺对本篇文章的贡献)

文 | 李燊楠
图 | 来自朱文瀚
审核 | 迟欣宇
微信编辑 | 吴雨洋
matters编辑 | 蔡佳月
围炉 (ID:weilu_flame)

文中图片未经同意,请勿用作其他用途
欢迎您在文章下方评论,与围炉团队和其他读者交流讨论
欲了解围炉、阅读更多文章,请关注本公众号并在公众号页面点击相应菜单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