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History of Eastern Christianity译文1-1
译者的话:
“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译者很久之前就听到过这句话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运动在中国新教群体中一直存在,但当代的传回运动经常被批评有骗钱的因素,译者不懂当代新教的情况,在这里不多点评是非。这项运动也经常被用来嘲笑新教徒的无知,因为近东本来就有基督教存在。但是,其他中国人知道的就很多吗?如果说东正教在中国还存在过成规模的教会,因着对俄罗斯的研究也能找到不少学术著作,那么东正教以外的东方基督教在汉语世界的存在感基本是零,相关的汉语资料非常稀少。恐怕大部分华人了解到东正教以外的东方基督教还是通过CK、EU等paradox出品的历史游戏。
汉语世界自己写的基督教发展史大部分是以早期基督教、西方基督教、宗教改革为线索的线性发展史,基本不考虑介绍东正教以外的东方基督教,引入翻译的欧美基督教通史,比如Justo L. Gonzalez的《基督教史》里,东方基督教的篇幅也很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从基督教世界整体来看,东正教以外的东方基督教就是信徒稀少影响力薄弱。译者每当需要了解东方基督教的时候,都痛惜资料的稀少,因此决定翻译一本专门介绍东方基督教的著作。
最早计划翻译的是《剑桥基督教史》讲东方基督教的第五册(Cambridg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Volume 5, Eastern Christianity)。但那本书还是偏重东正教,东正教的著作汉语世界已经有不少了。而且《剑桥基督教史》第五册的内容比较进阶,还是从11世纪开始的,不适合入门。剑桥系列有很出名,以后也许会有正式的汉译本,因此译者就打消了翻译这本书的内容,决定翻埃及科普特人学者Aziz Suryal Atiya的著作《东方基督教史》(A History of Eastern Christianity),这本书首版在1968年出版,再版多次,译者认为信誉应该比较好。但有一点需要注意,作者本人是埃及科普特人,作为当局者在著作里掺杂了大量个人的宗教情感和民族情绪,中立性有所欠缺,有的地方读者需要自行分辨。
本书是研究东正教以外的东方基督教的著作,一共分七章,分别介绍了科普特教会、雅各派、聂斯托利教会、亚美尼亚教会、圣多马教会、马龙派和其他消亡的东方基督教。本次翻译不是正式的学术翻译,只是科普性的简介,因此只翻译正文,前言和所有注释一概不翻译。所有注释若无特殊说明都是译者注。在术语上,因为东方基督教在汉语世界存在感薄弱,没有统一的官方翻译,因此术语以新教术语为主,音译上以英语为主。同时译者完全不懂阿拉伯语,因此文中的阿拉伯语人名地名翻译和拉丁转写很有可能不对,读者有兴趣自己想办法去查证吧。届时将在豆瓣和译者公众号“灰色的教室”同步连载,同时欢迎一切转载、引用与修改。也期待专业人士翻译出正式译本。
最后说一些题外话。开头提到“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运动,此运动起源于上世纪40年代,开封圣经学院的(汉人)牧师马可认为自己在1942年11月25日晚在凤翔的城墙上祷告时看到异像,神批评中国教会在福传上的薄弱,指示从甘陕青海向新疆福传,一直向西对伊斯兰世界福传,直到耶路撒冷。此运动开始时的重点是向整个伊斯兰世界福传而不是去近东福传,而运动的第一步就是进入新疆福传——1942年正是盛世才发动政变倒向重庆,改变新疆反教政策的时候。本运动的兴起要放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新教兴起和汉人向新疆移民的大背景中来看。至于在当代的发展,译者就不清楚了。
2023年12月17日 将临期第三主日
大连金州
第1章 亚历山大基督教——科普特人及其教会
第1节 导言
长期以来,科普特人在整个基督教历史中的地位一直被贬低,有时甚至被遗忘,因为科普特人自愿选择生活在遗忘中。在引领基督教几个世纪以后,科普特人选择将自己与西方日益增长的教会权威隔离开,以保卫他们的礼拜方式,保持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基督教分裂史上这不幸的一章发生在451年的迦克墩大公会议。迦克墩论战的细节将在后面的篇章中讨论。这里只需要指出,科普特人摒弃了罗马-拜占庭式的基督论以及大公会议决议背后所有其他的政治因素,在他们的宗教民族主义中变得尖刻而自我中心。随着阿拉伯人在7世纪的崛起,整个埃及由西方转向东方,伊斯兰教这一新宗教在中东的逐渐发展也使东方基督教相形见绌。因此,世界逐渐遗忘了他们在基督教信仰形成时期的角色。
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东方基督教的“再发现”。与聂斯托利派信徒和印度的圣多马基督徒不同,科普特人并没有完全被外部世界遗忘。像雅各派(有人认为“雅各派”这一称呼有歧视性质,但是原书作者用的就是“Jacobite”,而且“叙利亚正教”这种称呼无法概括书中的情况。本次翻译不纠结于用词以及各教派之间的矛盾,一律以作者用词为准。)和亚美尼亚人一样,中世纪到中东的欧洲旅行者们经常在著作中提到他们。但是他们不如马龙派出名,因为马龙派在十字军时代与罗马有直接接触。另一方面,科普特人被视为一小撮微不足道的一性论裂教分子,这是从很久以前开始就蒙在科普特人头上的古老阴影。事实上,直到最近(本书初版于1968年。)西方学术界才被科普特基督教的遗产所吸引,因此开始系统地研究广博丰富的科普特资料。
虽然我们只是了解了科普特历史的大致轮廓,现有的研究结果已经令人深思,揭露了很多重要事实。亚历山大基督教的意义才刚刚显露出来。随着对科普特资料认识的不断深入,逐渐形成了三派观点。第一派是新教学者,他们同情科普特教会,以深厚的感情书写科普特教会,但是理解有限。第二派是罗马天主教的学者们,他们一直对这些所谓“持不同意见”的科普特人怀有敌意,最宽厚的也是不加赞赏。第三派比较温和,由一些本土作者和西方学者组成,他们关注对原始资料进行冷静中立的研究。总体来说,在当下权威性的综合性的科普特教会史尚未出现。原始资料只出版了一部分,科普特考古学也处于起步阶段。与“埃及学”和“伊斯兰学”相比,科普特学的领域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科普特教虽然是埃及文明古代时期与伊斯兰时期之间最重要的核心阶段,但毫无疑问受了这两种文明结构的影响,因此需要做出大量努力来纠正科普特人在埃及历史与基督教编年史中的偏差形象。
根据最近的发现,学界普遍认为基督教通史的许多方面都必须重写,才能囊括科普特人不朽的,有时候甚至是动荡性的作用。教父研究的很多重要部分都需要修改甚至重写,教会关系与早期传教活动的故事也应当重新考量。科普特人在亚历山大教理学校(Catechetical School of Alexandria)与修道规则发展中的杰出贡献,尽管并非无人知晓,但也应当重新评估。我们对于科普特圣经文学的知识——包括正典与伪经以及早期基督教许多所谓的异端文献,了解依然十分有限。近年来,科普特艺术与建筑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兴趣,但这些领域的最终定论尚未出现。
我的任务就是去介绍这一切以及科普特人历史的许多其他阶段,尽管作为科普特世界的一员,我的书写会充满不可避免的激情,但是我也必须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冷静地从外部看待这些事件。
“科普特”
“科普特”(Copt)和“埃及”(Egyptian)这两个词含义相同,都是希腊语“aigyptos”(Αἴγυπτος)的衍生,希腊人用这个词指代埃及和尼罗河。这个词是古埃及语“孟菲斯”的音变,即Hak-ka-Ptah,古埃及语意为普塔神(Ptah)灵魂的居所或是庙宇,埃及神话中最受尊崇的神灵之一。他是创造万物的神,在孟菲斯比所有其他神灵更受崇敬。希腊语的前缀和后缀脱落后,我们可以看到词干“gypt”在所有欧洲现代语言中对应“Egypt”和“Copt”的词中保留下来,在阿拉伯语中也留下了许多像“Qibṭ”或者“Gybṭ”( قبط)这样的细微变体。
其他传统说法认为这个词主要是演变自阿拉伯语和闪米特词源,从“Kuftaim”(“Kuftaim”一词译者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根据上下文猜测可能是某种闪米特语对麦西儿子们的称呼。)演变而来,指的是挪亚之孙麦西的儿子,他最早在尼罗河谷定居,并将自己的名字赋予埃及古都底比斯附近的古镇“Qufṭ”或是叫“Gufṭ”。阿拉伯人称埃及为“dār al-Qibṭ”,科普特人的家园,也因为这里的原住民就是基督徒,在阿拉伯人的心目中,“科普特”和“基督徒”这两个词可以互换。然而,我们必须牢记,“科普特”的原始含义不是宗教性的,“科普特”和“埃及”两个词是严格的同义词,因此科普特教会应当仅仅被定义为埃及教会。
从种族上看,科普特人既不是闪米特人,也不是含米特人,而是地中海人。他们被描述为古埃及人的直系后裔,也有些人试图证明他们与尼罗河远古居民的相似性。无论真相如何,很明显宗教使他们没有和一波波其他信仰的入侵者混合起来。因此他们血脉的纯正并非单纯是传说。对科普特人来说,宗教是社群的黏合剂,正统宗教既是生活的方式也是礼拜的方式。直到18世纪末,科普特人都会聚居在同一村庄或是城镇里的同一街区。上世纪中东现代民主的勃兴和随之而来的争取选举权运动让这种隔离变得毫无意义了。在今天,科普特人和穆斯林比邻而居,在政治和种族上都不受到歧视;他们享受着宗教自由,教堂的数目在全埃及不断增长。总之,科普特人作为一个宗教实体幸存了下来,在其他方面则完全融入了埃及民族的政治共同体中,分享所有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无论其宗教信仰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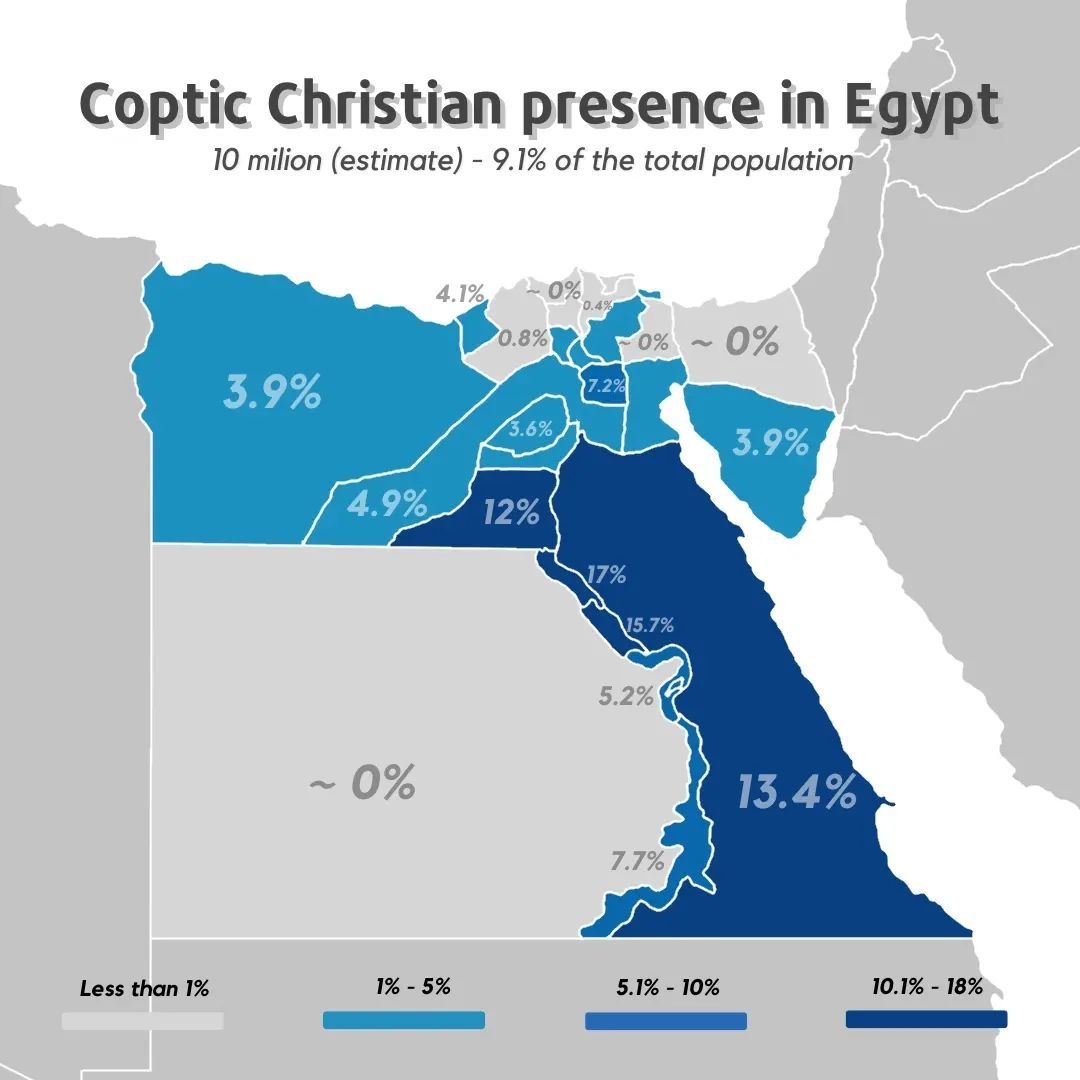
“科普特语言”
科普特人现在讲阿拉伯语,不过仍在在教会中保留了科普特语。科普特语是古埃及语言演化的最后阶段。早期的阶段代表有圣书体、僧侣体和世俗体。圣书体式用于神庙墙壁、陵墓和纸莎草上的文字,其代表是《亡灵书》。僧侣体更不正式一些,相对简化,主要被祭司们用于官方文书和皇家文件的编修,虽然在之后几乎只用于礼拜仪式。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两种形式都变得过于复杂,普通人很难用它们对照自己的语音。所以世俗体就兴起了,比前两种文字象形成分更少,但还是太复杂了,很难满足日益增长的日常生活的需求。随着希腊人的到来和基督教在埃及的传播,人们发现世俗体不足以抄录基督教经文,所以埃及学者和抄写员开启了用希腊字母表音译纯埃及文本的书写体系。他们很快意识到希腊字母表无法覆盖本土语言的所有发音,就在科普特字母表中添加了七个字母,而这些字母就来自于他们原本使用的世俗体。
因此科普特语可以定义为用添加了七个来自世俗体的字母的希腊字母表题写或音译的晚期埃及俗语。很难确定这一新书写体系出现的确切日期。在最终系统化之前,它必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渐进的发展过程。要说明这个现象,我们要注意很有趣的一点:第一份已知的用希腊字母音译的埃及语文件是在主前一个半世纪书写的。虽然我们不能据此孤例一概而论,但是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未来书写实践的一种显示。在公元2世纪后半叶基督教在埃及的稳步发展的过程中,可以推测科普特语和世俗体往往是同时使用,并不是科普特语注定要取代世俗体。伊西斯的祭司们可能是最后一批在公元452年菲莱神庙涂鸦上使用世俗体的旧秩序残党,虽然世俗体在其他地方早已不再公开使用。
很有趣的一点事,科普特语反映了古埃及语的方言。我们现在可以辨别出科普特语的下列方言:Bohairic或者说是下埃及方言、Sahidic或者说是上埃及方言、Faiyumic、Akhmimic 和Bashmuric。有时候这些方言会杂交出很多更本地的形式,比如次Akhmimic方言。现在的教会礼拜使用的是Bohairic,它可能早于其他所有方言,因为下埃及接近亚历山大港和瑙克拉提斯(Ναύκρατις)这两座希腊文化的重镇,比上埃及更容易受到希腊人的影响。
可能在2世纪末3世纪初,《圣经》的大部分篇目就已经被译为科普特语了。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圣经抄本包括了大量用科普特语在纸莎草上抄写的使徒保罗的书信片段,据估计这些抄本在公元200年前后抄写。实际上,现在已经发现了公元2世纪到5世纪大量的科普特语珍贵文献,这些文献大部分都是和圣经与宗教有关的内容,不过也有一些是其他方面的内容。
科普特语在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埃及的冲击中幸存下来,继续作为官方语言被大字不识的阿拉伯征服者雇佣的本地公务员在政府事务和簿记中使用。706年倭马亚总督阿卜杜拉·伊本·阿卜杜勒马利克(Abdallah ibn Abd al-Malik)颁布了有害而且不合时宜的命令,要求在所有政府事务中用阿拉伯语取代科普特语。虽然他的科普特语禁令在实践中并没有被执行,但这激励了本地的抄写员学习征服者的语言,结果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出现了大量双语文献。
在这些“穆罕默德诸王朝”更迭的动荡时代,科普特语作为一种口语和礼拜语言大约一直坚持到13世纪,本地学者用阿拉伯语撰写科普特语法,以及编写阿拉伯语-科普特语词典以帮助保存科普特语的危急情况在此时出现,标志着科普特语的衰落。这其中就包括Aulad al-Assal和Abu al-Barakat ibn Kabar这样在法蒂玛王朝和阿尤布王朝兴旺发达的人。(Aulad al-Assal根据译者在网上看到的资料似乎不是某个人,而是阿尤布王朝时期科普特人中一个比较有势力的家族。而Abu al-Barakat ibn Kabar是13世纪末到14世纪初著名的科普特神学家、语言学家、历史学家,一生著述丰富。他出生在开罗,早年是官员,在13世纪后期开始马穆鲁克王朝连续不断对科普特人的迫害中去职,1300年成为司祭,在1321年对科普特人的大规模迫害中逃离开罗,1324年去世。)然而这无助于科普特语的存续,科普特语逐渐被挤压到上埃及。德意志旅行者Vansleb(Johann Michael Vansleb(1635-1679),皈依天主教的新教徒,德意志神学家、语言学家,多明我会士,多次前往埃及旅行。)在1664年第一次访问埃及时,断言自己遇到了最后一个真的说科普特语的科普特人,名为Anastase。然而他的说法未必属实,因为后续的旅行者表示自己遇到过说科普特语的科普特人。
科普特语是否已完全不再使用?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除了在教会仪式中使用科普特语之外,据传在上埃及还有一些孤立的村庄保留着“关于科普特语发音的家族传统”。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说科普特语是一门仍然活着的语言也是错误的。可以肯定的是科普特语在埃及的阿拉伯口语中以两种形式留下了印记:一、埃及阿拉伯语中残留了一些来自科普特语的特有词汇;二、方言中的一些语法现象是早期双语科普特人带来的。目前,教会开办的主日学校正在积极地重新开设科普特语课程,以帮助科普特青年熟悉源于科普特语的礼仪术语和各种仪式。这些努力得到了超过预期的反响,减少了科普特事务中教众难以理解文本内容的形式主义。

古埃及宗教
从很久以前开始,埃及人在其本性和教养过程中的虔诚就广为人知。他们对古代神话中众神的深深崇敬,只有后来他们对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信仰的虔诚才能与之媲美。实际上,他们对宗教的求知欲展示了许多似乎和所有信仰都有关的事物。这点在他们从旧有的异教信仰转向基督教的过程中很清晰地体现了出来。他们对旧信仰基本思想的熟稔,让他们没经过什么困难和精神斗争就接受了新宗教的信条。我们可以举出新旧信仰之间的几点主要相似之处,这些相似性为基督教在埃及的迅速传播打开了道路。
首先,一神论的思想对于经历过第十八王朝埃赫那吞法老(前1383-前1365)一神教改革的埃及人来说并不陌生。这件事情已经非常久远了,但它构成了宗教思想的一个阶段。耶稣的神人二性和奥西里斯也是一样的,奥西里斯也同时是神和人。实际上,所有法老都是被神化的人。
新信仰中三位一体的概念似乎也只是重复了埃及的三大神(原文用的是“triad”,在宗教上指许多宗教存在三神组合的现象。)而已。几乎古埃及的所有重要城镇都有自己的三大神,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奥西里斯、伊西斯和荷鲁斯的组合。奥西里斯的复活和耶稣受难并被埋葬后的复活很相似,伊西斯和荷鲁斯也让人想起圣母与圣子的关系。实际上,早期的科普特圣母像就忠实地再现了伊西斯哺乳婴儿荷鲁斯的场景。这成为了科普特圣像学的既定特征。
圣母领报、圣灵和耶稣由童贞女玛利亚降生的奇迹故事对埃及人来说并不新奇。在埃及神话中,创造万物的普塔神(Ptah)向童贞母牛吹入圣灵,生出阿匹斯神(Apis)。其他事例也广为人知,比如最后一位埃及法老霍朗赫布(Horemheb)(不知道作者为什么用这种措辞,霍朗赫布是第十八王朝末代法老,不是最后一位埃及法老。)传说是因阿蒙神的灵魂由童贞女降生。
死后生命的问题是基督教教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埃及思想的核心,实际上埃及文明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对古埃及人来说,复活是一个生理过程,死者的灵魂(Ka)将返回作为他外壳的身体中。为了实现永恒,埃及人发明了防腐术来保存身体,防腐技艺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如果木乃伊因为未设想过的意外因素毁坏或者遗失,必须找到死者肖像的替代品, “Ka”辨认出身份后才能占据它。因此,古埃及人完善了绘画和雕塑的技艺。他们在殡葬建筑、金字塔、陵墓和神庙上也有很高的造诣,这些建筑宏伟而坚固,经得起时间的摧残。
此外,埃及人似乎早已把十字架作为生命永恒的标志,在纪念碑和记录中,只有神或是法老这样不朽的存在才能手持“安可“”(Ankh)。安可是一个顶端为圆形的十字架,基督徒很早就开始使用安可,在各种浮雕、绘画、雕塑、灯具、墙饰,油灯之类的黏土制品,甚至是多色和单色的纺织品上。对整个基督教来说,在君士坦丁大帝胜利之后十字架才真正成为新宗教的标志,但几乎可以肯定科普特人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将生命的标志安可作为他们的基督教标志了。
在图像上也很有趣,荷鲁斯和他与邪神赛特的斗争与圣乔治和龙的形象相合。这一场景在石刻、绘画和编织品上被反复描绘。
为了通过歌曲传播新信仰,三至四世纪的圣人与殉道者圣米纳斯(St. Menas of Egypt)把埃及神话和民间传说里一些流行歌谣中的旧信仰三大神改成三位一体,从而把人们熟悉的曲调用在新目的上。
埃及晚期旧神话的衰败与腐朽和迷信以及神秘主义的兴起对古埃及宗教的衰落起了重大作用。希腊人进入埃及对埃及宗教产生了奇妙的影响。为了将东方和西方在自己的霸权下结合,托勒密王朝致力于将旧宗教重塑成希腊人和埃及人都能接受的样子。这引发了一个融合的进程,是双方的一些问题复杂化了。最显著的例子是普世神灵塞拉比斯(Serapis)的创造,他是奥西里斯和阿匹斯的拟人化代表,但同时和希腊神宙斯和普路托有某种程度上的联系。在希腊化的埃及人和东方化的希腊人之间,本地人的精神四处游荡,想知道哪里能找到真正的信仰。
与这些宗教动荡结合的是接下来罗马统治下埃及期间的绝望与极度贫困,此时的埃及只是罗马粮仓里的一个工具。生活是漫无目的枯燥无聊的,只剩下来世的慰藉和精神安慰,而基督教对此做了充分保证。舞台已经搭建完毕,基督教将如野火般烧遍整个尼罗河谷。

圣家逃往埃及
科普特人今日依然怀念圣家从巴勒斯坦的迫害者手中逃入埃及安全的避难所的故事。实际上他们对此感到非常自豪,科普特作家几乎在每个可能的场合都要纪念这件事。在科普特历Pashons月24日(Pashons月(Ⲡⲁϣⲟⲛⲥ),科普特历9月,大致在儒略历4月26日至5月25日,传统上古埃及收获季的开始。)诵读的我主荣入埃及地瞻礼的科普特三一颂上,信众用下面的话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埃及和她的子女以及她的众边疆,你们当欢欣喜悦!因为那在万世之先的人类的爱人已经到来。”
主降临尼罗河畔引起了埃及基督徒的想象,这在科普特文学中显而易见。这段情节在早期的福音书伪经与科普特圣徒传(原文用的是“Synaxarium”,科普特语称作“ⲥⲩⲛⲁⲝⲁⲣⲓⲟⲛ”。这个词意思比较复杂,译者认为在西方基督教中不太容易找到完全对应的词,结合语境觉得这里应该是指圣徒传记。)中都有出现。在初期教会形成的年代里,这一现象的历史意义可能在于吸引了更多的人皈依新信仰。
追寻圣家从伯利恒逃往上埃及最远处的传奇旅行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可能圣母就把婴孩耶稣抱在怀里,一路上骑着驴,约瑟在旁边步行。对现今熟悉中东国家的人来说,这一景象并不陌生。这队旅行者一定是顺着北部沙漠旅行的路线穿越西奈半岛,沿着地中海沿岸从加沙到拉法(Rafah),涉水渡过水量很小的界河“埃及河”(原文是“River of Egypt”,应该是埃及与加沙边境地区的一条小溪,因为作者没给阿拉伯语名字,所以译者没查到是哪条小溪。也许现在已经干涸了。)来到Rhinocolura,也就是现在的阿里什(Arish),那是罗马人流放罪犯并割掉他们鼻子的地方。他们从那里去了Ostrakini(现在叫“Ras Straki”或“Gazirat El-Felusiyat”,在西奈半岛北部。),那里后来成为一位名叫亚伯拉罕的主教的教座,他参加过431年的以弗所大公会议。圣家在西奈半岛的最后一站是贝鲁西亚(Pelusium),也就是现在的法拉玛(al-Farama)(这一地名来自于科普特语Pheromi(维基百科上科普特语名是“Ⲡⲉⲣⲉⲙⲟⲩⲛ/Ⲡⲉⲣⲉⲙⲟⲩⲏ”,和作者的音译不完全对应,但译者不懂科普特语。)),埃及的东方锁钥。6世纪的波斯人和随后7世纪的阿拉伯人都是走这条路线入侵埃及。
虽然逃亡埃及的过程淹没在各种奇迹与传说中,但我们可以推测难民正是顺着这条波斯人和阿拉伯人都走过的路线逃入埃及内陆。他们前进路上的传统站点可能证实了这一推测。历史上朝圣者与旅行者对这一主题的兴趣为列举这些站点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穿过曼宰莱湖(Manzaleh)下方的苏伊士地峡,旅行者一定经过了布巴斯提斯(Bubastis),第二十二王朝的首都,希罗多德在公元前5世纪访问过的地方。去布巴斯提斯的路线位于东部省(Sharqiya)的南部。这里被认为是圣家在树下躲避的第一站,那棵树据说一直幸存到1850年。第二站Matariya村(现在是一座城镇。)更加知名,中世纪的朝圣者和现代旅客都经常光顾这个地方,圣家在那里的一棵悬铃木下休息,附近第十八王朝的一座方尖碑现在仍然矗立在原地。根据传统,这棵悬铃木被虔诚的人们世代相传,可能是通过不断移栽一直存续到今天。现在这棵可以追溯到1672年,在岁月的重压下1906年树木倒塌,但它那可敬的枝干上仍然在冒出新绿。
科普特人在开罗Haret Zwayla的蒙福童贞堂(不是开罗悬空教堂。开罗有很多献给玛丽亚的教堂,这座在现在的英文材料里一般叫Church of the Virgin Mary (Haret Zuweila),1400年至1520年间为亚历山大科普特教宗座堂。)和女修道院纪念第三站。但是再往南的路线上最吸引人的地标是巴比伦区(可能是埃及的一个地名,译者没有查到。)的一处洞穴,或者可能是一座小型地下庙宇,圣家在这里暂住了一段时间。在这第四站的地上,科普特人在4世纪建起了Abu Sarga(St. Sergius)教堂,而地下的建筑被小心地作为一个礼拜堂保存起来,里面有一座祭坛和一处壁龛,婴孩耶稣可能就在那里休息过。
之后圣家的停留地包括了开罗老城南面尼罗河畔的一座犹太庙宇,科普特人在那里的马底(Maadi)建起了另一座圣母堂(St Virgin Mary Church(Maadi))。现在带着三座粮仓式圆顶的建筑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纪。旅人在这里渡过尼罗河,深入上埃及,远到艾斯尤特省(Asiut)的Meir和Qusiya。在那里他们又在一个洞里藏了六个月,虔诚的本地人后来在那里修建了圣母修道院,以Dair al-Muharraq之名闻名,直到今天源源不断的朝圣者献出的财富让那座修道院比全埃及所有其他帕科缪(St Pachomius,团体修道创始人,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修道院。)修道院更富有。早期的穆斯林作家,穆罕默德·巴基尔(Muhammad al-Baqir)(大部分什叶派承认的第五任伊玛目。)记述了圣家经过中埃及的Dair al-Ganus与al-Bahnasa,通过复述这些奇迹来美化自己的故事,是阿拉伯人征服埃及期间很流行的做法。
在圣家逃往埃及的故事中,我们很难区分真实和传说,正统信仰和伪经。但是科普特人对本地传统的敏感就在这圣统的祝福下存活下来了。埃及一直充满着关于虔诚和奇迹的奇妙传说,但没有任何传说能与虔诚而单纯的信众对圣家脚步的敬礼相提并论。
圣家在埃及寄居的时间是未知的,也无法准确定义。当然屠杀无辜婴孩的凶手希律在耶稣出生的同年就死了,圣家一定发觉没有在海外继续逃难的需要。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必须意识到当时旅行条件的糟糕,以及他们行程的漫长,这次逃难一定持续了很长时间。此外,《圣多马婴孩福音》(Infancy Gospel of Thomas)(早期基督教的一部福音作品,讲述了耶稣童年时期行的各种奇迹。主流基督教均不承认此部福音书,包括科普特教。)记载了耶稣三岁时复活死鱼的奇迹,因此不难想象耶稣可能是在那个年龄以后回到巴勒斯坦的拿撒勒的。圣家逃难的故事引起了后来基督教传教者的想象,有助于在埃及传播新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