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丨革命性时代的全球自由主义危机


译按本文作者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1964年生于印度,1993年在哈佛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美国记者、专栏作家、政治评论员,现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政论节目主持人。本文节选自W. W. Norton & Company 2024年3月推出的作者新著Age of Revolutions: Progress and Backlash from 1600 to the Present。原题“How to beat the backlash that threatens the liberal revolution”,见于《华盛顿邮报》网站,2024年3月22日发布。所有插图及摄影作品均来自原文。译者听桥,对原文有多分段,对机器提供的初步译文有校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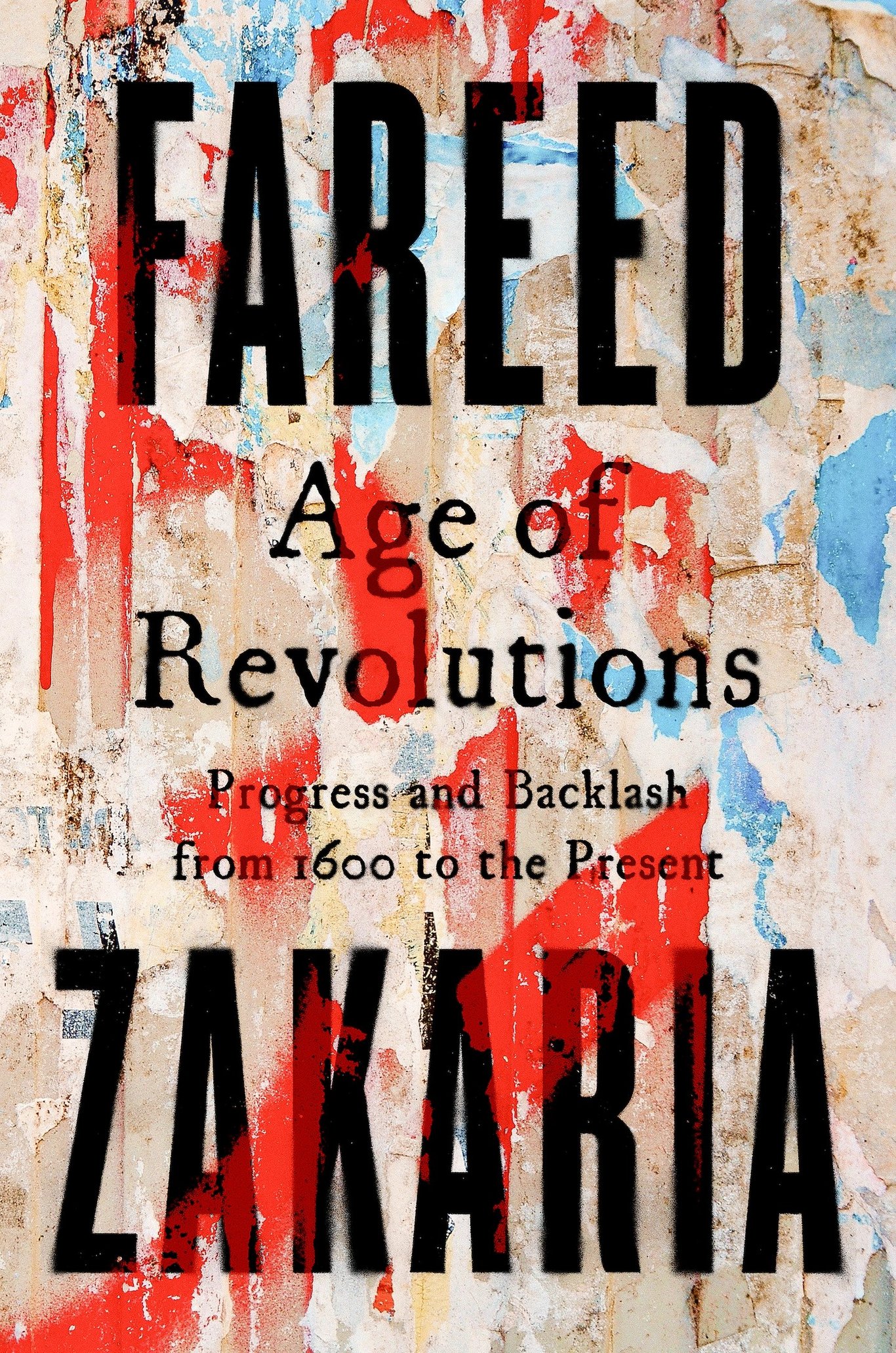
书摘:革命性时代的全球自由主义危机
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我们生活在一个忤逆三十年来不同领域革命的时代。
自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来,世界见证了市场的自由化、政治的民主化和信息技术的爆炸式发展。那些趋势中的每一个,似乎都强化了另一个,形成了一个总体上更加开放、活跃和相互关联的世界。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这些力量显得自然而然,能够自我维系。
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这个开放的时代,扩散到了全球的是美国的或至少是西方的理念,有美国实力的加持。过去十年,随着这种实力开始受到挑战,那些趋势开始逆转。如今,世界各地的政治充满了焦虑,这是对多年来加速运转的国际政治经济的一种文化反动。
在地缘政治领域,美国实力遭遇的反对显而易见。三十年无可置疑的美国霸权之后,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的回归将我们带回了一个大国竞争的时代。这些国家和一些地区强国,如伊朗,都试图破坏和侵蚀在最近几十年里指引世界的那个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
但这不只是对美国硬实力的响应,也是对西方自由主义理念广泛传播的响应。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伊朗最高领导人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在一个关键方面结成了盟友: 他们认为西方价值观与他们的社会格格不入,会削弱他们的统治。远为令人担忧的是: 对这同样一些价值观,西方世界自身内部,也形成了消极的应对。
西方的民主国家都面对愈发高涨的非自由民粹主义浪潮,这股浪潮怀疑开放、全球化、贸易、移民和多样性。结果是,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正经历民主的衰退,关税和贸易壁垒的不断上升,对人口迁徙和移民日甚一日的敌意,对技术和信息获取不断扩大的限制,甚至对自由民主本身的怀疑。
自由主义理念彻底改变了各社会,及它们相互作用的方式。看看周围。自1945年“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诞生以来,世界经历了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所称的“长期和平”,这是现代史上最长一段没有大国冲突的时期。自那以来,绝大多数国家在海外的行动通常都基于一套共同的规则、标准和价值观。目前有数以千计的国际协议,规范着为研讨、辩论和联合行动而创建论坛的各国和许多国际组织的行为。(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生于1941年,任教于耶鲁大学,美国军事史和冷战史学者。——译注)
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出现了爆炸式增长。1913年,贸易约占世界经济产出的30%,那个时代通常被认为是和平与合作的最高点。今天,这一比例约为60%。自1945年以来,以武力吞并领土这种一度司空见惯的事突然极为罕见,是故,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显得异乎寻常。
随着对美国实力和理念的强烈忤逆态势高歌猛进,问题就是,在大国和平、全球贸易和一定程度的国际合作仍然存在的情况下,现有国际秩序会否得到维持,抑或,我们会否回到现实政治的丛林。
自远古以来,对抗和现实政治的世界就与我们如影随形。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世界是相对较新的。像许多自由主义理念一样,它源于欧洲的启蒙运动。格劳秀斯和康德等思想家开始为远离战争、走向“永久和平”的国家利益之类概念辩护。十九世纪,英国的自由主义者接受了其中的一些主张,英国有时开始在国外采取行动,以维护其价值观,而不只是利益。例如,它不只废除了奴隶贸易,还利用其海军封锁外国奴隶船只。但只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灰烬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美国才有能力构想一个真正崭新的国际体系,并使之成为现实。
联合国、布雷顿森林、自由贸易、合作,这一体系诞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但在很大程度上遭到苏联拒斥,因此在西方的泡沫中成长起来。直到1991年,苏联共产主义垮台,自由主义秩序迅猛扩张,将从东欧到拉丁美洲再到亚洲的几十个国家纳入麾下。老布什总统称之为“世界新秩序”。但它实际上是现有西方秩序的扩张,涵盖了世界绝大部分地区。
眼下这个秩序何以陷入危境?地缘政治方面的强烈忤逆无可避免?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的回归,这两股主要力量是实力中的结构性转变的产物?或者,理当受到谴责的,是个人的决定,尤其是西方那些个人的决定?

单极时代是如何结束的
许多现实主义者认为,冷战后北约成员国数量的持续增加刺激了俄罗斯的修正主义侵略行径。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有关北约扩张的辩论中,我在这一议题上持谨慎态度: 我赞成北约接纳主要东欧国家,即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随后暂停扩张,考虑俄罗斯的利益和敏感性。2008年,我和现在一样,认为小布什总统在当年的布加勒斯特峰会上的决定,即开启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但不向其正式提出邀约,是最糟糕的结果:激怒了俄罗斯,但也没有给乌克兰提供一条安全通道。
但即令没有北约的扩张,俄罗斯也可能入侵乌克兰。(一些人认为,它可能更早就动手了。)乌克兰长期以来在俄罗斯人的意识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沙皇帝国皇冠上的明珠。俄罗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国家“基辅罗斯”(Kievan Rus),其首都是基辅,而且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由莫斯科统治了三百多年。
普京称苏联解体为“本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这一说法众所周知,当时他接着解释了原因。那是因为数百万“俄罗斯人”不再属于俄罗斯母亲(Mother Russia):这一看法将乌克兰人当作俄罗斯人(尽管是二等人) ,将乌克兰当作俄罗斯的附属地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开始发动两场血腥战争,以阻止车臣脱离联邦,经历了一段疲软时期后,普京为自己设定了恢复俄罗斯实力,尤其是在“近邻”地区恢复的目标。这使他走上了颠覆乌克兰独立的道路。

苏联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巨型的多民族帝国,快速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就会明白,当这样的帝国崩溃时,通常会发生什么: 帝国主义大国为保住它从前的领土,会实施血腥手段。法国人发动了一场野蛮战争,以保卫阿尔及利亚,他们认为那是法国的核心部分。他们试图保住他们在越南的殖民地,如同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那样。在茅茅叛乱期间,英国人在肯尼亚杀害了超过一万人。普京对乌克兰的闪电突袭可以作差不多的理解:一场帝国复辟战争。
但许多现实主义分析人士仍没有将矛头指向俄罗斯。相反,他们批评美国的俄罗斯政策太过强硬和自信,北约的扩张则被视为对莫斯科“后院”的不适当蚕食。
在中国问题上,人们的共识恰恰相反,认为华盛顿太过软弱和顺从。美国欢迎中国加入国际体系,并打开贸易和投资的闸门,但没有顾及中国的剥削性经济做法和威权主义倾向。这样做是因为,美国相信中国会变得温和柔顺,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民主国家。希望与中国全面对抗的新冷战斗士声称,这一长达数十年的“接触”政策是幼稚和失败的。毕竟,中国没有变成一个自由民主国家。
实际上,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从来不是纯粹的接触政策,其核心目标也不是把中国变成丹麦。这项政策一直是接触和威慑的结合,有时被描述为“对冲”。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官员的结论就是,将中国带入全球经济政治体系,好过让其待在这个体系外面愤愤不平、制造混乱。但华盛顿将这些整合中国的努力与对其它亚洲大国的一贯支持结合了起来,作为一种平衡机制。它在日本和韩国维持军队,深化与印度的关系,扩大与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的军事合作,并向台湾出售武器。
很大程度上,这一平衡术奏效了。在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向北京示好之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流氓国家,为从拉丁美洲到东南亚的全球各地叛乱活动和游击运动提供资金和政治支持。毛泽东所痴迷的一种念想是,他身处一场即将摧毁西方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的最前线。对这项事业来说,没有什么措施是太极端的,甚至包括核浩劫在内。
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的一次的发言中解释说:“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 (本段引文取自谢加书《毛泽东是否说过“死3亿人没关系”》一文,较原文所引略多几句。——译注)
相较而言,自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是一个非常克制的国家,自八十年代以来,既没有参战,也没有资助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武装叛乱分子。

但习近平启动了一套更自信果断的外交政策。他推翻了相当多策动了中国成功的共识,抛弃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指令和胡锦涛“和平崛起”的承诺。中国与印度军队在喜马拉雅山脉发生冲突,施压韩国拆除了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实施威胁台湾的海军演习,这些动作毫不遮掩,几无和平可言。在中国等待了足够长的时间,并做好展示自己实力的准备后,也许这一天的到来不可避免。中国认为自己理当拥有世界大国待遇,而它就是这样的大国。
我们无法确定,假如华盛顿对中国和俄罗斯采取截然不同的政策,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另一种演变是诱人的。俄罗斯会否像战后的德国那样,已实现了民主化并融入自由秩序?假如华盛顿对北京采取强硬态度,中国会否已成了八十年代的日本那样,在经济上有威胁性,但在地缘政治方面是和善的?
事实上,出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德国和日本的和平崛起是一种反常现象。中国和俄罗斯最终肯定会展示它们的实力。讽刺的是,一些宗奉现实政治的高层人士通常会辩称,大国之间的冲突是相互竞争的国家雄心不可避免的结果,但仍指责美国的行动:在一件事上太过强硬,在另一件事上又太过软弱。
可以说,全球均势上的变化在鼓动俄罗斯和中国采取行动方面更为关键,尽管这两个国家的国内领导层都曾做出重大决定。从九十年代的羸弱中恢复生机和活力的俄罗斯,很可能试图再度斩获一些荣耀。对中国来讲,在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它绝不会逆来顺受地接受一个适中的地位。毕竟,习近平的《中国制造2025》发布于2015年,那是特朗普总统的关税和拜登总统的技术禁令出台之前。《中国制造2025》为中国设定的目标是,主导关键经济领域并在这些领域大体实现自给自足。单极时刻无法永远持续下去,历史注定要重演。

全球自由主义危机缘何而来
但大国竞争的回归是一个更恢弘故事的一部分。当新国家斩获实力和影响力时,出现争夺硬实力的紧张态势是可以预料的。但还必须这样理解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的回归:一种文化上的平衡之举,不只是回应美国在过去三十年里的地缘政治主导地位,还是回应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扩散。
历经多年的全球化和一体化,习近平和普京担心,他们的国家正脱离他们的掌控,变得更受全球价值观而非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他们开始重申国家利益和文化,而非世界主义的利益和文化。类似冲动也刺激了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和其他民粹主义者。他们攻击国内的自由主义理念和机构,如重要政党、法院和媒体,因为他们担心一个开放的世界正在腐蚀旧有的生活方式。
这些趋势中最危险的趋势,并非俄罗斯和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行动更加咄咄逼人。西方强大到足以牵制那些力量。更令人关切的是,这种文化上的忤逆似乎已经感染到西方,事实上已感染到美国自身,这威胁到我们现代的自由化世界的根基。西方民粹主义的兴起直击西方政治和经济最伟大成就的核心: 在法治之内,建立自由社会和自由市场。

这场全球自由主义危机并非凭空出现,而是迅速变革的社会和利用了对所有这些变化心生恐惧的领导人的结果。事实上,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全球化和数字革命已以无数积极的方式改变了世界。这些力量民主化了技术,释放出了创新,提高了人们的预期寿命,传播了财富,连接了地球的边远角落。
但根据定义,那些相当深入、相当迅速地现代化了社会的力量,也具有强大的破坏性。进步往往颠覆了传统的生活方式,使许多人感到无所适从。物质进步可以提高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但也可能损害个别社区和民众。被边缘化的群体可能有获得解放之感,但多数民众中的一些人可能感到不安。随着私营企业通过跨越国界获得效率和规模,人们愈发感到无能为力。
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在指引南非从种族隔离走向民主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曾写道: “成为人就是要获得自由。”我们都想要自由。我们想要选择、自主,想要对我们生活的掌控。但我们也知道,当人类拥抱自由时,他们最终会感到极度不安。自由和自主往往以牺牲权威和传统为代价。随着宗教和习俗的约束力逐渐消失,个人获益,但共同体往往失败。结果是,我们可能更富有、更自由,但也更孤独。我们在寻找将填补那种失落感的某种东西、某个地方,寻找那种法国哲学家布莱兹·帕斯卡(Blaise Pascal)称为“无限深渊”的空。
征诸历史,是政府定义了什么才是有意义的生活,这种生活指导人们服务于上帝、祖国或共产主义事业。结果通常是灾难性的。相比之下,自由主义国家不会告诉它的公民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美好的,而是把美好的生活留给个人。它建立了一套程序,如选举、言论自由、法院,以帮助确保自由、公平竞争和机会平等。现代社会保护你的生命和自由,这样你就可以作为个体追求幸福和满足;而只要不影响其他人做同样事情的能力,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定义什么是有意义的生活。
但是构造一个人自己的生命意义并非易事; 求教于《圣经》或《古兰经》则简单得多。许多人认为,自由主义的理性计划是对上帝可怕信仰的可怜替代品。上帝曾经鼓舞人们建造大教堂,谱写交响曲。
在其著名文章《历史的终结? 》的著作版本中,弗朗西斯·福山描述自由民主的胜利时,在自己的标志性说法后加了几个单词,于是书名就成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福山的担忧是,尽管战胜共产主义会让西方社会富裕而安宁,但也会让每个人都变得被动。在战胜共产主义之后,福山所召唤的图景由没有伟大的意识形态事业需要捍卫的人组成,他们会整日追求自己的物质需求和欲望,感到空虚、孤独和沮丧。
填补空缺的是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它们为人们提供了德裔美国学者艾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所称的“从自由那里的逃离”。弗洛姆是一位研究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杰出心理学家,他认为,一旦人类生活在自由的混乱中,他们就会感到恐惧。他写道: “受到惊吓的个体试图找到某个人或某种东西,以束缚自己; 他再也不能忍受成为自己的个体自我了,他疯狂地试图摆脱它,试图通过消除这种负担即自我,以重新获得安全感。”
在解释自己的非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时,欧尔班认为,自由主义过于关注个人及其自我。他去年告诉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有些事情比‘我’更重要,比我的自尊更重要:家庭、国家、上帝。”欧尔班的政策(据称)旨在将那些东西放在一个基座上,用弗洛姆的话说,要消除自我的负担。借鉴同样的剧本,普京恳求俄罗斯人不要追随西方那种个人自我表达的诱人但虚伪的话语,而是要帮助俄罗斯再次变得伟大。习近平以差不多的口吻谈到了中国伟大的民族复兴计划,该计划褒扬中国文化与西方的个人主义不同。(塔克·卡尔森,前福克斯新闻网节目主持人、保守派政治评论员。——译注)

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在物质方面,西方仍然强大。支持乌克兰的联盟包括美国、加拿大、欧洲、东亚民主国家、澳大利亚、新加坡和其他国家,人们或许可以称之为“西方+”(West Plus) ,它们占全球经济产出的差不多60% 。因为有乌克兰危机和俄罗斯的威胁,欧洲已经变得更加团结,“西方+”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结成了同盟。维持同盟将是一个挑战,但这不是比冷战更大的挑战,当时许多国家试图在美国和苏联之间找到第三条道路。但假如成功,“西方+”可以夯实和壮大和平与自由地带。
创设欧盟的外交官深谙历史,决心确保欧洲不再爆发战争。今天,欧洲领导人开始将一种类似的历史责任感注入日常决策之中。自成立以来,欧盟就有远大梦想,但从未成功克服分裂,成为一个意见一致的整体。假如欧洲最终成为世界舞台上的战略参与者,那种情况就可能改变,这将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最重要地缘政治后果。
就美国而言,它也必须以一种更具历史头脑的方式行事,并铭记上个世纪的主要教训: 一个最强大的国家退回到孤立状态和保护主义的国际体系将是一个凸显侵略和反自由主义特征的体系,而一个有超级大国参与的体系可以捍卫和平和自由主义。接触可以采取多种形式。美国可以与一个更加统一的欧洲,加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共同努力,印度、土耳其和其他一些国家或许偶尔也可以加入。国际秩序将由一个围绕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团结起来的大国联盟加以强化,而非由一个霸权国家去维系。

当下西方面对的最重大危险
除了有在国际上维护自由主义秩序的挑战,另有在各社会内部捍卫自由主义项目的额外挑战,两者是相互关联的。想想印度。印度的经济腾飞伴随本土民粹的民族主义高涨,这一版本的民族主义被称为“印度教至上主义”(Hindutva) ,是印度教至上地位的一种形式。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印度浓缩了美国将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更重大全球性问题: 它将如何看待那些自身的民族主义政治带有反自由色彩的潜在盟友?
世界各地的民粹主义强人经常声称,开放社会的价值观即多元、宽容和世俗主义是西方舶来品。他们说,他们正在建设一种有别于西方自由主义的正宗民族主义政治文化。有可能,这些社会中的世界主义和自由主义理念遭到侵蚀,将揭示出,那些理念有赖于一个受过西方教育或受到西方启发的精英阶层,在他们的背后,埋伏着一种不那么宽容的民族主义。
印度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曾就读于英国顶尖学府哈罗公学(Harrow)和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他曾对美国大使说: “我是最后一个统治印度的英国人。”尼赫鲁和他独立后领导人同侪缔造的国家,建立在他们从与英国和西方的深层联系中汲取的价值观基础之上。他们的印度是一个世俗、多元、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国家。印度抛弃大部分社会主义传统时,我是第一个庆祝的人,因为那些传统造成了闻所未闻的失能和腐败。但社会主义并非一些国家眼下正事后诸葛亮般批评的唯一一种舶来的西方思想。在印度、土耳其和巴西等国,各种各样的启蒙思想,如新闻自由、独立法院、宗教宽容,一直在失去光彩。
俄罗斯和中国在其他国家煽动反西方的不满,这是事实,但他们是在利用一种已经存在的忤逆。在许多地方,启蒙运动项目(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其重要组成)被视为西方主导地位的遗产。

但迄今为止,我们面临的最重大危险是,在西方自身的心脏,有一些人拒绝了启蒙运动项目。美国、英国和法国的许多选民选择了民粹主义者,这些人自称完全反对既有秩序及其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民粹主义者论及上帝、国家和传统的至高无上的重要性。这些主张收获了强烈的共鸣。
自由主义的麻烦在于,它太成功了。它早就是并仍然是全世界政治现代化的主要力量。看看几个世纪以前的生活: 君主制、贵族制、教会等级制度、审查制度、官方的法律歧视和国营垄断。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这些传统和做法都已崩溃和瓦解,因为自由主义理念提倡个人自由和权利,赋权于普通人,反对暴政和国家控制,具备强大的魅力。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理念——尊重私有财产,利用开放的市场,贸易和自由交换——已根植于几乎全球各地,尽管通常有所调整,以确保更大程度的经济公平。但自由主义并非完美的体系,其缺点和过分为敌人提供了充足的攻击素材。
我们生活在一个革命性的时代。面对已发生的所有变故和转型,人们不知所措,对未来更感到焦虑和恐惧,因为那个未来可能意味着更多动荡、混乱,和那个他们所成长的世界的失去。一些西方人已经做好了迎接激进主义的准备。一些外界人士认为,这是打破西方及其思想长期统治地位的时刻。
但假如我们在国内推翻自由主义,假如我们任由它在国外遭到侵蚀,我们就会发现,自由主义和民主业已缔造的思想和实践大厦也将崩溃。我们将回到一个比我们世世代代所熟知的世界更贫穷、更紧张、更充满冲突的世界。
